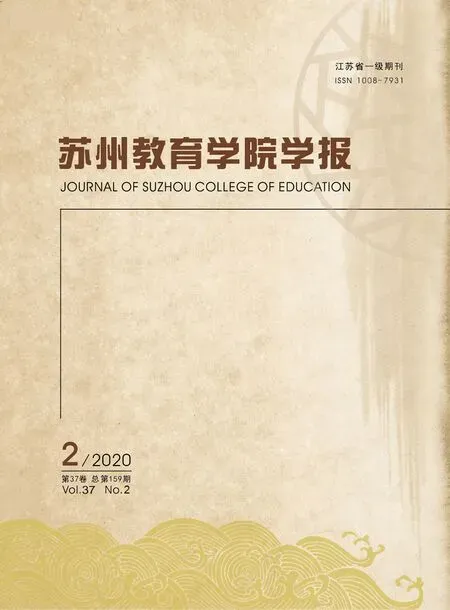朝鲜士人崔溥的仁、礼思想
——以《漂海录》为中心
马 季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崔溥,字渊渊,号锦南,朝鲜全罗道罗州(祖籍耽津)人。生于明景泰五年(1454),24岁中进士第三。明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初三,正于济州担任推刷敬差官的崔溥,突闻父丧,立刻乘船返里奔丧,渡海时不幸遭遇风暴,九死一生后漂至我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却又被当地人误认为是倭寇押解至杭州,经明朝官员审理,确认其一行43人为朝鲜人。随后,崔氏一行在沿途明朝官员的护送下抵达北京,还受到了明孝宗的接见与赏赐。最后,他们从北京途经辽东返回朝鲜。崔溥回国后,以日记形式撰写了三卷共六万四千余言的行程记录,即《漂海录》,详细记载了他们海上遇难、辗转回国的经历。
明朝自永乐帝迁都北京后,朝鲜使臣便改道由陆路经辽东进京朝圣,此后朝鲜使臣极少能到中国东南部地区,如朝鲜圣节使臣蔡寿所言:“我国人物亲见大江以南者,近古所无。”[1]152崔溥《漂海录》是目前留存下来的唯一一部明朝时期朝鲜人漂流至中国东南地区的见闻日记,记录了明朝中期东南沿海和京杭大运河区域的社会生活,以及文化、经济、政治和军事海防等方面的情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引起多国学者的关注①贡献较大的是葛振家教授,他出版了《朝鲜汉文古籍〈漂海录〉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出版),还撰有《〈崔溥漂海录〉学术价值再探》(《当代韩国》1994年第3期)、《〈崔溥漂海录〉价值再探析》(《韩国学论文集》1997年第1期)等专题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切和重视。有关注《漂海录》中关于大运河和沿岸风情的描述,例如范金民的《朝鲜人崔溥〈漂海录〉所见中国大运河风情》(《光明日报》2009年2月24日);有对《漂海录》语言学上的价值进行分析,如汪如东的《朝鲜人崔溥〈漂海录〉的语言学价值》(《东疆学刊》2002年第1期)。金贤德的《崔溥漂海登陆点与行经路线及〈漂海录〉》(《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考证了崔溥的登陆地点为浙江台州三门县。还有从政治视角来解读《漂海录》,如韩国曹永禄的《崔溥之漂海录所描写之十五世纪下半期中国——朝鲜士人官僚之批判性观察》(《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5年)。朴元熇的《崔溥漂海录分析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出版)则对《漂海录》作了较为细致、全面的研究,涉及到《漂海录》书志学、历史学研究。此外,还有曹春茹的《韩国崔溥〈漂海录〉中的负面中国形象》(《当代韩国》2007年第4期);崔溥的后代崔基泓将《漂海录》译为韩文;原首尔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高柄翊《成宗时期崔溥之漂流及其漂海录》一文对崔溥一行的漂流作了简单介绍,等等。。然综合他们的成果,较少从崔氏的言、行层面来研究崔溥对儒家礼节的维护与践行。本文以《漂海录》为中心,分析儒家仁、礼思想对崔溥的影响与塑造,以及崔溥对儒家仁、礼思想的坚守与践行,进而窥见儒家思想对朝鲜士人的影响,以期深化相关研究。
一、崔溥仁、礼思想的养成
公元前284年前后,儒学传入朝鲜地区,到公元4世纪,百济设置了五经博士制度,朝鲜正式有了儒学机构,新罗(前57—935)统一朝鲜后,于682年设立国学,以儒家经典《论语》和《孝经》为教科书,强调“孝悌忠信”,使儒家思想成为朝鲜一千多年之久的教育中心思想。[2]475新罗灭亡后,继之而起的高丽王朝(918—1392),于建国之初即定国策:“唯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3]在科举取士、儒学教育等文教制度方面均仿唐宋之制,推动了儒学在朝鲜的进一步传播。
第一,朝鲜统治者推崇儒学,形成社会慕儒风气。明朝时期(1368—1644)儒学处于理学阶段,此时朝鲜处于李氏王朝时期(1392—1910),极为崇尚儒家思想,大力引进和推广儒学,“至第九代成宗时,文物制度皆已确立,儒教思想皆已普及于庶民阶层,奠定了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基础”[4]。发展到15世纪,朱子学成为朝鲜官方的主流思想。朝鲜李氏王朝统治者有意宣扬程朱理学,将程朱理学作为维护国家统治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将官方儒学教育与科举取士结合,吸引了无数朝鲜士子,穷心钻研儒家经典,朝鲜全国上下“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为风”[5]。此外,在律法方面,刘灵枝认为:“《高丽律》以儒家的‘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制度为原则,维护皇权、父权,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6]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国甚至“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输入儒家文化的国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比儒学的诞生地中国更加遵从儒家文化的国家”[7]。在这样的一个崇尚儒学的国度里,崔溥的儒士品质也得以养成。
第二,朝鲜成熟的教育体系之培养。崔溥儒家士人品质的养成,离不开朝鲜在国内建立的成熟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之塑造。朝鲜统治者为保证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儒学教育体制。如崔氏言:“国都有成均馆,又有宗学、中学、东学、西学、南学;州府郡县皆有乡校,又有乡学堂;又家家皆有局堂。”[8]81朝鲜国内建有一套完备的教育体系,中央的成均馆是最高学府,又有宗学作为专门教育王室宗亲子弟的学校。同时,在国都按地域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南学等“四学”,“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国家主要教育机关。又在地方上按照州、府、郡县设有乡学,作为地方教育机关。朴贤淳《朝鲜王朝时代的成均馆和科举》一文论述道:“朝鲜王朝在开国之后便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种学校……此外国家还在汉城府设立了五部学堂,在各地方郡县里设立了乡校。”[9]
朝鲜教育体系中的教学内容也是以传统的儒家经典与思想为主,如崔氏所言:“我国人生子,先教以《小学》、《家礼》,科举亦取精通者,及其治丧、居家一皆遵之。”[1]123“儒士皆治四书五经,不学他计。”[8]81所立官私学校的教育科目也以“四书五经”为主,并推及日常生活中,治丧、安家皆以儒家礼仪为范。此外,崔溥有关本国科考文章体例的自述:“表仿宋元播芳,记论仿唐宋,义拈出五经文,疑拈出四书文为题,并遵华格,对策仿文选对策。”①崔溥:《锦南集》卷二(戊申二月初七日),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影印本。可知,朝鲜书文体例,表笺以《宋播芳》《元播芳》为体例,记、论以唐宋散文为标准,经义、对策以《文选》为教材推行传统的儒学教育。
第三,朝鲜完备的科举选官制度的激励。崔溥在路过杭州时,按察提调学校副使郑大人询问:“你国科目之制如何?”崔曰:“有进士试、生员试、文科、武科试,又有文武科重试。”[2]57又问曰:“其试士如何?”崔氏答曰:
(进士试)每于寅、申、己、亥年秋,聚儒生精业者,试以三场:初场,疑、义、论中二篇;中场,赋、表、记中二篇;终场,对策一道,取若干人。翌年春,又聚入格者,试以三场:初场,背讲四书五经,取通四书三经者;中场,赋、表、记中二篇;终场,对策一道,取三十三人。又聚三十三人,试以对策一道,分次第,谓之登文科第,许放榜,赐红牌给花盖,游街三日后,又赐恩荣宴、荣亲宴、荣坟宴,许通出仕之路。[8]57
朝鲜王国时期建立的科举体系之完备,科举所受国家重视程度之高,给予中举士人赐宴席、许出仕之路,这被视为朝鲜学人的最高荣誉,这种选官制度激励着朝鲜士人对儒学的学习与钻研。朴贤淳《朝鲜时代的科举应试法》论述道:“朝鲜的教育与科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准备科举的教材同时也是朝鲜时代知识分子获取基础知识的教材。”[10]在朝鲜的教育与科举体系下,朝鲜士子的知识体系基本在儒学领域之中。
第四,儒士家庭的熏陶。《锦南集·序》有载:“锦南先生崔公讳溥。字渊渊。罗州人。进士讳泽之子也。生有异质。刚毅精敏。即长。治经属文。卓冠时辈。年二十四。中进士第三。二十九。成化壬寅春。成庙谒圣取人。公以对正统策。登第第三。自为上舍居泮宫。才名大振。与申公从濩等为友。及筮仕立朝。累官为典籍。参修东国通鉴。著论一百数十首。明白的确。大为时论所推许。丙午。中重试亚元。”①崔溥:《〈锦南集〉序》,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影印本。崔溥之父为进士,想来崔溥的儒士品质也受到了家庭熏陶。而且,崔溥自小接受儒学经文教育,24岁时即中进士第三,居功名之身,才名冠于一时,参与典籍修纂,可谓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当为朝鲜真儒士。
总之,朝鲜王国崇儒的社会风尚、完备的儒学教育体制,以及成熟的科举取士体系,推动了朝鲜人士对儒学的学习。社会风尚的导向、成熟的教育制度背景与家庭环境熏陶,视为崔溥儒学仁、礼思想养成之主因。
二、儒士崔溥对仁、礼思想的践行
崔溥所受的儒家教育思想深深地影响到他的生活,他是仁、礼思想忠实的践行者。
(一)尽忠行孝
突遇险境,身居异国,崔溥始终坚守对朝鲜国王的忠诚,处处践行着儒学礼仪规范。自小受儒学教育的崔氏,对于儒家的忠、孝礼节观有着清晰、深刻的认识,始终能对儒家奉行的忠、孝礼节思想谨奉不渝,屡遭绝境而不改其志。
首先,崔溥认为身人臣者,首要尽忠。据《漂海录》记载,一次中国官员问崔氏:“你国王姓讳何?”臣曰:“孝子不忍举父母之名,故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况为臣子?其可以国君之讳轻与人说乎?”曰:“越界无妨。”臣曰:“我不是朝鲜之臣乎?为人臣者,岂可以越界而负其国、异其行、变其言乎?”[11]34本应熟谙避讳原则的中国官员贸然问起朝鲜国君的名讳,遭到崔溥的断然拒绝后,仍以“越界无妨”为由追问不休。为此,崔溥以儒家为子孝、为臣忠的观念,回避了中国官员的无礼要求,坚决维护朝鲜国王的尊严。
其次,崔溥在接受明朝皇帝赏赐之时,竟将全部的荣耀皆归之于朝鲜国王的君恩,曰:“帝之抚我赏我,都是我王畏天事大之德,非汝等所自致。汝其勿忘我王之德,勿轻帝赐,勿坏勿失勿卖以为他人之有,使汝子孙世守,永为宝藏也。”[1]134另外,在漂流生还之时曰:“是皇恩覆冒,使万物各得其所,故我等亦幸得保此生也。”[1]129甚至将自己的生还之运都归结于朝鲜国王的保佑,可见崔溥对朝鲜君王的赤诚之心,充分体现了崔溥的忠君思想。
再次,在漂流海上、身处异国的情况下,崔溥始终坚守儒家居丧守孝之礼。如崔溥一行人至海门卫桃渚所公馆时,一人问:“尔奔丧,可行朱文公《家礼》乎?”溥答曰:“我国人守丧,皆一遵《家礼》。我当从之,但为风所逆,迨今不得哭于柩前,所以痛哭。”[11]24崔溥一再申明遵循朱子家礼,守孝道为本国一贯之礼节,本国士庶皆以孝悌忠信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士子们以经学穷理为业。崔氏自幼接受儒学教育,且为朝鲜官员,对儒家家礼亦是坚决加以维护,对于质疑之声,崔氏毅然予以辩驳,申明自己坚守孝道的立场。
又次,崔溥居丧守孝期间,坚持不释丧服,不饮酒。如在宁波下山遇到海盗船,程保等跪劝崔溥释丧服,穿官服以避贼,曰:“凡事有经有权,请解丧服,权着纱帽、团领,以示官人之仪。”崔溥坚决不予变通,曰:“释丧即吉,非孝也;以诈欺人,非信也。”[11]12在身处如此险境的情况下,崔溥坚持不行变通之法,拒不改装易服,不免显得迂腐至极,然而以一个坚定的儒士角度审视之,作为受过正规儒学教育的士人,立身处世得以忠孝为先,崔溥的“迂腐”行为,深刻体现了对孝的践行与坚持。
最后,崔溥为了守孝“不释丧服”,竟然放弃面圣受赏的机会“独留馆”,叫随从程保等人去领赏。然而根据受赏的礼节规范,受赏者在受赏的第二天必须亲穿华服去谢恩礼拜,崔溥作为一行人中的代表,自是难以躲过,为此,崔溥谓通事李翔曰:“亲丧固所自尽也,若服华盛之衣,谓之非孝。我亦人子,岂可轻释丧服,处身于非孝之名乎?”[1]132是日觐见时刻,崔溥仍不肯释去丧服,通事李翔即刻拿下他的丧冠,戴上纱帽,无奈之下,崔溥才不得已脱去丧服,曰:“时皇城外门已启钥,常参朝官鱼贯而入,臣迫于事势,服吉服入阙”,崔溥才“迫于事势,服吉服入阙”,出来后立即“复穿丧服”[1]133。崔溥一再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家礼》释丧不吉的通例,集中表现了崔氏的尽孝之心。此外,朝鲜国内,崔溥的忠孝之名亦是昭著,如朝鲜文臣李克均、郑崇祖等均认为“崔溥素有操行,其守丧也,庐墓三年,绝不归家,非诚孝之至而然欤”[12]191,对于崔溥的忠孝节行给予充分肯定。
(二)守礼尊儒
崔氏对儒家仁、礼的坚守还表现为知礼守礼。崔氏经历九死一生,漂至中国陆地,仍处处以儒家礼节规范作为自己的言行标准,并规范着其一行43人等。崔氏为凝聚其一行人,遵循儒家礼节规范,对其同行人,一方面在生活细事上宽慰有加;另一方面,又在行为礼节上严格要求。如登岸后,崔溥特意宽慰陪臣、军属曰:“同此生死之苦,无异骨肉之亲,自此相保则可全身而还。汝等若遇患难则同救之,得一饭则分吃之,有疾病则相扶持之,无一人亡失可也。”[8]20要求同行人相互照料。他还要求同行人言行谨慎,不可违节失礼:
我国本礼义之国,虽漂奔窘遽之间,亦当示以威仪,使此地人知我国礼节如是。凡所到处,陪吏等拜跪于我,军人等拜跪于陪吏无有过差。且或于礼前,或于城中,有群聚来观者,必作揖礼,无敢肆突。[8]20
崔溥以儒家礼仪规范为准则,要求同行人于所到之地,按职位逐级跪拜,在村镇或城中遇人必作揖礼。可见,崔氏受儒家礼仪思想的影响之深,崔氏自身的礼节修养之厚,对儒家礼节的忠贞奉行。
同时,崔溥也敢于尝试以儒家礼节为依据,勇敢地维护自己及其团体的尊严与权利。在同行人遭遇中国内地官员不公正的对待时,崔溥不卑不亢,直言与之。如崔氏一行人过高邮州至界首驿时,“陈萱以军吏,随杨旺而来……萱贪婪无比,奸诈莫甚。至是怒我军人金粟,诉诸旺,旺拿粟,决杖十余”,崔溥令程保告于旺曰:“指挥当护送我等而已,擅自决杖,我异国人亦有法文乎。我有军众,实同盲哑,虽或违误,便当开说,在所矜恤,反为伤打,非上国护送远人之道也。”[8]92旺不能答,崔氏以儒家待远人之道,据理力争,使陈萱、杨旺等人无言以答,维护了同行人的权利与尊严。
此外,崔氏对儒家仁、礼思想的坚守与践行,又表现为崔氏对朝鲜佛教信仰态度的表述:
我国不崇佛法,专尚儒术,家家皆以孝悌忠信为业。[11]21
今我朝鲜,辟异端,尊儒道,人皆以入孝出恭、忠君信友为职分事耳。[8]64-65
我国重儒术,医方次之,有佛而不好,无道法。[8]105
诚如崔氏所言,专尚儒学,不崇佛法。当崔氏被问朝鲜是否崇佛时,崔氏毅然回绝之,朝鲜不崇佛法,专尚儒术。如弘治元年闰正月十八日记载,是日大雨,路遇隐儒王乙源,乙源怜其艰辛,设酒宴崔氏一行等人,崔溥曰:“我朝鲜人守亲丧,不饮酒、食肉、茹荤及甘旨之味,以终三年。蒙馈酒,感恩则已深矣,然我今当丧,敢辞。”[11]21在崔溥的坚持下,乙源遂以茶代酒而宴,乙源因问曰:“你国亦有佛否?”答曰:“我国不崇佛法,专尚儒士,家家皆以孝悌忠信为业。”[11]21再次重申了崇尚儒学、不事佛法的立场。
总而言之,身为儒士的崔溥,始终保持着对儒家仁、礼思想的尊崇,处处申明自己对儒家礼节的遵循、维护、践行,可见儒家思想对崔氏的浸润之深。
三、儒士崔溥对仁、礼的坚守
崔氏对儒家仁、礼的坚守又表现在不盲目迷信、不淫祀,对鬼神敬而远之的天命鬼神观。有研究表明:“孔子把鬼神从传统宗教意义上的神秘力量转变为已逝的祖先,进而通过对祖先的祭祀扩大孝道、仁心,以达至对人的伦理责任的确认和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最后又把祭祀的对象推扩到现实生活中文明的创造者,充分彰显了其鬼神观的人文意义。”[13]崔溥的天命鬼神观正是儒家所主张的“慎终追远”的反映,坚持孝道与仁义之心。崔溥坚持非礼不以祭之、不尚淫祀,在险境中经受住了重重考验。崔溥等在海上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过后,意志消沉,同行人之间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关于祭祀鬼神的论辩,如弘治元年正月十四日记:
安义与军人等相与言,使之闻之于臣曰:“此行所以至于漂死者,我知之矣。自古以来,凡往济州者,皆祭于光州无等山祠及罗州锦城山祠;自济州出陆者,又皆祭于广壤、遮归、川外、楚春等祠,然后行,故受神之祐,利涉大海。今此敬差官特大言非之,来不祭无等、锦城之祠,去不祭广壤诸祠。慢神不敬,神亦不恤,使至此极,尚谁咎哉?”军人和之,咸咎臣。[11]16
很显然,安义将他们此行的不幸遭遇皆归于崔溥不祭祀鬼神触犯神明所致,并得到了多数军士的支持。然而崔溥并不示弱,坚持自己的祭祀观,反唇相讥道:
天地无私,鬼神默运,福善祸淫,唯其公耳。人有恶者,谄事以徼福,则其可福之乎?人有善者,不惑邪说,不为黩祭,则其可祸之乎?曾谓天地鬼神为谄事饮食,而降祸福于人乎?万万无此理也……其于涉海,宜无漂沉之患。然而今日某船漂,明日某船沉,漂沉之船,前后相望,是果神有灵应欤?祭能受福欤?况今我同舟人不祭者,唯我一人耳,尔军人皆诚心斋祭而来,神若有灵,岂以我一人不祭之故,废尔四十余人斋祭之诚也?[11]17
崔氏以一个士人的角度为自己进行辩驳,天地至公,不在于谄媚也,祭祀有常,士庶人祭山川不符合礼节,非礼而祭是为淫祀也,淫祀又安能致福?崔溥作为一位士大夫,坚持不迷信、不淫祀、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思想。尔后,崔氏一次次在实际行动中坚守着自己的初衷,如崔氏一行人路过山神庙时:
杨旺与其徒入庙中,焚香礼神以祭令臣。臣曰:“祭山川,诸侯事。为士庶人者,特祭祖考耳。少逾其分非礼也。非礼之祭,人为谄神不享,故我在本国不敢拜山川之神,况可拜异国之祠乎?”[8]107
在此,崔溥坦言,祭他国之山川鬼神不是遵循礼节的表现,有违礼节的祭祀是谄媚也,士人所不耻为之。又如在杭州武林驿,掌驿中事者顾壁问崔溥曰:“凡人不事佛则必祀神,然则你国事鬼神否?”崔答曰:“国人皆建祠堂,以祭祖祢,事其当事之鬼神,不尚淫祀。”[8]65如崔氏所述,朝鲜主流尚尊祖,不随便祭祀鬼神。
至分水龙王庙。……陈萱曰:“此祠乃龙王祠也,有灵迹。故过此者皆致恭拜祭,然后行,不然则必有风涛之险。”臣曰:“观于海者难为水。我已经数万里大海暴涛之险,若此中土中江河之水, 不足畏也。”语未毕,萱告于旺曰:“此人不要拜,亦不可屈其志”云云。[8]107
崔溥直言陈萱所言为怪诞之说,不足以令人信服。崔溥更是坚信,大海暴涛尚且不惧,江河之水又何惧之有,坚持不拜龙王庙,不行淫祀之活动。
总之,崔溥作为儒家士人,坚持并践行儒家仁、礼思想,不迷信、不盲目祭祀、对鬼神敬而远之的天命观。
四、结语
朝鲜以“小中华”自称,中国与朝鲜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往来关系,中国儒家经典不断传入朝鲜半岛,对朝鲜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发展到15世纪,朝鲜俨然已是一个崇尚儒学的国度,儒家思想成为官方主流思想,全国上下崇慕华风,从中央到地方建有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与科举取士制度。生长于奉儒仕宦家庭,自幼接受正规儒家思想教育,并颇有功名在身的崔溥,其儒家品格的养成来自于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塑造。有研究表明:“崔溥的义理和士林意识使得在漂流至明朝和送还的过程中重视儒教性的礼仪,讲究上下尊卑和揖让进退的礼节。”①《崔溥 中國漂海 儒學思想》(《崔溥的中国漂海和儒学思想》),《韩国思想史学》第四十辑,韩国思想史学会年出版,第68页。崔溥在渡海返家奔丧时,突遇海难,漂至异国,面临重重困难考验,始终坚守儒家仁、礼思想,践行儒家规范;始终以儒家的礼节、仁爱思想为依归,面对同行人的诘难与不解,坚持以儒家礼节行事,虽死而不悔,坚持不尚淫祀,不盲目迷信山川鬼神,尊祖敬宗,崔溥可谓真儒士也。
面临险境,崔溥坚守儒家的礼节规范,不屈不挠,忠君、尽孝,虽略显迂阔,却始终如一。一方面可见儒家思想对崔溥的影响之深,以及崔溥对儒家思想的践行之坚;另一方面,亦可从中窥见儒家思想对朝鲜士人团体的影响。其实,崔溥对儒家思想的笃信、坚守与实践,也并非个案,诚如前文所分析,儒家思想在与明代同时期的朝鲜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影响。
——谈大型古装淮剧《马前泼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