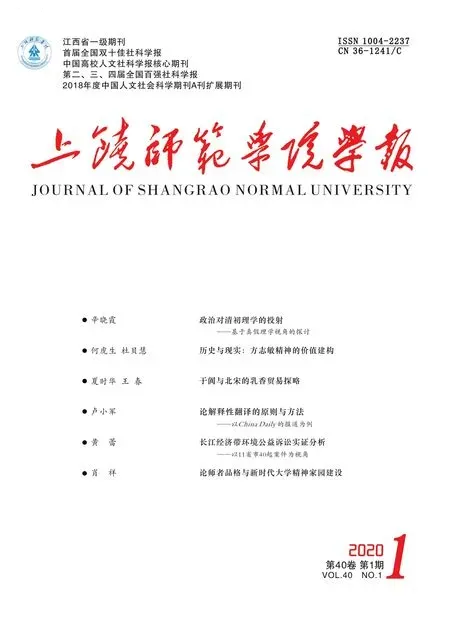《明诗别裁集》删诗改诗例说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裁”字,《说文》中解释为“制衣也”,即量体剪裁。《明诗别裁集》用“裁”字表明,编者依照自己的标准对于诗作是否入选进行取舍,以及对入选诗作进行剪裁,也就是删改。“抑予观陈卧子《明诗选》,其所采取,时有删润,故所收较完美。是编所录,务从善本,其有名言可采而疵类并见者略焉。”[1]2此句可见沈德潜对于删改诗的一个基本认知,即删改诗句是对于原作的润色,只有改动不合理之处,其诗才近于完美。排除编者个人的删改习惯,我们能够看出,《明诗别裁集》不仅仅是一个诗歌选本,更是沈德潜想以此来宣扬自己诗学主张的著作。此选本是用来辅翼诗教的,是用来拯救清初诗坛的弊端,改变时人对明诗的偏激评价,以使诗歌朝着雅正、复古方向发展的指路牌,所以凡是不符合自己审美标准的诗句都要加以改正,以达到典范作用。
本文对于删改诗句的判断,是以诗人较早的原始文集为依据,以沈德潜在序言中提到的明诗选,即陈卧子《皇明诗选》、朱竹垞《明诗综》、钱牧斋《列朝诗集》为辅助。凡是《明诗别裁集》中删改的诗句与上述三个选本重复的,本论文都不作为参考。如高棅诗《九月八日郭南山亭宴集分得下字》,相较于高棅的《高漫士啸台集》,《明诗别裁集》中删去了“千载同一时,黄花笑盈把。酣歌林壑暝,新月松萝挂”两句,但鉴于《明诗综》亦删掉此二句,沈德潜有因袭之嫌,故不算作《明诗别裁集》的删诗。
一、温厚和平的诗教观
诗教是沈德潜论诗的主旨,《说诗晬语》开篇即阐明诗教的重要性:“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继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衎之具,而诗教远矣。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2]81沈德潜论诗,反对无比兴寄托一味讲究声色之作,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其具体内容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思想的纯正,以《三百篇》为旨归,即《论语·为正》中所说的“思无邪”;二是情感表达的平和中正;三是雅言,即文辞的典雅。
(一)思想的纯正忠厚
沈德潜承认诗歌本出于性情,但他认为诗歌只有“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合乎风人之旨,才可以留存。所以《明诗别裁集》中一千余首诗,“皆深造浑厚,和平渊雅,合于言志永言之旨,而雷同沿袭浮艳淫靡,凡无当于美刺者屏焉”[1]1,仅有个别诗句需要删改。
薛蕙《昭王台》“儒生终报主,乱世始怜才”[1]67一句,明嘉靖十四年刻本《薛西原集》、明嘉靖《薛考功集》十卷附集一卷“儒生”皆作“腐儒”。这是一首咏史怀古诗,诗人感慨于战国时期燕昭王的求贤若渴,今昔对比,更突出了自己无人赏识的悲哀。据《明史·列传第七十九》载薛惠生平,举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刑部主事。谏武宗南巡,受杖夺俸。后被起用又因“大礼议”事件入狱,复出不久又因故遭贬,既而事白,吏部数移文促蕙起。蕙见璁、萼等用事,坚卧不肯起。此诗虽无法考证所作年份,但结合作者多次直谏被诬且终不复出的经历可知,“腐儒”一词实是对那些“诡经畔礼、上惑圣聪”的“二三臣者”的嘲讽,其中还有对君主终不识人的愤懑。沈德潜改为“儒生”可以说是把这种怨刺的情绪做了一个弱化,“儒生终报主”,如诗人一般全天下的读书人终究是要报答君主的,即便不被重用,也要“回首征途上,年年此地来”。诗人流连昭王台,便是寄托了对君主的期望,沈德潜改为“儒生”正是体现他的忠君思想。
徐熥《陈价夫归自崖州谈粤中山水因怀旧游》首句在《幔亭集》中载为“珠崖弹铗动经年,醉抱黎姬酒肆眠”,沈德潜改为“朱崖弹铗动经年,醉向黎姬酒肆眠”[1]67。此句描述的是陈价夫谈粤中宴饮的场景,友人们在一起开怀畅饮,一手拥着黎姬美人,一手握着斟满的酒杯,酒肆里满是醉倒的客人,如此良宵岂能不欢乐。沈德潜改“抱”为“向”,就使得宴饮中男女嬉笑纵情的场面变得可以控制,虽如此良宵,但人们的举止依旧符合礼仪规范,也就是所谓的“乐而不淫”了。
(二)情感表达的平和中正
沈德潜在《施觉庵考功诗序》中说:“诗之为道也,以微言通讽谕,大要援此譬彼,优游婉顺,无放情竭论,而人裴徊自得于意言之余。《三百》以来,代有升降,旨归则一。惟夫后之为诗者,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则放纵,而戚若有亡,粗厉之气胜,而忠厚之道衰。其与诗教日以傎矣。”[1]1314思想的纯正忠厚反映在诗歌情感的表达上,也一定是含蓄蕴藉的。他反对诗歌的放情竭论,“狂、纵、粗厉”与过度悲伤都是忠厚之道衰的表现,情感也要符合儒家的中和之道,有所克制,语言也不可毫无保留地痛快吐露,而要微言存大义。
高启《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始知欢乐生忧患,韩休老去无人荐”[1]10,《大全集》为“始知欢乐生忧患,恨杀韩休老无荐”[3]10。这是一首感时怀旧诗,诗人感慨昔日二人歌舞名动天下,万人追捧,而今国破家亡,梨园散落,此句能体现整首诗的主旨,乐极生悲,统治者的奢靡生活终究导致了黍离之悲,诗人痛恨朝中没有如韩休般敢于直谏的大臣,痛恨无人能挽救这场危机,痛恨自己不被赏识,用“恨杀”能体现出诗人对朝廷的不满和激愤,情感强烈。沈德潜改后便没有了诗人主观的强烈不平之气,只剩下诗人客观的议论。
边贡《送马欹湖赴河南提学》中“故人都在城南宿”[1]49,《华泉集》本作“故人却在城南宿”[4]。“却”字从情感来说更具转折意味,能使诗人的不舍情绪表达得更加强烈,且与下句形成情感上的呼应,或许城南较远,或许城南更近,但城南无疑使诗人愈觉离别的伤感,倒不如速行干脆。沈德潜改为“都”字,使此句的情感表现由强变弱,悲伤的意味没那么浓厚,一如此诗最后一句诗人对自己的宽慰,“临歧莫动殊方感,余亦东西南北人”[1]49,我也不过是一个漂泊的旅客,送别有什么可悲的呢?全诗情感哀而不伤,改动之后整体风格上更趋于沉稳古淡,可见沈德潜对于副词的把握也是基于全诗的风格与基调而言,注重炼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沈德潜诗歌创作的一个主张,作者的确可以自由抒发自己的情感,但也还是要有所节制。他更看重以儒家的中庸之道来中和诗人的情感,把这种强烈的情感抑制住,使它变得缓慢低沉。
(三)文辞典雅
沈德潜在用词上也颇讲究雅正,如顾麟《度枫木岭》一诗“高林忽在下”[1]50,沈德潜将“高林”改为“崚嶒”,二者虽都有高峻之意,但此处改为“崚嶒”显得更加文言化,具有古典诗的韵味,且“高林”仅能表示地势之高,而“崚嶒”则能表现山势高耸突兀之奇景,可见沈德潜在追求文辞典雅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词句的语言表现力。徐熥《陈价夫归自崖州谈粤中山水因怀旧游》中“笑语尚存湖海气,衣裳犹带岛夷烟”[1]103,沈德潜将“湖海气”改为“豪士气”,二者意思也基本相同,都是指豪侠之气。“湖海气”语出《三国志·魏志·陈登传》:“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13]97徐熥在这里用“湖海气”也暗合了他所在的海南。但“湖海气”带有一种江湖习气,少有人用,沈德潜改为“豪士气”,用词显得更加典正。刘基《梁甫吟》:“谁谓秋月明,蔽之往往由纤翳。谁谓江水清,淆之往往随沙泥。”[1]3《诚意伯文集》收录此诗为:“谁谓秋月明,蔽之不必一尺云。谁谓江水清,淆之不必一斗泥。”[6]3张羽《题陶处士像》:“五儿长大翟卿贤”[1]14,《四杰集》收录此作为:“五儿长大翟妻贤”。“一尺云、一寸泥”改为“纤翳、泥沙”,“妻”改为“卿”,前者都较口语通俗化,改后符合诗人语言文雅的要求。
二、有法到无法
如果说温厚和平的儒家诗教观是沈德潜论诗的宗旨,那么,除此之外诗歌的体裁、格律、属对、用事等诗歌创作规范都可以称为诗法。“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7]195,自诗法的概念在唐代确立之后,便受到了历代诗论家的关注。作为“格调派”的代表人物,沈德潜对于诗法无疑是十分看重的:“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谓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纵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著得死法?”[2]83沈德潜承认诗必须要有一定的规则约束,包括字句、起承转合、声律、用事等问题,否则诗也不再是诗,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个死法、活法的区分。恪守成规,拘泥其中是死法,只有以意运法才为活法,正如天地万物的变化那样自然,“纵”即是束缚,那么“运”便如沟渠引导溪流般自由。王槚《诗法指南引》中说: “且古人作诗,感于物而形于言,凡以流通情性耳。初,未尝拘拘然先立某格,而后为某诗也。如必欲宗其格而后成诗,则唐人果宗何格乎? 由此言之,则格之不必拘也明矣。”[8]2412唐人作诗除杜甫外鲜有论诗法者,可诗法自存,后人诗学理论众多,可佳作难得,这并不是诗法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具体运用出现了偏差。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曾批评皎然的《诗式》为“画地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4]2412,学习诗法的最高境界即是自由地驾驭,视它如无物,以达到“无法”之地。许印芳曾言:“诗文高妙之境,迥出绳墨蹊径之外。然舍绳墨以求高妙,未有不堕入恶道者。故知诗文不可泥乎法之迹,要贵得乎法之意且贵得法外意,乃善用法而不为法所困耳。”[9]此处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究竟何为“以意运法”,“意”的具体指向是什么,或许可以在他的删改诗中找到答案。
卷五边贡《运夫谣送方文玉督运》一诗:“运船户,来何暮。江上旱风多,春涛不可渡。里河有闸外有滩,断篙折缆腰环环。夜防虫,日防漏,粮册分明算升斗。官家但恨仓廪贫,不知淮南人食人。官家但知征戍苦,力尽谁怜运船户。尔勿哀,司农使者天边来。”[1]49《华泉集》载为:“运船户,来何暮。江上旱风多,春涛不可渡。运船户,来何暮。里河有闸外有滩,断篙折缆愁转船。夜防虫鼠日防漏,粮册分明算升斗。官家但恨仓廪贫,不知淮南人食人。官家但知征戍苦,力尽谁怜运船户。运船户,尔勿哀,司农使者天边来。”[4]49
通过这两首乐府诗的对比,我们能够看出,沈德潜删去了重复的两句“运船户”,从表面上来看,这样做无疑影响了乐府歌词的形式美,但沈德潜也一定注意到了此问题,否则不可能将“夜防虫鼠日防漏”改成“夜防虫,日防漏”。他并不拘泥于具体的乐府诗的形式字数,甚至是内容重复所带来的独特的审美体验,而是在抓住乐府诗本质的基础上,随性抒发。“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齐梁以来,多以对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岂复有咏歌嗟叹之意耶?”[2]91乐府与近体诗的区别在于它的音节变化曲折繁复,乐声之高低抑扬依随自然歌咏而变化,至于哪一小节该用几字,只要符合整体的韵律和谐即可。齐梁以来随着“四声八病”说的流行,诗歌的对仗、声律等规范越发繁琐,人们往往刻意追求诗歌的音节美而失掉了乐府诗自然的声调所带来的嗟叹之意,沈德潜看到了这一点,故此处不拘泥于原诗的形式,删繁就简的同时依旧保持乐府诗歌音节曲折感人的本质。这也就是所谓的“以意运法”,在诗法之上的灵活变化。沈德潜虽然对于诗法有过具体表述:“然所谓法者,行所谓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其中”[2]83,但是这其中的“神明”究竟为何,沈德潜又以什么为标准来评判诗法?单看他的诗学批评话语,我们对此依然模糊,或许换个角度,从他的删诗改诗中可窥一二。
何景明《秋江词》一诗:“烟渺渺,碧波远。白露晞,翠莎晚。泛绿漪,蒹葭浅,浦风吹帽寒发短。美人立,江中流。暮雨帆樯江上舟,夕阳帘拢江上楼。舟中采莲红藕香,楼前踏翠芳草愁。芳草愁,西风起。芙蓉花,落秋水。江白如练月如洗,醉下烟波千万里。”[1]52原在“江白”句前有“鱼初肥,酒正美”二句,沈德潜将此二句删去,并有评语:“‘美人娟娟隔秋水’,风度似之温飞卿,乐府过于旖旎,诗格转不逮也。一本节去末二语,更有余韵。”[1]52此处删去“鱼初肥,酒正美”二句,表面看来与开头六句形式上不合,但也是“以意运法”的结果。除此之外,沈德潜还提出了“余韵”一词,并将“以意运法”删去此二语的原因归咎于“更有余韵”。他认为整首诗风格旖旎,意境清美而又婉约,蒹葭浅浅,美人立于江畔,芙蓉秋水,西风芳草,弥漫着思而不得的淡淡哀愁,“鱼初肥,酒正美”二语显然跟诗歌的整体氛围稍有不符,偏于疏朗豪放而少柔美,将其删去后整首诗更有余韵。也就是说诗法服务于诗韵,“以意运法”中的“意”固然是指诗人本身的情性,作家的主观审美风格,还必须要包括整首诗歌的意境、风格及神韵。它是作家与作品的结合,带有中国古代诗文评所特有的玄虚的称名,本于体悟,从创作实践中来,类似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5]26它与《庄子》的“言不尽意”《周易·系辞》的“圣人立象以尽意”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不仅包括作家的情性心境还符合作品的整体意境,是二者的浑然交融。
再比如薛蕙《杂诗》:“富贵使心惑,嗜欲致行妨。宴安损性灵,美疢生膏肓。吾观古来士,高躅互相望。首路或暂同,中道何苍黄。班生嗣前烈,马融遁远方。藉梁奄为累,附窦终自戕。通人识尚尔,咄咄可悲伤。”[1]67明嘉靖十四年刻本《薛西原集》最后还有两句:“小人难久要,君子贵其常。草木有贞心,岁晚盛芬芳。”[17]诗人通过用典,举班固、马融攀附权势,最终为权势所累的例子,劝诫文人坚守本心,不因富贵权势、安逸贪求而丧失自我。最后两句单看并无不妥,是诗人对于此种现象的一个议论总结,运用了比兴的手法,以草木比喻君子,希望能像草木那般,保持初心,愈久弥香。但诗人开头两句便已说明自己观点,紧接着又举例论证,最后抒发自己的感叹,读者已能从最后的惋惜悲叹中读出作者想要说明的点,所以此时结尾恰有回味,学识渊博之人尚且沉溺于富贵权势,何况常人?这的确令人心悲。此处结尾点到即止,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也就是沈德潜所谓的“止所不得不止”[2]83。
诗法自然,无迹可求,何处该行,何处该止,以诗韵为重要的评判依据。沈德潜删去“鱼初肥,酒正美”与“小人难久要,君子贵其常。草木有贞心,岁晚盛芬芳”几句,都是“以意运法”的结果,而目的皆是为了使诗歌更有余韵。诗法就好比古代的刺绣针法,它纷繁复杂,通过直绣、平绣、缎文绣等技巧在织物上绣制的各种图案,而诗韵就好比是最终织品呈现给人的美感,每一个细密的针脚都受其影响,这是一种高级的美学理想,虽然依旧无法对它作具体的说明,但就像是它一开始便存在于人的意识一样,每一个字词在落笔的那一刻就已经感受到它的存在,并有意无意的向其靠拢。沈德潜论诗虽注重诗歌的“体格声调”,但他以“诗韵”作为评判诗歌的最终标准,摆脱了对于诗歌外在形式即法的束缚,诗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地创作,从而达到“无法”的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与主张“格调不在性情外”的袁枚反倒有一致之处。袁枚虽然强调诗歌重在抒写性灵,但却也绕不开诗法的问题,格调从属于性情正如沈德潜主张的诗法服务于诗韵一般,这是所有诗家所共同面对的矛盾,我们不能将其划归为“格调派”“性灵派”等便认为一是一二是二,诗法与性情是不可调和的两面。与此同时,讲究“诗韵”也就不同于对某一特定风格的欣赏,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回归到了诗歌的本质,注重诗作的回味无穷意味深长所带给人的审美的享受,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宽泛的诗学取向。正如蒋寅先生所说,“沈德潜的诗学观念与其说是发展了格调派的学说,还不如说体现了古典诗学的一般观念”[10]。无论是其“去淫滥以归雅正”,还是对于“诗韵”的强调,都不能仅仅以“格调说”完全概括,而是要看到其中的传统精神和古典审美特征。
概而言之,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对于入选诗作的删改,固然不利于原始诗作的保存,有些改动将作者的情感做了弱化处理,使之更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有些改动则是直接给读者传递了错误的信息(如边贡《送马欹湖赴河南提学》一诗,四库本《华泉集》载其题为《送马欹湖赴湖南提学》,《明武宗实录》卷五十六记载马应祥在正德四年冬被升为湖广按察司佥事,故此处改为河南应是错误),但他的某些改动也使语词更文雅,诗歌表达更活泼(如顾麟《度枫木岭》一诗“衣襟有云雾”改为“衣襟带云雾”[1]50)。总体来说,我们能够从这些删改中看出沈德潜的审美标准,可以作为他诗学理论的论据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