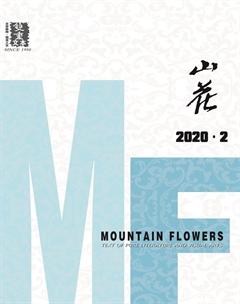滩涂的踪影
复达
一
我将岛的四周团团扫描了一圈,忽然发现,除了零星的几块沙滩,岛周边几无一处曾经的滩涂。
在人们的想象里,海总是蓝得舒心悦目,蓝色的海水,白色的浪花,金色的沙滩,时时漾诗情,处处见画意,带给人的是一种惊喜欢欣,一种悠扬舒畅。不知何年何月始,我所处的海却成了浑黄一片。即使过滤一下,也似乎脱不了黄浊的因子。长江、钱塘江、甬江带着内陆的黄土,滚滚东流,与海相交融。海纳百川,只能默默地将泥土揉和在江口那一片海域。而江口周边千百座的岛屿,又如一道道的堤坎,挡住了潮流向外海扩散。潮起潮落间,浑黄的海水就在一道道的堤坎间腾来捣去,变得越发浑浊。
浑浊的海水,必然导致泥土的积淀。渐渐地,一层层的泥土在岛脚的凹口处凸显出来,越积越厚,从堤岸慢慢地向外拓展,形成浅浅的泥坡——潮间带滩涂。涨潮时,岛脚边依旧一片汪洋,浑黄的海水像是拉上了皱褶的帷幕,遮盖住底下的滩涂。退潮后,滩涂才露出真面目。一副灰不溜秋的模样,布满了洞洞孔孔,几条细小弯曲的水流缓缓地流淌,零零落落的几处水滩在阳光下映现几许温情。一只只的小蟹爬来爬去,横冲直撞抑或闲庭信步。弹涂鱼瞪着头顶的两枚眼珠,警觉地不时跃动。那些香螺、泥螺悠然地爬动,海瓜子、蛤蜊、蛏子则窝藏泥下,透过气孔呼吸。滩涂滋生了小鱼小蟹和贝类,也养育着它们,给它们提供生存空间。
那些滩涂,其实就是翻卷的波浪将淤泥推积到了岛屿触角似延伸的海岬间,仿佛海在自动地确保航路的畅通;又如沙滩一般,呵护着岸线,呵护着岛屿。滩涂成为了海与岛之间的一段纽带,将近岸海域的生态自然地维系着。
可是,如今,我作为这座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海岛上的人,已难以见到港湾里那些曾经的滩涂。
二
我的老家在岛的北部,一个叫做念母岙的地方。念母岙以费家门口为中心,扩展到了北畚斗水库下面的村落。费家门口所在的区域是城镇,为东沙镇的一部分。我记事起,那里就有一条狭长的小街,几家商铺、大饼油条店、铁匠店、生资公司等遍布小街的两侧,沿着小街,还有路边菜场。也就二三百米的距离,我的家所在的区域却属农业户口,晒盐为主,兼带耕种一些农用地。我的骨子里就烙上了咸嘞嘞的元素,也染上了泥土的气息,与城镇里的人似乎有很大区别。
费家的后面就是沙滩头。沙滩头东起前往东沙镇里的狗嘴部岭墩,西至西沙角,一弯滩涂——我们称之为泥涂——镶嵌其间。说是沙滩头,却从未见到过沙滩。想来原先该是黄灿灿的沙子吧,落潮后,能露出浅浅的一弯黄沙,熠熠生光。却不知从何时起,淤泥越积越多,将一抹黄沙渐渐地蠶食,湮没在淤泥之中,沙滩头便徒有其名了。
十来岁开始,每年的初夏直至秋日,我与小伙伴们常去沙滩头。尤其是暑假,下午时分,我们赤着脚,穿着短裤,有时穿背心,有时干脆赤裸上身,拿着只铝锅或长椭圆形的铝饭盒,嘻嘻哈哈地向着沙滩头前进。
到沙滩头时,潮水大多已落下,或正在渐渐地退下去。灼烈的阳光下,湿漉漉的滩涂亮亮的,像是抹了淡淡的油光,生动地挥洒着,那样地诱人。几处水洼泛着亮光,仿佛在标注滩涂的起伏不平,而非铁板那样平整。滩涂就若岛屿沉浸海中的一大片青灰的色块,紧紧地攀附着岛,与岛相依相随,不离不弃。
落潮的海水自是有气无力样的,在滩涂的边缘来来回回漫步。但是,我们从不迈向那波浪深处。大人们告知我们,滩涂是滩涂,海是海。滩涂边缘的海下已被波浪推搡得空空的,那里的水就深呢。后来,我才知道,强大的波浪像是清道夫,将航道等区域的淤泥渐渐地推向岸边。波浪也非一推了之,每逢涨潮,总会漫上滩涂,给滩涂清洗、抚摸、洗礼。滩涂就享受波浪的抚爱,尽情地让波浪在躯体上荡漾,成为海的一部分。退潮后,便沐浴阳光,或者雨露,畅快地伸展,呈现海边的一片湿地,将岛滋润。
滩涂就那么诱惑着我们。
靠岸边的滩涂有点紧绷着似的,一脚下去,感到有点硬实。越往外,泥涂越软越细,差不多深及膝盖,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在滩涂上可以深切地体验跋涉的含义。
滩涂上硬实的部分布满了一个个的小洞,星星点点,像一个个出气孔,还在呼吸着似的。洞口多为拇指般大,里面都蓄着水,未溢满,离洞口差那么一二厘米的样子。退潮后,洞里的水定当满至洞口,里面的小蟹见到白白的天光,抖抖身,慢慢地爬出来,水便浅了些。数不清的洞,就如滩涂的毛孔,抹不去,填不满。滩涂,总有洞洞孔孔的。
我们起先常捉小蟹。滩涂上的小蟹以沙蟹为主,中指的指节那般大,外壳呈长方形,有点粗糙,淡褐色,两枚大蟹钳上长有细细的绒毛。也有和尚蟹、膨元蟹。和尚蟹顶着圆形的外壳,光滑,坚硬,如一顶铜帽。想来圆圆的壳像和尚,故名之。膨元蟹则差不多为方形,淡青色,比沙蟹厚实。沙蟹和膨元蟹可以红烧,也可腌着吃,和尚蟹似乎只用来红烧,偶尔也煮在白菜之中,搭色,调鲜。因为小吧,几无蟹肉,吃的是一种鲜味。
那些小蟹实在胆小,一见我们,就慌乱逃窜,纷纷钻入洞里,一下子全无踪影。我们就近蹲下,拿右手臂直往洞里插去,先是一泡水溢出来。洞壁湿滑,却又箍紧着手臂似的,只觉深若无底。有时明明感到已触底,却摸不到小蟹的身子。当然,小蟹还是有的,它们会从另一个洞里逃出来。我们便扑腾过去,用手按住,小心地捏住它的后背,以防被大蟹钳钳痛。钻洞里的多为沙蟹和膨元蟹,和尚蟹爬得慢,似乎也懒得打洞,只会逃入水坑里,搅混水,躲匿起来。只是这蟹量少,每次捉不上几只。小蟹难捉,却是非常有趣。有时往往为了作耍,像是要非捉住小蟹不可似的,就起劲地往洞孔里伸进胳膊,还把双脚用力地支撑在泥涂里,显出一股倔犟。待捉住小蟹,便欢呼起来,仿佛大功告成一般。
后来,见到菜场上有卖沙蟹、膨元蟹的,一大堆,就在心里产生疑问,这么多的蟹是如何捕捉来的呀?后来,才听人说是用六六粉药的。有人将六六粉撒在洞口边,小蟹爬出来后一嗅,就晕倒了。我也曾在隔海相望的双合岛,与大姑的儿子一起捉红钳蟹。红钳蟹形似膨元蟹,只是其中的一只大蟹钳特别大,红色,醒目。大姑的儿子拿一片旧网,系上一根长长的绳子,往滩涂上铺平整,将长长的绳子拉向岸边。等了好一会,红钳蟹以为安全了,渐渐从洞里爬出来。正当它们觅食或玩耍时,我们使劲一拉绳子,网子嗖地一下子收缩,那些蟹就缠在网上了,一只只被摘取下来。我宁愿相信,菜场上的沙蟹、膨元蟹是用这种方式捕捉来的。
在沙滩头捉蟹,是前凑,或者收尾时的玩乐。我们主要的是拾螺采贝,更多是采海瓜子。
柔软的泥涂上,爬着泥螺,慢悠悠样的。见到人,也不闻不问,仿佛目中无人一般,继续缓慢地爬行。起先,我们也捉泥螺,但放在铝锅或饭盒子里不久,它们就在不知不觉间爬出来,惹人空欢喜一场。后来就很少捉泥螺了。也有香螺、蛤蛎、蛏子,但量少,若能采到几枚,我们便像中奖似的高兴。
泥涂上最多的是海瓜子。像少女的指甲那般,红润,清亮,透着一种鲜活的光彩。可红烧,也可煮汤,鲜美得很。
夏天是吃海瓜子的最佳季节,那时节海瓜子硕大,壮实。湿润光柔的涂面上,随处可见梅花状的印痕,仿佛雨滴不轻不重地整齐地喷溅过,抑或波浪用模块印过一般。就在这梅花状的花纹下,海瓜子静悄悄地藏着。那花纹,该是它们呼吸的气韵吧。
弯腰,躬背,右手张开五指,往花纹处插下去,一捏,一粒扁扁的小巧的海瓜子就在手掌间了。掏出来,挤一下手上的泥,便可以将海瓜子放进铝锅。有时,躬在一个地方,待上一会,将一处处的花纹都捣腾一下。有时,缓缓地往前,寻觅花纹大的,想采到更壮实的海瓜子。每个人都似乎专心致志样的,一门心思地采拾,像是默默地在竞赛。
一枚接一枚,铝锅里渐渐堆叠上带着青灰泥衣的海瓜子。然而,我的技艺较差,常常比不过人家。好几个专门采海瓜子的妇女,一手提着竹篮,一手快速地插进泥涂,又敏捷地将海瓜子扔在竹篮里,机械一般。一个落潮,海瓜子总有半竹篮,几斤哪,可卖好多钱,真让人羡慕。
不过,一个多钟头后,我们看看约有半铅碗的海瓜子,能炒一大盆的,也心满意足了。何况,潮水再过会也要涨上来了。
此时,太阳往往已悬在西边的山头上。我们就开始打泥仗,仿佛长时间的采拾后得活动一下。你抓一把泥,我也抓一把,互相掷来抡去。见到对方将泥掷过来,或低头,或转身而逃,有时躲过,有时便打在背上,却还是哈哈大笑,然后,反转身,又抓起泥,朝对方打去,在一阵掷泥中将欢乐倾洒在泥涂之中。没一会,身上已是泥渍斑斑,若一朵朵灰色的花斑刻印着。于是,索性来个趟地滚,将身子躺在柔软的滩涂上,左滚一下,右翻一下,全身染上湿滑的泥浆,犹如穿着一件泥衣。有时,干脆掏起一把把的泥浆,抹在脸上,只露出两只小小的闪光的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他,再扮一下鬼脸。
回家路上端着铝锅或饭盆子,将阳光下泛着淡淡光照的身子穿过费家门口,如得胜的小英雄,一路雄赳赳气昂昂的。到达北畚斗水库后,一个个扑嗵扑嗵地跳下去,把泥浆洗去。
少年的乐趣,就在沙滩头的滩涂上年年回旋。
后来,我读书,工作,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对于沙滩头的滩涂,也少有关注。过了好些年,才知沙滩头的外侧被攔上了堤坝,改成了养殖场,与东沙镇早已存在的养殖场连在了一起。费家还在,却没了沙滩头的滩涂。每当吃着海瓜子,我就会想起沙滩头采海瓜子的情景,一阵失落。年少时的乐趣,像在梦幻中似的。
三
时代的变迁让人始料不及,我压根没想到过自己会涉足滩涂的事。
本世纪初,我被任命为县发改局局长,兼任招商办主任。过了四年多,又被委以重任,担任了副县长,主管发展改革、工业经济、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等,分管和联系二十来个部门、单位。期间,恰逢全县临港工业尤其是船舶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工业强县”的号召得到了快速高效的落实,工业经济的发展可谓方兴未艾。我任发改局长之初,全县工业总产值才二十多亿元,到2006年底,突飞猛进似的,便突破了百亿大关。之后几年,以每年一百亿元的速度增长。我当副县长那几年,可说是当时全县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海岛的优势就是岸线资源,以及小岛的开发利用,这是得天独厚的。因而,凡涉及临港产业发展的,必会利用岸线,也就必涉及用海。用海,除了十几乃至二三十米水深的岸线,大多离不开滩涂的利用。
当时经济开发区所属的五里塘岸线规划成建造五至八万吨级的船舶修造业集聚区,并规定塘外的海域只允许延伸一百五十米。沿海的岸线连同海塘内的盐地就被一段段分隔开来。
五里塘位于岛西南部。将岛西南部两端的山咀连接起来,建成海塘,故名西南塘。因长达五里,又名五里塘。海塘内改造成了盐地,达一万五千亩,俗称万亩盐场。远眺,一望无际似的。
1997年,我高中毕业,恰逢恢复高考,却榜上无名。随后,我就在大队的盐场里晒了一个月的盐,曾踏上过五里塘。那塘坝顺直绵长,一块块坚硬的石头密密匝匝地拼镶着,仿佛一条粗壮的石龙将海直挺挺地阻隔开来。塘内,一格格的盐滩井然有序铺陈起来;一座座梯形的盐坨排列在盐滩边,白色的盐粒闪闪发光。塘外,灰黄的滩涂围拱着海塘,像长卷般铺陈。三三两两的人在滩涂上跋涉,躬身采贝;也有几个站在塘脚边,一下下地抛掷钓钩,钓着弹涂鱼。沉闷的滩涂上就点染出一番动态和活力。
当规划建设船舶修造业集聚区时,我就想,这五里塘内的万亩盐场原本也该是滩涂吧,因为淤积严重,所以可筑塘成地。几十年来,海塘的外侧又起了淤积,形成新的滩涂。好在外面的海域茫茫一片,几无岛屿,水也越来越深。将这样的滩涂围填掉,也就是将现在的海塘再向外推一百多米而已,该不会影响潮汐的流动。过一两年,最多三五年,十几家的船舶企业就可拔地而起,一座座的龙门吊将洋洋大观地矗立在海边。
没几年,五里塘内的部分盐地和塘外的滩涂就变成了建设用地,建上了厂房、船台、船排或船坞,以及大大小小的堆场,一艘艘的船只在在这里拼接起来,三五个月便建造成一艘散货船。然后,崭新的船只交付给货主。五里塘连同它外侧的滩涂,早已湮灭在龙门吊之下。
岛南边有座小岛,叫做江南山。一步之隔,最近处相距一二百米。早些年,我们与几户朋友家庭乘航船去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片滩涂上捉望潮。望潮是一种小型章鱼,八只小爪,身躯如蛋,柔软,很少见到的。时值夏秋时节,见滩涂上有人在采拾,年少时在沙滩头采海瓜子的情景立时浮现上来,不由得脱掉鞋子,还鼓动孩子们一起踏入滩涂中。与沙滩头不一样,这滩涂上没见到梅花状的花纹,其他的贝类也不清楚,就只好往洞里搜寻,想捉到几只小蟹也行。却不料,几个洞里都空空如也,挤出的只是一泡浊水。于是走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当地人旁边,问在捉啥,才知是捉望潮。看他竹篓里的望潮,十几只,鲜活地相拥。这滩涂上竟有望潮?出人意料,又令人大喜过望。就学着他的样,往一个洞里插入手臂,不停地穿插,像做活塞动作似的,却不见从周边的洞里爬出望潮来。试了几次,一只望潮也未出现。想想,捉望潮也需有技巧,也不是每个洞里都有吧,得凭经验。问这望潮多少一斤?他说八元一只。原来望潮按只卖的。前些日子在饭店里吃到望潮,却已是二十多元一只了。
江南山的东南面也被人看中,要建造一家大型船厂,可建造二十万吨级的船舶。为了引进这一船舶企业,县里真是下了大决心,除正常的项目开发外,最主要的是要开发商出资五千万元,建造了江南大桥,与我所在的大岛相连接,以方便江南渔村群众的出入。船舶企业建成了,彩虹般的大桥也竣工了。
江南山与我的岛连在了一起,我有空可随时过去。然而,那片生长着望潮的滩涂却再也找不到了。
那些年,岛上的人深深地体会到,发展临港工业的路子走对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呼呼响”——劲头十足,潜力很大。每每碰到市里的人员,总夸我们的发展势头大好,岸线的后发优势越来越足。岛上的人也似乎很少想过滩涂的被利用、被填埋,有什么不妥,已司空见惯似的。看看整座岛的周边,除了山脚沉浸在海中,哪里不是围垦的?历古以来,海岛就在围填了。能围填的地方,无不都是滩涂,或者就是浅海,浅海的底下也还是泥质。他们就很少关心滩涂的被填埋,仿佛对滩涂的消失已麻木。而临港产业的发展又哪能不用到浅海和滩涂?
有人说,炸药一响,税收就进账。确实如此。围填滩涂,自然得开山。开山就得用炸药。山一开采,企业就得支付资源税。哪一家临港工业不围填的?山一层层的被开采,被削掉,一辆又一辆的拖拉机将开采的山砂运往海边,倾倒在滩涂上,击起一阵碎泥。渐渐地,滩涂上堆满了黄白色的砂石。铲车在上面平整,压土机硕大的铁轮在缓缓地来来回回地碾压。然后,变成一块块的土地。
当一车车的砂石倾倒在滩涂上时,我不知道滩涂有没有感觉疼痛,有没有皱眉,有没有声嘶力竭地呐喊,有没有产生悲怆之情。也不知滩涂上的小蟹、弹涂鱼是不是钻在洞中,还是惊慌失措地逃向了外侧的海中。即使逃了出去,没有滩涂,它们该如何生存?那些海瓜子、香螺、泥螺、望潮,只能在砂石的倾倒声长叹一声吧,就被没头没脑地压在底下。我也不知潮流是不是改道,会不会影响鱼蟹虾的洄游,更不知大海有没有痛楚,有否怀恨在心,意图报复。
我只觉得,临港工业的发展,必然要利用滩涂,这是很自然的。滩涂的被利用,也恰恰说明了它有被利用的价值。假如滩涂涨潮时被海水淹没,退潮时露出灰蒙蒙的一片,还不是废地?何况滩涂就是滩涂,对潮汐的影响该微不足道吧。即使被填埋,也如剥了海的一小块皮肤,毫不伤筋动骨。只是以后小鱼小虾、贝呀螺呀恐怕要减少,价格要高,可这与发展经济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经济的发展哪能不付出一定的代价?
每次去察看项目的进展情况,看到滩涂上围填得平整包满的样子,油然称赞进展得顺利,鼓励企业抓紧施工,早日投产。当一栋栋钢结构的厂房闪亮现身,一座座的龙门吊高高矗立,一只只的船台长长铺卧,我心里涌现的是一种美滋滋的欣喜。
现在想来,也算是屁股指挥脑袋吧。在那个位置上,只有一门心思地去发展经济,而刚巧恰逢临港工业的发展期,不利用滩涂,又哪能大力发展临港产业?我的规划,我的布局,我的全力支持配合企业的发展,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行。利用滩涂作为工业用地,也没有多少人在意,仿佛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海岛人习惯了滩涂的被填埋。
从担任副县长到现在,我已转岗了两次。许是意识上有所转变,许是静下心来在回望过去的岁月,许是感到海产品价格的大幅提高,甚至有些贝类鱼类的影子已难以见到,我不由想到了滩涂。
没有了滩涂,后悔吗?我自问。仔细想想,似乎未曾想过。后悔吗?我当真难以回答。此一时,彼一时,一切都在变化,让我如何回答呢?
只是现在,我却在寻觅滩涂的踪影了。
四
滩涂还是有的,却是新生长出来的。
在岛北部仇家门大坝的东侧,一大片滩涂横卧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粗大的堤坝将仇家门湍急的潮流硬生生地拦腰斩断,目的是为了形成淤积,也将对岸悬水的双合岛连接起来。至八十年代末,这里便淤积成了六千亩的滩涂。近年,在其外侧的东垦山、西垦山两座小岛间又筑堤相连,仇家门滩涂的淤积也越来越快,越积越厚。
早些年,那一片的滩涂上有人在采贝或拾螺。后来,又用淤泥堆叠起一棱棱的泥坝,围成方形,搞起了滩涂养殖。据说,是专门养殖海瓜子的。海瓜子的繁衍期为夏日,秋冬时节的肉就瘦下来,便无人去采。有了养殖的,怪不得冬季也能吃上海瓜子。再后來,滩涂被淤泥越挤越紧,渐渐增高,臃肿起来样,连海水也只是轻轻地拂一下,便匆匆地退回去,就失却养殖的价值。
如今,仇家门的滩涂已是芦草丛丛,几乎成为一片绿州,更显湿地的绿意。若干年后,这一方滩涂或将与东垦山、西垦山之间的堤坝相连相拥,形成一万多亩的绿色滩涂。然而,围填出来的滩涂是用来储备土地,增加发展空间的。一旦有了新的大项目,这一方滩涂或许又将消失。
仇家门大坝的建设,据说影响了岱衢洋大黄鱼的洄游。岱衢洋的大黄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仿佛集体失却了影踪,退出了东海洄游的舞台。
面向岱衢洋的东沙古渔镇还有一处叫铁板沙。
说是铁板沙,我一直未曾见到过沙子。我只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这里是渔用码头。岱衢洋捕捞上来的大黄鱼,大多被运输到铁板沙码头,渔船在此卸货、销售、补给。大黄鱼最旺发时,岱衢洋上渔船云集,最多时达一万多艘。小小的铁板沙码头被挤得水泄不通,桅杆林立,篷帆片片,整日整夜地忙碌着。镇里的横街就在一百多年前形成了远近闻名的鱼市,一家家的商铺挤满街道两侧,石板路天天潮湿样的,鱼腥气久久萦绕在街道的上空。
但如今连渔船的影子也见不到,铁板沙也被抛弃似的,无人问津。现在,早已淤积成滩涂,几片芦草郁郁葱葱样的,形成小小的湿地景观。
不过,总算让我见到了滩涂,像见到久违了的朋友,触手可及,那样亲切,那样欢欣。然而过后,心里又有点酸楚。那滩涂可是曾经如此繁忙的码头被废弃以后才形成的,要是大黄鱼还年年在岱衢洋洄游,这铁板沙还会淤积?
五
据史料记载,元大德年间,即七百年前,这里的岛上就开始筑堤,“始得为田之举”。清康熙年间,各岛均有土塘和塘脚。乾隆年间,又在岛上筑念母岙大塘,长三百五十丈。之后,一条条的海塘在岛的周边不断兴建。在那经济和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能筑海塘的地域,即为滩涂。一条条的海塘内,成了一处处人们的家园,也成了一块块盐地、农田。海塘外,渐渐地,又淤积成新的滩涂,诸如念母岙沙滩头的滩涂一般。后来不仅将滩涂填埋,而且十廿米深的浅海也成为了围垦的对象,硬生生的在海上造出地来。岛在膨胀,海在缩小。
过去,我知道哪里有滩涂,滩涂上总有人在跋涉,在躬着腰采拾,海瓜子、蛤蜊、香螺、泥螺等被源源不断地拿到菜场上出售,都是野生的;也能见到长长的串网、地笼网卧在滩涂上,里面定然会有许多的小鱼小虾。现在,我在岸边、海塘边见到的大多是黄浊的海水,即使有滩涂,也已芦草丛生,或者随时要膨胀开来似的,与过去的截然不同。
过去,我看到的滩涂洋洋洒洒地平躺着,任它潮涨潮落,也不必顾虑它的自我扩张,它就是海的一部分,那样自然地延伸在岸线和堤坝脚下。现在,曾经的滩涂上,已是一座座的码头,是一幢幢簇新的房屋,是一个个养殖塘。
好在,如今,一些围填海项目据已被叫停,对违规用海的项目,也已一次次的督办整改。
滩涂终于可以不再悲凉。让它使之紧依山脚,自在生长,潮涨似海,潮落成涂。阳光下,湿乎乎的滩涂如一幅温情的泥绸,镶嵌海边,不离不弃,透出一缕缕咸腥的潮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