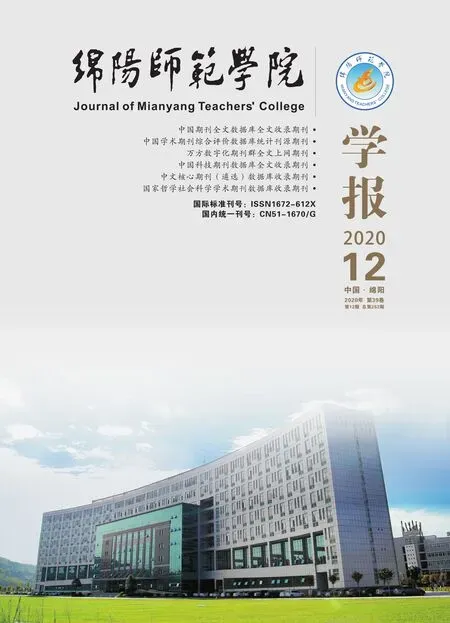中国生态美学之“浑然与物同体”说
李天道,魏春艳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成都 610066)
这里所说的中国生态美学,应该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于与西方的生态美学平等对话,既受西方现代生存论美学、生态美学等的影响,又浸润传承着中华古老文明精髓的、极具中国元素、民族特色的一门学科。这样一门学科的建构,其旨意在于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吸取其中的文学审美智慧,接续其思想的脉络。这一经由传统文化滋育出的、极具本土特色的中国生态美学,具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传统。正是基于这种传统,中国生态美学突出地呈现出一种极具中国气派与中国精神的风貌。这种精神风貌在“天人地”有机互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浑然与物同体”、“生生之为美”、“仁者天地之心”、“与天地合其德”、“天人感应”、“为仁求仁”等命题中有充分体现。由此,中国生态美学是从“天人”相与合一、交感构成,“天人”间为“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来探讨基本的文学问题的。在中国生态美学看来,作为“生命共同体”,“天人”,即“人”与自然是“合一”的,体现于生态美学中,则文学美与人性美是和煦一致的。所谓“明天人之际”,就是要求懂得“天道”“人道”及“天人”相与合一、交感构成的关系与审美诉求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生态美学话语体系建构来说,回头、反过来思考、研究、阐释中国生态审美智慧、环境美学思想,寻找中国古代生态美学的思想资源,结合中西方的生态美学理论,以建构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的、“人”与“文”和谐圆融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是极为重要与有益的。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考虑到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人”言说和行动的产物,为今天提供了理解审美实践的视角和建构当代生态美学的文化资源与工具。因此,在建构当代生态美学话语体系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尤其必须考虑到中国古代的生态美学思想,如此建构的中国当代生态美学才是具有民族文化性格与特色的生态美学。越具有中国特色则越具有全球化色彩,因此,为重新建构当代生态美学,必须挖掘和深入阐释传统生态美学思想,以丰富当代美学智慧,实现中西方生态美学交流。中国生态美学以“天人一体”“天人不二”“一阴一阳之为道”“道法自然”等为核心思想,在审美理想上追求“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在审美诉求上则推崇“浑然与物同体”“致虚守静”“无为无不为”“亲亲”“仁民”“爱物”“致中和”等等,对当代生态美学学科的开拓、生态美学的发展以及话语体系的建构与理论形态的确立,都至关重要。这里所谓的“审美诉求”,即“人”的一种诗意化、审美化生存态与发展变化诉求。在“天人”生命共同体中,“人”的审美诉求应该是多样的,审美的存在态势乃是“人”的一种最佳生存态势。中国生态美学主张“人”应该保持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化、诗意化审美诉求,“以天合天”,“顺其自然”,“浑然与物同体”,以更好地与自然万物相亲相和,相依相成,诗意栖居。“人”的审美存在态势乃是为了更加适应“人”的生活。“人”的生成发育与天地自然密切相关。“人”来自自然,源于自然,为“道”所生成,与天地自然为一“生命共同体”。因此,“人”的存有态势应该顺应天地自然,相互依存,即“人”应该与“道”合一,遵从自然,与之相适应,“如其所生”,“顺其自然”,“浑然与物同体”,“同于大道”。这里仅就“浑然与物同体”所规定的审美诉求问题进行阐释。
一
中国生态美学洋溢着一种盘然生意,就创作者而言,应该以仁者情怀,与物同体,诗意地创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自然万物皆备于我。二物有对,以己合彼,始终不可能契合无间,也不可能圆融无碍,如是,能不能达成“浑然与物同体”的境域则成为诗意化、审美化生存活动追求的极高审美境域。
从诗意化生存活动审美追求来看,所谓“浑然与物同体”境域突出的呈现为“与物无对”。“无对”,即物我无间,物我一如。在审美化、诗意化生存活动中,“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天人一体,圆融和熙。必须指出,“浑然与物同体”,不是一种“以己合彼”、以人合物的态势,而是两者浑融为一、动静一如、内外合一、相互依存的生存流,在这种浑融一体的态势中,进而达成“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也就是“自然万物皆备于我”的态势。这种态势下,“我”就成为了与天地自然万物浑融一体的“大我”,当真正实现这种“与物无对”的“大我”境域时,再来反观自己,便会感到一种至大之乐,也就是实现了这种“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境域时的至大之乐。生生之仁、盎然生意、“以天合天”、顺其自然的态势对于生态审美具有重要意义。只有“齊(斋)以静心”,“不敢怀庆赏爵禄”[1]659,排除外界的干扰和杂念,超越“非誉巧拙”,不再心存非议、夸誉、技巧或笨拙的杂念,淡却利、名、我,“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忘物忘我,“巧专而外滑消”,致使心灵进入“无待”的境域,澄明本真纯然之心性,才能以“人”之本真自然之“天性”与“木”的自然本然“天性”相应相合,以“天性观天性”,以天观天,“以天合天”,“浑然与物同体”,进入这种审美诉求,才能创作出鬼斧神工、与自然相合、与天工同化的出神入化、“见者惊犹鬼神”的“鐻”。显然,以此类推,“天人”之间,“人”在维护与自然、社会的生命共同体关系中,要致使其生存活动诗意化、审美化,也应该营构出如此之审美诉求,顺其自然,“以天合天”,“浑然与物同体”。“以天合天”的“天”,其意旨应该为“自然”、本然,即“人”之自然心性,或谓本然属性。如冯友兰所指出的,这里的“天”,意指天地万物的自然属性,而与此相对的“人”,指人为[2]302。也就是说,“以天合天”之所谓“天”,为“天性”“本性”“真性”;万有大千,一切任运,无为而无不为,尽皆真性自然呈现,自然而然,无为无造,天然如此。
对此,正如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所强调指出的,“《庄子》中的很多‘天’字,郭象《注》皆以‘自然’释之。在‘自然’一词的本身意义上,郭象与老庄有出入,但在以天为自然的这一点上,大体上是对的。而此处之所谓自然,即老子之所谓‘道法自然’的自然,亦即是道。所以他在《齐物论》中之所谓‘天钧’、‘天倪’,与他所说的‘道枢’实际上是一个意义。因为他常常好以‘天’字代替‘道’字。庄子所以用天字代替道字,可能是因为以天表明自然的观念,较之以道表明自然的观念,更易为一般人所把握”[3]329-330。也就是说,庄子所谓的“自然”,就是老子所提出的“道法自然”之“自然”,也就是“道”。由此看来,“以天合天”,就是“顺天”“循天”“浑然与物同体”,也就是一种诗意化、审美化审美诉求。“顺天”“循天”“以天合天”,不把“人”的意志强加于“天”去改变规律,而是掌握自然规律,并利用它为自身服务,即“知天”“顺天”。这里的“顺”也就是顺其自然,是通过掌握技术和规律,“以天合天”,使生命更加顺遂。从“顺天”“循天”到“知天”,以知道“人体”的生命密码。了解“人体”的生命信息,“认清”自己,以更好地顺应自然,调整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以效法天地,“合天”,更好地为自身服务。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万物赖天地以诞生,遵循天道四时,万物始得以顺利生长。提倡“以天合天”“顺天”“循天”,“浑然与物同体”,符合今天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美学精神。“人”与自然共生并存,崇拜自然,敬畏自然,顺应天意,“人性”与“天性”相融相合,善待自然,“以天合天”,其实质就是“顺天”“敬天”“尊天”。
在中国生态美学中,“天”,其符指意之一就是“自然”。从这样的意义出发,应该说,所谓“天人”,即天地自然与“人”;而“天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与天地自然间的生命共同体关系,则一直是关乎“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永恒命题。中国生态美学把“天地人”看成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每一个物种都是这个有机生命体的构成部分。天地万物的发生同源于“道”。“道”本性自然,这种本性、天性决定了其对事物的作用不在事物之外而在其中。“天人”关系的和谐有序,必然是以“人”与“天”,即“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合理的规范与节度,即遵循“以天合天”的审美诉求为前提的。如此,则“人”与“天”、“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才能各遂所欲,各得其情,和谐共存。因此,老子指出,“人”应该“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4]103(《第二十五章》)。“法天”之“天”,就是自然,自然而然。在中国生态美学中,“天”“地”“万物”皆符指“人”之外的“自然”,而所谓的“天道”则指的是“天”“地”“万物”生成与化育的规律,或谓自然规律。“道”的自然本性使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受外力的干扰而呈现其自然状态,天地万物皆因其自然本性而存在和运动。顺应自然便是顺应“天道”,而顺应“天道”就需要“无为”。但是,“无为”绝不是一味地排斥人为,它所排斥的只是违反自然而随意强加妄为的那种人为。因此,“无为”实质上是要求人们遵循事物内在的法则,按规律办事。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仍是顺应自然。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应遵从天道,顺应自然,才能“无为而无不为”。“无为”的意思就是不做违反自然的事,亦即不固执地要违反事物的本性,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79(《齐物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1]694(《秋水》)。“人”只是天地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因此,必须尊重自然,维护自然的完整、稳定与和谐,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彼此尊重,协同并进,美美与共。庄子指出,人生的最高意义就在于把握好“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洞悉“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自觉地追求“人与天一”的“道”境,“浑然与物同体”。只有达到“天人合一”和“浑然与物同体”的审美域,才会自觉地放弃征服自然的活动,并且以审美的鉴赏态度去体味“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之美。“道法自然”之“自然”,即本然,也就是万有大千本身圆融自足,如来去之自然真性。所谓的“天”,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意思,是与“人为”相对而言的,“自然”“天然”“天生”的意思。也就是说,所谓“以天合天”的“天”,就是“天性”“生性”。一般说来,前一个“天”,其意指应该是“人”的“天性”,即“人”之本然、自然、天然的属性;后一个“天”,则意指“木”的天性,也就是“物”的自然、纯然、由然的本性。所谓“合”,意指“人”的自然天性与木材的自然天性的相合,但需要指出,这里的“合”,并不是简单的、一般的相加与结合,而是说“天”与“人”具有一种“天性”相通的内在联系,具有一种一体相依的一致性,或有同一种生命元素,或有同一种生命因子。就生态美学意义看,“以天合天”,“浑然与物同体”,就是在“天人”生命共同体中维护“人”与自然生存圆融和熙、相依相成关系的体现。即如郭象所解释的:“必取其材中者,不离其自然也。尽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1]660(《达生》)所谓“不离其自然”“因物之妙”,也就是说,“以天合天”是顺其自然,就是指“人”顺应木材的自然天性、依凭物本身的“妙”来“为鐻”,即砍斫、雕刻。对此,林希逸也解释云:“观木之天性形躯,若现成者,然后取而用之,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而已。……观夫木材天性合鐻形者,然后加手,则用力少而见功多,此器之所以疑神也。”[5]276王先谦解释云:“以吾之天,遇木之天。”[6]188显然,他们的解释与郭象的看法相同。第一个“天”,即所谓“我之自然”,“吾之天”,也就是“人”之自然天性;第二个“天”是“木之天性”,“物之自然”,“木之天”,即木材的自然天性;“合”即这二者之“合”。换言之,“以天合天”之所谓“天”,是指“自然”。所谓“以天合天”,即以自然之天性合于自然、本然之天性。万物自然和“人”一样,都是依照自己的本性而生存的。因此,在“天人”生命共同体中,“人”必须“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尊重万有大千的自然本性,而不能以“人”的价值观念去衡量一切、剪裁一切。所谓“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就是“以天合天”的具体内涵。按照自然万物的本性去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这个叫“以天合天”,以致“浑然与物同体”,“天人合一”。
“以天合天”“浑然与物同体”说应该是中国生态美学所推崇的一种诗意化、审美化审美诉求。这里所谓的“天”,就是“天性”,“天性”自然、本然、纯然、旷然、渺然、悠然。具体而言,“以天合天”,即通过“天性”的还原,原初本真心性的敞亮,而彻底忘掉物我、是非差别和道德功利的念头,而去蔽存真,达到与“天”同一的审美心态。在生存活动中以如其所生,以“人”之天性合于事物之本然,在有限中把握宁宙无限的生机,与审美对象在精神意念中沟通契合,把握对象的内在神态和意蕴。排除一切人为意念,在忘我、入神之中,质性形态合一,即排除一切人为与作为,恢复自己的本然天性,并以这样的天性合于物的天性,从而达到审美极境。“天”是自然,自然就是“美”,万物化生化合,本乎自然,宇宙间万有大千,尽皆自然而生,本性自然,“人”也只有归复自然天性,才能更好地感受生命,认识自己,才能与万有大千之自然“天性”相合,以察天机,深契生命之真趣,感悟“生命”的真谛,进而维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圆融关系。同时,这种对“生命”真谛的感悟源于“人”对“天”,即万有大千之本真自然态的遵循。也就是说,审美生存活动中,最高审美域的达成应当是“人”“天”间的合一互动、一体交通,即“人”的审美生存之极致体验与本源性世界的本真敞亮。换言之,即应该是“天人”间的同一化、一体化。依照“以天合天”“浑然与物同体”的审美诉求论,“天”乃是“美”的本原,由“人”之“天性”合于万有大千之自然属性,始能够达成“合天”之审美域,以获得生命的真谛。“合天”审美域的达成,生命共同体的还原,必得“返朴归淳”“致虚”“守静”,敞亮原初本真心性,任心随意,顺应自然,自由自在,自适自得,悠然陶然,即境缘发,触目道成,以获得直观感悟,通过“返身”“归朴”,“复归”到“深心的自我”,以达到真力弥满、气势恢宏、含而不露。万千滋味,尽在其中,兴到神会,超脱自在,从而在“天人”生命共同体中体验自我,实现自我,顿悟天地生命奥妙的审美境域。也就是说,“以天合天”,是“人”之本心、本性的还原,是去蔽存真,致使“人”之心性归复于原初纯然、本然之态,从而在审美创作活动中以天然纯粹之态势关照自然万物。如其所是,“以天合天”,对生命本真的审美体验活动才能深入,“天人”才能有机结合起来,“天人合一”,进而“天人一如”,“天人一体”,“浑然与物同体”,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合一。
在中国生态美学中,就某种意义层面看,“天”“道”“自然”“太极”等,应该是并列的,都是“美”之本原。“道”与“天”“地”“人”乃是宇宙间的“四大”。庄子所谓的“大美”,就是生成宇宙间万有大千的“道”所呈现出来的“美”,“道”之“美”即为“大美”。即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指出的,隽永不朽之经典之作,“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7]2-3。这里所谓的“道心”“神理”,应该就是蕴藉于天地间的生命奥秘,为“道”“天”之生命活力所在,也是“美”之本原所在,因此,审美活动中,就应该“原道心”“研神理”,“人”与“天”合,“人”同“道”俱。故而中国生态美学主张,“含道应物”,强调在澄净空明的审美心态中去体味蕴藉于自然万物中的“道”,主张“体道”,“悟道”,“与道合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所谓“外师造化”,则以“人”之生存的自然万物为师,互动互学,穷尽宇宙大化的神变幽微,以陶冶“人”的内心,“天人”交相构成,以进入极高审美域。即如王夫之所指出的:“天地之际,新故之际,荣落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危,形于吾身以外者,化也,生吾身以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际,几与为通,而悖然兴矣。”[8]68“人”之外,万有大千,化生化合;“人”之内,“求道”乃至“悟道”的心坚固,念念不息;“心”与“物”、“人”与“天”、“意”与“象”、“情”与“景”之间,“相值相取”,内外相通,“几与为通”,“人”通过去蔽,澄明自身纯真之心性,以心灵映射万象,用心灵节奏去契合宇宙间的生命韵律,天人交感,乃审美活动所追求的极致。“以天合天”,“浑然与物同体”,自然天性为“美”之所在,审美域的构成在于“人之天”与“物之天”的交相感应、相互融合。具体分析起来,其融合构成既是由“天”至“人”,又是由“人”达“天”,“天人”间生命体的有机互动、交相往返、互融合一。所谓由“人”达“天”,即如《中庸》所指出的:“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9]1632“人”澄明自身至真至纯之本性,就能辉映万有,照彻宇宙万有的生命原初域,以深契宇宙万物的生命底蕴,“以天合天”,“与天地参”,达成“人”与生存间互动合一的最高审美域。“人”原初本真之“仁心仁性”的澄明,尽心知性,则能够参赞天地之化育,以达成“浑然与物同体”“天人合一”之审美域。“人之天性”与“自然之天性”是相通相似的。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人”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将“仁心仁性”扩展到自然,既“尽人之性”,又“尽物之性”,顺应自然,则能够达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域。庄子曾经强调指出,“人”与“天地”间的关系是“并生”的,“万物与我为一”[1]79(《齐物论》)。因此,“以天合天”所达成之“天人一体”审美域,给人带来的审美愉悦乃为一种“天乐”“至乐”。这种审美愉悦是与“天”相合、一体共生所带来的至真至纯的快乐感,能够给人一种“物我两忘”的感受。此即所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1]735(《天道》)。“天乐”是“人”与生存间互动合一所获得的审美愉悦,是“以天合天”的审美结晶,即人与自然合一的情感体验结晶。中国生态美学所谓的“曾点之乐”“孔颜之乐”“圣人之乐”“贤人之乐”,其实质,就是通过“以天合天”以获得“天乐”“至乐”,亦即“人”的心灵世界与“人”之生存间圆融和熙所带来的审美化、诗意化体验。所谓“闲来无时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其传达出来的审美意蕴就是“人”在“以天合天”的“静观”中所到达成的自在自由、“鸢飞鱼跃”的审美境域,以及于此审美域中获得的一种审美体验或感受,为“人”之感性生存向审美生存的转化与仁心仁性的澄明和敞亮。“达天”“合天”乃中国生态美学所追求的至高审美域,由此,始能够致使“人”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并实现同宇宙的一体互动。在中国生态美学看来,要达成“合天”“达天”之审美域,必须让“人”的意识审美化,即“人”应该进入到“以天合天”的审美诉求,进而于“以天合天”“天人一体”中“体道”“合道”“悟道”,感悟天地生命意旨,并致使其生动到审美体验层面,以审美化、诗意化的生存方式来融汇“天人”,“浑然与物同体”,来维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相依存。这种“人”之意识的审美化,突出体现了生命体验活动中澄明心性,“反朴归真”,回归原初纯粹本真心性的意义。即如老子所指出的,要体认到无形无象的,作为宇宙间生命生成原初域的“道”,“人”必须“致虚极”“守静笃”,通过“抱一”“守中”“涤除玄鉴”以保持“虚静”的审美心胸。通过此,才能达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相依存审美域,而致使“人”的生存审美化、诗意化。《庄子·大宗师》云:“隳支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这里所谓的“大通”,即“道”,“同于大通”,也就是“人”与物相融相合,还原到生命共生体,没有了自己与外物的对立,身与物化、与物相游,“同自然之妙有”,“浑然与物同体”,“天人合一”的生气流畅之域。这种境域是“人”摆脱尘世杂念、心灵自由的生命状态。就审美活动而言,由此才能于“寂然凝虑”中“思接千载”,于“悄焉动容”中“视通万里”,以上天入地,包孕古今,达成“天人合一”之审美域。这种审美活动,也就是“以天合天”。
按照中国生态美学的意旨,“天人一也”,即“天人”间为一生命共同体。因此,要进入“以天合天”的审美活动,“人”必须保持心灵的自在自由,去蔽存真,归复“天性”,以“人”之“天性”与自然万物之本性相互合一,“同于大通”,由“人”合“天”。所谓“万趣融其神思”,“人”必须要将自我渗入宇宙大化中,心随物以宛转,物与心而徘徊,在“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生命体验中获得对宇宙间万有大千生命奥秘的洞见。“人”同自然间相亲相和,于“天人”同一生命体中致使生活本真自然。将“人”与自然互动共生,为同一生命体的关系,拓展到“人”与社会和熙融洽、互动共处的关系,以“以天合天”的审美化、诗意化生存方式最大限度地适应自然与社会生活。生存是“人”生存的基础。《中庸》有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10]37这就是说,自然万物和“人”一样,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万物平等,并行不悖。因此,“人”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从自然中来,终归于自然。“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必须放下征服者的姿态,秉持“道法自然”“以天合天”的理念,心怀谦卑,最大限度地去顺应万物自然,适应万物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人”的生存、社会的发展皆以自然万物为依托。“人”头上的天空,脚下的土地,清澈见底的河流,一碧千里的草原……小到一草一木,大到山川河海,如茵的绿草,潺潺流水,燕语莺啼,都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人”与自然万物皆生成于“道”,“道”乃天地万物之所从出的生命原初域,只能通过“仰观”“俯察”,通过身心体验,直观顿悟,“目击道存”。因此,中国生态美学特别强调透过对审美对象的整体直观把握,于“以天合天”“顺其自然”“浑然与物同体”的审美诉求中以“神遇”“目想”等体验方式获得对生命本真的洞见,而获得“与天和”,得到“至乐”。
二
应该说,“以天合天”的审美诉求乃是“人”的一种生存态度,一种与天地万物为同一生命体的、彻底解放的、自由的精神活动,即解脱一切外在束缚,进入到纵肆逍遥的、“以天合天”的审美化、诗意化生存活动中。“人”来自自然,与自然相依相存、有机互动,利益与共,价值诉求相同。“人”以天地自然为生存进行生命活动。“人”的生成与生存活动离不开天地自然,而天地自然则因为“人”的生命存有而获得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天人”之间休戚相关,为生命共同体。
“人”与天地自然既然属于同一“生命共同体”,而“人”又为“万物之灵”,那么,“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熙关系的维护,必须通过“人”自身的努力才能达成。“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是对自然的尊重。“以天合天”,“顺物自然”,“浑然与物同体”,实现“人”的自然性和自然的属人性的相融相合,才能“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1]735(《知北游》),进而于“天人”互动交感中相互发现、相互确立。在诗意化、审美化活动中,通过“心游”“神游”,“人”达成与自然的同一,在与宇宙、自然、天地万物的同一中,获得超越,“应之以自然”[1]502(《天运》),“欣欣然而乐”[1]765(《知北游》)。“人”与自然是协调共生的,他们之间原本就是一种平等、和谐的共生关系。复归“天然”之生命态,“自然而然”,“淡泊无为”,去掉一切生命的遮蔽,摆脱一切关系的束缚,完成生命由非本真状态向本真状态的复归,“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以虚静、本然之心与“道”合一。由保全“人”的生命渗透到保全自然的本性,“游乎万物之所终始”,“通乎物之所造”[1]634(《达生》),“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1]462(《天道》)。在“以天合天”中,真切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并在与万物自然的交流中,“乘物游心”,以获得自然生生不息的活力,而感受到与宇宙自然同为一体的永恒、不朽,“与天地和”,回归至创造性生命的原初,“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相合补充,共同完善。所谓“神与物游”,就是一种“以天合天”的审美诉求。“以天合天”审美活动中的“神与物游”,一方面是以心物互渗来实现心与物的同形同构或同质同构,彻底消解“天人”间的屏障,归复原初“天人”生命共同体,从而使对象结构与生命结构具有相似之处或契合点。同时,“神与物游”其呈现态就表征着“人”之情、意、趣,与“物”之景、象、物间的相互依赖,获得“合天”“悟道”,必须通过形而中的审美“观气”活动来完成。完成“人”之形而下的感性观照,并进而向形而上的,对生命真谛的洞悟飞跃。因于“气”的中介,“人”得以入乎物内、游物游心、神与物冥。因此中国生态美学推崇气势,标举气韵,崇尚空灵。“以天合天”“天人合一”“浑然与物同体”审美诉求与同一之所由,因而“天人”本为共同生命体,审美化活动中注重“以天合天”“天人合一”,追求“天人”生命共同体的还原,同时也重视一方对另一方的主导地位或超越性关系。“道性自然”,因“道”而生成的万事万物本性自然。这种本性使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受外力的干扰。天地万物皆因其自然本性而存在和运动。顺应自然便是顺应“天道”,而顺应“天道”就需要“无为”。但是,“无为”绝不是一味地排斥人为,它所排斥的只是违反自然而随意地强加妄为的那种人为。因此,“无为”实质上是要求人们遵循事物内在的法则,按规律办事。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仍是顺应自然。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应遵从天道,顺应自然,才能“无为而无不为”。“无为”的意思就是不做违反自然的事,亦即不固执地违反事物的本性,而应该通过心物互渗,来实现心与物的同形同构或异质同构,彻底消解“天人”间的屏障,从而使作为审美对象的天地万物之生命结构与“人”的生命结构具有相似之处或契合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形容》谓:“俱似大道,妙契同尘。”“道”“大道”既是“人”与天地万物生成的原初生命域,又是“天人”相通相融的中介。“俱似大道”,就是以“人”之“道性”“天性”与万物之“道性”“天性”相合,“以天合天”“浑然与物同体”也就是以“人”自然之天性合于万物自然、本然之天性。万物自然和“人”一样,都是依照自己的本性而生存的,因此,在审美活动中,“人”必须“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尊重万有大千的自然本性,而不能以人的价值观念去衡量一切、剪裁一切。所谓“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就是“以天合天”“俱似大道”“浑然与物同体”的具体内涵。
按照自然万物的本性去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这个叫“以天合天”“俱似大道”。所有这些不是建立在双方的冲突或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的基础之上,而是从双方相融相合的关系中生发出新的“俱似大道”“同于大通”“以天合天”“天人合一”审美诉求来。正是由于“以天合天”“俱似大道”审美生态论的渗透与浸润,使得中国生态美学从本质与形态上看都呈现出一种自然直观性。这是从整体性、有机性、共生性来理解宇宙及万物关系,追求“人”与生存间互动合一。可以说,“以天合天”“俱似大道”“天人合一”审美诉求论构成了中国生态美学的基本特征。“以天合天”是以人合天,“人”依照自身存在的天然属性,去适应自然,复归于自然,复归于“道”。“以天合天”“俱似大道”是以“人之道”顺应于“天之道”,即以人合天,天人和谐,“浑然与物同体”。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所达到的一种审美域,“人”与生存间互动合一,“人”与“天”同归于大道自然的目的。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恒德乃足,复归于朴。”[4]112-113(《第二十八章》)知道它的雄,持守它的雌,成为天下的溪流;成为天下的溪流,永恒的德不会离失,复归于婴儿的状态;知道它的白,持守它的黑,成为天下的模式;成为天下的模式,永恒的德不会差忒,复归于无极的状态。知道它的荣,持守它的辱,成为天下的川谷,成为天下的川谷,永恒的德才会充足,“俱似大道”,“同于大通”,“浑然与物同体”,即复归于原初纯朴“天人”生命共同体中的状态。
就诗意化、审美化活动而言,要“俱似大道”“同于大通”,则必须“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且要善于以雌御雄,以黑御白,以辱御荣,而把握万物的全面(整体),得以“与道合一”,从而便宛如天下的溪流,宛如天下之模式,宛如天下之川谷。溪流者,以其柔弱低卑,而百川众流自然归趋,这样永恒之德不会离失。复归到“人”之生存之初的赤子、婴儿状态,“精之至”,“和之至”,阴阳太和,“以天合天”,“天人合一”,从而深根固柢、长生久视。复归到“大道”,还原万物的本初无极,玄德无极,以大顺自然。于是“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4]140(《第三十五章》)。川谷者,以其谦虚卑下,而为涓涓细流所汇聚,这样永恒的德才会充足,复归于“大道”,回复“天人”生命共同体的始初纯朴,达成“与道合一”之域。由于能把握大道的整体,复归于本真自然的状态,从而实现“人”与“天”合一、“天人一体”、“浑然与物同体”的审美化、诗意化生存,实现“人”与“天”、“俱似大道”、“同于大通”之功效,即纯任自然与天地生命共融。“浑万象”,“兀同体”,超乎是非荣辱之外,“超脱自在”。这应该是“以天合天”审美诉求论的特殊体现。
基于“以天合天”的审美诉求论,以“人”与生存间互动合一为贵的信念,中国生态美学往往把与世界的“外适”和导致身心健康的“内和”作为“人”之生存的最大审美愉悦。“外适内和”,可以从中获得身心俱适、恬淡自甘的一种审美感受。“内和”,重在心灵的平和恬静,感受到一种超然物外的情趣和乐趣。包含着中国生态美学所推崇的“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美学意义,也就是“养志忘名”“从容于山水间”“天人合一”的最高审美域。“以天合天”,“人”与生存间互动合一是自然的最佳审美诉求和终级状态。中国生态美学一贯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动静的统一,推崇淡泊、平和、清新、幽远的生存方式。“人”与自然相亲相近、相依相成。审美化生存活动中,“人”与自然万物间互动合一,通过“以天合天”,“人之天”与“物之天”相通相合进入“天和”常乐的至境,乃是“人”之生存的最佳选择。应该说,“以天合天”“浑然与物同体”是“人”自觉遵循的审美诉求与自然审美观,源远流长,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带有强烈的地域化、民族化色彩。“人”与“天”本来就相依一体,“人”在“天”,即自然生存中生存,就要主动把自己融入“天”之中,达到“以天合天”、“天人”共生同体中的审美化、诗意化生存。“人”从对自然的敬畏到与自然相亲相和,“敬天”,“顺天”,进而达成“以天合天”的审美诉求,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审美实践过程,是“人”追求生存空间诗意化、审美化的生动体现。“人”和生存是不能分离的,“人”生存在土地上,食用土地上长出的东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当然应该适应生活,顺乎自然,努力维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遵循“以天合天”“天人合一”的审美诉求论,保持“人”与生存间圆融无碍,则能够出艺术杰作与精品。
在现代社会,工业化进程加快,“人”与自然间的融洽关系被打破,相互间日渐隔膜。在此背景下,依据“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重新审视中国生态美学“浑然与物同体”审美诉求论,以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系统性生态美学话语体系,以之规范“人”的行为方式,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增强人生的诗意化、审美化,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生态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