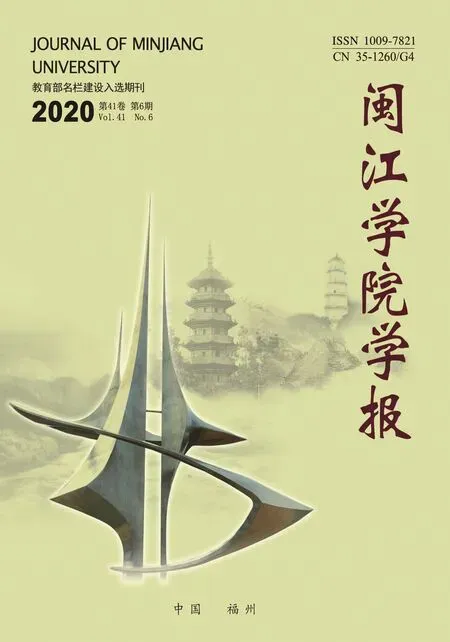再论冰心的女性主义思想
黄长华
(闽江学院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冰心是“现代中国女作家的第一人”[1]。20世纪90年代,“冰心是否具有女性意识”以及“冰心女性意识的实质”问题再次引发了争议(1)孟悦、戴锦华、王侃、盛英、刘思谦、姚玳玫、李玲、林丹娅、任佑卿等都先后发文阐述对冰心的性别意识、女性意识的分析。,肯定者认为:冰心的性别意识始于“她对‘自我’的探究”,而母爱歌颂、家庭意识、兼具“新思想旧道德”特色的道德观、婚恋观是冰心女权思想的主要表现[2];“冰心对现代新女性的构想尺度,乃是把她置放在能够更完美地充当家庭传统角色的位置上来要求”,“从冰心系列‘问题小说’来看,冰心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接受过现代教育,拥有现代知识的女性;她们寄身所在的理想环境是不受旧式父权大家庭拘束的小家庭结构,这些都表明了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指向的某些一致性”[3];冰心等现代女作家的写作乃“纯然女性化的文学书写”,“‘空白之页’上的女性书写”[4]。以批判眼光审视冰心女性书写的声音也不少,《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就颇具代表性。该书用“长不大的女儿”来标识冰心,认为她所有写作缺乏“女性的自我评判或自我分析”,“她那滞留于前俄底浦斯阶段的女性意识萌芽,不足以满足她作为一个性别社会中的女性自我确定之需,而她的全部文化积蓄中又没有任何一种发自女性自我或促生女性自我的既成观念”[5]75。有的将冰心创作归属“闺阁文学”,认为她的作品“母爱”与传统 “妇德”达成同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女性意识的一种退步”,“不具有现代性内涵”,背后有深刻的男权意图(2)参见王侃《历史:合谋与批判——略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王侃《〈冰心性别意识辨析〉的辨析》(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徐坤《现代性与女性审美意识的转变》(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等。
综上所述,冰心作品所体现的女性意识值得再进一步探讨。冰心有意忽略两性的对抗性,而强调女性自我反省、自我成长的自觉性,书写女性生活、女性经验成为冰心创作中的重要内容。出于对塑造不同阶层、不同个性的女性形象以及对如何成就“‘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6]3,即对如何成为一个具备“真、善、美”(3)冰心在《关于女人·后记》中高度评价女性,认为她们具备这世界“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冰心在思考现代女性人格建构问题时是以“真、善、美”为出发点的。之美好品质的现代女性人格建构问题的持续关注,冰心用数量不多、篇幅不长却主题丰富的成熟写作建构了一部冰心话语式的“女性经验的史诗”[7]。尽管有人坚持认为真正的“女性写作”是批判性的[8],然而,建立在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化修养之上的女性作家用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话语来表达对世界、生命及性别关系的认识、探索,是否也是具备一种女性意识呢?作为一个接受过教会学校教育和新文化运动洗礼,且有留美游欧背景的现代职业女性,冰心思想结构里的“女性意识”的与众不同之处何在?
一、女性生活、女性经验的发掘与书写
冰心不是一位擅长表现“宏大叙事”的作家,她的写作自觉摒弃高于现实的传奇性和想象性,主要是“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9],对妇女问题多有涉及。尽管也曾对女性生存处境予以关注,如《最后的安息》就颇关注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小说采用全知视角,借助到城外消夏的小女生惠姑的见闻,描绘乡下小女子翠儿的悲惨遭遇,直接将导致翠儿惨死的根源归结为可恶的童养媳现象及普通民众,特别是乡村妇女的愚昧残忍。但太过惨淡的女性生存现实显然不是冰心小说表现的首要主题,对冰心来说,她更关心的是女性的平常生活和普遍经验。
《六一姊》和《冬儿姑娘》两篇小说的篇名来自各自文中普通而出色的女主角之名。“普通”,是因为她们与大多数女性的生活并无区别,为“活着”而劳作;“出色”,则是因为站在她们所能拥有的现实层面上,她们不怨天、不求人,勤奋善良,安稳生活。两个短篇皆以底层劳动女性为主角,并没有搭配男性角色——冰心小说中男性角色常常缺失,即便有,也多为年幼的小男孩(如《别后》)或具有女性阴柔气质的男性(如《关于女人》里的叙述者“我”)。这是否意味着,在女性人格建构问题上,冰心有意忽略男性的作用而单向度地强调女性作为?尽管对底层女性生存处境的艰辛也有轻微涉及,但小说作者的注意力显然落实在劳动女性自足的精神世界及其纯真的人格魅力方面。两篇小说以平等的视角,以理解并尊重女性真实存在的态度,呈现了六一姊、冬儿姑娘这两位底层劳动女性的平凡而自足的人生。现代作家常将出身底层、未受教育的民众与愚昧无知、丑陋贫困、性格扭曲画等号,对其报之以居高临下的怜悯或进行启蒙的冲动,如冰心这般,始终认同并赞扬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底层女性身上的美好品质并报以理解、尊重态度的作家不太多,此种“底层立场”确实难能可贵。
贞静、朴实、理智的女性始终是冰心最热衷于表现的形象。两类女性(底层劳动女性和知识女性)的生活和经验是冰心表现的重点。相较于用较长篇幅来对某个或某种类型的女性做较系统的不同侧面的描绘,冰心更擅长抓住一种性格、一个侧面、一个细节来塑造女性形象。她对女性形象的关注,并不刻意圈定于某一阶层、某一群体或某一类型,她小说里的“女性”有老有少,既现代又传统,既有智者亦有常人。这个“她”,有时是缺少教育机会的底层劳动妇女(《六一姊》《张嫂》),有时是具备新思想新做派的知识女性(《两个家庭》);有时是取得专业成就的新女性(《西风》),有时又是家庭妇女(《我的邻居》《叫我老头子的弟妇》);有时是慈爱智慧的长者(《我的母亲》《我的朋友的母亲》),有时又是聪慧严谨的青年(《惆怅》);有时是持有不同生活理念和生活态度的外国人(《相片》《我的房东》),有时是海外归来的传奇女子(《我的学生》)。这些女性既多温婉沉静之中国风(《我的朋友的太太》),也不乏沽名钓誉之虚伪者(《我们太太的客厅》)。在《斯人独憔悴》这样一篇以爱国青年受到旧式家长禁锢为主题的小说里,作者顺带呈现了一个较弟弟们更聪明婉转的女学生“颖贞”的形象。这类短篇小说,完全克服了冰心早期小说“谈理说教”的缺点,于含蓄克制的朴素描写中呈现出独具个性、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显示了其较为开阔的社会观察视界以及将生活裁剪成精妙艺术的能力。而描绘出女性作为“人”的真实才是冰心女性题材小说最重要的主题。
《三年》与《相片》特别显示了冰心用举重若轻的技巧描绘女性生活和女性经验的能力。《三年》用全知者视角讲述三位年轻人的情感纠葛,更兼含蓄地描绘了一位“完全的女性”隐秘的虚荣心。《相片》“前半部分以倒叙的方式概述施女士在中国二十八年的生活,后半部分则以顺序的方式描述施女士与养女淑贞在美国半年多的生活”[10],小说主人公施女士,久居中国,渐渐培养起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热爱,她主动关爱并收养了淑贞,及至养女长大成人,她却一反常态,制造种种借口以阻止淑贞离开,“这时的施女士无疑又是自私而卑鄙的”[11]。小说不动声色地描绘了一位融高尚与自私、贞静与守旧、慈爱与卑鄙、隐忍与刻苦于一体的女性形象,完全颠覆了常规的女性角色设定,呈现的是女性作为“人”的复杂性。
二、“理想现代女性”的预设与建构
“在所有的‘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12]茅盾此言,既指冰心写作有着自身鲜明的风格特色,也指冰心有着与众不同的思想情趣,这种与众不同集中体现为冰心努力探讨并构建“理想现代女性形象”。“冰心的第一篇论说文与第一篇小说,以不同文体的形式传达出同一个主题思想,无可置疑地显示了冰心当时最为关注的是现代新女性的形象问题。”[3]冰心曾言“女人永远是我的最高超圣洁的‘灵感’”[13],她的一系列以“平凡女性”为主角的文本实际上组织起“理想现代女性”群像。
冰心的理想女性兼具“寻常”与“超常”两种品格。“寻常”即与常人无异,正如《关于女人·后记》里 “男士”所描绘的女性,“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超常”只因为她们总是比常人多出一点东西,“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14]403。具体来看,冰心之“理想女性”的具体标准和表现是什么呢?
冰心早期文章《“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诚恳呼吁“我们女学生”[6]5做好自己,建设“第三时期女学生”的新形象,“我们所图谋的是永远无穷数千万人的幸福。他们的失败,只关系自己。我们的失败,是关系众生”[6]8。冰心之谓“女学生”,当指受到当时妇女解放新思想影响,勇敢地走出家门,接受新式教育,具有一定新知识、新思想,谋求女性权益及男女平等,行为思想有别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
冰心认为女性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她非常看重女性成功之于社会认同,呼吁新女性须谨慎行事,因为,每一位新女性成败关系着身后万千女性的成败,新女性须凭借自身努力得到社会认同以开启身后万千女性的解放。“怎么样方能作成这样的事业?就是要得社会的信仰。怎样方能得到社会的信仰?就不能没有我们自己修养的功夫。”[6]4而“我们自己修养的功夫”归结起来,即是以“实际”“规则”“稳健”的作风完全取代“空谈”“放纵”“浮嚣”的作风,建立起“欧美女学生的模范表式”[6]8。
提倡理性稳健作风是冰心设想中的新女性形象的核心。她甚少从改造社会或男女平权的角度或男女对话的背景语境来谈论新女性建设,而是选择从“女性的本能和自觉”来建构新女性形象。《“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认为“女学生”之所以招来“厌恶”,一是因为一味模仿欧美,举止失范,二是由于“推翻中国妇女的旧道德,抉破中国礼法的藩篱”,制造“种种嚣张的言论行为”及“种种可怜可笑的事实”,在行为上和道德上失范。冰心以为,新女性唯有自觉自省,行为道德合规,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她将女性取得社会认同和自身幸福的唯一出路归结为养成实际、稳健、规范的作风,做到“有彻底的新思想,还兼擅吾国固有的道德的特长”[15]。这一点,冰心可谓始终没有改变。而在小说里,冰心赞美“我的母亲”即因其“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地接受现代的一切”[16]314,甚至将她的理想女性观转化为“稳健作风=幸福浮嚣作风=痛苦”的隐性模式。《两个家庭》里,亚茜和陈太太皆是新女性,亚茜和蔼静穆,相夫教子,因而家庭圆满;陈太太,则以“尊重女权”为借口不理家政,玩乐轻浮,导致经济拮据,丈夫早逝,自己无所依靠。《六一姊》里作者对“六一姊”的赞赏和祝福也是完全出于对“六一姊”的“女儿范”的敬佩,而《我们太太的客厅》里的那几位虚矜任性、张扬造作的女性(包括太太、袁小姐、露西等)无意中都被讽刺了!
“家庭”之于冰心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五四”时期号召女性“打出(家)的幽灵塔”的风气迥异,冰心始终秉持着家庭至上观念。冰心不认为新女性能脱离家庭而获得人生的美满,没有家庭的和谐幸福作为基础,新女性的成功是无从谈起的。20世纪40年代,冰心曾写过三篇有关“宋美龄”的文章,分别是《我所见到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近况》《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有趣的是,冰心并不是从“伟人”角度而是从“中国真正伟大的主妇之一”[17]50的角度来描绘宋美龄,她赞扬宋氏“爱好文学和艺术。这一切使两个人的家庭生活美满充实”[17]55,“体现女性本能,尽心尽力让蒋主席享受家庭女主人的爱和家庭温暖”[18]67,称赞蒋宋婚姻“是在爱和理解中成长起来的完美的婚姻”[18]65。正如家庭幸福、多才多艺又服务于国家的宋美龄是冰心笔下的完美女性一样,冰心所寄予期望的新女性与传统女性迥然有别。冰心重视家庭,但她反对女性成为“家庭的依附者”,坚持女性应是新式家庭的建设者和庇护者,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圆熟的智慧,像“我的母亲”那样“热烈地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16]314。冰心认为,新女性在重新认识“贤妻良母”的立场和职责的基础上,“应该是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16]316,以沉静温柔的态度,卷起家中成员的畏惧懦弱的心。至此,“家庭”在冰心笔下不再是女性破坏和逃离的对象,而是新女性倾注心力全心维护的对象,也是新女性价值体现的所在。
概而言之,冰心笔下的“理想现代女性”形象是: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新女性,获得社会认同,作风稳健,家庭幸福。西方女性主义作家“用怀疑、激情与想象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7],冰心则很少将女性问题置于重大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她始终以一种温和清明的态度,力图在尊重女性自然人格的前提下发掘女性的个性美,将寻找女性觉醒、女性之成为自立利人之完美人格与女性的生活幸福、家庭幸福紧密联系。现实日常层面的女性生活和女性经验才是冰心小说的重要场景和重要主题的来源。
三、多重视角下的探寻与反思
冰心小说对女性生活的描绘及新女性形象建设问题的探讨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女性“我”的视角与男性“他者”的视角。这儿的“我”与“他”消除了性别冲突及男性压迫的强烈色彩,仅仅代表着性别的区分。冰心首先是站在女性“我看”之立场上来刻画完美女性的正面形象以及家庭之于女性的意义,又以“看她”模式描绘现代女性之种种,探讨新旧女性的个性差异;其次,冰心还借助男性“他看”的眼光描述了平凡女性身上的不平凡特性并反思理想女性之不易。
(一)女性“我”的视角
冰心对女性生活的关注,并非秉持外在性的第三者姿态,而是以同在性的“我”的姿态介入,这里的“我”即“现代新女性”群体中的一员。《“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一文里,冰心用着两种称谓来称呼“女学生”:称呼社会所厌恶的“第一时期女学生”为“她们”,称呼“第三时期女学生”为 “我们”,称谓的背后,隐藏着冰心对待不同时期女学生态度的亲疏远近。“第一时期女学生”,言论嚣张、态度轻浮,称之为“她们”,以示厌恶、疏远之意;而“第三时期女学生”,“要竭力的造成中国女子教育的新基础,要引导将来无数的女子进入光明”,冰心视之为同道,即“我们”。
冰心女性题材小说里的女性,如以个性特征及作者对其爱憎态度来加以区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如亚茜、冬儿姑娘、六一姊、我的奶娘、张嫂等女性,她们具备传统女性善良勤劳质朴的优点,沉默地担负起责任,不浮夸、不怨忧,以踏实的工作支持家、国,冰心认同并赞赏此类家庭幸福、人格完美的女性;另外一类女性则是陈太太、“我们太太”之流,耽于享乐、矫揉造作,逃避责任、误人误己,冰心对此是反感的,她将这类女性视为“她们”,常以审视的目光揭示她们的错与伪。
《六一姊》《冬儿姑娘》两篇的叙述者讲述的是身边人六一姊及冬儿姑娘的事迹。《六一姊》的叙述者“我”既是六一姊的童年小伙伴又是受到六一姊庇护的人,在叙述过程中时时流露出对叙述对象的好感和祝福;《冬儿姑娘》的叙述者则是“冬儿”的母亲,也以“我”的口吻叙述,总是有意无意地突出了在困境中长大的“冬儿姑娘”的优点。这样的叙述方式连带亲近友好的叙述语调,表明叙述者“我”认同六一姊和冬儿姑娘的行事作为,也表明作者对六一姊及冬儿姑娘等平凡而美好的劳动女性的认同和肯定。更多时候,冰心常以亲切的“我(们)”之视角描述家庭幸福、人格完美的女性。《两个家庭》从头到尾都是叙述者“我”对精明能干、治家有方、善教子女、事事有成以致家庭和谐幸福的新女性亚茜的褒奖。
“看她”的叙述方式是“我看”模式的延伸,也是冰心女性题材小说针对现代女性的行为做派而应用的叙述方式,在《西风》《我们太太的客厅》《相片》等篇中,叙述者不介入事件,而以外在旁观的姿态,以或关切或调侃的目光审视新女性。
《西风》的女主角“秋心”是一位人到中年的成功女性,因旅途偶遇而触发了事业与家庭的困惑伤感。小说叙述者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描绘秋心与远的偶遇情形,刻意将秋心的失落低沉情绪与远的知性体贴家庭相对照,表明事业型中年女性对错失婚姻的遗憾和焦虑。但在叙述过程中,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常常悄然转换为女主人公“秋心”的视角,从“秋心”的角度披露景致和心情的变化,感叹其如今事业有成却婚姻缺失的孤寂心境。小说的聚焦模式从“看她”(全知视角看秋心的故事)变到“我看”(秋心反省自己的人生抉择),对新女性的事业心、家庭观、中年心态予以了客观呈现,意图强调圆满的家庭对女性的非常意义。
《我们太太的客厅》虽将女主角名之为“我们太太”,叙述者其实是将“我们太太”置于“她”的位置上,以全知视角观察并描述“我们太太”周旋于“客厅世界”的情形。全知的“看她”视角包含了较丰富的信息量,不仅将“太太”客厅里的所言所为加以细致呈现,甚至解释了太太与某些人(陶先生、彬彬、露西)的关系渊源,全篇略带调侃的叙述语调表明作者对“太太”之流的反感和讽刺。
(二)男性“他者”的视角
冰心又借助男性“他者”视角强化对完美女性的敬意并反思过分强调女性自我完美的尴尬和艰辛。冰心小说引人喜爱之处在于她会别具匠心地转换视角,由写作者的女性视角转换为叙述者的男性视角,从男性的立场来看待女性,思考女性处境。《关于女人》设置了一位自诩是一位“最尊敬体贴女性的男子” 的“男士”叙述者,他总能针对社会上习以为常的男权意识提出自我批评,这部“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的小集子以“男性反思”和“理想太太的25条”开篇,一方面描绘了当时的性别文化大环境,另一方面又以幽默轻松的语气含蓄地强调男性尊重、体贴女性的必要性。
《关于女人》中的叙述者“他”,在对女性予以理解和赞美之外,更注意从广阔平凡的生活中寻找女性生活的点滴,体会具体事务中女性的优秀和魅力。他赞美办事稳健、品味高洁、遵守伦理规则的女性,无论其身处社会的哪个阶层。《我的朋友的母亲》表扬了一位理智处理儿子婚外恋并维护家庭完整的K老太太。小说设置两个叙述层次:最外层——读者听“我”叙述K老太太的故事;第二层——“我”听K老太太细谈如何妥善解决K的婚外恋情的故事。在男性视角之下,小说将叙述主动权交给K老太太,由其自序事件始末,顺带着将其性情修养、行事原则都一一呈现,而外层的男性“他者”视角补充并强调了老太太的个性:明理、机智又处事稳妥。
“他”(男士)较之以往的叙述者“我”(女性)对女性更加尊重和体贴,更欣赏女性重视爱与亲情的特性,也更加理解女性忍耐与无私的品格,甚至怜悯和同情女性的感情用事,惋惜某些女性常常“靠爱情来维持生活”[14]403。“他”注意到,那些才情与道德兼具的新女性却往往备受生活的打击。《我的邻居》中的M太太没能用自己的文学才华拯救婚姻,她有读书的才华却没有处理生活杂务的能力,虽辛苦劳作但穷困的家境始终得不到改善,频受家人的指责又只好默默忍受。M这样的凄凉抑郁,是读书所误?抑或是生活所误?《我的学生》中的S,生在上海,长在澳洲,求学在北平,生活在战乱下的中国,“处处求全,事事好胜”,这样一位聪明美丽、能干善良的女性,最后却因为操劳过度、献血过度而染病身亡,令人扼腕叹息。透过这样一位品格、智力、性情、能力皆上乘的完美女性的凄凉结局,叙述者“男士”不禁慨叹:做一位理想女性的修行之路何其艰难?如果说冰心早期常常以“我”之为其中一分子的认同感来塑造完美而理想的新女性形象,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对生活,尤其是女性生活的体验加深,冰心也时常意识到她所提倡的“严谨理性”+“真、善、美”+“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女性观甚至有可能对追求完美的女性造成负担和困扰——这是否是冰心转换视角以“男性他者”身份来观察女性、讲述女性故事的更深层原因?
冰心关注女性生活和女性经验,她的女性主义思想,以热爱肯定、理解褒扬为底色,选择“爱的哲学”为信念,倡导女性的自立自尊、稳健理性及道德完美。这一思想的形成,既与时代思潮相关,“像历史上一切弱势群体一样,她们也往往易于接受一种更适合弱者利益的、不带侵犯性的信念或哲学来抵抗、削弱、控制乃至消除强者的侵犯性和权威。于是在涌入中国的大量外国思潮中,女作家率先撷取的便是基督教文化中爱的观念和泰戈尔爱的哲学的混合体。这一混合体逐渐衍化为弱者——女性自己的一种哲学和信念”[5]21,又与冰心生命成长、受教育背景及个性特征有很大关系,是独具冰心特色的,也可看作是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的第三种模式,与“越轨”地触及女性隐秘情爱心理的丁玲式女性意识不同,也与冷静地揭示女性依附性异化性人格的张爱玲式女性意识不同。冰心的道德意识及家庭观念又促使她从融合旧道德精粹与新思想精华的方面,从“家庭建设”及“现代人格建构”两个向度来探讨女性的自身建设、女性与社会的关系,虽然这样的女性思想理智、中庸、温和,完全不以批判性见长,却是冰心超越时代局限与性别局限,奉献于社会的一份建设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