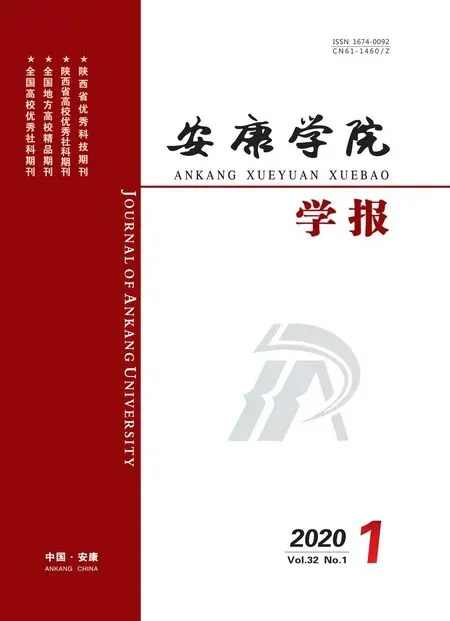灯,为何由“我”熄灭
——论《灯,我来熄灭》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
蒋宗萍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00)
佐雅·皮尔扎德(Zoya Pirzad) 于2002年发表长篇小说《灯,我来熄灭》①该书的英译名为Things We Left Unsaid。,该书一出版便斩获伊朗各大文学奖项,并经翻译传播到世界各国。小说主要描写的是20世纪60年代伊朗的一位中年妇女的生活片断,以及她平静琐碎生活中的一丝涟漪。主人公克拉丽斯38岁时发觉自己从未为自己做过任何事,而此时她的新邻居艾米勒让她心生爱慕。在繁杂的生活琐事中,克拉丽斯的生活发生了些许改变,她隐秘的感情让她的女性意识逐渐苏醒。该书已出版十余年,然而国内外鲜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因此,这本书为何能屡获奖项、广为传播,尚未有明确的定论。该书的中文版译者沈一鸣在后记中写道:“物是人非,那个时代的故事引起了当代伊朗人对往事的追忆和怀念”[1]303,故此书在伊朗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而笔者认为,该书之所以成功,原因不仅在于它反映了一个处于特殊时期的伊朗社会,它还通过一件件琐碎到乃至不值一提的小事,反映了当时伊朗妇女潜藏在心中的女性自觉,以及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反叛。该书尽管描写的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女性的生活琐事,却隐含着整个女性群体女性意识的探讨以及对不平等两性地位的抗议。
皮尔扎德以她的女性写作实践来挑战传统的男性写作,在文本内部借助主人公克拉丽斯发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目前国内关于《灯,我来熄灭》这部小说的研究较少,其中潜藏的女性主义观点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挖掘。因此,笔者希望通过细读该文本,考察作者是如何对菲勒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的,以了解伊朗女性作家的女性书写方式,同时管窥女性主义在伊朗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初读文本,读者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小说的中文译名有何深意?灯为何要由“我”熄灭?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就需要理解皮尔扎德如何实现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笔者认为,作者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策略,集中体现在“熄灯”的隐喻中,并以“熄灯”一事作为“杠杆”,试图撬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权威,以此表达对伊朗女性及女权运动的深切人文关怀。下面,笔者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融入女性主义相关理论进行阐释,主要从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的表征、解构以及女性话语的建构三方面展开探讨。
一、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的表征
菲勒斯(Phallus)一词含义丰富,在不同学科和语境下的意义不尽相同。该词由弗洛伊德提出,并在拉康的理论中得到进一步阐释。菲勒斯是男性生殖器图像或符号,因而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也被称作阳具中心主义。拉康所说的“菲勒斯”更多的指向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学领域,“在拉康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中,菲勒斯的地位无法取代,因为它集性别、名号、父权、法权象征为一身,后现代理论的核心几乎都借助于它来展示了”[2]。在本文中笔者为探讨《灯,由我熄灭》的女性主义思想,主要采用的是女性主义者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定义,而非拉康笔下的“菲勒斯”。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菲勒斯可以引申为男性权力的象征,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指男性在政治、经济、家庭、社会等方面优于女性,这与拉康所说的“菲勒斯”概念有所不同。同时,拉康也率先提出了“超越菲勒斯”的概念,“拉康的‘超越菲勒斯’之说是拉康学说的一个必然结论。不可否认它对于女性主义虽然没有实质性内容,却有精神关联。女性主义者们接过了这一口号,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3]。女性主义学者们对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定义,伴随着她们试图“超越”的愿望,进而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则是她们关注的重要命题。
《灯,由我来熄灭》中描写的诸多女性生活都在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之下,她们按照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逻辑生活,尊崇“父亲”的教导,并以“相夫教子”为己任。小说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表征于父权体系及父权体系统治下女性的生活状态中,不论是克拉丽斯还是西蒙尼扬太太,她们始终受制于父权的影响。
(一)父权话语的存在:死去的父亲“不死”
“父亲的角色并不取决于一个实际父亲的在场,而是取决于一个能指,即父性隐喻。”[4]父权话语并不会因父亲或丈夫形象“死去”而消失,父权话语是一种隐喻式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受父权支配的女性。小说中克拉丽斯和西蒙尼扬太太的父亲都已死去,他们只存在于回忆和话语中,但他们对于女性的影响贯穿始终。从这两对父女的关系来看,死去的父亲“不死”,说明象征着父权话语不会随着“父亲”的消亡而逐步瓦解。
克拉丽斯对父亲有着潜在的俄狄浦斯情结,她对艾米勒心生爱慕时,在艾米勒的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在克拉丽斯反复的叙述中,尽管父亲已经去世多年,她仍多次想到记忆中父亲的模样,并且牢牢铭记着父亲的教诲:
我想起父亲曾经说过:“不要同别人理论,也不要批评别人。不管谁说了什么,你都要说:说得对……同人们争论并没有多大用处。”[1]29
父亲认为克拉丽斯在生活中应该学会包容和隐忍,不要同他人理论争辩,但在这一过程中她丧失了重要的话语权。所有愤怒、不甘无处宣泄,话语权的缺失是她压抑的根源。在与母亲、妹妹争吵时,克拉丽斯虽心生不满,但她从不用激烈的言辞回绝;面对邻居西蒙尼扬太太时而尖酸的嘲讽时,她在内心独白中反驳了无数次,却难以直接和对方说出一句话;她想回到德黑兰,却不得不迁就家人留在阿巴丹。父亲已经死去多年,但她仍遵循着父亲的教导,直至38岁时才恍然发现她从未为自己做过任何一件事。
西蒙尼扬太太同样自小受到父亲的规训,直至父亲死后,对她的影响也没有丝毫减弱。幼年时她身材矮小,照相时被父亲要求坐下拍照;到了适婚年龄,父亲不允许她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导致了她婚姻的不幸。她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是由父亲塑造而成,这导致了她对于后代的管教也异常严苛。作者在小说中借西蒙尼扬太太之口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克拉丽斯与西蒙尼扬太太十分相似。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被父权主宰的女性,父亲规范着她们成为怎样的人,以至于她们忘了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
(二)父权话语体系下女性的地位与角色
菲勒斯中心主义中既然有所谓的“中心”,也就会有边缘的存在。女性在菲勒斯中心主义体系中被视为“他者”的存在。这种存在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与男性进行区别,女性的存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是女性的地位能帮助男性确立地位,但又不足以威胁到男性的中心地位,因而女性应该要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
小说中的已婚女性,大多为全职家庭主妇,她们的生活以家庭为核心。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其社会地位也取决于家庭中男性的社会地位。克拉丽斯的妹妹爱丽丝与他人攀比的对话即是好的例子:
她先是看了一眼镜子,从整齐的头发和艳丽的口红中获得了信心,接着面向玛格丽特的妈妈问道:“对不起,萝莉特,您的丈夫级别是几级?”
玛格丽特的妈妈扬起两弯新月眉:“叫我萝萝。十五级,怎样?”
爱丽丝微微一笑:“真巧,那还有三级才到得了我姐夫的级别。”[1]71
克拉丽斯的妹妹爱丽丝未婚,在医院中担任护士而非全职的家庭主妇。然而在与另一位太太的对话中,她不是依靠自身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而是利用姐夫的社会地位来讥讽对方。这说明不仅是家庭妇女,职业女性同样需要凭借家庭中男性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自身的社会地位。
小说中的已婚妇女需要打理好一切家庭琐事,生活只能围绕着丈夫和孩子。她们除了照顾丈夫,还主要负责养育和培养下一代。因此,受到父权/夫权主宰的女性扮演者将菲勒斯中心主义传入下一代的“代理人”的角色。克拉丽斯的母亲对于克拉丽斯言行的约束,往往不是凭借自己的身份,而是仰仗着“父亲的名字”才能得以实现。无形中成了将菲勒斯中心主义灌输给女儿的代理人,并强化了父亲对于克拉丽斯的规训。克拉丽斯的母亲在对克拉丽斯提出要求时,常用到“我以父亲的名义请求你……”这样的句式。这意味着母亲只是在代替父亲进行传话,本质上拥有权力的是已经死去的、不在场的父亲,而克拉丽斯也只是乐于听从父亲的命令,而非畏惧母亲的权威。又如西蒙尼扬太太的儿子艾米勒很早就失去了父亲,于是她代替丈夫担任了艾米勒父亲的角色。而她的教育方式,本质上源于父亲对于她的严厉管教,其教育的内容和思想流淌着父权的“血脉”。她严格教导自己孙女,并且反对艾米勒与薇莉特的感情,重走了父亲的道路。这无疑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影响又扩展到了下一代,于是催生出一个新的问题,即父亲体系的结构问题。
(三)父权话语体系的循环结构
如上所述,女性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控制下,既是男性的附庸,又成了将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或父权主义思想传达给下一代的“代理人”,这也就导致了父权话语体系循环结构的产生。
父权话语体系的循环结构按照以下路径代代传承:
父亲(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妻子(父权“代理人”)——儿子(新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女儿(新的父权“代理人”)——孙子/孙女(被纳入父权体系中)
从这个循环结构来看,女性在整个体系中都处于弱势地位。而由于女性的参与,菲勒斯中心主义能够更好地将下一代人拉入体系的秩序中,从而将体系延续下去。如小说中克拉丽斯父亲死后,她的母亲“以父亲的名义”继续用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控制克拉丽斯的言行;而西蒙尼扬太太阻止艾米勒追求自由的爱情,借助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话语将自己的悲剧延续到下一代身上。克拉丽斯的儿子在青少年期已经对克拉丽斯产生叛逆心理,艾米勒的女儿艾米莉被西蒙拉扬太太严格管教,小说中所有人物包括最年轻的后辈也都被纳入了父权话语体系中。可以看出,父权体系的循环结构决定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代代传承,而女性在这个体系中难以脱身。
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
(一)熄灯隐喻与男女不平等关系的解构
皮尔扎德对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主要集中在她对男女不平等关系的解构。这一解构过程,集中在克拉丽斯生活中一个极其微小的“熄灯”的细节上。小说中,丈夫几次询问“我”同一个问题——你关灯还是我关灯?这一描写并非闲笔,而是有着特殊隐喻意义,同时作为一条线索暗示了主人公克拉丽斯的心理变化过程。小说中有四次熄灯的情景:
第一次熄灯:丈夫提出谁关灯的问题,刚开始“我并没有注意”,直到丈夫第二次询问,“我”赶紧答道“我”来关灯。
第二次熄灯:丈夫询问后,“我”回答说“我”来关灯。而后“我”想起艾米勒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忙的场景。
第三次熄灯:没有丈夫询问,“我”直接关上了灯。
第四次熄灯:没有丈夫询问,“我”直接关上了灯。
熄灯这一行为,首先直接隐喻的是平淡的婚姻、冷漠的丈夫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为数不多的温情时刻。丈夫的询问,是这段婚姻中难得的温暖。当丈夫提出这个询问的时候,克拉丽斯会认为丈夫不像别人口中说的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其次,熄灯象征着“我”主动地去行动而非被动地等待,同时象征着“我”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中拥有着平等的自主选择权。“我”之所以要主动去熄灯,正是“我”在以行动证明“我”能够自己做出选择并付诸行动。尽管熄灯只是一件小小的家庭琐事,但预示着男女不平等关系有了平等的可能性,女性在其中也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利。“我”的回答和熄灯的行为,正是“我”试图掌握话语权的表现。
在菲勒斯中心主义体系内,男性与女性的地位显然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并不是说生理的不平等,而是权力关系的不平等。“社会性别(gender)体制是一种不平等的二元化社会体制,它体现了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5]30男性与所有主动的、光明的、文化的、高的或者一般来说正面的事物相关联,而女性则是与所有被动的、自然的、黑暗的、低的或者说负面的事物相关联。克拉丽斯熄灯的举动,是对于男女不平等关系的解构,但这种解构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实现的。因而上述的几次熄灯情节的细节处及其变化同样耐人寻味。
“我”来熄灯的前提在于丈夫的询问,这个问题尽管非常微小,却表现出男性对于女性的关怀。在“熄灯”问题上,奥尔图什不是命令或派遣克拉丽斯去做这件事,而是尊重克拉丽斯的意见。这表明至少在熄灯这件事上,男女两性是平等的,“我”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力。“我”选择主动关灯,这种主动性意味着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也可以拥有主动的一面,不再是男女不平等关系中被动的一方。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熄灯情节中,“我”虽然选择关灯,但是在丈夫提出询问后才执行这项行动。而在第三第四次熄灯中,没有丈夫询问,“我”依然选择熄灯,说明随着故事的发展,克拉丽斯本人的主动性逐渐增强,这种主动性的增强无疑与克拉丽斯心中女性自觉的唤醒是分不开的。几处“熄灯”细节的改变,对应的是一条暗线,即克拉丽斯的心理成长,详见表1。

表1 熄灯情节与克拉丽斯生活状况变化一览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在熄灯情节中克拉丽斯越发主动地选择熄灯;另一方面在生活中她也渐渐主动为自己内心的欲望做出尝试,并试着为了自己和其他女性做些什么。这意味着她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不再受到父权/夫权等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的左右,开始思考自己真正需要的生活,并开始为了其他女性争取更多平等权利。熄灯这样简单的行动,是她生活中微小的改变,同时也是她崭新生活的开始。
(二)女性悲剧与对父权话语的反抗
小说中的各个女性基本都处于社会的中上阶层,物质条件充裕的她们不需要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克拉丽斯和西蒙拉扬太太不幸的生活源于父亲对于她们的教导,而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从一个侧面表达了父亲并非“永远是对的”,因而颠覆了父权话语的权威性。
克拉丽斯的父亲对于克拉丽斯而言,确实是宽容和慈爱的,但他对于克拉丽斯的教导却成了一种无形的枷锁。克拉丽斯的父亲要求她不要反驳其他人的意见,其结果导致克拉丽斯直到38岁也从未为了自己做过什么。在日复一日繁琐的生活中,克拉丽斯在每一个无法忍受的瞬间,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父亲的教诲。她的生活围着丈夫和孩子转,母亲和妹妹时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她争吵,她痛苦却又无处言说,生活充裕却没有精神上的自由。直到艾米勒出现,他肯定了克拉丽斯热爱阅读的习惯,成了克拉丽斯的知己,才使得克拉丽斯开始逐渐正面自己的内心想法。
西蒙尼扬太太的处境与克拉丽斯十分类似。她自小就因为身材矮小,被父亲要求在拍照时保持坐姿,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坐姿,让自己显得更加得体,于是她“只是为了坐,练习了一辈子”[1]182。西蒙尼扬的父亲认为,他已经给了女儿一切想要的事物,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女儿更好地生活。西蒙尼扬太太对父亲如此描述道:“我的父亲总是说,你还想要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我要什么。可当我明白了,向他要求的时候,他却说不。”[1]185她希望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父亲却出于利益需要将她嫁给另一个人。她被迫和父亲指定的人结婚,当她的丈夫去世后,她希望再找回心中所爱,但为时已晚,她心爱的人也不幸离世了。于是她从一个天真可爱的少女,渐渐活成了父亲的模样,成了一个对他人刻薄,对家人严苛的克拉丽斯眼中的奇怪的老妇人。西蒙拉扬太太因为受父权的压制,又把这种压制转嫁到下一代身上,因而她儿子艾米勒的爱情不得实现,孙女艾米莉与朋友自由交往的权利被剥夺,悲剧的结局顺延到了下一代身上。
可见,不论是充满慈爱的父亲(克拉丽斯的父亲),还是虚伪的父亲(西蒙拉扬太太的父亲),都可能导致女儿的不幸结局。因为父权是一种隐形的压力,女性在父权的压制下难以获得真正精神上的自由,而父亲本人的出发点好坏也许并不能改变这种结局。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在对西蒙尼扬太太的过往描述中,隐秘地揭示了西蒙拉扬太太对于她父亲的反抗——西蒙拉扬太太的儿子艾米勒并非她与丈夫所生。她终究是瞒着父亲随着自己的心意与心爱的人结合了。这一情节的补充,实则表达了作者对于悲剧女性的关怀,皮尔扎德希望女性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试着反抗父亲的权威。
(三)男性角色参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
要实现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光依靠女性自身的力量显然是非常难做到的。这部作品中除了女性自身的努力和尝试外,男性角色对女性的内心觉醒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换言之,男性角色通过帮助女性,间接参与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
小说中的主要男性包括克拉丽斯的丈夫奥尔图什以及艾米勒,他们两人已为人父,在家庭中充当着父亲的角色。奥尔图什被克拉丽斯认为是冷漠的丈夫、不关心孩子成长的父亲。他对家庭琐事毫不在意,反而更关注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尽管如此,晚上睡觉前奥尔图什仍会提出谁来熄灯的问题,体现出他对妻子仍有温柔的一面。如上文所说,奥尔图什把这个问题摆在克拉丽斯面前,代表着他们在这件事上拥有平等的权利。至少在这样的生活琐事上,奥尔图什将选择权交给克拉丽斯,表明他心中对女性有着基本的尊重。正是由于奥尔图什提出了熄灯问题,克拉丽斯才借此明白自己能够拥有一些主动权,并尝试着主动为自己做些什么。
艾米勒是小说中一个较为理想的男性形象,他把克拉丽斯视为好友,举止得体,性格友善,恰好与奥尔图什形成对比。艾米勒成为克拉丽斯的邻居后,在生活中帮助、关心她,与她有着共同的爱好。艾米勒是唯一能够理解克拉丽斯阅读兴趣的人,他温柔并且善解人意,很快俘获了克拉丽斯的芳心。而克拉丽斯自从对艾米勒产生爱慕后,发现了自己身上仍保留着对于爱情的向往,这种隐秘的内心情感是她内心欲望的体现。她尽量避免妹妹爱丽丝接触艾米勒,珍惜每一次与艾米勒的相处机会,她不再被动地生活而是主动地争取一段被视为不道德的感情。
小说中这两位男性,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克拉丽斯女性意识的成长。奥尔图什的一句简单问候,让克拉丽斯意识到自己拥有平等自主的选择权利;艾米勒的出现,唤醒了克拉丽斯内心的真实欲望,让她麻木而繁琐的生活有了色彩。因此笔者认为,这两位男性角色间接参与了对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而唯有男性参与到这个解构过程中,男女不平等的二元关系才能真正地被击溃,这样的角色和情节设计体现出皮尔扎德对两性关系问题的透彻思考。
三、女性话语的建构
(一)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除了解构本身,还应该包含新的话语的建构。依照福柯的观点,话语并非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话语是借助语言而生产知识,“它涉及语言和实践”[6]。女性话语的建构,需要由女性自己用语言去表达,这种表达包括语言和实践两方面。克拉丽斯被父亲教导“不要与他人争论”,使她在交流中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而随着克拉丽斯对于自身认知的变化,她开始借助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用女性的话语为自己发声。
首先是口头语言。克拉丽斯不再缄默,她用语言接近艾米勒,用语言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她在艾米勒面前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阅读经历,希望用相同的“语言”拉近与艾米勒的距离。在一次激烈的吵架中,克拉丽斯第一次滔滔不绝地诉说着生活中的无奈和痛苦,她终于将她身上的一切委屈倾诉出来。
“我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着。奥尔图什听着,听着,只见他从桌上拿起糖罐……第一次,他没有在我的话还没说完前就走开,我趁机把心里所有的话一吐为快。”[1]262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到,克拉丽斯终于用自己的语言将压抑在心中的一切释放了出来,她的丈夫在这样的情境下,第一次成了一个合适的倾听者,听见了克拉丽斯埋藏在心底的声音。克拉丽斯在语言上获得了对方的尊重,取得了对话中的话语权。
其次是身体语言。克拉丽斯要发出女性的声音,除了在口头上勇于表达自己内心想法外,她也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主动性。克拉丽斯为了见艾米勒精心打扮,艾米勒的微笑让她也随之微笑,艾米勒的赞美让她脸红。她用身体语言回应着内心对于爱情的真切渴望,用身体语言表达出自己的女性欲望。在与丈夫奥尔图什的相处中,克拉丽斯选择“熄灯”是在用身体语言表达自我。包括小说结尾,克拉丽斯决定独自一人到德黑兰旅行,也是以自己的身体语言告诉她身边的所有人:她要努力为自己做些什么。通过口头语言与身体语言的表达,克拉丽斯终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除了克拉丽斯外,小说中另一个不容忽略的女性角色——努尔拉合太太,也是付诸语言和行动,为妇女发声的代表人物。努尔拉合太太是女性主义者,她在不同场合以演讲的方式宣传女权主义,同时希望克拉丽斯协助女权社团的组建。她为了女权社团的组建几次找到克拉丽斯,并向克拉丽斯介绍女权运动的相关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努尔拉合太太是克拉丽斯的精神导师。小说结尾处,通过克拉丽斯与两个双胞胎女儿的对话,暗示了努尔拉合太太的女性主义思想得到了支持、延续。
阿尔米娜说:“妈妈,女权是什么意思?”
阿尔西娜重复道:“女权是什么意思?”
我把菜单交还给服务生,说道:“你们长大了就明白了。”[1]284
这段对话寄寓着女权主义得到延续的美好愿望,男女平权的种子被种下,等待萌发。而上文中所提到的父权体系的循环结构,则可能因此无法继续在下一代人的思想中持续。
(二)女性欲望的书写
皮尔扎德创作《灯,我来熄灭》本身就是在用女性写作的方式书写女性欲望以建构女性话语。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揭示了欲望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语言所具有变革性的力量,拉康的相关理论给女性主义者以启发。“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既然欲望是一切语言的动机,文学作为最强烈的语言的运用者,更是欲望的一种集中表现”[5]125,而男性的语言无法描绘女性的欲望,据此,法国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女性写作”的概念。女性写作有别于男性写作,传统的男性写作重视论说而富有逻辑,而女性写作更多的则集中在对于自身的思考和对压抑的宣泄。如海伦娜·西索的观点,女性写作是在“写自己”,是“听见自己身体的声音”,《灯,我来熄灭》这部小说无疑是以女性写作的方式进行创作的。“女性批评主义认为,妇女问题正在于它是男人生产的文学的消费者。”[7]女性写作不仅是让女性发声,还是把女性放在了一个重要的立场上。传统男性写作中,预设的是“男性读者”,而女性在阅读过程中,在这种小说结构的推动下,会站在男主人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甚至可能反对女性自身。而《灯,我来熄灭》以克拉丽斯为第一人称视角,也是试图将女性置于读者的地位,让女性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理解文本,从而有所体悟。
小说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伊朗石油城市阿巴丹,时值伊朗石油工业发展迅速,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隐藏着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不稳定因素。但这些内容在小说中仅仅是在克拉丽斯的丈夫身上略微体现,并没有被重点叙述。小说的所有内容都是克拉丽斯的所见、所闻、所感,没有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只是一些平淡无奇的生活小事而已。皮尔扎德坦然地将女主人公克拉丽斯中年时期的一段隐秘的情愫详尽地描写出来,实际上就是在建构女性话语,在为女性的欲望正名。此外,西蒙拉扬太太、爱丽丝、薇莉特等女性角色对于爱情的追求也穿插在克拉丽斯的故事中,体现出那个时代伊朗女性对于自身诉求的坦率与执着,成为皮尔扎德所描写的女性欲望的一个脚注。
四、结语
上文笔者已经把《灯,我来熄灭》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详细梳理了一遍,现在也就可以解答本文开篇所提到的问题。首先,《灯,由我来熄灭》这一中文译名,不仅强调了熄灯这件事的重要性,更强调的是熄灯对于“我”的重要性。在上文的分析中,笔者已经阐述了熄灯隐喻着克拉丽斯的女性意识及主动性等方面。“熄灯”是消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过程中一件微小却又富有意义的行动,对“我”而言是迈出一成不变生活的第一步。其次,“灯为何要由‘我来熄灭’?”这一问题的解答同样要追溯到熄灯的隐喻作用。“熄灯”这一行为,象征着“我”主动地去行动而非被动地接受,同时代表着“我”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中拥有着平等的自主选择权。“我”通过主动选择熄灯,意识到了自己在生活中可以付诸实践,为自己做些什么,而不是被动地为了丈夫、为了家人而活。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由此女性也需要按照要求戴上头巾。与之相比,小说所写的20世纪60年代的伊朗社会对女性而言要更加开放。当时女性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开展,皮尔扎德借主人公克拉丽斯的言行表达了对女性运动的支持。她对于女性欲望以及女性心理的书写是透彻的,整部小说通过一件件小事和“喧嚣”的人物对话塑造了一个中年时迷茫却又走出了迷茫的女性形象。皮尔扎德的写作策略是以微小的事件和女性微小的尝试来解构宏大而坚固的事物(菲勒斯中心主义),丰富的细节和真实的心理活动令人动容。故事的结尾“娜拉”式的女性克拉丽斯没有走出家庭,但她在这件小事上得到了自主选择的权利,意味着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同样也是一个独立个体,在爱情、家庭等方面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克拉丽斯勇敢地迈出了一步,尽管只是到德黑兰旅行,尽管只是为女权运动社团提供一点建议,但就是这些类似于“熄灯”的小小动作,在她整个人生经历中,意义非凡,弥足珍贵。所以,在克拉丽斯的内心独白中,灯,必须由“我”来熄灭。当然,女性主义思想的体现只是皮尔扎德小说众多主题的一个侧面,对其小说主题的深入挖掘和阐释尚需学界同仁更多的努力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