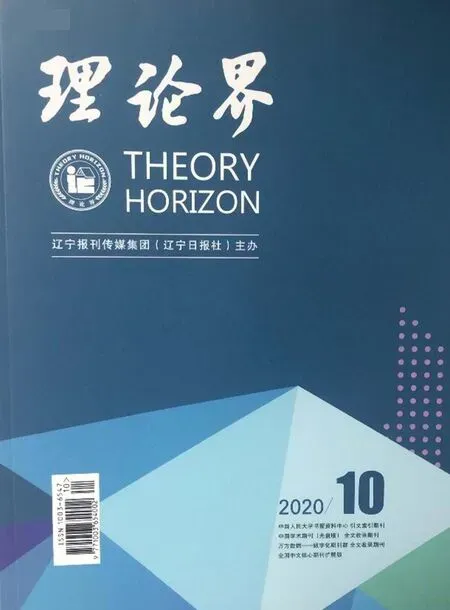何处是吾乡:尤金·奥尼尔《长夜漫漫路迢迢》中的家园书写
孙奇锋 卢 敏
一、前言
《长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也译《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是“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家庭问题剧之王”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的后期巅峰之作,也为其一举摘得第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奥尼尔以自传性的笔法,“不仅提供了奥尼尔一家四人的丝毫不差的复制品,还描绘了他们的真实情况和作为他们悲剧见证的那个家”。〔1〕在该剧作中,“他并不伤感化,不做假道学,也不将这个家庭集体的失败怪在什么外在的因素上面”,〔2〕因为在他看来,他们一家的不幸并不是诸如金钱、疾病,而是“没有一所可以‘定居’的房子”,〔3〕“没有归属——不论是心理的还是物理意义上的”。〔4〕
家的意象往往与亲密、热情、关爱等联系。“我们在家屋之中,家屋也在我们之内。我们诗意地建构家屋,家屋也灵性地建构我们。”〔5〕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那样,从人生存的世界来看,作为特殊存在者的现代人的命运大多是“无家可归”,对于奥尼尔来说,他“一生始终感到无家可归,仿佛命运并不完全知道该把他安排在哪儿”。〔6〕而他也借剧作中埃德蒙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无所归依之感,“作为一个人,我永远是一个生活不惯的外人,一个自己不怎么要,也不怎么被人所要的人,一个无所依归的人,始终不免有一点儿爱上了死亡!”〔7〕
无根之感一方面来源于奥尼尔爱尔兰裔的族裔身份。奥尼尔曾经同其儿子小尤金抱怨过,“关于我和我的作品,评论家们往往忽略掉的最重要的事是——事实上我是爱尔兰裔”。〔8〕其父母都是爱尔兰裔美国移民,他虽然从未真正到访过真正的爱尔兰,但是他一直在追寻自己想象中的文化家园。作为流散作家,奥尼尔或许正如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eshdie)所自述的那般“像我这样的流散作家,心头可能总是萦绕着某种失落感,有着某种冲动想去回顾过去,追寻逝去的时光”。〔9〕所以,《长夜漫漫路迢迢》中的玛丽在控诉没有一个真正正常的家的时候,总是借助吗啡回到过去未嫁时的幸福生活,变成一个“过去的冤魂”。〔10〕但是,作为民族特质,归属感“爱尔兰人可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11〕因而奥尼尔一家都处于一种家园缺失的无根状态,主要反映在父亲詹姆士的地皮购买癖、母亲埃拉的沉迷吗啡以及奥尼尔自己的四海漂泊。
而另一方面,奥尼尔自出生起,很长一段时间都跟着他父母到处奔走,因为“他父亲是有名的舞台演员——根本没有过固定的家”。〔12〕而这个场景借剧作中玛丽之口也进行了说明,“每一晚到一个不同的地方排戏,住的是蹩脚旅馆,整天坐肮脏的火车,把小孩丢在家里,根本没有一个家”。〔13〕幼年的这段经历,在赋予奥尼尔高超的戏剧创作技巧的同时,“也使他缺乏安全感,一生永远像在追寻什么”。〔14〕正如他所自述的那样,“我从来没有家,从来没有机会扎根”。〔15〕
家园的缺失,让奥尼尔一生处于身体和精神上的无所归依状态,但正如雷恩所说,“奥尼尔身上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敢于让你和他一起走到最远处,和他一起跳下悬崖,跌入最深、最黑暗之处”。〔16〕在他用“泪和血”写就的这部自传性四幕剧《长夜漫漫路迢迢》中,奥尼尔将其家庭悲剧赤裸裸地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让读者深切地感受盘踞在他内心深处的创伤过往,以及“存在于他和他父母之间的莫名的悲哀”。〔17〕
二、创伤的家园:地皮和地产
“家屋形构出种种意象的身躯,这种种意象为人类提供稳定感的证据或幻象。”〔18〕在巴什拉看来,家屋往往存在两种意象——“垂直的存有”和“集中的存有”,既有着与天地的纵深联系,又有着内部的中心轴意识。但是,在《长夜漫漫路迢迢》中,蒂龙却热衷于购买地皮或者地产,并进行倒卖以进行谋利,而不肯给他的妻儿安置一个好好的家。地皮是家屋的基础,没有地皮就没有家屋。可是光有地皮是没有用的,没有实现“垂直的存有”,不能称之为家屋,所以这是一种家园的缺失。地产也是如此,地产本是家屋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在蒂龙手里,地产不是用来给妻儿居住的,而是用来赚钱收益。从这点来看,地产无法实现内部的“中心轴”,因而也是一种家园的缺失。
杰米曾经抱怨父亲蒂龙对地皮地产的狂热,“老是要买地,没完没了地买。假如埃德蒙是一块倒霉的地皮,你要想买,那么天大的价钱你都舍得出!”〔19〕父亲蒂龙对一切都十分节省,连一分钱也不愿多花。在妻子玛丽产后身体不适的时候,为了省钱,便请了一个出诊费相当便宜的庸医,从而导致玛丽吸食吗啡成瘾。等到发现玛丽吗啡上瘾之后,也没有趁早送她去疗养院医治,因为“那样做得花点儿钱啊”。〔20〕在小儿子埃德蒙患肺结核需要治疗这件事上,也是能省则省,甚至为了节约钱,要将儿子送入山镇疗养院,即州政府办的慈善机构。但是,却转身“到俱乐部去和麦桂会面,又让他敲了一笔竹杠”,买下了“一块蹩脚的地皮”。〔21〕作为“这一带地产最多的财主”,〔22〕蒂龙在对地产的渴求上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甚至不惜以自己周围最亲密的妻子儿子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购买地皮,然后谎称自己“几个钱通通放在地产上了”,〔23〕没有多余的闲钱,但是“在酒吧间里灌饱了威士忌之后”,却慷慨地“请张三李四喝酒,或是慷慨地借钱给揩油的朋友,明知道借出去是不会还的”。〔24〕可以说,在蒂龙心中,自己的家人远远没有地皮地产,甚至外面的酒肉朋友来的重要。蒂龙声称“他还是要一个家”,〔25〕但是在所谓的家里待的时间相当有限。玛丽一直抱怨他“一辈子只晓得住旅馆”,〔26〕或者上俱乐部或是上酒吧,喝得烂醉才知道回来。蒂龙对家人态度的“异化”表现无疑是在家园缺失下对家园的“异化”解读。蒂龙心里想有家,但是他的家就是未成形的地皮地产,是一种缺失,甚至他的家一直就是处于“抵押”“等待倒卖”的状态之中,是没有任何“垂直”或者“集体存有”的。
蒂龙的这种极端的地皮购买欲其实是其童年的创伤场景再现。秋丽安·斯莫尔(Trillion Small)认为“创伤试图用幕帐遮蔽我们的双眼,我们在成年后会再次经历那些童年创伤性体验”。〔27〕蒂龙是第一代爱尔兰裔美国移民,从小的时候就备受世人冷眼,吃尽了苦头。玛丽曾这样向埃德蒙解释蒂龙的吝啬成因,“你也得想法子认识他、原谅他,不要因为他手头那么紧而瞧不起他。他小的时候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来还不过一年多,他父亲就把他母亲和六个孩子抛弃不管了。他对他们说他得到一个兆头就快死了,同时又想念爱尔兰老家想得要命,所以一定要回去好死在家乡。所以,他就这样走掉,后来果然死掉了。他一定也是一个怪人。你父亲才十岁的时候就在一家机器厂里做工了”。〔28〕蒂龙在午夜长谈中,也同埃德蒙解释他为何会对地产那么着迷,“我就是小时候在家里吃过苦,才知道一块钱的来之不易,又唯恐到老会住穷人院。打那时起,我就不相信我一辈子能靠运气。我老是怕运气会转变,弄得不巧有一天一生赚的几个钱都会搞光。说来说去,多置一点儿地产心里总觉得安全些。这虽然不一定合理,但这是我的想法。银行会倒闭的,银行一倒你的钱也跟着没了,可是脚踏实地的地产永远是丢不了的”。〔29〕童年时候的贫穷创伤记忆,始终犹如过去的幽灵一般萦绕在蒂龙的心头,让他格外“注重事物实体的态度,反感那些不可预计的、不稳定的和动态的东西”。〔30〕因而在购置地产的过程中,虽然屡次上当受骗,但是他认为自己始终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产,不至于到最后像小时候那样“前后还有两次因为付不起房租被房东轰出来,家里仅有的几件破家具给扔到大街上”。〔31〕
土地本是家庭统一的符号,“是唯一能够保证连续性和统一性的东西”。〔32〕但蒂龙的这种家园缺失创伤一直没有得到疗愈,他的地产始终不是完整的“家”,只是一块地、一幢空荡荡的房子。他一直以为有了地皮就是有了自己的家,不用被人扫地出门,但是真正的家应当是一家人长久地生活在一起。“大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恐惧是不察觉的。潜在的恐惧通常正是那些使我们的动力持续消耗已近枯竭的因素。”〔33〕蒂龙的童年创伤让他恐惧老年流落街头,住进穷人院,因而他只能以不断地购置地皮地产来进行自我蒙蔽,但是恐惧依旧存在,渐渐磨蚀了他对家园美好的希望,只留下一块块空荡荡的地皮。而作为一家之主,蒂龙的创伤也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孩子,让这种家园缺失在代际中一直存续。
三、空荡的家园:消夏别墅
奥尼尔的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之中,居无定所,“可是他唯一的、真正的‘家’——也是《长夜漫漫路迢迢》这出戏发生的地点——新伦敦”。〔34〕在这个海滨工业地区,他们有了一幢真正属于自己一家的房子,在每年的夏天,都会来这里短住,而其他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在旅馆度过的。在剧作的开篇,奥尼尔是这样介绍这幢房子的,“舞台后方有两道挂着门帘的双门。右面的门道前客厅,看上去摆设得整整齐齐。另外一对门通过一间暗淡无光、没有窗户的客厅,除了用来做起居室与饭厅不常用的屋子之间的走道外,别无其他用处”。〔35〕这里展示的空间是密闭空间,虽然由客厅进行连接,但是整个通道是昏暗的,且没有窗户与外界进行沟通,因此,看似收拾整齐的别墅其实是压抑的,生活在里面的人很容易发生口角、争吵;看不到希望、热情,只想从中逃离,不然只能深深地被锁在其中。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奥尼尔对这幢消夏别墅的态度——虽然像家,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家,没有温情。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鲍尔德温和朗赫斯特认为“当人们之间充满情感的关系,通过重复和相互熟悉而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找到停泊地的时候,它们就变得更富有意义了”。〔36〕可是,消夏别墅这个地方并非是蒂龙一家都喜欢定居的场所,同时这里见证的也多是他们一家无休止的怨怼和争吵,而非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玛丽曾说过:“女人需要有一个家才能做一个好母亲。”〔37〕而这里显然不是她眼中的“家”,她和埃德蒙抱怨,“我一向就讨厌这个城市,讨厌本地这帮人,你是知道的。我当初并不愿意住到这个地方来,可是你父亲老是喜欢这里,一定要盖这幢房子,我也只好每年夏天跟着来这儿住”。〔38〕同时,该地方也不是一个长久的“停泊地”,只是一个消夏的别墅。正因如此,玛丽抱怨道:“你又不当家,不需要对付一帮夏天临时的佣人,他们知道不是长工,做起事来什么都是马马虎虎的。真正好的佣人都到好好的人家去做,没有人愿意在避暑别墅的人家打短工,再加上你父亲连夏季最高的工钱都不肯出,所以每年我都得应付这帮乡下来的又蠢又懒的新手。”〔39〕因此,这幢房子对于蒂龙一家的意义不过是又一处暂居地,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了自己的佣人和不需要交房费而已。蒂龙一家从未有过真正的家园,他们有的只是一幢空荡荡的房子,没有属于家园的情感联系。
蒂龙可以忍受住在这所破破烂烂的房子,却“不肯花点钱把这个房子修饰修饰,只顾再去买进地产”,〔40〕不愿给玛丽和孩子们好好安置一个家。而且,蒂龙父子在知道玛丽嗑药的时候,只知道一味地去监视、去责怪玛丽自己意志力不够坚定,怪玛丽“见了你就好像周围造了一道墙一样,把你堵住。也许更像一层浓雾,躲在里面不见人”,〔41〕而不去思考玛丽为什么不愿放弃嗑药,为什么始终“把自己更深地藏在内心里,同时逃避、放纵在一种幻梦之中”。〔42〕
玛丽嗑药的缘由是为了缓解生产埃德蒙时的疼痛,但是之后的上瘾,更多的是蒂龙一直以来对其的漠视和疏离。蒂龙可以因为自己想念玛丽,而让玛丽跟着他到处跑,甚至因此让玛丽间接失去了第二个孩子尤金。尤金之死可以说是玛丽内心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她怪自己把尤金丢在家里让她母亲管,结果让杰米将疹子传染给了尤金。蒂龙对此的解决方法是再生一个孩子,但是这并不能真正缓解尤金死去所带来的创伤。奥尼尔在该剧中“把以自己为原型的人物命名为‘埃德蒙’,而把那个夭折的孩子命名为‘尤金’”,〔43〕因为他认定自己的出生只是父母在绝望之时发生的一个错误,只会让母亲“不断想起对于埃德蒙的愧疚”。〔44〕玛丽吸食吗啡的那个空房间就是死去尤金的在场。在本该属于尤金的空房间里,玛丽在吗啡的刺激下,一遍遍地弥补自己的过错,一遍遍地回忆过去美好的生活,哪怕只是虚幻的,因为“药可以止痛。吃了就带你往回走——走到不再疼痛为止。一直回到从前快乐的日子”。〔45〕
蒂龙自结婚起,虽然没有外遇,但是一直都让玛丽孤身一人,冷冷清清,从未想过给予玛丽关爱。之后的许多年里,让玛丽一次又一次地在又脏又臭的旅馆房间等他,自己却跑去酒吧或者俱乐部喝得烂醉。就像埃德蒙指责蒂龙的那样,“那是因为你从来没做过一件事使她自己要戒!你不让她有一个好好的家……每年巡回演戏,你把她拖着到处跑,每个地方演一晚戏,第二天就得上路,可怜她一个人,又没人可以说话,一天到晚待在肮脏的小旅馆里等你回来——等什么?等到酒吧关门让你喝得烂醉回来!我的天,怎么能怪她要戒也戒不掉?他妈的,我每次想到这个,我真把你恨死了!”〔46〕在剧作中,玛丽不止一次地表现出自己对于家中无人的寂寞和无援,“这里好冷清啊。不要又来欺骗自己了。你情愿他们都走掉,不要他们在家陪你——瞧不起你、讨厌你。都走了,你才高兴呢。那么我的圣母啊,我干吗觉得这样孤单?”〔47〕玛丽很害怕自己一个人在小旅馆、在消夏别墅待着,但是她又不得不这样待着,直到蒂龙喝酒回来。她只能习惯这样的孤独寂寞,但是她内心是抗拒的,她也想有朋友,想要自己家人的陪伴,可是她知道自己是得不到了,所以只能借助吗啡,回到过去未嫁时的美好时光,过去温馨的家庭生活。
虽然消夏别墅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家园的期待,但“就跟在路上什么肮脏的小客栈里过一晚就走一样”,〔48〕并不是真正的家园。在这幢房子里,有的只是寂寞、冷清和空荡,有的只是亲情的缺失、家人的漠视和疏离。
四、自由的家园:大海
在奥尼尔剧作中,“最重要和最具有自然象征性的是大海本身”。〔49〕大海或是一种与上帝相对的神秘力量,或是人物的精神寄托。而在其自我归属的认同中,大海是一个重要的家园意象。这一点在其自传戏《长夜漫漫路迢迢》中格外明显。“在他看来,大海呈现出神话般的浩淼,正是在大海里,他为自己漫无目标的生活找到了归属,并看清了他在剧作中体现的那种神秘的生命背后的动力。他沉湎于大海之中,而大海在他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50〕这与奥尼尔早年的航海经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自传性剧作《长夜漫漫路迢迢》中的第一幕,通过杰米之口,我们可以得知埃德蒙曾经“去当水手,走遍了五湖四海”。〔51〕虽然在外当水手,意味着离家远行,但是航海之旅却给予了他追寻精神家园的契机。一方面,埃德蒙本身之前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另一方面航海让他“自己独立,知道吃苦是怎么回事,挣钱是多么不容易”,〔52〕从而让他对自己的人生归属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
在和父亲蒂龙谈及自己人生得意事的时候,埃德蒙举的都是与航海相关的经历。“迎面吹着风,天空上一轮明月……我躺在斜桅杆上面,脸朝船尾,脚底下的海水打成泡沫,头顶上每根桅杆都高高地扬着帆,在月光里一片雪白的。眼前的美景和船身唱歌一般的节奏整个把我陶醉了,一时忘掉了自我——的的确确好像丧失了生命,像是突破了樊笼,飞向自由!我整个融化在海水里,化身为白帆,又像是浪花飞溅。我自身变成美丽的节奏,变成月光、船和星光隐约的天空!我感觉到自己的伟大,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觉得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平安,与自然融为一体,有说不出的喜悦,超越了自己渺小的生命、人类共同的生命,而达到了永生!”〔53〕埃德蒙这番细致生动的描述,让人不由得了想起了苏轼《赤壁赋》中的相关场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由此可见,不管是泛舟江上,还是驰骋于海洋,夜晚明月当空、天人合一的和谐之景致,均让人感慨人生之自由与世界的永恒。奥尼尔借埃德蒙之口再现了其在大海中所得到的自由与归属。
大海之于埃德蒙亦或是奥尼尔,是自由的化身,也是人生的归属所在。在航海过程中,“摆脱了人生的桎梏,浑身自由……只有满足的快乐和安慰”。〔54〕作为爱尔兰裔离散作家,奥尼尔一直都在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当年奥尼尔的先祖们就是通过跨越大西洋到达了美国,开始新的生活。海洋,既是爱尔兰人的重要地理元素,同时也是奥尼尔寻求家园的重要载体。虽然奥尼尔并未到访过爱尔兰,但他始终通过海洋来回忆以及建构自己的故乡。在航海过程中,他不光在船上感受海洋的魅力,更是“泅水远远地泅到海里去”,〔55〕“远离了土地与在地上的生活,这个水之维度烙着无边际感之印记”。〔56〕在大海中,体会真真切切的纯粹之感。在菲利普·迪奥莱(Philippe Diolé)看来,“一个与深海熟稔的人,再也无法变回一个跟其他人一样的人……在想象里,每当走过,我就在我的四周空间里注满了水。我活在一种随念头而来的浸润里,在里头,我在一种流动的、闪耀的、有助于人的、浓稠的物质之核心四面游动,这是海水,或者倒不如说是海水的回忆”。〔57〕这样的描述也同样适合于奥尼尔。奥尼尔的记忆是关于海洋的回忆,曾经缺失的家园建构,他通过海洋的追忆完成了重构,所以在《长夜漫漫路迢迢》中,他借埃德蒙之口,表达对自己归属的思考,“真是一个大错,我生而为人。假使生而为一只海鸥或是一条鱼岂不是更好?”〔58〕在奥尼尔看来,自己作为人的话只能像现在这样格格不入、无处可归,只有在大海上,他才能真正找到自己人生的归属和价值,因此,他想成为一只海鸥,或者深海里的一条鱼,在浩瀚无边的海洋的怀抱里尽情地享受自己的人生。虽然他始终不能真正变成一只海鸥亦或是鱼,海上航行的日子也始终是有期限的,但是在大海上所体验的自由家园的感觉是永恒的、是真实的。最终,在海洋中,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属。
五、结语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 《The Theory of the Novel》)中提出,小说建构的是此岸世界,但是“在彼岸世界之外,每一个迷途的漫游者都已经找到期待已久的家园;每个渐行渐弱的孤独之声都被一个聆听它的歌队所期待,被引向和谐,并因此成为和谐本身……彼岸家园的每一个居民都来自于此岸世界,每一个人都因命运之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与这个家园相连”。〔59〕在奥尼尔创作的自传戏《长夜漫漫路迢迢》中,代表金钱利益的地皮地产只是家园构建的外壳;充满相互抱怨、指责和家人间的疏离与冷漠的消夏别墅因缺失家园应有的温情、信任和关怀也只构建起虚幻的家园。在这个虚幻的家园中,蒂龙沉迷酒吧俱乐部,玛丽吗啡成瘾,杰米沉迷花街柳巷,这注定了他们对真正意义上的家园追寻是徒劳的。当埃德蒙在浩淼的海洋中抵达了彼岸世界时,他转向了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也就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园归属。这在现实中亦是如此,奥尼尔一家的不幸亦是家园缺失,其父母兄弟的家园追寻之旅是不幸的、注定失败的。而奥尼尔则就像诗人荷尔德林在《归家》中的祝福那样“你所寻者近了,正上前来迎接你”,〔60〕在大海的怀抱中寻到了自己永恒的精神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