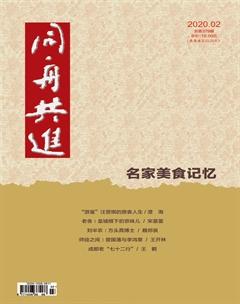成都老“七十二行”
王鹤
【背 夫】
这可真是一堂好家具。紫得凝重深沉的红豆木,经药水处理后更显出木质的精密细腻;设计和做工一看均出自高超匠人之手,大气典雅,一丝不苟。较之店里别的楠木、香樟等高档家具,它依然显出超凡出尘之态。一辈子看过各色各等家具的张师,也不禁暗自赞叹:不知是个什么样的富人才置办得起呢。
旁边家具店的老板一直在惴惴地观察张师的神色,“能行吗?”张师用肩和手感受着面前大立柜的重量,沉吟片刻说:可以。老板听罢,笑逐颜开。
那天,做好了各种准备的张师用力吸一口白酒,猛喷在捆绑家具的绳索上,随即屏息运气,收紧肩绳,大立柜像被连根拔起的古树,稳稳地移动起来,徒弟们也背起其他家具上路了。背负着庞然大物的队伍,令店外看热闹的人都惊呆了。
这是1920年代,张师他们从事的是当年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搬运业,他是此行中赫赫有名的状元。当年的风习,棺材要抬,家具要背,因为家具形状多是长方形,与棺材相仿。为着避讳,出售家具不用人抬。张师傅面前那堂红豆木家具,此前不知难倒了多少搬运工,店老板好不容易到手的生意差点因此而打水漂,幸而请出了“背山状元”,他果然身手不凡。
背夫们背负过像大山一样重的箱柜床桌,却没有谁能给自己家添置一堂贵得咋舌的高档家具,那是富人的专利。背夫们是些凭一把力气辛苦度日的小人物。
成都底层社会就是由这些小人物组成的。他们从事的,很多是现在已不存在的職业。
【轿 夫】
大热的天,连树叶都没精打采地低垂着头。可今天是母亲的生日,张嫂还是回了趟西门的娘家。母女姑嫂一阵嘘寒问暖,不觉又到了傍晚。母亲照例叫小弟弟:“去轿铺喊乘轿子,送你姐姐回去。看仔细点,别像上回那样,坐垫又脏,窗玻璃又没换成布帘子,把你姐姐热病了。
官绅人家一般都长年雇用了轿班(又称大班)。张嫂的娘家、夫家都只是小康之家,当然没有专门的轿夫,但她出门拜客,回家省亲,也经常坐轿子。街头轿铺分布很广,十字路口也随时有三三两两的轿夫或坐或站等生意。那种两人抬的小轿,又称街轿,普通人家出行、拜客,喊乘轿子是很方便的。
在老成都人出行,要么走路,要么坐轿,轿子是很常见的交通工具。轿夫则是从业者众多的一个职业。
轿钱视路途的远近而定。清代末年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周孝怀要求下,警局对轿费作了具体规定——每四条街之内,一乘轿40文;四条街之外,每多一条街加钱5文;等候一个小时之内,每个轿夫加钱10文……以此类推。有此明码标价,乘客、轿夫都省了许多口舌。
城门边还摆放着更脏也更简陋的鸭篷轿,轿夫们的衣衫也更破败。鸭篷轿有二人抬的,也有三人丁拐子抬,是专供出城下乡用的。走长路者可以去轿行雇轿,若临时需要出行,也很方便。临近几个城门的街口,都有轿夫空着手在招徕顾客。一旦揽到生意,说好价格,他们立即飞跑去城门口外将轿子抬来迎客。一般一里地的脚钱需要10文左右。客人的行李也多用人挑或抬,长途轿夫和挑夫每日每人有300文左右收入。每走三四天或遇到翻山越岭,乘客照例要犒劳轿夫,大致相当于小费。所以,轿夫如果揽到走长路的客人,吃饭歇脚时客人的酒钱又给得大方,这几天就是累点,也算是交到好运了。
据司昆仑所著《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记载,1920年,大约有20%至30%的成都男人以做轿夫为生,其中有些就是为出游的富人抬轿子。但是,不少轿夫每天在辛苦地长途跋涉之后,往往将他们微薄收入的很大部分用来买鸦片。司昆仑转述了一位1923年在成都的英国官员的话:“城中轿夫购买鸦片的价格是100铜圆一泡,他们每天赚得的薪水从600到1000铜圆不等,除了用300到400铜圆购买食物外,其他都花在了鸦片上。”
【更 夫】
晚上的成都,早早就沉入墨一样的夜色。在没有电灯或电灯尚不普及的年代,除了少数娱乐去处,成都的夜晚来得安祥而迅速。没有事做,就早点睡觉吧。随着一阵接一阵的锣声由远而近,便是二更天了。待到街上阒无人影,连晚归者都像倦鸟投林时,三更的锣又响起了。打更匠孤独的身影和着空旷的锣声,在沉寂的街巷中倍显寥落。
天刚泛出一抹淡青色,五更锣又敲响了,忙于生计的人也该起床了。
从前,繁华街道不打更,公馆集中之地也不打更。一来,公馆里的人们睡得晚,起得也晚;二来,公馆里有的是自鸣钟,谁还耐烦听那老得掉牙的锣声呢?所以,打更匠差不多就是穷人的钟表。
打更无疑很辛苦,因为晚上几乎无法连续成眠,所以更夫多数由上了年纪的人担任。打更匠也算最底层的公事人了,除了晚上打更,白天也跑公事、送告示,比如去城外乱坟岗埋葬无主的尸体,或边打锣边通知:保长的命令,明天是双十节,咣咣,家家户户挂国旗,咣咣,欢迎!

【烘 笼】
过去,冬季取暖生炉子的人家不多,老人畏寒,不但白天烘笼不离手,还常常提着烘笼上床,等被褥煨得暖和、干燥后才撤去烘笼。但烘笼尚未取出而人已入睡的情形却很多,时常引发火灾,有时还酿成大祸,旧式穿斗结构的木檐瓦舍,一燃烧便是一大片。警局为此很头疼,特要求打更匠冬季在每天三更时将锣打响些,再伴之以高声吼叫:“烤烘笼的,赶快把烘笼提下床!”
静夜的更声和“小心火烛”之类的警告,往往使刚到成都的外地人初闻之下,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盎然古风。
烘笼其实就是竹编或马口铁皮敲的手炉,内胆是陶罐,以木炭或煮饭后的余火作燃料,用以取暖,也可烘烤孩子的尿布之类。烘笼一般做工不甚考究,价格低廉,但也有编制得非常精美的,竹编的花纹繁复细腻,小户人家用作赠品,也是温馨漂亮的礼物。
从前,宽裕的人家可以烧炭做饭,天寒时则以铜、铁火盆或火炉置于室内取暖。一般家庭冬天没有经济实力随时烧煤炭或木炭烤火,有的衣服鞋袜还十分单薄,怎么办呢?好在有烘笼,还有卖火的大爷大娘。卖火人围着又遮灰又御寒的大围腰,手里拿一把芭蕉扇子,在家门口摆口大铁锅,用火引燃了细木炭、桴炭,再在上面盖一层炉灰,等着买火烤的人提着烘笼来续火。卖火的大爷大娘拿小铲给已经冷却的烘笼加两铲炭火,提烘笼的手立刻变得暖暖和和。最好是坐在低矮的竹椅上,将烘笼放在围腰下面,双脚之间,将手伸进围腰,手和脚都同时受益——几星微火就能让全身暖酥酥的。有些卖火人会担着担子沿街叫卖。卖抄手、担担面等小吃的商贩经过,与之协商,也能得到方便,添加燃料。
给烘笼加一次火,能用三两个小时,费钱极少,却令成都人、尤其是老人在阴郁潮湿的冬天不那么瑟缩。卖火的营生虽然收入微薄,却真的予人以极大方便。上世纪40年代初寓居成都的何满子,被这一街景中的人情味所打动:“此类行业之存,也说明了旧时代缺乏生计的贫民之多。只有无以为生的人,才会干这类琐屑的营生,赚几个零星的小钱,自己暴露在凄冷的寒风之中而为旁人散播温暖。但这种顽强的求生意志用之于为他人服务,毕竟是令人感念的。”
【水 碾】
清末成都全城每日需用米500石左右,所以运米进城的牛车、鸡公车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后因鸡公车太易损坏路面街石,警局禁止其入城,只用牛车运米。如果荒年歉收,或连日阴雨绵绵,土路泥泞不堪,牛车无法行走,这时官府会开仓碾米平抑米价。光绪末年,城内粮仓如皇城的丰裕仓等共储有谷子60万石,可备全城三年之需。这时,城边的各处水碾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全市有东门苏家碾、余家碾,西门王家碾、陈家碾、将军碾,北门肖家碾等20来处水碾。碾房都引渠水冲碾,由二三个工人轮流值班,每昼夜可出米20余石。川西平原盛产稻米,水碾比旱碾省力,它加工的米又比人工臼或依赖畜力的旱碾所出更匀净白洁,因而水碾的工人虽不多,却是很受欢迎的角色。一说到成都居住的优越性,老成都人往往会脱口而出:米好。
【挑 水】
市民离不开的还有担水人。
从前,居民的吃喝用水不是井水就是河水。成都地下水位高,一般掘地数尺便有水,清末城区有水井2500多眼,遍布各处。到1927年,城区水井已增加到2795口。当时,成都在册的挑水人有400多人,他们既挑河水也挑井水,由警局分段编了号,各人按街道分段,分户挑水。河水距离远些,价也高些。因而有的家庭就将河水、井水分别使用,前者煮饭泡茶,后者洗衣洗漱。
一般人家里都至少有一只大水缸,挑水人每天来给倒满。离河流近的人家付给卖水人的工钱很便宜,离河远的稍贵点,但每月所费,都不算多。
卖水人往往边走边吆喝着节奏短促的号子,一来是减轻疲劳,二来也招呼行人让路。到了送水人家门口,则提高声调,用以招呼主人。留心一看可知,卖水人都是赤脚,这既为节约,更包含一种职业道德:他们汲水时总是要涉水朝河心处走,尽量避开河岸边洗菜淘米洗衣服的人们。若有人问起,为自己“讲良心”而骄傲的卖水人会正色道:当然,我们卖的是河心水,没得一丝丝脏的。清代宣统年间,每担河水的价格为16至24文,井水则只需两三文一担。
自来水的普及使挑水这一职业永远成为历史了,而锦江的清波碧浪,也成为老成都人脑海中一段渺远的旧梦。
【剪 发】
从前,看一个男人是不是清雅整洁,只须打量他的头面是否光鲜——辫子梳得可光滑?前额剃得干净否?标准非常简单。至于女人,她们虽然也想方设法在头上摆弄有限的花样,却根本就无需进理发店。
老成都人把理发叫作上理发铺或称去剃头。宣统年间,成都有理发铺619家,还有一些挑着担子沿街流动服务的。梳辫子一次20至30文,剃发一次30至40文。理发铺的围单、面巾、梳子、篦子往往污秽不堪,所以,讲究的人家都自己预备理发工具,将剃头师傅叫上门来服务。比起今天的发型师,剃头师傅那套头上功夫简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约也缘于此,他们收入不高,是为数不少却容易被小觑的一群人。
等到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相继爆发后,大汉四川军政府1911年11月底在成都宣告成立,尹昌衡担任都督后,发布剪发令——因为梳辫子是满清政府强令推行的,现在既已光复,汉人当然应该革除这一旧俗。赞成并自愿剪发的人很多,也有不少老百姓出于惯性,一时还难以割舍。军政府就在几个城门口挂起大剪刀,那些当兵的不由分说,遇见梳辫子的男人,拉过来咔嚓一下,剪掉了事。刚开始那一阵子,竟然有人为了保住辫子,不肯出门。而必须进出城门谋生的那些脚夫、商贩、农民等,辫子往往最先遭剪。他们相互看着剩余头发披散的模样,一时又惊又恼又喜。
大势所趋,男人的辫子已荡然无存。剃头师傅只精通为人剃光前额、梳理辫子那套程序,如今面临新的挑战,必须学会打理短发。有的客人不太讲究,把周围剪整齐就行了。但是新派人士满口洋话,就不那么好懂了,有人要理个什么拿破仑式,有人则想要华盛顿式……原来,前者是偏分式,后者是中分式。好在,理发师们很快就能与时俱进了。
当时,成都妇女剪发也蔚然成风。女学生最先引领风潮,她们不仰仗理发师,相互动手剪掉辫子再略为修剪就行了。起初也不讲究式样,不过是前面一排刘海,后面有的齐耳,有的齐肩。就算这么简单,走上街头,已经相當引人注目。专为女客烫发、剪发而花样百出的新式理发店,要等到1930年代才慢慢兴起。
【接 生】
西医刚传入成都的时候,人们还不大能接受产妇在医院生孩子的新派做法,即使公馆里有钱人家的妇女,也大多羞于上医院。接生婆(又称捡生婆、稳婆)算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职业,她们多由不谙脉理、不通药方的贫家妇女担当。据傅崇矩的《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时接生婆每接生一次,之前付定钱一两百文,临行给轿钱一两百文。喜钱的多少,则与新生儿的性别有关,也要视产妇生产时是否顺利——若接生的是男孩,可得1000至2000文,是女孩则几百至1000文。
因为无知,生孩子的过程也被蒙上了神秘色彩:临产之时,床前燃七星灯,所有箱柜抽屉均打开不关,否则孩子难以下地;产妇房门必须用锁倒锁上,否则乳汁会被生人带走;孩子降生,要用葱叶洗口,如此才会聪明……有些荒诞不经的做法葬送了产妇、胎儿的性命,不知令多少亲属扼腕叹息。破伤风在当时的四川极为普遍,很多新生儿死于此病,因为接生婆往往用脏的刀、剪切割脐带,还有人抓一把稻草或泥巴糊上婴儿肚脐。
有鉴于此,在人们对西医普遍陌生甚至排斥的年代,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呼吁:接生工作应由医生的妻女、家属担任,她们应知书识理,会切脉定方,并应通过资格考试——这些当时很前卫的声音仍然不加考虑地将医生本人(当然是男性)排除在产妇的门外。由训练有素的助产士接生或上医院生孩子,是后来的事了。
距离华西协和大学不远的小天竺街,有一幢朴素的两层木楼,成都式的青灰色瓦屋顶,中间一个院落,一口井。美国医生、传教士玛利安·曼利开办的助产士学校兼小型妇产科医院,就设在此地。一半木楼里住着来自四川各地的二三十位学员,她们在此接受三年培训,成为合格的助产士后,大多会到四川的小城市开办诊所。
木楼的另一半是病房、手术室和门诊室。医院有五六个完全合格的助产士与3名教师,可以同时接收20至25个病人,还有一个可容纳30多个婴儿的托儿所。产科、妇科的疑难病症由玛利安亲自处置。医院收费有好几个等级,有钱人多付一些,穷人少付一些或者免费。
1939年,心情低落的韩素音进入这所学校学习。学员们除了上课,也经常跟着助产士到各种各样的产妇家里接生。忙碌使韩素音暂时摆脱了在重庆当家庭主妇的沉闷与婚姻的愁烦,也更宽泛地接触到父亲家族(成都著名士绅家庭)之外不同阶层的生活——从拥有深宅大院与好几房姨太太的军阀,到茅檐摇晃、衣不蔽体的穷家小户,了解到妇女受制于旧俗、难以自主的窘迫处境。
韩素音在其自传《寂夏》中写到的助产士马小姐,在成为自信的职业女性之前,有过曲折伤痛的经历。马小姐40岁左右,从小被父母卖掉,后因得了天花而成为麻脸。她的脚是缠过又放开的,却居然可以一瘸一拐、不知疲倦地走好几英里。之前给人当丫头时,马小姐两次逃跑未遂,被女主人用篾片痛打,背上与腿上一直留有伤痕。后来她被逼给一个小店主、有几个女儿的老鳏夫当小老婆,他想让她生儿子,整整用了一周她才在暴力下屈服,但两年都未怀孕。马小姐的命运是再次被卖或被扫地出门,甚至沦落妓院。之后,她当过女佣又再次逃跑,最后幸运地遇到一位仁慈的女主人——半身不遂、眼睛半瞎的老太太。她悉心照顾老太太,后者请了一位老师教她念书写字,马小姐最终成为一名助产士。她痛恨男人,憎恶婚姻,决心终身不嫁人。她的遭遇让人看到,民国前期,虽然提高妇女权益的声音已经此起彼伏地响起,但底层妇女谋求独立自主之路,依然艰难崎岖。
【奶 妈】
以前,喂养婴儿可没有多少代乳品可供选择,旧时婴儿能吃到的是千年不变的母乳。当奶妈也是老成都贫困妇女所能觅到的职业之一——有钱人家的太太生了孩子不愿亲自喂养,可以花钱雇奶妈给孩子哺乳。1908年左右,奶妈每月工钱为2000文至3000文,由主人供给衣服,比起女仆或看门大爷的每月600至800文工钱,要高许多。由于别无选择,那时人们只能用最原始、自然的方式喂养婴儿。殊不知,后来的人比较过很多喂养方式后,才发现还是由母亲亲自担任“奶妈”最完美无缺。
当时,公馆里除了女仆、跟班、看门人、厨师(当时称为厨子),还会雇佣花匠(人称花儿匠)。若是深宅大院,为着安全考虑,也会雇佣更夫巡夜。更夫的月工钱仅五六百文,跟班也不超过1000文。花匠与厨师技术含金量高些,视手艺的高低,月工资可达2000至3000文。为厨师打杂烧火洗菜烧水的叫下手,收入则低得多。
其他工匠,木工、泥工每日工钱96文,三天食肉一次。裁缝的待遇与之相仿,但每日另有6文烟钱。如果缝制嫁衣,开工前可以向主人索要一两百文喜钱。
同一时期的公务人员,收入则相对高得多。官报书局的总办月薪200两银,编辑月薪80两,校对、采办、文牍等职员月薪四五十两。机器局总办与制造委员月薪均为200两银,制造、采买、文案等员工,月薪三四十两。矿务总局的总办月薪100两银,其余办公人员也是三四十两。当时一两银约折合一千四五百文。
【婢 妾】
清末民初,官绅之家纳姬蓄婢,被视为寻常小事。对于那些为谋求子嗣而纳妾者,旁人比较能体谅,觉得他有不得已的苦衷。而有的男人七姬八妾,也会让亲友摇头叹息——姬妾成群,争宠斗妍,往往酿成各种事端,或凭添风流孽缘惹人嗤笑,或增加至亲骨肉之间的嫌隙,甚至引发家庭惨案。
婢女地位低下。没能生下一男半女的妾,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有的人今天还是张三之妾,明天就随手被赠给李四;有的女子起初为妾,不久又被降为婢女。当时讲究维新,婢与妾也各有了一个新名词,婢女叫锅边菜,妾则叫耍耍妻,“所谓招之可以使来,弃之不甚可惜者。”(徐心余《蜀游闻见录》)这种称谓毫不遮掩对婢与妾的轻亵、轻蔑,所谓新名词,实则老旧而粗劣。
虽然早在1910年,清政府已颁布禁止买卖人口的法令,但是直到上世纪30年代,买婢蓄妾的旧习在成都等城市依然没有绝迹。贫家女子也就经常被卖来卖去,或者像礼品一样被送来送去,她们往往才十一二岁就充任使女。当年青石桥、盐道街一带,常有“人经纪”也即人贩子聚集,雇请丫鬟乳母的家庭,或贫困人家鬻女,一般都由人贩子居中介绍。时不时要增补丫鬟仆妇的公馆,则有熟悉的人贩子上门服务。

在新文化運动中以批判封建礼教而著名的学者吴虞,就多次与人贩子打交道。1918年,他以8元钱买了一个才11岁、来自中江的王姓姑娘,给她取名小梅;次年,他又买了一个叫仙禽的丫鬟,将她的名字改为瑶华;过了将近20年,成都物价已经大幅度上涨,但丫鬟的价格却似乎变化不大,吴虞1938年买回12岁的童素真,仅10元钱(另付中介费1元),随即又买了一个11岁、来自广安的丫头,取名张岫云——这些女孩,连名字都无法自主。素真来了才十来天,吴虞不太满意,让人贩子将她带走,后来素真被转卖到梨花街某公馆。
吴虞的妻子曾兰与他结婚时才15岁。吴虞性格偏狭,与父亲矛盾尖锐,但他与曾兰却彼此欣赏,关系融洽,在旧式婚姻中十分难得。曾兰在成都以书法知名,一笔篆字尤其惊艳;她还是著名的女权运动家,民国初年作为四川第一份妇女报纸《女界报》的主笔,撰写了不少批判男尊女卑、提倡妇女解放与女子教育的文章,强调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应与男子平等,反响颇大。随后,曾兰还在北京《新青年》、上海《小说月报》等期刊发表文章,还创作过有关女性权益的剧本。
曾兰与吴虞生了九女一男,唯一的儿子在婴儿时就夭折了。在1917年42岁去世之前,作为妇女解放先驱者的曾兰,也曾经很费心地为丈夫购买并调教小妾。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同样有“一夫一妻之主张”,提倡男女平权,另一面又希冀老年得子,也热衷于置妾。1931年,59岁的吴虞买回十五六岁的彭姓姑娘。据吴虞的讲述,好像是因为妻女相劝,自己又心生怜悯,才留下彭姑娘的。但实际上,无论之前之后,他都兴致勃勃地多次买妾。大半年后,彭姑娘请求归家,平时在银钱上斤斤计较的吴虞,这一次十分慷慨大方,命人将这位小老乡送回新繁父母家,之前的60元身价银也不索回了,就送给彭姑娘做嫁妆,嘱咐其父母不要再卖女儿。待到姑娘涕泣拜辞,他因了却一事而“如释重负”,也略感郁闷:“盖徒负纳妾之名,并无纳妾之实,反多惹烦恼,太不值也。”而彭姑娘回家不久就遭逢噩运,父母以30元将她卖给一个流氓。
比较一下当年的工资与物价——1931年,适逢成都“百货昂贵,银价飞腾”,居民的日常花销已上涨许多,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依然不高,且每天工作时间达10至11小时。兵工厂的工人,月薪为20元,造币厂工人月薪10元,均自理伙食;石工、厨工、油漆工、裁缝、制帽共、泥工、机关杂役等,由雇主供给伙食,月薪为六七元。金银首饰匠人比其他工匠收入稍高,每月可达12元……在这样的物价水平下,彭姑娘的父母,以30元或60元就卖掉女儿,令人欷歔。
1939年冬,16岁的惠卿被吴妻以100元为吴虞买回。惠卿家在新繁开有一家彩灯铺,但父亲去世后,她与母亲、祖母、弟妹度日维艰,家里不得已将少女卖给年近七旬的老翁为妾。
像商品一样被卖为婢妾的女子,是特别心酸无奈的人群。
【女 工】
对于那些没有婢女的人家,洗衣的妇女带来的方便不言而喻。衣服既可按件零计,也可包月。每月花销不多,衣服被褥床单就可干净熨帖。遇到纽扣脱落之类的小毛病,好心的洗衣妇还会帮顾客缝补妥贴。单身的客居者对此最为感激。
女革命家胡兰畦在《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年)》中讲述,民国初期,成都石马巷有所女子缝纫学校,教授机器缝衣,吸引了许多妇女前往学习,她的母亲也去学了3个月。
这个学校其实是为了推销美国胜家公司的缝纫机而建立的,在当时的成都,缝纫机非常稀有,它比手工缝制快得多,针脚又细密整齐,很令女人们神往。厂家相当舍得下功夫做宣传,在大街小巷张贴了许多花花绿绿的广告,承诺对缝纫机的用户包教包修,五年保用,因而石马巷的缝纫学校热闹一时。
胡兰畦的母亲学成以后,还利用自家的右厢房,办起了一所机器缝纫学校,她希望女人有一技傍身,能够自立谋生。胡兰畦的启蒙老师曹师母也来兼课,教学员们识字、写字、记账、写收条,另有两位女教师教大家剪裁、做花。这些课程非常实用,学校小有名气,有几十位少妇、少女来此上学。
后来,成都兴办了一系列女子实业学校,开设缝纫、化工、养蚕、种桑、手工艺等技术课。招收的学员当中,有人得以靠一技之长,成为民国早期的职业妇女;还有人借此拓宽眼界,参与社会活动,在“五四”之后成为活跃的妇女运动家,比如茅盾长篇小说《虹》的原型秦德君。
【手 艺】
从前,搓纸捻子卖的贫家妇人也不少。草纸做成的纸捻子供烟铺出售,用于点叶子烟。缭绕着呛人辛辣气的叶子烟,是老派男人的至爱,一根烟杆一根纸捻的形象,差不多是与平和、满足的心境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烟瘾缠身的人来说,没有叶子烟的日子是无法想象的;而若是失去搓纸捻子的营生,很多家庭恐怕会更捉襟见肘,因为这类费时间却不花力气的活计,妇孺老幼皆可为,真的帮许多人家贴补了家用。
如同冬天有人卖火炭出售温暖,夏天也有人销售“荫凉”。用竹篾条编成的竹凉席做工细腻,大热天肌肤接触竹席,相对清凉。摩挲日久的旧凉席光滑熨帖,最为舒服,有点破损还真舍不得扔。有人就瞅准了售后服务这行,带着篾条沿街吆喝“补凉席”。小孩子则在茶铺、戏院等公共场所替人摇扇,充当人力电风扇。
技艺高超的手艺人仿佛什么都能补。除了补凉席,還有补扇子的,有补伞、补锅、补碗、补坛子、补棉絮、补衣的。这类职业将大量市民物质匮乏的生存状态暴露无遗,同时却也显露了手艺人化腐朽为神奇的回春妙术。服务性行业的发达,则让市民必然拥有了居家度日的舒适与实惠。
一根扁担,一个竹篮,或一把力气,一身手艺,负载着谋生的家当,走街串巷。老成都有无数这样的手艺人和出卖劳力的人,他们构成了这个城市散漫、凝重的底色。他们是面对现实的一群,在可触可摸的小营生中赚些小钱,养家糊口,安身立命。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