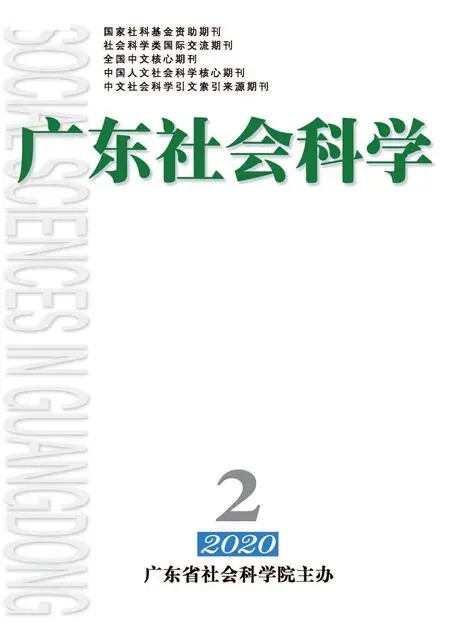概念发生与公孙龙子诸论篇的解读
吴汉民
《公孙龙子》共包含五篇文论:《坚白论》、《白马论》、《指物论》、《名实论》、《通变论》。《指物论》被认为是《公孙龙子》诸篇中语义最艰深的篇章,笔者已全文解读①(以下称为前篇)。《指物论》的讨论涉及到对其他论篇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对其他论篇也做出解读。前篇解读以“概念发生”理论为基础,此篇与前篇同一理论,前篇已述理论,此篇不再赘述,故需联系参照前篇。五论篇贯通的解读,进一步展现公孙龙概念思维的主线,更有利于揭示公孙龙概念思维的深刻性。
一、《指物论》与《名实论》
《指物论》的“指”与《名实论》的“实”,如何区别,成为一些解读的困惑。
前篇已述人类初始建立概念的过程。人类的概念库建构完成后,使用概念时有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这个概念怎样理解?第二,这个物是什么?在熟悉的概念环境中,以上问题似乎不存在困扰。但在人们遇到不明白的概念与物时,问题成为:第一,这个概念怎样理解,指的是什么?如,“美”怎样理解?“美”指的是什么?第二,面对一个陌生物,问这是什么?这是蜗牛。蜗牛是牛吗?如何表达这样的概念与物,就成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公孙龙是人类最早开始思考的智者之一。
《指物论》,是公孙龙对“这个概念怎样理解,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的回答。名称指物,不是问题,手指现场物,没有必要解释,只有概念指物,才需要说明。如前篇所述:概念指属性,不指物;属性在物中,指属性要指物;指物指类,不指固定的个体物。如,“美”指的是什么?答:至今“美”没有明确统一的文字定义,唯有举例,例1,例2,例3,……。此为“非指”。
《名实论》,是公孙龙对“这个物是什么”的回答。“这个物是什么”,是以概念规定物,给以称谓,归类操作。如问:这是什么?这是蜗牛。蜗牛是牛吗?蜗牛不是牛,蜗牛是软体动物。
“指”与“实”的区别。指: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的外在表达)。实:这个物是什么(物的归类操作)。
现在做《名实论》解读。开头语:
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
天地及其所产生的东西,为“物”,自然之物。(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
物,以物的概念,规定为此物(物以物其所物)。即:自然之物,以物的概念做规定,自然之物转变为有规定性的物,表达为“这是什么”,此为“实”。(实:实在内容;通“寔”,是,此。②)确认这是什么,不是什么,明确定性,清楚划界,为“不过”。物没有规定,什么也不是,自然物只是“存在”,并不是“是什么”。物被概念规定后,称为“这是什么”,才是“实”。《名实论》就是讨论概念对物的规定。
概念规定“这是什么”,实质是归类操作。概念规定物的归类操作,有两个方面:
第一,概念的规定。以概念的名称,给以称谓“这是什么”,此为观念中的归类操作。
第二,现实的归类操作。物必须能够放入现实的相应类中,以展示此物是此类中的物。
概念规定“这是什么”,以现实的归类操作,完成观念的归类操作(实以实其所实),此即“位”。(位:就位,使居其位。③)物居其位,不能缺失,为“不旷”。(旷:空缺④)
概念为物定性为“实”,物要放入类中为“位”。前篇已述,人类概念思维的矛盾是:属性在思维中与对象物可分离,属性在现实中与对象物无法分离。概念以称谓规定物是思维中的操作,通常以语词表达。现实的操作要把物归入类中,多个物的叠加呈现才能外在地显现思维所要分离的属性。语词的表达必须要以现实的归类操作为基础。
因此,物的规定与物的归类要一致。规定的物不在规定的类中,是“非位”。规定的物位于规定的类中,为“正”。(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
《名实论》此后的论述,都是在说明应该如何归类操作。(限于篇幅,不做逐句解读。)
故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其以当而当也。以当而当,正也。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
(为表达简明,以符号代替。彼:B;此:A。)
所以,B把B当作B,且仅当作B,才能说这是B。A把A当作A,且仅当作A,才能说这是A。(故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也就是说,把B规定为B,且归入B类中,才能说“这是B”。此即为“这是什么”的两个方面:第一,规定;第二,归类。
这就是以“当作什么”而去“当作什么”。以“当作什么”而去“当作什么”,为“正”。(其以当而当也。以当而当,正也。)前“当作什么”是概念规定物;后“当作什么”是物归入规定的类中。前后一致即为正。
所以,B规定为B,必须是在B类中(止于B);A规定为A,必须是在A类中(止于A),这才可以。把B当作了A,既在B类中 ,又在A类中;把A当作了B,既在A类中,又在B类中,是不可以的。(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规定为B,却归入A类,这是用“类”又规定对象为A,与概念规定为B不一致了,这是不可以的。
需要说明的是,公孙龙不是说一物不能做多种规定。实际上任何物都可以做多种规定。公孙龙反对的是规定与归类的不一致,要求规定与归类必须一致。一物规定为A,就要归入A类中,不能归入B类中。这不是说此物不能规定为B,但规定为B就要归入B类中,不可规定为B却归入A类中。菠萝是水果,也可以当蔬菜,完全可以做多种规定。但做了某一规定后,规定与归类必须一致,不能把已经与牛肉炒成菜的菠萝,当水果端上来。这即是以“当作什么”而要去“当作什么”。
概念规定与归类操作可能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任何事物都具有多种属性。概念规定分离某一属性,归类操作再次分离属性,两次分离的属性是否一致成为问题。公孙龙强调了规定与归类必须一致。
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 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
名,就是“概念规定物”(实)的表达。(夫名,实谓也。)给规定物的概念一个名称,以这个名称称谓物,以“这是什么”的句式,表达概念对物的规定:这是A。但这个规定是否合适,要看与现实的归类操作是否一致,如果条件不能满足,就不能说这是A。所以:
知道A不是A,知道A不在A类中,就不能称A是A。知道B不是B,知道B不在B类中,就不能称B是B。(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
“指”“实”“名”的关系。
前文已述“指”与“实”的区别。概念无法用语词表达时,需要外在表达为类的展示。概念规定物时,在称谓之外,要把物归入类中。二者都涉及到类的操作,因为归类操作是本源。这是二者的交叉与重叠,但二者的性质不同。概念做表达时的类操作(指),是属性已经分离出来,为展示所分离的属性,通过类的多个对象叠加呈现分离的属性。概念规定物的类操作(实),是把物归入确定的类中,通过类完成属性的分离,使物有明确的概念标示,表达为“这个物是什么”。
名与实,是对概念规定物的操作的表达。这个物是什么,规定与归类要一致。
名与指,是概念外在表达操作时的区别。名称指物整体;概念指属性。
人类早期1:1的专有名词阶段过后,除了必要的专有名词以外,名称基本上都是概念的名称,因为人类的表达是以概念名称表达不在场的对象物为最普遍的表达方式。概念名称,类群名称,个物名称,人类以同一语词表达,如“鱼”。因为是同一语词,概念也可以当名称用,然而概念指类,不指固定个体物。一类有多个个体,要区分就需要使用限定词,以指向特定的个体,因此现实中“有特指”的名称是识别名称,“非特指”的是概念名称。
概念也指单个物,但是有条件:1、概念库已建构完成;2、要有限定词。概念库建构完成后的概念使用,与概念的初始发生有不同。这时表达概念无需划定一个类群,因为概念和对象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举一例即可知相对应的类。这样人类在运用熟悉的概念时,概念和名称都成为与对象物1:1的关系,概念与名称的重叠性更强,更不容易区分概念与名称,所以公孙龙在《指物论》中专门论述了“指”与“名”的关系。概念与名称的区别与重叠,前篇已有论述。
然而人们在遇到不明白的概念时,仍然需要列举出多个对象物。举例数量的多少与人们对于概念和对象类的熟悉和理解程度相关。越是难以明白的概念,越陌生的概念,需要的举例就越多,直到举例形成足够多的大类群。大类群多数量的对象物的叠加,为理解者提供了理解的“读本”。这实际是返回到初始的归类操作,重演了概念建立的过程,以展示这个概念表达的意思。
长期的熟悉概念的运用,陌生概念的日渐减少,使得人们已经忽视了概念的原初归类操作。概括论即是人们在长期使用和学习熟悉概念的环境中,对概念的一种理解和表达。现在需要揭示长期使用熟悉概念所掩蔽的概念的初始归类操作。
人类概念思维的核心,在思维内部是分离的属性,在外部就是归类操作。两种归类操作:1、没有概念,建立概念的归类操作,前篇“概念发生”已有论述。2、已有概念,概念规定物的归类操作,《名实论》就是说明概念规定物的归类操作。
二、归类操作与《通变论》
在《名实论》论述了概念对物的规定及其归类操作之后,公孙龙在《通变论》中进一步论述概念与概念的合并及其归类操作。
概念合并的实质是归类操作,不是复合概念。把《通变论》理解为概念与概念合并而成复合概念,实为误区。概念有名称,以语词表达,如果不能把概念名称与识别名称区分清楚,就会把概念的合并误解为语词的合并。语词有复合词,概念没有复合概念。
公孙龙对概念合并的理解,已经触及到现代关于概念分层的思想。现代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对概念进行了分层:基本概念,上位概念,下位概念。
“我们把处于层次图中间地带的类别称为类别的基本水平,较高的水平称为类别的上位水平,而比基本水平更具体的类别水平则是类别的下位水平。”⑤
“人类概念层次具有三个水平,即是上位水平(如武器、家具)、基本水平(如抢、椅子)和特定概念的下位水平(如手枪、来复枪、厨椅、安乐椅)。”⑥
基本概念。一个概念是一个类,一个名称统称个物和类,如“苹果”。“苹果”可以称谓一个苹果,也称谓整体的苹果类,类与个物使用同一个名称。
上位概念不同。上位概念是类与类的合并,由多个类构成上位概念,如“桃和梨合称水果”。这一上位概念包含了3个名称。因此,上位概念的称谓,与构成上位概念的各个子类的名称各不相同,不使用同一个名称。《通变论》以此开始。
曰:二有一乎?曰:二无一。
“二”:上位概念。公孙龙的时代没有概念一词,更没有上位概念一词,但公孙龙已经有了概念分层的意识。公孙龙认识到至少要有两个基本概念才能组成上位概念,因此以“二”表达上位概念。这在当时已经是对概念思维非常深入的理解,因为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不清楚概念分层,以至于无法理解“二无一”。
问:“二”这个上位概念,可以用一个名称统称类与子类吗?
答:上位概念的类与子类,没有一个统一使用的名称。
曰:二有右乎?曰:二无右。曰:二有左乎?曰:二无左。
以“二”表达上位概念,是先设定有两个子类。这是最基本的设定,一个上位概念至少要有两个子类,“左”“右”是表达两个不同的子类。
问:从上位概念的称谓中可以体现出“右”子类吗?
答:上位概念的称谓中体现不出“右”子类,同样也体现不出“左”子类。(即从上位概念的称谓中体现不出所包含的子类,如从“水果”的概念中,看不出是桃还是梨,但从苹果的概念中,可以看出所包含的是苹果。)
曰:二苟无左,又无右,二者左与右,奈何?
(曰:右可谓二乎?……安可谓变?省略)
问:“二”这个上位概念,既体现不出“左”子类,也体现不出“右”子类,可是“左”“右”两个子类合起来,却可以称为上位概念“二”,为什么?
公孙龙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了更深刻的思想。基本概念的类概念,可以通过归纳方法获得,如苹果的类概念,通过1,2,3,……N个苹果,归纳得出。上位概念无法通过归纳方法获得。桃和梨的上位概念可以是水果,可以是蔷薇科植物,还可以是果酒原料。
令人惊奇的是,两千三百年前的公孙龙竟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也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上位概念的产生不是概括论能够说明的。
公孙龙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
羊合牛非马,牛合羊非鸡。
答:羊合牛不包括马。牛合羊不包括鸡。
这个回答不是上位概念产生的全部,但却是极其聪明的回答。在当时,对羊和牛合起来给予什么样的上位概念称谓都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下,在当时还远没有近代才出现的动植物分类知识体系的情况下,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给出这样的回答,真的是很了不起!
公孙龙举例“羊合牛”,正是所说“左”“右”两个子类基本概念,合成“二”这个上位概念。可是很少见到以“羊合牛”为例,解读“二、一、左、右”的合并与分层,原因在于不了解概念的上下分层。
上位概念是类与类的合并,多样性大幅增加,出现多个共有属性,不同于基本概念的归纳所得只有一个共性,即是归类标准属性。上位概念拥有多个共有属性,如何从中选择合并类的归类标准属性,成为问题。
公孙龙的方法是,提供一个参照物:马。通过“非马者,无马也”,即“羊合牛”的类中不包括马,从而排除与马也共有的属性,如食草类。确立“羊合牛非马”,就是不能以“食草类”作为“羊合牛”的归类标准属性。“羊合牛”的归类标准属性是什么,公孙龙没有说,但公孙龙通过“非马”做出了示意。在现代动物分类体系中,羊和牛属于偶蹄目,马属于奇蹄目;动物分类有食肉目,但没有食草目。
曰:羊与牛唯异,羊有齿,牛无齿,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类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类之不同也。
羊牛有角 ,马无角,马有尾,羊牛无尾,故曰羊合牛非马也。非马者,无马也。无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马,可也。
答:举出羊和牛的差异,如羊有门齿,牛没门齿,由此说牛不是羊,羊不是牛,不可以。门齿虽不是共有,但羊和牛是同类。举出羊有角,牛也有角,由此说牛就是羊,羊就是牛,不可以。角虽是共有,但羊和牛不同。
羊牛有角,马没有角。马有尾,羊牛没尾。所以说羊和牛是同类,与马不同类。与马不同类即不包括马。不包括马,仅有羊也构不成上位概念“二”,仅有牛也不行。羊和牛合起来才能构成上位概念“二”,成为羊和牛的合并类而不包括马,这才可以。
若举而以是,犹类之不同。若左右,犹是举。
像这样列举属性(要有参照物),才能区分类的不同,以确定类别。如果要区分左右子类,也同样应该这样列举属性。
对于类类合并来说,由于包含多个类,各个类不同,各个类又有多个子要素,所以类类合并包含的要素很多,各类之间均可以找到共同性,也都可以找到差异性。如,羊和牛的齿与角。因此,仅仅是寻找共同性和差异性,并不能合理地划分类,必须还要有其他的参照物,以排除不需要的共同性或差异性。如,以马作为羊和牛的参照物,比较相互之间有和没有的角和尾。
故曰牛合羊非鸡,非有以非鸡也。与马以鸡,宁马。
由此也可以说“牛合羊非鸡”,用“非有”的表达式,以“非鸡”作为牛羊的参照物。但鸡与马相比,宁可用马作为参照物。
材不材,其无以类,审矣!
材:做参照物的材料。鸡不能做牛羊的参照物(材不材),因为鸡与牛羊相隔的类别太远。这就是理由!马与牛羊虽不是同类,但却是相邻平行的类。鸡则不是。
举是乱名,是谓狂举。
(曰:他辩 …… 其无有以正焉。省略)
因此,不顾类别之间的相互关系列举参照物,是狂乱的列举。
概念合并的实质是归类操作。类类合并不同于个物的归类。难能可贵的是,公孙龙以参照物确定类类合并的方法所包含的思想:上位概念不是对多项子类概念归纳产生的;如何从类类合并出现的多项共有属性中选择新的合并类归类标准;如何选择参照物的类别,以表达合并类的类别和层面。这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三、《坚白论》与《白马论》
《坚白论》限于篇幅,不做逐句解读。仅看公孙龙《坚白论》的最后回答。
曰: 目不能坚,手不能白,不可谓无坚,不可谓无白。其异任也,其无以代也。坚白域于石,恶乎离 ?
曰: 坚未与石为坚而物兼。未与物为坚而坚必坚。其不坚石物而坚。天下未有若坚而坚藏。白固不能自白,恶能白石物乎 ? 若白者必白,则不白石物而白焉。黄黑与之然。石其无有,恶取坚白石乎 ? 故离也。离也者,因是。力与知果不若,因是。且犹白以目见,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坚以手,而手以捶,是捶与手知,而不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谓离焉。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
问:看不到坚硬,摸不到白色,不能说没有坚硬,不能说没有白色。只是观看和触摸的感知功能不同,不能相互替代。坚硬和白色都存在于石头中,怎么能说分离?
答:坚硬不是存在于石头才有坚硬,坚硬在所有的物中都是坚硬。不是与物结合才有坚硬,坚硬就是坚硬,不是有了坚硬的石和物才有坚硬。天下没有这样独立存在的坚硬,是因为这样的坚硬是隐藏着的。(公孙龙意识到,坚硬作为分离的属性,仅存在于人类的思维中。)
白色如果不能自身就是白色,怎么能使石头或物成为白色?如果白色自身就是白色,则不因为有白色的石头和白色的物才有白色。黄色、黑色也是如此。石头如果不是自身即为石头,怎么能成为坚硬的白色的石头?所以,坚硬、白色、石头,是相互分离的。所说的分离,就是如此。肢体感触与思维终究不同,即是如此。
就如同(公孙龙叙述了一个逐步分离的过程),白色以眼睛看到,眼睛凭借火光看到,到用火光也看不到。用火光和眼睛都看不到的白色,还可以在人们的想象中呈现(神见)。到想象的白也不见时(还能够言语和思考“白”),这就是抽象的白,概念的白,这就是分离的属性。
坚硬是手触摸的感知,用手握锤,是锤给手传递了感知(中间物介入开始分离),到手通过锤也感知不到坚硬,成为想象中的坚硬,到想象也不呈现的坚硬(坚硬与感知已完全分离),神奇啊,这就是分离的属性。
分离的属性构成世界。概念分离出来的独立的属性,是构成(规定)万事万物的根据!(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
公孙龙的回答已经表现出非常成熟的概念思维:任何对象都具有多种属性,人类的认知是从对象物选择和分离属性;人类的不同感官感知不同的属性,属性与属性分离;从感知到概念思维,属性与对象物分离;独立于物的分离的属性构成世界。这已经近似于两千年后黑格尔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⑦黑格尔以概念重建对象,公孙龙表达主体对概念的实际运用。
以概括论理解《坚白论》,可能会有解读的困扰。概念发生论的理解,“概念是思维中分离的属性”,几乎可以直接作为《坚白论》的主题。
《白马论》限于篇幅,不做逐句解读。《白马论》主要论述了三点。
第一,马者,形也;白者,色也。两个不同的属性,这是基本的出发点。(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第二,两个不同的属性,标志两个不同的类。归类对象的不同,证明这是两个不同的类。(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第三,此后所述,均为第三个问题:白马的概念中,白与马的关系。反方:白马中有马,所以白马是马。正方:白马是一个独立的类概念,白马不是马。围绕三个问题争论。
第一,马可不可无色。正方:无色后,还有马,但没了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第二,可不可以白命马。正方:以白命马,白马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反方:以白命马,命名错了,白马不是一个独立的类。公孙龙用反证的方法说明,如果白马不是一个独立的类,说有白马为有马,推论的结果是黄马不是马。可以说黄马非马,为什么不可以说白马非马。(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第三,白马的白可不可分离出去,因而有白马为有马。正方:白马的白不可分离。如果可分离,白马的马也可分离,只剩下了白。白与马是固定组合,标志一个独立的“白马”归类标准。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
“白”作为单一属性,不当作与物固定结合的属性时,可以被忽略,如说“椅子”时,可以不考虑颜色。但“白马”的“白”,是与马固定结合为独立的类标准。这种固定的类标准中的“白”,不同于单一属性的“白”,是不能“忘之而可”的。
马,是没有固定颜色的类标准,不按照颜色做取舍,所以黄马、黑马都可以进入此类。(无去:没有取舍。取于色:按照颜色。)
白马,是有固定颜色的类标准,按照颜色取舍,黄马、黑马都因为颜色不合标准被排除(以色去),所以只有白马可以进入此类。“没有固定颜色的类”与“有固定颜色的类”是不同的,所以说“白马非马”。
其实,按照“马者,形也;白者,色也”的认知,马可以称为“形马”。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白马”和“形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类,所以“白马类”非“形马类”。只不过公孙龙说,“故其为有马也,不可以谓马马也”。“马马”的前马为类标志,“马马”可称为“形马”,与“白马”相对。公孙龙的意思是说,已经说了“马者,所以命形也”,因此一个“马”字就可以了,用不着“马马”即“形马”了。
公孙龙在《白马论》中表达了如下的思想:
第一,分离的属性是独立的属性,不分高低上下,如“形”和“色”。
第二,属性的独立性表现在下位概念不受基本概念的束缚。《通变论》涉及到上位概念,《白马论》涉及到下位概念。“马”是基本概念,“白马”是下位概念,与上位概念不同,基本概念的称谓包含下位概念,都有“马”。下位概念隶属于基本概念,这是常识。公孙龙的辩论在于打破常识,把下位概念与基本概念平行,把“白马”与“马”平行,称这是两个平行的各自独立的类。这是《白马论》立论的根本要点。
第三,独立的属性建立独立的类。“白马”和“马”是类不是个体,“白马非马”不是“一匹白马不是马”,而是“白马类不是马类”,白马类与马类是平行的两个不同的类。
第四,公孙龙的思维中,已经具有了以属性看世界,不以实体看世界,以概念看世界,不以感官看世界的思想。“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白马非马”是概念思维强调属性独立性的结果,常识理解以及感官感知不易接受。
四、贯穿《公孙龙子》各论篇的主线思想是:属性分离,归类操作
综上所述,五论篇体现了公孙龙关于“属性,概念,类”的思想。贯穿《公孙龙子》各论篇的主线思想是:属性分离,归类操作。五论篇的要点及其逻辑关系如下:
《坚白论》,属性的分离。《白马论》,独立的属性独立的类。《指物论》,概念的外在表达。《名实论》,概念规定与归类操作。《通变论》,类类合并与概念分层。
这样的解读是新的理论与方法的体现,传统的方法和理论在解读效果上进展艰难。就方法而言,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对于中国古典文献的解释,要有字词的考据。中国古典文献大多是记叙文和散文,文字考证一旦确定,字词含义即能明确。这一类文体数量众多,经史子集,篇幅浩繁,但纯粹哲学思辨的文本并不多,所称“文史哲不分家”,长期形成的惯例是以文字考证的方法适用一切古典文本。在没有电脑和网络的时代,因工作量的巨大,被视为“学问功夫”。但在面对《公孙龙子》《道德经》这样的文本时,则陷入解读困境。《公孙龙子》《道德经》是哲学文本,不是文学文本。这样的文本,字词考证固然需要,但不是字词考证后,篇章的意义即刻能够明确,字词句的含义存在于全文本的贯通逻辑中,而不在文本之外的文献考据中。普通文本的逻辑关联即显在字面上,哲学文本则是要揭示出字面背后的深层含义。
如果通过字词考据能够解决问题,两千多年来,应该早已出现依据充分考据的解读版本,但是没有。《公孙龙子》《道德经》始终没有公认的经典解读版本,至今充满争议,这已经说明以字词考据解读这类文本并不成功。原因在于这样的考据无法形成全文本的贯通解读。因此,根本的是要揭示出贯通全文本的主线逻辑内涵。《公孙龙子》《道德经》都是拥有上千言的文本,有着足够形成语用意义的空间,语词的意义、语句的划分都需要在贯通全文本的逻辑链中确立。目前的解说多是对“只言片语”的解说,始终没有形成全文本逻辑贯通的解释效果,因而更无法揭示出文本背后的深层含义。
在对公孙龙思想的解读上,没有证据表明公孙龙是借鉴了同时代什么人的思想,作为传统考据的惯例延续,以他人的片言比赋予公孙龙,既形不成对《公孙龙子》各篇章的贯通解读,也遮蔽了对公孙龙概念思维深刻性的揭示,实际上也矮化了公孙龙。公孙龙概念思维的深刻性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人,与老子相比肩。如前篇所述,公孙龙论述了概念的属性分离,老子论述了概念的外延边界及其移动,公孙龙与老子是中国先秦诸子中对人类概念思维具有深刻理解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世界同时代的智者。
在古代经典文献的研究上,特别是在文本解读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把解读与研究问题割裂开,已入误区。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来说,首先是“解读”问题,特别是古代哲学经典,经千年解读依然莫衷一是,这正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个逻辑贯通更流畅更完美的文本解读,正是对以往解读难题的解决,也正是问题如何被解决的展示。脱离解读的研究,无视解读效果的优劣,对于经典文本的研究来说意义不大。一些解说没有文本解读的展示,仅就某些词语一味地“说开去”,这已经与经典文本的解读不相关了。
文本字面背后的深层含义始终没有明确的揭示和表达,除了方法的不当,重要的原因在于理论的欠缺。概括轮的解读明显存在困境。借用现代关于语言的理论,也没有带来更好的解释效果(前篇已述)。绕开文本解读,只做片言片语的阐发,解读问题仍然悬置。试图提出新的解释,但理论支撑不足。
一种说法是,《指物论》中的“指”需要联系“用手指”的动作理解。“用手指”的动作指向简单明了,但前提是:对象物必须在现场。这是动物已经具有的能力和方法,同类个体共在现场,一个个体的动作示意,其他个体都能感知到。人类继承这一能力。但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能够表达不在现场的对象物。动物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前篇已述,人类思维的根本特征是:为了向他者表达不在场的对象物,人类创造了替代所指物的替代物。替代物的出现,才使得表达不在场的对象物成为可能。使用替代物表达“不在场”的对象物的特征是:第一,对象物无法直接呈现,要使用替代物表达;第二,替代物只能表达对象物的部分属性,无法表达全部整体;第三,他人需要转换理解,首先接受替代物,再理解为对象物,用思维而不是用感官。用手势比划不在现场的对象物,是建构替代物,不是“用手指向”对象物。而且 “用手势比划”必须是人们熟悉的对象,对于人们不熟悉且又不在场的对象,“用手势比划”不起任何作用。
由此应该清楚:《指物论》的“指”,不是指“在场的对象物”,“用手指”在场的对象物,没有论说的必要;《指物论》的“指”,是指“不在场的对象物”,只能通过替代物来表达,人类后来主要是通过语词来表达。这样才产生了问题:当人们用语词表达不在现场的对象物时,是在用名称还是在用概念?是在表达个体还是在表达类?是在指向属性还是在指向实体?这才是公孙龙要解答的问题。同一语词,可以是名称,也可以是概念。公孙龙要说明,在思维中应该而且必须分清二者的不同:名称指物整体,概念指属性。因此用“指”字是说明,以语词表达的“概念”或“名称”在指什么,而不是“用手指”在指什么。
即使在语言无法表达概念含义,需要通过外在物表达时,通常也都是通过语词调动外在对象呈现在人们头脑中,而不是现场直面实体对象。“指物”是语词调动对象在思维中的呈现,而不是现场用手指物。特别在人类的语言发展成熟以后,人类的概念库建构完成以后,现场手指对象,已成为特定条件下特意安排场合中才有的特例。用语词调动对象,通过思维交流而不是现场直面,才是人类最普遍的表达和交流方式,也才真正是人类的表达和交流。至此可以看出,在理解 “指”与“物”的关系时,拉入进来“用手指”的动作,只会造成混乱,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对象物“在场”与“不在场”的根本区别。
把“用手指的动作”几句话一笔带过,就“引申”为所有事物均可被指出的“可指性”,过于含糊其辞了。“可指性”是人的指认活动赋予对象的性质,不是物本身的性质。事物可以被指出的根据,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事物本身的性质是“存在”和“属性”。事物本身存在的可以被概念思维分离的属性,才是事物普遍可以被指出的根据。即:当人们的认知活动面向对象时,指的是什么?用手指,指的是实体“存在”;用名称,指的是“物整体”;用概念,指的是“属性”。“可指性”是什么?把“可指性”说成是事物本身的性质,是对事物的主客性质没有分清的缘故。
古代哲学经典文本全贯通的理解和逻辑关联,字面背后深层含义的揭示,需要新的理论。概念发生论的提出,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公孙龙子诸论篇的内容、逻辑、主线思想得以展示。文本解读是不断建构的过程,希望出现更好的贯通全文本的理论解读。
①吴汉民:《概念发生与公孙龙〈指物论〉的解读》,广州:《暨南学报》,2018年第11期。
②③④《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338、1543、846页。
⑤[美]John B·Best:《认知心理学》中译本,黄希挻、张志杰、周榕、吕厚超、杨红升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5月,第346页。
⑥[英]M·W·艾森克、[爱尔兰]M·T·基恩:《认知心理学》中译本,第四版(上册),高定国、肖晓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428页。
⑦吴汉民:《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与人类概念的发生》,上海:《学术季刊》,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