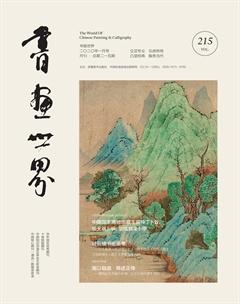由“以书入画”浅议中西绘画异同
费秋生



内容提要:近百年来,中国艺术在各方面借鉴西方。其实,不同民族的艺术相互影响本无可非议,只是对西方艺术的这些借取夹杂了较多他律因素,反而使我们对中西艺术都产生了误解。因此,辨析中西绘画的异同对学习传统和借鉴西方都有意义。本文借“以书入画”浅谈中西绘画异同只想说明两点:首先,“程式化”在各类艺术中广泛存在,并不为国画特别是文人画所独有,这是相同之处;其次,中西绘画在内在的认知和观看方式上的差异基于各自民族长期不同的生存经验和感受方式,这是差异之处。
关键词:以书入画;中西绘画;中国画改良
一、从绘画改良说起
近百年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几乎处在全盘西化的方向上,美术领域概莫能外。虽然近几十年来,思想界开始了反思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大讨论,如李泽厚先生提出五四一代学习西方的努力最终不过落实为“救亡压倒启蒙”,人们也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自身的价值;但这些评判至今没有定论,我们看到今天不少国画是经由西方写实绘画改良的结果。
绘画改良之类的观点最早由康有为、陈独秀等人提出,康有为认为:“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矣......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1]陈独秀认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2]表面上,国画在造型状物上的弱势成为当时推崇西洋古典绘画的根本因素。但我们为什么突然承认国画需要改良,并认为“写形”上的弱势便是艺术上的弱势,进而把中国绘画纳入西方的价值标准中去?毕竟,早在晚明时期西画就已被传教士带到中国并在民间出现。另外,郎世宁更是将作品中的西画因素加以改造以适应中国宫廷的审美趣味。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国画改良的主张最早不是由画家自己提出的,很大程度上出于救亡图存的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使以康有为、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转嫁到艺术上来。对于自身科技工业的落后,当时知识分子迁怒于文人画对能巧繁复的轻视。一百年的坎坷历史或许已经将中体西用的态度改成了文化自卑心,我们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的各种标准作为衡量自身的坐标,自甘为西方世界的“他者”存在。所以,今天要重新辨析并确认中国绘画乃至文化的自身价值。
二、文人画的出现
中西绘画的表面差异很容易列举,并且水墨画经常被作为中国绘画的代表来与西画比较。比如,传统水墨画较西方古典绘画更重临摹而轻写生,相对西画也更多强调笔墨程式,等等。“程式化”经常是人们诟病传统水墨脱离现实生活和过于保守的依据。我们姑且把先入为主放在一边,从画史和画论的角度看看何以造成这些独特的程式。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绘画发展史中,也曾有并不短暂且十分辉煌的追求形似和极依赖写生的传统,比如五代、宋时期的花鸟画。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画家的状物写照能力尚未发展成熟,但如谢赫《画品》也都明确把“应物象形”作为绘画六法之一。对于追求形似的鄙薄发端于宋,宋代社会政治结构不同于唐,文人阶层的地位空前提高,宋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文艺最为繁荣的朝代之一。当时文人身兼各领域,像欧阳修既是官员也是文坛领袖。宋代书法也是宋有别前代的一个实例。魏晋书风的经典作品在宋代已较前代更难一见,代替法书真迹的《淳化阁帖》一类刻帖开始盛行,然而经典作品的缺席反而促使文人们自由抒发,最终形成尚意书风。
可见,自宋代开始,文人阶层进一步掌握了文艺领域的话语权。在绘画上,不同于画工的精巧,他们利用自身的广博学识、思想上的优势,对传统进行了扬弃和新的诠释。代表性的言论很多,如苏东坡《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3]米芾评价五代董源绘画时又说:“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4]283这些都体现了当时文人对自然情趣的追求和对机巧的排斥。
三、“以书入画”的提出
如果说宋代苏轼、米芾等人是从宏观精神的角度引导绘画发展,那么元人赵孟则在具体实践层面进一步指明了画家摆脱宋代院画形似而追求古意的具体操作方法。赵孟不仅认为“若无古意,虽工无益”,还在《秀石疏林图》中题曰:“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4]538此语可算是画论史上首次在技法层面明确提出“书画同源”和“以书入画”。后世也有持此论者,如黄宾虹在《古画微》中说:“书画同源,贵在笔法。士夫隶体,有殊庸工。”[5]总的来看,赵孟 的这一说法影响了其后的元四家、明四家。直至晚明,董其昌在这条画史发展道路上提出“南北宗论”,这算是对这几百年来的绘画史做了总结。董氏的“以书入画”观点集中在他的《画禅室随笔》中。他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似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4]544继董以后,清初“四王”更将董氏的说法奉为圭臬,以临摹古人为能,将笔墨作为山水画的本体,最终的结果就是绘画对象在画面中呈现出越发突出的“程式化”“符号化”倾向。
类比书法,我们或许可以对文人画发展的这种程式化趋势有所包容。书法所书写的文字也同样在经历了最初的象形阶段后不断符号化,但这并不妨碍历代书家在作品中体现格调和才情。正是这种“符号化”让线条笔墨走向纯粹、深入。与“四王”同时的还有“四僧”。“四僧”虽然更注意师造化,但也与“四王”同属文人画家范畴。“四僧”的艺术成就足以说明我们所诟病的“程式化”“不擅写实”等特征,并不是阻碍国画发展的根本原因。
四、与西画的比较
正如贡布里希在其《艺术的故事》中谈到的那样:“事实上,我们拿起铅笔动手一勾画,被动地服从于我们所谓的感官印象,这整个想法实际上就是荒谬的......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总是不能不从某种有如‘程式的线条或形状之类的东西下手。我们内心的‘埃及人本性可以被压抑,但是绝对不能被彻底摧毁。”[6]因此,不同艺术家所依赖的不同程式就构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我们对比西方绘画史,就会发现印象派追求外光效果丢失了物象结实的造型和轮廓,而当塞尚想借此上溯普桑,把印象派的外光成就和古典绘画坚实的结构相结合时,他又不得不牺牲正确的透视而稍加变形。传统水墨的发展同样如此。本文用文人画的“以书入画”特点作为这种程式化的例子,这是中西绘画的同,或者说是艺术发展的规律。
但在文人画以外的中国绘画中毕竟没有发展出像西方写实绘画那样的艺术,即便五代宋花鸟强调观察、追求形似,也不能等同于西方写实。西画中的透视、光影以科学作为基础,背后透露了西方人意识中的宇宙秩序。这种中西差异是更为本质的。中国绘画的基本模式早已由先民的观看方式决定,而文人画的“以书入画”只是这一脉络最为鲜明的一部分。宗白华先生在讨论中国画时曾拿中国戏曲来打过一个比方:“中国戏曲的程式化就是打破团块,把一整套行动化为无数线条,再重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最有表现力的美的形象。”[7]雷德侯在《万物》中也试图通过分析,从中国不同门类的艺术中梳理出中国艺术背后的一类共性,并试图指出这种“程式化”“模件化”特征与中国人特有的地理、制度等外在条件的关联。
抛开艺术不谈,近百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整套东西都存在此类质疑,全盘西化和固守传统两种声音都很大,但真正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深入分析的似乎不多。它们到底是优劣的差异还是方向上的差异?理清异同并非为了反对借鉴西方艺术,只是这些取舍应基于艺术家个人感受和视觉经验。夹带民族情绪和心理,进而刻意为之的艺术口号,以及其带来的强大惯性,我们应该逐渐摆脱。
参考文献
[1]康有为.万木草堂画目:节选[G].素颐.民国美术思潮论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21.
[2]陈独秀.美术革命:答吕澂[G].素颐.民国美术思潮论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24.
[3]苏东坡.苏东坡全集[G].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720.[4]周積寅.中国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
[5]黄宾虹.黄宾虹谈艺录:古画微[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56.
[6]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M].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562.
[7]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