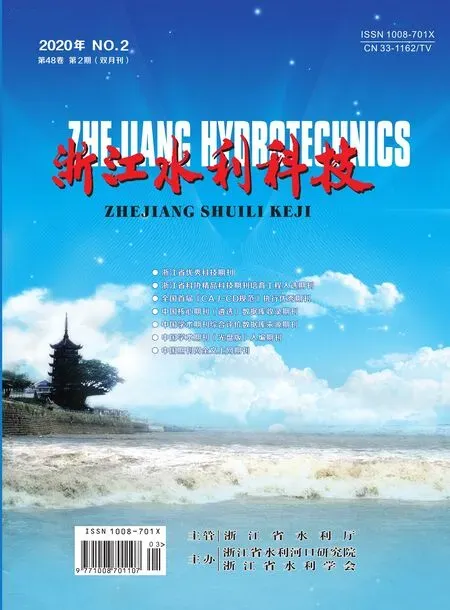我所亲历的水利建设及涌潮研究
——林炳尧访谈录(上篇)
李海静 访谈整理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水文化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18)
受访人林炳尧(1942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涌潮研究专家。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被分配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工作。1970年,参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1978年,考入清华水利系跟随许协庆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速水流。1981年,进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机电所工作。1984年,调入钱塘江管理局从事钱塘江涌潮研究工作,曾任钱塘江管理局、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著有《钱塘江涌潮的特性》《涌潮随笔——一种神奇的力学现象》。
访谈时间:2016年4月14日上午;2016年5月23日上午
访谈地点:杭州市中北花园24 - 4 - 201林先生家中;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4楼办公室。
一、早期教育和工作情况
受访人(以下简称“访”):林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您个人的成长情况。
林炳尧(以下简称“林”): 我父亲林建英1林建英,男。193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构造门。资料来源: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姜玉平教授提供。,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与张光斗2张光斗(1912.5.1 — 2013.6.21),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和工程教育家,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是同学。父亲曾受马歇尔计划资助赴美考察,回国后一直在铁路系统工作。母亲姓杨,海南文昌人,曾任上海总工会会计。
儿时的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家庭多次搬迁,这是由父亲的工作性质决定的。1942年1月,我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市。此后,父亲奉调到江苏省镇江担任铁路工务段负责人。父亲命运多舛,1948年下半年镇江铁路工人开展了工潮运动配合全国解放,他因保护工人而触犯国民政府高层而被招到上海,继而被控入狱。后经亲戚朋友帮忙,担保获释。1951年镇反运动中,又因此事被关进监狱,直至1982年才得以平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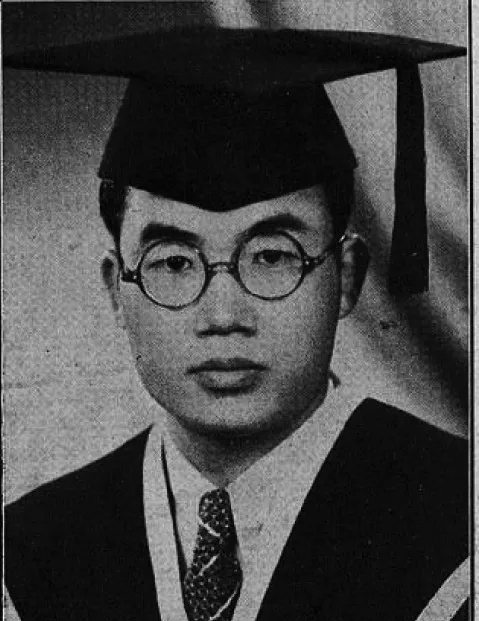
图1 林建英大学毕业照
1950年,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搬迁到上海,我进入广肇公学3广肇公学由广东籍教育家卢颂虔创办于1913年,曾更名为上海私立粤东中学、六十六中学、四川中学。读书。195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华师大附中的3年对我而言,可以说是一个顽皮儿童的“从善”过程,这里的教育使我脱胎换骨,并有幸遇到了很多好老师4林炳尧曾著文深情回忆在华东师大附中学习生活的精彩片段,详见华东师大一附中校友会网站:http://www.hsdyfzxyh.com/cn/News/Contents.asp?TypeID=3&RsID=464。
高中,我考入上海复兴中学。中学生活最大的印象就是有很好的图书馆,老师鼓励我们多读书。在这里我获得了良好的人文教育,阅读书籍、拓展视野,同时也激发了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因为兴趣,我报考了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在这里同样遇到优秀的老师,接受了良好的数学教育。总结大学生活:第一,学习了数学和力学知识;第二,大量的数学训练培养了逻辑思维能力;第三,训练了提出问题的能力。苏步青先生5苏步青(1902 — 2003),男,浙江温州平阳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被誉为“东方国度上灿烂的数学明星”“东方第一几何学家”“数学之王”。经常在学校大会上讲:“看一本书,看了一半,仍不能发现问题,这本书就白看了。”第四,培养了自学能力。读书从不是从头读到尾,而是用自己的话、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学数学最基本的能力。第五,结识了一批热心能干的师长,始终得到他们关心和帮助。知识和能力的获得、结交的优秀师友成为我一生的宝贵财富,为未来工作的不确定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访:1964年大学毕业后,您被分配到三峡工作?
林: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6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该机构以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为基础为开展长江治理问题而组建于 1956年,首任主任为林一山。就三峡工程,李锐与林一山曾公开论战。资料来源:李锐,崔敏。李锐自述人生百年: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N/OL]. 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culture/2016 - 02 - 25/108122.html;佚名.建国以来关于三峡建设的争论[J]. 经济视角,1994(1)∶ 40 - 41.(现为长江水利委员会),先被安排到工地实习,成为位于蒲圻县(现为赤壁市)的三峡试验电站——陆水枢纽的一名土石工人。1年实习期结束,正赶上“四清运动”的高潮期,有段时间我被抽调到四清工作队从事文书工作。此后,又被安排到办公室科学院河流室水库组担任技术员,参加三峡枢纽水库的淤积分析。最初主要参与整编水文资料,如一些控制性水文站的多年平均流量、平均含沙量等,后来主要研究三峡卵石推移规律问题。

图 2 1968年,四川灌县都江堰柏条河一干渠上开展的三峡卵石推移质试验
访:当时围绕三峡工程主要做那些工作?
林: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民国时期,美国水利专家萨凡奇对长江流域治理做出了初步规划设计方案。解放后,苏联专家提出高坝大库的建设设想。如按照苏联专家的设想,修建三峡工程将被淹没整个四川省,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独享的地中海”。这与中国国情显然不符,苏联地广人稀,淹没土地没有关系,大库容可以发挥最大发电效力。我们人多地少,淹没四川损失太大。当时,没有预料到外部泥沙会进入库区的问题。

图 3 1944年美国水利专家萨凡奇考察三峡(右二为萨凡奇)
史无前例的工程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遇到许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当年的对策是每遇到一个问题就组织一套班子专门研究这个问题,逐个解决,以求万无一失。现在看来,这办法还是比较有效的。
我当时主要从事泥沙研究,第一次出差是到重庆收卵石。长江的川江一带卵石很多,一到三峡出口的南津关就很少。这就需要研究卵石到底是否会通过峡谷的问题。为此,我们在卵石内放入放射性同位素,再将这些卵石投到四川黄草峡上游,然后到下游寻找。在几十公里的河床上找卵石实在困难,我们背着放射性探测仪在卵石滩上找了很久,从未找到过。这段工作结束后,我被安排到灌县7灌县,现为都江堰市。在韩其为8韩其为(1933.11 — 2019.10)男,湖北省松滋县人,著名河流泥沙专家。1957 — 1961年在荆江河床实验站(沙市水文总站)工作,曾任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程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一级教授级高工、博士生导师。领导下做卵石实验。
访:通过您的实地勘查,三峡卵石是否会移动?
林:当然会移动,不然卵石从何而来?只是动得很少,因此输移量很小。
当年,黄万里谈到长江卵石移动的问题。在我导师韩其为主持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当年调查研究的结果是:卵石每年移动量为11万t。此来,几批人继续研究此问题,卵石数量不断增加,最多的认为有60万t。
川江和三峡有个特点:最大的洪水决定了河床“涨冲淤落”。别看河滩上有着大量卵石,但是绝大多数时间,卵石并不移动,河流输运的是大量细泥沙。长江卵石输移量之所以小,大致有2方面原因:一是卵石个体特性;二是山区性河道水流特点。卵石体积大,分量重,起动困难,况且容易形成鱼鳞状排列,使其更加稳定。只有当水流流速特别大,足以破坏排列结构时,卵石才会移动一批,这种现象可以称为“阵发移动”。
另一方面,山区河流,包括三峡和钱塘江,因为受到地质构造的影响,总是峡谷、宽谷相间,河道忽宽忽窄,河床时浅时深。因此,洪有洪水滩,枯有枯水滩,不论洪枯,都是一段急来一段缓。
洪水期间,峡谷内水流很急,峡谷内的卵石被输运到下游宽谷。这时峡谷上游则在壅水,大量泥沙淤积在峡谷进口的上游段。这时,卵石不可能飞越壅水段进入峡谷。也就是说,大洪水时卵石在宽谷走一段,就歇在峡谷出口处;枯水季节,峡谷内的水流变缓,这时,峡谷进口的上游却形成了滩,水浅流急,于是这里(例如瞿塘峡上游奉节的臭盐碛)的卵石有些被冲进峡谷,停留下来。如此一段一段移动,绝不可能像细颗粒泥沙那样一泻千里。
由于这些原因,虽然卵石不是静止不动,但是输移量很小。即便每年有60万t,对于长江这个巨大的河流算得了什么?长江每年的输沙量有好几亿吨,两者差3个量级。
二、结缘业内名师
访:您还曾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工作?
林:是的。长江规划中,葛洲坝枢纽是三峡枢纽下游的一个梯级。三峡负责年调节,葛洲坝负责日调节。1970年秋,葛洲坝工程9葛洲坝水利枢纽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的长江三峡末端河段上,距离长江三峡出口南津关下游2.3 km。它是长江上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低水头大流量、径流式水电站。1970年12月26日开工兴建, 1988年12月全部竣工。开工前,我到了这里。葛洲坝是毛主席批示的全国重点工程,各路诸侯齐聚于此。当时备战备荒,除长办以外,其他水利研究、设计单位都被解散了,不少人来宜昌参加大会战。单位太多,之间的争斗很厉害,争地盘和话语权。工地非常混乱,工作无法开展,1971年底开始整顿。当时周总理讲,“如果葛洲坝出了问题,是要记入党史的,必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10康荣禄. 学习周总理 建好葛洲坝[A]. 三三〇文艺丛刊,三三〇工程局政治部编. 缅怀敬爱的周总理[M]. 北京:三三〇工程局政治部编,1978:4 - 5.1972年,钱正英部长和9位副部长,组织泥沙专家来到葛洲坝。
我当时是设计团试验连泥沙班战士,参加泥沙研究工作,主要从事整体模型试验,及其他相关试验,如:电站防沙试验等。泥沙班成员来自于不同单位,有长办、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1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创建于1954年,2000年并入武汉大学。、水利部长沙设计院、湖北设计院等。一起在葛洲坝工作的同事都骄傲地自称“芦席棚战友”,大家在艰苦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在这里,我遇到了诸多国内知名的水利专家,如:张瑞瑾12张瑞瑾(1917 — 1998),男,湖北巴东人,水利科学家、教育家,曾任中央水利实验处研究员、武汉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泥沙运动基本规律的研究,提出的水流挟沙力公式被广泛应用。、谢鉴衡13谢鉴衡(1925 — 2011),男,湖北洪湖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泥沙专家,中国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专业的创始人之一。先生就长期在泥沙班,钱宁14钱宁(1922 — 1986),男,浙江杭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泥沙运动及河床演变专家。1951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1984年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并创办了英文版《国际泥沙研究》杂志。、窦国仁15窦国仁(1932 — 2001),男,辽宁北镇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泥沙及河流动力学专家。1956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水运学院,1960年获技术科学博士学位。、李浩麟16李浩麟(1934 — ),男,江苏无锡人,1956年毕业于河海大学,同年入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工作,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河口动力学和河口航道治理研究。、黄胜17黄胜,男,江苏海门人,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水利系,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等则时常过来,陈椿庭18陈椿庭(1915 — 2016),男,江苏人,水利学专家。193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1949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工作,历任南京水利实验处水工室主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工研究所副所长、水工冷却水研究所所长、副院长等职,中国水利学会第三、四届理事。、谢家泽19谢家泽(1911 — 1993),男,湖南新邵人,水文学家。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1938年获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土木系凭证工程师学位。等。其中,李浩麟、谢葆玲20谢葆玲,女,武汉大学教授。成了我一生的挚友。
访:当时,您与这些专家是否有工作上的接触?
林:有。我们在他们指导下工作。当年,这些专家动辄挨斗,处境艰难,只在参加实际业务工作才能得到些许安慰。大多数技术干部惺惺相惜,如果在政治上没有过多、过高的追求,一般都对他们相当尊重,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力减轻他们生活和精神压力。
我那时年轻体壮,常被下派到一线开展现场勘查工作。第一次是参加中国地质水文七大队的三峡河道考察,后来又参加了几次库区的实地测量工作,野外作业基本上都会派我去。这种“流放”的工作使我因祸得福。对河道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掌握是河流研究很重要的工作,常年的外业工作使我对三峡情况非常熟悉,从而有机会经常向各位专家汇报情况。
访:这些先生中,最令您敬佩是哪位?
林:我受过许多大师的教导,最令我敬佩的师长是许协庆21许协庆(1918 — ),男,字胜权,原籍江苏南京,流体力学家,水利工程专家。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1950年获美国衣阿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owa)博士学位。和钱宁两位。两位先生性情不同。许先生功课非常好,他喜欢解难题,越难越来劲。钱先生格局很高,一直考虑整个泥沙界的发展问题。1978年,我考取清华大学水利系的研究生,跟随许协庆先生研究高速水流问题,论文题目是《重力场中二维空腔流动分析》。在先生精心指导下,深入学习可变域变分原理,分析、理清了自由面重力流动的各类变分原理。

图4 1985年与导师许协庆合影
科研最关键的“提准问题”。问题既要有学术和现实意义,又要能够完成。先生给我出了一个好题目,研究过程中,使我得到锻炼,科研能力上了新台阶。
许先生非常重视学问,要求学生,包括他自己,经常复习基本知识,反复思考基本问题。硕士毕业后,我来到中国水科院工作,与他在同一间办公室。每年招录研究生,我负责批阅考卷。批卷之前,他要求我按照考试要求先做一遍试卷,他自己用新的方法也做一遍。第一年,我勉强过关。第二年,我就想尽办法用2种方法做,许先生却用第三种方法再做一遍。曾有一次,他因一道题目没有想出新的解题方法而生气,并折断手中铅笔。
我第一次见到钱宁先生还是在他被下放山西省沂县专区期间,总把“咱沂县”挂在嘴上。钱先生虚怀若谷、直言真诚,致力于泥沙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他心里装的是泥沙研究的全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千方百计拉人做泥沙研究,哪个单位的人都可以。在清华大学,钱先生特地为我们4个非泥沙专业的学生开泥沙课程,那时他已经病重,仍坚持亲自授课,直至无法再上讲台。钱先生从不重视分数,重视兴趣和实际科研能力。初次见面,先生就教导不要紧扣数学不放,以后还经常教导我要好好学物理。送给我英国风沙专家拜格诺的《风沙物理学》、美国地理学会的《河流调查报告》。钱先生很有情趣,喜读英文小说《双城记》,还喜欢杭州知味观的小笼汤包。先生著述甚丰,字字都是他的心血。看到这些书就想起先生的勤奋。当年,开学术会,墙上都挂满图表,一到休息,先生总走到大字报前,一份一份抄在练习本上,他的练习本很多。我少不更事,跟先生说笑:应该再加一个,用来记录哪个本子记哪些东西。先生笑了笑。
我钦佩窦国仁。他身体壮实,为人豪爽,在泥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首先指出薄膜水对细颗粒泥沙运动有很大影响,在苏联获得了正博士学位。回国后,当时水利部钱正英副部长找他谈话,亲自安排他到南京水科院工作。老窦特爱喝酒,每次喝多了,总要吹一遍当年在苏联和泥沙权威列维辩论的“英雄事迹”。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葛洲坝,他是交通部派来的,当时他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后来,他主持了在武汉开展的葛洲坝泥沙变态模型,这个模型和宜昌工地的正态模型互相对比论证。他曾把一大厚本笔记让我读,这是他15年潜心研究紊流理论的心得。我非常感动,这是此后出版的《紊流力学》的核心内容。
2000年我出差南京,李浩麟先生说:快打电话给老窦,“芦席棚战友”喝一杯!不料老窦在电话里说我已经出不来了。此时,他已处在癌症晚期,全身疼痛。即使如此,仍不忘泥沙,支着脑袋说跟我讲工作计划。壮志未酬泪沾襟!2个月后,接到李浩麟电话,告知我老窦去世了。自相识以来,老窦就是我的榜样、我的兄长、我们的旗帜。
戴定忠22戴定忠,男,原水利部科教司司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著名泥沙专家,首届钱宁泥沙科学奖获奖者。195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水利工程建筑系(现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原水利部科教司司长。他很了解我。给我3个建议,第一,研究问题不要去研究细小的事情,研究大的、跟国民经济有关系的问题;第二,不要那么细,研究河床演变,只要说出哪里淤积,就很有意义了,不需要计较淤积多少厘米之类的细节;第三,要学会组织人一起去做。
张瑞瑾先生比我大20余岁,早年曾患肺结核病,人很虚弱,在葛洲坝他也住在芦席棚里,我和先生头对头睡。先生所著《河流动力学》对我影响深远。这本书结构严密取材精到叙述严谨,成为了优秀教材并多次重版。先生研究问题,总从全局出发,从工程出发。为解决葛洲坝三江航道问题,先生苦思冥索,深入研究,提出“静水行船,动水冲沙”办法堪称经典。我与张先生相识之时,革命高潮虽过,但余震仍烈,先生处境不好,心情也差,我们几个“战友”总帮先生打饭、抢打开水、到池塘提洗脸水,尽量减轻他负担。 晚饭后经常陪着他一起散步,谈天论地。一丝不苟满脸严肃的先生此时才见笑容。他跟我说他这一生钻了3个牛角尖,都没有钻通,教导我别钻牛角。他对水利、对人生、对事物的认识成为我们交谈的话题。
我见过先生2次特别高兴。一次听到恢复高考,先生一时满脸笑容;另一次是钱正英率领几位泥沙专家前来,为此先生高兴得穿上了中山装。
韩其为先生,我水利的启蒙老师。我在长办跟他工作近10年。后来调到中国水科院,2001年成了工程院院士。他是位传奇式人物,初中毕业参加工作,在只有他一人的松滋水位站自学微积分,并用微积分分析积分式流量计。后来被长办河流室的唐日常主任看中,把他调到长办的荆江河床试验站,开始做河床演变和观测。他很有想法,把航空流向仪器用于水文研究工作。因表现优秀,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受到毛主席接见。后来又不断学习,奠定了研究基础。先生在推移质泥沙运动理论、水库泥沙淤积研究上有很深造诣,这都是围绕三峡工程建设积累的成果。此后,先生研究黄河泥沙问题,采用水库调节的办法解决黄河泥沙淤积。我曾跟随他做卵石和水库淤积试验。他教导我注意总结,比如怎样利用气体力学的办法解决涌潮的问题、该如何创造一些新的办法。《钱塘江涌潮的特性》这本书就是他动议我撰写的。
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多从事国防方面的工作,搞水利的极少,我接触频繁的是忻孝康23忻孝康(1937 — 1998),男,1937年出生,浙江宁波人。复旦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原流体力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著有《计算流体力学》等专著。、戴世强24戴世强(1941 — ),男,浙江定海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复旦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1966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师从郭永怀教授。曾先后任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现为中国力学研究学会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水动力力学专业组副组长,中国力学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2位师长。因为都是《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的执行编委,10多年间,几乎每个季度见一次。
我非常感谢这些师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