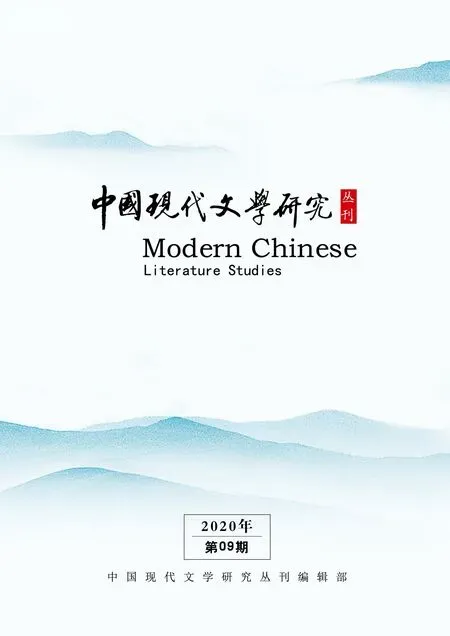师承关系与叶公超“实际批评”的理论构建※
内容提要:叶公超的“实际批评”理念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当我们深入探究这种影响时不难发现,“实际批评”理念并不等同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体系。这本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语境后一种正常的、必然的“错位”,而叶公超的“错位”接受恰恰基于其对文学教育现状,尤其是文学批评课程设置弊端的认知。从师承关系的角度,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叶公超“实际批评”原则的理论构建:首先,“实际批评”的理念构想是针对文学教育的现存问题而提出的;其次,这一理念直接应用于叶公超的教学实践,并在师生互动中得以传递与完善;最后,学生对这一理念的传承才真正发挥其影响与效用,完成了“实际批评”的理论构建。
叶公超西学根柢深厚,在1912年9岁时即先后赴英美读书,1917年回国进入南开中学读书,不出三年又赴美国读中学,毕业后短暂回国,1922年考取爱默斯(Amherst)大学后又赴美国读书,1925年获学士学位后至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文艺心理学,其间结识了爱略特(T.S.Eliot),可谓亦师亦友。至1926年学成归国之后,便先后在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主讲“英文作文”“英国短篇小说”“现代英美诗”“文学批评”和翻译等外国文学课程,他的学生有钱钟书、季羡林、杨联升、梁遇春、卞之琳、常风、辛笛等。可以说,在1940年“弃文从政”以前,他几乎一直身处学院环境之中。
以往对叶公超批评理念的研究无一不注重其西学背景,西学经历的确构成了叶公超批评理念、文学思想的重要影响因素,但除此之外,叶公超对中国文学现状的认识与思考始终基于学院立场的考量。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教学既是谋生的手段,也是相对固定的日常活动,其他如编辑、撰文等,都是与学院背景相伴而生的文学活动。在这样一种教学环境中,包括课堂教学、师生互动及理念传承等往来的师承关系构成了生活、教学以及文学活动中最为便利、熟悉的场域,激发并塑造了叶公超“实际批评”的批评理念。
一 在教学中发现“问题”
“实际批评”理念的形成深受瑞恰慈(I.A.Richards)、爱略特等西方批评家的影响,对此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分析。1但叶公超对西方理论的借鉴融汇多元,并不全盘接受某一家的思想理论,如他的“实际批评”理念较为接近英美新批评的方法思路,但他并不排斥印象主义的某些批评方法;他推崇瑞恰慈的某些观念,但同时也直接指出其中的某些不足。这种“错位”的接受离不开对中国文学批评实际问题的认知与发现。对文学教育现状的不满,尤其是批评史课程设置的弊端直接激发叶公超提出了“实际批评”的理念。
这一理念所针对的问题,基本上是叶公超在文学批评教学实践中切身感受到的:
其一,在文学批评课程设置中,理论与作品的脱节。叶公超在《从印象到评价》一文的小注中明确指出:“现代各大学里的文学批评史似乎正在培养这种谬误的观念。学生所用的课本多半是理论的选集,只知道理论,而不研究各个理论所根据的作品与时代,这样的知识,有了还不如没有。合理的步骤是先读作品,再读批评,所以每门文学的课程都应该有附带的批评。”2清华大学自1926年设置文学批评课程,其课程说明是“讲授文学批评之原理及其发达之历史。自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至现今,凡文学批评之重要之典籍,均使学生诵读,而于教室中讨论之”3。可以看出,文学批评课程的教学目标更加偏重对既往文学批评理论的学习与理解。叶公超讲授文学批评,既了解课程设置,也参与教学实践,他深悉,对文学批评理论的讲解脱离作品与时代,正是当时课程讲授的一个普遍现象,因而叶公超“实际批评”理念的首要原则就是理论与作品的结合,强调要先读作品,再读批评,通过对作品的理解加强对理论的学习,在互通中获得方法,以便更为切实地将理论方法运用于作品分析。叶公超将文学批评分为“理论的”和“实际的”两种,所谓“理论的”是一种固有的、现成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如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布亚罗等的《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他们的“动机”与“目的”都是为文学或人生定下几条永远适用的公式和法则。而实际上任何理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叶公超进一步举例说明,“理论的”批评根据的是既往的时代和作品,如亚里士多德提出“史诗”(epic)概念的作品依据是荷马的两部史诗,故认为史诗应该全篇都用herotic metre的格调。而其后,米尔顿的Paradise Lost(《失乐园》)或哈代的Dynasts(《列王》)显然都是史诗,却并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因而前人的理论批评只适用于其所根据的作品和时代,不应当作为“实际批评”的标准。叶公超强调,对于前人的理论我们应该从它所根据的作品去了解,而不能用近代作品去证明,更不能将其作为实际批评的标准。
其二,在文学批评史编写中,过于夸大前人理论的效用。叶公超指出,“学校之所以设置批评史这门课程,实际上是希望前人的批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所根据的那些作品或者作品所代表的时代,抑或在方法上做一种参考。而写批评史的人却往往从批评的定义讲起,夸大了前人理论批评的作用”4。叶公超反对批评史从批评的定义讲起,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理论,前人的理论无从了解当下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具备跨越时代的普适性,但这并不代表批评史的存在并非毫无意义,它可以引领我们了解前人的理论,学习前人的作品、时代与方法。因而我们既应该重视既往理论的价值,也不能夸大既往理论的效用。叶公超提出,文学批评应该是“主动的”批评,是读者自己的印象,强调个人的价值和标准,这种标准实际上是个人经验的反映,大致包括三种根据:“一、关于作品与作家的各种事实;二、已往所有同类的作品以及当时的评论;三、批评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环境。”5在叶公超看来,要进行文学批评至少应做到三个方面:一是明确的对象,全面了解作家与作品;二是历史的考察,综合评价已有的同类作品及文学批评;三是自我的立场,立足于批评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环境。在叶公超看来,前两种根据是“事实的功用”,事实可以防止批评者个人情绪的起伏,保持冷静,伸张知觉;而个人的经验则更为复杂和重要。
其三,在大学语言文学的院系设置中,偏重文学而忽视语言。叶公超曾指出,当时各大学对于外国语文与文学的课目虽在形式上略有不同,但“在原则上与事实上则皆偏重文学方面之课目,而置语言与文字于附属地位”6。叶公超倡导一个独立的语言文字学系,让文学的课程与语言文字的课程能够均衡地发展。对语言文字的重视也构成了叶公超“实际批评”理念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讲求事实的根据,尤其是历史的事实,客观地溯其本源,尽可能还原文学作品的本来面貌。叶公超之重视《牛津大字典》也正在于此,他在《牛津字典的贡献》一文中对英国语言学家编纂《牛津大字典》的原则、过程及贡献进行了详细说明,并极为推崇编纂者极尽考据之能事,还原每一个字词的历史演变与当下意义的编纂思路。所谓“事实的根据”能够修饰个人经验的主观性,因而也特别注重运用历史的眼光、比较的方法进行文学批评,强调把作品还原到客观的历史背景中,通过比较的方法得出对作品的评价。如在《爱略特的诗》一文中,叶公超通过比较爱略特《荒原》前的诗和《荒原》评价其诗歌的思想与技术,通过比较瑞恰慈、墨瑞(J.M.Murry)和爱略特的专论评价其宗教信仰,通过比较马克格里非和威廉生两位批评家的论著以及文本细读还原其创作的本来面貌。最终得出以历史的、客观的眼光,同时又不乏个人经验色彩的评价:“他的重要正在他不屑拟摹一家或一时期的作风,而要造成一个古今错综的意识。”7
总体来看,叶公超“实际批评”理念的提出有着强烈的教学针对性,针对教学过程中不同的问题,生发出不同的应对措施,构成了“实际批评”理念的雏形与基本原则。我们并不否认“实际批评”理念的西方理论来源,从叶公超的批评实践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西方影响,但在具体分析其批评理念源起的时候,教学活动与教师身份反而成为其理论建构的直接动力。
二 在互动中传递理念
“实际批评”既是针对文学教育的现实问题而提出,反过来也直接应用于叶公超的教学实践,并在课堂传授知识与课后指导学生翻译、批评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完善。一般来说,文学理念与教育实践的互通对于身为教师的学院文人而言是一种常态。如朱光潜的《诗论》经多次删改,最初即为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诗论》课程的讲义,朱自清《诗言志辨》的成稿与他长期教授“中国文学批评”课程不无相关等,叶公超也是如此。据温梓川在《叶公超二三事》一文中回忆其讲解《江雪》一诗,文中引述内容其实是叶公超《谈读者的反应》的原文,一字不差。叶公超在上课的时候自然不可能逐字背诵自己的文章,但在课堂上大致按照文章提及的内容讲解这首诗,倒是有可能的。
叶公超在课堂讲授中渗透出“实际批评”的理念与倾向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文本,注重对原典的阅读,包括文学文本与文学批评文本。清华大学曾流传一句评价“叶公超太懒”,除了“述而不作”以外,不少学生都曾提及一点:叶公超似乎不备课。据卞之琳回忆,叶公超在北大教授戏剧课的时候,“显然不怎样作课前准备,只是从指定我们各备的一厚本叫《英国戏剧杰作选》(Great English Plays)当中挑几个十八九世纪的散文戏剧(因为从一年级开始就另有莎士比亚戏剧课),到堂上就叫我们同排几位同学轮流合念对话”。8赵萝蕤称叶公超在文艺理论方面消息灵通,总是能够买到最新的好书,并且熟稔每本书的内容。“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9而根据许振德在《水木清华四十年》中回忆,叶公超教西洋文学系大一的英文课,教材是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太懒”以至不备课的叶公超,其讲义或教材往往就是文学文本或批评文本。
二是重视发音,注重对语言文字基本功的训练。据温梓川的回忆,叶公超讲课极重考据,“一堂五十分钟的课,常常为了一个字引经据典而耗去”,“他最注重发音,如果发音有误,必照例挨骂。他动辄以英国语音学家坦尼尔琼斯教授的字典为标准,所谓英格兰有教养者的发音”。10卞之琳也说,叶公超十分重视发音或语调,“每听到我们发音或语调有误或不妥,就爆出教桌上那么一声拍案巨响”11。无论是以文本为重,还是对语音文字的强调,都体现了叶公超“实际批评”的理念构想,课堂上的严格要求不仅补足了文学批评教学的缺陷,更加向学生传递了“实际批评”理念的基本原则。
除了在课堂教学中的直接渗透,叶公超还具体指导学生展开翻译与批评的实践。对于普通的文学青年而言,在当时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作为《学文》《新月》的编辑,叶公超在一群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学生中,地位是比较特殊的。反过来,对于叶公超而言,学生既是知识的接受者,也是理念的传导者。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在叶公超的直接引导、扶持下走上了文学道路。如叶公超主编《学文》,虽然只刊发了四期,却也登载了卞之琳、钱钟书、赵萝蕤、曹葆华、季羡林、废名等不少学生的文章。叶公超在《学文》第三期《编辑后记》中提到:
本刊决定将最近欧美文艺批评的理论,择其比较重要的,翻译出来,按期披载。第一期所译的T.S.Eliot:《传统与个人的才能》,本期的Edmund.Wilson:《诗的法典》,都是极重要的文字。另有老诗人A..E..Housman:《诗的名与质》译文一篇,拟在下期登载。12
其中,《传统与个人的才能》由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卞之琳翻译,据卞之琳回忆:“后来他(叶公超)特嘱我为《学文》创刊号专译托·斯·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亲自为我校订,为我译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13卞之琳称,叶公超的指导不仅影响了他在1930年代的诗风,同时也对三四十年代一些较有成就的新诗篇的产生起到一定作用。《诗的法典》由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曹葆华译,后来叶公超还引导曹葆华翻译瑞恰慈的《科学与诗》,并为之作序,序中真切地写道:“我希望曹先生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因为我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14《诗的名称与性质》由清华大学外国文研所学生赵萝蕤译,赵萝蕤后来翻译了爱略特的《荒原》,据她回忆,翻译《荒原》是戴望舒所约,其“译者注”得益于美籍教授温德先生,但“很可能叶老师(叶公超)的体会要深得多”15,这一点从叶公超为之作序《再论爱略特的诗》中可见一斑。显然,叶公超在推动文学批评发展的过程中是颇费心力的,无论是引导学生翻译最新的批评理论,为学生亲自校订文稿,包括撰写序言进一步阐明翻译对象以扩大影响,实际上都灌输了“实际批评”理念的引导与传递。
三 在传承中形成影响
相较京派中的其他批评家,叶公超既不像朱自清、朱光潜等有完整厚重的理论著作,也不像李健吾有特色鲜明的诸多批评文章,但叶公超在三四十年代文学批评界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这离不开叶公超对师生传承的重视。叶公超对“实际批评”理念的书写大致存在两个层面:一是观念的提醒,即一种宏观理念的倡导、思路方法的启发与总结;二是在具体的批评文章中进行示范性的尝试,从不同角度践行其批评理念。如叶公超在《谈书评》一文中将评书者的工作性质概括为历史的、比较的、评价的,并通过多个层面的例证说明这一理念的合理性,但究竟应该如何撰写书评,在一篇短文中无法充分展开,叶公超便先后写作大量短篇书评加以印证。仅从文本层面来看,叶公超的文学批评就包含了理论与实践的整体建构,因而在师承关系的场域中,“实际批评”理念对学生有着很强的示范效用。
这种示范效用不乏对内容观点的直接继承与延续。卞之琳在《读诗与写诗》(发表于1941年4月《大公报·文艺》)一文中提及的观点,如强调诗歌形式的“音乐性”;认为诗歌应该是读的和听的,而不是看的;分析诗歌节奏中“逗”和“顿”的问题等都是叶公超在《论新诗》(发表于1937年5月《文学杂志》创刊号)一文中详细论述过的内容。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对批评方法的传承与发挥。作为叶公超的得意弟子,梁遇春显然承继了其“实际批评”的理论方法,他十分擅长比较,如在《查理斯·兰姆评传》一文中,梁遇春的评述对象是兰姆(Charles Lamb),但他却从莎士比亚、爱默生(Emerson)、John Brown、斯夫特主教、近代小说家Butler等不同时代的西方作家开始讲起,并对这些人所代表的三种类型(痴人说梦、躲避人生、诅咒人生)加以概括,在这种对比中提出兰姆正是另外一种“真真地跑到生活里面,把一切事都用宽大通达的眼光来细细咀嚼一番”“有欢欣的同情,真挚的怜悯,博大的宽容,而只觉得一切的可爱,自己生活也增加了无限的趣味”16的一个人。最后还不忘将之与中国文人的文学态度进行比较:“和中国文人逢场作戏,游戏人间的态度,外表有些仿佛,实在骨子里有天壤之隔。”17无论是客观比较的方法,还是最终落脚到对中国文学的思考,都与叶公超的“实际批评”十分契合。
此外,正像叶公超一样,梁遇春在批评文章中也显示出他对英美文学的了然于胸。《高鲁斯密斯的二百周年纪念》一文以假设性的语气让18世纪英国文坛的文人都坐在一起:
坐在第一排的是曾经受过枷刑,尝过牢狱生活的记者先生狄福Defoe;坐在隔壁的是那一位对人刻毒万分,晚上用密码写信给情人却又旖旎温柔的斯魏夫特主教Dean.Swift;再过去是那并肩而坐的,温文尔雅的爱狄生Oddison和倜傥磊落的斯特鲁Steele;还有蒲伯Pope皱着眉头,露出冷笑的牙齿矮矮地站在旁边。远远地有几位衣服朴素的人们手叉在背后……中间有一位颈上现着麻绳的痕迹……便是曾经上过吊没死后来却疯死的考伯Cowper。18.
文章又在列数了格雷(Gray),奔斯(Burns),约翰逊博士(Dr.Johnson),包士卫尔(Boswell),伯克议员先生(Burke)之后,才细致地描绘“此外还有一位衣服穿得非常漂亮(比第一排的斯特鲁的军服还来得光耀夺目)而相貌却可惜生得不大齐整;他一只手尽在袋里摸钱,然而总找不到一个便士,探出来的只是几张衣服店向他要钱的信;他刚要伸手到另一个衣袋里去找,忽然记起里面的钱一半是昨天给了贫妇,一半是在赌场里输了——这位先生就是我们要替他做阴寿的高鲁斯密斯医生Goldsmith”19。简要几笔就勾勒出每位作家最为鲜明的外貌或性格特征,足以见得梁遇春对这些作家的熟悉程度。叶公超也曾在《〈泪与笑〉跋》中提到“驭聪平日看书极其驳杂”,“他最后那一年很用心的去看了许多近代传记作品”。20
梁遇春虽英年早逝,但他的散文创作与文学批评都获得了颇高评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方文坛产生过一定影响,当时已有人将梁遇春称为“中国的爱利亚”21。叶公超自然十分欣赏梁遇春,他曾将其评价英国传记文学作家斯特剌奇的遗作《Giles Lytton Strachey(1880—1932)》发表于《新月》第4卷第3期,并在编者附记中提到:“自斯特剌奇死后,英国的《泰晤士文学副刊》,美国的《星期六文学周报》以及法国的法文《新评论报》均先后有专论发表,但是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们觉得梁君了解与鉴赏似乎都在它们的作者之上。梁君不但能从斯特剌奇的几部传记中找出斯特剌奇的面目来,还能用如斯特剌奇那样邃密的眼光和巧妙的笔路来反映他自己对于一个伟大作家的印象。”22除叶公超外,冯至作为梁遇春的同窗好友,也对他的创作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散文总能“给人以一种印象,作者毫无拘束地面对读者说自己心里的真话”23。而废名的评价则颇有意味,他坦言梁遇春的成绩不大为人看得见,“只有几个相知者知道他酝酿了一个好气势而已”24。所谓“好气势”的意义实际上远远重于“好成绩”“好作品”,它是风气的扭转,是风格的塑造,是更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不同于左翼文学批评的阶级色彩,也不同于印象主义批评的主观臆断,叶公超开启的“实际批评”理念以历史的、客观的、评价的独特风格引领了一批学人的效仿与传承。在师承关系的场域中,叶公超“实际批评”的理念得以不断打磨、补充,并传递给一代代学人,建构起颇具影响的理论体系。对于京派文人而言,刊物的凝聚,“读诗会”“太太的客厅”等集会,学院环境的依托,北平社会的风气等都是影响其群体认同观念的诸多因素,但师承关系的存在从学理上、师道传承上直接影响了京派文人文化姿态与文学选择的趋同性,也为我们探讨其交往及群体意识提供了一种新的视点。
注释:
1 如陈太胜《现代主义的倡导:叶公超的文学批评》,季剑青《“实际批评”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学院文学批评——以叶公超、瑞恰慈为中心》等。
2 4 5 叶公超:《从印象到评价》,《学文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6月。
3 《国立清华大学一览》(民国廿一年十二月),清华大学1932年,第50页。
6 叶公超:《大学应分设语言文字与文学两系的建议》,《独立评论》第168号,1935年9月15日。
7 叶公超:《爱略特的诗》,《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1934年4月。
8 11 卞之琳:《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186页。
9 15 赵萝蕤:《怀念叶公超老师——代序》,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10 温梓川:《敢说敢为的叶公超》,《文人的另一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12 《编辑后记》,《学文月刊》第1卷第3期,1934年7月。
13 卞之琳:《纪念叶公超先生》,叶崇德主编《回忆叶公超》,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14 叶公超:《曹葆华译〈科学与诗〉序》,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原载《科学与诗》1937年4月商务印书馆初版。
16 17 梁遇春:《查理斯·兰姆评传》,《梁遇春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287、288页。原载《文艺月刊》,1934年第6卷五六期合刊。
18 19 梁遇春:《高鲁斯密斯的二百周年纪念》,《梁遇春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298、298~299页。原载《新月》,1928年11月10日第1卷第9号,署名春。
20 叶公超:《〈泪与笑〉跋》,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92~93页。原载《泪与笑》,1934年6月开明书店初版。
21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0页。
22 《编者附记》,《新月》第4卷第3期,1932年10月。
23 冯至:《谈梁遇春》,《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24 废名:《〈泪与笑〉序一》,梁遇春:《泪与笑》,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