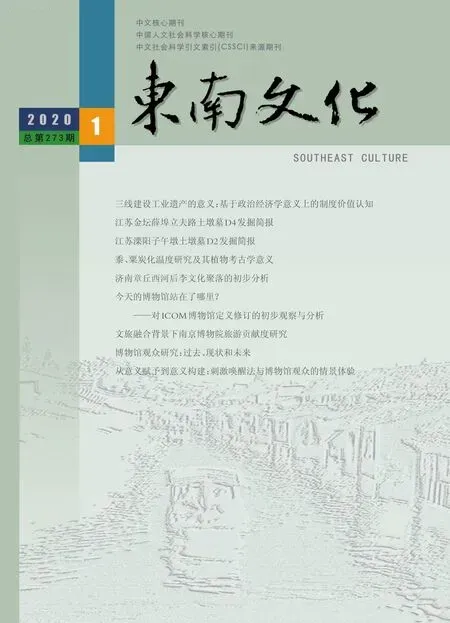西方考古学的关键概念:context的含义分析
刘 岩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Context(背景)是西方考古学中的关键概念,也是考古学区别于古物学的标志。“背景”的含义十分丰富,包括考古材料的出土背景与特征,以及考古材料背后与“透物见人”研究有关的诸多关联性。“背景”的含义同西方考古学的理论范式密切相关,并随着西方考古学理论范式的革新而不断拓展。中国考古学自身的发展特征使得“背景”概念并未在实践中受到足够重视。鉴于“背景”概念的重要性,中国考古学应拓展理论范式,在理解不同范式差异的基础上,优化并整合不同范式所提炼的背景信息;深度发掘并完整公布考古材料自身的背景信息,将不同类型的材料及其背景信息进行关联,从而产生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从多个视角对同一批材料或同一个问题进行反复阐释。
Context是西方考古学中的重要概念。考古学研究是以遗存的context信息为基础或试图解释遗存的context。西方考古学通常认为,context是对遗物的堆积环境(matrix)、出处(provenience)以及共存关系(association)的记录,它涉及考古材料的时空背景以及人们对考古材料出土位置的评价,其具体形态受到了遗物原初拥有者的制作与使用方式、遗物的废弃方式以及废弃后的历史过程的影响[1]。上述定义突出了考古材料的出土背景,是对“Context”的狭义定义。鉴于此,本文将context译为“背景”。本文认为,“背景”除了上述狭义定义外,还包括了考古材料同古人社会生活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关联,以及考古学家构建上述关联时涉及的理论背景、考古背景和古代与当代的社会背景。“背景”的含义是随着西方考古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其背后反映了西方考古学理论范式的革新。中国考古学界同样关注“背景”。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背景”概念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论分析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2]。但从目前来看,中国考古界对“背景”概念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尤其对西方考古学中较为晚近的过程考古与后过程考古语境下的“背景”概念还缺乏足够认识。本文试图将“背景”概念放在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的背景中,分析这一概念在不同理论语境下的具体含义以及对中国考古学实践的重要作用。
一、不同理论语境下的context概念分析
从考古学史中可知,考古学自诞生之初就开始关注遗存的背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研究范式,“背景”概念的含义也随之不断丰富。特里格(B.Trigger)将西方考古学分为进化考古、文化历史考古、早期功能—过程考古、过程考古与后过程考古几个阶段[3]。戴维·克拉克(David L.Clark)认为,1960年之前的考古学没有出现一套系统、规范、科学的理论学说,因此处在前范式状态[4]。而“背景”在前范式状态的考古、过程考古与后过程考古中有着不同含义。
1.前范式状态的考古语境
考古学同古物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关注遗物的出土背景。“背景”让遗物成为了具有时空特征与组合关系的考古材料。不同于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Winckelmann)根据没有出土背景的雕塑建立古典雕塑年代序列[5],汤姆森(C.Thomsen)建立的“三期说”所依据的是在同一出土背景中出土的成组器物,根据这些成组器物的形态与纹饰确定不同材质遗物的相对年代[6]。此时,“背景”指的是同一出土单位内器物的共存关系。此后,汤姆森的方法被继续完善,形成了考古类型学方法。器物在经过类型学排队之后,具有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背景”因此也具有了年代学上的时间先后关系上的含义。但类型背后有更深层的背景信息。学者们就类型是考古学家对材料的分类还是古代社会中的实际存在、类型的差异同功能还是同风格相关进行了激烈争论[7]。此时的“背景”涉及到了主观与客观、科学与建构等理论问题。
19世纪兴起的进化考古为“背景”概念提供了一种特殊含义。进化考古认为,达尔文进化论已经揭示了史前社会的发展进程,民族学材料则为这一进程提供了证据支持,考古材料只是细化了这一进程。将考古材料同民族学材料进行形态类比,便可知其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而将现代民族文化从简单到复杂进行排列,就能表明史前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8]。可见,进化考古并没有从考古材料自身的背景出发去了解过去,而是将材料放置在进化论的背景中,来证明理论的科学性以及土著群体的原始性。这一“背景”由于忽略了文化的复杂性并同种族主义相联系而遭到后人的批判。
同类型学一样让“背景”概念具有时间意义的是考古地层学。地层学通过强调层位、遗迹之间的时空位置关系,尤其是纵向的叠压、打破关系来建立可靠的文化年代[9]。20世纪后半叶,“哈里斯矩阵”(Harris Matrix)将地层学的方法进一步完善[10]。同传统地层学相比,“哈里斯矩阵”更加强调层位之间的水平关系、层位之间的分界面,并对地层与遗迹进一步细化,对层位形成背后的自然与人类行为动因更加敏感。“哈里斯矩阵”中的“背景”超越了时间,具有了自然与文化过程的意义。
类型学同地层学一起构成了文化历史考古的基本方法。文化历史考古根据反复共生的遗存特征定义考古学文化,通过地层学与类型学确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范围,进而确定某一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及不同文化区的相互关系[11]。此时,考古学家关注的“背景”是考古遗存的时空关系。但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背景”含义不止于此。由于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基本预设是文化特征背后是某一特定人群的观念,考古学文化总是同特定的族群联系在一起[12]。因此,“背景”在文化历史考古中的深层含义是将考古材料放在文化或者人群的背景中进行研究,探索考古材料与人群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群的历史与迁徙。
随着人们意识到文化历史考古在解释文化变化上的缺陷,考古学家开始采用功能的视角去研究考古材料,开始关注生态环境、经济生产、技术、人与环境的关系、社会、聚落形态等史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此时的考古发掘更加注意收集和研究孢粉、土壤、动植物遗存、聚落与房屋形态分布等与环境、生计及社会生活有关的遗存。特里格将这种考古形态称为早期功能—过程考古[13]。这里的“背景”侧重考古材料同技术、环境、经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14]。
2.过程考古语境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过程考古开始批判文化历史考古规范的、水波论式的文化观以及见物不见人的研究策略,主张用实证主义认识论去建立有关人类行为及文化发展过程的规律,让考古学变得更科学、更人类学[15]。此时,“背景”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大量出现在有关考古材料与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中。
行为考古学家希弗(Michael B.Schiffer)区分出了两种类型的“背景”,分别是“系统背景”(systemic context)和“考古学背景”(archaeological context),前者可以理解为考古材料背后的动态人类行为过程,后者可以理解为物品废弃后在埋藏环境的作用下所形成的考古材料背景[16]。希弗认为,考古材料的空间形态并不直接反映人类行为,其背后经历了复杂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的改造过程,行为考古就是要研究考古材料所经历的一系列过程,进而归纳考古材料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17]。因此,“背景”在行为考古中指的考古材料所经历的生命史、人类活动与埋藏环境改造。近年来,行为考古受后过程考古学影响也开始针对仪式、象征与意义等问题提出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同样与“背景”有关,即通过研究考古材料背后的象征行为、生命史与物理特性,去获知考古材料在表达象征意义、参与仪式活动、彰显社会权力方面的作用[18]。此外,行为考古的研究范畴还涉及通过研究古代与现代物质文化去探索具体社会中的人类行为模式与历史、物质文化与人类行为的一般关系以及人类行为方式变化的一般过程[19],因此,行为考古中“背景”的深层含义是将物质材料放置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中,去研究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以及揭示人类行为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与希弗的理念不同,宾福德(Lewis R.Binford)认为,考古材料背后的文化系统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不存在一个原初的背景等待人们去发现。考古材料所经历的文化改造过程本身就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考古学家要做的是对当代狩猎采集群体的行为机制进行观察与研究,去发现他们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会产生何种适应与行为,进而留下何种结构的考古材料,去理解文化系统的运作机制,以此构建可靠的参考框架,用以强化从静态考古材料到动态人类行为的推理[20]。综上所述,“背景”在宾福德的理论体系中主要指的是通过民族考古建立有关狩猎采集者适应方式的参考框架,完善考古研究的推理过程,在可靠的推理链条中探索考古材料背后的人类行为与环境适应。此外,宾福德还认为,文化是由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所组成的超肉体适应系统,在实践中运用多变量分析的方法,通过研究与传统、社会关系以及环境适应有关的材料,探索文化系统内部的关系与变化[21]。因此,“背景”在宾福德理论中的含义还包括了将考古材料同文化系统的各部分建立联系,重建文化系统及系统内部的关系。
过程考古学家弗兰纳里(Kent V.Flannery)与巴策(K.W.Butzer)也对“背景”概念做出了系统论述。弗兰纳里更侧重研究宗教仪式在复杂社会中的作用,主张将宗教遗存放置在其出土背景中进行背景分析,去研究宗教物品在个人、家户、社区与区域中所发挥的功能[22]。除宗教遗存外,一般考古遗存也适用于背景分析。由此,“背景”在弗兰纳里的理论体系中指的是将考古遗存放在家户、社区与区域等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间与出土背景中分析其社会功能,进而重建史前社会的生计—聚落组织、社会政治结构与宗教仪式[23]。环境考古学家巴策也提出了一种背景分析方法,主张考古学应去研究经济与聚落形态背后的环境背景,以遗址为单位,去研究人类群体及其生计—聚落系统如何在空间、经济与社会等层面同环境背景互动,进而理解该群体所处的人类生态系统[24]。因此,“背景”在巴策的理论体系中指的是考古遗址的环境背景、生计—聚落系统同环境的关系以及整个人类生态系统的运作。
3.后过程考古语境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过程考古让“背景”成为考古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其含义被进一步丰富。后过程考古和过程考古在考古材料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上存在显著分歧。过程考古认为考古材料同人类行为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但后过程考古认为二者的关系涉及人的实践与能动性、文化观念与特定的历史背景[25]。对此,后过程考古认为物质文化是人们有意构建的,人们会主动运用物质文化去构建社会关系、彰显能动性,物质文化的意义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产生的[26]。
为了理解物质文化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的意义,霍德(Ian Hodder)提出了背景考古(contextual archaeology)的研究理念。背景考古主张将物质文化放在特定的背景关联中理解其意义。在背景考古中,“背景”概念指的是与物质文化意义相关的所有背景关联,它囊括了文化历史考古中的时空背景,过程考古中的功能、环境、堆积过程,着重强调物质文化在社会与象征背景中的意义[27]。在实践中,背景考古试图寻找考古材料在时间、空间、堆积单位与类型等相关背景中的诸多关联性、相似性与差异性,将这些关联进一步抽象并同结构主义、结构化(structuration)等社会理论相联系,对考古材料在具体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深层意义进行解读[28]。如果某些关联在不同的背景中大量出现,那么我们对考古材料意义的解读会更合理,更接近古代[29]。
背景考古还强调物质文化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中的意义。这种意义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共享语言,让所有人都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与境况加以理解,犹如棋牌游戏的规则一样,能够让所有的参与者参与其中,让游戏顺利进行[30]。对此,背景考古应用惯习(habitus)(又译作习性)与物质性(materiality)理论来恢复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惯习作为能够让实践者产生特定的行动方式与文化品位的实践准则,在考古材料上表现为特定的空间形态与文化风格[31]。惯习理论对背景的构建主要根据高精度的考古材料勾勒出古人日常生活实践的技术、经济、社会、仪式与空间背景,从中归纳出惯习的空间与物质表现,进而研究惯习同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物质性理论认为,物承载着人的创造性与能动性,有着人的性质与力量,是人心智与人格的延伸,其物质特征能够表达社会观念,如黄金的质地与颜色能够表达永恒与不朽[32]。物质性通过将遗物放在古代的世界观与本体论背景中来研究其社会与象征意义。物质性理论对历史时期社会观念背景的构建主要根据文献,而史前时期社会观念背景的构建则通过民族志或人类学理论实现。
背景考古认为,物质文化的意义还是行动者在行动中主动赋予的。此时的“背景”包括行动者的意图与后果,以及行动者的感官体验,其中,前者通过能动性(agency)理论实现[33],后者通过现象学(phenomenology)理论实现[34]。能动性理论构建背景的方式存在较大争议[35]。一些研究者认为,能动性理论更适合研究处在文化变革阶段,且各阶段的社会文化特征清晰的社会,那些同社会文化整体特征不一致的现象即为个体能动性的体现[36]。另有研究者认为,在考古材料中区分出行动的意图和结果是很困难的,主张从实践本身出发,从考古材料中构建不同时间背景下,实践发生的空间背景(如房屋空间)与物质条件,进而去理解能动性同实践的发生及其同社会演变的关系[37]。现象学构建背景的方式是研究者对所要研究的景观建筑进行实地走访,记录考古学家在不同方位、不同地点行走时的感官体验,最后结合民族志、物质性、意识形态等理论阐释景观的意义[38]。
除了上述“背景”之外,背景考古还研究物质文化在当代社会背景中的意义。此时的“背景”涉及当代考古学家在阐释考古材料的意义时所采用的理论方法,包括:强调从考古学家的知识背景与理论视角出发去阐释考古材料的阐释学(hermeneutics)方法[39];通过提问—回答的方式重建古人行动背景的问答逻辑(the logic of question and answer)[40];将考古材料民族学材料进行关联类比(relational analogy),增加重建古代社会背景的合理性[41]。此外,背景考古对当代社会背景的关注还涉及物质文化对当代社会及民族群体的意义以及揭示考古阐释所存在的各种偏见[42]。此时,“背景”主要指的是与考古阐释及材料意义直接相关的利益群体,以及对科学、唯一性与权威性的后现代反思与批判。
随着研究的深入,物质性、能动性与现象学理论在研究史前文化的象征意义及构建意义产生的背景时遭遇了困境。对此,后过程考古在2010年前后出现了理论转向,从关注物质文化的社会与象征意义转向研究人与物在日常实践中的关系。这以霍德的纠缠(entanglement)理论为代表。纠缠指的是包括人、动植物、观念、社会制度等在内的各种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在纠缠中产生并联系在一起的[43]。纠缠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在充分考虑特殊的文化背景基础上揭示了人—物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复杂这一一般特征,使得考古学家能够将社会文化变化这样的大问题放在人—物关系一般特征的理论背景中进行宏观解释与微观研究[44]。除了理论背景外,纠缠理论重点关注古人的日常实践背景以及通过对材料的精细发掘与科学分析建立的考古背景,在此基础上,对人与物在具体文化背景中的复杂关系进行构建[45]。
为了将“背景”的多重含义贯穿在考古实践中,霍德提出了反身的方法(reflexive method)[46]。反身的方法主张对考古材料进行高精度发掘与多学科研究,最大限度地提炼考古材料在功能、堆积、废弃等人类行为方面的背景信息,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理论对材料的意义进行阐释。反身考古注意到了当代社会背景对考古阐释的影响,主张考古学家记录自己在阐释材料时的理论背景与思考过程,并就考古知识产生的过程进行研究。反身考古还认为,不同参与者具有各自的视角与立场,因此主张多元视角阐释,而阐释的合理性则从考古阐释的内在逻辑、同考古材料的一致性,以及道德、政治、伦理等背景中去评价。
二、Context与中国考古学实践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背景”概念同西方考古学的理论范式密切相关,它在不同理论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可以分为考古材料自身的出土背景与特征和考古材料背后的关联性,后者包括考古材料同古代社会文化的关联,以及与“透物见人”有关的理论与社会背景(表一)。
“背景”的诸多含义在中国考古学实践中均有体现,但体现的程度不均衡。文化历史考古的“背景”体现的程度最高[47]。随着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聚落形态研究的广泛开展,早期功能—过程考古的“背景”也被大量关注[48]。过程考古的“背景”概念仅在农业起源[49]、遗址废弃过程[50]、器物技术分析[51]、社会复杂化[52]等个别研究中有所体现。而后过程考古的“背景”概念在中国考古实践中还处在理论探索与尝试性研究阶段:陈胜前等在石器、陶器与艺术研究中使用的“关联的方法”同背景考古相似,主张将遗物的形态、功能、风格等特征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关联[53];一些学者尝试应用结构主义、性别考古、惯习等理论研究聚落空间的社会与象征意义[54];物质性理论的思想被应用到对玉器、器物纹饰、神圣空间以及岩画的意义解读中[55];当代社会背景对考古阐释的影响体现在文明起源尤其是夏文化的研究中[56]。

表一// 考古学中“背景”概念的含义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背景”一直是西方考古学的重要概念,但在中国考古学实践中却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这一方面同中国考古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中国文化都偏重形象思维,不擅长逻辑思辨与概念抽象有关[57]。另一方面,根据背景考古的观点,我们或许应该从中西方考古学发展的背景中去看清楚上述差异的来龙去脉。从特里格对西方考古学史的梳理可知,西方考古学的最大特点是存在着理论范式的多次变革。由于“背景”概念涉及对考古材料的解释与“透物见人”研究,而且理论范式的变革也不是新范式完全取代旧范式,不同的范式会同时并存,因此,范式变革并没有舍弃“背景”概念,反而让其含义越来越丰富。中国考古学自诞生时起,就受到民族主义以及追寻中华文明起源的影响,表现出了浓厚的史学倾向,并以重建国史为己任[58]。这一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这使得文化历史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形态。虽然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聚落形态考古等偏向功能主义与过程考古的研究在中国考古学实践中已经取得诸多成果,但中国考古将其看作是一种研究方法,忽略了其背后的理论思想与关键概念,上述研究因此成为文化历史考古的补充,并没有构成新的研究范式[59]。这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实践中重点关注考古材料的时空与类型背景,而考古材料的环境、经济与社会背景则成为时空与类型背景的陪衬被放在考古报告的附录之中。由于缺乏基本概念与研究理念,对推断人类行为的考古推理、废弃过程对考古阐释的影响以及从考古材料的诸多背景关联中理解其社会象征意义等“背景”的关注无法开展。
鉴于“背景”概念在考古学中的重要作用,“背景”概念应当在中国考古实践中受到更多的重视。考虑到影响“背景”概念在中西方考古学中存在差异的因素,我们应该拓展考古学理论范式与“透物见人”的研究视角。考古学理论范式可以分为科学与人文两大阵营,分别以过程考古与后过程考古为代表。不同阵营的理论在适合解决的问题、理论来源以及认识论上存在着分歧[60]。例如,在科学阵营中,行为考古能够解释器物的生产技术、遗址的废弃与生计方式的关系等[61]。而在人文阵营中,惯习理论可应用于房屋空间的社会意义、日常实践与社会凝聚力的构建、技术产生的社会背景、宗教产生的社会实践背景、族属研究等领域[62];物质性理论能够阐释历史时期遗物的社会意义,反思文化遗产实践中对本土物质观的忽视,研究史前社会的世界观与本体论等[63];纠缠理论可应用于社会演化研究,如研磨工具与磨制石器的使用所引发的人—物关系变化是如何让近东地区定居与驯化得以发生[64],狩猎的社会象征意义如何延缓了驯化的发生等[65]。不同阵营的理论在思想来源上也存在着重大差异。例如,生态适应的理论多来自文化生态学;惯习、物质性理论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纠缠理论中蕴含了有关物的哲学本体论思想以及事物间关系的辩证法思想。了解上述差异可以拓宽我们研究的广度,有助于我们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选择合适的理论,并让我们在进行理论构建时有据可依。上述差异还表明,不同阵营与范式的理论所能揭示出的考古材料背景信息是不同的。对此,中国考古学要在理解理论差异、拓展理论范式的基础上,优化不同范式所能提炼出的背景信息,完善考古材料的背景构建,为考古学家深入研究社会文化变迁提供高精度的年代学背景、不同材料的特征与关联性背景、环境背景、生计方式与人地关系背景,理解人类行为的参考框架、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以及物质文化的社会象征意义等。
即便不同阵营的理论在构建考古材料的背景上都有所贡献,但这些理论在认识论上依然存在根本分歧。科学阵营的理论强调考古材料的客观性,主张实证主义认识论。人文阵营的理论认为考古材料中蕴含着理论,主张阐释学认识论,强调考古学家自身的理论背景与立场。认识论的差异让这两种考古学具有不同的研究目标。科学的考古学试图建立客观的知识、规律与理论,揭示人的自然属性,而人文的考古学则试图阐释考古材料的社会意义与人文价值,揭示人的社会属性。这告诫我们要根据研究目标选择合适的理论。在具体实践中,更多的学者采取的是更为实际的策略。考古学家们针对特定的问题,或将手中的材料放置在某一合适的理论框架中产生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或运用多种类型的材料去产生强有力的论述、给出更具说服力的答案。前一种策略强调考古学阐释的理论背景,后者则更强调考古材料自身的背景。对此,我们除了要拓展理论范式外,还要加强考古材料自身背景的发掘。由于文化历史考古是当下中国考古学中的主流实践形式,在田野实践以及考古报告的编写中,对考古材料自身背景的关注很多以类型学研究为导向,关注风格特征明显的典型遗物,而非遗存的背景关联。虽然我们也对动植物、环境、器物功能、原料成分等与复原人类行为背景有关的遗存进行科学分析,但除部分重要遗址、遗迹的报告中有对这些遗存的综合分析外[66],相关成果多以附录或者附表的形式罗列在考古报告中,这一定程度割裂了同一背景下各类遗存之间的联系。遗存背景信息的残缺,尤其是房屋居住面各类遗存(包括土壤微形态等微小遗存)的空间与功能背景的不完整,使得诸如利用房屋微观空间探索社会结构与社会意义的这样的“透物见人”研究无法深入展开。对此,我们需要在提高发掘精度、对各类遗存进行详细分析与研究的同时,平等对待各类考古遗物,并将其放置在出土背景中进行公布[67]。材料的多样性及其背景关联的完整性是进行考古学“透物见人”研究的基础。在“透物见人”研究中,同一种材料可能有不同的阐释,而哪种阐释更合理取决于同其他相关材料的关联,对此,我们可以将不同类型的材料及其背景作为证据链关联在一起,排除对每一种材料的不合理解释后产生生命力更久、更具说服力的解释[68]。
此外,考古材料背后蕴含着与人类社会有关的诸多背景信息需要我们用不同的理论予以揭示,因此,在面对一批材料或者一个问题时,应鼓励不同学者从多个理论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反复研究与阐释,多角度地“透物见人”。如面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址,文化历史考古可以进行细致的年代学分析,了解遗址的时空、年代、同其他文化的关系等;功能—过程考古可以揭示当时的人地关系;过程考古可以探究遗址的废弃;后过程考古可以将三段式“之”字纹筒形罐、房屋室内空间的严整结构同器物功能、性别分工、社会经济背景相结合,揭示这些结构背后的社会与象征意义。再如宗教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中的作用这一问题。霍德以土耳其恰塔霍裕克遗址(Çatalhöyük)的高精度材料为基础,让不同学科的学者从惯习、神经心理学、万物有灵论、历史与记忆构建、物质性、纠缠等诸多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反复阐释,揭示了宗教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中的诸多表现,以及在构建定居社会的秩序与稳定、规避社会冲突、构建历史记忆等方面的作用[69]。不同视角能够让我们对一批材料或者一个问题有着多方位、全景式的认识,将不同范式所提炼的背景信息进行整合,进而触摸到历史的多个侧面。
三、结论
“背景”作为西方考古学的关键概念有着多重含义,包括了考古材料自身的出土背景与特征,以及考古材料背后与“透物见人”有关的诸多关联性。“背景”的含义与考古学理论范式密切相关。这其中,又以后过程考古的“背景”概念最为复杂,不仅囊括了文化历史考古与过程考古的“背景”含义,还涉及阐释物质文化意义时涉及的古代与当代的社会背景。虽然“背景”的多种含义在中国考古实践中得到体现,但体现的程度是不同的。这同中西方考古学发展过程的差异有关。“背景”概念由于涉及了考古材料自身以及对材料的解释,使得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中要对“背景”概念给予足够重视。对此,我们要拓展考古学理论范式,理解不同理论之间的差异,优化不同范式所提炼的背景信息;还要加强考古材料自身的背景发掘,提高发掘与研究精度,完整公布各类遗存及其空间信息;在研究中,运用不同类型的材料产生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并从多元视角对同一批材料及同一个问题进行反复阐释。这样我们则有可能通过考古材料的诸多背景信息勾勒出历史的大致轮廓与不同侧面,更好地实现考古学“透物见人”的目标。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胜前教授对本文提出了诸多建议,特此感谢!)
[1]Brian M.Fagan.In the Beginning:An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81:81.
[2]a.李新伟:《context方法浅谈》,《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b.郭立新:《墓葬情境分析与身份标识:以博罗横岭山墓地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c.陈胜前:《学习考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53—57、63—67页。
[3]〔加拿大〕布鲁斯·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4]David L.Clarke.Archaeology:the loss of innocence.Antiquity,1973(185):6-18.
[5]同[3],第47—48页。
[6]同[3],第99—100页。
[7]Gavin Lucas.Critical Approaches to Fieldwork.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82-90.
[8]同[3],第162页。
[9]同[7],第36—47页。
[10]Edward C.Harris.Principles of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The 2nd edition).London and San Diego:Academy Press,1989.
[11]同[3],第188页。
[12]〔英〕希安·琼斯著,陈淳、沈辛成译:《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0—32页。
[13]同[3],第240—289页。早期功能过程考古的方法有很多,包括经济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生态考古、聚落形态考古、遗址资源域分析、缀合方法等。
[14]虽然早期功能—过程考古中的“背景”概念在形式上同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过程考古学相似,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考古学家没有摆脱文化历史考古学中有关文化是特定人群观念的表达的思想,在研究中依然应用归纳法分析材料,并没有像过程考古,在文化及系统的运作与变迁以及推断人类行为等方面发展出富有建树的理论方法。因此,在“背景”的含义上,早期功能过程考古中依然存在着文化历史考古的影子。见[3],第205—267、282页。
[15]〔英〕马修·约翰逊著、魏峻译:《考古学理论导论》,岳麓书社2005年,第19—23页。
[16]Michael B.Schiffer.Archaeological context and systematic context.American Antiquity,1972,37(2):156-165.在考古材料背景中,希弗根据器物的使用地点与废弃地点是否相同区分出了原生背景(primary context)和次生背景(secondary context),使用地点和废弃地点相同的是原生背景,反之则是次生背景。
[17]Michael B.Schiffer.Formation Process of Archaeological Record.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96.
[18]Michael B.Schiffer.Behavioral Archaeology:Principle and Practice.London and Oakville:Equinox,2010.
[19]a.同[18].b.Michael B.Schiffer.Studying Technological Change:A Behavioral Approach.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2011.c.Michael B.Schiffer.The Archaeology of Science:Studying the Creation of Useful Knowledge.London and New York:Springer,2013.
[20]Lewis R.Binford.Behavioral archaeology and the‘Pompeii premise’.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1981,37(3):195-208.宾福德运用民族学和当代气象站材料构建了生态环境同狩猎采集者适应方式之间的关系模型,还对爱斯基摩人进行民族考古学研究,试图理解狩猎采集者如何利用动物资源,如何狩猎,如何改造动物骨骼,如何选择与利用居址空间等,从而构建了解释史前狩猎采集者适应方式与文化过程的参考框架。见:a.Lewis R.Binford.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b.Lewis R.Binford.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c.Lewis R.Binford.Bones:Ancient Men and Modern Myth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d.〔美〕路易斯·宾福德著、陈胜前译:《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21]a.Lewis R.Binford.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iquity,1962,28(2):217-225.b.Lewis R.Binford.Archaeological systematics and the study of culture process.American Antiquity,1965,31(2):203-210.
[22]Kent V.Flannery.Contextual analysis of ritual parapher-nalia from Formative Oaxaca.In Kent V.Flannery ed.The Early Mesoamerica Village.New York and London:Academic Press,1976:333-345.
[23]E.DeMarrais.Holistic/contextual archaeology.In C.Renfrew,P.Bahn ed.Archaeology:The Key Concept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106-108.
[24]K.W.Butzer.Archaeology as Human Ecology:Method and Theory for a Contextual Approa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25]Ian Hodder,Scott Hutson.Reading the Past: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The 3r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2-19.例如,宾福德认为墓葬的复杂性同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但皮尔森(M.P.Pearson)对英国剑桥公墓的研究表明墓葬的复杂程度同当时社会中的丧葬观念以及不同人的丧葬意图有关,见a.Lewis R.Binford.Mortuary practices:their study and their potential.Memoirs of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6-29;b.M.P.Pearson.Mortuary practices,society and ideology:an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y.In Ian Hodder ed.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99-113.
[26]a.同[25]。b.Ian Hodder.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In Michael B.Schiffer ed.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Academic Press,1985:1-26.
[27]同[25],第157—166页。
[28]同[25],第173—186页。
[29]Ian Hodder.The contextual analysis of symbolic meanings.In Ian Hodder ed.The Archaeology of Contextual Mean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8-10.例如,某一遗址中A型的胸针只见于女性墓,B型的胸针只见于男性墓,且A型胸针的装饰设计见于同生殖有关的遗物中,B型胸针的装饰设计见于同生产活动有关的器物上,而根据民族史材料,生殖和生产活动分别同女性和男性有关,那么A型胸针和B型胸针则很可能分别是女性与男性的性别表达,见[25],第176页。霍德对欧洲农业起源的研究是背景考古的典型案例。研究认为,欧洲新石器时代早期定居的发生是“家”(domus)和“野外”(agrio)作为行动准则将社会组织起来的结果,在考古材料上表现为室内/居家/女性与室外/生产/男性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发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见:Ian Hodder.The Domestication of Europe.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
[30]同[25],第158页。
[31]a.P.Bourdieu.The Logic of Practice.Translated by R.Ni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b.P.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Translated by R.Ni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2]D.Miller.Materiality:an introduction.In D.Miller ed.Materiality:Politics,History and Cultur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7-14.
[33]能动性理论关注个人(行动)与社会的关系,认为物质文化的意义可以源自行动者的意图与动机,也可以是行动者无意识实践的结果,是惯习、社会结构与社会观念的作用,见M.-A.Dobres,J.E.Robb,Agency in archaeology:paradigm or platitude?In M.-A.Dobres,J.E.Robb eds.Agency in Archaeology.London:Routledge,2000:8.该论文集提供了能动性理论的诸多案例,如人们如何利用物质文化彰显自身的意图,彰显权力,掩盖或操控意识形态,或者如平民阶层的集体劳动无意识地创造了酋邦社会等。
[34]现象学理论认为,物质文化的意义是在人的经验生活中发生的,人的身体与感官体验是意义起作用的媒介。现象学理论多用于研究史前纪念性建筑的象征意义是如何通过对人的感官体验施加影响而体现出来的,见:C.Tilley.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Oxford and Providence:Berg,1994.
[35]J.L.Dornan.Agency and archaeology:past,present,and future direction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2002,9(4):303-329.
[36]M.Johnson.Conceptions of agency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1989,8(2):189-211.
[37]a.J.Barrett.Agency,the duality of structure,and the problem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In Ian Hodder ed.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Oxford:Blackwell,2001:141-164.b.J.E.Robb.Beyond agency.World Archaeology,2010,42(4):493-520.罗布(Robb)对意大利新石器时代人们实践中所涉及到的房屋、食物、陶器、石器及雕塑等物品进行分期并同青铜时代进行对比,表明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崇尚多样性、社会等级较弱的社会,而青铜时代则是一个崇尚整体性、社会等级较强的社会。
[38]a.C.Tilley.The Materiality of Stone.New York:Berg Publishers 2004:224.b.C.Tilley.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es to landscape archaeology,In B.David,J.Thomas eds.Handbook of Landscape Archaeology.Walnut Creek:Left Coast Press,2008:274.
[39]阐释学方法主张从研究者对被阐释事物的先在理解。(pre-understanding)(如阐释者的知识背景、概念工具、价值判断等)出发,去看被阐释事物是否符合先在理解,研究者通过不断地阐释、不断地更正先在理解将分散的考古证据连接成一个整体,得出条理清晰、逻辑连贯的论述,让考古阐释同考古材料保持一致,从而获得对材料更加完整的理解。见M.Shanks,C.Tilley.Re-constructing Archaeology:Theories and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103-115.
[40]同[25],第196页。问答逻辑是英国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的思想,主张研究者根据已有的知识以及对现实的理解,针对考古材料提出与人类活动意图有关的问题并寻找答案,在当代社会背景中重演过去,重现古人行动时的背景。
[41]Ian Hodder.The Present Past: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for Archaeologist.London:B.T.Batsford Ltd,1982:24-27.关联类比更加注重类比对象在社会观念尤其是赋予物质文化以意义、利用物质文化表达观念的方式上所具有的相似性,以及类比对象中与研究问题关系密切的诸多因素,以此来增加类比过程以及恢复古代社会情境的合理性。
[42]同[25],第218—231页。偏见包括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与男性中心论、揭露当代意识形态对考古学的影响以及性别关系的多种文化构建等。
[43]Ian Hodder.Where We Are Heading in?The Evolution of Humans and Thing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8:91.人与物之间的纠缠包括依赖关系(dependence)与限制关系(dependency)。依赖关系指的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物,人造物的存在也离不开人的维护与照管,限制关系指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当人造物出现问题时,人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对其进行维护,在这个过程中物对人起到限制作用。举例来说,汽车由全球各地生产的成千上万个零部件组成。空间上,汽车的生产还涉及到不同地区的贸易协定、税收体系、行政手续、运输手段等。因此,我们可以说汽车的生产依赖不同地区的人与物。时间上,汽车依赖于数千年前发明的轮子与数百年前发明的发动机等。在与人的关系上,人的出行依赖汽车,但它出现故障,人们就无法使用它,就必须对其进行维修,就会受到车的限制。
[44]a.同[43];b.Ian Hodder.Entangled: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Things.Oxford:Wiley-Blackwell,2012.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复杂,是因为物自身的不稳定性、多变性、复杂的时间性与空间性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以至于人们在利用物去解决问题时,不仅仅同该物品发生联系,还同该物品背后的纠缠关系产生联系,这样人与物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掌控,出现问题的几率会更大,人们会引入更多、更复杂的物去解决问题,这样周而复始,人与物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复杂。
[45]同[44]b.霍德根据恰塔霍裕克遗址精细化发掘与研究所提供的丰富背景信息,用纠缠理论勾勒出了该遗址与黏土及房屋有关的人—物关系以及由宗教与象征性房屋所建立的复杂社会关系。
[46]a.Ian Hodder.Developing a reflexive method in archaeology.In Ian Hodder ed.Towards Reflexive Method in Archaeology:the Example of Çatalhöyük.McDonald Institute Monographs/British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Ankara Monograph 28,2000:3-14.b.〔瑞典〕阿萨·柏格伦、比约恩·尼尔森著,刘岩译:《回顾与展望:反身考古学还是反身的方法?》,《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47]具体包括:(1)碳十四年代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2)地层学,如a.霍东峰:《考古层位学之“层位关系”》,《考古》2017年第5期;b.汤惠生:《哈里斯矩阵:考古地层学理论的新进展》,《考古》2013年第3期;(3)类型学,见孙祖初:《考古类型学的中国化历程》,《文物季刊》1998年第4期;(4)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关系,如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5)文化的远距离交流与族属,如a.李伯谦:《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52—459页;b.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48]a.袁靖:《中国家养动物起源的再思考》,《考古》2018年第9期;b.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c.夏正楷:《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49]陈胜前:《史前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起源过程的文化生态考察》,科学出版社2014年。该研究以宾福德有关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为参考框架,揭示了中国农业起源的文化生态背景。
[50]李彬森:《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废弃过程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该研究应用行为考古中的遗址形成过程理论研究遗址废弃同生计方式之间的关系。
[51]与行为考古中器物生命史相似的“操作链”概念被用到石器、陶器的技术分析中,见a.陈虹、沈辰:《石器研究中“操作链”的概念、内涵及应用》,《人类学学报》2009年第2期;b.郭梦:《操作链理论与陶器制作技术研究》,《考古》2013年第4期。
[52]在复杂社会研究中应用到了弗兰纳里主张的从家户、社区、区域三个尺度对社会复杂化进程进行分析的背景分析法,如a.〔澳〕刘莉著、陈星灿等译:《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b.李新伟:《仪式圣地的兴衰: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53]a.陈胜前等:《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石铲的功能研究》,《考古》2013年第6期;b.陈继玲、陈胜前:《查海遗址陶器风格变化的功能视角》,《边疆考古研究(第18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61—178页;c.陈继玲、陈胜前:《史前艺术方法新探》,《东南文化》2016年第3期。
[54]a.陈畅:《结构主义重构社会组织的考古学探索》,《江汉考古》2019年第1期;b.林嘉琳、孙岩:《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c.刘岩:《后过程考古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55]a.邓聪:《兴隆洼文化玉器与植物宇宙观》,《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S1期。b.曲枫:《图像时代的精神寓言——中国新石器时代神话、艺术与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c.F.Qu.Rice ecology and ecological relations:an ont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Jiangjunya masks and crop images from China’s east coast.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2019,29(3):1-22.
[56]陈胜前:《为什么夏是一个问题》,《读书》2019年第2期。
[57]陈胜前:《当代考古学概念的重建》,《南方文物》2012年第4期。
[58]陈星灿:《以古史重建为己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4日第B07版。
[59]陈淳:《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60]Ian Hodder.Introduction: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debate in archaeology.In Ian Hodder ed.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The 2nd edi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12:1-14.
[61]同[18]。
[62]a.T.Yates.Habitus and social space:some suggestions about meaning in the Saami(Lapp)tent ca.1700-1900.In Ian Hodder ed.The Meaning of Things.London:Routledge,1989:249-261.b.Ian Hodder,C.Cessford.Daily practice and social memory at Çatalhöyük.American Archaeology,2004,69(1):17-40.c.M.Dielter ,I.Herbich,Habitus,techniques,style:an approach to the social understanding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boundaries.In M.Stark ed.The Archaeology of Social Boundaries.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8:232-263.d.W.Keane.Marked,absent,habitual:approaches to Neolithic religion at Çatalhöyük.In Ian Hodder ed.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Çatalhöyük a Case Stud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87-219.e.G.G.Bentley.Ethnicity and practic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87,29(1):24-55.
[63]a.L.Meskell.Object Worlds in Ancient Egypt:Material Biographies Past and Present.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4.b.D.Byrne.Archaeology and the fortress of rationality.In L.Meskell ed.Cosmopolitan Archaeologie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9:69-88.c.D.Boric.Theater of predation:beneath the skin of Göbekli Tepe images.In C.Watts ed.Relational Archaeologies:Humans,Animals,Things.London:Routledge,2014:42-64.
[64]Ian Hodder.Things and the slow Neolithic:the Middle Eastern transformation.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2018,25:155-177.
[65]Ian Hodder.Studies in Human-Thing Entanglement.2017:44-63.参见http://www.ian-hodder.com/books/studies-human-thing-entanglement.
[66]如: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H85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6期。
[67]恰塔霍裕克遗址的发掘报告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范例。在每年的年度发掘初步报告中,会重点公布所发掘房屋或遗迹单位在建造、不同使用阶段、叠压打破关系、所反映的人类行为活动的空间背景信息,还会涉及各类遗物以及所反映的人类活动信息的初步研究结果。该遗址每年的初步发掘报告见:http://www.catalhoyuk.com/research/archive_reports.
[68]Ian Hodder.Assembling Science in Çatalhöyük.In Ian Hodder, A.Marciniak eds.Assembling Çatalhöyük.Leeds:Maney Publishing,2015:7-12.如陶器、石器等原料产地很远可能说明了远距离交换的存在,也可能说明了古人对资源的大范围利用,如果人骨、植物遗存、同位素等证据都支持后者,那么后者则是对材料更具说服力的阐释。在研究恰塔霍裕克遗址的流动性时,研究者用到了七种类型的考古材料作为证据,分别是:人股骨横切面形态表明远距离行走,芦苇草的远距离入侵,山羊同位素证据表明对植物的大范围利用,陶器、石器、串珠、黑曜石原料的远距离来源。
[69]a.Ian Hodder ed.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Çatalhöyük as a Case Stud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b.Ian Hodder ed.Religion at Work in a Neolithic society:Vital Matt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c.Ian Hodder ed.Religion,History and Place in the Origin of Settled Life.Loui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2018.d.Ian Hodder ed.Violence and the Sacre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Girardian Conversation at Çatalhöyü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