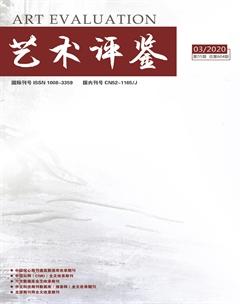从美术文论看西画东渐对明末清初画学的影响
曹明
摘要:西画东渐对明末清初画学的影响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学界基本不否认这种影响的存在,但影响的力度、是否对后来中国画的发展产生影响则是争论的焦点。我们不囿于个别画家或传教士的魅力,也不着迷于社会学、经济学的宏大叙述,而是翻阅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画学专著或笔记题跋,试图从文本的角度一窥西画东渐在明末清初画学的印迹。
关键词:美术文论 西画东渐 明末清初 画学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5-0043-03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众多文档的解密,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相关资料如书籍、来往信件不断被发现,人们对那段似乎被历史的风尘有意或无意遮蔽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界对明末清初西画东渐的研究也渐趋活跃。其中西画东渐到底对中国当时的画学和以后中国画的发展是否产生影响及其深度、广度均产生较大的分歧和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西画东渐并没有对中国画学的发展产生实质影响。无论从当时还是以后的绘画理论和实践上,中国古典绘画的话语体系依然是民族的、自足的。与之相反,一些欧美学者则认为西画对当时的一些画家个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画的发展。
明清之际执掌画学牛耳的依然是那些文人士大夫。他们在创作或鉴赏之余,总会把自己的观察和体悟行诸文字,或画学专著、或笔记题跋。研究那些几百年前文字中鲜活的思想和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痕迹,或可追索西画东渐对国内画学产生影响的草蛇灰线。
明朝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发现利用宗教绘画进行传教活动可以起到语言文字难以企及的效果,如传教士金尼阁、毕方济等人“皆言及用西洋画及西洋雕版画以为在中国传教之辅助而收大效之事”[1]。1583年,罗明坚在肇庆所建的小教堂中悬挂圣母像,供信教民众参拜。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传教士利玛窦呈献给神宗皇帝的礼物中就包括一幅天主像和两幅天主圣母像。乔瓦尼则在澳门教习中国人学习油画。清朝前期的皇帝对异域文化相对抱有较宽容的态度,除了有对汉族文人集团所把持的学术话语权有所抑制的考虑外,也不乏宣扬其战功伟业的“政治写真”的需要。康熙末年 ,清廷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使得传教士在内地的生存环境日趋严苛。“苏州教案”和“江南教案”事件实际上使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乾隆中叶趋于绝迹。
马渭源在《论西画东渐对明清中华帝国社会的影响》一文中述及社会各阶层对西画东渐作出的回应,并把西画东渐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范畴。对一种美术现象的考察固然可以有宏大的视角,但针对文本的考察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有接近于事件真相的可能。
明代姜绍书在《无声史诗》“西域画”条目写道:“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嬰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2]。苏州知府赵心堂初见利玛窦携来之天主像,不禁赞叹道:“是像非常,真为天地万物之大主矣”,
乃设高堂,行跪拜礼。[3]
杜赫德曾描述过满清官员无法理解在一张纸上如何能如此逼真的再现亭台楼阁,“初见时,还以为是真的”。康熙时代,画家切拉蒂尼用巴洛克风格装饰北京耶稣会教堂的墙壁与天花板,当时参观教堂的人们“不能相信那柱子是画出来的。当他们抬起头看天花板时,那些按照透视方法描绘出来的巨大空间,那些似乎在天国中漂浮的人物,令他们惊叹不已”[4]。
中外美术交流的历史早已有之。南朝画家张僧繇的佛道壁画人物就吸收了源自印度的“凹凸法”,通过晕染加强人物表现的立体感,敦煌壁画也依然保存有“凹凸法”的画迹。但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基因来源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中国传统绘画并不是真正的视觉艺术,它只是文化的一种表征,是文人士大夫对于自身生存环境和所持儒家思想的一种隐喻。长期以来,文人绘画并没有追求技法和视觉真实的需要。民间画工也只是把绘画当作糊口的技艺,缺乏变革的动力,最多也只是一些炫技的刻苦罢了。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中国传统绘画在自足的发展,虽然也有风格的流变和个别画家的嬗变,但终不离传统的笔墨语言和丘壑样式。普通民众在突然面对全新的一种绘画样式,特别是写实主义这种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艺术形式,其不解和震惊自是难免。
传教士出于传教的目的,与北京、南京的官僚士大夫集团多有接触。部分思想开明的文人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一些画家对西画亦持相对公允的态度。
明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翻译其实已经把画法几何传入国内,为国人掌握和运用真正意义上的透视法奠定了基础。清代画家丁皋在《写真秘诀》附录《退学轩问答八则》有云:“夫西洋景者,大都取象于坤,其法贯乎阴也。宜方宜曲,宜暗宜深,总不出外宽内窄之形,争横竖于一线”[5]。宫廷画家邹一桂认为:“西洋善勾股法,故其绘画於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宽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6]。这些以乾坤阴阳等民族语言来理解西画,相较于科学的透视法,还都属于经验的层面。
作为清高级官员的年希尧在初版《视学》序文《视学弁言》中有云:“余囊岁即留心视学,率尝任智殚思,久未得其端绪。迨后获与泰西郎学士数相晤对,即能以西法作中土绘事”[7]。其所附图版详细介绍了西方透视法。在再版序言中,年希尧甚至有中西融合的想法:“中土工绘事者,或千岩万壑,或深林密箐,意匠经营得心应手,固可纵横自如,淋漓尽致,而相赏于尺度风裁之外。至于楼阁器物之类,欲其出入规矩毫发无差,非取则于泰西之法,万不能穷其理而造其极”[7]。遗憾的是,在那个时代能以科学的态度和精神研究中西绘画的学人和画家实在太少。
在16-18世纪的画论文本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中国社会至少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西画的态度从较宽容到日趋保守。
万历崇祯年间汪坷玉《珊瑚网》记载《西士作曼倩采桃图》,有“亦颇神彩生动……虽吴道子运笔谅莫能过”之语。[8]陈烺在《读画辑略》中述及焦秉贞:“工人物,能以仇十洲笔意参用泰西画法,流辈皆不及”[9]。蒋廷锡对所画《牡丹》对西画也颇多赞誉,他曾自题扇面:“戏学海西烘染法”。得意之情跃然纸上。清初几位皇帝对西洋绘画也情有独钟。康熙认为:“西洋人写像,得顾虎头之妙”。[10]并多次下旨征召懂西洋绘画艺术的画家入值供奉御用。他还把传教士马国贤刻印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铜版画颁赐给他的子孙和皇亲贵戚。
但在“四王”的艺术审美价值取向与审美标准成为官方和文人士族的精神灯塔的情况下,即便皇帝的艺术喜好也只能囿于紫禁城。作为宫廷画家的邹一桂虽也习学西画,但骨子里仍坚定自己文人画家的风骨:“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6]。这基本代表了当时文人画家对西画的基本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的一些画家在看到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后,虽然不以为然,甚至义愤填膺,但确实在自己的创作中多少吸收了西画的透视技巧和色彩表现,以使作品显得更加立体,画面空间更加真实。但这种将中西不同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技法加以综合,创造出的所谓折衷主义画风,影响范围既不出紫禁城的高墙,也很快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而趋于消亡。
从大量文本的记述来看,基于文艺复兴写实主义风格的西画在承担宗教的功用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西画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特别是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也着实吸引了一部分思想开明的文人画家和市井画工的兴趣,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体现。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西画的影响确实有限:
就影响的人群而言,明末的万历皇帝对西画的兴趣仅在于新奇,新鲜感一过,也就不了了之。清康熙帝虽然征召懂西画的传教士为皇家服务,而且着令培养了一批掌握写实技巧的院画家,但所有的影响基本不出紫禁城的院墙。另外,康熙帝对西画的重视,固然有个人喜好的原因,但作为一代英主,其实更看重西方古典写实主义绘画的强大视觉冲击力和可复制铜版画所具有的巨大传播力量,这些都可以为政治服务。特别值得玩味的是,那些曾经在清宫供奉过的院画家在离开紫禁城之后,又都回归文人画的传统,几无西画的痕迹。如院画家陈枚虽然学习过西画技法,也创作过运用透视法的作品,但告老还乡之后,其创作完全是传统文人画的趣味。明末清初,执画学牛耳的董其昌和“四王”等学派虽然据考证都曾接触过西画或传教士画家,但在他们的书论画论中,都绝少见到有关西画的文字。至于广大的士大夫画家群体,西洋绘画在他们的眼中就如茶余饭后的谈资,却也很快风轻云淡。民间画工虽然以西画为炫技,吸引市井百姓的兴趣,但缺乏专业的画法指导,终不免粗疏。随着时间的流逝,民间绘画残存的那一点“泰西法”的印迹也逐渐消亡。
就影响的地域而言,西画东渐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南京。根据莫小也等专家学者的研究,北方天津杨柳青和南方苏州桃花坞作为民间年画的重镇,也留下了西洋画的印迹。另外,1614年,乔瓦尼在澳门的基督教圣保禄修院里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传授西方繪画的美术学校,培养了倪雅谷、游文辉等一批中国的油画家,并把与澳门相邻的广州发展成一个西画中心。但这些地区相比广大的明清疆域而言,实在微不足道。当时绝大部分地区的中国人可能终其一生也没有接触过西画。即便是广州,这个当时最“西化”的城市,按苏利文的说法:“没有迹象证明,在广东与其它开放港口的文人学士受到过欧风艺术的丝毫影响,因为采用外国风格的画家并不是与耶稣会有关的学者,而是那些没有地位的画家,他们竭尽全力为外国市场制作西画,仅此而已”[4]。
就对当时社会各阶层思想层面的影响和推动封建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而言,西画东渐的作用也并不显著。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传教士自身的素质所决定。许多传教士及其信奉的宗教本身就对近代科学技术抱有敌意,更遑论传播西画所体现的文艺复兴之人文主义和科学思想。二是传教士到中国的目的并不在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是进行宗教思想的传播,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力。据统计,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的近200年间,耶稣会士在中国译著西书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 种,占总数57%。[11]他们秉承的“文化传教”策略,是通过权衡当时中华帝国国力而采取的一种妥协的手段。
西洋绘画进入中国恰逢董其昌的“文人画”与“南北宗”理论及“四王”的“袭古”“泥古”之风席卷画坛,代表中国士大夫阶层审美价值取向之时。画家的绘画风格趋于同质化,任何变革创新的努力都会被视为异端。在这样的范围中,写实主义的西画和以笔墨意趣为旨的文人画当然显得格格不入。我们现在翻阅那个时代的画论和笔记题跋,终不免臆测,如果西画东渐一直延续下去,如果后来的文人画家能持更宽容的态度,现在的中国画会是何种面貌?
参考文献:
[1]胡光华.中国明清油画[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
[2]姜绍书.无声史诗[A].于安澜.画史丛书卷七[C].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3]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M].北京:上智编译馆,1947.
[4]苏立文.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反应[A].黄时鉴:东西交流论谭(第一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1998.
[5]李来源,林木.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6]邹一桂.小山画谱[A]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十四)[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7]年希尧.视学[A].《续修四库全书》编篡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067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汪珂玉.铁珊瑚[A].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9]王伯敏.132名中国画画家(三国-现代)[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4.
[10]方豪.中西交通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