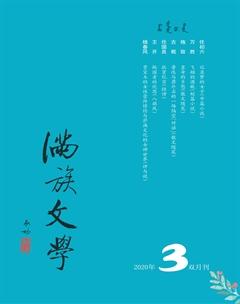皇帝的乡愁——春夏篇
〔满族〕格致
吉林乌拉到北京,这中间隔着多少公里?我一直说不出那个准确的数字。但这并不妨碍我在两地之间频繁地往来。频繁地往来,还记不住里程,说明这件事不需要我操心。记住里程和忘掉里程,都不妨碍我在规定的时间到达北京或回到吉林。我需要牢记的,是这两地的交通工具以及它們的起始时刻。我发现,我还是记住了该记住的。这两地之间有四种交通工具:普通火车,那种已成为很多人记忆的绿皮火车,完成这个里程要用十六小时——下午两点多从吉林发车,第二天早上八点多到北京;T字头特快火车,把穿越这一距离的时间成功缩短了。似乎车型没变,颜色也没变,只悄悄改变了速度——晚上九点四十发车,第二天八点四十到北京(很长一段时间,这趟火车,都是北京和吉林之间最快的交通工具。那时领导去北京开会,也就是坐个软卧,老百姓坐硬卧硬座);公路客车,因我没有那么走过,不知要用多少小时,也不知起始时间。现在是高铁时代,是七个小时了——上午九点多发车,下午五点多到北京。实现了朝发夕至。我认为高铁已经不是火车了,它已经面目全非。车型变了,颜色变了,速度更是变了。绿皮火车是毛毛虫,高铁是它蜕变出来的白蝴蝶。绿色是慢的,而白色可以飞——你看火箭和航天器大多是白色的。如果把高铁漆成红色,我想也并不影响车的速度。可能是考虑视觉。一辆那么长的车,那么高速地贴着地皮飞,要是红色或其他深色,看上去像是一条火龙。它所过之地似乎都被点着了。如果从蝴蝶的角度想,把高铁车在白底上涂些个绚丽的斑点,也应该可以。真正能飞的是飞机,从长春机场起飞,用时两个半小时,到北京机场。
这几种交通工具,除公路,我都使用过。其中特快我用的最多。这趟火车晚上太阳落山从吉林发车,走一宿夜路,到达终点的时候,刚好是太阳升起来之后。而这个早上,已经是北京的早上了。虽然也经历了十一个小时的路程,但因这趟车上有卧铺——如果你在火车上睡觉没有什么障碍——那么,你也就是睡了一觉,顶多还做了一些醒来想不起来的梦,十一个小时的路程被睡眠这个约数约得所剩无几。每次,我都是坐这趟特快,我爱在火车上睡觉,晃晃悠悠的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我爱卧铺不仅仅是因为摇晃起来我更容易入睡,卧铺车厢的另一好处是放包裹的地方要比其他车厢多。如果能买到下铺,那么一个床下面都可以放东西了。我很在意这个空间的大小。因为每次去北京,我都是和一个两个甚至三个包裹一同上路。我对货架望而却步。对于我来说,货架太高了,我的包又往往太重。我举不上去,每次都得请人帮助。我一般选择高个子男人,这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难。矮个子男人我不求,因为那看上去像我故意制造剧情。我自己就个子矮,并深以为不便,因此在需要把我的包裹举到货架上的时候,我首先看我身边人的身高。有一次,我一如既往地选了一位高个子帮我放行李。在这件事上,我没有被拒绝过,也就是所有被提出要求的人,都毫不犹豫地把我的或重或轻的包放到了货架上。在这里要对他们提出表扬。我国男人,虽没进化到主动帮助女人的阶段,但女人要是要求他们干点类似的活,他们还是有求必应的。但有一次出了点意外,不是我被拒绝了,而是当那个高个子男人把我的大包放到高处的货架后,他自嘲地说,你可真敢用人啊!连残疾人也不放过。我看了半天,才发现,该人只有一只胳膊一只手。他刚才是用单臂把我的包举上去的。为此,我和他还有周围的人,大笑了好一会儿。该事件的男主角也很高兴,他被当成正常人——尤其在一个女人眼里成为正常人,并被女人看作很有力气。整个车厢,因此充满了欢快的气氛。就在我们沉浸在快乐中的时候,火车徐徐启动了。
虽然不缺帮我把包举上货架的人,但我还是希望不求人。我总是想办法买到卧铺,买到卧铺中的下铺。我把包裹放到我的睡铺的下面,为和我同行的大包裹找到妥帖的安放之地。火车的高处太热,那么多人喘气,热气上升,盘旋在货架的位置。我包裹里的物品,不喜欢那么热的气流,也不喜欢那么复杂的空气成分。而卧铺的下面,就是大地了,只隔一层铁板。地气就算上不来,但那铁板也是凉的。我的包裹喜欢凉气。夜晚大地的凉气努力透过铁板,安抚着我的包裹。里面的物品也能安安静静地睡觉了。我在床板上睡觉,我的包裹在我的床板下睡觉。我们离得那么近,近到我一伸手,就摸到了我的包裹。我携带着我的包裹,一宿跑了上千公里,而我一点也不感到累。我包裹里的物品,在床铺的下面,没有受到车厢污浊空气的干扰,一千多公里之后,还是水灵灵的、还是香喷喷的……
如果我背着我的包裹徒步去北京,那要走多少天?我会累成什么样?我能走到北京吗?我能携带着我的包裹一同走到北京吗?
其实这里不需要问号。我了解我自己。我走不到,更无法携带沉重的包裹走到北京。但我走不到,不能说别人也走不到。就有人按我不敢设想的方式走。走了不只一次,走了很多次,很多年。走过整个大清王朝。他们也是从吉林乌拉启程,终点也是北京。他们也携带着大大的包裹。我和这些人的起点和终点一样,携带包裹里的内容也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他们徒步,有时坐牛马车,而我坐T字头的特快火车。我十个小时左右到,他们要走一个月。我是把包裹里的东西送给哥哥嫂子,他们是送给敬爱的皇上。
T字头特快经停这些车站:长春、四平、沈阳北、山海关、秦皇岛。在每个车站,火车停三到五分钟。这些大站之间,还有很多小站,都被火车一带而过。而那支步行进京的队伍,要在三十几个驿站停歇。他们不能省略任何一个驿站,因为那是他们休息、重聚力量的加油站。每一个驿站,几乎都是人力的极限点。
和我一同坐上火车的包裹,躺在我铺下的地板上的包裹,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呢?那得看我在什么季节去北京。不同的季节,里面的物品大不相同。
春天,是我挖的野菜——小根蒜、柳蒿芽、荠荠菜、婆婆丁、刺老芽、蕨菜……
夏天,是玻璃(满语音译,意为树叶)叶饽饽、岛子鱼(我已煎熟)、八里香香瓜、杏梅李子……
秋天,是松子、榛子、木耳、人参、猴头、乌拉草(可做靠枕)……
冬天,大蒜、乌拉白小米、大黄米、吉林大米——
春天
每年总得到四月的时候,我们乌拉地间的大地上才会长出绿草。这些绿草的芽,刚刚从解冻的泥土里钻出来。它的高度还不够穿透去年的枯草,因此,它们几乎是被枯草完全覆盖着,你不弯腰是看不见的。它们这样小心翼翼,是有原因的,四月的东北,还会有倒春寒。这样的寒流来了,那些细嫩的小草是会被冻死的。但是,那些藏在去年枯草下的嫩草不会被冻死,去年的枯草罩住了嫩草,像母鸡罩住嫩黄的小鸡。
我小的时候,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时还没有反季蔬菜。你怎么着急,也得等待春天的到来,等待野草和种下的蔬菜慢慢长大。那时候,人还比较老实,没有能力把自然规律像摆积木一样随心所欲。我们整个冬季吃菜窖里储存的白菜、萝卜和土豆。这些菜其实也挺好吃的,可是再好吃也架不住天天吃、顿顿吃,就算是山珍海味这么吃下去也吃烦了。到春天的时候,我们东北人吃白菜、萝卜、土豆,已经吃了几乎六个月了。六个月,足以使我们和土豆、白菜、萝卜结下深仇大恨。
四月,当我们脱下穿了一个冬天的棉衣——这棉衣也几乎穿了六个月了,这时候我们对棉衣也有仇了。野地里的嫩草悄悄长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女孩就都从风里得到了消息。虽然嫩草隐藏在去年的枯草里,但还是被我们发现了。其实我们这些女孩儿是那些嫩草的天敌、是嫩草的寒流——我们要把一部分嫩草吃掉。我们并不吃所有的嫩草,只吃其中的几种。我们给那几种野草都命了名字(不是我们命的名。不知道哪代人命的名),并管它们叫野菜。野菜在我们心里比野草要高级。那几种倒霉的野菜是:柳蒿芽、小根蒜、河芹菜、枪头菜、蛰麻菜、婆婆丁、鹅掌菜、荠荠菜……
清明节的时候,柳蒿芽就长出来了,它们的嫩芽是那种红色的,长大了才变成绿色。当它们长出大叶子,完全变成绿色,这个菜就不能吃了;小根蒜确实很像蒜,叶子像兰花的叶子,细长,它的根茎长在土里,嫩白,水灵灵的,吃起来很辣。它有可能是野蒜,是家蒜的祖先。枪头菜的样子是像枪头,所有的小叶子都朝上,并且包成一个流线型。千万不能让蛰麻菜的叶子碰到你的手背,它会让你的手背像着火了那样疼。我每次都很小心,但是每次都会被这种植物在手背上撒下看不见的火苗。有时看到一大簇蛰麻菜,虽然喜欢但也不会去采它,当然得在别的菜足够多的时候。但这种有神奇的自卫能力的菜做汤是很好吃的。荠荠菜很温和,你怎么做它都不生气,连根拔起它也没有一句怨言。荠荠菜很绿很绿,叶子是锯齿形状的,切碎做饺子馅贼好吃。河芹菜是水生植物,长在小水塘的边上,它的根在水里,叶子在水面上。河芹菜能包餃子也能做酱汤,它的味道太霸道了,一般要用大酱来治服它一下。婆婆丁可以蘸酱吃。婆婆丁苦,但清热解毒,一个冬天吃不上青菜,我们已经上火了,春天吃婆婆丁,就等于吃中药了,药引子就是我们自己做的黄豆酱。剩下的菜都可以放在一起,做汤。我妈一般要在这样清香的菜汤里放一些黄豆,有时放一些土豆。虽然土豆已经吃了一个冬天,但是,当土豆和青菜煮在一起的时候,土豆也变成清香的了,土豆因此也不那么烦人了,有了冬天从来没有过的味道。
这些野菜已经吃了多少年?这些野菜已经多少年吃不到了?就在我开始怀念野菜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本《话说乌拉》,里面有几篇文章是写打牲乌拉给清廷的贡品。在文章里,还有贡品清单。这些贡品都是给皇上和王公大臣吃的、用的,都应该是稀罕物,是咱布衣草民见不到的。可是出乎我的意料,在这个清单上,我看见了我小时候挖的那些野菜的名字:小根蒜、枪头菜、河芹菜、鹅掌菜、寒葱……原来咱皇上也爱吃这些乌拉地间出产的野菜!皇上在皇宫里,也吃了一个冬天的土豆、白菜、萝卜,也吃出仇来了,也在春天迫不及待地要吃绿色的野菜嫩芽。
听说慈禧太后就爱吃寒葱。寒葱是长在东北的野菜。寒葱刚采回来又新鲜又水灵。慈禧爱吃这寒葱,但这新鲜脆嫩的寒葱离慈禧隔着上千公里。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送到慈禧老佛爷的嘴边。青菜一周就会腐烂或干瘪。一个月的路程,他们请出盐和寒葱结伴而行。盐使运送的过程变得从容了。盐像安眠药,一个月,足够盐把野菜哄睡着了。因此,慈禧吃到的寒葱,不是活蹦乱跳的寒葱,而是在盐水的浸泡里,酣睡的寒葱。这样的寒葱原来的味道还都在,只是多了咸味。慈禧并没有因为吃不到水灵的寒葱而震怒而加罪打牲乌拉的负责人,她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慈禧也是讲道理的。她并没有因为有权,就那么任性。当吃到带着咸味的寒葱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赏呢。
史料记载,野菜贡品一律装坛盐渍。而我给哥哥送的野菜,并不用装坛,也不用盐来帮我。我的路程只用十一个小时。野菜们还没打蔫呢,就到地方了。在火车上,我总是悄悄把装野菜的口袋打开,给挤在里面的野菜放风。野菜怕热,我不能把它们放到货架那个比较热的地方去,我要把野菜放到下铺的下面去。那里隔着一层可以导凉的金属层,下面就是泥土。野菜是长在泥土里的,它们有了泥土就会活。现在它们离开了泥土,但把它们放到离泥土很近的地方,它们嗅到泥土的气味,也能继续活着。
慈禧在众多的野菜中为什么单爱吃寒葱?《乌拉皇贡》这本书里,作者姜劼敏先生说了一句话,他说,寒葱主要出产在叶赫境内。原来,叶赫那拉氏哪里是在吃寒葱,她是通过寒葱,遥想东北的老家。吃到了老家的野菜,就是和老家接通了电话。她哪里是在吃寒葱,她是在一口一口地和家乡唠嗑呢。
打牲乌拉春季送贡的日子定在正月。这时山野菜还未长出来,正月这次的大规模送贡的贡品里,没有山野菜。主要是挂冰的冻鱼和獐狍野鹿、熊、貂皮、野猪等。最重要的贡品应是鲟鳇鱼。因鲟鳇鱼只能这个季节送。其他季节都解决不了保鲜这个技术难题。鲟鳇鱼体型大,不能像化(音)鱼那样打捞出水后立刻在岸边架火烤炙,以干鱼的形式储存。鳇鱼只能用冰。打捕后送渔圈圈养,等待冬天。
鲟鳇鱼也是祭品,是顶级祭品。因为鱼很大,大的上千斤一条,小的也百斤。算巨兽数量少,捕捞困难,每年的送贡尾数只有二十条。这些大贡品,打牲乌拉衙门是怎么送去的?
鲟鳇鱼出水不死,蓄养成为可能。捕到后快速送到鳇鱼圈,先养着,等冬天,捞出挂冰,然后送贡。也就是送的鲟鳇鱼是鲜冻鱼。鱼的身上先浇一层冰,然后用芦白席包裹。又是在冬季送贡,鱼到地方,还是冻着的。
满江红 乌喇江看雨
鹤井盘宫,遮不住,
断崖千尺。
偏惹得北风动地,
呼号喷吸。
大野作声牛马走,
荒江倒立鱼龙泣。
看层层,
春树女墙边,
藏旗帜。
蕨粉溢,鰉糟滴;
蛮翠破,狸红湿。
好一场莽雨,
浇开沙砾。
七百黄龙云角矗,
一千鸭绿潮头直。
怕凝眸,
山错剑芒新,
斜阳赤。
这首诗写于康熙到乌拉后,乘船去冷堋(今九台市莽卡乡冷堋村)钓鲟鳇鱼。冷堋位于松花江西岸,距大乌拉八十里。这里水深、江阔,是鲟鳇鱼爱呆的地方。当时是三月末,四月初,吉林地间正是春季,多雨。康熙没钓到鲟鳇鱼,只好返回大乌拉虞。在返回途中又遇大雨。曹寅身为銮仪官,时刻不离皇帝左右,因此,康熙被大雨浇了,曹寅也被大雨浇了。他被雨浇得够呛,不但不恼,还做出一首好诗来。这首好诗还流传下来了。其实,因为这场大雨,康熙也做了一首诗:
江中雨望
烟雨连江势最奇
漫天雾黑影迷离
掀翻波浪三千尺
疑是蛟龙出没时
这诗写得真没有曹雪芹他爷爷的好。但人家玄烨使用汉语,那等于是使用外语。写这样就不错了。再说了,人家本职工作做得好啊!皇上当得几千年谁能出其右?看看康熙在任那些年的中国版图——那个公鸡(海棠叶。清朝版图是个海棠叶。),长得多胖啊!你不服行吗?
此次东巡,康熙除了“观兵”,为来年雅克萨之战做准备,还对打牲乌拉的朝贡事宜做了指示。一些事很细小,但康熙体恤民生之情,让人感叹:
户部题:乌拉打貂鼠不足额,该管官应议罪。
上曰:数年来因常捕,故貂少。但得如数而已。以此议处,是无辜获罪。若不得佳者,朕但少御一裘,何关紧要。且貂价甚贵,而又非必需之物,朕亦不甚需之。
另:鹰鶽窩雏,于三月寻觅,四月内捕取,最妨农事,兼数无益,况所得鹰隼,不谙呼饲,难至京师,徒劳人力,应行停止……
还有许多指示,不录了。这两条就够了,足见康熙之仁心和对家乡人的体恤和怜悯。
夏天
夏天是不送贡的。大规模的送贡是在正月一次,秋后一次。但小规模的送贡应该是不断的。比如椴树叶饽饽。椴树叶饽饽是夏天吃的。是六月六(农历)虫王节吃的满族食品。这种食品的制作方法连我都会:打下新鲜的椴树叶子(圆心形的),洗干净,然后晾干备用。糯米或大黄米泡一两天,然后用石磨磨成水面。用柴草灰把水面里过多的水吸出去。把红小豆煮烂捣碎做馅。这三样东西备好后,就可以制作了:把椴树叶里面擦上一些食用油(可防与粘面粘连),面里包上豆沙馅,放叶子上,叶子对折(左右对折),把面团包里面,使之与树叶相同形状,上蒸锅蒸十几分钟,等凉一凉就可吃了。而且越凉越好吃。在暑天,所有的食物都爱坏,而椴树叶饽饽,可以放好多天不坏。在热天,它可冷食,不硬、不柴。
椴树叶饽饽是满族夏季最重要的时令点心。我从小看我妈做椴树叶饽饽,吃椴树叶饽饽。如果没有椴树叶饽饽,夏天就变得淡而无味。但自从我进城之后,就很少吃到纯正的椴树叶饽饽了。就算回到老家,也吃不到。主要是原料,那种石磨已经没有了。代之的是干面粉。这就差老多了。水面细腻滑爽,而面粉颗粒粗,怎么都不对劲了。还有就是我妈她老人家不在了。去年我到了满族海西四部之一的乌拉部所在地乌拉街镇,意外的在街里的露天市场上,看见了两份用大蒸鍋,在那现场包椴树叶饽饽,现场蒸。我买了几个一吃,立刻,童年场景忽然来到眼前。这里的椴树叶饽饽,竟然保持着当年我妈做的味道。面是水面,我一口就能吃出来。我妈就是乌拉街人。
我终于又找到了一种童年食品,我每天都去买两个。因为,这种食品是有节令的,椴树叶老了就不能做了。从树叶长到够大,到树叶老了之前,应该能有两个月时间吧。我每天吃着椴树叶饽饽,想起我哥我嫂子,远在北京,他们吃不到。如果他们不爱吃也就罢了,偏偏他们爱吃。如果这时我需要出差,到北京或路过北京,我哥我嫂子就有口福了。我会给他们带二十个三十个椴树叶饽饽。装一大包。这东西很沉,多了拿不动。我还是需要下铺。椴树叶饽饽也喜欢被放在凉快一些的地方。
我嫂子说,给她带些叶子就行了。因为面和豆馅都能买到。粮店里是有卖糯米面的,但那是干面,没有水面口感好。而且那糯米,也不知是哪产的。我嫂子是退而求其次,能把面、豆馅、叶子凑齐就行了。面是哪产的不计较了,水面干面更不敢计较,小豆产在哪里也没关系,而树叶一定要老家的,因为别地可能有椴树,但没人想到用这个叶子制作食品,因此没有人供货。我嫂子想不管哪里的东西,只要能包成椴树叶饽饽就行了。她想自己制作。有时吃到家乡的食品还不行,吃是记忆,制作也是记忆。我哥只有吃的记忆。但我嫂子,她有制作的记忆。她只有自己动手包制,家乡的记忆才能像电影一样在她的眼前出现。
我在夏季去北京,主要是给我哥嫂送椴树叶饽饽,而打牲乌拉衙门,夏季是重要贡品——东珠的采捕季节。打牲乌拉的贡品有上百种,但有三种是最重要的——东珠、鲟鳇鱼、人参。东珠是这三种贡品之首。
东珠产于松花江、牡丹江、嫩江、黑龙江流域。产于湖南广东的叫湖珠,产于广西的叫南珠。东珠也称北珠、胡珠。珍珠产于江河中的蚌蛤之中。清代纳贡的东珠共分四等:一等大正珠,二等小正珠,三等微光珠,四等无光珠。东珠色彩斑斓,有白色、粉红色、天蓝色、浅绿色等。东珠大者如枣,小的像黄豆那么大。由于东北的自然环境因素,所产珍珠优于其他地区的珍珠。
东珠是清朝恭品第一大宗。东珠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东珠是高级观赏品和宝物。用它做皇室后宫女性及器物的装饰品,并用来赏赐功臣和外藩;第二,它是权贵和身份的象征。清朝规定,皇冠用东珠三十七颗,皇后凤冠用东珠九十八颗。一品朝冠用一颗,二品以下不准用东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