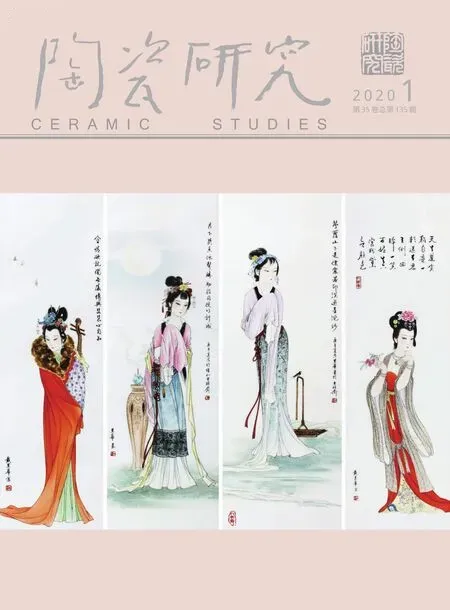时势造艺
——当代枫溪戏曲瓷塑艺术的发展历程
陈沛捷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揭阳市,522000)
0 引言
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将戏曲的概念定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1]”。戏曲瓷塑,则是以瓷塑的形式来再现戏曲故事的一种陶瓷工艺,运用雕、塑、刻、彩等技法的交互作用来塑造人物形象,通过作品的肢体语言、神态特征与装饰手法来展现出戏曲艺术的内容与情感。
枫溪戏曲瓷塑是潮州枫溪陶瓷主要的表现题材,与其他产瓷区相比,枫溪戏曲题材作品数量更多,内容更为广泛。建国初期,在“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指导下,枫溪逐渐形成以陶瓷研究所与美术瓷厂为中心的瓷塑创作群体[2],影响力逐渐扩大。在1959年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由林鸿禧、郑才守共同创作的《十五贯》瓷塑作品(图1-2),突破了以往戏曲人物形象模式化的框格[3],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赏,并荣获全国优秀作品一等奖。这极大地鼓励了枫溪瓷塑的从业人员,也为枫溪瓷塑的创作找准了发展的方向。随后,枫溪瓷塑界涌现出了陈钟鸣、吴为胜、吴德立、佘纲旭、吴承华、吴维潮、丁培强、卢茂昭、吴映钊等一批优秀的工艺美术师,极大地丰富了枫溪美术瓷塑的创作群体,诞生出一批精彩绝伦、雅俗共赏的戏曲瓷塑作品。

图1 起步发展阶段戏曲瓷塑的代表作品
枫溪戏曲瓷塑属于小型雕塑艺术,这门“小艺术”是陶瓷艺术研究中的一项 “冷门”。尽管拥有诸多精美作品传世,但是枫溪瓷塑的研究基础却十分薄弱,受文献与实物资料的双重制约,学术界对枫溪瓷塑的研究大多是作简单的形态归纳及艺术评论,学术影响与研究深度方面仍有待提升。今天我们研究过去几十年的艺术作品,我们不能以当下的审美观念进行价值判断,而应该把艺术作品置身于当时的社会背景进行多维度的探讨。因此,成熟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情境学研究方法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种方法是把作品的艺术风格、母题内容等回归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行讨论[4],这种理论来自于贡布里希与波普尔,他们认为艺术风格的改变,根源不仅仅艺术家个体精神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整个文化氛围的转变。比如社会的期待、市场的喜好、赞助人的趣味等,都会影响艺术作品的形态,甚至决定了作品的风格。这种研究视角,是一种较为宏观的视野,对我们的工艺美术研究带来许多新的思考。
建国以来,枫溪瓷塑行业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分别是1949年至1964年的起步发展阶段,1965年至1973年的逐步发展阶段, 1974年至1990年的快速发展阶段,以及1991年至今的创新发展阶段。枫溪戏曲瓷塑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从建国初期的孕育,到80年代中期风格趋于成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1 起步发展阶段(1949年-1964年)
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曾号召人民要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传统戏曲、传统技艺等文化一度得到振兴。在振兴文化、恢复生产的号召下,五十年代初期,枫溪地区成立了手工交流组、瓷器联销组、生产自救小组和生产自救厂等行业自救组织,并从土改的胜利果实中划拨4亿元扶持陶瓷产业[5]。此外,政府还委派了雕塑家高永坚、庄稼到枫溪指导艺术瓷的复兴工作。在这个阶段,陶瓷产业纳入计划经济管理,枫溪的瓷塑业也随着兴起。
在探索起步时期,枫溪瓷业整体技术水平仍处在一个学习模仿的阶段,早期枫溪瓷塑业在吴金福、林鸿禧等人的带动下,开始突破传统以佛像观音为主的生产格局,增多了很多现实主义题材的表现内容。其中,戏曲题材因思想主题富有强烈的“平民性”,深受百姓喜爱,也开始成为工艺师们热衷于表现的主题。

图2 快速发展阶段戏曲瓷塑的代表作品
吴金福是大吴泥塑的重要传承人,受父辈影响,抗战胜利后吴金福就在枫溪地区从事人物瓷塑的创作工作。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将“贴塑”技艺应用到了戏曲瓷塑的创作中。如作品《百里奚会妻》(图3-1),塑造了青衣和老生夫妻相见的场景。青衣挽腰裙,抚琵琶,秀美娇柔;老生端坐执册,神情惊愕。作者娴熟地运用了贴塑技法,使得整套作品看起来体态轻巧、戏剧感强。而作品《薛丁山与樊梨花》(图1-1),则表现了薛丁山与樊梨花深情对望的一幕。薛丁山屈膝跪地,伸出左手诉衷肠;樊梨花回旋顾盼,面露微笑。整套作品动静结合,高低有致,刚柔相济,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吴金福的作品与大吴泥塑一脉相承,细腻的贴塑技法虽提升了戏曲瓷塑作品的精致度,但是吴金福在作品形态上处处模仿大吴泥塑,人物头身比例多为四个半头,头大身短,面部神情欠缺生动,作品仍带有着强烈的民国遗风。
同时期,部分枫溪戏曲瓷塑作品开始遵循了科学的人体解剖规律,采用了七个头或七个半头的标准体型比例。这种手法使人物造型比例更加和谐,作品也更具现实主义色彩。鲜为人知的是,传授这种写实性技艺的先驱是一位江西师傅曹明銮,他将景德镇的瓷塑技艺带到了枫溪地区,并在当地大获成功。而林鸿禧则将这门技艺发扬光大,衍生到戏曲题材的表现上。建国初期,整个文艺界强调作品必须反映阶级性与人民性[6],一些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受到了艺术家们的强烈关注。林鸿禧本人就是一名潮剧爱好者,表现戏曲文化成为了林鸿禧早年艺术上的成功尝试。50年代中期,昆剧《十五贯》蜚声全国,林鸿禧在《人民画报》得知该剧在瑞士获奖的消息,受剧情启发,他与郑才守合作创作了《十五贯》中况钟探鼠的场景。这组作品细节丰富,扎实严谨,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生动地表达出剧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况钟胸有成竹,平静安详地“观枚测字”;娄阿鼠神情紧张,坐立不安。人物刻划一静一动,举手投足都是戏。这件作品突破了以往戏剧作品“脸谱化”“模式化”的风格形式,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从1957年到1960年期间,林鸿禧运用写实手法陆续创作了《秦香莲》《王昭君》《秋香》《望江亭》等戏曲题材作品。这批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物表情生动传神,并且善于运用人物的服饰来表现戏曲人物的性格,如《秋香》这组瓷塑,秋香衣着干练利落,而华家二公子却衣冠不整,美与丑截然分明,在当时意识形态强调阶级性的情况下,这种泾渭分明的“现实主义”,反映林鸿禧早期艺术上的追求。

图3 当代戏曲瓷塑女性形象的发展衍变
1960年初,伴随着广东轻工业厅枫溪陶瓷研究所的成立,瓷区之间的技术调配日益增多,美术团体愈发壮大,“学院派”青年艺术家到枫溪陶瓷界工作,工艺师们开始接触到愈来愈多的艺术形式。此时的林鸿禧并没有满足于自我,而是更加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为了体验生活,反映生活,林鸿禧经常下乡,追随潮剧团到各地演出[7],观察戏曲艺术的舞台表现。此时的林鸿禧在熟练掌握人物造型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形似到追求神似的过程,探索出一批与前期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张飞审瓜》《活抓孙富》《芦林会》《扫窗会》《挡马》《铁弓缘》《刺梁冀》等作品,就是采用轻松娴熟的技法,捏塑一批戏曲瓷塑玩具。这批瓷塑造型虽小,但肢体语言极为生动,人物的头身比例均夸张到1:2的样式,形象卡通化,带来了一股清新的亲民趣味之风。这批作品风格活泼生动,轻松自由,形神兼备,可见当时随着文艺创作环境的改善,林鸿禧的艺术感受是乐观的、愉悦的。
在建国初期,枫溪戏曲瓷塑创作在林鸿禧等人的带动下,造型写实,内容丰富,折射出人民的喜好,有着强烈的平民美学特征。如林鸿禧的《桃花过渡》《杨子良讨亲》作品等都是传统题材的再创造,作品给予观者强烈的亲切感。
2 逐步发展阶段(1965年-1973年)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的政治题材作品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时代呼声下,“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受到追捧,艺术家们被要求“必须按比现实更高大更完美的原则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8]”。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表现传统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开始大量减少,而表现领袖形象、工人阶级及农村生活的艺术作品则逐渐增加。戏曲瓷塑因多涉“才子佳人”“帝皇将相”的故事被限制生产,导致古装戏曲瓷塑的创作直接进入了低迷期。然而,有一类新兴的戏曲瓷塑作品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受到了社会的推崇——样板戏瓷塑。
一场始于1964年的京剧改革树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等二十几个经典舞台戏剧作品,并确立它们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最佳代表。轰轰烈烈的样板戏运动可谓“耗十年之时,倾一国之力[9]。”这些样板戏充分地体现了工农兵的核心地位。在政治的主导下,样板戏作品里任何一种姿态语言、形体特征、舞台灯光及演员情绪等,都经过了精心筛选,周密策划。所有一连串的艺术语言成为当时新的艺术标准。这套艺术标准在当时国家文艺工作中迅速铺开,枫溪瓷区也接受了样板戏瓷塑作品的制作任务。样板戏瓷塑作品由于是一种政治行为,它的制作十分严谨,需经过多次审核、修改,作品中人物的神情、姿态、动作都必须符合舞台剧所展现的人物特征,属于一种标准化的制作。枫溪瓷区根据指示也创作出了《吴清华》《杨子荣》《红头绳》《山神庙》等一批优秀戏曲瓷塑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遵循了程式化的要求,如枫溪地区塑造的《杨子荣》作品与景德镇地区塑造的《杨子荣》作品,从人物的体态、动作、服饰基本上一致,都清一色符合英雄化的特征,主要区别的就是泥料差异和施釉工艺。在这个阶段,枫溪陶瓷工业稳步发展,陶瓷研究所的工人们对釉上、釉下工艺及色釉、高温色土进行了充分的试验研究,一些新材料新工艺也运用到了作品的创作中,如《吴清华》瓷塑作品(图3-2),表现了娘子军吴清华送荔枝的场景,吴清华脚尖挺立,虽有芭蕾之姿,但是体态干练,俨然一副“高大全”的女性形象[10]。作品用细白泥做底胎,并运用陶瓷研究所新研制的高温色土来表现衣饰,既简练大方又富有装饰性。可以说,这个阶段枫溪瓷塑领域主要的任务就是“塑造英雄”,而伴随着材料工艺的进步,新成果的应用也使“英雄”作品也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3 快速发展阶段(1974年—1990年)
改革开放前夕,当时破四旧风波已经过去,思想解放的春风即将吹响,枫溪地区已经慢慢开始恢复传统题材的创作。此时,林鸿禧、陈钟鸣等工艺师们正当壮年,他们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去思考如何创作出与时代相适宜的作品。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化进程的推动,创作者比以往更加关注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枫溪瓷塑的创作面貌渐渐出现了从众从俗的倾向。但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艺由于政治依附性降低,工艺师们开始追求形式上的流变,因此,作品仍有很高的艺术性,其思想主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种是表达经历了苦难的磨砺,迎来新时代的喜悦;另外一类作品则是研究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如何让作品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时代面貌。可以说,这两类主题既反映出了个人的呼声,也反映出了时代的呼声。
1974年,林鸿禧创作了《牛郎织女》,表现了夫妻离散,苦尽甘来的团圆画面。在作品中,牛郎领着一儿一女,他与织女深情对望却又彼此克制。作者把这件作品的感情焦点集中在孩子身上,小女孩张开双臂哭喊着欲投入母亲的怀抱,天真无邪表达了最真实的感情力量。这件作品回归了妇女和儿童本该有的家庭性的特征,它有别于以往“铁姑娘”的形象塑造,恢复了传统仕女的美学形象。
从80年代开始,陈钟鸣也佳作频出,开始引领瓷塑美学的发展。他认为“装饰之美”并非“精细”与“满工”的概念,而是有的放矢,适当去掉一些多余的装饰,让艺术形态尽量简洁明快,这样更能抓住重点,塑造典型。他强调人物瓷塑贵在“塑”,少施“彩”。由于枫溪瓷塑人物的肌肤均不予施釉[11],因此头、面、手、脚可表现得精细清晰,陈钟鸣利用这一特点设计了很多唯美化的仕女瓷塑。这些仕女脸部做精细刻画,服饰则简练概括。如《黛玉葬花》(图3-3),人物线条简洁明快,陈钟鸣运用方直的衣服来表现林黛玉的“刚”,用低头俯视之姿与轻抚胸口之态来表现林黛玉的“柔”,刚柔相济,生动反映了林黛玉的性格,使得作品极富艺术感染力。而作品《醉眠芍药姻》(图2-1),则表现了美人醉卧的题材。陈钟鸣重点刻画出史湘云不羁的睡态与柔美的身姿,这样既表现出史湘云醉酒后的“憨”,又兼顾了花丛丽人之“美”,彰显出这位“睡美人”奔放爽朗的格调。
与陈钟鸣的简洁明快的风格不同,郑才守创作的戏曲瓷塑作品颇有浓厚的装饰味。他善于吸收民间艺术,热衷于表现色彩缤纷、斑斓夺目的戏服。如1975年创作的《穆桂英》(图2-2),作品表现了穆桂英在天门阵中与马荣刀光相见的场景,精美的刀马行当装饰使得穆桂英的形象更加饱满与立体,展现出穆桂英以女代男,挂帅出征的英姿。
佘纲旭则擅长表现戏曲瓷塑中丰富的感情色彩,如在《荔镜记》(又名《陈三五娘》)中,佘纲旭巧妙地表现了五娘梳妆意懒的场景。众所周知,在闺怨题材作品中,久不梳妆,对镜自怜容易产生出丰富的内心变化。作者巧妙得塑得两尊瓷塑,奴婢益春捧镜,五娘对着镜子梳理头饰,仙姿佚貌,楚楚动人。作者让五娘以转身低头之姿对应益春弯腰仰望之状,三角形的构图使得这组瓷塑形成良好的呼应关系,堪称枫溪瓷塑的精品。
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枫溪戏曲瓷塑中的仕女人物开始蓬勃发展,如卢茂昭的《昭君出塞》、吴德立的《蔡文姬》、吴为胜的《女娲》、吴承华的《赏春》,都是根据古代的戏剧人物故事来塑造仕女形象,这些仕女形象大多有着祥和恬静的面容,线条流畅,形态优美,彩工俱佳,奠定了枫溪瓷塑以柔为美、细腻含蓄的艺术形象(图3)。
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这个时期的作品,我们发现由于重塑传统文化的要求与渴望,使枫溪瓷塑业迎来的发展的高峰期。戏曲瓷塑不仅在创作上题材上不断增加,而且整体的艺术形态也有着唯美化的倾向。人物瓷塑不仅重视大块面的整体塑造,也讲究衣物袖口、衣带等边饰装饰的精巧性,并且釉面施色更爱黄色、绿色、桃红、金色等鲜艳色彩。在这个阶段,追求形式美与装饰美,是枫溪戏曲瓷塑的主要特征。
4 创新发展阶段(1991年—至今)
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我国的物质文化实现了快速发展,百姓的观看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各种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慢慢取代了剧场、戏班等传统演出模式。百姓与传统戏曲艺术的距离越拉越大。随着市场化的驱动,艺术家们不再热衷于表现戏剧类的题材,枫溪的瓷塑业也迎来了艰难的瓶颈期。伴随着国营瓷厂的改制,老艺人们的相继老去,戏曲瓷塑已是风光不再。在新时代,枫溪瓷塑作为一门非遗传承项目,必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艰难地探索着自己的传承创新之路。
当代戏曲瓷塑如何适时而变?如何探寻新的路径?[12]近几年兴起的“瓷塑二代”或许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吴映钊(吴德立之子)、陈震(陈钟鸣之子)、陈响(陈钟鸣之子)、郑奕林(郑才守之子)等人均继承父业,并在当代瓷塑创作领域有着不俗的表现。相比起老一辈,这批“瓷塑二代”大多是专业艺术院校的“科班”出身,他们有着更加开拓的艺术视野,更加善于博众所长,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化。他们深知传统戏曲瓷塑也需要转化与发展,因此,他们的瓷塑作品比以往更加强调个性化、差异化的特点。如吴映钊创作的《贵妃醉酒》(图3-4),该作品造型硕大,高度达50厘米,一改以往戏曲瓷塑作品规模和格局都显小的问题,并且在造型上也改变了枫溪仕女瓷塑身材纤瘦的特点,表现了杨玉环圆润娇美之姿。杨玉环衔杯醉步,青纱滑落,既表现出贵妃的天生丽质,又展现了她的放浪不羁,可以说出色地阐释出戏曲《贵妃醉酒》的精神内涵。而陈震也在当代瓷塑的创新上做了很多新探索,在作品《醉八仙》中,他一改枫溪瓷塑固有细腻精致的程式,运用写意的捏塑手法刻画出神态各异的八仙,手法轻松随意,自然畅快,并留下捏塑的自然痕迹,夸张地表现出了八仙憨态淋漓的面貌,与以往追求工整唯美的枫溪瓷塑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5 结论
由此观之,不同的时代背景造就了枫溪戏曲瓷塑不同的艺术风格。艺术作品风格的形成,不仅仅是艺术家本人的主观创造,环境与时代的要求也对艺术风格的走向取着决定性的作用。伴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枫溪戏曲瓷塑走过了平民化、英雄化、唯美化及多元化的发展历程,如今,枫溪戏曲瓷塑正慢慢淡出群众的视野。它俨然已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物”,见证了新中国70年来审美风格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