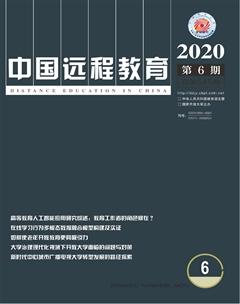MOOC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积极老龄化的大数据发现
詹泽慧 邵芳芳 范逸洲 何国庆 姚佳静 汪琼



【摘 要】为探讨MOOC在教师专业化发展和终身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各年龄段教师的参与现状,本研究建构了评估MOOC学习者参与度的分析框架,从中国大学MOOC平台教师专业发展类课程中抽取了教学方法类、研究方法类、工具技术类课程各1~3门,对多期课程共49,070名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进行分析,从资源利用、作业互评、论坛互动三个维度考察各年龄段教师在MOOC中的课程参与度与行为模式及对其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发现:教师培训MOOC中个体参与度最高的是处于平静保守期和职业消退期的资深年长教师。职业消退期教师的各项参与度和成绩均不逊于其他阶段教师,可见其仍然有着旺盛的自主发展与学习动力,且对工具技术类课程需求较强。在职前期、职初期和稳定期阶段,论坛互动环节对成绩有显著作用,但对于年长教师来说作用降低。结果表明:各年龄段教师参与MOOC培训的需求与行为模式存在差别,MOOC个体参与度模型勾勒出非常显著的积极老龄化需求;MOOC培训有助于弥补传统培训中资源分配不均、年长教师缺乏培训机会的问题;利用MOOC的“大规模”优势效应,可在MOOC中形成教师互助共同体,促进跨龄段教师的远程教研和协作,为推动“积极老龄化”和实现全阶段“终身学习”形成合理的在职培训机制。
【关键词】 慕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积极老龄化;大数据;学习参与度;学习资源;同伴互评;在线交互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58x(2020)6-0040-12
一、引言
MOOC免费、在线、开放的属性为教师专业化发展开辟了有别于传统培训的便捷路径,为多元化拓展提供了更多可能。一方面,与集中式和精英化的“国培计划”相比,MOOC教师培训有分布式、扁平化、开放便捷的特点,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类教师获取优质培训资源的需求,更有助于受训教师点对点便利获得权威课程团队的直接指引和辅导,避免了培训效果层层衰减和培训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另一方面,与贴近各校实际的小范围校本培训相比,MOOC培训通常会聚全国各地、各年龄段、各学科、各学段的众多教师,更容易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化学习效应(Zhan, 2015; 詹泽慧, 等, 2016, 2019)。
那么,作为一种新式的教师培训,MOOC能否吸引处于职业发展各个阶段的教师充分参与?能否起到积极的培训效果?处于不同年龄段的教师在MOOC学习中的行为模式有何差异?对以上问题的深入探讨,都离不开对MOOC学习者参与度的测量与分析。其中,参与度可分为群体参与度与个体参与度。学习者的群体参与度与MOOC的受益面紧密相关,如果一门MOOC的学习者群体参与度较高,通常认为这门课程的社会公益效应较大。学习者的个体参与度则与当前正处在热议中的MOOC辍学率问题密切相关,人们普遍认为学习者参与度与辍学率呈反向关系,参与度的提升有助于降低辍学率(Ramesh, Goldwasser, & Huang,2013)。
此外,年龄作为教师专业化发展中重要的时间属性,对学习者年龄段的分析有助于从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来理解MOOC学习者的需求与行为模式。对年龄参数的关注还源自对国内老龄化社会形成的预期:在生育观念转换、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计划生育政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日益加重(谢秋山, 岳婷, 2019)。预计到2036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增至4.23亿,老龄化水平达到 29.1%,成为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总报告起草组, 李志宏, 2015)。同时,5G和智能化技术时代的到来,带动了终身教育的加速发展,也引发了社会对教师群体中年长者的担忧:年长教师是否能快速适应这一技术丰富的时代?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持续他们的专业化发展?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将立足于学习者年龄这一人口统计学变量,聚集MOOC学习者参与度问题,对教师职业生涯发展阶段进行调研和划分,以中国大学MOOC平台的后台数据指标为蓝本,建立MOOC学习者参与度评价模型,在教师专业发展类课程中依托大数据分析,探索不同年龄段学习者的参与情况、行为模式和学习需求。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涉及三个具体的研究问题:
其一,在教师专业发展类课程中现有学习者的年龄分布情况如何?
其二,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的MOOC学习者参与度如何?
其三,学习者的参与度与学习成绩的关系如何?
(二)课程筛选
考虑到不同的课程类型可能会对不同年龄段学习者的参与行为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将平台上现有的教师专业发展类MOOC课程分为三种类型:①教学方法类课程:“教你如何做MOOC”“智慧课堂教学”;②研究方法类课程:“教师如何做研究”;③工具技术类课程:“微课设计与制作”“教学动画制作与实战”“交互式电子白板的教育应用”。这三种类型分别代表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三个方向,即教学型、科研型、技术型。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为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参与教师专业发展类课程的49,070位学习者。在教学方法、研究方法、工具技术三种类型课程的后台数据集中,剔除年龄信息缺失的学习者和课程团队ID后,总样本量为49,070人。其中,男性18,041人,女性31,029人。若按年龄段统计,18~22岁2,274人,23~25岁4,313人,26~28岁4,612人,29~35岁1,1315人,36~45岁15,471人,46~55岁9,871人,55岁以上1,214人。各类课程的学习者年龄段人数分布如表1所示。
(四)教师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
国外教师职业生涯周期研究中有几种较具代表性的划分方法:①保罗·伯顿等(Newman, Burden, & Applegate, 1980)提出“教师发展阶段论”,指出教师入职后第1年为求生存阶段,第2~4年为调整阶段,第5年以后为成熟阶段;②拉尔夫·费斯勒等(Fessler & Christensen, 1992)提出“教师职业生涯发展周期模型”,将教师职业生涯划分为职前期、职初期、能力建构期、热情成长期、职业挫折期、职业稳定期、职业消退期和离岗期八个阶段;③司德菲(Steffy, 1990)提出“教师生涯发展模式”,将教师职业生涯划分为预备生涯阶段、专家生涯阶段、退缩生涯阶段、更新生涯阶段、退出生涯阶段;④休伯曼(Huberman, 1989)提出“教师职业生命周期主题模式”,将教师职业生涯周期阶段与年龄阶段做出对应,以22岁作为教师职业生涯起点,分为入职期(工作后的第1~3年,年龄段为22~25岁)、稳定期(工作后的第4~6年,年龄段为26~28岁)、实验和重估期(工作后的第7~25年,年龄段为29~47岁)、平静和保守期(工作后的第26~33年,年龄段为48~55岁)、退休期(工作后的第34~40年,年龄段为56岁以上)。
在国内,贾荣固(2002)对教师职业生涯做了粗略划分:职前准备期(大学四年的职业学习及见习、岗位培训等)、上岗适应期(1~2年时间)、快速成长期(从初步适应后到30岁高峰期)、高原发展期(30~40岁)、平稳发展期(40~50岁)、缓慢退缩期(50~60岁)和平静退休期(60岁以上)。国内另有范逸洲(2018)结合教师职业生涯发展规律提出了MOOC学习者年龄阶段的划分方式:22岁以前为职前期,23~25岁为入职期,26~28岁为稳定期,29~47岁为实验和重估期,48岁以后为平静和保守期。
参考以上学者对教师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以及年龄阶段的划分方式,结合MOOC教师培训中学习者的具体情况以及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现有数据的特点,本研究将教师职业生涯划分为职前期(18~22岁)、职初期(22~25岁)、稳定期(26~28岁)、能力建构期(29~35岁)、实验重估期(36~45岁)、平静保守期(46~55岁)和职业消退期(55岁以上)七个阶段(见图1)。
(五)参与度分析模型
参与度主要反映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程度(Astin, 1984)、注意程度(Fredricks, Blumenfeld, & Paris, 2004)、兴趣和努力(Meece & Blumenfeld, 1988)、动机(Skinner & Belmont, 1993)与投入时间密切相关,提高学习者参与度有助于降低辍学率和提高学习绩效(潘丽佳, 2015)。里夫(Reeve, 2012)提出了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参与度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分别是行为参与度、情感参与度、认知参与度和代理参与度。
在传统的课程中,研究者通常通过观测学生行为(如出勤率、课堂讨论等因素)来评估学习者参与度。参与质量观察体系(Engagement Quality Observation System, E-Qual)是较典型的测量方式之一(McWilliam, 1998; Aguiar, 2013)。在信息化环境下,更多的技术手段可用于测量学习者参与度。研究者可以通过线上行为模式反映学习者参与度的水平和类型。巴尔杰(Bulger, 2008)使用与课程相关网络行为的时间作为衡量参与度的指标,用计算机辅助测量(CBAs)记录课程中学生使用计算机的行为,编码为学习状态和非学习状态。拉梅什(Ramesh et al., 2013)则从四类线上行为特征来刻画MOOC环境下的学习者参与度:①线上论坛讨论;②浏览他人发布的内容;③学习课程材料;④完成课程相关的评估。通过行为、语言、时间和结构四个类别的指标将学习者参与度划分为积极参与、被动参与和脱离三个层次。
在参考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中国大学MOOC平台的后台数据,建立了MOOC学习者参与度分析模型(MOOC Learner Engagement Analyzing model, MOOC-LEAM)。我们匹配了被试样本在平台上的行为数据与各项成绩数据,将MOOC学习者参与度划分为资源利用、作业互评、论坛互动三个维度(如图2所示)。每个维度都有频次、时长和成绩三类数据,前二者表征学习行为的数量,后者表征学习行为的质量。为避免日志文件(log data)中無效数据的计入,我们将间隔1秒以下的多次重复点击频次作为无效点击并排除,将间隔1小时以上无操作的时长作为学习者离开的无效时长并排除。此外,为了分析MOOC学习者的行为模式,我们将参与度模型中所能捕捉到的学习者行为分为三类。
三、研究发现
(一)学习者年龄分布
图3、图4、图5展示了三类课程中MOOC学习者的年龄分布情况。在三类课程中,学习者参与人数的最高峰无一例外出现在37岁左右,即教师职业生涯的实验重估期(36~45岁)。这一阶段的教师正处于一种自我反思的状态中,且经过前面阶段的积累,已经具备较丰富的工作经验,MOOC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进阶学习机会。
23岁左右,即处于职初期(23~25岁)的学习者参与人数形成了总样本量的次高峰,这一峰值在三类课程中也是高度一致的。这一时期的学习者大多刚迈入教师岗位,满怀憧憬和期待,却又有很多的迷茫和困惑。他们可从MOOC上获取很好的教学资源,也可以参考资深教师的教学方法。其中,教学方法类课程的职初期峰值最为明显,可见职初期学习者亟需教学方面的素材和经验。
与我们预期差距较远的是职前期(18~22岁)学习者的参与人数。职前期学习者大多处于师范生本科阶段,有着较为纯粹的学习时间,且随着目前混合学习模式的推广,不少师范类高校教师在教学中都会鼓励学习者修学同类或相似的MOOC,以作为面授教学的补充,甚至以MOOC的课程证书来替代部分专业学分,因此我们预期职前期学习者的参与人数会较多。然而这一设想与实际并不相符。从三类课程的参与人数上看,处于职前期阶段的学习者人数均偏少,但呈逐年递增状态。到了本科高年级阶段,随着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和碎片化学习需求的增加,职前期学习者人数也随之增加。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参与人数方面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处于职业生涯初期和中期的MOOC学习者中,女性人数远多于男性;进入平静保守期(46~55岁)后,男女人数差异递减;进入职业消退期(55岁以上)后,男性人数超过女性,成为高龄阶段MOOC学习的主要群体。另外,在资深年长教师的群体中,对工具技术类课程的需求显著强于教学方法类课程和研究方法类课程。
(二)各年龄段学习者参与情况
1. 群体参与度
根据MOOC-LEAM模型对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加权计算得出三类课程中各年龄段MOOC学习者的总参与度,并将其区分为群体参与度与个体参与度两种。群体参与度是某一年龄段中所有学习者的参与度总和,可反映课程的受益面,即若一类课程的学习者群体参与度高,可以说明该类课程产生的社会公益效应较大。如图6、图7、图8所示,在MOOC这种新型的教师培训形式中群体参与度最高的并非我们预想中的数字新生代—职前期的年轻教师群体,而是实验重估期(36~45岁)这一阶段的学习者。其中,37岁左右的教师对于教学与研究方面课程的需求是最强烈的;对于工具技术类课程,32岁左右教师的需求更强烈。
2. 个体参与度
个体参与度是某一年龄段中学习者的人均参与度,可表征个体学习者的参与积极性。从图9、图10、图11可见,个体参与度最高的是工具技术类课程,研究方法类课程次之,教学方法类课程最低。
在工具技术类和研究方法类课程中,处于实验重估期后的平静保守期(46~55岁)和职业消退期(56岁以后)的学习者个体参与度随年龄递增,但递增方式有差异。递增趋势最明显的是研究方法类课程,呈正指数形式递增,工具技术类课程呈负指数形式递增,趋势较缓,但二者峰值均出现在最末的职业消退期。教学方法类课程的学习者个体参与度则是在实验重估期上升到峰值后缓慢下降,峰值较其他两类课程有所前移。总体而言,在个体参与的层面上,各类课程均有沉积效应,年长参与者的个体参与度较高。将个体参与度与参与人数相比照,发现在实验重估期的参与人数高峰过后,一部分学习者流失了,而另一部分适应MOOC的学习者留下来了,并且更投入地参与到MOOC学习中。
3. 资源利用维度
图12、图13、图14为各年龄段学习者浏览课程内容的人均频次情况,其中资源浏览频次和时长的归一指标用以表征学习者对资源的使用量(参与量),章节测试平均分则表征学习者对资源使用的效果(参与质量)。在资源利用维度,职前期(18~22岁)学习者的资源使用量在整个职业生涯前期是较高的,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其一,职前期的学习者大多数是师范院校的学习者,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有更强的动机来学习和使用MOOC上的资源。其二,学校的课堂时间有限,近年来随着MOOC和混合学习模式的深入人心,不少师范院校或高职院校的教师会将MOOC资源推荐给在读学习者,让他们课后自行学习,然后在课堂上汇报或讨论,所以这部分在校学习者对于MOOC资源的使用频率很高,时长也较长。但这些学习者大多为初学者,远程学习经验不足,因此从章节测试成绩来看,参与质量和学习成绩在三类课程中都处于最低点,即职前期学习者的资源使用量与资源使用效果之间均存在一个较显著的落差。
职初期(23~25岁)学习者在资源使用量上达到一个低谷,很可能是因为职初期的学习者正在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且准备新课等工作占用了非常多的时间,所以他们更追求MOOC学习的效率,而不会反复地看资源。整体而言,入职节点过后各年龄段学习者的资源使用量整体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从中也可以看出,MOOC资源的使用情况与职业生涯阶段所能支配的学习时间成正比:在校学习者具有最多的自主学习时间,而入职初期的新教师们是最忙碌的群体。
此外,三类课程中的浏览频次与人数基线相比,教学方法类课程的学习者人均浏览总频次最低,研究方法类课程居中,工具技术类课程的人均浏览频次最高。三类课程的资源利用人均频次均随年龄增长而递增。在教学方法与研究方法类课程中,学习者偏好视频资源,视频资源使用频次和浏览时长远高于pdf文档资源、测试、论坛等其他资源;在工具技术类课程中,学习者对pdf类资源的使用频次与视频资源相当,特别是在职初期和稳定期前期(22~26岁)的学习者pdf资源的使用频次高于视频资源。可见,对于初入职的教师来说,工作忙碌,所以pdf这种文字性的资源更有助于他们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從平静保守期晚期起,视频资源的使用频次和浏览时长逐渐上升。也许随着学习者年龄增大,自主学习的时间变多,且部分年长学习者视力不如从前,视频资源的动态呈现更有助于他们的学习。
4. 作业互评维度
作业互评参与量由学习者主动评价他人作业的频次和被他人评价作业的频次归一指标来表征。由图15、图16、图17可见,作业互评参与量与作业得分之间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这可能是由作业互评的计分机制决定的——交作业不参加互评的只能得一半分数)。三类课程的作业互评参与度峰值出现阶段不同:教学方法类课程中作业参与度峰值出现在实验重估期,研究方法类课程峰值出现在职业消退期,工具技术类课程峰值出现在平静保守期。由此可大致推测教师在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对三类课程的需求顺序:需要先提升教学能力,再熟悉相应的工具技术,最后进入研究阶段。教学、技术和研究三方面的学习需求是终身化的。另外,在三类课程中,职前期学习者的互评参与度和作业质量都是最低的,可见对于职前期学习者来说,还没有形成远程学习的习惯,也许对于作业和互评无所适从,参与积极性低,需要更多的引导。
5. 论坛互动维度
论坛互动的主力军是处于实验重估期和平静保守期的学习者,尤其是在教学方法类课程中,实验重估期学习者处于群体参与度非常显著的峰值地位;在研究方法类课程和工具技术类课程中,实验重估期和平静保守期学习者均有积极的参与。在三类课程中,论坛互动参与度整体呈现随年龄增长而递增的趋势:教学方法类课程中学习者论坛参与度随年龄增长呈指数形式增长;研究方法类课程中学习者的论坛参与度各指标的分布较离散,但峰值集中出现在平静保守期;工具技术类课程中学习者的参与度则呈加速度为负的缓慢增长。
此外,如图18、图19、图20所示,职前期和平静保守期学习者的表现较引人注意,这两个阶段的学习者均有较高的社会交往意愿。尤其是平静保守期的学习者,无论在发帖、回帖、被回复还是被赞频次上都是最高的,可见平静保守期学习者有着很高的论坛互动参与积极性,且其发帖和回帖质量都是较高的,所发的帖子容易形成论坛热点,所回的帖子也常获得他人的认同。较之其他的年龄段,平静保守期的学習者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可以与他人分享的经验较多,所发的帖子也倾向于提出较贴近教学实际的想法和观点,往往能得到同行的认可和点赞。他们回复其他学习者的帖子也较多,存在着“礼尚往来”效应,因此遇到问题也较容易得到其他学习者的回复。而职前期学习者虽然论坛互动的热情高(主动回复他人帖子的频次较高),但人均发主题帖的数量、人均被赞频次、讨论成绩都是最低的(尤其在研究方法类课程中),可见其参与讨论的频次高但质量并不高。
(三)参与度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
1. 各年龄段学习者的成绩分布情况
如图21所示,三门课程中学习者成绩的趋势是较一致的,成绩总体随年龄递增,可见随着年龄增加和职业发展阶段的逐步成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是越来越好的。且各成绩分项(章节测试、作业成绩、论坛讨论成绩)几乎成比例增减,可见认真对待作业的学习者也会认真对待测试、考试、讨论等各项活动。在性别差异方面,从职前期至平静保守期,一直是女性学习者取得更好的总分和各分项成绩(期末考试、章节测试、讨论成绩、互评成绩),然而到了职业消退期,则无一例外是男性学习者取得更好的成绩。从培训效果来看,平静保守期和职业消退期的学习者学得最用心也取得了最好成绩。
2. 各参与度指标与考试成绩的回归分析(整体样本回归分析)
(1)“资源利用”“作业互评”“论坛互动”与考试成绩之间的相关程度
对整体样本进行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发现学习者总参与度与课程考试成绩显著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668,p<0.001。
对整体样本的“资源利用”“作业互评”“论坛互动”“考试成绩”四个指标进行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发现指标两两之间均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但相关程度有所不同。“考试成绩”与“资源利用”(0.781**)和“作业互评”(0.755**)的相关性远大于与“论坛互动”(0.345**)(见图22),即学习者成绩与其利用资源和参与作业互评的程度高相关,而与其参与论坛互动存在低相关。三个指标之间,“资源利用”与“作业互评”的相关性较高(0.799**),而与“论坛互动”仅存在较低相关性(0.380**)。可见MOOC学习者的总参与度与其学习成绩呈显著正相关,其中资源利用行为对学习成绩影响最大,论坛互动行为对成绩影响最小。
(2)各二级指标与考试成绩的回归分析
将各二级指标与考试成绩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模型R值为0.884,调整R方为0.782,F=10741.465,p<0.001。结果发现,各时长指标(如观看视频的在线时长、浏览pdf的在线时长、参与随堂测试的在线时长、参与论坛讨论的在线时长等)均对考试成绩没有显著作用或存在副作用;在频次指标中,参与论坛回复频次、被赞频次、观看视频资源频次、浏览pdf资源频次、浏览讨论区频次与MOOC学习者考试成绩有显著正向作用。在各成绩分项中,互评作业成绩对考试成绩影响最大,其次是章节测试成绩。这可能与互评作业有时间限制有关,错过就会失分。同时,也可见MOOC平台上学习者完成作业及互评环节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四、思考与讨论
(一)各年龄段MOOC学习者参与特征归纳
1. 职前期(18~22岁):高意向、低绩效
职前期学习者对MOOC平台所提供的资源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也有着较强的社会交往意愿,但章节学习和参与讨论的质量不高,需要有效的引导。
2. 职初期(23~25岁):工作繁忙、需提升效率和恰当的时间管理
职初期的学习者的整体参与度较低,可能由于繁忙的入职适应。他们更需要情绪上的激励和效率方面的支持。在各个年龄段中,只有22~26岁(职初期、稳定期前期)的学习者花在文本阅读(如pdf资源)上的时间多于论坛上的时间,可见对于忙碌的初入职教师来说,文字性的资源更有助于他们节省时间并提高效率。
3. 稳定期(26~28岁):资源利用意愿低,社交意愿不高
稳定期学习者使用资源和参与评价他人作业的意愿并不高,喜欢发主题帖却不喜欢回帖。也许经历了稳定期后,一部分人会离开教师岗位,另一部分人留在教师岗位上却暂时还未明确自身定位和找到自己的专业发展目标,因此许多学习者还处于职业生涯中较为消极和迷茫的阶段。
4. 能力建构期(29~35岁):工具技术类课程需求大
能力建构期学习者对工具技术类课程兴趣高,参与工具技术类课程的学习者人数最多,且群体参与度最高。
5. 实验重估期(36~45岁):人数占比最大,群体参与度高
在样本课程中,处于实验重估期(36~45岁)的学习者最多,尤其是37岁左右峰值明显。这一阶段的教师正处于一种自我反思的状态中,且经过前面阶段的积累,已经具备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因此MOOC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学习机会。
6. 平静保守期(46~55岁):社会化学习参与度高
平静保守期的学习者喜欢在线讨论,论坛互动参与度较高,尤其在研究方法类课程和工具技术类课程中得到显著体现。从个体学习者回帖均值来看,个体回帖频次随年龄增长,这一趋势可能意味着:在教师职业生涯中,年龄与交往意愿之间成正比增长,越年长交往意愿越强。
7. 职业消退期(55岁以上):总人数少、个体参与度高、男性多
处于职业消退期的学习者人数不多,但资源使用的人均频次很高,可见这一阶段仍坚持学习的高龄学习者对于MOOC是具有一定黏着性的,学习态度积极主动,参与度较高。职业消退期前期(55~60岁)学习者的平均成绩处于各年龄段的高位,可见处于退休前夕的教师并非一定放松学习或产生职业倦怠。相反,大多数高龄学习者在MOOC上表现出了很高的参与度,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论坛互动中个体回帖和被赞的最高峰期均在職业消退期(55岁以后),再次印证了职业消退期教师强烈的自我学习和发展的需求。然而,这一阶段的女性学习者在各方面的参与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而男性学习者则参与度不减甚至提高,可能与男性和女性教师的退休年龄差异有关,也与男性和女性在退休后的重新职业发展取向有关。此外,职业消退期教师对工具技术类课程的需求显著高于对教学方法与研究方法类课程的需求。
(二)以MOOC教师培训推动积极老龄化的反思
MOOC参与度模型所勾勒出的教师专业化发展进程中的积极老龄化需求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ing)”概念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在面对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挑战所提出的政策框架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指的是老年人为提升生命质量,充分利用各种机会追求健康、参与、保障的过程。其中,“参与”是积极老龄化三大支柱之核心,也是老年人保持身心健康和获得优质保障的重要途径。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MOOC教师培训也彰显了推动积极老龄化的巨大潜力。以下是我们对此的一些思考。
其一,MOOC培训与传统培训互为补充,有助于弥补传统教师培训中各年龄段、各地区资源分配不均和高龄段教师缺乏培训机会的问题,为教师专业化发展营造开放、平等、共享的平台环境。
目前主流的传统教师培训方式有“国培计划”(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由教育部、财政部实施,旨在提高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包括“中小学教师示范性培训项目”和“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两项内容)、区域性的教师培训(依托地区教育局等行政或管理机构组织,采用自上而下的外接式模式,教师短时集中进行培训,形式包括岗前培训、校外集中培训、课题研修等),以及各校根据自身情况组织的校本培训(以教师任职学校为主阵地,以教师互教互学为基本方式,兼顾学校需求与特色)等。受经费限制,在传统教师培训中,各区各校一般都是挑选新入职教师或青年骨干教师接受培训(通常覆盖程度较高的是处于职初期、稳定期、能力建构期和实验重估期的教师)。根据本研究的统计结果,MOOC上参与人数最多且群体参与度最高的是处于实验重估期的教师群体。可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首先考虑参与需求高的群体是合理的。但传统培训普遍存在教师专业发展资源地区不均衡、资源受限或重复开发、受训时间不灵活、培训周期短、学习者交流范围小等问题。MOOC作为开放在线人人可学的课程,开课团队多为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资深专家和优秀教师。二者互为补充,前者以集中式精英化的培训为主,后者以泛在式个性化方式提供,有助于兼顾各年龄段各区域教师的学习与发展需求。
其二,平静保守期和职业消退期学习者是MOOC中个体参与度最高的群体,因此不能忽视对高龄段教师的关注,应为推动“积极老龄化”和实现全阶段“终身学习”设计合理的机制。
MOOC的终极价值追求之一是实现“包容和公平的全民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目标,构建一个开放的教育体系(林世民, 2018)。这与《教育2030行动框架》所提出的“确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使人人可以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徐莉, 王默, 程换弟, 2015)。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老龄人口的比重在逐步增加。社会应以何种方式保证老年人接受继续教育,促进老年人保持自信、健康、思维活跃和较高的社会参与度,进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2002)提出:终身学习、健康、社会参与和社会安全都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因素,有助于促进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其中,接受继续教育则是保证55岁以上老年人平等参与社会活动(Jackson, 2011)、获得较高收入和维持身体健康的有效方式(丹尼斯, 2018)。
根据本研究的统计结果,处于职业消退期的MOOC学习者在各项参与度以及学习成绩方面均不逊于其他阶段的学习者,可见高龄段的教师们并非人们想象中处于职业倦怠和准备退休的消极状态,而是仍然有着较高的自主发展和学习需求,且随着子女成长和养育责任的减少,也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以学习和丰富生活,进而追求终身的发展。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高龄段教师普遍未能充分享有培训机会,目前主流的传统培训集中在职初期至实验重估期的教师群体,一些培训的学习者年龄受限。例如,国培计划的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培养对象原则上不超过45岁(教育部,2016),其他培训主体也大多为青年骨干教师。在这种情况下,MOOC更应该承担其在促进终身学习和社会公平中的责任,充分考虑平静保守期和职业消退期教师的学习困难和发展需求,为教师培训提供创新支撑。
其三,利用MOOC的“大规模”优势效应,在MOOC中形成教师互助共同体,促进跨年龄段教师的远程教研和学习,推动教师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MOOC最激动人心之处在于其“大规模”“开放”的特征,可形成跨年龄段、跨学科、跨学段,甚至跨区域地对话与协作。从上文结论可见,各年龄段MOOC学习者的学习参与特征和自身优势各异。例如,职前期学习者精力充沛,好奇心强,思维活跃,技术素养高,但缺乏实际教学经验和远程学习经验,碎片化时间管理能力不强;职业消退期的学习者一线教学经验丰富,但通常对于新的信息化工具技术较陌生,对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前沿的研究方法的了解也较为欠缺。这两个阶段的学习者都有较高的远程学习与交往意愿,可考虑在MOOC上有策略地形成跨年龄段学习团队或共同体。例如,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定期举行经验分享会,鼓励跨年龄段教师进行分享和交流;设计多元化的项目式学习活动,鼓励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学科背景的学习者共同完成任务,等等。通过跨年龄段学习者结对、结伴学习达到广泛交流、相互协助、相互促进的效果。
[参考文献]
丹尼斯·雷赫扎尼·卡恩斯, 张馨邈. 2018. 澳大利亚老年教育研究:内涵及价值阐释[J]. 开放学习研究,23(05):48-55.
范逸洲,张国罡,陈伯栋,汪琼. 2018. 他们为什么回来?——MOOCs中重复注册者行为与动机分析[J]. 开放教育研究,24(02):89-96.
贾荣固. 2002. 略论教师职业生涯发展[J]. 大连教育学院学报,18(1):4-6.
潘丽佳. 2015. MOOC设计、学习者参与度和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
谢秋山,岳婷. 2019.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必要性及路径研究[J]. 当代继续教育,37(04):10-16.
徐莉,王默,程换弟. 2015. 全球教育向终身学习迈进的新里程——“教育2030行动框架”目标译解[J]. 开放教育研究,21(06):16-25.
詹泽慧,蔡韶华,方识华,梅虎. 2016. 开放在线课程教法的适应性变革:从OCW到MOOC[J]. 现代教育技术,26(04):68-73.
詹泽慧,霍丽名,姚佳静,戴莎莎. 2019. 人工智能时代MOOC将如何发展:机遇与挑战——与Curtis Bonk教授和Paul Kim教授的对话[J]. 中国电化教育(2):1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016-6-11. 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DB/OL]. http://www. moe. gov.cn/srcsite/A1o/s7034/201006/t20100630_14607/.html
总报告起草组,李志宏. 2015.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J]. 老龄科学研究,3(3):4-38.
Aguiar, C., & McWilliam, R. A. (2013). Consistency of toddler engagement across two setting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8(1),102-110.
Astin, A. W. (1984). Student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al theory for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ersonnel, 25(4), 297-308.
Bulger, M. E., Mayer, R. E., Almeroth, K. C., & Blau, S. D. (2008). Measuring learner engagement in cmputer-equipped college classroom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ultimedia and Hypermedia, 17(2), 129-143.
Christensen, J. C., & Fessler, R. (1992). The Teacher Career Cycle Understanding and Guid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llyn & BaconBoston: 160.
Fredricks, J. A., Blumenfeld, P. C., & Paris, A. H. (2004). School engagement: Potential of the concept, state of the evidence.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4(1), 59-109.
Huberman, M. (2005). The professional life cycle of teachers.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91(1):31-57.
McWilliam, R. A., & De Kruif, R. E. L. (1998). E-Qual III: Childrens engagement codes. Chapel Hill, NC: Frank Porter Graham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Meece, J. L., Blumenfeld, P. C., & Hoyle, R. H. (1988). Students goal orientations and cognitive engagement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0(4), 514.
Newman, K. K., Burden, P. R., Applegate, J. H. (1980). Helping teachers examine their long‐range development. Teacher Educator, 15(4):7-14.
Ramesh, A., Goldwasser, D., Huang, B., Daume III, H., & Getoor, L. (2013). Modeling learner engagement in moocs using probabilistic soft logic. In NIPS Workshop on Data Driven Education, pp.1-7.
Reeve, J.A. (2012).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on student engagement.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student engagement. 149-172.
Skinner E. A., & Belmont, M. J. (1993). Motivation in the classroom: Reciprocal effects of teacher behavior and student engagement across the school year.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5(4), 571.
Steffy, B. (1990). Teacher Career Development Pattern. Teacher Development, 12(3): 29-3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No.WHO/NMH/NPH/02.8.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2002).Active ageing:A policy framework[R].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Zhan, Z. Fong, P. S. W., Mei,H., Chang, X., Liang, T., Ma, Z. (2015).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in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A Content Analysis Approach. Sustainability, 7(3), 2274-2300.
責任编辑 郝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