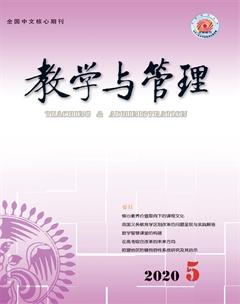基于文体特征的初中语文统编教材解读策略
郭跃辉
摘 要 依据文体特征确定教学内容,展开课堂教学,这是语文教学的基本原则。统编本教材强化对文体的辨析,意在引导教师依据文本的文体特征进行教学。教师在指导学生解读文本时,应注重文本体式的辨析,尊重文体的规约,挖掘文体的内涵。
关键词 统编本教材 文体 体式 规约 内涵
王荣生教授曾说:“依据体式来阅读,是阅读的通则;依据文本体式来解读课文、把握一篇课文的教学内容,是阅读教学的基本规则。”[1]不论是阅读取向还是阅读方法,都跟文本的文体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生的阅读能力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针对特定文体的阅读能力,例如散文阅读能力、小说阅读能力、实用文阅读能力等。因此,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都要依据文本的文体特征。教师在阅读教学时,自然也需要辨析体式,在一定的文体规约下,充分挖掘文体的内涵。
一、辨析文本体式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特别重视“辨体”,这一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实际上包含了文体学、创作学、鉴赏学等多个层面的知识,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对不同的文体进行解说与分析。此处说的“体式”,不是宏观分类意义上的文本类型,而是在一定文类下的更为具体的文本的特质。甘其勋认为:“文章体式,是文章成型之后的直观样式。它是文章的结构、语体、体裁等诸多形式要素的综合呈现,也是文章外在的格局模样,包括标题、行款格式和其他意义的符号标志。”[2]可见,解读文本的前提就是对文本的体式特征有清晰的认识与把握。
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曾一度在教材中“消失”,最新的统编本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重新收入。以前很多教师习惯于将本文当作议论文来教,即通过《纪念白求恩》教议论文的文体知识,如论点的概括、论据的选择与论证的过程,并把对比论证作为重要知识点。实际上,议论文是一种剖析事物、论述事理、发表意见、提出主张的文体。而《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从题目上看就不似议论文,“纪念”本身是表达对人或物留念、怀念情感的词语,其本意是表达情感而不是发表议论。即使文中出现了多处议论性的句子,也不能否认“纪念”一词中所包含的情感成分。虽然本文对白求恩身上的品质与精神进行了概括并评论,并号召共产党员学习这种精神,但不是中学语文教学意义上的“议论文”。《纪念白求恩》不能被纳入到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类”文本序列,更不应将其归入记叙文、议论文、抒情文等“教学文体”的序列,而是一篇实用类文本,其具体的体式应该是“人物纪念类文本”,即简述人物经历,概括并推广人物的精神品质,表达对人物的怀念之情。也就是说,《纪念白求恩》并不是一篇典型的议论文,试图从文章中寻找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试图给学生讲解“对比论证”的手法,都无异于缘木求鱼。《纪念白求恩》的教学内容,应围绕“纪念”一词,从写作目的、人物形象、作者的态度情感等方面进行分析。
再比如康拉德·劳伦兹的《动物笑谈》一文,有教师将其作为“科学小品文”来教。科学小品文,或者知识小品或文艺性说明文,是用散文的笔调,即借助某些文学写作手法,将科学内容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实质上还是说明文的一种类型。这篇文章虽然涉及到一些动物习性的科学知识,也有文学化的写作手法,但本质上不是说明文,它不是以介绍、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的。文中写到“我”实验、猜想等科学研究的过程,也写到了小鸭子的生活习性以及大鹦鹉的生活规律等。但这些动物学的知识并不是重要的教学内容,更不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例如,作者在观察研究小鸭子的行为之后说道:“我因此得到一个颇为清晰的结论:如果我要小凫跟着我走,我得学母凫一样叫才行。”作者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结论,只是一种个人生活经验的描述。而且,作者还饶有兴趣地引用了德国诗人布什的诗句来印证这个结论,这更说明知识本身不是写作目的,“趣”才是作者着意表现的内容。“动物笑谈”与“笑谈动物”的含义是有区别的,“动物笑谈”的真实含义应该是:用幽默的笔调讲述“我”与动物之间的趣事。本文的价值在于:从内容上获取关于科学研究的一些趣事,从情感上体悟“我”的科学研究精神,从理性上思考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存在关系。
因此,对于文体特征不是很明显的文本,教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辨体,不仅将文章归入某一大的“文类”中,还要辨析具体的体式特征。如果文体归属有误的话,就会出现很多似是而非的、奇奇怪怪的解读方式。
二、尊重文体规约
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规范,这种规范是人们在不断的创作过程中形成的,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愿,因此也可称之为“文体规约”。著名文艺理论家南帆先生认为:“每一文类都拥有其特殊标志,被赋予了某种足以使其相对独立的性质;这些试图指示出某一文类独一无二的身份,以便让它的家族成员共享一种相似性。”[3]南帆先生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原理来阐述文类的概念,更形象地揭示了文体的“规约”特征。
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单个文本纳入到某一文类中时,该文本已经不自觉地与其他同类文本有了“家族相似性”,不论是言语形式还是文本结构、内涵,都打上了某一类文章的“独特印记”。这种“印记”,并非阅读该文本的具体方法,而是决定着阅读心理的结构与阅读内容的走向。在王荣生教授看来,所谓的“阅读能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阅读取向,即由读者的阅读目的决定的阅读姿态与阅读样式;二是阅读方法,即运用适合于该文本的方法。“阅读,就是对某种特定体式文章的阅读,对具体作品的具体阅读活动。阅读作品,抱着什么目的、持什么样的姿态,我们叫‘阅读取向。在这种体式的文本里看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看出什么东西来,我们叫‘阅读方法。”[4]“看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实际上就是一种文体的规约。
例如,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教师在教学时首先应该将文本归入“童话”这一文类,而不是记叙文、小说或寓言故事。归属清晰之后,教师自然应该引导学生按照童话的文体规约进行阅读。所谓童话,是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的一种文体,它与小说不一样。虽然它们都可进行想象与虚构,但小说更讲究塑造典型人物,而童话里的人物多是脸谱化的类型人物,他们甚至没有名字,个性特征并不十分突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重復比率比较高。童话里的人物是抽离了时代社会、家庭背景、人际交往、生平经历等方面的“单面人”,人物身上没有多重的甚至矛盾的性格,其性格也没有明显的转变。作品中的皇帝,虽然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但其生活的时代很模糊,作者只是说“很多年前”,其性格其实也是“扁平”的,即由某种嗜好引起的轻信、虚荣、自欺欺人等缺点,人物本身并不是恩格斯所说的“典型人物”。两位诚实的老大臣,也只是某一类人物的代表,他们并没有突出的个性特征。他们去骗子屋子里查看新衣制作的进程,两个情节相似度很高,虽然具体的语言有差异,但性质是一样的。这种“重复”,不同于鲁迅小说《祝福》里祥林嫂叙述阿毛被狼叼走的反复叙述,后者是有某种特定表达意图的,而童话里的“重复”,更多是考虑到儿童的接受心理特点。这一点在儿童阅读的绘本故事中最为常见。童话是为儿童创作的,属于儿童文学的一种。在解读文本时,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阅读体验,如果学生感受到“故事很有意思,很搞笑”,那就要顺水推舟,请学生畅所欲言其感觉到的“趣味”是什么,从文中哪些地方读出了这些趣味,而不是先入为主地给学生灌输社会反映论的阶级观点,或者是讲真话之类的道德教育内容。这其实也是一种尊重文体规约的表现。在此基础之上,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进一步思考,挖掘童话的社会价值与生活意义,但不论如何引申,其基础还是童话这一基本的文体规约。按照童话的文体规约进行阅读或文本解读,可以确保方向不会偏离。假如教师不顾及这一点,在课堂上大谈特谈“叙述视角”“人物形象”“文本的思想内涵”等,都是一种脱离甚至违背“童话规约”的表现。
当然,“尊重文体规约”并不是说教师或学生只能按照某一种文体的已有规范进行阅读。文体规范是历史地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尊重”并不是“不准越雷池半步”,文本解读,尤其是文学类文本的解读,也要尊重学生或其他读者的个性化解读。
三、挖掘文体内涵
文本的“文体规约”只是文本解读的方向,同一文类内部还会有更为细致的区别,例如同样是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与后现代派的小说就存在不同的阅读策略,诗化小说与伤痕小说也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用“情节、人物、环境”三要素作为解读所有小说的依据与框架。我们在阅读作品时,不仅要考虑到该作品属于哪一“类别”,更要考虑到“这一个”文本所具有的独特的特征,即挖掘具体文本的文体内涵。教老舍的《济南的冬天》,不能只会讲散文的“形散神不散”、散文的情感等,而应该深入到“这一篇”散文具有的独特特征,例如老舍是如何言说“个人化的济南冬景”、作者的写作姿态与语言风格如何、独特的写作手法等,这才是这篇文章独特的教学价值。
这就要求教师立足于文本本身,不仅从“个别”上升到“类别”,更要从“类别”返回“个别”。就拿《纪念白求恩》来说,纪念类文章的共同特点就是多种表达方式的使用。既然是纪念某位人物,那么概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或者详细讲述人物的某一生活片段,就要进行叙述;如果要对人物的品质进行高度概括,揭示人物及其品质对他人的意义与价值,就要进行议论;如果要抒发人物的离去所带来的悲痛与怀念之情,就要进行抒情。如果作者须要渲染氛围,或者借助景物来抒发情感,还可能用到描写这种表达方式。这些属于纪念类文章的“类特征”。具体到《纪念白求恩》,作者也表达了某种悲痛与怀念之情,但这并不是本文最主要的写作目的。或者说,本文的重心不在于抒发情感,而在于将“白求恩精神”作为教育全党的素材,揭示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启示意义,这是由作者的身份决定的。对于这种“启示意义”的具体表现,教师须要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文本,归纳要点,概括出“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等内容。这一点也是“纪念”的本职所在。
当这种“启示”意义转化为“行动”时,就须要“学习”这种行为。据悉,毛泽东主席在1939年12月21日写下的文章,原名就是“学习白求恩”,1940年刊发于《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也是《纪念白求恩》的最初版本。1952年入选《毛泽东选集》时才更名为《纪念白求恩》,并做了诸多的改动,包括注释、个别概念以及一些字词与语法。这也暗示出,“学习”白求恩身上的精神并转化为实际的工作、行动,才是对白求恩最好的“纪念”。在行文过程中,作者在四处都用到了“学习”这个动词,分别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这一点也是“这一篇”纪念类文章的特殊之处,是须要引起教师关注的。
另外,文中对白求恩的称呼,也需要从“纪念类文本”的角度加以理解。文章多处称呼白求恩为“同志”,这说明毛主席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甚至中国人民表达对白求恩的哀悼之情,并号召党内人士向白求恩学习。当讲到白求恩的职业及其职业精神时,作者又称呼其为“白求恩医生”。文中还有一处,即“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此处既不称呼他为“同志”,也不称呼他为“医生”,原因在于这是转述从前线回来的人对白求恩的称呼。从前线回来的人,并不全是党内人士,自然不能称其为“同志”;也并不全部都接受过白求恩的治疗,因此不便称其为“医生”。作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称白求恩为“同志”体现出党内的民主亲密关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和白求恩虽然国籍不同,但都是共产党人;称其为“医生”则是对白求恩的职业与贡献的尊重。例如“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改为“我和白求恩只见过一面”,难免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感。对于文章的题目来说,“纪念白求恩同志”或“纪念白求恩医生”,都有其合理之处,但直接说“纪念白求恩”,也合情合理,因为文章是面向所有读者的,而不是只给党内人士读的。
总之,依据文体特征,既须要依据某一文类的“类特征”,也要善于把握具体文章的“个性特征”,两者结合才能够进行合宜的文本解读,进而把握课堂教学的内容。辨析文本体式是前提,尊重文体规约是方向,挖掘文体内涵才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王荣生.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王荣生给语文教师的建议[J].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
[2] 甘其勋.文章教育学[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3]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4] 王榮生.求索与创生:语文教育理论实践的汇流[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责任编辑 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