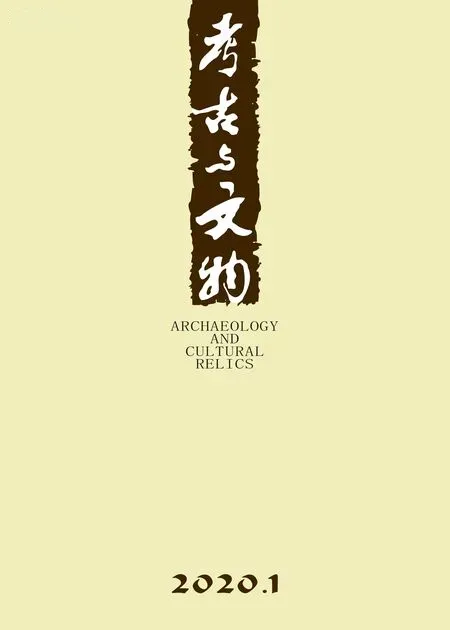唐濮恭王李泰墓志铭考
刘志军
(湖北十堰市博物馆)
1975年,湖北省博物馆在十堰市郧县城关镇砖瓦厂发掘了唐太宗李世民之子李泰墓。出土文物较为丰富。其中有墓志一合。志盖篆书,共16字[1]。志文楷书,共34行,满行33字,其中14字漫漶不清。该墓发掘报告尚未发表。李泰是唐初的一位重要皇子,对初唐的历史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对于李泰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与《唐会要》等史籍中的记载,而史籍中关于李泰的记载又多有漏误与矛盾,导致在诸多研究文章中,对李泰的研究出现争议、猜度甚至臆断。李泰墓志铭的发现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图一、二)。
李泰墓志铭全文如下:
盖文:大唐赠太尉雍州牧故濮恭王之墓志铭
志文:大唐赠太尉雍州牧故濮恭王墓志铭/
王讳泰,字惠褒,高祖武皇帝之孙,太宗文皇帝之第三子也。华盖极天,讵足仰其/神搆;仙槎上汉,无以汎其灵源。国史详焉,今可略而言矣。王降辰象之粹精,稟河岳之/沖气,蕴清眀于岐嶷,立端懿于绨绮。夙著聪敏,轶北海之流声;早擅文章,掩东阿之远/誉。于是括词林而逰刃,揔儒肆以撡矛。鸾文凤艳之奇,迴翔于玄翰;玉策金縢之秘,昭/晰于灵府。武德三年,封宜都王,食邑四千户。四年,进封卫王,邑万户,授上柱国。周京宗/子,是曰维城;汉室皇枝,允膺磐石。眷言疏爵,义光前典。贞观二年,改封越王。拜使持节/大都督,扬、常、和、润、滁、楚、舒、寿、庐、豪、歙、苏、杭、宣、东睦、南湖十六州,越州都督诸军事,扬州/刺史。包衡霍而为宇,控江沲而奄宅。雄风且扇,好剑之俗先懲;高义方申,背淮之客爰/萃。仍以壤带渠戎,地隣獯虏。三阳抗其峻跱,五龙摽其形胜。俗多尚气,人皆好勇。隆周/以为荒远,炎汉致其空虚。绥道之方,良归懿戚。六年,授使持节大都督,夏、胜、北抚、北宁/、北开五都督,鄜、坊、延、丹四州诸军事,鄜州刺史,余官封如故。八年,改授雍州牧。匪行钩/距,无待藉名。便移分赘之风,自革并兼之弊。举提封之五万,不失其时;追风教于二南,/克隆其美。寻领左武侯大将军,余官封如故。执金吾而式道,发缇骑以禽奸。声姿高畅/,鄙季珪之威重;性理矜严,宠孝孙之处议。十年,改封魏王,授使持节都督,相、卫、黎、魏、洺/、邢、贝七州诸军事,相州刺史,竟未之藩。又除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余官封如故。亦犹/咸林列国,入纂中台;东平胙土,留居上将。夫吉凶匪召,倚伏难源。未极抟摇之举,俄招/害盈之谴。十七年,解职降封东莱郡王,寻改封顺阳郡王,邑三千户。仍奉纶言,远令之/国。翘心魏阙,等归陈以责躬;齐志老庄,异还梁而不乐。廿一年,进封濮王,邑万户。方兴/淮南道术,终控羽以高骧。岂谓东海谦□,□下床□永恸。以永徽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薨于郧乡第,春秋卅三。爰申追远之诏,式被哀荣之典,赠太尉、雍州牧。班剑卌人,羽/葆鼓吹。赙物三千段,米粟三千石。赐东园秘器,葬事官给,务从优厚谥曰恭王,礼也。以/四年岁次癸丑二月癸未朔廿日壬寅葬于均州郧乡县之马壇山。惟王风宇凝畅,神/姿秀远。振松干於千寻,跱琼峰於万刃。孝惟成性,仁非外奖,体包上德,道叶中和。该众/妙于玄旨,综多能于群艺。加以情深□士,敬爱忘疲。类西河之拥篲,同南荆之置醴。饰/无金采,居犹布素。庄敬温恭之道,冲虚雅憺之怀。游之者不测波澜,奉之者如登廊庙/。信人伦之隐括,宗室之仪表者矣。自违迹上京,分珪下国,寂寥遐路,淹留积祀。悼四时/之代序,怀九重而永慕。呜呼!阅水成川,伤百龄之讵几;倾羲无旦,何千月之能终。懼英/猷之或泯,□纪德于泉宫。

图一 唐濮恭王李泰墓志志盖拓片(比例为1/9)
其铭曰/:侚齐基永,疏□业遥。相秦藩魏,振野光朝。化凝迁邑,道盛归谣。庆高复禹,功深纂尧。玉/产惟崐,珠生伊汉。实华帝□,□隆宗干。敏架五行,言符一贯。琱章擅美,良书允玩。思/穷通□,神夷乐善。孝德内申,忠亲外展。七萃云肃,六条斯阐。麟趾攸歌,甘棠勿剪。宠冠/刘武,□□陈植。物忌满盈,灾沿□□。恩流析壤,礼优就国。奉藩弥敬,循躬愈饬。忽悲/过隟,□痛摧梁。恸深宸扆,泽备徽章。昭涂永绝,幽穸何长。行看宰树,更指咸阳。

图二 唐濮恭王李泰墓志铭拓片(比例为1/4)
综观《新唐书》与《旧唐书》等史籍,在唐太宗李世民十四子的记载中,记述比较丰富的是李泰。史料中既有因唐太宗宠泰而引起的朝臣疏谏记录,也有太宗对其所颁之诏文记录。李泰为唐太宗第四子,除第二子李宽出继与早逝外,能与其相较的当数太宗长子皇太子李承乾和三子吴王李恪。
三人中,李承乾乃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嫡长子,为皇太子。《旧唐书》记载“(李承乾)性聪敏,太宗甚爱之。”[2]“(李)恪母,隋炀帝女也,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3]“(李泰)少善属文。……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复令乘小舆至于朝所。其宠异如此。”[4]“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5]《新唐书》亦载:“(承乾)特敏惠,帝爱之。”[6]“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且儿英果类我。”[7]“帝以泰好士,善属文,诏即府置文学馆,得自引学士。又以泰大腰腹,听乘小舆至朝。”[8]
后皇太子李承乾在太宗时因谋反事被废,吴王李恪因陷入谋反事而被诛,李泰也因与皇太子李承乾争位而被贬。
可以说,唐代初年唐太宗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儿子都因为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而退出历史舞台。围绕他们三人的斗争,涉及到整个唐初,特别是贞观朝的政治格局与人物活动,正如《旧唐书》所载:“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9]对他们的研究也是唐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李泰是其中最有争议的人物。
一、关于墓志铭与史籍文献
整篇墓志铭,依序简略记载了李泰一生。从武德三年始封宜都王到永徽三年薨及永徽四年下葬,所叙之事,与史载大体吻合。“国史详焉,今可略而言矣。”《新唐书》与《旧唐书》中关于李泰的记载一致,相对而言《旧唐书》较《新唐书》略详。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史载的年月时辰较墓志铭为详细,墓志铭中关于李泰所封及官职则要较史载丰富、具体和严谨。
《旧唐书》载:“五年,兼领左武侯、大都督,并不之官。八年,除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七年,转鄜州大都督。十年,徙封魏王,遥领相州都督,余官如故。”[10]先述其八年,再述其七年,而后述其十年,顺序有异,这里当以墓志铭记载更为合理。而“七年,转鄜州大都督。”在《新唐书》无此记录。墓志铭中则是“六年,授使持节大都督,夏、胜、北抚、北宁、北开五都督,鄜、坊、延、丹四州诸军事鄜州刺史。”
又《唐会要》:“贞观二年五月。濮王泰除使持节大都督扬州、常、海、润、楚、舒、庐、濠、寿、歙、苏、杭、宣、东睦、南和等十六州诸军事扬州刺史。”[11]这里与墓志铭中略有区别。《唐会要》中说十六州,可只列出了十五州名。相比墓志铭记载,少和州、南湖州和滁州,但多出一个海州与南和州。
据《旧唐书》,贞观年间的扬、楚、濠、滁、和、庐、寿、舒、润、常、苏、湖、杭、歙、(东)睦、宣州属江南道所辖。而在《新唐书》中,濠州属河南道,扬、楚、滁、和、庐、寿、舒属淮南道,润、常、苏、湖、杭、睦、宣、歙属江南道。无论两唐书中如何归属,但这十六个州集中分布,可以连成一片。
分析《唐会要》所载,海州属河南道,且与楚州之间被河南道的泗州所隔断,治域并不接壤。湖州处在苏、杭、常、宣州之间,被此四州包围;滁州处在濠、庐、和、楚、扬州之间,被此五州包围。如果无湖州与滁州,那么李泰所督区域中出现空域,则于理不合。这同时也说明了墓志铭记载的合理性。由此看来,湖州与滁州当在此十六州之列,而海州则不在。同时也不难看出,墓志铭中的南湖州应为湖州。至于为何称为南湖州,两唐书均无载。故《唐会要》中的南和州当为墓志铭中南湖州之误,且漏载了滁州。因此,综合而论,当以墓志铭的记载完备而准确,可以校正《唐会要》此段记载的失误。
另,《唐会要》中为濠州,墓志铭中作豪州。据《新唐书》“河南道:濠州钟离郡,上。‘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从‘濠’。”[12]《旧唐书》“淮南道:濠州下,隋为钟离郡。武德三年,改为濠州。”[13]《旧唐书》“睦州,隋遂安郡。武德四年,平汪华,改为睦州,领雉山、遂安二县。七年,废严州之桐庐县来属,又改为东睦州。八年,去‘东’字。旧管县三,治雉山。万岁登封二年,移治建德。天宝元年,改为新定郡。乾元元年,复为睦州。”[14]《新唐书》中的元和为唐宪宗年号,元和三年为公元808年。而《旧唐书》中的武德则为高祖李渊年号,武德三年为公元620年。二者记载有异。至于贞观永徽年间是濠州亦或豪州,尚难断定史籍与墓志铭谁之误。而贞观永徽年间的睦州,以史载来作比较,则墓志铭中又或略有笔误。
二、关于李泰的身份排行
李泰,墓志铭中云“太宗文皇帝之第三子也。”但这与两唐书的记载明显有别,并且两唐书的记载保持了一致。《新唐书》记载:“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十四子:长曰恒山愍王承乾,次曰楚王宽,出继。次曰恪,次曰濮王泰,次曰庶人祐。”[15]《旧唐书》记载:“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16]这里有明显的区别。显然,这里的次序就与太宗第二子楚王宽有密切的关系。《旧唐书》:“楚王宽,太宗第二子也。出继叔父楚哀王智云。早薨。贞观初追封,无后,国除。”[17]
《旧唐书》又载:“楚王智云,高祖第五子也。……智云本名稚诠,……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武德元年,追封楚王,谥曰哀。无子,三年,以太宗子宽为嗣。宽薨,贞观二年,后以济南公世都子灵龟嗣焉。”[18]表明,楚王李宽于贞观二年或之前就去世了。以此来看,李泰为太宗第四子也无疑。
《旧唐书》:“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承乾、濮王泰,杨妃生吴王恪、蜀王愔,……后宫生楚王宽、代王简。”[19]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太宗十四个儿子,除楚王宽和代王简之外,其余十二子之生母均为正式封号,独李宽与李简之母为“后宫”,没有正式的名份,可见其母身份较为卑微。加之已“出继”,故在实际生活中未列入太宗诸子排行,李泰就排序为太宗第三子了。至于作为国史的《新唐书》与《旧唐书》,因为后世所修,按事实还原排行,亦是符合修史要求的。
在同期发现的李泰之妻阎婉墓志铭中,亦称“(濮)王是太宗第三子。”当为同理[20]。
此外,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在出土的李恪墓志铭称李恪“陇西狄道人也,太祖武皇帝之孙,太宗文皇帝之第二子也。”[21]显然,也是因为楚王宽出继的原因,李恪的排行也由第三子进序为第二子。
三、关于李泰的年龄与生卒年
《旧唐书·高宗上》:“(永徽三年)十二月癸巳,濮王泰薨。”[22]《新唐书·高宗》:“(永徽三年)十二月癸巳,濮王泰薨。”[23]《旧唐书·濮王泰》记载:“永徽三年,薨于郧乡,年三十有五。”[24]《新唐书·濮王泰》:“薨郧乡,年三十五”[25]。
李泰去世的时间与年龄,新旧唐书记载一致,均在永徽三年十二月,年仅三十五岁。如果按年龄来推算,李泰的生年当为武德元年(618年)。
但是,《旧唐书》关于太宗长子李承乾的记载:“冬十月,癸亥,立中山王承乾为太子。”[26]“太宗即位,承乾时年八岁。”[27]这一年为武德九年,此年的八月份,太宗继皇位。按此推算,李承乾当出生于武德二年。如果以新旧唐书为准,则身为太宗长子的李承乾比李泰要小一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此,黄永年认为,“‘永徽三年’‘盖五年’之误,泰实生于武德三年。”[28]这就是说,黄先生首先是认定李泰的“年三十有五”之说是正确的,并以此为基数进行推算。又因其不可能比李承乾大,故只得认为其薨年有误。此后出版的著作中,黄先生一直持此观点[29]。而其实李泰的薨年是无误的,墓志铭与唐史一致,黄先生认为泰实生于武德三年的观点也是正确的,真正导致黄先生误判的是唐史记载李泰的年龄有误。
岑仲勉在《唐史余沈》中,亦对李泰之生卒年提出了疑问[30]。更有甚者,在史料相互矛盾而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剑桥中国隋唐史》还提出了大胆的推测:“有关这一时期的正史说李泰是文德皇后的第四子,但其他史料说他可能比‘大哥’承乾还年长,而且可能是太宗的另一妃子所生。”[31]
此外,新旧唐书中对于李恪的出生年月亦载不详,仅知其武德三年始受封为王,但据李恪墓志铭:“春秋卅有五,以永徽四年二月六日薨……。”以此推算,李恪出生于武德二年。显然也要小于李泰史载的三十五岁,亦是不可能之事。至于李承乾与李恪同为武德二年所生,因其母不同,在同一年出生的月份上略有区别却是可以成立的。
在新旧唐书中,对于李泰的生年及与其年长于其兄李承乾和李恪的问题,再无其他旁证史籍可以解决这一谬误。但李泰墓志铭中却明确记载:“以永徽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薨于郧乡第,春秋卅三。”这里与史籍所载相差两岁,其薨年与史载无异,仅年龄少了两岁。按此推算其为武德三年(620年)所生,这样李泰与其三个兄长的年龄就没有疑义了。
又《旧唐书·高祖纪》:“(武德)三年六月壬辰,……封承乾为恒山王,恪为长沙王,泰为宜都王。”[32]《新唐书·濮王泰》:“始封宜都王,徙封卫,继卫王后。”[33]《新唐书·常山王承乾》:“武德三年,始王常山郡,与长沙、宜都二王同封。”[34]“(武德)三年六月壬辰”中的“壬辰”日为初一日(阳历7月5日)。李承乾与李恪同年,而李宽又在他们之间,故他们三人当是一年所生,即武德二年,李泰在他们的次年,武德三年出生,且在此年六月之前。
四、关于李泰贬居郧乡的时间与卒年的公元年
《旧唐书·太宗下》:“(贞观十七年)六月……闰月,丙子,徙封东莱郡王泰为顺阳王。”[35]《旧唐书·濮王泰传》:“寻改封泰为顺阳王,徙居均州之郧乡县。”[36]这里并没有指出李泰到达郧乡县的具体时间。
《资治通鉴》则对李泰迁居郧乡县的时间记载就非常准确:“(贞观十七年)九月,癸未,徙承乾于黔州。甲午,徙顺阳王泰于均州。”[37]贞观十七年九月的癸未日为公元643年10月24日,甲午日则是11月4日,中间只相隔了10天,李承乾与李泰先后被徙。
关于李泰去世的公元年份。墓志铭云“(李泰)永徽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薨……。”据《中国历史纪年表》,农历永徽三年的十一月廿六日为公元652年12月31日[38]。以此推算,故永徽三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当为653年1月20日。据此推算出下葬时间“四年岁次癸丑二月癸未朔廿日”为653年3月24日。故李泰逝世之年应为公元653年,这里不能简单的把永徽三年定为公元652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要具体的确定到其日期才能作出定论。所以,李泰的生卒年如果转换为公元纪年,则应为620至653年。
五、余论
综观相关唐代史籍和李泰墓志铭,不难看出,在对待李承乾、李恪和李泰等几个皇子的态度及处理上,唐太宗李世民及稍后的唐高宗李治都对李泰比较宽厚。这一点,史籍与墓志铭所表现出的基本一致。
此三人都受到唐太宗的宠爱,甚至都被许诺或意欲立为皇太子。从唐史分析,李承乾占据嫡长优势,被立为太子,但李泰也曾是唐太宗心中的皇太子人选,甚至到李泰被贬郧乡县后,“太宗后尝持泰所上表谓近臣……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39]至于李恪,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后,曾认为似乎不妥,而欲立李恪。《旧唐书》载:“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于是建立遂定,因加授无忌太子太师。寻而太宗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40]长孙无忌加授太子太师是立李治为太子之后的第三日,“丙戌,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41]《新唐书》记载:“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乃止。”[42]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之后,还想改变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亦可见李恪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
李承乾与李泰在被贬之事上,亦是有很大区别的。李承乾贞观十七年九月癸未日迁居地蛮荒之地黔州,十天之后的甲午日,李泰被贬居均州郧乡县。相比之下,李承乾迁居之地更为遥远与落后。此外,李承乾被贬为庶人,而李泰则只是降封爵为郡王,并于四年之后再进封濮王。李泰墓志铭载:“廿一年,进封濮王,邑万户。”这也是唐太宗对李泰念念不忘的偏爱之情。相反,李承乾却在第二年,即被贬一年之后的贞观十八年十二月辛丑日,死于迁居地黔州。
李泰死后,谥曰恭。“恭,尊贤贵义曰恭,爱民长悌曰恭,既过能改曰恭,执礼敬宾曰恭,率事以信曰恭,……赠太尉濮王泰。”[43]李泰的谥号应与其既过能改有关。
通观墓志铭全文,字里行间对李泰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志文部分亦与两唐书史载基本吻合,充满了褒溢之辞,但也对其遭遇表示出了同情。从唐史记载来看,李泰的人生经过了一次极大的起伏,从先前的“宠冠诸王”,到贬迁郧乡县,再进封濮王,仍食邑万户。这些记载都能在墓志铭中得到印证。
[1]全锦云.试论郧县唐李泰家族墓地[J].江汉考古,1986(3).
[2]刘昫等.旧唐书:太宗诸子(卷76)[M].北京:中华书局,1975:2648.
[3]同[2]:2650.
[4]同[2]:2653.
[5]同[2]:2666.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太宗子(卷80)[M].北京:中华书局,1975:3564.
[7]同[6]:3566.
EBV是CCB-Ⅱ制动机重要的人机操纵平台,EBV主要由手柄杆,转轴,摩擦盘,弹簧开关,拨杆,大、小齿轮,机械排气阀,电位器,微动开关,面板,控制板卡、信号采集模块、LON通信模块组成,其中共有7个微动开关,2个电位器(大小闸各用1个)。EBV是整个制动系统Lon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通过采集手柄所处的位置信息,这个位置信息包括电位器读数与微动开关状态,经过控制板卡分析计算后由Lon网传输至IPM,IPM下发指令至EPCU实施相应制动操作。
[8]同[6]:3570.
[9]同[2]:2656.
[10]同[4].
[11] 王溥.唐会要:亲王遥领节度使(卷78)[M].北京:中华书局,1955:1435
[1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地理二(卷38)[M].北京:中华书局,1975:991.
[13] 刘昫等.旧唐书:地理三(卷40)[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75.
[14] 刘昫等.旧唐书:地理三(卷40)[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94.
[15]同[6]:3563.
[16]同[4].
[17]同[2]:2649.
[18] 刘昫等.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卷64)[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23.
[19]同[2]:2647.
[20] 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1987(8).
[21] 郑炳林,张全民,穆小军.唐李恪墓志铭考释与有关问题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7(3).
[22] 刘昫等.旧唐书:高宗上(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75:71.
[2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高宗(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75:54.
[24]同[9].
[25]同[6]:3572.
[26] 刘昫等.旧唐书:太宗上(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75:31.
[27]同[2].
[28] 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3).
[29] 黄永年.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C]∥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一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24-59.
[30] 岑仲勉.唐史余沈:承乾与魏王泰之年龄[M].北京:中华书局,2004:10-11.
[31](英)崔瑞德(Twitchett Denis)编.剑桥中国隋唐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34-235.
[32] 刘昫等.旧唐书:高祖(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
[33]同[8].
[34]同[6]:3564.
[35] 刘昫等.旧唐书:太宗下(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75:55.
[36]同[9].
[3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7)[M].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2:6204.
[38] 方诗铭,方小芬.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402.
[39]同[9].
[40] 刘昫等.旧唐书:长孙无忌(卷65)[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53.
[41]同[35].
[42]同[7].
[43] 王溥.唐会要:谥法上(卷79)[M].北京:中华书局,1955:1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