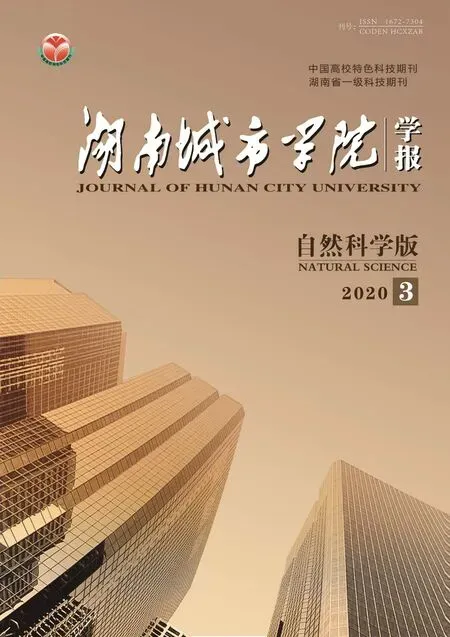杭州市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刘逸辉,彭伟斌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杭州 311121)
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包括不同空间尺度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过程、驱动机制以及资源、生态和环境效应影响等诸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体系[1-2]﹒其中如何准确描述土地利用景观的空间格局及变化,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3]﹒现有研究表明:利用景观集聚度、破碎度等相关指数能很好地解释土地利用变化的景观生态现状[4-5];基于分形理论,可以计算土地利用斑块的分维数和稳定性指数,从而构建分形模型来分析土地利用的分形特征[6-7]﹒景观格局指数的优点在于能够高度浓缩景观格局信息,反映其结构组成和空间配置某些方面特征,可以从斑块尺度、斑块类型尺度和景观尺度3 个层次进行分析[8]﹒杨珊[9]通过构建景观格局指数,在景观尺度上分析了汉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格局、生态安全之间的时空演变关系;李玉华等[10]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分析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景观格局的时空分异特征,探讨景观格局时空变化与城市化之间的联系;DADASHPOOR H 等[4]通过景观指数分析了伊朗西北部地区的景观时空特征﹒可见,结合景观生态学,运用景观格局指数来分析景观空间格局是 目前应用十分广泛的定量分析方法之一[11]﹒
杭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岳文泽等[12]采用建设用地扩张强度、空间自相关方法,研究了杭州市城市扩张的空间模式;徐丽华等[13]根据杭州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各地类重心的转移,分析其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杨杨帆等[14]分析了近30 年来杭州市土地利用的变化;田鹏等[15]则对杭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但现有研究对杭州市景观生态格局考虑不足,未能定量描述其破碎度与异质性等景观空间特征﹒本文将《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 年)》[16]确定的规划区范围作为研究区域,运用GIS 的空间分析工具,对2010—2017年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空间特征与各类用地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进行分析,得到其土地利用变化矩阵,并结合杭州城市发展进程,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同时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对土地利用的景观破碎度、集聚度和异质性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总结杭州市规划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特征﹒这对全面掌握土地利用的变化特征,制定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域概况
杭州市位于浙江省北部,钱塘江下游北岸,京杭大运河南端,地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南翼,是该区域重要的中心城市﹒杭州市下辖10 个区、1 个县级市和2 个县,总面积1 685 357 hm2,其中市区面积829 231 hm2,2017 年常住人口946.8万,其中市区824.1 万﹒研究区域包括上城区、下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江干区、滨江区、余杭区和萧山区8 个市辖区,总面积333 594 hm2,约占市区面积的40%、市域总面积的20%,而GDP 约占全市的75%(2017 年);2017 年末总人口691.1 万,占全市总人口的73%[17],在杭州市城镇、人口和产业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包括2010 和2017 年2 个时期土地利用数据(空间分辨率均为30 m),其中2010年数据是利用Landsat TM 和ETM+数据绘制的全球30 m 地表覆盖遥感制图数据(Glabeland30)(数据来源: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doi:10.11769/GlobeLand30.2010.db)),经检验其整体分类精确度为83.50%[18-19];2017 年土地利用数据则是基于Landsat 8 OLI 多光谱影像绘制的全球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后期采用高分卫星数据进行辅助训练、验证样本等处理,并利用高程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进行修正,一级分类精确度在75%以上[20]﹒2010 和2017 年2 个时期数据均由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制作发布,分类精度均满足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精度要求[20]﹒
2.2 研究方法
2.2.1 GIS 空间分析
在GIS 软件的支持下,利用研究区域边界矢量数据对2 个时期的分类影像进行掩膜处理,得到2010 和2017 年的土地利用分类图(见图1)﹒

图1 2010 年和2017 年杭州市规划区土地利用分布

2.2.2 景观格局分析
将2010 年与2017 年土地利用栅格数据导入景观格局分析软件Fragstats 4.2 中,根据研究需要和景观指数的含义,在景观尺度与斑块类型尺度上,选取斑块密度(PD)、斑块数量(NP)、周长-面积分维数(PAFRAC)、最大斑块指数(LPI)对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的破碎化程度、景观集聚度和景观异质性进行分析(见表1)﹒

表1 景观指数及其含义
3 结果与讨论
3.1 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2010 年至2017 年杭州市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较为明显,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占比皆有所减少﹒耕地面积变化最大,由2010 年的49.09%减少至2017 年的27.96%,减少21.13%;草地面积由2.72%减少至0.60%;未利用地面积占比由0.88%减少至0.10%﹒林地、水域和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则出现增加,林地面积占比由20.29%增加至 23.72%;水域面积占比由 6.22%增加至9.79%;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增加最多,由20.79%增加至 37.84%,增加了 17.05%(见表 2)﹒

表2 2010 与2017 年杭州市规划区土地利用结构 %
分析发现,研究区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加较多,城市扩张现象明显,耕地面积严重萎缩;未利用地在原本低保有量的情况下继续减少,土地利用率持续增加,导致规划区土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严重影响杭州市区的持续发展,直到富阳市(2014年)与临安市(2017 年)撤市设区并入市辖区,这一问题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3.2 地类转换与影响因素
采用GIS 软件的相交分析方法,求得2 个时期杭州市规划区土地利用转换矩阵(见表3)﹒

表3 2010—2017 年杭州市规划区土地利用转换矩阵 hm2
在矩阵中,行表示期初年份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列表示期末年份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对角线表示未发生转换面积[21]﹒耕地的转换最为显著,7 年间大量耕地转换为林地、草地、城乡建设用地等其他用地类型,其中耕地向城乡建设用地转换面积最大,为63 848.88 hm2﹒由于城市不断扩张,大量分布于郊区的耕地被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占据,转变为建设用地;耕地转为林地是低丘缓坡综合开发、退耕还林、土地生态修复以及山区村庄合并等复合因素作用的结果[13]﹒在“旅游西进”战略下,杭州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将原有的环城游憩带进一步发展为“环都市休闲游憩圈”,继续实行生态保育,对林地面积增加有很大推动作用﹒同时,耕地也存在对其他地类的占用,且类型多样﹒林地、草地、水域、城乡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均有部分转换为耕地,其中林地、草地、水域和城乡建设用地转换为耕地的面积分别为 4 900.86,2 480.76,2 425.86 和9 054.00 hm2,未利用地转换为耕地的面积不显著﹒城乡建设用地的变化显著,来源多样,净增加面积为69 735.24 hm2,耕地对城乡建设用地的转换最为显著,转换面积为2010 年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的113.57%﹒土地利用规划中未针对水域面积制定指标,而在建设用地方面,2017 年的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125 952.12 hm2,未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126 900 hm2的控制指标﹒研究期内,研究区域处于扩张状态,城乡建设用地代替耕地成为该区域最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从空间上看主要以2010 年的建成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但扩张的主要部分在规划区东部的萧山区,钱江新城的逐步建成完善、地铁四号线的开通是2 大主要驱动因素,而西部虽有未来科技城的布局,城市扩张效应却并不明显,其原因除了出于旅游发展的目的而进行的生态保育与退耕还林,还有西湖景区和西溪湿地对城市扩张的阻碍作用,进一步证实了此前研究的结论[22]﹒研究期内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83.15%,相比之下,人口由434.82 万增加到493.99 万,增长了13.6%,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粗放状态﹒总之,新城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合力使研究区域的布局形态逐渐从环西湖的单中心格局向跨越钱塘江两岸的多中心格局转变[19],这也是杭州“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23]空间策略的执行结果﹒
水域的主要转出地类是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转换面积分别为2 425.86 和2 501.46 hm2,而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也存在转换为水域的情况,这说明水域的减少既有人为活动的影响,也存在耕地结构调整的因素﹒围湖填河和城乡建设用地的扩张对水域湿地等区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未利用地转换为水域说明杭州市在水域保护方面较为重视,城市建设对天然水体的占用较少﹒其他各类用地之间也存在相互转换的情况﹒
3.3 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景观尺度上,2017 年各类用地的斑块数量增加了59 045 个,而最大斑块指数则下降了3.091 8,说明整体而言,土地利用的景观集聚度在降低、景观优势度有所下降;斑块密度增加了17.651 9,意味着整体景观的破碎度增加较多,土地利用更加破碎化;同时,周长-面积分维数的数值增加了0.067 5,说明土地利用的景观形状变得更复杂,各类用地分界变得更模糊,整体景观的稳定性在降低(见表4)﹒可看出整个杭州市规划区的土地利用存在一定生态风险,景观破碎化和不合理的人工干预可能导致城市景观生态的恶化,但因各用地类型的景观格局指数评价标准存在差异,因此需在斑块类型尺度上根据不同地类进行分析﹒

表4 景观尺度上的景观格局分析结果

表5 斑块类型尺度上的景观格局分析结果
表5 所示为斑块类型尺度上的景观格局分析 结果﹒从表5 可知,所有土地利用类型的斑块数量和斑块密度数值都出现上升,但同时耕地、草地、未利用地的最大斑块指数数值出现下降,而林地、水域、城乡建设用地的最大斑块指数则出现上升﹒结合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所有地类的景观异质性都在增加,而在面积减少的同时,耕地、草地、未利用地的破碎度增加,呈现出愈发破碎化的趋势,土地利用集聚度和景观优势度也在下降,说明这3 类用地的景观生态存在恶化的风险;林地、水域、城乡建设用地的破碎度呈上升趋势,而空间集聚度也在增加,但由于这3 类用地的面积也在增加,因此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变化﹒
周长-面积分维数方面,除林地和草地分别下降了0.011 9 和0.040 8 外,耕地、水域、城乡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皆有所上升,即林地和草地斑块形状的复杂程度有所降低,表明林地和草地研究期内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受到的人工干预在减少,水域和未利用地受到的人工干预在增加﹒耕地与城乡建设用地需结合土地利用转换矩阵分析:大量耕地转为城乡建设用地,城市面积不断扩张是其周长-面积分维数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也表明大规模的城市化会导致土地利用格局趋于破碎﹒
4 结论
1)耕地、草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林地、水域、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耕地与林地、城乡建设用地之间的互动作用十分强烈,城市扩张效应显著,土地利用方式较为粗放﹒具体特点为耕地减少仍然可控;城市空间不断以东部为重心扩张,呈现出多中心的发展特点;土地利用方式较为粗放,城市发展精细化程度不足﹒
2)耕地减少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加主要由城市新区建设等开发性政策和退耕还林等保护性政策共同推动,其分布更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影响;林地的变化主要与城市游憩带规划、生态保护的需要有关,其空间分布也对城市蔓延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3)景观破碎化程度、异质性增加,景观优势度有所降低,土地利用更为平衡,但有生态安全风险﹒大规模的城市化和人为活动会导致土地利用景观的破碎度增加和稳定性下降,由于耕地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城市水体被侵占,建设用地集聚度增加,长远看会破坏生态廊道的连通,造成生态景观破碎化、生物栖息地的消失和生物多样性的削弱;另一方面,建设用地过度扩张会导致城市地表温度上升,加剧热岛效应,也会带来空气污染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