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床考
[日]藤田丰八
【关键词】胡床;踞坐;绳床;交椅;东汉灵帝
【摘要】通过对传统坐姿进行区分,确认垂脚踞坐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坐姿。胡床由东汉灵帝时传入中国,魏晋渐盛,隋唐在民间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不仅使用地点与床、榻有别,而且取独坐和踞坐为坐姿。1世纪前后胡床传入日本,传入途径可能并非由中国,而是直接通过东胡输入。宋人名胡床为交椅,故推想胡床为交腿折叠椅,初为革面,后改绳面,因而北朝、唐也称绳床,且可能带有靠背。折叠椅早于固定椅子由西方舶来中国,是因为游牧民族尚其便利,并由其传入中国。《补遗》根据胡三省所记元时实物定绳床为固定扶手靠背椅,胡床为折叠马扎,而板制固定椅子后出,仍袭用胡床的旧称——绳床为名。
一
古代中国皆用平坐,至少晚至东汉,中国人似皆用平坐,今之倚坐习惯未之有也。征诸古代文献,或观东汉所建孝堂山及武梁石室壁画,即可了然。尤其是画中表现的诸色人物,无一例为倚坐者。至于平坐之法,据古代文献所见文字,约略可别为“居”和“跪”两类,进而细分,则有“凥”“跪”“居”和“箕踞”四种。
“居”,依《说文》即蹲也。又同书“足”部曰:“蹲,居也。”换言之,“居”即今之“踞”字,也即蹲踞。《论语·宪问篇》:“原壤夷俟,……以杖叩其胫。”“夷俟”即蹲踞不出迎。“夷”也解作夷踞,据《后汉书·郭林宗传》可知。该传载茅容事迹,记其与同伴避雨树下之情形:“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此坐姿依段玉裁所述,为以足底触地或著席,臀部垂下,膝盖耸立【译注1】。
此种居即为蹲踞。然而被视为更不敬的,则是“箕踞”。《史记》卷九七《陆贾传》述陆贾出使南越见南越王尉他时的情状:“陆生至,尉他魋结箕倨见陆生。”其后尉他闻陆生说辞,“乃蹶然起坐”,谢之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此处之“箕倨”,《汉书》作“箕踞”,颜师古注之曰:“谓伸其两脚而坐。”然则箕踞者,即谓以臀及地或著席、两脚前伸,与蹲踞之别惟在两条小腿直立或是伸展。晋皇甫谧《高士传》“严光”条记侯霸受光武帝之命,遣属吏奉书于严光,其时,“光不起,于床上箕踞抱膝,发书读讫”。
蹲踞与箕踞,本通行之坐姿,惟中国古代有教养之士视其为不敬,故而受到排斥,此由上举诸例应可看出。士人使用的规范坐姿大致为“跪”或“跽”。《释名》卷三曰:“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倪也”,谓两膝著席、上体耸立也。而《说文》云:“跪,拜也,从足危声”,或当如段玉裁所疑,本作“所以拜也”【译注2】。《说文》于“跪”之外复有“跽”字,各本均作“长跪也”,而段玉裁改作“长跽也”。《史记》卷七十九【译注3】《范雎传》“范雎入秦谒秦王”条:“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索隐》曰:“跽,其纪反。跽者长跽,两膝被也。”此或段氏所本?跪与跽虽同样是将双膝一并触地或及于席,臀部上提躯体耸起,然跪为“首至于手”的拜姿,跽则未及拜也,故而可解何以名之曰“长跽”了。跽未及于拜,由范雎与秦王问答后“范雎拜,秦王亦拜”可知。跪与跽固然本义有别,但多作同义使用。此外,《毛诗》中与跪同义的文字是“启”,也即《小雅·四牡》中的“不遑启处”,《小雅·采薇》中的“不遑启居”与“不遑启处”,以及《小雅·出车》中出现的“不遑启居”。而《毛传》曰:“启,跪也;处,居也。”这些不过是文字上的异别,内容则一。再有,此等所谓之“居”乃“凥”也,“居”为其俗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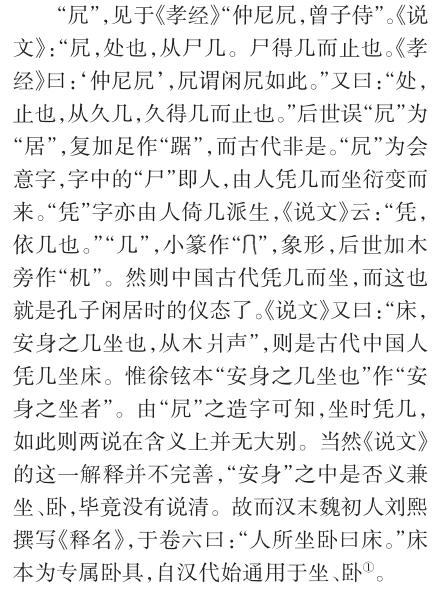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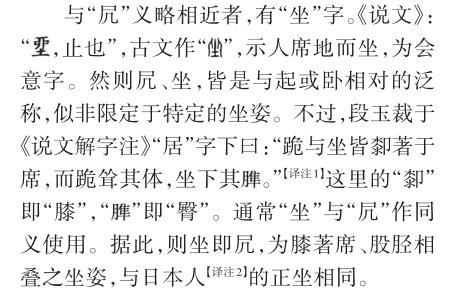
今观孝堂山和武梁石室画像,卑微者坐姿既有跪坐也有跪拜,如臀部落下,看上去与日本人的正坐无别;而尊者尚有盘膝坐姿,这在日本同样属于正坐。此种盘膝坐,于古代中国未见专名【译注3】,但就臀部著席一点来看,似应视作居或踞的一种①。此外与日本人正坐相同的这种形式,或谓之跪,或谓之跽,用表当下恭敬之意,持之久,臀部不得不落下,此自然使然,故而恭敬者取以为坐姿。前引《后汉书·郭林宗传》中“容独危坐愈恭”之危坐,当即此也。此外,同书卷七六《郭躬传》:“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其中的“端膝”亦应指此。很明显,同书《向栩传》中“常于灶北坐板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与《三国志·魏志·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高士传》“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所说的也是这种坐姿。此外,《晋书》卷六六《陶侃传》有“终日敛膝危坐”,《梁书》卷二三《长沙嗣王业传》述其弟藻之为人“性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即便在中国古代,这也被视作是正规的坐姿,此由《周书》卷二三《苏绰传》亦可断言,其文曰:“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
席为床上的坐垫。回顾《史记》,尉他闻陆贾说辞“蹶然起坐”,其所谓的“坐”当亦是此种正式的坐姿,而“仲尼凥”之“凥”,想來必也是如此。反过来,降及后世,此一坐姿遗风犹存。甚至到了清代,椅式坐姿已成主流,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二四中还提到:“今人虽不席地,而北方多用床上坐,谓之盘膝坐。此尚合古礼,不伸脚。若南人皆坐交椅,背及两手皆有倚,无不伸脚者矣。”
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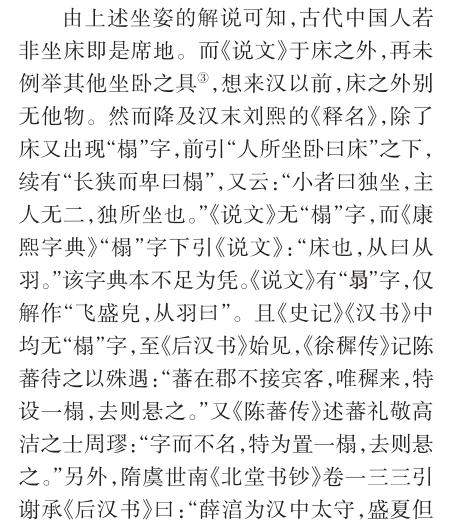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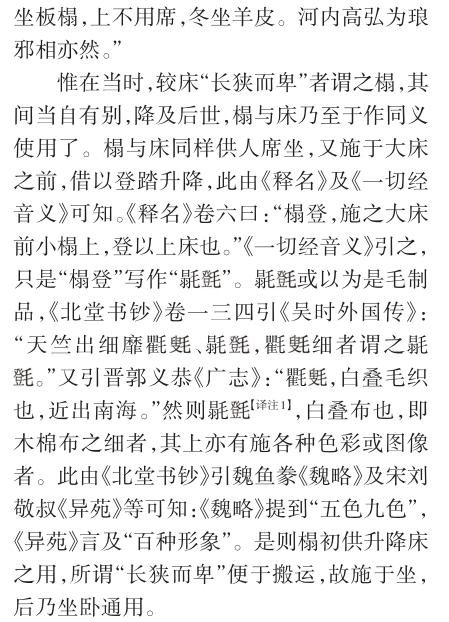
另外,《释名》谓:“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此谓小榻。前引《后汉书》卷八三《徐穉传》“特设一榻”,同书卷九六《陈蕃传》“特为置一榻”。而且榻不拘小大,皆与床供人席坐,但不用于后世的那种垂足倚坐。此由前引管宁和薛湻的例子即可鉴识。再如《三国志·蜀志》卷八《简雍传》有曰:“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可见其横卧榻上,对临他人。此固属特例,然据此等实例,榻之如何使用,当可大体想象。
惟与后世倚坐相近的坐姿,于特殊场合亦非没有。《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所言即是:“郦食其谓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此事又见于《汉书》卷一《帝纪》及卷四十三《郦食其传》,惟“洗足”单作“洗”。此处“踞床,使两女子洗足”,则“踞”非蹲踞也。颜师古注之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据。”是则臀部著于床上、两脚垂于床下。后代中国画家每每以此故事为画题,莫不绘作两脚垂于床下之状。毋庸赘言,此处谓之“踞”当就臀部着于床而言。再有王充《论衡》卷二六《实知篇》:“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亡。其后,秦王兼吞天下,号始皇,巡狩至鲁,观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此固不过是附会传言,但似可作东汉仍以踞为非礼坐姿的证据。他如《晋书》卷三八《平原王幹传》:“(齐王)冏既辅政,幹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床,不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儿。其意指(赵王)伦也。”同书卷九一《刘兆传》亦见:“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延世(兆字)。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既进,踞床。”若以“著靴骑驴”观想,则刘兆之访客乃著胡服者也。两处所谓“踞”,当即据床垂脚而坐。此外,《晋书》卷九五《王嘉传》又可见:“下马踞床,一无所言。”据下马推之,王嘉所著似仍为胡服。再如唐人小说《虬髯客传》:“隋炀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杨素守西京。素骄贵……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李靖谒之,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
总之,自晋代起,踞床的例子渐多,但我以为这大概并非是由本文将要提到的胡床所带来的影响。而且在当时,床、榻通常为平坐器具,即便以为上述踞床皆是垂脚坐姿,那也应将其视作为数不多的特例①。
三
众所周知,魏晋以降的历代史籍中,于床、榻之外,坐具中又见胡床。如其名所示,此当为舶来之物。《后汉书》卷二三《五行志》曰:“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饮、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此条似以东汉应劭《风俗通》为据。《太平御览》卷七〇六“胡床”条下引《风俗通》:“灵帝好胡床,董卓权胡兵之应也。”“权”当“拥”之伪误,且似为《风俗通》之节录。今传《风俗通》本已残缺,《隋书·经籍志》谓三十一卷,现仅存十卷,且此十卷似亦不完整,故今本《风俗通》未见其文,而原本或确有此条。可见东汉灵帝(168—188)时,胡床已用于宫掖,而京城贵戚皆竞相效颦。应劭与灵帝为同代人,故当可确信。
然而《晋书·五行志》云:“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宋书·五行志》文字略同,惟“泰始”前冠“晋武帝”三字。《晋书》纂于唐代,《宋书》由梁沈约撰述,自不待言,而两书似皆本于晋干宝《搜神记》,其书卷七:“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太始”,西汉汉武帝之年号。惟此“太始”与晋武帝“泰始”年号同音而致伪误,其由《晋书》《宋书》可知。又文中有“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戎翟乱华事在晋朝,与汉无涉,故而略无疑义。然则胡床自泰始以来为中国相尚,而所谓“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是晋人述本朝事,想来大致不误。
应劭及《后汉书》,干宝与《晋书》《宋书》,虽所传抵牾若此,然大致仍可疏通:东汉灵帝之际,胡床始入宫掖,在贵戚间使用;晋武帝泰始以来愈益兴盛,行之于贵人和富室之家。实则除《五行志》外,《后汉书》不见胡床,其名于《三国志·魏志》中却已可寻。如《武帝纪》“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条,记曹操西征与马超相拒于潼关的故事,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同书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潜为兖州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又《北堂书钞》于上条之外,更引《魏略》:“苏则从文帝行猎。槎桂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则谏乃止。”《三国志·魏志》卷十六《苏则传》亦载此事,文字略同,惟“槎桂”作“槎桎拔”,“床”前也无“胡”字;不过何焯以为宋本“床”前有“胡”字。然则胡床于灵帝时进入中国之说固可凭信,至少献帝朝曹操已用。换言之,将胡床进入中国的时间断在公历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应是恰切的。
四
然而胡床究为何物?其施于坐固明,惟其采用何种坐姿?吾辈于此不惮其烦,将史传中所见胡床用法,胪列如次。
以吾辈所知,三国时代不过上述三例,入晋则证据稍多。
其一,《晋书》卷四二《王浑传》附子王济事迹,其中可见:“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济请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恺亦自恃其能,令济先射。一发破的,因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更而至,一割便去。”
其二,同书卷六五《王导传》亦附子王恬事迹:“性慠诞不拘礼法。谢万尝造恬,既坐,少顷恬便入内,万以为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头散发而出,据胡床于庭中晒发,神气慠迈,竟无宾主之礼,万怅然而归。”此事又见于《北堂书钞》卷一三五、《艺文类聚》卷七〇,文字稍有异同,且载作“郭子曰”,意《晋书》约取自于《郭子》。《隋书·经籍志》曰:“《郭子》三卷,东晋中郎郭澄之撰”,今惟有玉函山房辑本,原书无传。
其三,《晋书·戴若思传》:“少好游侠,不拘操行。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据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
其四,《庾亮传》云:“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竞坐。其坦率行己,多此类也。”
八
至若西方,椅子起于埃及,希腊、罗马等国古已有之,罗马人使用的官座型椅子(curule chair)不过是其中一种。若椅子是从此等西方国家舶来,不知何故,最先进入中国的却似是这一型的椅子。近年,斯坦因在突厥斯坦发掘出普通型的椅子和扶手椅,虽时代不明,但也应相当地古老。官座型椅子(curule chair)何以会早于普通型的椅子和扶手椅,最先进入中国?倘若承认胡床西来,那么大概任谁都会对此抱有疑问。
设以此型椅子经由塞外游牧者为媒介输入中国,则此疑问或即涣然冰释。curule本是拉丁语currus——车辆的衍生词,因其便于车载搬运,故得此名。然则于中国塞外逐水草移徙、惯于骑乘的民族而言,此型坐具既便携又无须屈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继而传入中国,其本来属性亦未丧失,故而施之于军阵、行旅。作为裴潜廉洁的例证,《魏略》载:“及其离任,未持胡床而去”,倘非便携之故,此等记事便无从措意。
要之,胡床,即官座型椅子(curule chair),其初传中国乃假塞外游牧者之手。另一方面,若做此解说,则该型椅子之东来即变得顺理成章,了无滞涩之感。
及此再就“机”“桌”附识一言。如前述及,“几”本坐时人所凭倚之物,而“机”原作木名。《说文》曰:“机,机木也。”《山海经》“单狐之山有机木”即是,与几席之“几”本无瓜葛。然而“机”字陡现于《三国志·魏志·华歆传》①,王鸣盛据此以为几在制作上出现了变革。所谓《华歆传》中的“机”字,见于魏明帝【译注1】谕歆的诏书,作“机筵”,文字连言,与“几筵”略无异同。不管怎样,“机”字用于“几席”肇始于此。机和几的制作和用途于魏晋间似乎渐显变化,《晋书》卷六二《张华传》“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又同书卷六二《刘琨传》有“宾客满筵,文案盈机”。然则其时,机与仅供倚凭的几相揖别,用于承载书籍文案,其形制似较几增大。惟当此之际,供人席坐的正规之具仍是床、榻,故窃以为机在制作上当无太大的变化。
然隋唐以降,胡床盛行,遍见于人家之中。及入唐末五代,与胡床有别的椅子得以应用,机之外出现了“卓”“棹”“桌”等字。至于宋代,世俗间称椅为“椅子”、卓为“卓子”②,故而机之形制不得不增大,或最终导致了供八人同坐共食的八仙桌的出现。
*《胡床考》及《〈胡床考〉补遗》,皆采自1943年荻原星文馆出版的《东西交涉史研究——西域篇及附篇》。该书由池内宏编定。作者藤田丰八(1869—1929),日本东洋史学家,南海史、西域史学家。民国时期,杨炼选译了他的《东西交涉史研究——西域篇及附篇》一书,以《西域研究》为题,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惜未录此篇。
【译注1】《说文解字注》699页:“若蹲,则足底著地,而下其、耸其厀曰蹲。”凤凰出版社,2007年12月,后文同。
【译注2】《说文解字注》144页:“‘拜,首至手也。按,跪与拜二事,不当一之,疑当云‘所以拜也,后人不达此书,‘所以往往删之。”
【译注3】原文作十九,非。
①虽曰东汉床始用于坐,但不能说西汉绝无。如《汉书》卷六十四上《朱买臣传》即是。该传记买臣怨张汤之由:“汤数行丞相事,知买臣素贵,故陵折之。买臣见汤,坐床上,弗为礼。”此为原文注,后文同。
【译注1】“跪耸其体”则臀与上身皆直立,“坐下其”似指臀部著于小腿上。
【译注2】“日本人”前原修飾“我们”,略去。后文同。
【译注3】似即跏趺坐或趺坐,但此名在中国或后起。
①或即夷或夷踞?《后汉书》章怀太子注,夷踞之“夷”解作“平也”。
②《高士传》汉魏丛书本中,“箕股”作“箕踞”。
③几、帷、枕、筵、箦附属物除外。
【译注1】原作“氍”,误。
①关于汉高祖踞床之“踞”,或以为无妨视作蹲踞(踞床洗足,又见于《汉书·黥布传》),但此说似不妥帖,故颜师古将其注作“据”。尤其是《汉书》卷四十《张良传》:“从东击楚,至彭城。汉王兵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此处之“踞”当视作“据”而非蹲踞。再有同书卷五十《汲黯传》记武帝敬惮汲黯之状:“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视之。丞相弘宴见,上或不冠。至如见黯,不冠不见也。”这里的厕,如淳以为“溷也”,孟康解作“床边侧也”。颜师古以“如说是也”,而刘奉世奉孟说为圭臬,予亦思孟说至当。不论孰是,此处之“踞”断非蹲踞之义。
①然北朝《周书》、南朝《陈书》不见。
①《旧唐书·刘文静传》“共榻”改作“共食”,然则与文静言论难相契合。
【译注1】此谓前后偏,非偏于左右也。
②此一坐姿,敦煌千佛洞造像中亦多有实例。
【译注1】原文为“我国”。后文同。
【译注2】日文中的汉字写法。
【译注3】第三节末谓:“将胡床进入中国的时间断在公历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应是恰切的”,那么作者似又以为,胡床进入日本早于中国,作者的观点不很肯定。
①《说郛》陶刻本中,“敌制也”作“乃〇〇所制”。
【译注1】原文作《释名》,误。
【译注2】原文脱“管宁”。
①《太平御览》卷一二二“陈义郎”条下。
②“文斜”之“斜”,《太平御览》鲍刻本作“邪”,而《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庾度支集》作“斜”。“邪”与“斜”相通。司马相如《上林赋》有“邪与肃慎为邻”句,颜师古以为:“邪读为斜。”细思,庾肩吾诗或本作“邪”字,而后人改为“斜”。虽则我在本文中将日本式之正坐,即中国之危坐、端膝、敛膝,与“孔子凥”之“凥”视同,然其间仍多少存有疑问。“凥”为人凭几之义,但身体下半部的姿势不明。若以其为闲居之态,或未必即是日本式的正坐。特别是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有云:“吴王懼然改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据此可知,危坐至少当去几。然危坐与跪用作同义,故危坐意即跪,则孔子闲居之“凥”,想来似亦无妨视作日本式的正坐。总之,我所举为坐姿的凥或坐,均带有日本式正坐之意味,惟望对“凥”字的理解,务必不要拘泥于其本义。
③行于猿乐。
④僧侣等人用之。
【译注1】这里的床木和折叠椅,即中国人常素所说的马扎与交椅。
【译注2】古罗马最高级别的民事官员坐的腿部为弧形的装有垫子的椅子,可折叠,无靠背。
⑤如“却行”之“却”。
⑥仰卧。
【译注3】李濯凡注的《古事记》是以岩波书店的《古事记》、小学馆的《古事记》和仓野宪司校注的《古事记》为底本,该书此处作“天若日子寝朝床”(70页)。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邹有恒译《古事记》亦作“朝床”(41页)。但明治七年(1874)发行、由中西忠诚和内藤傅右卫门、坂田铁安所撰的《假名古事记》却作“胡床”,并注音あぐら(12页)。明治三十年(1897)出版的“国史大系”《日本书纪》卷二提及此事,只说:“其矢落下,则中天稚彦之胸上,于时天稚彦新尝休卧之时也,中矢立死”(43页),未及寝具。故此条史料存疑。
附:
《胡床考》补遗
予尝以《胡床考》为题,在《东洋学报》第十二卷第四号上刊载过一篇小文。其原本是为“东洋史谈话会”准备的讲演稿,故极不完备。文中虽以诸史所见胡床的用法和用途为据,并引证庾肩吾的诗句,将该种坐具断为官座型椅子(curule chair),然仍颇显含混,惟至今仍信持不移。顷者偶阅《资治通鉴》,读胡三省之说,益觉其可信,故借同好文末余白,绍述如次。
《资治通鉴》卷二四二《唐纪》:穆宗“长庆二年(822)十二月辛卯,上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云云。胡三省注引程大昌《演繁露》:“今之交床制,本自虏来,始名胡床,隋以谶有胡,改名交床。唐穆宗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群臣,则又名绳床矣”,继之曰:“余按交床、绳床,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床以木交午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而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绦,使之可坐。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午,故曰交床。绳床以板为之,人坐其上。其广前可容膝,后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阁臂,其下四足著地。”对此类胡床——即交床解说之精密,似为他处所不见。如此,则谓其交床的理据明矣。而胡三省以板制、后附靠背、左右带托手者为绳床,此固扶手椅也,制作与胡床或交床迥异。三省以目见为凭,其说当大致不误。然而此不过是元时论调,至若北宋以前,据绳床之名,考以宋王观国《学林》和宋程大昌《演繁露》的观点,交床座面用绳,故立绳床之名,其说也无不妥。故而予今仍信,胡床本以革制座面,后更用绳,故有绳床之名。即如此,座面用板、附带靠背、托手的纯粹的扶手椅,何以入元却用绳床相称?倘以三省之说不误,则除以此类扶手椅袭用交床别名——“绳床”这一古称而外,似再无旁的解释。换言之,当时既有古老的折叠椅,亦见板制座面的扶手椅;前者已具交床之名,而后者为与之别,故假交椅别称,名之曰绳床;除此,当无可解说。
大正十三年(1924)二月二十七日
〔責任编辑:李琳〕
①王氏《十七史商榷》卷二四。
【译注1】原文作“后汉明帝”,误。
②方以智《通雅》。
——胡床与文化适应现象
——李白《静夜思》误读辨正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