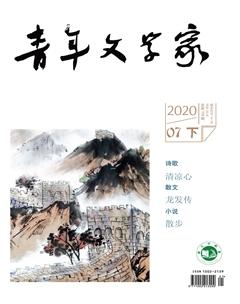小说中人物塑造双重脉络的相辅相成
摘 要:迟子建是一位黑龙江籍女作家,在她的小说《晚安玫瑰》中以俄罗斯风情浓郁的哈尔滨市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身世离奇的女子在寻父又杀父的过程中发生的一段人间悲欢。在这部作品中,迟子建在这部作品中每塑造两个人物,都会用两种不同的故事脉络联系起来。看似不同,又仿佛双轨并行般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凸显作品想要表达的观点。这种颇具特色的写作手法使得人物塑造更加鲜活深刻,让作者表达的观点更加完整清晰,值得借鉴。
关键词:人物塑造;双重脉络;相辅相成
作者简介:张园(1980.12-),女,满族,辽宁省锦州市人,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1-0-02
一、凉生枕簟泪痕滋——两个扭转人生的“弑父”故事
这部作品中有两个身世曲折的女性主要人物角色:赵小娥和她的房东吉莲娜。一个因为对利益的贪婪,而牺牲女儿爱情、出卖女儿被下了砒霜毒杀的继父;一个因满足私欲,造成母女凄惨人生的强奸犯,被逼跳河的亲生父亲,他们都是因为自私伤害了女儿,从而被复仇。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周丽娜在《“弑父”的玫瑰:一个崭新的两性故事——评迟子建新作<晚安玫瑰>》认为吉莲娜和赵小娥的复仇都源于男权施加于她们身上的巨大屈辱,“弑父”则是摆脱屈辱的方式和选择。继父与生父带来的伤害,影响了她们的婚恋观和生活方式。[1]
作品中塑造的两个本毫无关联的女性人物,她们身世的秘密相伴而生。不同的是,赵小娥没有忏悔之心,在吉莲娜眼里是“看不到另一个世界的曙光”的表现;而吉莲娜认为自己的弑父行为是洗刷自我的罪恶,见到小林扮的摩西,坦然离世。赵小娥的弑父行为使她童年的噩梦有了一个了断,可真正实施之后,她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直到吉莲娜离开之后,她意外得知了吉莲娜的遗嘱,才对父亲产生了忏悔。[2]
两个有着极其类似的经历的女性,秘密的共享让她们的心灵再一次靠近。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王海文在《弑亲者的迷失与救赎——论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和<晚安玫瑰>》中认为,弑父行为代表着女性对父权的一种反抗,无论是吉莲娜的继父或是赵小娥的生父,在她们人生的初期阶段都是“缺席”的,这种缺席对情感的维系造成了一种隔阂和割裂。[3]不同的是吉莲娜怀着忏悔之心将这段痛苦的往事藏于内心,而赵小娥却从最初的痛快到后来的自我折磨,始终无法摆脱罪恶。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张洁在《冰雪世界中的血色玫瑰——浅析迟子建<晚安玫瑰>中的女性形象》中认为吉莲娜的弑父罪恶在宗教关怀下得到救赎,赵小娥复仇的罪恶却成了她的煎熬。[4]虽然作者不吝强调宗教的力量,但内心的力量与观念的不同才是两位女主不同人生态度的主要原因。
二、花褪残红青杏小——两段向现实投降的爱情
在赵小娥遇见真爱齐德铭之前,作者交代了她的两段爱情,一个是她在大学时代的初恋——陈二蛋,一个是工作后认识的宋相奎。不管是淳朴实在的大学同窗,还是貌不惊人的宋相奎,他们一边喜欢女主,一边选择向现实低头,选择了家里认为的能生娃的女人和在哈尔滨本地有房子的哑女。两次失败的爱情,让赵小娥渴望关爱的心越来越冷,让她对后来偶然邂逅的齐德铭无比地上心,而齐德铭的猝然离世自然也对她的打击十分刻骨。
三、重泉一念一伤神——两种面对死亡的人生态度
小说中对于死亡的描述贯穿了作者对于死亡的态度,而作家在作品中往往又融合自己人生经历所造就的观念,比如迟子建因为在现实中丈夫的猝然离世,她对于死亡的描述既向往平和地接受,又无法摆脱突如其来的极端恐惧。这种心态在小说中塑造的两个人物形象齐德铭和吉莲娜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齐德铭作为一个经常需要出门在外的销售工作者,作者交代他的母亲是因为照顾病重的爷爷而累得猝死,齐德铭的父亲意外入狱多年来一直怀念他的母亲,并且有着很多怀念的方式,比如清明供奉红皮蛋、插柳枝,七月十五放河灯、撒玉米粒,用这种方式让齐德铭也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母爱的缺失和父亲跌宕的人生让他对死亡有着偏激的恐惧,又似乎在平静地时刻准备迎接它的到来。为此,他在行李箱里备了一件寿衣,可是当赵小娥提问万一发生事故,和寿衣一起灰飞烟灭,该怎么办的时候,齐德铭暴怒的反应正说明他对于死亡的恐惧。
而吉莲娜对于死亡比齐德铭多了更多的淡然,即是多了几十年人生的赐予,又和她的宗教信仰有关。她经常阅读犹太经书,并向赵小娥描述她心目中的神——摩西。当赵小娥向吉莲娜讲述梦境中见到的摩西形象的时候,吉莲娜的惊呆也证明了她对此更加深信不疑。因此她找好律师,立了遗嘱,对身后事做了详细的安排。人生的阅历和年岁的增长给予了吉莲娜面对死亡而具备从容的力量,她坚信死后有另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镯耳在《读迟子建<晚安玫瑰>有感:一个为精神而活着的人》中认为,吉莲娜是一个为精神而活着的人,她是一个经历非凡的岁月老人,是一个有信仰的女人,是宗教和爱的力量驱散了她心中的阴霾。景德镇陶瓷学院的何芹、李新青在《救赎与皈依——评迟子建的中篇小说<晚安玫瑰>》中认为,小说背后蕴含的精神世界和宗教问题显得格外沉重和发人深省。所以,吉莲娜的面对死亡的淡定态度,较之齐德铭极端,她的力量源泉除了岁月带给她人生的洗礼和丰富阅历之外,就是宗教的力量。
四、一寸还成千万缕——两段失去真爱的经历
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赵小娥与吉莲娜都有着遇见真爱又失去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对她们两个人的人生都造成无比巨大的影响,前者终身未婚,后者发疯进了精神病院。
吉莲娜的余生都在用仪式感纪念与之相爱的苏联外交官:别胸针、梳辫子、去马迭尔用餐,即便唯一的真爱没有失而复得,她却一直沉浸懷念。而赵小娥面对真爱的失去,虽然没有像吉莲娜那样贯穿了一生,但也给予了她致命的打击:“觉得这个世界一下子变得漆黑”、“走在平坦的街路上,我却有跋涉在泥泞中的感觉”、“三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夜凉如水时,我浑身燥热,而阳光灿烂的正午,我却冷得打寒颤。”[2]这些刻骨的感受来自于作者丈夫猝死的打击,她把自己突然失去爱情的感受用于对女主的内心刻画,生动而精准,读来真实感刻骨。行超在《迟子建中篇小说<晚安玫瑰>:两个女人与一座城市》中认为,吉莲娜再没有爱上过任何一个人,但她却始终保持着自己年轻姑娘般对美的热爱,像玫瑰一样美丽;而赵小娥的爱情更加接地气,象征了玫瑰的梨刺。
文中两处巧合略显牵强,一是赵小娥在齐德铭父亲的工厂里偶遇亲生父亲,也就是她眼中造成她母女悲剧人生的强奸犯穆师傅,就这样刚好出现;另一处是齐德铭的父亲又恰巧是她闺蜜黄薇娜的情夫,报复性出轨的对象竟然就恰巧是赵小娥男友的父亲。这两处巧合虽然将文中人物都贯穿起来,但不免让人觉得过于牵强,为了巧合而巧合。
总体而言,迟子建的这部作品细腻而真实地展现了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爱情、亲情、友情状态,并且贯穿着人道主义与宗教主义情怀,双轨并行的故事叙述也是手法的巧妙之处,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周丽娜.“弑父”的玫瑰:一个崭新的两性故事——评迟子建新作<晚安玫瑰>[J].文艺评论,2013,(9):93.
[2]迟子建.晚安玫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43.
[3]王海文.救赎与皈依——弑亲者的迷失与救赎——论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和<晚安玫瑰>[J].文教资料,2018,(8):22.
[4]张洁.冰雪世界中的血色玫瑰——浅析迟子建<晚安玫瑰>中的女性形象>[J].名作欣赏,2015,(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