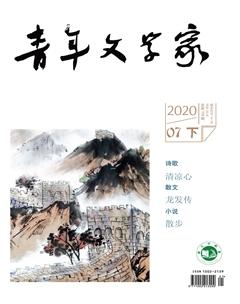《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解读
王文兴 金雨
摘 要:徐坤的女性题材作品大多以律师、教师、记者等职业知识女性为主人公。这些女性涉及很多中上层行业,她们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就是一般人说的“优秀女性”,他们跟一般女性比起来,无论从事业和生活哪一方面来讲,都是更具竞争力的一方。不仅在竞争力方面胜于一般女性,她们烦恼的也不是生活在的琐碎问题(例如温饱),而是情感、事业理想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等精神层面的东西。
关键词:徐坤;知识女性;精神困境
作者简介:金雨(1997.2-),女,汉,重庆人,长春理工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作家作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1-0-02
徐坤曾在一次访谈中说:“知识妇女也要为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付出代价。《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不同于徐坤以往作品中的调侃和嘲讽,具有自传化色彩,可以说是温情的“疼痛感”写作。在《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徐坤以毛榛这一知识分子女性视角出发,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为中心建构作品,直面女性生存的社会现实。小说通过对知识女性情感历程的书写,揭示出这一女性群体的精神困境,而需要注意的是小说还通过主人公“撕心裂肺”的三段情感经历,代表徐坤希望建构的一种女性意识——健康的、自由的、积极的当代女性意识,以及女性在追求爱情和婚姻中的平等、真诚的理想。
爱的本能与自我实现的矛盾
女性主義学者西蒙·波伏娃说过“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1]在这部小说中,徐坤将自己的感情经历与思考融入其中,探究现代社会中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破裂的原因以及两性关系中潜伏的情感破灭因素。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是“男主外,女主内”,即便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步入社会的女性增多,可是这种传统依然存在:男性习惯无论多晚回家,家里总有亮着的灯光与温热的饭菜,女性将家庭当做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一切都维系于家。而当一部分女性开始勇敢迈出家门,成为独立、自尊和自立的现代女性之后,又有新的矛盾出现,追求事业与理想必然有对家庭的牺牲,而成功的女性也会渴望情感的满足。在《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主人公的情感危机酝酿于90年代,这是一个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时代,所以人们都不得不选择投身其中,以免自己被淘汰。毛榛和陈米松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经过十年相濡以沫之后在外人看来应该是幸福的,可是他们却用陈米松的一封信作为诀别。
我走了,这 10 年是我永生难忘的 10 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彼此最相知的人,也是最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后我想也依然会如此。
但理智告诉我,我们不会是完美的婚姻……
我必须得走了,如果再在你面前强取欢颜,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2]
世纪末,毛榛决定考博,“因为她们那种科研单位里,像她这个年纪的,都在纷纷考博”,而且她周围的人都是“一考一个准”,这就更增加了她的压力,陈米松则要在短期内写一本完整的海峡对岸出版史。从前家里恩爱和谐的氛围变了,变得紧张与焦虑,两个人甚至顾不上说话,各干各的。基本的交流已经消失,睡觉“背对背”,直到最后的离婚连聊聊的方式都没有,陈米松用一封信通知毛榛离婚……
他们的爱情以及共同组建的家庭不是奴役女性的工具,但确确实实地失败了,毛榛也希望爱情与事业的同等成功,所以她仍不断地寻找爱情,即使屡屡失败,却依然满怀期望。爱情与事业无法两全其美,家庭一步步走向破碎,虽仍还期待着爱情,但是每次事业带来的喜悦也无法弥补感情失败带来的痛苦。毛榛并没有像张辛欣的作品《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女售票员一样为了工作不得不将自己“雄性化”,变得和男人一样大声吆喝,不让别人觉得自己好欺负,成为异化的“中性人”;她考虑的是自己的独立人格,自己作为女人不依附于丈夫,即使丈夫已经事业有成,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摆脱琐碎平庸的生活,实现更高一步的职业理想。她选择了不以家庭为中心,但同时她为了女性原始的情感渴望也会做出牺牲,夫妻之间的关秀冷淡,最终导致离婚,在这里她作为女性最纯粹的幸福感消失,于是她陷入新的困境。小说中的毛榛,可以说是一群现代化大潮中知识分子女性的缩影,在光鲜的外表下,只是一个经历一系列情感挫折之后迷茫与脆弱的落寞背影。
矛盾产生的精神困境的思索
中国古代,对一个女性最高的评价是“贤妻良母”,贤妻良母的整体意思是对丈夫是百依百顺、温柔贤良的;对子女是呵护有加的;对整个家庭是尽职尽责的。但“贤妻良母”中丝毫没有女子对自己的评价,可以说古代对女子的要求只体现在对家庭上,不提女子读书上进、求取功名,更别说是保家卫国,唯一对女子的评价就是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无需有才华,学习了知识便有了自主意识,可能就离“贤妻良母”更远一步了。“五四”运动中一些女作家吹响了冲破封建社会藩篱的号角,她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对“人”的探寻,但是这里的“人”是没有性别的人;到八九十年代作家们直面女性生存的社会现实,以新鲜的女性声音与犀利的笔触与男权文化对抗,例如林白、陈染、张辛欣、张洁等作家不仅对女性内心的独特体验与渴望进行书写,还书写知识分子女性群体在面临自我实现与情感之间的困惑。新时期的很多女性主义作品也表现女性在实现自我价值之后失去婚姻和家庭带来的情感缺憾。90年代步入文坛的徐坤继承了二十世纪女作家共同创造的女性人文主义脉络,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她在继承这些女作家们对自我实现与家庭角色无法统一的困惑时,她没有走向女性自恋,沉溺于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书写,也不向男性屈服而是保持理性,直面残酷的社会现实,书写中国当代女性命运,真实地再现知识分子女性群体在面对事业与家庭、情感与理性、理想与现实的无奈。就像她本人说过:“男性与女性应该同时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不光有男性粗粝、坚硬、喉结上下窜动翻滚的声音,这个世界是男女共存的世界,还有女性那纤柔、细腻、充满弹性与质感的声音于无声处坚忍不拔地响着。”[3]
小说中陈米松说他想要离婚的原因是:“婚姻就像是鞋子,这鞋子穿在自己的脚上,舒不舒服也只有自己的脚趾头才知道。”显而易见,在婚姻中即使是比一般女性优秀的毛榛也在老公觉得婚姻这个“鞋子”不舒服的时候被抛弃。毛榛曾经为了这份爱情与父母彻底决裂、两地分居、远离家乡……他们也曾有过不计其数的甜蜜瞬间:无数夜晚的长途电话、想马上见到爱人的路途颠簸、教工宿舍里的甘之如饴……这一切都在陈米松的一封信中彻底结束。毛榛在婚姻破裂之后曾想过自杀,但是想到父母也就放下,心里的爱最终没有让她放弃。后来遇到导演庞大固埃,庞大固埃曾经也给她带来过久未有过的爱情的愉悦与幸福,但好景不长,她发现他只是和她在做性爱的游戏,她再一次选择离开。第三个男人是汪新荃,如果说前两个男人让毛榛还怀着爱情的冲动,汪新荃对毛榛来说只是医治她爱情受挫之后的药,于是放弃。但她心里是明白的一个人是寂寞的,庞大固埃和汪新荃不能和她做长久的伴侣,而陈米松,虽然她依然爱他,但是这份爱只能是乞求,她也做不到。那些事业的风光背后也需要有两人的恩爱加持,所以她依旧耐心等待那个人的出现……徐坤在这篇小说中对于男女平等的解构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毛榛与陈米松相恋时无论做什么事陈米松都是绝对的权威,他们共同生活在教工宿舍时毛榛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变成“陈米松他媳妇”、“陈米松他爱人”;在与庞大固埃相处时毛榛与他见到熟人,他也不会主动介绍,他身边的朋友也不会好奇毛榛的存在。可以说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由男性定的。
在小说结尾,毛榛在一次次的爱情失败之后并没有陷入绝望,而是用一句“爱人啊,不要不告别就走啊,衷心祝福你有个好的前程……”她原谅了陈米松,这时候的毛榛是成熟的,笑着回忆起以前不敢回忆的甜蜜往事,虽然仍存爱意,也成熟地选择离开期待另一份爱情。徐坤通过主人公毛榛表达了她自己对现代知识女性在面临事业与感情时产生的困惑,探寻现代都市人两性和谐相处的方法。当代的知识女性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自己的工作,她们拥有了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是爱情和家庭仍然是她们割舍不掉的一部分。徐坤正视当代知识女性在面临这些困境时的无奈,用冷静理性的态度将这种现实融入自己的理解,认为女性文学并非以女性话语完全代替男性话语,而是应该支持两性的和谐对话。实际上,《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毛榛的最后的谅解就体现了徐坤对于两性关系的理性反思,当伟大的爱情离开的时候,不是一味地歇斯底里,而是勇敢地道一声“珍重”,不仅是对感情另一方的宽容,也是对自己的真诚,真诚地面对以后的生活。
作为一名学者型的女作家,徐坤没有沉湎于完全地反叛男性话语和进行女性自身经验与身体的书写,她用冷静理性的态度审视当代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用人文主义情怀烛照俗世中的男女。徐坤的作品不像90年代很多女性主义作品中对性或者男性话语的肆意颠覆,而是注重表现与男性生命体验不同的女性在事业与家庭、自我与现实之间的困惑和无奈以及对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期待。
注释:
[1]西蒙 ·德 ·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167.
[2]徐坤.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9):158.
[3]徐坤. 因为沉默太久[N].中华读书报,1996(2):3.
参考文献:
[4]黄瑶.女性文学“新视界”:徐坤小说创作新论[D].重慶师范大学,2012.
[5]潘柳园.论徐坤小说的世俗关怀[D].湖南师范大学,2014.
[6]隋东风.旷野上的碎片: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读徐坤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6(3):39-46.
[7]侯磊,杨莉.论徐坤的知识分子小说[J].山东大学学报,2011(3):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