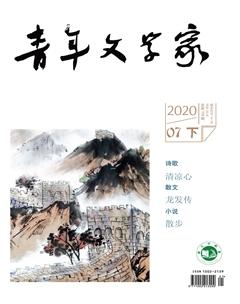论臧懋循对元杂剧《陈季卿悟道竹叶舟》的改编
摘 要:本文在立足于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比分析明代臧懋循编《元曲选》对元杂剧《陈季卿悟道竹叶舟》(简称《竹叶舟》)的改编较《元刊杂剧三十种》本在舞台提示、曲牌、宾白、唱词等方面的变化,揭示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说明《元曲选》的改编对整部作品的整体立意、主题表现、舞台演出和人物塑造方面的得失。
关键词:《竹叶舟》;《元刊杂剧三十种》;《元曲选》
作者简介:蒋文正(1996-),男,汉族,山东德州人,研究方向:宋元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1-0-02
一、《竹叶舟》基本情况介绍
《陈季卿悟道竹叶舟》是元代范康所作的一部神仙度脱剧,这种度脱剧大量产生于道教思想盛行的元代。剧情主要是对神仙生活的描写,剧中主人公多为天赋异禀具有良好修仙根骨的凡人,经过尘世的一番洗礼,经神仙指点顿悟,由对世俗生活的留恋到最后决心求仙抛弃俗世生活。《竹叶舟》的剧情也大致如此,但其故事原型最早却可见于《太平广记》所引唐代李玫《纂异记》。[1]今本《元刊杂剧三十种》中题为“ 新刊关目陈季卿悟道竹叶舟”[2]。明代臧懋循所编《元人百种曲》(《元曲选》)收入《竹叶舟》,并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整理、改编。臧氏对《竹叶舟》的改编虽然较好地保存了故事的原貌,但是从一些方面也显示了与元刊本相比不同的面貌。今就《元曲选》对《竹叶舟》的改编进行细致梳理分析。
二、臧本对元刊本《竹叶舟》的改编内容
笔者主要通过元刊本和《元曲选》本在剧本结构、音乐结构、演出结构、人物出场下场方式、科白、曲词等方面来对比两个版本《竹叶舟》的不同。首先看剧情形式方面,元刊本题目作“吕纯阳显化沧浪梦,陈季卿悟道竹叶舟”;臧本作“吕洞宾显化沧浪梦,陈季卿误上竹叶舟”。二者皆突出主要剧情和剧中主要人物,剧情虽大致相同,但元刊本显然更注重主人公的“悟道”经历,臧本则将主人公的主动悟道改为被动地误上竹叶舟,暗中隐含了对道教求仙修身的怀疑和讽刺。
其次在剧本、曲词和宾白方面,臧本对元刊本也进行了改、增、调、删等一系列动作。[3]详细来看,元刊本一本四折,无楔子。第一折正末(吕洞宾)唱仙吕宫一套,第二折正末(列御寇)唱双调一套,第三折正末(吕洞宾化作渔翁)唱南吕宫一套,第四折正末唱【节节高】、【元和令】、【上马娇】、【游四门】、【胜葫芦】、【幺篇】、【后庭花】、【柳叶儿】八支曲子,不入套内,之后正末唱正宫一套。而全剧基本只有正末和外末有科白,其余角色几乎没有科白,只是提示“云了”。而臧本在一本四折的基础上增加楔子,扩充了文本内容和信息量,并且为剧中主要人物、次要人物补充大量的宾白,完善剧中的人物身世、性格,使得剧情更加连贯饱满。在演唱曲词中第二折的主唱者正末由元刊本中的列御寇变为吕洞宾,第四折列御寇承担外末并首唱【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胜葫芦】四支曲子,不入套内,之后正末(吕洞宾)唱正宫一套。如果比较元刊本和臧本之间的曲词,可以发现臧本与元本在宫调的安排上大致相同,但也部分调整了元刊本的曲牌安排,这一部分后文有较详尽的分析。臧氏还从当时的语言、音律和个人文学观念出发,几乎对每一支曲词都进行了修改和增删,有的甚至还被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动,使得唱词表现出的感情和思想主旨发生了变化。
从曲牌的变化来看,首先对《竹叶舟》在元刊本和臧本中的曲牌进行对比:
1、楔子。元刊本:无曲牌;臧本:赏花时。
2、第一折。元刊本: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咤令、鹊踏枝、寄生草、幺、醉中天、金盏儿、尾;臧本: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咤令、鹊踏枝、寄生草、醉中天、金盏儿、赚煞。
3、第二折。元刊本:新水令、驻馬听、雁儿落、挂玉钩、沽美酒、滴滴金、折桂令、元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离亭宴煞;臧本:新水令、驻马听、雁儿落、得胜令、挂玉钩、沽美酒、太平令、甜水令、折桂令、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鸳鸯煞尾。
4、第三折。元刊本:一枝花、梁州、隔尾、贺新郎、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牧羊关、哭皇天、乌夜啼、三煞、二煞、收尾煞;臧本:一枝花、梁州第七、隔尾、贺新郎、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牧羊关、哭皇天、乌夜席、三煞、二煞、黄钟尾。
5、第四折。元刊本:节节高、元和令、上马娇、游四门、胜葫芦、又、后庭花、柳叶儿、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明叨令、尧民歌;臧本:村里迓鼓、元和令、上马娇、胜葫芦、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叨叨令、十二月、尧民歌、煞尾。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臧本中较元刊本多出的曲牌,有的在元刊本中并没有出现。但在臧本新增的曲牌中,有些曲牌出现的位置比较特殊。如第四折正宫前增加的四首曲子,打破了元本一人主唱的形式,臧本中的正末是吕洞宾,按照惯例只有他才可以演唱,但是本折中作为外末的列御寇却也可以在剧中演唱。从整体来看,臧本较元刊本增加的曲牌数量还是在少数。除第四折套数之前的曲子改动较为明显外,臧本的曲牌还是严格按照曲牌和宫调的关系进行编排。
最后从演出结构来看,元刊本每折都是正末主唱。臧本的形式更加灵活,楔子为冲末(陈季卿)唱一支曲;第一折到第三折为正末(吕洞宾)主唱;第四折先由外末(列御寇)唱不入套内的四支曲,再由正末(吕洞宾)主唱。人物出场时,元刊本的正末在第一、三、四折都有入场诗,如一折吕洞宾吟“朝游北海暮苍梧,袖内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三折正末渔夫吟“月下撑开一夜舟,风前收起钓鱼钩。箬笠遮头捱日月,蓑衣披体度春秋。”而臧本的改编赋予楔子中外末陈季卿入场诗“惭愧微名落礼闱,飘零不异燕孤飞。连天大厦无栖处,来岁如今归未归。”显示陈氏悲惨境遇,显然一开始就将叙述中心对准剧中真正的主人公陈季卿,将仙人身份的吕洞宾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因此在第一、二折都舍去了吕洞宾的入场诗。在人物下场时的安排上,我们更可以看到臧氏突出陈季卿凡人身份,弱化原剧求仙修道的主旨。元刊本的四折在每一折最后都是身为正末的吕洞宾(第三折化为渔翁)唱最后一支曲结束;臧本则改变元刊本稍显固化的下场方式,楔子中外末惠安吟“故人昔未遇,借此山中居。则恐登枢要,何曾问草庐。”下场,第一折惠安吟诗下场,陈季卿梦醒下场,第二折陈季卿吟“渐觉乡音近,翻增旅况悲,途遥归梦绕,心急步行迟。”下场,第三折陈季卿醒来念“篮中诗”追下,行童回报惠安,下场等。可以看到,臧本对每一折末尾的处理方式在于突出多角度叙事,弱化元本正末独大的情况,使得前一折的结束能够流畅地接入后一折的演唱,增强全剧的流动性推动剧情的前进。如第三折末尾陈氏苏醒阅读篮中诗幡然醒悟追逐吕洞宾的安排就很自然地接入最后一折陈氏找到吕洞宾表示自己顿悟拜吕洞宾为师一心修道的圆满剧情,在陈氏追下后,行童回报惠安又显得剧情十分合理,行童和惠安的戏份虽然结束,但仍给人留下遐想的空间。
三、臧本对元刊本《竹叶舟》的改编意义
(一)宾白的补充
元刊本《竹叶舟》中的宾白大量缺失,给后世读者理解剧情造成很大不便,也使后世研究者难以接近全剧原貌。而《元曲选》本赋予剧中人物丰富的宾白,使得读者通过人物的宾白了解他们的身世乃至性格。比如惠安长老,在元刊本中没有宾白,但是在《元曲选》本中,惠安长老的宾白介绍本人身份、来历,点明与陈季卿之间的身份关系,提示观众陈季卿身负才学而时运不济的现状。
陈季卿在来到青龙寺后,宾白中又增加了惠安对陈氏的宽慰和接下来带领陈氏游览终南山和青龙寺的这一段对话,并引出接下来陈季卿題《满庭芳》表达思乡之情的一段剧情,而在《元刊本》中,第一折折首只是提示“外末题《满庭芳》云了”,显得不知所云,《元曲选》本的这一改动,使得剧情上更加的合理,惠安长老这一角色的重要性也被体现出来。由此可见,《元曲选》本对元刊本宾白方面的改编主要是补元本之阙,或是对元本的宾白进一步丰富。起到了展示剧中人物性格,完善情节,连贯剧情的作用。
(二)韵文的增设
《元曲选》本改编元刊本宾白另一比较明显的变化便是增加很多元刊本中没有的韵文,比如楔子中陈季卿上场后的一句感叹诗“才离紫陌上,便入白云中。”楔子结束后惠安念的一首诗:“故人昔未遇,借此山中居。则恐登枢要,何曾问草庐。”另一种情况是元刊本中提示有韵文但是并无内容的地方,《元曲选》本据此都一一补全。如元刊本第一折提示陈季卿作《满庭芳》一首,但并没有记录《满庭芳》的具体内容,《元曲选》本中,这首《满庭芳》就被补全:
坐破寒毡,磨穿铁砚,自夸经史如流,拾他青紫唾手不须忧。几度长安应举,万言策曾献螭头,空余下连城白璧,无计取封侯。可怜复失意,羞还故里,懒驻皇州。感君情重,僧舍暂淹留,暇日相携登眺,凭高处,共豁吟眸。家山远,如何归去?都付梦中游。
又元刊本第二折【川掇棹】一曲前提示外末吟《临江仙》一首,却并无内容,《元曲选》本同样也在相同的位置予以补全:
一自长安来应举,本图他富贵荣华,谁知不第却归家。妻儿年稚小,父母鬓霜华,中道迷踪何处问,遇羣仙下访乘槎,低回无语漫嗟呀,断肠俱失路,延首各天涯。
臧氏增加的韵文读之流畅自然,对补充剧情,增进全剧主旨的理解有很大帮助,而且也成为研究臧氏戏曲理论、戏曲创作的重要资料。
四、结语
总之,臧氏对元本改编的优势在于使得剧情更加完整,宾白的大量增加有利于塑造更加饱满的人物,韵文的增加既符合剧中人物陈季卿作为读书人的这一身份设定,又与改编者臧懋循的文人身份相吻合,体现了这部剧改编过程的文人旨趣。但臧本改编的不足之处在于,过度增加的宾白使剧情连接、曲文缀合的同时,对剧情发展的简练、连贯造成一定的牵绊。臧本改编的《竹叶舟》被赋予了更多的个人化色彩和文人情趣,但也使得此剧渐渐地远离民间土壤,逐步地变为一种案头文学。但不可否认的是,《元曲选》的改编较好地保存了元杂剧的整体样貌,为我们增加了一个可以和元刊本进行比对的版本,成为元代杂剧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1]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徐沁君校点.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臧晋叔编.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