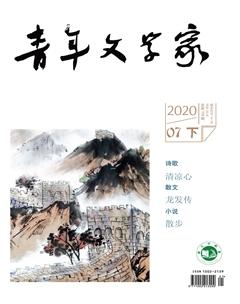矛盾修饰法与悲剧问题
刘维
摘 要:特里·伊格尔顿悲剧理论专著的中文版,即《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一书的中文标题存在不妥。“甜蜜的暴力”这个译法,既不符合英文原名中sweet violence 这一词组被提出时的原意,也不能起到指明伊格尔顿悲剧理论核心与关键的作用。Sweet violence的原名在修辞上是一种矛盾修饰法,其点明了该书的理论要点,即伊格尔顿对种种悲剧观念辩证矛盾关系的看法,中文版译名应当完成对这一要点的传达。澄清的译名问题,将对我们深入了解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的核心观点有所助益。
关键词: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矛盾修饰法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1--02
一
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1]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于2003年出版的悲剧理论专著。200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国内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2],并且其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中文译本。该书一经译介,就引起了国内悲剧理论研究者和伊格尔顿研究者的密切关注,随着国内研究的深入,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的大致面貌被解明,其理论上的重要性也逐渐为学界所认可。但与此同时,该书中文版在翻译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慢慢地暴露了出来,而这些问题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便是对所谓“甜蜜的暴力”这一书名的质疑。最早指出该书书名存在问题的学者是陈奇佳,他曾指出,中文版将该书的原名“sweet violence”处理为“甜蜜的暴力”是不确切的。这里的表述跟“甜蜜”二字的意思毫无关系。中文版将其译作“委婉的暴力”才更为妥当。[3]的确,考察原意,“甜蜜”的意思根本毫无由来,这里将sweet 一词直接对应“甜蜜”,很有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望文生义。但这一问题不能到此为止,正如下文将要说明的那样,实际上将sweet一词翻译为“委婉”二字也并不恰当。译者对一本外国理论著作的中文译名的处理,将对其在国内的传播与接受产生最直接的影响。错误的书名将在传播中产生误解与障碍,伊格尔顿该书书名的问题还需要得到分析与澄清。
伊格尔顿这本专著最早是以英文写成并出版的,其首先面向的是英语读者。鉴于以英文版为研究对象的国外学界不存在翻译等问题,因此国外学者的理解与意见,可以成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有力参考。2004年,Adrian Poole 在他对该书的评论中认为,“sweet violence”这一词组,是伊格尔顿对锡德尼在他的《为诗辩护》一文中的经典用法的沿用。[4]锡德尼使用它是来形容悲剧艺术所产生的独特效果。Adrian Poole又指出,sweet violence 的用法,不管是在锡德尼还是在伊格尔顿那里,都是一种矛盾修饰法(oxymoron)。[5]而所谓矛盾修饰法,按照牛津词典的释义,是指包含截然相反的两个性质或概念的用语,如“震耳欲聋的寂静”,或者“苦涩的甜蜜”,均是典型的矛盾修辞。这种修辞正是以造成明显矛盾的方式来达到特殊的修辞效果。如果我们采取这一判断来分析“sweet violence”的中文译法的问题,一切都将豁然开朗。首先,“甜蜜的暴力”这个译法,完全不能体现所谓“矛盾修饰法”的性质。甜蜜与暴力二词,根本说不上是一对截然相對的矛盾。而如果我们采用国内学者的意见,对sweet一词取“委婉”之意,矛盾修饰法的矛盾性质也难以彰显。“委婉”同“暴力”的的确差别很大,两者又确实是不相协调的,但这种处理依旧不太符合矛盾修饰法的“截然相反的两个性质或者概念”的描述。这里笔者认为,应对sweet 一词,取“温和”或者“温柔”之意。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暴力”与“温和”或者“温柔”,可以形成一对明显截然相反的矛盾,并且,按照英汉牛津词典对于sweet一词的第七个释义,“温柔/温和”译法也能得到支持。总而言之,不管是按照词典的标准解释,还是国外学者对于该标题“矛盾修饰法”性质的判断,乃至对伊格尔顿理论实际状况的考察,或许“温和的暴力”或“温柔的暴力”这样的译法才是对原标题“sweet violence”更为妥当的处理。
二
《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一书译名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技术上的细枝末节,这个译名的不当之处还在于,它未能传达出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的核心思想。正如上文所述,sweet violence这一词组,其在修辞上是一种典型的矛盾修饰法。而伊格尔顿之所以选择以这样一个词组作为他整个悲剧理论的标题,是因为它恰到好处地点明了自己悲剧理论的核心关键词:矛盾。如该书的副标题“悲剧的观念”所示,伊格尔顿在他的理论中展开的是有关命运、自由、正义、怜悯、恐惧等悲剧观念的探讨。而这些观念,熟悉悲剧学说史的人会知道,均已经过理论家们的反复研究,已经很难产生新意了。尽管如此,伊格尔顿在他的理论中仍做到了不同于前人。他不是分别孤立地把握各种悲剧观念,而是以辩证矛盾关系为核心,来将这些观念组织起来。这也正是其悲剧理论的创新之处,即对理论史上种种重要的悲剧观念的特殊组织方式。
举例来说,所谓“命运”的观念,在人类悲剧学说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考察经典悲剧作品我们也能发现,悲剧主人公所遭遇的,经常是某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围绕“命运”二字建构起来的悲剧理论也着实为数不少。但与之相对的,“自由”的观念在悲剧理论中的重要性又不能被忽视,自由意味着悲剧人物对自己行为的负责,就如同黑格尔曾指出的那样,主人公的自由和自我决定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悲剧的前提。这样,两种理论的冲突便出现了:悲剧艺术向我们讲述的,究竟是一个有关命运的故事还是一个有关自由的故事?所谓命运强调的是悲剧主人公自由的缺乏与自由的幻觉。而所谓自由则是指免于某种必然性的自我决定、自我归因的原则。那么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容的概念,可能在悲剧艺术中同时成立吗?
伊格尔顿在他的理论中直接地指出了这两个观念的辩证矛盾关系。按照他的观点,命运和自由,不能孤立分别地看待,只能将它们当成一组辩证矛盾来分析。如果说命运意味着必然性,那么对这种必然的理解与把握,必然地又是自由的前提。例如,如果我们对万有引力法则的必然性没有起码的理解与把握,那么人的自由行动就根本无从谈起。在这种意义上,命运之必然性正是自由的基础。[6]反过来说,自由或者自由的行动,也最终将显示出必然的性质。伊格尔顿认为,人自由的行为,会在最不可预见的地方无止境地播种后果,它们就像无线电波一样在宇宙中传播,却永远不可能被召回至源头。[7]人的行为及其后果是无法撤销的,这些后果最终会聚集在某个阴暗的领域,它们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显现出决定性的力量,而这个领域的一个名字,就叫做命运。自由正是在这里完成了向命运的转化。这样,这两者相反相成的辩证矛盾关系就被伊格尔顿阐明了。
要说明伊格尔顿悲剧理论对各种悲剧观念的辩证矛盾的结构方式,还可以以他对怜悯和恐惧两个观念的探讨为例。怜悯与恐惧的观念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是整个悲剧学说史上历史最悠久,也是经过阐说最多的两个关键词。尽管如此,伊格尔顿以辩证矛盾为核心的把握方式,依然给我们带来了认识这样一组古老观念的新契机。首先,怜悯与恐惧,作为人类情感的两个基本方面,两者的矛盾关系体现在悲剧欣赏者的基本心理活动上。怜悯代表趋近的渴望,而恐惧则代表拒斥或逃离的冲动。当悲剧的接受者怜悯悲剧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时,主体同客体的距离无疑被大幅缩短了。甚至在审美体验的高潮阶段,观众能达到主客统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戏我不分”的状态。但如果悲剧艺术所展示的悲惨场景过于强烈和直接,那么欣赏者便会自然地产生一种拒斥或者躲避的冲动,表现为欣赏者可能会移开或者用手遮挡视线,甚至干脆地逃离悲剧欣赏。这样,欣赏者在欣赏悲剧艺术时,内心可能总是处于“趋近”和“逃离”的两极“煎熬”之中,比起其他艺术,悲剧的欣赏者更经常地处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当中。
在怜悯和恐惧的问题上,辩证矛盾的思想,使得伊格尔顿透视到了这一组矛盾观念表面之下深层的对立统一结构。这样一种深层结构,体现为亲密性和相异性(otherness)的关系。在趋近和逃离的基础上,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怜悯是一个关乎亲密的问题,而恐惧则是对相异性的一种反应。”[8]这也就是说,我们会怜悯我们所感到亲近的,而倾向于去恐惧具有相异性的事物。这里显示的是两者的对立。而两者的统一表现为,亲密性的过度发展将显出相异性,而相异性又是亲密性的基础。就如同悲剧《俄狄浦斯王》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俄狄浦斯娶了自己的母亲,无限度地靠近了自己的源头。造成的结果就是“过剩的亲密讽刺性地导致疏离”。[9]而这种疏离与陌生状况的原理,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是因为主人公违反了一项基本法则,即“主体必须同自我建立一定距离才能认识自己”。反过来说,“相异性又是亲密性的基础。”人际關系的建立,正取决于彼此之间的相异性,否则我们就难以逃脱某种自恋的循环。例如,男女亲密关系的建立,正是取决于对彼此明显的相异性的认识,相异性在亲密关系中起到基础和决定性的作用。伊格尔顿提出的亲密性与相异性两个范畴,在悲剧欣赏中有着集中的体现。比如,欣赏者在目睹悲剧主人公的种种苦难时,在亲密性与相异性的共同作用下,就会反复摇摆于“这可以是我”或“这不是我”之间,而正是将它的欣赏者处于这样一种张力状态,悲剧艺术才给人们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
除了对上述两组悲剧观念的分析,伊格尔顿的理论还包括对无序与正义、毁灭与价值等辩证矛盾关系出色的分析与探讨。总览全书,伊格尔顿已经雄辩地证明,以辩证矛盾为核心的建构方法,在解决有关悲剧的疑难问题上极具效力。正如其英文原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辩证矛盾的精神与方法,是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的重要观点,也是我们理解其理论的入口,不管是译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应该对这一点有所把握。
注释:
[1]Terry Eagleton. Sweet Violence: The Idea of the Tragic. Blackwell.2003
[2]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3]陈奇佳.自由之病:伊格尔顿的悲剧观念[J].文学评论,2018(04):205-213.
[4]Adrian Poole. Review: Sweet Violence: The Idea of the Tragic by Terry Eagleton.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New Series, Vol. 55, No. 218 (Feb., 2004), pp. 106-107
[5]同上。
[6]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4.
[7]同上:119.
[8]同上:174.
[9]同上:174.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