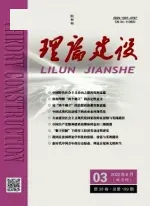毛泽东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防疫宣传教育
马先睿
(1.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611756;2.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上海200433)
疫病的防治不仅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同时深刻影响着国家社会的有序运转。其中,作为疫情防控的关键一环,防疫宣传教育对于整个防疫事业的推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疫宣传教育工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他更多次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精神文明教育,加强对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明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1]。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毛泽东带领下,党和人民政府就坚持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积极探索防疫宣传教育事业,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为今天的卫生防疫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正因如此,有关这一历程的回顾与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目前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病防治情况已有诸多阐发,但就毛泽东与防疫工作中的防疫宣传教育问题,既有成果虽偶有涉及,但一直缺乏针对性的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下的防疫宣传教育工作,尝试梳理其发展过程及客观实效,提炼个中的历史经验,为今天进一步加强卫生防疫工作、扑灭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病概况及其成因
揆诸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种灾害,疫病危害尤其严重。毛泽东在1951年下发的《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就曾明确指出,“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2]446。从种类上看,这些疫病大致可分为烈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一般传染病三类。其中,鼠疫、天花等烈性传染病由于致死率高,影响最为剧烈。据统计,1950—1954年全国各地罹患鼠疫者就达6 800余人,年均超过560人丧生,疫情遍布中国20个省(自治区)500余县[3]27。察省等地因为疫情严重还一度进行封锁管理(1)。另据《人民日报》1951年报道,“天花的死亡率很高,平均四分之一的患者要死亡,因天花而失明的也不少……根据最近十年来极不完全的统计,全国每年发病数不下一百万人,曾使人民生命和生产遭受极大的损失。”[4]除烈性传染病外,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猩红热、白喉、麻疹等疫病虽致死率不高,但也一度造成广泛流行。1950年2月中央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向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下发的一份文件中即提到,“最近各省、市疫病流行,传播很快,蔓延很广……湖北枣阳一带,半月内脑脊髓膜炎及上述各种流行病蔓延400余公里,死亡约400余人……白喉曾先后在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发现。猩红热、百日咳也在不少地区为害”[5]829。疫病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之所以猖獗如斯,主要原因无外如下几个方面。
(一)旧时疫病残留,防治难度较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开展防疫工作时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旧时大量疫病的残留。一方面,由于过去民国政府防治疫病不力,国内疫情“几遍全国,每隔三至五年,必大流行一次,江南地区及城市,有二至三年接连流行的……过去反动政府,从来没有做过有效的预防,每年照例推行预防注射,饮水消毒及冷饮料的管理,大多流于形式,或强迫命令,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这些防疫措施,常落在疫病流行之后,徒然劳民伤财,没有效果。以致少数病患,竟迅速蔓延成灾”[6]。因疫病长期得不到有效防治,其传染范围波及日广,给新中国的防疫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另一方面,日本侵华期间曾在中国内陆广大地区大量投放鼠疫、伤寒等传染病菌,其感染性强、覆盖面广,危害蔚为严重(2)。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731部队”更变本加厉,在炸毁集中营、实验室以毁灭罪证的过程中,造成建筑物内蚤鼠向四周大量逃遁,致使哈尔滨一带每逢秋季便暴发鼠疫,并最终引发1948年东北全境鼠疫流行,导致3万多人罹难[7]。旧时疫病的大量残留,使新中国的防疫工作从一开始便面临极大考验。
(二)生活环境恶劣,医疗条件不足
新中国的诞生对于党和人民而言自是来之不易,但历经多年战火,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都亟待改善。从住居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主要城市中破旧和危险房屋约占全部居住房屋的一半以上。“如北京有2/3的危险和半旧及破旧房屋,上海则有1/5以上的居民住在棚户区,还有许多居民挤在阁楼和楼梯间里,甚至常年栖息在马路上和屋檐下,而长沙的棚户竟高达77%”[3]104。这样简陋的居住环境无疑为各种疫病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与居住环境配套的厕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公厕基本继承自民国时期的旱厕,且“因建筑不善,兼一般市民不到厕内即开始溺便,以致亚摩利亚气四溢”[8],为血吸虫病、钩虫病等疫病的产生制造了温床。由于如厕环境恶劣且缺乏保护措施,市民中多有感染疾病或中毒者,有人甚至发出“医病无分文,惨死在粪坑”之语[9]。与此同时,当时的医疗资源仍非常短缺。首都北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仅有61个公共卫生机构,市郊则仅存3个公立的保健站,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严重,人口死亡率高达11.9‰。因没钱看病吃药,坊间流传“小病扛,大病躺,重病等着见阎王”[10]。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与医疗条件下,人民群众饱受疫病之苦。
(三)封建迷信盛行,防疫意识淡薄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1950年的全国防疫工作会议上特别指出,“过去大量的疫病之所以在中国长期存在并危害中国人民,主要由于反动统治所造成的贫穷、愚昧和环境卫生不好,卫生常识及个人卫生习惯很低造成的”[11]。实际上,迷信现象盛行以及防疫意识缺乏,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众多疫情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部分群众受到封建文化影响,对各类疫病与鬼神关系笃信不疑。如陕北一带居民将疫病视作“魔鬼附体”,川西地区有人罹病后不正规服药,改去求神问卜,“打保符”驱病[3]126。察北地方的鼠疫患者不配合政府防疫,反倒聚众设坛,杀羊献供来祈祷免疫[12]。此类封建迷信的盛行,使许多病患无法及时就医以致病况危重。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干部防疫意识薄弱,面对疫情不作为或消极作为。当时《人民日报》对此多有报道。如平原省聊城专区曾一度流行赤痢,儿童多有感染,但区政府对疫情视若无睹,既不研究防治办法,更不将情况向上级报告。有的区干部甚至扬言,“小孩已到死的时候,还能不死吗?”[13]肇因于错误的思想意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疫病由于得不到有效重视和及时医治,疫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从上述成因不难看出,防疫工作的开展除受制于经济发展的客观水平外,其余或多或少与人的主观认知存在关联。也就是说,无论是旧时沉疴的积极治愈还是卫生环境的后续改善,无论是医疗条件的持续进步或是防疫观念的纠偏更新,“人”的改造都占据重要地位。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在防控各项疫情的同时,尤其注重人民群众防疫观念的培育。在这种情况下,防疫宣传教育的推动成为建国初期防疫工作的一大重点。
二、毛泽东领导防疫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举措
受多年战争影响,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面对各地疫情的肆虐,能否有效预防和控制疫病、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正确的防疫观念,不仅关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与人民政权的稳固和发展休戚相关。迫于疫病防治的紧急形势,毛泽东厘清疫病形势,指导党和人民围绕防疫宣传教育展开了一系列探索,采取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措施。
(一)确立防疫宣传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了防疫宣传教育的重要性,明确将“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视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14]1082-1083。在他的关切下,1950年2月中央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的指示》,其中明确提出“必须扩大卫生宣传,结合群众,破除迷信,安定人心”的工作原则[5]831。同年8月,人民政府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对包括防疫宣传教育在内的各项防疫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毛泽东亲自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5]。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会上提出“以预防为主”的防疫工作总方针,即强调疫病的预防“必须是组织工作与宣传工作同时进行,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与科学研究工作及卫生人员教育工作同时进行,必须做到卫生部门与其他文教部门的密切配合,特别是与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的密切配合”。至于具体的“教育方针”一项,“是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普及与提高的结合;就目前情况从全国范围来说,尤应该是以普及为主”[16]。这一总指导方针和具体方针的出炉,对后续防疫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定盘星作用。1951年9月,针对贺诚在《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的若干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拟定了《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2]446。这份发往基层的文件,将疫情防控提高到了政治高度,极大地推动了防疫宣传教育工作向纵深发展。
(二)开展多种形式的防疫宣传教育
针对民间看待疫病时存在的迷信现象,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14]1011在他的指示下,党和政府围绕基本卫生常识的普及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防疫宣传教育,旨在破除人民群众的错误思想认识,切实提高民间防疫卫生水平。首先,各级政府充分调动各类媒体资源,运用报纸、书刊等大众传媒手段展开集中宣传。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相继开辟专栏,针对疫病防治发表了大量社评和文章。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还组织专家编写了《防疫宣传大纲》《防疫工作手册》《可怕的鼠疫》等普及读物,帮助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正确认识疫情,在社会中产生了积极影响。截至1951年8月,全国各地共发行卫生读物20余种,发行量超过15万份[17]。其次,各级政府还通过讲演会、座谈会、干部会等形式深入民间,对广大群众进行面对面的宣传教育。据统计,1949年仅东北地区就开展了大量基层防疫宣传教育座谈,其中1/3的教育时间都集中在疫区,对于提高疫区当地民众的疫病预防知识、揭穿巫神巫医的欺骗效果十分显著。又如苏州市卫生防疫站自1951年开始共作了565次卫生宣传,大连市聘请医学院教授在社区进行通俗演讲70余次,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卫生防疫观念[3]143。再次,各级政府在防疫宣传教育中积极与文艺界结合,采用了生动丰富的宣传形式。如华北影片经理公司就响应政府号召,举办了主题为“怎样预防鼠疫”的免费防疫宣传教育影片放映会,仅第一日就有超过3万人报名参加[18]。一些地方政府结合当地防疫实际,还尝试推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防疫宣传手段。如上海市就通过江淮剧、话剧、宣传队和腰鼓队展开防疫巡演,黑龙江等地则用唱大鼓、拉洋片、蹦蹦戏、驴皮影等穿插各地现实防疫内容,所获效果显著。此外,在毛泽东倡议下,各级政府还借鉴过去中央苏区的经验,以竞赛形式推进防疫宣传工作[19]。这些形式多样的防疫宣传教育活动,展现了新生人民政权的无穷活力,有效提升了防疫宣传教育的效果。
(三)高度重视校园防疫宣传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向广大青年发出了“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此后他更多次强调,“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教育”[20]。正因如此,人民政府在推动防疫工作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校园防疫宣传教育。从1949年10月到1951年10月,全国各主要城市先后成立了学校卫生委员会(或卫生教育委员会),并根据中央部署,各高等学校卫生工作改由当地文教与卫生两机关合作领导[21]43。在毛泽东和各级政府大力推动下,各地校园防疫宣传教育工作推进十分迅速。如河南省大力开展校医培训,有效扩大了学校防疫知识教育的队伍规模;辽宁省则组织师生亲身调研地方病,加深对疫情的认识;浙江省各级教育机构和学校在“捉老鼠”等课文中进行防疫宣传教育,极大激发了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疫情防控工作的热情[3]271-272。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督促下,文教部门编写了大批高质量的卫生防疫教材。如山东自然科学教育研究所在1950年编辑出版了《传染病挂图》,系统介绍了当时流行甚广的天花、霍乱等各种传染病的防治知识,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卫生挂图(霍乱、赤痢、伤寒)》一书也从防疫角度普及了疫病传播的途径及防治方法。另外,授课教师的防疫培训也一并被纳入到校园防疫宣传教育的环节当中。根据中央卫生宣传处统计,截至1951年,全国各地接受学校卫生训练的教师就将近3 000人,极大增强了校园防疫宣传教育工作的力量[21]44。
(四)通过群众运动巩固防疫宣传教育成果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即提出“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并在大会上确立了“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与科学研究工作及卫生人员教育工作同时进行”的路线方针。换言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防疫宣传教育工作的核心理念之一。在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组织下,自1950年开始,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一系列以防疫宣传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如在东北的鼠疫防控中,当地群众结合政府宣导的防疫知识,主动开发数十种捕鼠方法,掀起了一股除害防疫的高潮。在扑灭血吸虫病疫情的运动中,疫区民众也将政府宣导的防疫方法付诸实践,积极运用开水烫、火烧、撒生石灰等方法进行灭螺,取得了显著成果。1950年5月,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卫生部特别下达文件,要求各地卫生机关务必“使预防霍乱的工作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以此提高人民对霍乱等疫病危害及其预防方法的认识[22]。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党政领导率先垂范,如北京、南京等市市长先后亲自投身防疫宣传教育的相关群众运动。在部分地方,政府还尝试开展“诉苦”活动深化群众的防疫观念。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后来对这一举措给予了高度赞扬:“进行卫生宣传时,举出真人真事,不讲空话,或者开诉苦会,诉说在旧社会无法讲卫生的痛苦,算细账讲明卫生有利,也是好办法。”[23]显见,以群众动员的方式巩固防疫宣传教育成果,不仅立竿见影,而且切实提高了民众参与防疫宣传教育的积极性和凝聚度。究其原因,如个别学者所言,“在高密度的舆论宣传中,极易形成一种比较竞争心理,进而转化为一种指标评价体系……当这些数据被用来作为评判地方政治信仰的依据时,必然会有力地刺激各地干部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国家也因此而实现卫生防疫工作的政治动员”[24]。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防疫宣传教育的成效分析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带领下,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我国的防疫宣传教育工作取得了卓著成效。一方面,防疫宣传教育的开展增强了国民的卫生防疫观念,改善了国家的卫生面貌。人民群众普遍养成不喝生水以及不吃生食冷饭和不洁食物的良好习惯,认识到灭蝇、灭蚊、灭蛆、灭鼠以及修缮厕所、开窗通风等卫生活动的重要。特别是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广大群众在防疫宣传教育中深切体会到除害防疫的好处,进一步破除了封建迷信的错误思想。他们遇病不再求神问卜,而是主动上报疫情、积极治疗。如四川省一带的群众就主动将供神的香炉改作痰盂,把神架改为垃圾箱,把土地庙修成了公共厕所。他们还自发将防疫知识编成了歌谣,唱道“除害讲卫生,千年疾病断了根,要得不生病,必须讲卫生”[25]。随着人民观念的进步,国家和社会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全国各主要城市基本实现了“六光”“八不见”(3),不仅街道院落积存的垃圾被扫除一空,污水沟池也一律被疏淘填平。在许多地方,相继涌现出一批先进卫生集体、人物和事迹。仅1952年,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就评选出模范单位90个,模范工作者数百名[26]。正确防疫观念的确立,使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的众多疫病得到有效控制。据中央卫生部统计,与1950年相比,1953年全国鼠疫发病数降低了90%,天花降低了95%,霍乱疫情几乎难觅踪迹[27]。这无疑彰显了防疫宣传教育对于疫情防控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防疫宣传教育的推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赢得了人民对党及其领导事业的真诚拥护。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防治疫病方面的各项举措,特别是在防疫宣传教育中体现出的群众路线精神,使刚刚翻身解放的广大人民切身感受到了新生人民政权的温暖和效率。四川地区在抗击鼠疫的过程中,就有群众向政府激动地表示,“以前也不懂得不讲卫生会生病,人民政府来告诉我们怎样除病的方法,着实为我们着想,现在打扫干净了,眼睛看到的、鼻子闻到的也都新鲜了,人也爽快了。”“只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才这样关怀着我们,以前在反动统治时代,做梦也想不到,以后要更努力地做好卫生工作,来报答毛主席和共产党。”[28]浙江杭州则在防疫宣传教育期间广泛流传一首歌谣,唱道“过去痛苦海洋深,富人哪会管穷人,自从来了共产党,挖掉穷根挖病根”[29]。上海市青浦县也有居民感谢党和政府对于当地血吸虫病防治宣传的良苦用心。他们深有感触地表示,“要是没有共产党,我们全家七口的坟上野草可能比人还要长得高呢……至今全家都能活着,这是党给的第二次生命。”[30]这些都是当时民间的真实心理写照,是建立在人民生命健康利益得以保证的基础上的真情流露。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面对疫情时的积极作为,以及在预防疫病过程中关怀人民、帮助人民树立正确防疫观念的一系列举措,向广大群众生动诠释了与旧中国截然不同的执政理念,深刻昭示了新生人民政权强大高效的执政能力。
在肯定新中国成立初期防疫宣传教育突出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受限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这一工作也存在若干不足。其一,宣传教育与防疫实践存在一定程度脱节,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医疗卫生条件不足造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整体尚处于恢复当中。许多防疫举措因为缺乏必要的物资作为支撑,只能流于口头和书本的宣教,短时间内无法付诸实施。这使一般民众在接受政府防疫宣传教育的过程中产生犹疑,影响了防疫宣传教育入脑入心的深度。其二,防疫宣传教育的开展仍然偶见形式主义的倾向。1951年时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呈交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就曾提到,“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实际上因疫病而死的人数远超过饿死的,而其中大多是可以预防的”[2]447。除此之外,个别地方还存在瞎指挥、乱作为的情况。这无疑对防疫宣传教育工作的成效构成了一大阻碍。其三,在运用群众运动方式巩固防疫宣传教育成果的过程中,过度动员也带来一些负面效果。如有的地方每逢遇到卫生大检查时,盲目发动群众开展卫生整治、大肆张贴防疫宣传资料、连续举办各类宣讲座谈,在使运动规模看上去声势浩大的同时,严重搅扰了群众的正常生活。这些做法不仅脱离实际,更违背了党和政府开展防疫宣传教育的初衷,降低了人民群众参与防疫宣传教育活动的积极性。
当然,对于上述不足的存在,不能加以苛求。这是因为,“研究历史是从今天看过去,故能洞若观火,但对创造历史的当事人来说,就不可能这样幸运”[31]。在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防疫宣传教育工作的诸多成效时,应当跳脱现代语境,给出符合历史语境的评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艰苦环境中,毛泽东和党中央能够克服当时的种种不利条件,带领人民群众积极探索防疫宣传教育事业并取得卓著成就,这本身是一件充满挑战的创举,是值得敬佩和肯定的。
四、毛泽东领导防疫宣传教育工作的经验启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摆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一个疫病横生、缺医少药、人民体质极度低下的窘迫局面。面对疫情肆虐带给人民群众和国家建设的严重危害,毛泽东和党中央积极探索卫生防疫事业,将防疫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迅速推广开来。通过一系列卓具成效的措施,新中国成功打赢了这场疫情攻坚战,不仅使当时流行的众多疫病在数年之内便得到有效控制,而且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防疫观念,使国家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如今70载过去,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卫生防疫水平同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诸如新冠肺炎等突发性重大疫情仍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峻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疫情防控是一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严峻斗争。”[32]抚今追昔,如今再度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下的这段防疫宣传教育史,个中经验启示在今天无疑仍是一笔重大财富。
其一,党对卫生事业的正确领导是防疫宣传教育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曾指出,“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33]。新中国成立初期,防疫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绩,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在整个防疫宣传教育的开展过程中,从毛泽东到各级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不仅及时确立了防疫宣传教育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并且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手段,将指示精神与防疫知识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达。不少党政负责人主动深入基层一线,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类群众运动,不仅夯实了防疫宣传教育的既有成果,切实提升了群众对党和国家防疫宣传教育事业的参与度和凝聚力,而且为防疫宣传教育工作的继续深化提供了新的路径支撑。在这一过程中,党一直是防疫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核心。无论是各类指示文件的相继出台还是各地政治动员的迅速铺开,无论是社会资源的协调组织还是诸多困难的集中攻克,党始终站在“政治任务”的高度对防疫宣传教育工作进行全盘指挥,使整个防疫宣传教育工作具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不断前行的方向。有学者就提出,“当卫生防疫和卫生服务成为政治哲学的体现时,既能够为快速消除疾病危害提供保障,同时也能够形成另一种应对机制”[24]。新中国成立初期防疫宣传教育的成功,彰显了党的领导这一重要的核心优势。
其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开展防疫宣传教育的总体旨归。民生存在于每一件小事,千万人的小事就是一件大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战火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一去不复返,中国人民迎来了社会安定、民心团结的崭新气象。如何防治曾在旧社会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各类疫病,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过程中需要重点攻克的难题。为此,毛泽东坚持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出发,带领党和人民经过一系列艰苦探索,补齐了卫生防疫这一影响市民生活品质的短板。通过防疫宣传教育等一系列防疫工作的有效开展,类似鼠疫、天花、霍乱、猩红热等传染病疫情相继得到扑灭或控制,发病率和致死率明显下降,人民生命健康权益得到有效维护。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以人民为中心、致力改善民生的执政理念,不仅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同时维持了建国初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新生政权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冲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4]。解决好每一个攸关人民日常生活的点滴问题,就是在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初期防疫宣传教育的开展以及今天卫生防疫事业的持续推进,意义都正在于此。
其三,开展防疫宣传教育要注重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但要避免完全依赖于群众运动。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14]933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指导防疫宣传教育事业的历程,无疑充分贯彻了以群众为主体的原则,让人民大众不仅成为防疫宣传教育的受益者,更促其化身为这一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通过发动群众的方式,一面极大激活了群众中蕴藏的无穷力量和智慧,加速了防疫宣传教育工作的实绩,一面切实提升了群众认识,使防疫宣传教育成果得以在群众的自我约束中长久保持。可以说,依靠群众而又善于领导组织群众,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防疫宣传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但必须指出的是,群众运动固然有助于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因其本身的特殊性质,不能将之视作唯一的路径依赖。譬如在群众动员的过程中,部分干部中曾一度出现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由于盲目求进、追求运动的气势和速度,使防疫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因为脱离实际而带来一系列负面问题,影响了人民群众参与防疫宣传教育活动的热情。直到今天,这仍是一条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
其四,防疫宣传教育的实效有赖社会各部门的有效配合以及社会资源的合理调度。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其内部的各项活动都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防疫宣传教育本身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其他各项建设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如果将视野跳脱防疫知识的一般灌输及其相关的有限事项,把防疫宣传教育同更为繁杂的公共卫生治理、人的现代化养成、社会动员机制重塑等问题联系起来,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防疫宣传教育工作实际上是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同步推进的。正是在政府和国家的统一集中领导下,社会各部门协同运转,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各类社会资源相继被引入到防疫宣传教育的各项环节中,保证了防疫宣传教育开展的高效和顺畅。今天,面对日益多变的社会生态和以网络为主的舆论阵地,诸如新冠肺炎等突发疫情的防治宣传工作同样离不开社会各部门以及社会资源的密切配合。立足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还需要在充分汲取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创新,继续推动防疫宣传教育等各项卫生防疫事业的进步发展。
注释:
(1)可参见《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华北局发出通知紧急防鼠疫,察北实行紧急封锁》(1949年10月28日第2版)、《记取察北鼠疫蔓延教训,察省厉行严密封锁》(1949年11月4日第4版)、《封锁成效显著,察北疫情近无变化,仍有漏洞正追究》(1949年11月4日第4版)等。
(2)可参见《人民日报》相关报道:《日寇曾组织特别远征队在华中华南散布传染病》(1949年12月28日第1版)、《湖南常德华德医院院长证明日寇曾用飞机散布鼠疫,常德地区很多同胞因此死亡》(1950年2月5日第1版)、《前美国记者和日本医官证实日寇曾使用细菌和毒气武器》(1950年2月26日第4版)、《亲身受害的宁波市民证实日寇曾散布毒菌》(1950年2月21日第1版)、《二野后勤工作人员指控日寇散播病菌毒害华北各地人民》(1950年2月10日第4版)等。
(3)“六光”是指室内四周墙面及房顶、地面无灰尘脏物,“八不见”是指不见砖头、瓦块、垃圾、污水、粪便、杂草、痰、蚊蝇、老鼠。
——宣教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