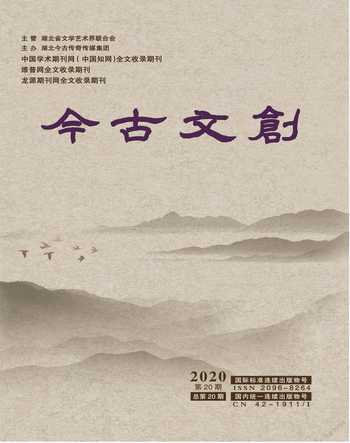澳大利亚作家群二战创伤书写
【摘要】 由于过于屈辱和痛苦,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澳主流话语甚少提及的话题。澳大利亚作家群为数不多的二战创伤书写可以分为直接参与者的创伤体验和间接卷入者的创伤体验。不同人物在不同事件中的创伤沉淀在澳大利亚的民族心灵的深处,走出创伤依旧任重而道远,但勇敢的书写则是迈出了第一步。
【关键词】 澳大利亚作家群;二战;创伤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0-0026-03
澳大利亚的历史有着独特的黑暗面,自大英帝国驱赶流放犯登陆澳洲后,流放、殖民的创伤就深深烙印在这块土地上。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对其民族心理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颇为吊诡的一点是,尽管澳大利亚在二战中的战争规模和惨烈程度都远远超过一战,当今主流话语对一战的精神传承和价值认同远远超过二战。澳新军团日每年都举行盛大的活动,以纪念一战中在加里波利牺牲的澳新联军将士,文学作品中对此也涉猎较多。原因在于,一战是维护民族尊严,将民族血液中的流放犯基因换成为母国尽忠的英雄之血的光荣与梦想之旅。二战是澳大利亚本土被轰炸,士兵在日军东南亚战俘营饱受身心摧残,挣扎求生的屈辱和不堪之旅。在澳文学中,二战创伤的题材为数不多,本文进一步将之细分为以参战士兵为主的直接书写和以卷入人物的为主的间接书写两部分,以多维度立体化地展现了澳大利亚作家群二战创伤书写的全貌。
一、二战直接参与者的创伤
澳大利亚文学中描写参战士兵的小说大致可分为三个時期。第一个阶段为战争正在进行或刚刚结束之时。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汤姆·汉格福德(Tom Hungerford),其《山脊与河流》(The Ridge and the River,1952)取材于亲身经历,描写澳大利亚士兵在热带丛林中残酷艰辛的战斗生活。小说的亮点之处在于并没有将士兵们塑造成单一的高大全的形象。而是描写他们作为常人的矛盾痛苦,人物塑造较为丰满和立体,但是最终士兵们都能突破生理心理的极限,成了默默忍受的平凡的英雄,汉格福德笔下的士兵是澳新军团精神的延续。
在这个时期,文学界对二战的描写较少且多从正面的角度,歌颂战斗英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时战争刚刚结束,千疮百孔的人类心灵已经不愿意重温过去痛苦的历史,而只希望抛弃过去的创伤,迎接快乐新生活。《山脊与河流》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多次再版,长盛不衰,这也说明了战争英雄主义的叙事依然是主流话语的宠儿。
第二个阶段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世纪末,此时澳大利亚文学开始反思二战的创伤。伦道夫·斯托(Randolph Stow)描写太平洋战场澳军战俘的小说《海上旋转木马》(The Merry-Go-Round in the Sea,1965)可以被看作是战争小说的另一个版本,作家通过一个男孩的视角,透视男孩的表哥在战争中的创伤。旋转木马是一个稳定自足的封闭世界,象征着澳大利亚一开始地理上的孤立造成的安全感。但一旦至于海上,则随时有可能被大环境所吞没。作家通过“海上旋转木马”这一美丽而脆弱的意象展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澳大利亚面临的巨大危机。
剧作家约翰·罗默里尔(John Romeril)的《漂浮的世界》(The Floating World,1974)中,前战俘勒斯哈丁和妻子艾琳战后乘“每周女子樱花巡游”号返回日本,在途中精神崩溃。
这部作品结构新颖,富有想象力,生动描绘了创伤作为一种事后的影响,如何在较长时间内占据了主体的生活,战争后遗症亟待解决。但作品中有一点倾向也需要注意,“在战争期间,日本人被视为一个极其邪恶、非人的敌手,这与其东方的他者性有很大关系。”(Pierce,2009:311)这一点在早先的作品中就有所涉及。诺曼·巴特利特(Norman Bartlett)的《胜利岛》(Island Victory,1955) 是描写太平洋空战的小说,作家写道,敌人“比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同胞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要陌生得多”(Bartlett,1955:88)而创伤一旦与种族主义相结合,后果是致命的。勒斯哈丁踏上游船就是不情愿的。当妻子在卖弄风情时, 勒斯哈丁在酒精中回忆死去的同伴。眼前一切都给了这个昔日的日本囚犯强烈的刺激。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语言越来越种族主义。抵达港口后,他沿着舷梯冲下,刺伤了最近的日本人。在随后长达20分钟的独白中,勒斯哈丁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数十年前的创伤记忆喷涌而出,那种痛苦的感觉依然鲜活,丝毫没有被岁月冲淡。卡鲁斯(Cathy Caruth)认为潜意识中的创伤不会被岁月所改变,遭受创伤就是重温一次“无人认领的经历”,创伤每一次从潜意识走向意识,对受创主体来说都是一次初体验。
上文提到的汉格福德在此阶段创作了《军帽的使命和军人情结》(A Knockabout with a Slouch Hat,1985),同为自传体小说,但这次不再描写正面战场的作战,而是描写退伍士兵在战后的生活。书中12个故事不光是其本人的,还包括澳大利亚士兵的群像。全书充满了退伍军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有着深深的怀旧,最让作家自豪的是澳大利亚军队官兵之间平等关爱的“丛林友谊”。
在《创伤与复原》中,美国精神病专家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也观察到对战争创伤神经性官能症的医治,不是依靠爱国心,也不是依靠抽象的理论,而是依靠战友之间死生一命的患难之情。(赫尔曼,2019:18)书中罹患创伤官能症的萨松重返战场并不是因为创伤已经治愈,而正是由于这种友谊和对战友的忠诚。大卫·玛洛夫(David Malouf)的《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1990)中两名澳大利亚士兵在二战中被俘。彼此的丛林友谊使他们承受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摧残,在集中营日复一日的折磨中活了下来。
第三个阶段是二十一世纪,此时小说创作的主体不再是退伍的老兵,而是创伤的第二代。较为著名的有布克奖获奖小说《深入北方的小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2013),作家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的父亲在二战中沦为日军战俘,被强征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中修建死亡铁路。弗拉纳根以主要人物多里戈·埃文斯的视角回忆了那一段极度黑暗荒谬的历史,并认为二战创伤的影响远未随着战争的胜利而结束。《深入北方的小路》是作家献给父亲的小说,也是家族的疗伤之旅。
二、二战间接卷入者的创伤
二战的创伤除了体现在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士兵身上,所有在这个时空中的人物都无从幸免。残酷无情的战争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将一切卷入其中。广大的小人物无法成为时代的英雄,但他们的生活却被这战争时代完全改变了。
参加过二战的澳大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怀特(Patrick White)凭借《战车上的乘客》(Riders in the Chariot,1961)获得弗兰克林文学奖。小说四位性格迥异的主人公中,犹太教授希姆尔法勃毕业于牛津大学,在德国教授英语,二战中被送往集中营。他辗转来到澳大利亚,却只能做一名普通的蓝领工人,他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最后却被恶作剧的工友钉在十字架上。这四个人物都用忍受苦难来达到精神上的净化,最后他们都看到了精神升华的象征——战车,并成了上面的乘客。
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的小说《惧怕》(The Fear,1965)中,青春期的少年有着特有的幼稚和迷茫,当时即将入侵澳大利亚的日本帝国,就像一把高悬的达摩克里斯剑给少年造成了深深的恐惧。当然,肯尼利更有名的小说是《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1982),該小说以纳粹犹太人大屠杀为背景,描写了德国商人辛德勒这一不完美的英雄用行贿等手段救出1000多名犹太人的故事。《辛德勒的方舟》随后获布克奖,尽管没有集中描写澳大利亚本土的创伤,但这是澳大利亚作家以全球的视野书写的二战创伤,其价值不可估量。
泽维尔·赫伯特(Xavier Herbert)二战中曾在太平洋地区服役,他留意到丈夫服役期间澳大利亚妇女的生活的艰辛,据此创作了《士兵的女人》(Soldiers'Women,1961)。他的《可怜虫,我的国家》(Poor Fellow My Country,1975)描写在日本战机的轰炸下澳大利亚人的惶恐与不安。这洋洋洒洒1500多页的小说,获得弗兰克林最佳小说奖。
上文中提到的弗拉纳根在其创作初期还有一部与二战密切相关的小说《单手掌声》(The Sound of One Hand Clapping,1997)。博扬一家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澳大利亚新移民,在战争中,因为人种和宗教的原因,德国纳粹对斯拉斯洛文尼亚的统治尤其残酷,博扬曾目睹纳粹将游击队员的头颅当球踢,博扬的妻子玛利亚一家因为从事地下抵抗运动而受到残酷的报复。
因此,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在战后开出了十分苛刻地带着种族歧视的移民条件,博扬和妻子还是毅然地割裂与过去的一切联系,前往澳大利亚寻找新的生活,但是创伤的规避只会导致更大程度的展演,往日的阴影阴魂不散地萦绕着这个家庭。妻子玛利亚无法忍受这种痛苦,走进了塔斯马尼亚的丛林结束自己的生命。失去母爱的女儿索尼亚在澳大利亚社会艰难求生。博扬一家作为历史中的小人物,被战争的强力蹍成了齑粉。
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 的《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2003) 以叙述者安东尼奥·卡斯特罗的口吻描摹了一个大家族几百年来的兴衰更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人物一路辗转上海、澳门和香港,最后在悉尼定居。安东尼奥四海为家的父亲曾在苏州河射杀日本侵略者,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只是为了求生。在日军占领香港以后,母亲为了给孩子们换回食物,不得不跟日本上校跳舞。父亲对随后发生的一切选择性地失忆了。
此时价值观的判断似乎都停止了,在战争的苦难面前,活下来成为第一宗旨。战争是残酷而荒谬的,创伤的内核决定了其痛苦无法被直接诉说,只能在顾左右而言它的间接诉说中得到隐晦的表征。
三、结语
澳大利亚二战的战争体验是一种屈辱的经历。如在《深入北方的小路》中,从集中营生还的澳大利亚士兵被要求对那段经历沉默,因为“白种人在热带雨林中给日本帝国当牛做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但未曾解决的创伤,扎根在民族无意识的深处,“澳大利亚人本来就缺乏坚定的信仰,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后,原有的薄弱信念也开始动摇了……信仰危机滋生了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又导致了享乐主义。”(黄源深,2014:221)以肉体的放纵来忘却创伤是澳大利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毒品和性泛滥的重要原因。但创伤是一种潜伏的无法言说的痛苦,逃避无法解决问题,只有将创伤从黑暗的潜意识中上升到意识,从创伤记忆转化为叙述记忆,才能走向康复。
澳文学界对二战创伤书写不多,与犹太人大屠杀叙事汗牛充栋的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创伤依然潜伏在民族无意识的深处,但不论是描写正面战场军人的创伤,还是描写卷入战争的小人物的痛苦,勇敢的书写为创伤发声,都是走出创伤关键的一步。
参考文献:
[1]Norman Bartlett. Island Victory[M]. Sydney: A&R, 1955.
[2]Peter Pierc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4]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施云波,女,汉族,江苏常州人,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当代澳大利亚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