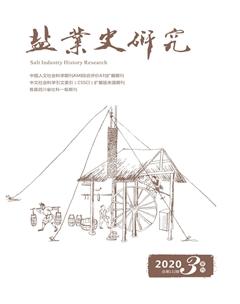从“西盐”到“盐官”:陇蜀易盐史的演进与变迁
摘 要:陇蜀通道的军事经济往来,在周秦时期就有。秦封泥“西盐”的出土,标志着陇蜀营盐活动和易盐历史在秦早期就已发端。从“西盐”到“盐官”的演进,实际在秦汉时期的陇蜀交通领域已经基本完成。在整个陇蜀易盐史的演进与变迁中,西汉水流域的盐官设置及其机制的发挥贯穿着整个汉后历史进程,基本属于秦汉“盐官”体制的继承和发展。整个陇蜀营盐和易盐史的变迁,表现为周秦以来“盐官”制度源与流的演进,其脉络清晰地反映了中国西北—西南一线营盐易盐史的主要特征和内涵。由此表明,陇蜀易盐史早就成为了中华盐文化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周秦;西盐;盐官;陇蜀;营盐易盐;演进与变迁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0)03—0011—09
陇蜀毗连,视为一地,在周秦时期就已定型。《战国策》卷五《秦策三·范雎至秦章》中范雎给秦昭王献策说:“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今反闭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国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①在这段放眼周秦天下的分析中,居于秦国西南的陇蜀之地不仅是连片的屏障地区,也是重要后方纵深和战略根据地,位置极其关键。战略家如是观,延及秦汉并未改易:“张良亦(谓高祖)曰:‘关中右陇蜀,盖以陇坂险阻,与蜀道可并称也。”② 张良认可了“陇蜀”西护关中的战略地位和襟带作用,还特别强调了陇关和蜀道的险阻功能,这和刘邦开汉的战略意图、进兵路线密切相关③。
与战略家视野不同的是商业论者和史地论者,他们的视野似乎更关注陇蜀之地的物流通道价值。《史记·货殖列传》云:“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④“隙”字,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隙者,间孔也。地居陇蜀之间要路,故曰隙。”言下之意,在秦早期的东周之初,秦陇与巴蜀之间的交通孔道就已经发挥着显著的经济交通功能,不仅货物输送繁忙,而且多有商贾通行其间,可见陇蜀早在秦文公时期就属于重要的商业交通地域。令人想进一步探究的是,自周秦以来的陇蜀贸易中,盐业史的演进与变迁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似乎学界还鲜有人涉及。故本文拟就此作一深入探讨,以为引玉之砖。
一、陇蜀营盐易盐史发端于周代秦早期,
“西盐”的出现即为标志
秦封泥“西盐”的出土,标志着陇蜀营盐活动和易盐历史在秦早期就已发端。20纪90年代末于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秦封泥实物,被誉为20世纪秦文化发展史上三大考古发现。其中的“西盐”“西盐丞印”等秦玺印封泥① 的存在,至少从历史实物的角度证明《说苑》《史记》《汉书》《盐铁论》关于秦穆公以来“盐官”的秦盐制度之不诬,而且由来已久。依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至迟在东周初的秦早期秦襄公、文公时代,营盐史和局地易盐史就已经滥觞。“西盐”封泥表明了从西地(西犬丘)输盐至关中地区的历史事实,而“西盐丞”的存在,说明营盐和易盐均非民间私贩,而是一种官家(诸侯国)职能。
秦封泥“西盐”之“西”,在“西盐”意义的内涵中占有重要地位。学界普遍认为“西”属秦汉陇西郡,单就封泥所指而言,西盐出于陇西郡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秦早期之“西”一地,其历史文化内涵丰厚,“西”地和“西盐”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秦人“西”地的最早历史文献记载是《尚书》。《尚书·尧典》有载:“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② 对此,祝中熹先生论说:“西垂,又名犬丘,即尧、舜时代肩负‘寅饯纳日使命的和仲一族西迁后所宅之‘西。它的位置,汉晋至唐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就是汉代陇西郡的西县。”③ 秦人“西”地的最早出土文献记载是《不其簋铭》,该簋铭文记载了一场大规模的征伐猃狁之战,周王命伯氏“羞追于西”。李学勤先生认为,“西是具体地名”,即秦汉陇西郡之西县,古称西垂④。实际上,西犬丘、西、西县等称谓,在《史记》《汉书》之中也不一致。从秦庄公到秦二世很长时间里,称西垂祖地“西”“西县”,不称“犬丘”和“西垂”,只有别族称“西”地为“西垂”。司马迁和班固有如此之分,溯源在周孝王时期。《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养马有功,孝王封赏他“保西垂,西垂以故和睦”,是他与犬丘大骆部族为邻的申国君主“申侯”直接说的。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到公元前2世纪时西都(西垂)故地仍有先祖宗庙,其地位依然重要。从殷商时期秦先祖中潏“保西垂”算起,到始皇统一天下,基本上包括殷商后期和整个周朝 (西周、东周)至少在八百年的时间里,“西”担当过陵园及宗庙重地的显要角色。
“西”地今天的地望,虽然专家看法不一,但基本不出大堡子山以上西汉水流域。《辞海》“西犬丘”条称:“古邑名。在今甘肃天水西南。原名犬丘,因另有一犬丘在东,故改名。西周时,秦国祖先大骆、非子居此。非子后改封于秦(今甘肅张家川东)。自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后人因称西犬丘为西垂。其后襄公、文公均曾居此。”①《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云,西犬丘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其余承袭《辞海》之说②。就大体方位来说,指称“西”为西犬丘未出大错,但不能具体而微。《说文解字》云:“西,鸟在巢上也。”小篆“西”字属鸟栖巢上之会意,系原始意义,符合“西”是秦人鸟图腾之说,当然可指秦人居住的地方。祝中熹认为,秦人为阳鸟部族,崇拜鸟或太阳。先秦文献频繁出现的“西山”即“兑山”或“崦嵫山”,是太阳落下的地方。远古的关中及中原居民,对日落西山有很重的神秘感,《山海经》之《夸父逐日》等神话可资为证。汉时“西”一度被称为“西丞”。《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云:“围章邯废丘。破西丞。”③《史记·樊哙传》云:“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④ 王莽时改西为“西治”。后刘秀复原名。《晋书·地道记》载:“天水始昌县,故西城也。”⑤《水经注》载“始昌峡”和“始昌城”位置,在今长道镇和盐官镇之间,最早于1942年由商承祚在《秦公簋跋》一文中提出。祝中熹却认为,其不会在今礼县红河附近⑥。他主张礼县永兴“店子上”,是古“天嘉县”所在,也即秦汉西县城故地。赵逵夫认为,秦汉至三国的“西县城”治地在今永兴镇和长道镇⑦。张希仁主张西县(西城)位置在今长道镇⑧。现今礼县永兴、西和县长道两镇分属两县,旧称“店子川”实为一地,连为一体。甘肃省博物馆藏出土于永兴、长道地域的春秋晚期秦剑,铭“羊(羌)侯永用”四字。可见,秦早期的“西”还处于秦人和西戎的杂居状态。
由这些史料和学家论述来看,周秦时期产“西盐”就在西汉水上游地区,包含地域上连成一片的相邻渭河流域。秦封泥“西盐”,为秦陇西郡西县官物,基本已成学界共识⑨。鉴于此,秦人的兴起,有论者以为与盐有关。周秦考古专家梁云先生说:“秦人从甘肃发源,陇南山地(即“西”地)盛产食盐,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食盐可以为秦国提供极大的财富,正是依靠陇南山地的哺育,秦人在其后的600余年间,逐渐扩大领地,直至扫灭六合,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⑩类似论断亦见于其他文献,但实际的史料支持还比较贫乏,考古支持也未展开,故“盐业强秦”之论目前学界研究尚弱。即便如此,秦早期“西鹽”的出现,标志着陇蜀营盐和局地易盐的发端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二、陇蜀营盐易盐史的演进路径:
秦“盐官”的设立及其继承与发展
据史可知,秦早期已有“盐官”体制,但并非他们的首创,其源在对西周“盐人”制度的继承和发扬。《周礼·天官·盐人》记载:“祭祀,共(供)其苦盐、散盐;宾客,共其形盐、散盐;王之膳羞,共饴盐,后及世子亦如之。”①这段史料给我们提供了周人关于盐政的几个重要信息:第一,周人已设盐官,从事盐政管理,此载“盐人”,应是秦人效法之盐官,《管子·海王》里载有“铁官”“盐官”之属,情况相类;第二,从事祭祀活动的盐已经分为两大类,有苦盐和散盐;第三,接待大宾客(朝觐诸侯)用形盐,小宾客(诸侯卿大夫)用散盐;第四,天子、王后、世子食用盐,则是带有甜味的岩盐(矿盐),即“饴盐”,为岩盐中的上品。形盐虎状是周人传统,《左传》中“盐虎形”的记载,表明秦人早期继承并吸收了周人盐文化,且崇虎传统也一并袭用周文化而来。
东周时秦人征盐税,春秋早期已经很普遍,穆公时期(前659年—前621年)官营盐业的记载今见已较详备。刘向《说苑·臣术》载:“秦穆公使贾人载盐,征诸贾人。”② 秦穆公不仅可以做战争的誓众之辞(《尚书·秦誓》),而且对向商人易盐的行为征盐税也很在行。他允许商人运销食盐,但要交税,并在中国西北部最早施行民营征税的盐制。秦穆公时期的盐商(贾人载盐),应非一般的散户,而属于“包商”一类。营盐易盐路线应该是从“西”地(西犬丘,西汉水、渭河上游地区)到雍城(汧渭之会,今陕西凤翔一带)。
到了战国时期,秦人以盐税来保证战争的经费,孝公时(前361年—前338年)官营盐业、局地交易成一时之盛。《汉书·食货志》载:“至秦(孝公)则不然,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③ 说明那时盐税已经相当高了。《盐铁论·非鞅》:“盐铁之利……足军旅之费。”④ 秦孝公行营盐业,已能保证战争费用,因其管理得法,而民不苦。“佐百姓而不急……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王利器《盐铁论校注·非鞅》指出:“秦孝公官煮盐业,如果不设置盐官,是无法管理的。”⑤ 此论甚笃。
战国中后期,秦官营盐业已成完整体系。秦惠文王时期(前337年—前310年),在产盐郡县基本设置了盐官。《华阳国志·蜀志》载:“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⑥ 看来,在当时的秦都咸阳,早就实行了郡县盐铁市官、盐铁(长)丞制度。蜀地成都各县设置盐铁市官,不过是秦都制度的推广和落实而已。同时,此期也允许私人煮盐营盐。《华阳国志·蜀志》还载:“(自秦惠文王灭蜀后)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⑦ 看来,惠文王不仅一改孝公时期商鞅盐业专卖制度,而且包户情形已经较为普遍。迨至始皇时期(前246年—前211年)秦产盐郡县建立盐官,已经成为政例,在中央则设少府主管山海(盐铁)资源。《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司马)靳孙昌为秦主铁(盐)官,当始皇之时。”⑧《汉书·司马迁传》则载:“靳孙昌,为秦王铁(盐)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① 秦朝时盐铁一政,各地设立盐官已很普遍。汉承秦制,从汉初的一些盐铁政策看,盐铁私营课税和民包政策并行存在。《史记·货殖列传》载:“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②足见营盐易盐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造富运动。对于发“盐财”的不轨盐铁商,秦国采用了迁徙荒远的措施,惩戒的同时还带动了僻远之地的经济开发。
纵观春秋战国,秦国不同阶段的“盐官”经营,有一个连贯而流畅的发展机理。穆公时盐业民营尚允,但必须纳税;孝公时商鞍变法,施行盐业专卖;到惠文王时期,“盐官”与民营征税的盐业“宽管”俱存;至始皇主政,秦人盐业政策差不多普遍定型下来,设置郡县“盐官”,同时施行民包政策,但对不轨盐商予以打击③。这种情况为汉初所继承,影响深远。
考古发现,今陇南礼县盐官镇北有以前的盐池及夯土遗迹,被当地人称之为“涝坝”,据传为汉代以前生产池盐,唐以后才转为井盐④。从考古情况判断,秦汉时期西县“盐官”(今礼县盐官镇)产盐规模最大且为池盐,唐以后规模缩小转为井盐⑤。杜甫陇蜀纪行诗《盐井》摹写盛唐时期该地产盐的情况:“青者官盐烟”,“煮盐烟在川”,“汲井岁榾榾,出车日连连”。说明官家营盐有其机制,而煮盐在川、汲盐水不断、每天盐车连连,说明该地营盐规模、产盐数量都不可小觑。从“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的易盐情况看,当时隶属成州长道县的“盐官”之地,官、私营盐易盐也很发达。所以正史对此明确记载:“唐有盐井六百四十,成州、嶲州井各一。”⑥《唐·食货志》:“盐井,在成州长道县东三十里,水与岸齐,盐极甘美,食之破气。有盐官故城。”⑦
三、陇蜀易盐史的变迁,表现为周秦以来
“盐官”演进的源与流
乾隆《西和县志》载“按汉初已设盐官”,盐井之发现想在周秦时代⑧。而秦早期玺印封泥“西盐”“西盐丞印”的发现,表明“西盐”发祥于周代秦人占据的“西”地(西垂、西犬丘),具体地望就在今陇南市东北和天水市西南的结合部。后来秦人崛起,因“马大蕃息”而被周孝王首封“秦”,乃至逐渐东扩跨越陇坂至关中而后成霸业,与盐业开发有密切关系⑨。秦汉时期西汉水上游设有“盐官”,表明此处营盐易盐规模已经相当盛大。遗憾的是,在此区域内进行的专门盐业考古调查工作还不多,目前还不能确定可以与秦封泥“西盐”等直接对应的遗址,研究還有待深入进行⑩。清《读史方舆纪要》载,此处“有盐井,水与岸齐,味甘美。汉时尝置盐官于此,唐亦谓之盐官镇。”①勾勒了一个大体的汉唐易盐文化发展脉络,郦道元《水经注·漾水》所记“右则盐官水南入焉,水北有盐官,在嶓冢西五十许里,相承营煮不辍,味与海盐同,故《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是也。”② 也是对前人论断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汉水上游盐官营盐的一个有力补充。
考察文献资料可以看出,从秦汉陇西郡到唐时陇右道,西汉水上游所产食盐的官营与交易,基本是在本土进行,还没有进入陇蜀易盐的商贸文化体系。但考古发现却证明,汉唐时期“西盐”民间交易(私营)的范围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北据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下通川蜀南丝绸之路起点,易盐商贸颇具规模。20世纪70年代在礼县盐官镇周边永坪、永兴两镇出土的铅质饼钱(别称“波斯铅币”)上,有西文字母,夏鼐先生认为是希腊文或波斯文,考古界定为两汉间流入的西方铸币(或为西亚),显然是陆上丝路贸易的遗留,或为陇蜀易盐佐证;20世纪80年代在盐官、祁山一带出土的三国“蜀五铢”“定平一百”“直百五铢”等蜀汉钱币,说明陇蜀商贸(包括易盐)颇为频繁;同期在盐官镇出土“突骑施钱”,有粟特字母拼写的回鹘文,属西突厥钱币,流通中亚,因贸易至陇蜀地域,黄文弼先生认为时在开元年间③。说明陇蜀古道从汉唐时期始,即是连接南北丝路的重要连线通道,在经营丝绸、茶马和盐方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只是其营盐规模相对于其他地方,因缺乏可靠史料记载无法佐证而已。
陇盐入蜀,是随着宋夏、宋金战争的发生发展,特别是宋廷经略陇蜀地带成为护佑朝廷的重要屏障,盐官之盐一度输入汉中,再转输进入蜀川。因此,盐官镇的营盐、易盐规模一度成为宋代整个行政区划里面重要的部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诏减西和州官卖盐直之半,先是州之盐官井岁产盐七十余万斤,半为官吏柴茅之费,半鬻于西和、成、凤州,岁得钱七万缗,为利州铸钱之本。”④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盐官镇的盐由官方确定为外输型,易盐范围向东扩展到京兆府(今西安)以东地区。盐官陇蜀营盐和易盐收入,一半用于官衙运行开支,一半行销陇蜀古道之祁山道、青泥道或阴平道沿线地域,所得利润作为利州地方发行货币的价值保障。因此,南宋实行的陇蜀易盐策略,实际已经扩展到了陇蜀的行政文化和金融文化,意义不同寻常。
实际上,早在宋仁宗庆历初(1042),因西北爆发宋夏战争,西川食盐匮乏,朝廷为筹备战备物资,允许池盐入川,陇蜀易盐文化由此抹上了主流色彩,但禁止民间以盐通商。盐官营盐一度进入四川,走上陇蜀易盐之路。《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且军兴用度调发不足……偿以池盐……又禁商盐私入蜀。”⑤ 这种陇蜀易盐以官府垄断的形式进行,一开始还是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体现出了其不切实际而松弛的情况。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益、利二路井盐(包括盐官镇所产之盐),在官盐之外可以自卖交易,“由市易司榷卖,其两路(益州、利州)井盐,须俟官无解盐,始听自卖,但此非经常之制”①。这个允许陇蜀民间易盐的“非常之制”持续了多长,无确切记载。但按时间推算,也就是几十年时间。南宋经略陇蜀,实际一直重视入川私盐的控制。这个控制的枢纽在陇盐南下和川盐北上的要地——兴元府(汉中)。淳熙十年(1183),兴元府都统制吴挺上奏朝廷称:“本司同安抚司增置赏钱,募人告捉盗贩解盐入界,见系出戍官兵把截去处严行搜捕外,有不系官兵出戍地分,乞行下沿边州郡督责捕盗官司搜捕。”② 吴挺作为南宋把守陇蜀的劲旅“吴家军”后期统帅,也是陇蜀一线重要的行政长官。他对落实朝廷的禁贩私盐入蜀政策身体力行,即便是当时戍守官兵涉嫌贩盐,也是严行搜捕,对戍地军营也不随意放过。他更知道兴元府延边地出盐的陇蜀要地阶、成、西和、凤州等州郡,需要督责搜捕,从源头解决陇盐私贩入蜀的问题。从吴挺的稽察部署和汇报朝廷的言辞可以看出,当时陇蜀易盐除了官营的主渠道外,私盐在陇蜀的交易规模不小。
元蒙初期,陇蜀易盐以官为主,兼有私盐和民间交易的情况,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后来由于朝廷增税主因,严厉禁止陇蜀私盐贩运,加上巴蜀井盐产量跃升,陇盐到达汉中以后向东入陕,基本鲜有南下入蜀的情况。这种陇蜀易盐的消弭状态,一直持续到明清乃至民国。稍有变化的是,西汉水上游的盐官易盐范围,在晚清民国不仅销往陇东南,而且向西北销往枹罕(今临夏)一带。
民国所出《盐务会刊》所载:“西和盐井(今属甘肃礼县)由井水熬煮,漳盐成块,销陇西、临潭、岷、漳,西盐(盐官井盐)不成块,销西和、武都、徽县等处,年产共约万担云。”③这已经是上世纪30年代再次收缩范围后的“西盐”行销局面。
民国到新中国初建的前几年,西和(礼县)盐官镇营盐年10余万斤,最多时达到了40万斤,易盐范围主要在陇东南地区。但随着交通的发达,外盐尤其青海雅盐进入陇东南,以低廉的价格消弭了西汉水上游盐官井盐的优势和特色。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式碘盐的供给成为时代背景下市场易盐的主流。盐官井盐因成本过高且无法降低,向东南地区的营盐易盐活动在21世纪初的十几年里艰难存留④,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四、探讨陇蜀易盐史的演进与变迁,
对丰富中华盐文化史有重要意义
陇蜀易盐史演进与变迁的辉煌篇章在唐宋时期,至元明清时期则各有特点。西汉水上游盐官,唐以后易盐更甚,宋时纳入陇蜀易盐体系,文献记载较为翔实。《文献通考》载:“蜀盐有隆州之仙井,卭州之蒲江,荣州之公井,大宁、富顺之井监,西和州之盐官,长宁州之淯井,皆大井也。”⑤ 在宋廷看来,西和州之盐(即唐长道县西盐)不仅属蜀盐系统,而且与其他产盐诸州一样,属于产能和易盐的大井,已经在全国盐产地中占有一席之地。《宋会要辑稿》载,绍兴二十八年(1158)“见利州路西和州盐官镇盐井岁出盐七十余万斤……契勘盐官盐引给秦凤、永兴军一路。”①说明西和州盐官镇盐井的官营盐年产量达到70余万斤,私盐数量尚不包括其中。朝廷“各申严行下阶、成、西和、凤州禁止,毋得透漏,如未觉察,守令并取旨,重作施行”②。可见,盐官镇之出西盐在汉中入川,民间易盐之风不仅屡禁不止,而且还影响着朝廷对陇蜀之盐贸易政策的制定。
元蒙哥攻蜀时期,盐为军备“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③。盐官镇所出井盐大部分随陇蜀道(水道嘉陵江漕运)进入四川。这种情况持续到元世祖继位,阆州(今阆中)帅杨大渊于中统三年(1262)获准“于利州、大安军以盐易军粮”。但随着统治的逐渐巩固,元朝采用了官营之外易盐入川政策:“禁蒙古、汉军诸人煎、贩私盐。”西汉水上游的盐官镇营盐、易盐,遂主要以陇蜀道(汉中以北)区域“内运”“内销”为主。
明清时期,西汉水盐官因受易盐范围和规模限制,营盐状况已经与宋元时期大相径庭。《明史·食货志》载:“陕西灵州有大小盐池,又有漳县盐井、西和盐井。洪武时岁办盐,西和十三万一千五百斤有奇,漳县五十一万五千六百斤有奇,灵州二百八十六万七千四百斤有奇。”④ 显然,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县)、漳县、西和(盐官镇)三处产盐之地,盐官年产盐13万余斤,属最少,与宋代年产盐70余万斤相比,规模已骤减。易盐范围东不过秦陇,南止于汉中。明嘉靖杨典《盐井碑记》载,盐官镇“其盐,西南通徽、成、阶、文、礼县、汉中,东通秦陇”⑤。这个范围就在陇蜀古道的主体秦州至汉中一段的范围内,显然和元代相异甚大。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朝廷营盐规模的不断扩大,盐官镇产盐量一度超过了宋元时期,达130余万斤,易盐范围含西北至巩昌、临洮二府及河州一带⑥。清初,盐官镇营盐划归河东监管,康熙朝改令甘肃巡抚就近管理,雍正朝地丁银征税,盐官镇易盐归民自营,后改为招商运销。嘉庆、道光年间以票代引在漳县、西和(盐官)、惠定、花定、白墩子五处设立盐局,光绪时盐官在籍盐户250户,营盐规模(产销量)回落至23万斤⑦。
就整个中华盐文化史来看,陇蜀易盐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盐业的初始,古文献记载早在神农时代就已显现。至周代有形盐之习,西汉水盐官有所继承。东汉郑众注疏《周礼·盐人》时说:“筑盐以为虎形,谓之形盐。故《春秋传》(《左传》)曰:‘盐虎形。”⑧盐作虎形,象征威武。西汉水盐官镇民间传说称,大锅煮盐成品,多以碗形,也有人形、虎形,通为一理。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在肯定神农时代“煮海为盐”之说的同时,结合两淮盐区建有两处盐宗庙的情况,指出中国古代盐的来源有二:海盐和池盐(井盐)①。从“西盐”到“盐官”的陇蜀营盐易盐史变迁,无疑是池盐—井盐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比较而言,古文献记载远古盐业初兴,以东部地区为多,而关涉西北盐业渊源,似乎较为欠缺。但从现状看,我国西北在甘肃、青海交界之处,有众多盐湖。其最著名者如青海察尔汗盐湖、茶卡盐湖等;甘肃境内以高台盐池和靖远小红沟盐池,民勤苏武山、白亭、马莲泉、汤家海盐池和皋兰县八盘、红盐等盐池较为有名②,似可为陇蜀池盐(井盐)的营盐易盐体系做一个注脚。我们翻检文献发现,自汉代以来关于西北盐业,即广义“西盐”的记载并不少见。《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注称:“(陇西郡)秦置……有铁官、盐官。”③ 就是说,在班固所处的汉武帝时代,秦在陇西郡设置盐官,负责王朝对盐业的管理并课以税赋,从“西盐”到“盐官”已是人所共知的史实。汉以后诸历史朝代,随着陇蜀军事、交通、经济诸种情况的演进与变迁,陇蜀易盐的演进随时代而起落。整个陇蜀易盐史的变迁,反映了中国西北—西南一线营盐易盐史的主要特征和内涵。由此表明,陇蜀易盐史早就成为了中华盐文化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我们对此疏于探究而已。
(责任编辑:周 聪)
From “Western Salt” to “Salt Official”: the Evolution and Change of
theSalt Trading History of Shannxi and Sichuan
PU Xiangming
Abstract: The military and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Shannxi and Sichuan existed in the Zhou and Qin Dynasties. The excavation of “Western Salt” in the seal mud of the Qin state indicates that the salt activities and the history of salt exchange between Shannxi and Sichuan have been started in the early Qin Dynasty. The evolution from “Western salt” to “Salt official”has been basically completed in the transportation betweenShannxi and Sichuan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the evolution and changes of the salt changing history of Shannxi and Sichuan , the establishment of salt officials and the exertion of their mechanism participated in the whole historical process after the Han Dynasty, which basically belong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alt official” system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change of the history of salt marketing and trading in the whole Shannxi and Sichuan area is reflect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salt officials”system since Zhou and Qin Dynasties, which clearly reflect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salt change in the northwest-southwest of China. This shows that the history of salt trading in Shannxi and Sichuan has undoubtedl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alt culture.
Key words: Zhou and Qin Dynasties; Western salt; Salt official; Shannxi and Sichuan; salt marketing and Salt Trading; the evolution and change
作者简介:蒲向明(1963-),男,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及其生态保护研究”(项目编号:17BGL213)的阶段性成果。
①古敏.战国策注译[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38.
②薛秉辰.关中形势考[M]//杨虎城,邵力子,修.宋伯鲁,吴廷锡,纂.(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1-12).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6351.
③蒲向明.從文献书写“陇蜀叙事”到现实意义“陇蜀之城”:西汉水流域秦汉文化资源与陇蜀之城创建[J].档案,2019(2):36-42.
④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0:2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