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引(十九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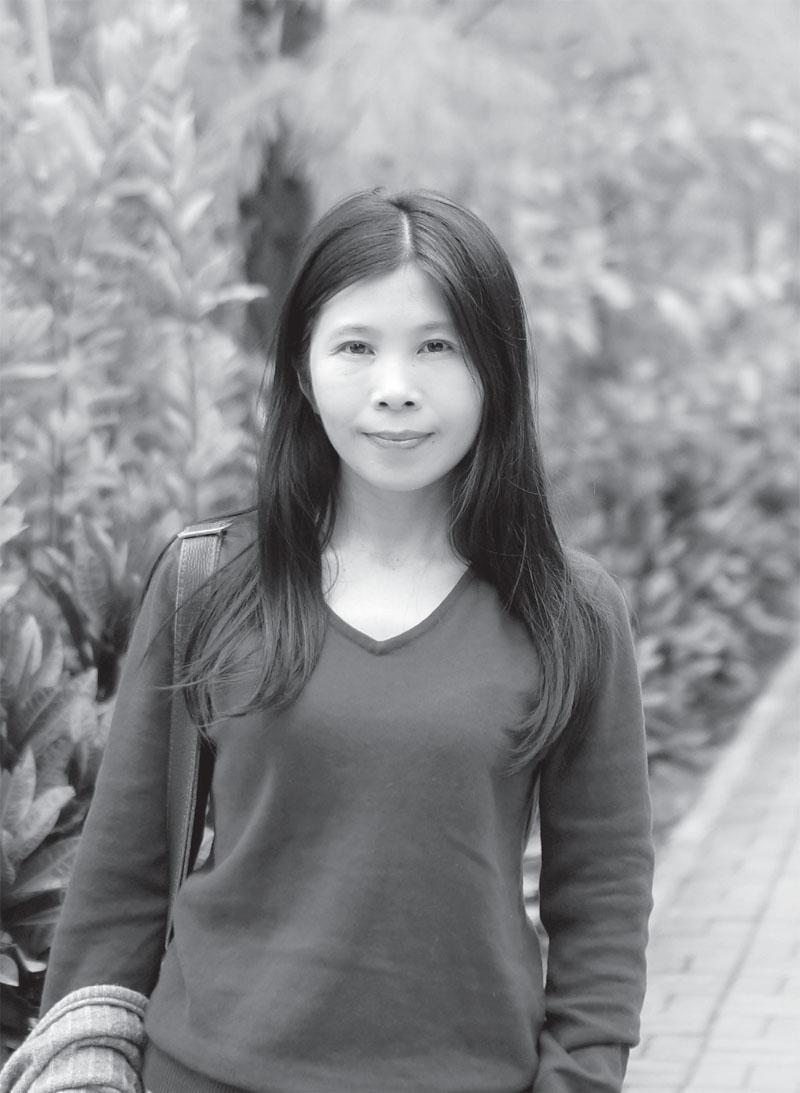
陆辉艳
陆辉艳,1981年出生于广西灌阳。中国作协会员。出版诗集《湾木腊密码》《高处和低处》等。作品发表于《十月》《天涯》《青年文学》《诗刊》《星星》等刊物。曾获2017华文青年诗人奖、2015青年文学·首届中国青年诗人奖、第八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参加诗刊社第32届青春诗会。
灰 雁
一直盯着岛上那些神秘的翅膀
白鹭,丹顶鹤,天鹅,孔雀
黄河突然变得轻盈
一阵振翅的扑扑声,接着是
游客们的惊呼:灰雁——灰雁——
遥远地,好像在喊我
哎——我在心里答应
好像凭借声音,才能确认自己
在人间的痕迹
——多么艰难。没有翅膀,更不能摆脱
来自大地的永恒召喚
一整个下午,我的视线追寻着
那群灰雁,它们有时代替我飞到远处
有时歇息在湿地的岸边和芦苇丛
后来天黑了。而我已无须确认
它们在夜晚是否还在继续
撞开空气的阻力。我知道
但我不再表述为飞翔,我称之为开阔
银河之夜
我也有一条铁道,通往银河
它铺在白云上,冷冰冰的,比彩虹还动人
那天凌晨,我生下一个孩子
他清脆的哭声像是从月亮里传来
他有银河系一切肃穆的美和悠远
他游荡在我黑夜的铁道上。没有一辆列车
沿途到处都是,紫色闪光的龙胆花
我哭泣
为那个从硝烟里
抱出满身尘土的孩子的
摄影记者,我哭泣
他跪在地上嚎啕
是一轮绝望的落日的样子
为那个躺在遥远土地上的女人,我哭泣
铁轨旁,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奶水还在滋养襁褓中的婴儿
为隔离墙上秘密打开的一道门缝
为陌生人对另一个陌生人的善意
为那匹断腿的骆驼
为荒漠中的一次日出
我哭泣,为并非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当我的世界发生崩塌
为何会突然失语,再也淌不出眼泪
我用键盘记录下它们
好像在讲述一个局外人的经历
平静,客观,剔除情绪地。直到
偶然的一天,在众多事物中
发现自己与世界的永恒交叉与重叠
在五爱屯
陌生的田野,我又看到了它们
稻草捆儿排成方阵,立在稻茬上
暮色中仿佛疲倦的士兵,即将卸下盔甲
而绑扎它们的手,一定是沉重的
有力的,紧握过生活的
与这一切的井然不同
一群黑山羊走在路上
零星,散漫,自由
有一只小羊落在后面
它总是为途中的事物停下来
当它细嗅一朵黄色小花
我靠近了它
多么澄澈的眼神啊
它竟然没有惊慌而跑开
它竟然将丰盈的更望湖带到我面前
因为这份简单的信任,我心存感激
并爱上了这里的黄昏
陡 峭
山脉起伏,白桦林闪退
一路跟着绿皮火车的隐喻飞奔
为记忆保存,倒退的镜头
直到失去参照物
但我没有看到北极光
在北极村,我的导师说:
注意,陡峭感
我没有登上悬崖顶
黑熊安静,狍子天真
却一直没有蹿出密林
正如我尚未写出,一首诗中突然的美
和转弯的诗意
可以比天空更让人惊诧
比额尔古纳河更幽深
因而我垒石头,在一首诗和现实之间
构筑一个锋利的锐角
因为一个诗人
雨下在汨罗江上
雨因此有了确切的样子
一个写诗的人走过洞庭湖,人间
从来没有如此辽阔
沧浪之水有清浊
香草枯了又长
世上的尘埃,让时间
开口说话,让词语从内部
获得它的锋芒和重量
余 生
还想去一趟草原
不用再担心别的了
在风中伫立,是最重要的事情
去任何一片草原都好
必须要有芍药和野罂粟
在各自的天空下,静静开放
互不打扰,但共同形成风景
牛羊低头吃草,偶然抬头的目光交换
像多年的朋友重逢
一切在安然中
有时,草丛深处一只遗鸥的突然振翅
提醒我们拥有的时间
是真切而具体的,可触摸的
在洛古河岸
捡到了玛瑙的人
在岸边发出惊呼
人群拥上去
他们的脸庞
有洛古河的蓝色和喜悦
我没有捡到玛瑙
在斑驳的石头中间
一根白骨,突兀地躺在那儿
我没有声张
甚至没有惊动一棵老鹳草
多年前的一天
妈妈坐在椅子上,默默地擦眼泪
岩石和大地没有流淌出蜜糖
来调和生活的苦与涩
爸爸那时还没有生病
还能一阵风似的走在路上
他低着头想说点儿什么
屋后竹林里一群鸟儿,翅膀拍打叶子的声音
传到屋子里,它们啼叫着:
不可比,不可比
爸爸走到屋外,滑稽地学它们的啼叫:
不可比,不可比
妈妈终于笑起来,来自生活的暗伤
仿佛因为一群鸟儿的到来,而减少了重量
她给爸爸收拾行李,送他去搭乘一辆
前往东莞某个工地的夜行大巴
壁 虎
几乎是一瞬间的,它的影子
猛然映在玻璃杯上
我的手迅速抽走,抬起头
那是一只壁虎,趴在落地玻璃上
静止得像是没有生命
它的存在,是为了与这喧闹的餐厅
形成某种对立?
对面的人,还在滔滔不绝
谈论暗物质
我喝了一口茶
——杯子上的影子消失了
包括落地玻璃,那儿空空的
壁虎仿佛从未出现
它产生于某个念头
最后又消失在某行诗中?
戒备之心
那一年,父亲捧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又欣喜,又忧愁
天黑了,他去了堂伯家
坐下来还没开口
堂伯就开始骂他的大女儿
我的堂姐,职校刚毕业
一声不吭,勾着头
蹲在火塘前烧一锅饭
干竹枝燃得噼噼啪啪的
后来父亲双手空空地
退出那扇门,仍听得见
堂伯骂人的声音
偶尔我回老家
将要经过堂伯家
远远地,抱着孩子的堂姐
就会闪进屋子里
十七年了,她仍然对我
怀有一份戒备之心
而她不知道,我对世界
怀有的谦卑之心,足以贴近地面
熄灭胸腔里噼啪燃烧的竹枝
猫儿山以东
有时,我独自一人
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仿佛有风在推着我
当我到达华南之巅,我看见了
低处更为美妙的事物。在它的东边
一条通向纵深的小径
我沿着它,越走越远
渐渐远离了高处和众人
渐渐的,听不见
他们的谈笑声了
我穿梭在灌木丛中
群山将我掩藏
群山啊,藏着顽石像藏一块璞玉
那么窄,又那么广
指 引
我的丈夫,在细雨的夜晚
迷路了。陌生的草木,标语牌和石堆
露出它们简笔画似的外形
他感到自己也在变成线条。疑惑使他
减缓车速。一团白雾指引着他
“就像神的召唤”
往西,一直往西
他回到了熟悉的路上
“应该是个消纳场。”后来他说
我想起那个位置
曾经是个打靶场
似乎还充当过法场
有次郊游路过,多看了一眼
蓊郁树木遮住静静的时间
但我没有告诉他这些
只是握紧他的手,并从心里
感激那晚的白雾
前进的,后退的
我爱上了黄昏 爱上了在湖边
两手空空地行走
心无旁骛 风一样地走
有时会走到时间的前面去
但那里往往空无一人
这巨大的沉寂使我惊惧得转身
我沿路返回
却发现这个举动比前进更难
那些向前跑着的
和倒退着行走的人
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
同时抵达湖的转弯处
同时亲近着春天的事物
他们手里捏着的迎春花
像逻辑学里的哑谜
深奥、模棱两可
前进,同时也在倒退
或者相反,在每一次倒退中向前
离开,并看得清身后的一切
生活已不能对称
仿佛从不曾存在这样一个坡地
它在春天长出荒草
如同他头部的一大块凹陷
发根白茫茫起伏
呼应着土地的形状和生长
清理它们的那个人,去了省城医院
年少时他曾独自攀上悬崖
时空是平面的
他失去的记忆,正被空白填满
渐渐覆盖了今天的事物
生活已不能對称
类似孤立的宇宙
左半球的世界
被一艘幻觉的火箭,轻易托起
太沉了,昨天的夕阳落到今天
夜晚变得短暂
自然处处显示出它的平衡哲学
他放弃复杂的语言
仿佛从不曾拥有
有翅膀飞过的窗口
巨大洁白的翅膀
从傍晚的窗口飞过去
但它们总是不够轻盈
并非因为不远处是机场
并非它们频繁地将我
从某处,带往另一处
我坐在那张椅子上
看它们静静地朝向地面
想起多年未见的人
带着好看的笑容出现在街角
它们亮起的灯盏
储存在我记忆的博物馆
父亲来电
出现在屏幕上的父亲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永远保鲜的人
那是2017年,他从电话里
向我倒出自己的隐忧:
未修好的房子,土地上的债务,衰老
疾病以及明天的去处
我一声不吭地听着
像一只灰色的编织袋,空着双手和将来
如果我开口安慰他,我怕说出的
会变成黑暗中的回音
会将他转交给我的无助,无形中放大数倍
因此我沉默着,直到他——
转移了话题,他问起我弟弟
二十年前他惩罚他,提起他的双脚
弟弟悬空倒立,双手乱抓着空气
他恐惧的,无助的尖叫声
现在终于变成了我的——
从湾木腊去鲍山
想从我住的地方,去一趟鲍山
想让内心的风暴停下来
在那场飓风中
我向众人摊开了掌心
从来没有预想过这一天
自己的阴影
会分散在万物边缘
那时,所有人都小心翼翼
几乎不向我提及
生死和命运的字眼
他们只给我一片
向日葵的光芒
他们知晓一切
包括我的羞愧,我对命的私心
包括无言,在那时
是最有力的拥抱
我视为管鲍之情,我视为在这人世
还能继续下去的
理由之一
对 话
——仿斯特兰德
你是誰?
一个病人。一个时刻想要脱离大地的人。
你是谁?
我是我。一个女儿的父亲。
你多大了?
二十岁。
你女儿多大了?
三十七岁。
你多大了?
刚刚出生。我所有的经历
不过是从子宫爬到人世的距离。
你从哪儿来?
大海上。一个看不见光的地方。
你从哪儿来?
从地狱那儿经过,又回到刚来的地方。
一个人退到一张白纸
一个人忍受了全部
一个人放弃时间的秩序、终点和命名
一个人将抵达永恒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