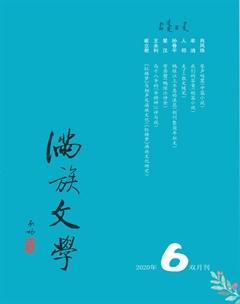《红楼梦》与相声及满族文化
崔立君
谈《红楼梦》与满族文化的话题,大概不会有人感觉奇怪。毕竟《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出生在清朝,是满族人,《红楼梦》书中也充满了满族的文化民俗描写。但把相声话题放到《红楼梦》里边一起谈,可能会让人感到诧异。相声与《红楼梦》有什么关联?相声与满族和满族文化又有什么关联?《红楼梦》里有大量的诗词歌赋以及民俗文化活动和戏剧表演的描写,可没看见关于相声的描写呀?不错,书中确实是没有关于相声的直接描写,但不等于与相声没有关联。细读之,《红楼梦》不仅与相声有关联,而且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相声在那个时代的存在和影响。而相声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又与满族有着深深的不解之缘。
我们先来谈谈《红楼梦》与相声的关联。
了解相声历史的人,都清楚相声一词经过“象生”——“像声”——“相声”这样一个衍变过程。“象生”一词最初是在哪本书籍中出现的?似乎无法查实。但最初出现的这个词,并不是指今天的相声,其外延是比较广泛的,画画、模拟、口技、杂耍等等都包涵在内。经过漫长的发展,这个词逐渐剔除了其它的表现形式,发展成单一指向,就是现在的相声艺术。而如今能够查到的最早体现与相声艺术相关表述的书籍,就是《红楼梦》。虽然“象生”这个词在《红楼梦》中仅仅出现了一次,但对我们研究《红楼梦》与相声的关联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过去不少相声老艺人曾把朱绍文认定是相声艺术的创始人,可侯宝林等人经研究后推翻了这个说法,考证出朱绍文之前就有相声艺人。现在曲艺界比较明确的说法,最早有记载的相声演员是张三禄。也有说朱绍文曾向张三禄学习过,应该算是张三禄的徒弟,但这一说法存有很大的争议。更多的说法是朱绍文把相声这种艺术形式予以确认,并首开先河正式收徒,开启了一代一代的师承模式。相声从业者的家谱,打他开始,一直传到了如今的第十代。所以,朱绍文在相声历史上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红楼梦》里出现“象生”一词,是在第三十五回。薛蟠惹哭了妹妹宝钗,后又将她逗笑。宝钗笑罢对薛蟠说:“你不用做这些‘象生了”。
薛蟠是凭什么本事把妹妹逗得破涕为笑的呢?他左一个揖,右一个揖,语言也诙谐幽默,既有动作表情,又伴之以怪异的腔调,这和如今的相声表演何其相似。这里的“象生”一词,显然既不是指画画,又不是指口技,说是模拟倒还贴切,而模拟恰恰是相声组织包袱的一种重要手段。所以,我们可以以此推断,宝钗口里的“象生”就是今日之相声。据此,薛蟠兄妹肯定看过相声,推而言之,曹雪芹看过相声也是无疑的了。可曹雪芹生于1715年,而朱绍文生于1829年,比曹雪芹来到人间要晚一百多年,张三禄具体出生年月不详,他比朱绍文大是肯定的,但也大不了很多。曹雪芹提到的“象生”,显然更早,那么无论把张三禄还是朱绍文定为相声的创始人都是说不通的。由此可见《红楼梦》在相声历史的考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有人会说,曹雪芹既然看过相声,那么《红楼梦》中描写了四百多个人物以及他们千姿百态的活动,为何没有直接描写相声这种艺术形式而仅仅是提到了一嘴呢?我的解释是,相声被承认为艺术,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此之前,相声一直被认为是下贱的“玩艺”,上不了大雅之堂。那么退到《红楼梦》的时代,贾府这样的高雅府第,是不能容许它“玷污”大观园的。而贾府之外的社会上,也并不太把它当回事。另外《红楼梦》中描写的艺术表演,主要是戏,因当时在元杂剧的基础上,戏剧艺术已发展得十分可观,被视为高雅艺术。
是不是使人发笑的东西都是相声呢?当然不是。笑话是纯粹逗人乐的,但它还不是相声,相声却是在笑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红楼梦》中有许多笑话,统统归为相声是不妥的。笑话一般短小、简单,而相声则复杂得多,它已经有了较完整、较曲折的故事情节(纯技巧性的段子以及后来发展的知识性段子除外),而且有独自的特点,就是采用多种手法制造“包袱”,讲究铺平垫稳,富于表演性。笑话是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的。一个笑话可以发展成一段相声,但一段相声绝不可以仅仅是一个笑话。对《红楼梦》中的笑话又要具体分析。有的虽称之为笑话,实际上已酷似相声了。让我们来看看五十四回里贾母讲的那段笑话吧:
一家子養了十个儿子,娶了十房媳妇儿。惟有第十房媳妇儿聪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说那九个不孝顺。这个媳妇儿委屈,便商议说:“咱们九个心里孝顺,只不象那小蹄子儿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说他好。这委屈向谁诉说去?”有主意的说道:“咱们明儿到阎王庙去烧香,和阎王爷说去,问他一问:叫我们托生为人,怎么单单给那小蹄子一张乖嘴,我们都入了夯嘴里头。”那八个听了,都喜欢说:“这个主意不错!”第二日,便都往阎王庙里烧香。九个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个魂专等阎王驾到,左等不来,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见孙行者驾着筋斗云来了,看见九个魂,便要拿金箍棒打来。吓得九个魂忙跪下央求。孙行者问起原故,九个人忙细细的告诉了他。孙行者听了,把脚一跺,叹了一口气道:“这原故幸亏遇见我!等着阎王来了,他也不得知道。”九个人听了,就求说:“大圣发个慈悲,我们就好了!”孙行者笑道:“却也不难,那日你们妯娌十个托生时,可巧我到阎王那里去,因为撒了一泡尿在地上,你那个小婶便吃了。如今你们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便撒泡你们吃就是了。”
这是一个完整的段子,说它是相声不合适吗?你看:铺平垫稳,层层收裹,攒底的“包袱”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相声演员稍加排练,在舞台上立起来,岂不是一段十分精彩的单口相声?
类似的段子书中还有。如第十九回,宝玉给黛玉讲扬州黛山的林子洞里闹耗子精一段,就很值得琢磨。在此不妨抄录下来:
林子洞里原来有一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老耗子升座议事,说:“明儿是腊八,世上的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里果品短少了,须得趁此打些劫来才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了个能干的小耗子去打听。小耗子回报:“各处都打听了,惟有山下庙里米最多。”老耗子便问:“米有几样?果有几品?小耗子道:米豆成仓。果品却只有五样:一是红枣,二是栗子,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老耗子听了大喜,即时拔了一枝令箭,问:谁去偷米?一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又一个耗子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各自领命去了。只剩下香芋。因又拔令箭问:“谁去偷香芋?”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应道:“我愿去偷香芋。”老耗子和众耗子见他这样,恐他不谙练,又怯惴无力,不准他去。小耗子道:“我虽年小体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这一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众耗子忙问:“怎么比他们巧呢?”小耗子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叫人瞧不出来,却暗暗儿地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这不比直偷硬取的巧吗?众耗子听了,都说“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变?你先变个我们瞧瞧。”小耗子听了,笑道:“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毕,摇身说:“变”。竟变成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众耗子忙笑着说:“错了,错了!原说变果子,怎么变出个小姐来了呢?”小子现了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家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芋。”
如果孤立地看这一段,似乎不甚可笑,但放在书中具体情节里去体会,则令人发笑。因为这个段子是宝玉专为黛玉创作的,所以撩得黛玉笑着和宝玉打闹起来。这段一开始就随着故事的展开层层装“包袱”,把读者(即听众)迷惑住,待时机成熟,猛地抖开,使人幡然醒悟,原来什么林子洞、黛山、香芋,不过是林黛玉的谐音。谐音“包袱”是相声中常用的
贯口,是传统相声中一项重要的表演技巧,一方面体现演员嘴皮子的功夫,同时往往在一大段贯口后轻轻一转,出其不意地抖响一个“包袱”。如《卖布头》《地理图》《菜单子》等等。新相声段子也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着,如《挖宝》《花花世界》《心中有数》等等。《红楼梦》第四十二回里宝钗给作画的惜春开了一个单子,在念单子时林黛玉插了话,宝钗又与黛玉一问一答,把众人都逗笑了,这和贯口活的相声实在没什么两样。让我们看一下:
宝钗说道:“头号排笔四支,二号排笔四支,三号排笔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须眉十支,大着色二十支,小着色二十支,开面十支,柳条二十支,箭头朱四两,南赭四两,石黄四两,石青四两,石绿四两,管黄四两,广花八两,铅粉十四匣,胭脂十二帖,大赤二百帖,广匀胶四两,净矾四两,……顶细绢萝四个,粗萝二个,担笔四支,大小乳钵四个,大粗碗二十个,五寸碟子十个,风炉两个,砂锅大小四个,新瓷缸二口,新水桶二只,一尺长白布口袋四个,浮碳二十斤,柳木碳十二斤,三屉木箱一个,实地纱一丈,生姜二两,酱半斤——”黛玉忙笑道:“铁锅一口,铁铲一个!”宝钗道:“这做什么?”黛玉道:“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我替你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啊。”众人都笑起来。宝钗道:“颦儿,你知道什么!那粗瓷碟子保不住上火烤,不拿姜汁子和酱先预抹在底子上烤过,一经了火,是要炸的。”众人听说,都道:“这就是了。”黛玉又看了一回单子,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画个画,又要起这些水缸箱子来,想必糊涂了,把他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探春听了,笑个不住,说道:“宝姐姐,你还不拧他的嘴?”
在这一大段里,若作为相声的一部分来剖析,宝钗念单子就是在组织“包袱”,而黛玉的打岔,则是在抖“包袱”,也就是相声术语所说的“插科打诨”。看来这个“包袱”是成功的,于是乎“众人都笑起来”。这时宝钗又有一番解释,用相声术语说叫“缝”,但刚刚“缝”好,黛玉又一次抖响“包袱”,再次把人逗乐。曹雪芹的这段描写,完全符合相声结构,我们只要把其中人物对话改为甲、乙二人的形式,原词挪到一段相声中去,表演起来,舞台效果一定是不错的。
《红楼梦》中运用相声手法不乏其例,而且“包袱”的种类也灵活多样。
“重复”,也是相声组织“包袱”的一个手法。在一大段台词里,某一词语反复出现,就可能引人发笑。柏格森对此解释说:“因为生动活泼的生活不应该重复。哪儿有重复,有完全的相似,我们就怀疑在生动活泼的东西背面有什么机械装置在活动。”我们十分熟悉的优秀相声《如此照相》中有这样一段:
“凡到我革命照相馆,拍革命照片的革命同志,进我革命门,问革命话,须先呼革命口号,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则革命职工坚决以革命态度不给革命回答。致革命敬礼。”
这是典型的运用“重复”手法组织“包袱”。在《红楼梦》第二十七回里也可见到这样的“包袱”:
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几丸延年神验万金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便给那边舅奶奶带了去。”
“奶奶”一词的反复出现,把李纨、凤姐都逗乐了。这里除“重复”外,还有其复杂的成分,即凤姐说道“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
《红楼梦》中运用相声手法的地方是很多的,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么相声与满族文化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相声是中国独有的民间艺术形式,尽管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表演,但也都是受中国相声艺术的影响形成的。相声属于曲艺,而曲艺里的多种形式都与满族息息相关。满族人似乎天生喜爱曲艺,曲艺界里向来也是满族人居多。好多影响比较大的曲种都是诞生于北京或天津、河北等周边地区,这与满人入关后,统治地位确定、社会逐渐平和、文化也相对繁荣有极大关系。子弟书与八角鼓是最能代表清代艺术成就并具有清代特色的曲艺形式,而这两个曲种都是满族的曲种。子弟书是乾隆年间兴起的一种鼓曲艺术,因首创于八旗子弟中间而得名。而著名子弟书大家罗松窗、韩小窗都是满族人。八角鼓,是子弟书的姊妹艺术,也是清中期满族的曲艺种类,因用满族乐器八角鼓伴奏而得名。后来在八角鼓的基础上又独立出来一个曲种,就是单弦。其它诸如评书、快板儿、时调、琴书等也都为满族人所钟情。相声艺术表演的自由度比较大,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过去相声演员不少都同时涉猎很多其它曲艺形式,有的在其它曲艺的表演方面也相当有腕儿。传统相声作品里也经常穿插这些兄弟曲种,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学唱其它曲艺形式是台上常见的。
曾振庭、荣剑臣、德寿山、常澍田、阿彦涛、春长隆、恩绪这些清代曲艺名家,都是满族人。快板、西河大鼓、铁片大鼓的满族演员更多。北京琴书的创始人关学曾是满族人,虽然当今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名字了,但他的孙女关晓彤现在是家喻户晓的影视明星。孙女的知名度超过了爷爷,但在艺术领域里的贡献显然还无法与爷爷相提并论。
关于相声,曲艺界有一句话:“相声,可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现在公认相声的祖师爷为东方朔,但这只是从幽默滑稽的风格那里去追溯的,并不是说打汉代就有了相声。相声的真正形成,则是在清朝,是诞生在满族人的生活环境里。朱绍文虽然不是满族人,但属于汉军旗人,足以说明与满族的密切关系。与朱绍文同时期有影响的阿彦涛,也是满族人。第一代相声艺人,从朱绍文的带拉师弟阿彦涛开始,现在能查到资料比较详细的相声前辈里,满族人都占有极大的比例。直到今天,相声界里公认的常氏、侯氏、马氏三大体系,都直接或间地流淌着满族的血脉。常氏相声不用说了,其缔造者常连安是满族人,他的后代常宝堃、常宝庭、常宝霖、常宝华以及再后代常贵田、常贵德直至当代喜剧人常远这一代,自然也都是满族人。侯氏相声的创始人是侯宝林,他也是满族人。虽然马氏相声的创始人马三立是回族人,但马三立的外祖父恩绪(阿彦涛徒弟)也是满族人。另外,马三立的代表作《买猴儿》《统一病》《十点钟开始》《似曾相识的人》等都是由著名曲艺作家何迟创作的,而何迟也是满族人。现当代的满族相声演员白全福、苏文茂、黄铁良、杨少华、赵霭如、郭启儒、赵佩茹、王培元、佟守本等,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另外,值得骄傲的是曲艺界里仅有的两位烈士常宝堃、程树棠都是满族人。他们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祖国慰问团赴朝鲜战场慰问演出时,牺牲在前线。
解放后,侯宝林等人于1950年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而这个小组的成员里有一半是满族人。他们还邀请了老舍、罗常培、吴晓玲这几位驰名的大作家、语言学者,帮助相声艺人净化语言、提升格调、指导新作品的创作,对相声艺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而这几位大家也都是满族人。
笔者作为一个相声作家,有幸受到侯宝林、常宝华等大师级相声艺术家的指教,并与常贵田、王培元、侯耀文、杨少华、王平等多位知名满族相声艺术家有过合作,深切地感受到满族艺术家对相声艺术的巨大贡献。
相声艺术到底产生于何年何月,目前曲艺界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说法,有待于專家学者的进一步论证。本文的宗旨是阐明《红楼梦》那个时代就已经有相声艺术了,所以无论张三禄还是朱绍文,都不可能是这门艺术的始祖,这也是《红楼梦》一书对相声考证和研究做出的贡献。而在相声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里,满族对这门艺术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这些都是应该载入史册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红楼梦》与满族文化与相声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此关联还有待于专家学者进一步挖掘。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