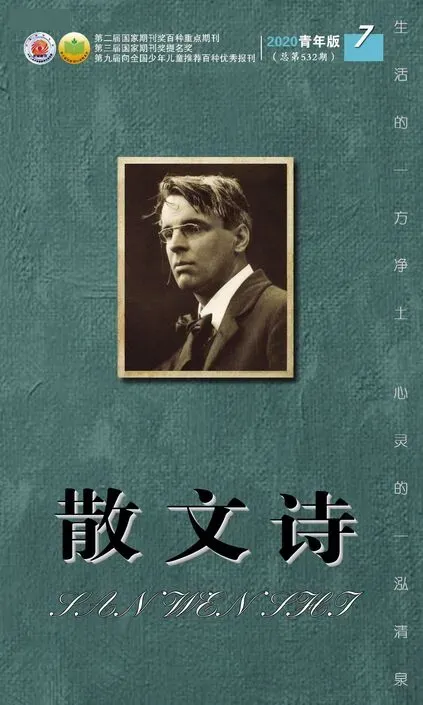母亲在黑夜唱起歌谣
甘 健

图/蔡建勋
我一直不喜欢黄昏。
是的, 确实, 不喜欢。
你眼睁睁地看着夕阳无可挽回地坠落, 田野里、 水塘中飘起暮霭, 漫长的黑暗从此刻出发。 黄昏, 像一个坑, 一天的琐碎,一家的悲欢, 都选择流向这里。
这样的时候, 似乎只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我看见生产队长背着手, 脸色沉重地, 从东头到西头, 挨家挨户地踱过去。
他跟每一家的大人低语几句, 然后又似乎不情不愿地转往下一户人家。 我感觉他对每一户说的都是相同的话, 他一直在做复制的工作, 而这些话显然是不方便粗着脖子、 鼓着腮帮在大喇叭里喊叫的。
本来安静的村庄在队长走访过后一下子长出许多喧闹的声音。有女人哭着骂自己的男人没有用的, 有男人怨自己家里要供养那么多吃闲饭的嘴的, 邻居家的二狗, 从屋里冲出来, 边哭边跑,后面跟着努力追赶着他的二姐。
我那时大约十岁, 是个懂事的孩子, 早就已经懂得察言观色了。 我敢肯定, 是队长刚才说的话直接点燃了乡村的沸腾。
我的父母, 总习惯在黄昏的时候发生争吵。 这一天, 他们放弃了争论, 他们在讨论一个严肃得多的问题。
耳尖的我从他们嘴里依稀听懂了一个词——
返销粮。
在我当时的理解范围内, 返销粮大概是在每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拥有的, 但也不会轻易拥有, 那是对抗灾难的最后一张牌。 队长刚才就是告诉各家, 返销粮下不来了, 要大家做好挨饿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整个世界如天塌一角, 一种抽象的恐怖铺天盖地地包围过来。
构筑我最初记忆的是故乡的花鸟虫鱼、 细长的竹子和大小高低不一的树。 我的故乡, 田野手牵手, 连成片, 默默向远方延展, 一直抵达天的尽头。 横竖交错的河渠穿行其间, 水与土的相处和谐而自然。 朴素的土和低调的水一直以它们无私的胸怀, 善待居于其上的每一个生灵。 它们是值得信赖的。 我从小就和它们打成一片了, 翻沟钻渠捉泥鳅, 爬树上房捣鸟蛋, 我每天都向这片天地源源不竭地释放热情。
但是, 那个有生产队长挨家走过的黄昏, 那个父母停止争吵的黄昏, 刻在记忆里。 我瞬间长大了。 十岁的我仿佛被拖入一个陌生的世界, 我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理解原来只是一种自以为是和自作多情。 我好像被整个世界抛弃, 觉得当时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迅速保持身体和语言的绝对安静。 四周是土砖墙壁的堂屋, 我慢慢收拢自己, 慢慢后退, 退到大人忙碌疾行时不会挡他们道的地方, 退到其他人不会因为陡然看到你而心生烦躁的地方, 退到煤油灯昏黄的光亮摇晃不定的角落, 退到如同消失了一般。
那时, 正是植物离开土地的冬天, 坦荡无私的大平原, 黑暗、荒凉和亘古如斯的寂静, 给了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来凑热闹的北风长驱直入的理由。 风, 由小到大, 刮得越来越起劲, 那种平原地带特有的北风, 拼命摇撼着我家屋后那片楠竹林, 修长的竹枝, 细密的竹叶, 发出疯狂而迷乱的摩擦声, 将北风的威力进一步助推。 我一度感觉北风是灾难的前奏, 它是来打头阵的, 它会把灾难一步一步地导引过来, 说不定, 马上会把我家屋顶的茅草掀个底朝天。
那些在大人嘴里说出的和还没有说出的灾难, 会不会赶在北风之后降临?
又会以怎样的方式降临呢?
我在那个时候已经知晓, 春天生长万物, 夏天万物生长, 秋天是果实入仓的季节, 只是该收获的东西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冬天是我们暂时离开土地的季节。 没有了土地的哺育和庇佑, 灾难就钻了空子。
昏暗的角落里, 小小的我, 翻江倒海, 绝望而自虐, 然后,我看到了接下来的一幕。
我的妈妈, 她从房间里搬出一个硕大的洗脚盆, 端正地放在堂屋的正中, 她从土灶的大瓮缸里舀出比平时多得多的水, 慢慢地浇下来, 坐稳, 卷起裤脚, 将双脚优雅地探进去, 直至两只脚全部伸进热气腾腾的水里。 妈妈的脸上浮起难得一见的满足感。水是让人感觉如此亲近和温馨的东西, 何况是冬天夜晚的热水,妈妈开始用两只脚认认真真地互擦起来, 脚与脚、 脚与水相击而发出响亮的、 咕嘟嘟的声音。
我诧异地看着妈妈, 像看着一个陌生人, 妈妈盯着那双被烫得通红的双脚, 像在鉴赏一件艺术品。
令我更加意想不到的是, 缭绕的水汽中, 突然飘出几句歌声。要将快乐进行到底的妈妈, 她用特有的腔调, 哼出一些短促的、不成曲调的旋律。 我看见晦暗的煤油灯, 仿佛亮了起来。
无论是之前的懵懂记忆, 还是之后的漫长岁月, 母亲基本上是不唱歌的, 相较于父亲磁性的嗓音、 准确流畅的曲调, 她明显逊色很多。 客观地讲, 母亲是五音不全的。
这五音不全的歌声传达给我一个巨大的疑惑, 母亲怎么会在这种万家忧虑的时候反而唱起歌呢?
她不合时宜的高兴多么令人费解啊!
母亲因何而高兴?
她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然而, 歌声却又适时地点醒了那个倚在墙角的木讷的我, 我要趁着歌声飘扬赶快去做点什么事情。 我怕歌声转瞬即逝。 事实上, 歌声却还在断断续续地绵延。 我赶快打水洗好脚, 一声不响地爬上了床, 就在我钻进被窝把身体安排妥帖的那一刻, 歌声戛然断在了隔壁的堂屋中。 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 被歌声灌溉了的小屋, 如同被炭火焐热了的冬天, 一切灾难和不幸都将被挡在门外; 无论北风如何肆虐, 我们的家, 都是生长希望的地方, 也终将在平稳安然中迎接春天的到来。
我一夜长大, 脑海里突然滋生出许多缤纷的念头。 我想起我家屋后面那口一年未干的塘坳, 应该麇集了很多鱼吧, 我明天就邀上二哥去筑围堰, 我会一脸盆一脸盆地把水舀干, 只要一个上午的工夫, 就可以把满满一桶鱼送到妈妈的跟前。 我家屋前面这口几十亩的大水塘, 在收罗和沉淀了一年的落叶之后, 塘底该生出了一层厚厚的虾米, 我要将一只烂箩筐用麻绳系上, 把蚌壳敲开, 再将蚌肉放进箩筐里, 沉入水底, 等拉上来时, 必会看见一筐傻傻的虾米铺在箩筐底下。 春天来时, 我还可以带上我的钓钩, 去水边寻找那些口吐泡沫准备产仔的鳝鱼, 等我钓满一水缸的鳝鱼, 天麻麻亮时, 我就跟二哥一起把它们提到镇上去卖。 听说女贞树的籽也可以卖钱, 我要趁天晴, 把屋角那两棵女贞树的籽一颗不留地摘下来, 晒干后, 用麻布袋装好。 我甚至想即刻就翻身起床, 把这些话告诉妈妈, 我们有沉默无私的土地和河流,它们永远慷慨, 值得信赖, 饥饿又怎么可能有机会找上门来。 当我激动地一遍遍构思我的计划时, 我对黎明的到来忽地充满迫不及待的憧憬。 同时我还发现, 眼角痒痒的, 有眼泪在爬行, 它们穿越脸庞, 流经耳廓, 最终无声无息地钻进我头下的枕头里。
在本应成为童年最黑暗的一个晚上, 在我稚嫩而脆弱的一颗心急剧沉沦的时候, 我的妈妈, 她用歌声, 将我拯救。
事实上, 在未来的日子里, 更大的艰难和挫折接踵而至的时候, 我可以肯定地说, 我的母亲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甚至完全相反。
等我后来长到足够大并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一个人抵抗灾难的力量其实来自童年。 而更多的时候, 我的整个童年都处在一种逃离的状态。 我想逃离有时沉闷但更多时候又充满争吵声的家庭气氛, 我想逃离亲戚之间那种被利益牵制的虚伪的关系, 我想逃离被所有人期待必须考出最好成绩因而再也没有时间亲近大地的学校, 我想逃离班主任不明所以冷冷看我的眼光。 这种逃离的心态使我没法安稳地呆在童年, 因而, 光阴也随之显得过于冗长而拖沓。 当我终于意识到我最终没有办法逃离古老偏僻的故乡时, 一张突兀的门旋即把童年关在了身后。
现在, 我住所的后面, 有一大片人造的竹林, 规规矩矩地种着粗细不一、 高低不等、 疏密相间的竹子, 自然, 风被逗引来了。 可是, 城市里养育不出童年时代那么霸道的风, 它们游戏一般在竹叶间穿梭。 鸟也来了, 但比起童年时代逆风中奋力飞翔的小鸟, 这些城市的稀客显然有着一种养尊处优的贵族气。 这片人造的风景, 永远上演诗情画意的平和。 平和的风景是我喜欢的,它们永远那么熨帖和标准。 可是, 在风景的深处, 我总是能听到一个年纪尚轻的女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唱起歌来。 她优雅地擦着脚, 慢镜头一样, 不动声色地与黑暗对峙, 与我心底无边无际的绝望对峙, 与即将到来的灾难对峙。 时间凝固, 停止流动, 世间的人和事退到毫无意义的夜之深处, 给这歌声作背景的, 是窗外啸叫的北风, 它们拼命地摇撼着一林密密的楠竹, 用一种千年如斯的、 洪荒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