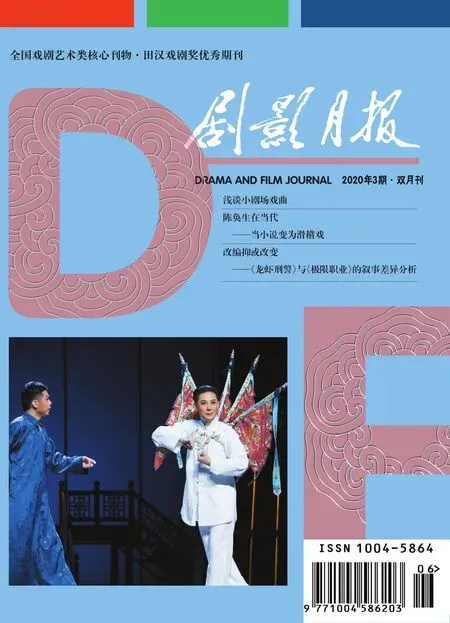《世说新语》折子戏赏析两则
“世说新语”系列为江苏省昆剧院石小梅工作室推出的一批新编昆曲折子戏,由罗周编剧。2020年“春风上巳天”跨年演出的四折,笔者以为俱属精品,而以《访戴》《索衣》最佳。
雪消冰融,梦醒人间——《访戴》赏析
昆曲可谓是最为精致的戏曲艺术。唱念做打,一颦一笑,尽是风流。可倘若以“精致”作为昆曲审美的评判标准,折子戏的《访戴》可以堪为其中的魁首。
《访戴》一折,源于《世说新语》中对于王献之的一则记载:王子遒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分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则故事被归在《世说新语·任诞》中,可见即使是以当时人的目光看来,这也是颇为个性而不拘流俗的一则趣闻。以普通编剧的视角来看,这则趣闻的故事性并不强,甚至有点无厘头,可罗周正是以她多年的学养,将魏晋人旷达不拘的人生观与故事相结合,为观众奉献了一折精彩绝伦的昆曲折子戏《访戴》。
《访戴》的演员很少:一生一丑。生为王献之,丑为苍头。《访戴》的故事很简单:王献之夜来兴起,千方百计令苍头与他同往旅途。然而正是这样一对简单的组合,这样一段枯燥的旅程,却令观者趣味盎然,若有所悟,这便是编剧的高明之处了。
倘若细细看来,《访戴》可以被划分为这样几个大的段落:一是王献之雪夜见酒起兴,二是山路之上怀想兰亭,三是小舟之上主仆笑谈,四是临近剡溪巧言相劝,五是戴府门外兴尽而返。几个部分之间相互烘托,相互铺垫,才使得最后王献之的了悟合情合理,似是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王献之和苍头两个人物的设置非常有意思,一雅一俗,一贵一贱,既是相互对立,却又和谐统一。这种身份的鲜明区分与立场的不同贯穿了整场戏。从王献之雪夜起兴开始,这一主一仆之间就有了微妙的矛盾——天寒地冻,在王献之眼中自是好雪好景,可苍头心中却是一心“转去”,不愿出门。山路之上,他们便是一个要“疾行”,一个要“徐行”,从而引出了王献之对于昔日兰亭集会的回忆。这段回忆恰是为了最后两人立场的反转所作的一个铺垫。兰亭集会的喧闹,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此一节,正是以往日之喧闹,衬托今日之寂静,此处伏笔,明而不显。水路之上,主仆二人争辩,也恰是凸显了两人身份立场的不同。雪片飘飘,在富贵人家看来是“皇家瑞气”,而在乞丐平民看来,则无疑是灾难。对于苍头来说,王献之之“雅趣”,使他不得不在大雪纷飞的半夜起身,去往不知名的目的地,对他而言,亦是灾难。船行靠岸,苍头的抱怨也达到了顶峰——他被王献之诓着走了那么远,抱怨王献之“老爷三更不睡、四更不眠,偏偏山一阵、水一阵、车一阵、船一阵、东一阵、西一阵、行一阵、停一阵”,再不肯挪一步。而王献之则抖出真相,以音乐、美酒、美女作为诱饵,使得苍头态度大变,极力催促他前往戴府——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次反转,倘若没有苍头的极力催促,王献之的兴尽而返便失去了戏剧上的价值。催促是为了离去——当两人终于来到戴府门前,王献之却被枝头融雪点化,忽觉美人、知音乃至人生的富贵荣华都失去了颜色,如同消融殆尽的积雪,索然无味,因此过门不入,兴尽而返。
整场折子写的趣味盎然。开场,作者并没有直接告诉观众王献之雪夜兴起,是要去往何方,而是卖了个关子,直到船行靠岸之时,才将谜底揭晓,此为一巧;主仆对话,趣而不俗,斗智斗勇,使得观众在观赏中不觉疲惫,时而开颜,此为二巧;描摹人物,世情毕现,对比鲜明,此为三巧:正是有了这三巧,才使得这折戏“理”“趣”相生,丰腴多姿。
倘若《红楼梦》的元妃省亲一折乃是以乐景写哀情,那么《访戴》一折便是以至乐写至悲。雪夜独饮,忽忆知己,前往探之,此一乐也;怀想往事,嘉宾云集,君子笑谈,此二乐也;少年英才,好酒好宴,美人在侧,此三乐也。正是出于对这三乐的欢欣憧憬,才使得王献之不惜雪夜出游,山一程水一程,前往剡溪访戴。可灌入脖颈的融雪却让他忽然明白,所有的这些,美景佳客,美人知音,所存在的都不过只是一个瞬间,唯有虚无永恒——这与魏晋时期崇尚玄学、崇尚虚无的价值观是相契合的。前面所有的喧闹都是为了最后这一刻的宁静,前面所有的欢欣都是为了这一刻的悲伤,在生命的短促和无常面前,所有的一切都褪去了颜色,失去了光彩,仿佛雪消冰融,梦醒人间。
从“乘兴而来”,到“兴尽而返”,究竟是什么让王献之突然失去了兴致?《世说新语》的原作中并没有给出答案,我们现在在《访戴》一折之中看到的,是编剧自己的发现与想象,是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一种大胆怀疑。正如《兰亭集序》所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人生的短促与生命的脆弱,对于刚刚经历过晋代初年血雨腥风的魏晋士人来说,感慨尤为深刻。倘若所有的存在都将消亡,我们的所喜所悲、所爱所恨都将成为云烟,那么我们的存在本身又有什么价值?这是人类始终追寻却又无法取得统一答案的一个永恒的疑问。无是包含了一切的无,而有却只是局限的、有条件的有。因此,为了将这脆弱而无常生命无限延长,去追逐生命本身的光亮与价值,他们才纵情欢乐,享受当下,以这短暂的美好去对抗永恒的寂灭,才会一时兴起,便雪夜奔袭,去往剡溪,探望友人。也许正是魏晋士人这种不计得失的纯粹与可爱,才成就了这折精彩绝伦的《访戴》吧。
笑中含泪的昆曲美学——《索衣》赏析
昆曲的美究竟美在何处?这个问题可能足足困扰了昆剧迷们数百年。在大多数剧种已经面临衰败窘境的今天,昆曲却在当代的时尚青年中赢得了不少的受众。从美学上来说,昆曲是生长于中国古典美学之上的一株奇葩,不同于西方写实主义或者荒诞派的戏剧,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传统,“明确宣示是在演戏”的演剧主张,以意象性为特质的“时空自由”,以虚拟性为手段的“空台艺术”,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而昆曲,更是这其中的佼佼者。昆曲高度的程式化、完善的脚色分行、以及细腻的人物刻画,都标志着它是一个成熟度极高的剧种。
相比较于大批的昆曲正剧或者悲剧,昆曲中的喜剧少之又少。而昆曲中的喜剧多以丑等行当为主角,描写小人物的滑稽与可笑,如《狮吼记》《风筝误》《贩马记》等。而折子戏《索衣》,则是以副净和闺门旦作为主角,佐以丑和花旦作为配角的一折喜剧。
《索衣》的主角是王戎。这位出身琅琊王氏的晋代名士,年少时为“竹林七贤”之一,常与七贤中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纵酒鸣琴,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一位。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出身贵胄的名士却悭吝无比,在《世说新语》对于俭啬的9 条记载中,一人独占四条,可以说是当时名士之中的吝啬之王。《索衣》的故事便主要源于《世说新语》中的两则记载:“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和“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
王戎的性格可以说是极端复杂的。他出身名门,少而聪慧,十五岁便成为“竹林七贤”的一员。他事母至孝,识人至明,却又随波逐流,性格狂放;他既好利贪财,嗜钱如命,却又可以视千万钱财如粪土,拒绝贿赂。《索衣》正是把世说新语中关于王戎的数条记载融于一体,从而让我们有幸得以窥探一下王戎的内心世界。
《索衣》可以分为两组人物:王戎和他的仆人青奴,王姣(王戎长女)和她的丫鬟红叶。王戎的女婿裴頠曾从王戎处借走单衣一领,王戎想到女儿处要还,可又不好意思。整场戏的戏剧性便围绕着这个“不好意思”展开。按照编剧借王戎之口的说法“单衣一领,怎生开口?总要想个法儿,使她自悟!”因此,王戎便变着法儿提示王姣,终于使王姣明白了父亲的来意,将那单衣还给了他。
故事依旧是简单的故事,而戏剧的情与趣便在这层层叠叠的绕圈子中展开。老父想要要回单衣,却不想失了面子,不肯明言;女儿孝顺懂事,却又不解父亲来意。随着折子戏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折子实际上所包含的是两个时间线的描述——现在的生活,登门索衣,是幸福生活中的一点小插曲;而过去的生活,竹林七贤的悠游,少年意气的追忆,今不胜昔的慨叹,则像是洞穿了数十载的光阴,款款步来。二者的衔接点,正是落在了那一件单衣之上,那一个“衣”字之上。可以说,现在的故事是骨,是王戎得以追念往昔的情境,过去的故事才是魂,对于王戎来说,那个曾经光彩照人、高步竹林的自己,才是他千方百计想要寻回的。
在这里我们窥见编剧对于独特主旨的挖掘。若是《索衣》之中只见王戎的俭吝,颜色便失了一半。倘若没有“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悲凉底色,王戎的俭吝,便只剩下可笑可怜,再无厚重与回味。我们可能还是会为王戎的俭吝之极笑出声来,却不会再愿意去回想这背后的深层原因。
在那样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能够从风云中保全自己,得养天年,就已经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智慧。也许正像王戎自己所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在那样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全的时代,是非善恶,成败毁誉,皆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唯愿放肆着自己的本性,俭吝也好,嗜酒如命也好,就仿佛是在被崩的死死的神经上的一个小小的缺口,唯有如此,才能在被乌云压迫的即将崩断的世界上继续战战兢兢地活着。
《索衣》有趣吗?剧中的王戎滑稽可爱,他对于索回单衣这一件事的执著、对于女婿穿走单衣无法取回的担心、数次话到嘴边却又不肯言明、分明十分想要取回单衣却又极力推脱的虚伪,都是那么鲜活动人。编剧喜剧写作的手法十分圆熟,戏剧节奏的掌控令人击节。《索衣》感伤吗?王戎所回忆的竹林七贤,物是人非,唯留下“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老夫战战兢兢、浮沉俗世。今过黄公酒垆,视此虽近,邈若山河、邈若山河!”的恍如隔世的慨叹,它是笑中的泪,是时刻放在心上,不可触摸却又不可追回的往事与岁月,是找不回来,却又难以忘却的曾经的自己。
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洗礼,才使得曾经明媚的少年郎变成了如今这种晦暗的颜色?这段故事,《索衣》并没有写,可是我们却可以透过那夹缝依稀窥见真相的一角。“新衣虽假,旧情是真。”对于王戎来说,或许那单衣便宛如数日不逢的老友,即使女儿嫌弃寒酸,也再不能失去,再不忍别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