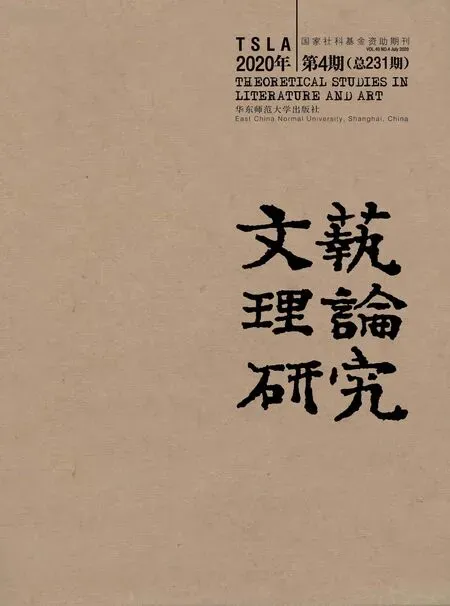从创作到制作: 网络新媒体视域下文学生产方式转型
李灵灵
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地图又变了。自王晓明撰文《六分天下: 今天的中国文学》,①距今已十年,今日之文学版图格局,大致呈三足鼎立之势: 严肃文学、畅销书文学和网络文学。前两者可归为纸面文学,严肃文学延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期刊文学,继承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传统;畅销书文学是商业图书出版机制下,以打造畅销书为目标的纸面文学;网络文学又可细分为原创文学网站机制下的网络类型小说、自媒体文学以及跨媒介平台的文学存在。三者各自适用于不同的市场逻辑。
王国维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十年前网络文学已占半数,如今更以燎原之势,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主角。其中以网络类型小说和自媒体文学为甚,较之严肃文学和畅销书文学,这是完全不同的文学类别,在文学生产方式上与传统纸面文学有本质的区别。
网络文学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催生了一大批网络职业写手和职业作家。2006年,体制内作家洪峰为声讨文化局不发工钱,展示了一场“作家乞讨秀”。2009年,《南方人物周刊》策划了“网络文学”专题:“写小说赚大钱”。两相对比,更显严肃文学的“凄凉”。大批以文为生的写手作家们,纷纷从传统纸面文学转阵网络文学。艾瑞咨询《2018年中国网络文学作者报告》显示: 自2015年起,中国网络文学作者数量一直保持30%的高速增长,到2017年底,网络文学作者规模达到了784万人(艾瑞咨询6)。
习惯了传统文学创作的作家们转向网络的过程并不容易。较早从文学期刊转向网络写作的作家比如打工作家,他们为早已市场化的文学期刊撰写面向打工者的打工文学,对市场变化比较敏感。当媒介变迁之际,打工作家走向分化,一部分转向体制内严肃文学,一部分转向网络文学市场。②最初转向网络文学的作家们处处碰壁,他们发现: 这个新生的文学市场上,已经找不到他们的读者了。他们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手法,都和网络文学格格不入。“移民”网络的作家要改变写作策略,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产。
有两种作者不受新媒体带来的文学生产方式转型的困扰。一种是一开始就在网络上写作的作家,比如方舟子、蔡智恒、今何在等等,有意思的是: 在网络文学领域最先崛起的作家都不是中文系出身,如方舟子是生物学博士,蔡智恒是水利工程博士。因没有经受严肃期刊文学的“审美规训”,其作品语言鲜活,想象力丰富,思想大胆。另一种是新生代网络作家,几乎没有接触过“期刊文学”,没有太多的顾虑和桎梏。新生代知识储备、知识结构和前辈作家不同,他们一开始就生活在网络世界,读着网络小说长大,熟悉新生代的语言,相比之下,这些90后、00后更熟悉同龄人的审美情趣。
网络给文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是变换了发表和传播的媒介”(何平1—3),还意味着和此前完全不同的文学书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407),网络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不仅受到审美代沟和审美趣味差异的影响,③也受到新媒体文学生产机制的制约。和纸面文学传统相比,新媒体文学生产机制要求作家在文学生产方式上实现转型,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转变: 从写“我”到为受众写,从类型化写作所要求的知识“层累化”到反类型化,从文学小作坊到大规模的模式化生产。这种根本性的时代转型,将影响和造就文学范式的根本性转型,塑造一种新的文学生活。
一、 从写“我”到为“分众”写
网络文学出现之前,与之相区别的是肇始于19世纪末的“新文学”或“现代文学”传统,及已经形成秩序化的审美规范、评价机制和生产传播方式等(何平1—3)。这个传统几乎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整个百年文学进程,在网络文学前产业化阶段,网络精英或草根的自由写作也深受其影响。2003年,起点中文网首创VIP收费阅读制度,这个开创性的制度将网络文学推向市场,陈村感慨网络文学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④从此,网络文学在产业化之路上狂飙突进,一去不复返。
“现代文学”传统的诞生以“启蒙”为口号,由少数精英来“教化大众”,而网络文学写作却越来越呈现协商机制、互动文化特点。⑤网络作家首先要满足受众的需要,与受众“共同写作”。原创文学网站的文学生产机制中,在线连载的网络类型小说形成一个互动的文学空间: 网络文学读者不需要作者有多高深的写作技巧,不需要多精妙的语言表达,高明的读者都自带吐槽模式,在评论区的评点、调笑和怒骂中,作者经由读者“指引”合作共同完成小说,“在没有边界的讨论中,所有参与人员都成为延续话题的生产者”(许苗苗130—37)。
新媒体特有的互动属性,使文学生产脱离了印刷媒体时代创造一个完美文学典范的愿景,文学的“历时性”意义被打破,网络类型小说的生产更像是在空间意义上基于情感、审美、交际的粉丝文化。作家不再是孤独的创作者,他(她)有了更多陪伴者同行;但作家在20世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权威、神圣光环不再,从“启蒙精英”转变为文学“明星”、文学“大神”。更多时候,作家要照顾粉丝受众的阅读期待。网络作家高楼大厦接受周志雄采访时说:“不管是学生还是成人,现实生活中都有太多的犹豫[……]如果主角犹豫,我会很难受,我会把主角塑造得更果断一些,更多的是读者要求果断,倒不是因为作者,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不想果断,但是这个确实是为了迎合市场。”(周志雄编29)在新媒体文学交际场域中,粉丝受众是衣食父母,网络文学生产不可能“自说自话”,“明星作者-粉丝受众”的新型文学互动关系,打破了传统相对封闭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何平1—3),而转变为由印刷媒体时代“作家中心”转向新媒体时代“读者中心”的文学生产活动。⑥
严肃期刊文学时代单向传播,把受众假想为趣味单一的整体,与其审美趣味的单一供应相比,网络文学场域具有审美趣味分化和审美群落化特点。网络类型小说自带审美差异,趋向多样化的丰富类型,自媒体细分市场和自媒体文学具有“垂直”属性。⑦这意味着作家需要满足细分后的受众需要——专门为某一类读者的独特趣味而写,传媒行业称之为“分众”,网络文学受众也具有“分众”属性。网络作家一旦开始从事网络文学写作,他(她)首先要定位,为哪一部分读者而写,该类读者喜欢什么样的题材。这与纯文学“决不为取悦读者而写作”的路子大相径庭。
作家首先要作充分的市场调查。网络作家孔二狗以写《黑道风云二十年》一举成名,他说自己正式写作这本小说之前,花了两年时间考察各个中文论坛,用专业商业咨询的眼光挨个分析,最后锁定“天涯杂谈”,因为这里“有最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最多的普通人”,他把“商业策划与创作热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写之前,我否定了无数的题材: 《我的童年》——一个80后的历史,不行,关注的人太少了。
[……]然后想写我的奶奶,一个经历过张作霖、伪满洲国、国民党、共产党[……]写一个农村老太太历史,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觉得我在农民这个阶层红不太可能,应该是我红了以后写比较好。
我有3个关键词: 黑道(题材足够新颖)、风云(矛盾冲突激烈)、20年。矛盾冲突不缺、精彩程度不缺、社会意义不缺,这样的书不红,没天理。
我这么处心积虑地以专业市场咨询业人的眼光做文化产品,不成功没道理。(张欢28—31)
孔二狗的个案颇具代表性,他以管理咨询顾问出身,把网络小说当成一个文化产品来运作,这与当下影视文化产品制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SMG影视剧中心助理李捷文在《头脑风暴》节目中谈到韩国编剧十二法则,其中针对女性观众,又将她们细分为“看电影的女观众”和“看电视剧的女观众”,为她们提供不同的影视文化产品。⑧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写作越来越向影视文化产品制作靠拢,作家也自觉地迎合受众的审美需求。严肃期刊文学和网络文学市场“冰火两重天”,孔二狗解释为:“因为我们踩着地的,接着地气,比如我、当年明月,每天浸淫在网上,知道大家的关注点是什么,传统的高高在上的作家,早就不愿意了解人民想要什么。”(张欢28—31)网络作者选择文学题材时考虑的因素是什么?艾瑞咨询的数据也印证了: 星级越高的作者选择题材时更关注读者喜好(艾瑞咨询8)。
进入IP阶段后,网络文学衍生的文化产业链决定了网络文学的脚本性质,网络作者不仅要考虑差异化的小说受众,更要考虑“长尾”意义上的影视、游戏受众。这意味着不仅在题材上,并且要在写作手法、语言上对纸面文学传统进行改装。“许多小说在与游戏签约后,内容有了新变化,角色更丰富、性格更鲜明、情节更复杂。这并非写作者的意图,而是适应游戏市场用户喜好,方便改编的伏笔。”(许苗苗130—37)有了粉丝基础,才能被改编成影视、游戏、动漫,让更多人看见。而由于商业需要,能被改编成游戏、影视,决定了某些种类的类型小说能被拓展到整个文化产业链: 比如玄幻小说、科幻小说和游戏竞技小说等。网络作者在写作中为了配合改编需要,也自觉地采用“翻译画面”的手法: 用更形象化的语言来写作,文字更具有画面感等等。这一切是为了拓展更多网络文学受众及其衍生文化产品粉丝受众的需要。
总之,新媒体视域下文学生产的重心已经转移: 由写“我”到为“受众”而写。作家的“个体经验”和私人冥想不再是文学的表达核心,个性化的表达受阻。要想在网络文学市场生存下来,作家不能任性、率性到只写自己。由于审美代沟和审美群落化差异,传统作家在网络碰壁,学院派在市场碰壁;同龄人更了解同龄人,50后至70后无法理解90后、00后的世界,不太容易提供满足“网生代”的网络文学产品。在令前辈瞠目结舌、眼花缭乱的各种“功法”、二次元、腐女充斥的世界中,90后、95后年轻作家快速崛起,逐渐成为网络文学写作主流,30岁以下作者占了七成(艾瑞咨询36)。同一审美圈更理解同一审美圈,酷爱玄幻、军事的理工男不理解女生为何向往《魔道祖师》《花千骨》里的爱情,网文作者写作题材偏好性别分化更严重。不是圈内人没法理解沟通,更无法提供满足这个圈子需求的文学产品。文学场域从“计划文学”到“商业文学”的时代真正到来。媚俗化也好,⑨“审美衰减”也好(何平1—3),作家个性和主体性的滑坡,⑩是一个事实,受众崛起的时代已经到来。
二、 类型化套路、机器人写作与反类型化
以受众为中心写作,意味着提供受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产品,而通俗化的往往是类型化和模式化的。从新媒体时代越过印刷媒体回溯到口头文学时代,流传于民间的童话故事和民间故事就是类型化、模式化文学的代表。研究民间故事的学者都熟悉故事学的经典概念工具: 芬兰学者阿尔奈(A. Aarne)发现民间故事的叙述情节模式大致相同,按情节类型(type)对民间故事进行编排著有《故事类型索引》;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发现流传于整个欧洲、亚洲、南美、澳洲等地的民间故事都有类似的情节叙事单元母题(motif),其《民间文学母题索引》(1932年)展示了世界各地故事成分的同一性或相似性;另一位知名学者普洛普(Vladimir Propp)则探索故事的叙事结构,发现这些故事都有大致的结构特点,其《民间故事形态学》被认为是20世纪具有独创性的文学研究典范。我国民间文学研究者刘魁立对中国民间故事的生命树研究,弥补了世界民间文学中缺少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遗珠之憾。
中国文学传统中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只是一个小小分支,在厚重绵长的古典“诗文”传统中一直是被压抑的。胡适曾著《白话文学史》,提倡重视钩沉了近两千年的白话文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也致力于搜集民间歌谣,以期用“活的文学”来对抗强大腐朽的“山林文学”“庙堂文学”。这一切和今天中国文学处境竟依稀类似,不同之处在于,五四精英知识分子是从上而下“教化大众”,他们构建“新文学”传统的资源多来自西方,而不是民间通俗文学传统;今日新媒体时代的网络文学却是从下而上自发崛起的通俗“民间”文学,虽有附着于新媒体的新特点,但本质上,网络文学仍然是以普通受众为中心的通俗畅销文学。
由网络文学二十年发展史可见: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北美留学生群体的华语网络文学和2003年前处于自由创作阶段的网络文学,都带有“现代文学”传统的精英气质,少有类型化、模式化的痕迹;而当网络商业文学机制形成(VIP付费阅读)之后,网络文学随即急转为畅销文学,迅速分化出网络类型小说,开启了类型化和模式化套路。拉长岁月跨越媒介来看,网络文学中的各种“梗”:“女主跳崖脱胎换骨”梗,“少年被退亲受辱、励志发愤图强”梗,和民间文学中的叙事情节单元母题、类型颇为相似。网络文学的当红创作者“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我吃西红柿”的粉丝们都很清楚: 他们创作的小说看了一部就不用看其他了,因为都是一个“套路”。尽管如此,粉丝们仍然忍不住围观大神新作,架不住新成长起来的青年源源不断加入网络文学入口。“废柴”少年一路升级打怪(炼器炼级)逆袭得道(得正果、得成功、赢得美人归)的故事套路“深入人心”,跨越了时光和文化隔阂,只需看看《西游记》《魔戒》的流行就知道了。
通俗畅销的文化产品之所以类型化和模式化,概因人类共同的“审美心理机制”使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假设: 自己认为美的,也希望别人能引起相似的普遍性的审美认同(共通感)(康德57—59)。在什么样的文化产品能畅销流行这点上,美国编剧深谙人的“审美心理机制”: 畅销的都是模式化的。好莱坞影视大片自不必说,其电影小说叙事模式有固定的三幕结构:“第一幕介绍英雄所面临的问题,以危机和主要冲突的预示来结束。第二幕包括主人公与他或她面对的问题进行的持续斗争,结束于英雄接受更为严峻的考验这一节点。第三幕所呈现的应是主人公对应问题的解决。”(赵勇95—106)中国大陆的中文系素称“不培养作家”,美国大学却有各种各样的写作课程和编剧课程,教授人们如何创作出畅销小说。严歌苓曾在美国接受编剧课的训练,据说她接受冯小刚邀请写作《芳华》时表示: 不受电影剧本的规训,要写一部“抗拍性”的小说。结果学者发现她的小说和电影叙事三幕结构大体对应,是按照剧本化的影视思维模式和结构方式操作的,“虽然《芳华》用小说技法掩饰得非常成功,给人一种严肃文学的错觉,但实际上却是按照某种配方生产出来的‘电影小说’”(赵勇95—106)。某种“配方”当然是指类型化和模式化的写作套路,参照“配方”能制作出畅销流行的文化产品。日本动漫和韩国影视的文化产业体系成熟发达,他们也建立了一套类似的文化生产法则。网络类型小说和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一样,都是类型化和模式化的文学品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网络文学也因此唤起了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走红于海外,与美国好莱坞大片、韩剧、日漫相媲美,成为新媒体时代全球粉丝文化的重要一极。
既然故事元素早已根植在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结构中,民间故事中的母题有一百多个,“神奇故事”的叙事结构也有固定的套路和公式,那么,作家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口头文学时代,民间文学没有作者,作者是“广大人民群众”,“作者”和“作家”概念是印刷媒体时代伴随版权保护应运而生的。进入新媒体时代,作家面临的危机可能还不是“为受众写”导致自身独创性被抑制、主体性被消解,而是类型化和模式化的文学产品对作家个体的倚赖越来越小,受众只关心“梗”,不关心谁是最先发明了这个“梗”的人。很多时候说不清哪些是作家独创的“私人梗”,哪些是网络文学资源库里共享的“公共梗”,网络文学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困难。这也从侧面说明: 新媒体时代,与民间文学具有类型化本质的网络文学,正在慢慢遮蔽作者。
更严峻的挑战还不止于此。网络类型小说是众多以同一题材为创作内容的同质化作品,“同一题材”和“同质化”内容,加上与严肃文学相区别的模式化特点,以及网络文学资源数据库和网文写作软件的便捷,决定了网络类型小说更容易被抄袭改装: 不仅能被人类同类“抄袭”取用,也能被人工智能作家(AI)轻而易举地“抄袭”组装。丁帆曾忧心青年作家“在体制与资本构成的文学秩序中如何生存和发展”(丁帆1—3),没有料到的危机是: 当下作家还面临着机器人写作的挑战。微软诗人小冰已经出版了第一部人工智能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IBM诗人偶得能随意组合各类五言、七言古体诗。模式化极强的网络类型小说极易被人工智能改编。试想在类型小说题材库中输入:
男一: 花样大叔。女一: 野蛮妹。配角: 任意。类型: 爱情/悬疑。场景: 海岛/都市。主情调: 忧伤。宗教禁忌: 无。主情节: 爱犬/白血病/陨石撞地球。语调: 任意[……](韩少功,3—15)
一部网络类型小说可以在几分钟内“定制”而成。智能写作以编程的形式“用典”或“用梗”,将来的人工智能会制作出各种语言风格的琼瑶体、淘宝体、鲁迅体……智能写作软件的“数据库式写作”,使得文学“创作”这门需要作家匠人精雕细琢的“手工艺术”,直接跨入了信息产业时代(邵燕君等37—42),文学产业化制作大生产成为可能。
那么作家意味着什么?怎样证明作家个体还“活”着?智能写作软件一出世便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文学经典资源数据库,最不擅长遣词造句、最不会编故事的“小白”作者,也能凭借机器人创作出“像样”的故事,作家个体比拼不过计算机算法。可能的出路,就是为文学经典资源数据库贡献“知识份额”: 新媒体时代的作家,一方面要遵循类型文学的“审美心理机制”,要懂“套路”;另一方面又要突破类型化的写作,开创新的原创类型,在类型化写作和反类型之间走钢丝。但这一切需要时间、锤炼和积累,资本的力量推动文学向前,恐怕并没有给作家留出太多积累时间。
三、 资本的力量: 批量文学生产和团队写作
网络文学生产方式转型不仅包括以“受众”为中心的类型化写作,还包括与新媒介革命匹配的一整套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将文学带入工业化大生产的快车道。邵燕君研究了多年文学期刊后得出结论: 传统文学生产机制是坏死的,当代文学应寄希望于网络等新型机制(邵燕君12—22)。的确,网络文学吸纳了大量的文学青年,赢得了资本的青睐,一路开疆拓土,连体制内文学生产者、研究者和学院派研究者,也不得不提出“向市场学习”。那么由网络文学市场来教作者写作又当如何呢?
首先,无论是原创文学网站还是自媒体平台,都有一整套市场化的作者培育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激发了民间原创文学力量的爆发。网络文学三大巨头阅文集团、阿里文学和百度纵横文学,在网站主页都打出了诱人的写作奖励计划和优质培训广告。比如阅文集团针对作者所处的不同阶段,提供定制化的扶持计划,涵盖了从“一星作家”到顶尖“白金作家”的培养体系,在笼络“老作者”的同时,保证其文学生产有源源不断的“新作者”注入。培养体系包括: 作者定制化方案,为作者和作者能提供的内容定位;帮助作者塑造品牌,并提供针对性的营销支援,通过诸如电视节目、新闻发布会等方式提升曝光率;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潜力作者,为他们提供粉丝运作和用户分析;通过系列线下作者培训和研讨会、线上编辑互动、专题写作讲座等活动培育作者。2017年,阿里文学在北京召开“文学即世界”首届作者年会,承诺借助阿里集团淘宝阅读、UC书城、阿里影业等多渠道分发优势,使作者迅速积累粉丝和名气,打造全链路衍生模式(艾瑞咨询27—30)。
与严肃文学期刊和纸面商业文学出版相较,原创文学网站几乎涵盖了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其机制囊括了文学生产、文学渠道、文学销售、文学宣传、文学阅读、文学评论(主要是读者粉丝的评论互动)、评价系统(大数据分析)和文学全产业链开发,使之兼具生产机构、发行渠道和版权经纪人等多种角色。
自媒体文学平台同样有一整套类似的文学生产机制。剔除新闻类、行业类自媒体,自媒体文学网罗了网络类型小说(此类由原创文学网站承包)之外的文学品种,比如散文、随笔、微小说、杂文等。无论是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简书、大鱼号、企鹅号还是百家号,都有一套针对作者的培训、奖惩计划,以控制整个内容生产。
面对这样庞大的由资本力量构筑的具有强势话语权的文学体系,网文作者一旦进入,就如同链条上的一环,几乎没有太多自由操作的空间,文学活动的一切都在庞大体系下运行。
网文体系首先要求作者精准定位,这是精细化模式化大生产的第一步。入驻平台首先要确立个人品牌标识: 原创文学网站要求选择玄幻、科幻、都市还是言情类写作,自媒体平台要求选择娱乐、情感还是读书类别的个人号。自媒体平台对写作领域细分要求更为严格: 内容必须垂直,专注于某一个领域进行深耕细作。百家号将垂直细分度纳入新手作者转正的考核评分标准,头条号、大鱼号等也针对垂直细分程度决定是否将文章推荐给更多的读者。也就是说,如果作品的类型细分辨识度不高,写得再好,没有推荐,就不会被更多读者看到。这种机制满足了“分众”阅读需求,也提高了作者在某一个专业领域的“知识积累”标准,毕竟著文者都是该领域的“高手”,也有被高手养刁了胃口或本身就是行家的读者。这种写作方式颇似大工业化生产中的专业分工,作者被分配到一个个指定的工位,进行流水线上某个动作的熟稔操作。
网文体系的精细化模式化生产还体现在写作培训理念上。在传统文学观念中,文学创作是很难教的。文学网站和自媒体的写作培训以及市场上各路内容生产“大神”所开设眼花缭乱的写作课程,更偏重“术”的层面,即便有“道”,也是从心理学、营销学、传播学等角度阐发如何让读者更好地接受、如何吸粉等营销之道。比如17K小说网曾举办“网文大学”,简书有“简书大学堂”,教新入门作者如何写作: 从如何起标题,到某种类型的文章如何开头、如何架构、如何结尾,起承转合,要避免哪些雷坑,都有详细的讲解。写作讲师们总结出每一种类型怎么写才受欢迎的固定套路,想靠业余写作实现财务自由的作者们趋之若鹜。初尝甜头的作者们发现: 原来写作并没有那么神秘,不需要多少高深的知识和文学修养,写作不过是模式化的套路。
原创文学网站和自媒体平台还要求批量化、大规模、持续性的文学内容生产。一方面是因为资本的逐利属性,比如某个文学网站设立的“全勤奖”: 一个月内每天5000字合格更新,月奖金500元,一个月内每天1万字合格更新,月奖金1000元。奖励金额和写作字数相关,高强度的更新导致写作成为一个“体力活”:“每天醒了就写,写累了就吃,吃完了再写,写不下去就想后面的情节。做梦都是故事。”另一方面还因为新媒体平台机制下,粉丝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一不留神就会被读者取消“关注”打入冷宫,非如此不能在这个体系中生存。因为更新不及时被读者怒骂调笑者不在少数,唐家三少曾在节目中透露自己连续九年未有一日停更,有一次高烧到40度,晚上10点以后坚持爬起来写了8000多字才休息。
在这种机制下,作家们是文学艺术家还是文字匠人,或者说是“金钱的奴隶”?现有的网文平台机制把作者当成奶牛,不停地催奶。作者的知识累积很快被“压榨”殆尽。为了对抗这种机制,作者们抱团合作,以团队生产来运作,建立维护一个具有人格化标识的作者品牌。这种“团队写作”手法在纸质商业出版领域早已见怪不怪: 书商操作一个系列小说,为方便打造作者品牌标识,将所有作者署为一个作者名,而这个名字有可能是虚拟的。
新媒体时代的团队写作显然更受文学生产机制驱动。原创文学网站的类型小说动辄几百万字,按照起点中文网的签约条件,作者前20万字免费供读者阅读,更新了20万字之后才获得签约资格。20万字在纸媒出版中已经是一部长篇小说的规格,而在网文中才刚起了个头。面对洋洋洒洒卷帙浩繁的类型小说体量,一个人的精力和知识累积已经不够用,用团队合作来抵御知识累积所需要的时间差异便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也是智能写作软件流行的原因之一,团队伙伴有可能是机器人)。许多知名大神背后,有可能是团队创作,“三五个写手轮番上阵,一部动辄百万字的网络长篇半年就完成”(许苗苗130—37)。自媒体平台因为其媒介属性更强,有时需追热点、保持时效性,要持续稳定的内容生产必得采用团队“作战”方式,比如知名自媒体六神磊磊等公众号的运作。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口头文学时代,只知有《荷马史诗》《诗经》,而不用理会其“真正”的作者是谁。不同之处在于,今天为了打造作者品牌IP,必须要有一个符号意义上的作者。
这种适应新媒体文学生产机制的新的文学生产方式,更像是文学工业化大生产。文学更像是产品,而不是作品;新媒体的商业机制下,作家成了制作者,写作变得更像是制作,而不是创作。文学自古就带有商业化的特质,商业化并不是网络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传统、现代文学传统的根本特性。商业资本和新媒介叠加所带来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新的文学生产方式,才真正重塑了当下的中国文学。
以原创文学网站和自媒体为平台的网络文学活动对应着信息文明时代,正在造就一次彻底的文学范式转型,这次转型可能比中国现代文学相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范式转型更具有颠覆性。从写“我”到为“分众”而写、类型化模式化写作套路的适应与超越、大规模批量文学和团队写作,只是文学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呈现出的几个鲜明特点。从中可见: 1.“作家”真正面临“死亡”的危险。罗兰·巴特说作家“死”了,是从文本接受角度消解作者的“霸权”。在新媒体时代为受众写、类型化套路、团队写作中,作家个体的独创性“死”掉了。特别是原创文学网站小说类型化、机器人写作迎合的模式化需求,掩盖了作家的“个性”,这是从文本生产的意义上来说作家“死”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作家之死”。2.从创作到制作,文学成为文化产业链的源头活水,成为游戏影视动漫的脚本,需要大规模的批量生产。文学终于也面临本雅明所说“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的命运: 审美“灵韵”退化。3.文学产业化最大限度地释放了文学的活力,激发了民间原创文学力量的兴起,但文学也在产业化中消解着自身,或者说变成了另外一种形态。和“现代文学”传统相比,网络文学更接近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的类型化、模式化套路,产业规模需要批量化、规模化的文学生产。但是网络文学一直在变化,文学的“灵韵”如何在这种转型中延续、保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学史已经或将要跨入一个新纪元(王侃1—3)。
注释[Notes]
① 参见王晓明:“六分天下: 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5(2011): 75—85。昔日王晓明将中国文学地图分为: 严肃文学、反抗的文学、新资本主义文学、网络文学、博客文学等。
② 参见李灵灵:“媒介变迁与作家群落分化: 以打工作家为例”,《文艺争鸣》5(2016): 155—63。
③ 参见陶东风:“以记忆传承超越审美代沟”,《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0日第24版。
④ 参见程千千、章晓莎:“‘榕树下’与网络文学20年: 网络文学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网络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当年榕树下——网络文学20周年回顾”主题讨论会,邀请榕树下首任艺术总监陈村参与。澎湃新闻2017-12-6.2020-3-3
⑤ 参见许苗苗:“游戏逻辑: 网络文学的认同规则与抵抗策略”,《文学评论》1(2018): 37—45。
⑥ 参见单小曦:“‘作家中心’·‘读者中心’·‘数字交互’——新媒介时代文学写作方式的媒介文艺学分析”,《学习与探索》8(2018): 156—62。
⑦ 写作内容要“垂直”指专门从事某一领域的专业内容撰写。
⑧ 由第一财经传媒开办的全新演播室谈话类节目《头脑风暴》,《笙箫可以不再沉默》,2015年第314期。
⑨ 参见胡友峰:“消费社会与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生长背景”,《小说评论》6(2014): 58—63。
⑩ 参见张文:“媒介与百年中国作家身份的建构”,《兰州学刊》12(2016): 43—50。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丁帆:“青年作家的未来在哪里”,《文艺争鸣》1(2017): 1—3。
[Ding, Fan. “Where is the Future of Young Writers.”ContentioninLiteratureandArt1(2017): 1—3.]
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读书》6(2017): 3—15。
[Han, Shaogong. “When Robots Establish Writers’ Association.”Reading6(2017): 3—15.]
何平:“再论‘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文艺争鸣》10(2018): 1—3。
[He, Ping. “A Second Discussion on ‘Internet Literature is Internet Literature’.”ContentioninLiteratureandArt10(2018): 1—3.]
艾瑞咨询网.“2018年中国网络文学作者报告”.艾瑞咨询研究院.2018-9-17.2020-3-3
[IResearch Website. “2018 Report on Chinese Writers of Internet Literature.” IResearch Institute. 2018-9-17.2020-3-3.
康德: 《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年。
[Kant, Immanuel.TheCritiqueofJudgement. Trans.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刘勰: 《文心雕龙译注》,王运熙、周锋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Liu, Xie.Translationof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withAnnotations. Ed. Wang Yunxi and Zhou Fe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4.]
邵燕君等:“直面媒介文明的冲突,理一理‘文学的根’”,《南方文坛》4(2017): 37—42。
[Shao, Yanjun, et al. “Confronting the Conflict of Media Civilization and Fixing ‘the Root of Literature’.”SouthernCulturalForum4(2017): 37—42.]
邵燕君:“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的危机和新型机制的生产”,《文艺争鸣》12(2009): 12—22。
[- - -.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Mechanism of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Mechanism.”ContentioninLiteratureandArt12(2009): 12—22.]
王侃:“最后的作家,最后的文学”,《文艺争鸣》10(2017): 1—3。
[Wang, Kan. “The Last Writer, and the Last Literature.”ContentioninLiteratureandArt10(2017): 1—3.]
许苗苗:“作者的变迁与新媒介时代的新文学诉求”,《文艺理论研究》2(2015): 130—37。
[Xu, Miaomiao. “Changing Authorship: The Evolution on Literary Practices and Theory.”TheoreticalStudiesinLiteratureandArt2(2015): 130—37.]
张欢:“孔二狗: 哥写的不是黑社会,是时代”,《南方人物周刊》33(2009): 28—31。
[Zhang, Huan. “Kong Ergou: What I Write Is Not Gangdom, but the Time.”SouthernPeopleWeekly33(2009): 28—31.]
赵勇:“从小说到电影: 〈芳华〉是怎样炼成的——兼论大众文化生产的秘密”,《文艺研究》3(2019): 95—106。
[Zhao, Yong. “From Novel to Film: On the Production ofFanhua(Youth) and the Secret in the Production of Popular Culture.”Literature&ArtStudies3(2019): 95—106.]
周志雄编: 《大神的肖像: 网络作家访谈录》。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
[Zhou, Zhixiong, ed.ThePortraitsofCelebrities:InterviewswithInternetWriters. Jinan: Shandong People’s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