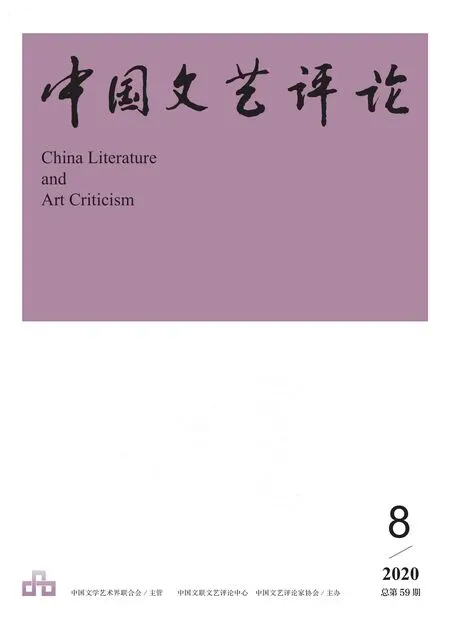《红楼梦》艺术美学中的佛道文化
杨 欢
佛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与古典小说的关系是引人入胜的话题。佛道文化有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对古典小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古典小说的杰出代表《红楼梦》的艺术美学融合了佛家色空观与道家逍遥境,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色空观与情僧说:《红楼梦》的佛学因缘
1. 色空:试遣愚衷
禅宗《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1]赖永海主编:《佛教十三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页。的十六字真言可谓妇孺皆知,《红楼梦》也有类似的十六字真言,可作为解读该书创作与佛教关系的一把钥匙。
读者及评论家多注意到第一回中“真事隐去,假语存焉”及“更于篇中多用梦字幻字”[2]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6页。,据此得出作者故弄玄虚以躲避文字狱的结论。但若说作者用意仅仅在此,恐不尽然。按书中所述,此书由空空道人抄录,而空空道人此后“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3]同上,第5页。。论者对此多不深察,然而其中别有用意。
佛家所谓色,并不等同于世俗理解的女色。色空,也并非民间所谓“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分明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1]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修订版)》(第一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第56页。。佛家以四谛为教本觉悟众生,使之摆脱绵绵无尽的生死轮回和诡谲可怕的因果报应,脱离苦海,修得正果。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通俗言之,即世间遍苦,无人不苦,无时不苦,此生是苦,来世亦苦,即使尊贵如孔雀王,富贵如维摩诘,高贵如婆罗门,在俗人眼中福禄无穷,喜乐无忧,然终有一死,也逃不过“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2]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7页。。世间苦恼如果分门别类,约略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盛。色,通俗而言,指的是世间万事万物的幻象,如镜花水月,不过是虚空假有、因缘和合的产物。人若将虚幻的“色相”视为实有,一味迷恋贪求,则为执着。执着则不能脱离苦海,只能在因果轮回中颠簸沉沦。苦谛阐释人生烦恼的状态,集谛则进而告诉众生烦恼之源。唯有斩断因果链条,跳出轮回怪圈,方能得到解脱,是为灭谛。道谛则是实现涅槃寂净的方法论。四谛环环相扣,构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2. 情僧:太虚幻境
《红楼梦》中“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情僧真言,显然是由《心经》中“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演化而来。曹雪芹在其中陡然增添一个情字,且以“情”关联前后,三足鼎立,寓意很可琢磨。
此一情字并非作者故作异说。须知菩萨即为觉有情,佛陀即为觉悟者[3]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31、1071页。。鲁迅先生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4]鲁迅:《答客诮》,《鲁迅全集》第7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4页。佛家以利益众生、救度世人为己任,“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5]《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第6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61页。,这才是至情至圣之境。释迦牟尼也是在尘世情海中颠簸之后,方才觉悟成佛。联系贾宝玉的人生经历,可以体味出作者一番悲天悯人的情怀。
贾宝玉是书中男一号,出生极为奇异。“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因“果然奇异,只怕来头不小”,“万人皆如此说,因而乃祖母便爱若珍宝”。更为奇特的是在抓周时,小宝玉对其他物件“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惹得道学先生贾政大为不喜,视为酒色之徒,独有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及至“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6]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3页。宝玉出世的这番奇异描写,颇似释迦牟尼佛本生故事。佛祖出生时,异香盈室,光华遍照十方世界,生而能行,指天画地,颂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聪明俊秀,万人不及,上下喜爱,在其父净饭王打造的温柔乡里缱绻不已[1]《佛本行集经》,《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第3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88-1089页。,与怡红院中的宝玉并无大异。
宝玉最后决绝出家,随一僧一道飘然而去,与释迦牟尼顿悟诸苦、悄然离宫也有相近之处。宝玉出家的命运曾在书中屡有暗示,如对黛玉两番赌誓“你死了,我做和尚”[2]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53、363页。,又如魇魔法时“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3]同上,第300页。,众人只当做玩笑话而茫然不觉,等到通灵宝玉莫名丢失,海棠花枯而复荣,绛珠归天而蘅芜得“玉”,此宝玉已非昔日宝玉,徒有玉之形耳,虽有“阻超凡佳人双护玉”,然神瑛早已“得通灵幻境悟仙缘”,人虽在,灵已逝,这可真是宝玉所冷笑的“你们是重玉不重人”[4]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931页。了。释迦牟尼出生时,便有婆罗门预言王子日后必入沙门行。净饭王出于对失去爱子和王位继承人的恐惧,将王子牢牢束缚在宫廷的欢乐安逸之内。然而事与愿违,王子的好奇心战胜了父王的旨意,得以多次偷偷出宫而目睹生老病死等人生残酷真实的一面。对人生无常的感叹和对因果轮回的恐惧,使王子冲破了世俗的网罗,悄然逃离宫廷而寻求解脱之道,修行成为教化众生的大觉悟者。
3. 箴言:谁为情种
然而宝玉何以由“富贵闲人”变为抛却尘缘的“文妙真人”?宝玉本是被女娲娘娘炼石补天时遗弃的一块顽石,日夜嘘嗟悲叹,幸而遇到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得其点化,化为一块晶莹透亮的通灵宝玉,被带入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5]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页。中,得以见证一番旷古罕有的传奇。
所谓因空见色,是指佛性本清净,惜被红尘各种“色相”(虚幻的欲望投射,不单指美色)诱惑,生出种种予取予求、贪恋执着的迷情,即由色生情。此情并非真情,不过是世俗贪欲的遁词。各种贪欲之中,又以食色为重。古人云“食色,性也”[6]《孟子·告子上》,《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97页。,“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7]《礼记·礼运》,《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9页。。食色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必要条件,但人作为高级动物,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还应该有更高的人生追求。《红楼梦》成书的时代,下层百姓为糊口疲于奔命,上层统治者衣食无忧,便纵情声色,介乎二者之间的士大夫,鲜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8]《礼记·大学》,《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92页。的襟怀,文人无行,风流自赏,唯功名声色是求。曹雪芹因清醒而孤独,只好将满腔愤懑借助稗官野史,宣泄“无才可去补苍天”[9]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页。的痛楚与无奈。
红楼梦借佛偈的外壳画出了世情百态。所谓世情,如警幻仙姑所言,“尘世间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那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1]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8页。继而警幻仙姑对宝玉做出了惊人的评定:“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2]同上。这足以使一般读者惊诧:既然宝玉与纨绔子弟是一路货色,还是其中佼佼者,缘何会成为令人称赏的主人公。
仙子不依不饶,耐心解释,使宝玉和读者摆脱困惑,由衷赞叹作者思想奇绝:“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都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兴趣,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尔。”至此算是对伪情矫情滥情的总结,紧接着便是仙子也是作者对真情的向往与刻画:“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3]同上。意淫在现代语境中频遭误解,倒也应了作者“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4]周义:《红楼梦中的意淫解》,《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3期,第74页。的慨叹。这里的“意淫”,是指一种对青春女性的尊重、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和怜惜,侧重于精神层面而非肉体欲望。宝玉自此便在情场中翻江倒海,在亲情、友情、爱情的红尘中“传情入色”,活化了一幅有情众生相。
面对红尘俗世,世间善知识欲“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5]《坛经·行由品》,赖永海主编:《佛教十三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7页。芸芸众生本来皆具佛性,但为一个情字所染,遂至“传情入色”,使得众生扰扰,纷乱不休。但正因为有了情字,大千世界才不会沦为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荒漠。若能看破此理,认识到何为真情,何为滥情、伪情乃至邪情,便离觉悟不远了。于纷繁浮扰、虚幻假有的“色相”中,以真情为圭臬,便能参透色空妙谛,求得心灵的宁静和谐,这便是自色悟空的归趣。就像明末冯梦龙撰《情史》,立“情教”,以“真情”对抗伪善的“天理”[6][明]冯梦龙评辑:《情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曹雪芹在书中既有对皮肤滥淫之辈的“风月宝鉴”[7]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35-142页。的揶揄,也有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有情儿女立“情榜”的宏愿[8]同上,第201、221页。。
二、合气说与逍遥境:《红楼梦》的道家精神
1. 交感:天生异人
《红楼梦》活化了一幅有情众生相,其中颇多奇人奇相。而奇中之杰者,莫过于这位含玉而生、聪明异常、淘气异常的宝玉。说起孩子话来亦是可笑,什么“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9]同上,第23页。然而作者却借贾雨村之口,借题发挥,别有怀抱,说出一番天地正邪二气化生异人的高论来:“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正邪二气偶遇激荡,“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1]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3-24页。
《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4页。,《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3][宋]朱熹:《周易本义》,《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6页。,天地万物莫不由阴阳二气和合而生,崇阳抑阴不合乎天道,是故儒家讲中庸,道家倡“冲气”。然自汉武帝以来,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术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至明清程朱理学取得官方地位,八股取士,兴文字狱,文人士大夫精神备受压抑,动辄得咎,“四书五经”沦为敲门砖,及时行乐成为座右铭,沦为贾宝玉眼中的“禄蠹”[4]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25页。。一些觉醒者则痛感希望渺茫,放浪形骸,悖离纲常,依正统观念便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5]《礼记·中庸》,[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49页。,贾宝玉便是此类人物的典型。
2. 放逐:任情恣性
贾宝玉的人生观,与正统观念格格不入:“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6]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0页。以往论者多视为作者正话反说,寓褒于贬,实是对宝玉这个贵族新人的赞美。如联系作者当日处境,念及“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悖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7]同上,第1页。,对比“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之现状,其中或有作者对往昔生活的怀恋,对家族败落的追问,对早年生活的忏悔。
依贾雨村实则曹雪芹的标准,宝玉既非大仁者,亦非大恶者,“上则不能为正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其聪明俊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其怪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一番“女儿是水,男人是泥”的高论已引得读者忍俊不禁。其人素不喜读书上进,最厌恶峨冠博带的士大夫诸男子,还为他们起个雅号叫“禄蠹”;既不应举,又不通世务;并痛斥“文死谏,武死战”的忠臣良将们为沽名钓誉。[1]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10-411页。
3. 逍遥:专气致柔
贾宝玉既已自我放逐于正途之外,连宝姐姐也对他蹙眉不已,那么他又到何处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呢?中国传统文化业已形成的“以儒治世,以道修身,以释安心”[2][元]刘谧《三教平心论》引宋孝宗《原道辩》,《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第7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56页。的文化格局,对那些不满于名教的士人形成了极大的吸引力。宝玉也不例外。宝玉因诸姊妹的罅隙而闷闷不乐,于是“便权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得。因命四儿剪灯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华经》”[3]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46页。,看至《胠箧》篇,兴致勃勃。《胠箧》是对《道德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4]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4-76页。思想的发挥,体现出老庄对于文明导致的“异化”现象的忧虑,“反者道之动”[5]同上,第165页。,“正言若反”[6]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3页。,故作反语以警醒世人。
抱朴守真,则性灵不失,人性最美好一面得以展现。然而人毕竟是社会动物,抱朴守真的理想恐怕只能在人尚未受到社会强烈熏染下才能实现。所以《老子》中频频出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7]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8页。,“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8]同上,第112页。等言。老子亦深知抱朴守真之难。而在男性主导的社会,女孩们自小囿于狭小环境中,相对保持了纯真的心灵,抱朴守真的理想大概率只能在女孩们身上体现。
宝玉自小在内帷厮混,调脂弄粉,甚是快意。然而女儿国也非想象中那般单纯,在以宝玉这大观园中唯一男性(贾兰尚小,可以忽略)为主导的女儿国中,为了争夺宝玉的喜爱、体贴以及服侍权,女孩们也像亘古不变的法则一样,展开了或明或暗、或可爱或不可爱的斗争。而宝玉这位泛爱主义者,当纠缠在林妹妹、宝姐姐还有半路杀出的云妹妹的明争暗斗、唇枪舌剑中,调解无效,反被误解,惶惑至极之时,只好退到老庄玄言中找寻安慰,乃至续写《庄子》,想要“焚花散麝”,“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自然“丧情减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甚至抛出“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邃其穴,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9]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47页。的红颜祸水论,宛若情至深处反无情的写照。
三、佛道文化对《红楼梦》艺术美学之影响
1. 亦幻亦真、亦奇亦正的艺术风格
《红楼梦》借用了佛道二教常见的度劫证悟神话,编织了一个顽石“思凡”——“下世”——“历劫”——“开悟”的奇幻故事,虚构了一个“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失落无考”的时空背景和一群在太虚幻境注册历劫的闺阁形象,正如开卷所说,本是“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不过是“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世”[1]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5页。。这就为作品蒙上了一层神话的保护色和借梦抒怀的意境。
在小说具体层面,佛道因素也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关键因素,如“贾天祥正照凤月鉴”,既是讽刺也是警醒;宝黛钗湘听鲁智深《山门》,引出宝玉续庄子、作禅偈,黛玉心证、宝钗讲慧能,推动了情节深化,预言了宝玉命运;贾敬清虚观炼丹身亡,全家守丧,引出“贾二舍偷娶尤二姨”“情小妹耻情归地府”大段故事。那块如影随形的通灵宝玉,更是发挥着“命根子”的作用,“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因它而起,“魇魔法”和“掉包计”因之而生,直至随一僧一道魂归大荒山,从此“夙缘一了,形质归一”[2]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下),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962页。。
《红楼梦》虽然遮掩了一层佛道神话的面纱,但对统治阶层的刻画、对风俗人情的描写等,都透露出背后的现实主义。如贾雨村从清贫书生、葫芦官到助纣为虐的转变,活画出官场现形记;贾赦强索鸳鸯、为古扇打死石呆子,贾琏重孝期间偷娶尤二姐,凤姐受老尼贿赂、拆散守备公子和张金哥等,揭露了贵族的腐化堕落和作恶多端,更借中秋夜祠堂祖灵叹息一节,揭示了腐朽阶级必然败亡的道理。书中对节令风俗的描绘,如芒种斗草、中秋食蟹、冬夜食鹿肉、除夕祭宗祠等,为今人提供了祖先生活的详实样貌。对各类小人物的关照,如刘姥姥三进荣国府、贾芸和舅舅卜世仁的罅隙、小红攀高枝等,更令普罗大众的读者心有戚戚焉。
借助佛道神话教义的外衣,《红楼梦》构建了一个亦幻亦真、似幻实真的世界,同时也塑造了一群亦奇亦正、似奇实正的人物形象。以主人公贾宝玉为例,其真身是一块女娲补天时被遗落的弃石,受正邪二气相感,来到人间历劫悟道,被家族寄予重振门楣的希望,却言行怪癖、不务正业、厮混内帏、沉迷酒色、非圣谤贤,放在当时的语境下,绝对是一位无可救药的纨绔公子。围绕奇公子宝玉的是一群“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的“异样女子”[3]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页。,颇有一些不符合三从四德的规范,如 “孤高自许、目无下尘”[4]同上,第57页。的“小性儿”黛玉,“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5]同上,第26页。的“女汉子”凤姐,目无尊卑、暴如炭火的“狐媚子”晴雯,自主跳槽、自择心上人的“不安分”小红等,在礼教社会里饱受诟病,命途多舛,放在当代社会则成为独立女性多样风采的写照。宝玉稀疏的同性朋友里,也多的是任侠浪子柳湘莲、戏剧名伶蒋玉菡这类当时社会的边缘人物,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2. 抱朴守真、心灵自由的美学追求
作者满怀悲天悯人、自度度人的慈悲之心,苦于“无材可去补苍天”,只得将满腔愤懑、追忆、思索托之梦幻,付诸笔端,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空空道人之口,借通灵宝玉思凡下界、西方灵河木石前缘、太虚幻境群芳历劫等神话,以佛道文化之壳,发明“情僧”及其箴言、正邪二赋合气说等奇谈怪论,为书中一干不通常情、不合礼法的奇人异事、悲欢儿女作辩护和笺注,含蓄表达对等级森严、漠视情感、压抑天性、以理杀人的礼教的反感,呼唤人人平等、真情相待、抱朴守真、心灵自由的朦胧的理想境界。
书中的荣宁二府,表面看来是一个诗礼簪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的守礼大家,但正如柳湘莲所说,“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1]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下),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721页。,这里道貌岸然,藏污纳垢,勾心斗角,正像探春所言,“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2]同上,第812页。。书中的老爷少爷们行为不堪、贪淫好色、斗鸡走马、谋财害命,即使端方如贾政也不过腐儒而已,外不能理政安民,反被胥吏要挟,放任手下妄为,只求独善其身;内不能齐家垂范,放任赵姨娘上蹿下跳,对亲生儿子唯有棒喝教育,对家族颓势毫无办法。书中沾染了男人气味的“鱼眼睛”[3]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下),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44页。们则忙于内斗,或争风吃醋,或贪图小利,面目可憎。主人公宝玉生长在这样的家族氛围中,还能近乎出淤泥而不染,着实奇迹,或许这才是《红楼梦》最大的神话。
宝玉这位主人公,既然脱离了“仕途经济学问”[4]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71页。的正途,便只好寄情佛老,留意庄禅,熏染了众生平等、精神自由的“异端”思想,在有限的天地(大观园和荣国府)内以自己有限的特权,为尚未成为“鱼眼睛”的“无价宝珠”[5]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下),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44页。们提供了有限的庇护,在这里俨然没有主奴之分、贵贱之别、男尊女卑,每日不过是少男少女的吟风弄月、游戏拌嘴,一切是那么的天真烂漫、发自天然、平等而自由。在正统社会眼中,宝玉不过是好色的公子哥而已。但在作者眼中,这位贵公子却有着世俗不解的别样的纯真,对人格平等、心灵自由的渴望,对自然天性、普世真情的追求,不以身份为限,不以性别为囿,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女儿国中。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大观园也只是借助贵为皇妃的元春特权而构建的临时乐园,根基不牢,脆弱异常。因而在“风刀霜剑严相逼”[1]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25页。之下,经历了抄检大观园、魂归离恨天等悲剧后,这方桃花源也终究成为失乐园。
3. 梦醒时分、石归大荒的悲剧结局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2]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红楼梦》中妙玉的判词为“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3]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2页。,用在贾宝玉身上倒是恰如其分。在贾府被抄、贾母宾天、“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4]同上,第67页。之后,宝玉再也得不到家族和亲人的庇护,精神自由缺少了物质基础,自我抗争没有社会变革配合,只好勉强打起精神与世俗妥协,将佛老之书统统搬走,“只有这一入场,用心做了文章,好好地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喜欢喜欢,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5][清]曹雪芹著、[清]高鹗续:《红楼梦》,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946页。,从此“走来名利无双地,打出樊笼第一关”[6]同上,第945页。,彻悟“内典语中无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7]同上,第944页。,中了第七名举人,留下遗腹子,飘然遁世。正是“尘梦劳人,聊倩鸟呼归去;山灵好客,更从石化飞来”![8]同上,第964页。然而出家并非出路,皈依亦非归宿。红楼梦众多续书中,有一版本称贾宝玉沦为更夫,与沦为乞丐的史湘云破镜重圆,贫贱夫妻白头偕老,似乎更接近现实。
鲁迅先生对《红楼梦》评点颇多,如“正因写实,转成新鲜”[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2页。,“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一语道破了《红楼梦》突破性的现实主义风格,并给予了“自有《红楼梦》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高度评价[10]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继而批评到,“然而之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11]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3页。这就揭破了不仅《红楼梦》续书同时也是古典小说的通病,不敢直面现实的“瞒和骗”[12]同上,第252页。的艺术。《红楼梦》浓郁的神话色彩背后,是深刻的现实主义关切,打破了“大团圆”的文化传统,开出了文学创作新的范式。
四、结语
曹雪芹并非匍匐拜倒的虔诚信徒,而是借用佛道文化的内涵,创造故事的神话背景,串联情节的关键脉络,赋予人物行动的内在逻辑,推演出一套“情僧”观、“合气”说的夫子自道,形成了亦幻亦真、亦奇亦正的艺术风格,表达了抱朴守真、心灵自由的美学追求,塑造了梦醒时分、石归大荒的悲剧结局,开拓了古典小说与传统哲学的思想意蕴。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1]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红楼梦脂汇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页。曹雪芹发愤著书写成这部世界名著,不仅以其文学魅力吸引一代代读者,更以其宏博渊远的文化魅力在中华文明史上独树一帜。而作者在卷首写下的这首自题诗,也激励着研究者和读者为追寻红楼真意而努力。这正是“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2][清]曹雪芹著、[清]高鹗续:《红楼梦》,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9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