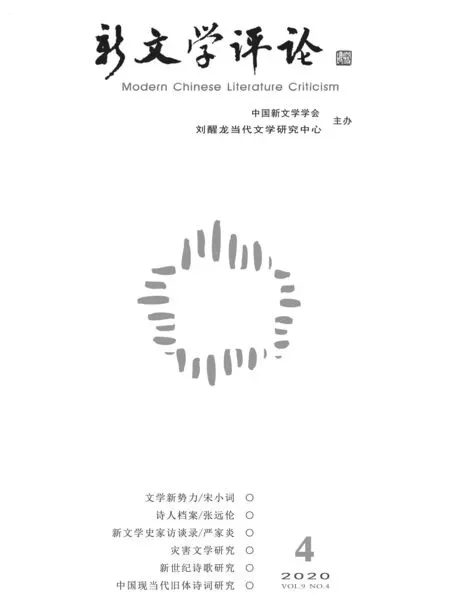从个体挫败到社会批判
——宋小词的“进城叙事”分析
□ 俞佩淋
《开屏》和《直立行走》是宋小词的两篇代表作品。这两部小说在故事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是基本的情节都与一个乡下女孩进城后的爱情婚姻有关。两个女主人公,秦玉朵和杨双福都来自贫穷的农村,都上了大学,并希望在城市扎根,过上光鲜体面的生活。秦玉朵依靠美貌,在大学期间和区长儿子相恋后结婚;杨双福单纯虚荣,无意中成为拆迁户的闪婚对象。但是,她们都不幸福,秦玉朵被丈夫暴打一顿后决定离婚,杨双福则倒在了前夫的秤砣之下。和前一代进城的乡下人相比,国家放开户籍管控,通过教育改革创造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她们进城后不用从事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路遥《平凡的世界》),或者嫁给身体残疾的城郊市民以便蛰居城市(王安忆《富萍》),为什么她们显得更加不满意,更加不幸福?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两个乡下姑娘的人生悲剧? 本文分成四个部分,分析这两个女性进城的理由,进城受阻产生的心态,以及进城后的命运,发现宋小词小说的乡下女性往往背负着家庭改变命运的使命,充满期待地进城,进城之后受到城市的“嫌弃”,激发她们更加坚定地扎根城市。当她们争取平等物质权利的时候,往往因触动权力体制而遭遇困局。
一、 主体虚空与价值幻象
改革开放至今,农村成为城市提取人口红利的窗口。素质良好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地流入城市,随着城市的崛起,农村逐渐衰败,乃至“空心化”。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意义表述系统中,农村是“传统”“落后”的代名词。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经济利益这个标准下,已经毫无意义。就像宋小词的作品里说的一样,“犁田的牛望天叫声‘哞’,便是一股子穷味。一切都毫无指望的样子”。进城打工,送孩子进城读书成为农村家庭离开乡土、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对照文本,宋小词所认识的乡村是这样的,“我们这里都是山,那山其实离我们很远,只能看到连绵起伏的形状,这形状给我们带来一种被包围的感觉,无论目光放得有多长远,终究要被这形状给挡回来,日子因此变得逼仄冗长。又是丘陵地貌,田地被地势弄得不成规矩,只能进行原始的刀耕火种”。这是一个典型的乡村景观,贫穷,封闭,人在这个空间当中周而复始地生活。除此之外,在乡土世界中个体的命运往往早早地被血缘和礼俗所决定。《呐喊的尘埃》中,小节从小就被认为将来会像奶奶和姑姑一样,拿来“垫日子”。秦玉朵家里因为只生了一个女儿,在重男轻女的农村,“爸妈为这还是受过一些气”。周围的目光和言论令小节气恼,令秦玉朵“耳朵里长出麦芒”。
乡村在固有的权力和文化秩序崩塌之后,因焦虑而产生的比较心理处处可见。弱者希望变强,强者希望能更强。《路遥遥的心事》中父亲这样的乡镇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热衷于与学校的老师攀比,“一只眼盯着别人的收入,一只眼盯别人的家事”,“比完能力比权力,比完老婆比儿女”。舍勒认为,比较是怨恨的根源,而怨恨是由对某些情感冲动加报复、憎恨、敌意、嫉妒、诋毁冲动以及恶意等进行系统压抑而产生的一种持久心态。这些情感冲动本是人性的正常要素,但由于人们不敢也不能把它们宣泄出来,只能对其进行压抑;压抑的结果就是,人生活在了“价值幻象”中①。送孩子进城读书就是“主体虚空”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重要的“价值幻象”。
然而,“供养子女进城读书”这一行为包含着深刻的悖论,从父母的角度来说期待子女遵从“知恩图报”的道德逻辑,但就“子女一代”来说读书就意味着在城市扎根,争取个体自由独立。从情感的层面来说,培养子女本来是非功利的“爱”的付出,在“渴望改变家庭”的目的下,培养却染上了功利的色彩。这两层悖论为进城读书的农裔子弟未来的城市生活埋下了悲剧的伏笔。宋小词对乡村家庭供养大学生进城这一行动内在的伦理隐痛做了细致而全面的探索。比如《开屏》中的秦玉朵努力维持表面上的体面,以免让母亲失望、担心。《天使的颜色》中南音面对母亲的数落,尽量将内心的烦恼控制在“引而不发”的状态。但在《祝你好运》中走投无路的舅舅向同样贫穷的伍彩虹索回房子宣布了舅舅对乡下亲戚决绝的态度。伍彩虹的母亲供舅舅上大学后,“跟得了天下似的,一切都有了靠”。她一次又一次地请求舅舅帮助家庭渡过难关,舅舅屡次伸出援手,但却导致舅舅一次又一次地离婚。舅舅的人生悲剧是乡村传统伦理与城市的生存法则冲突的结果。乡村的家庭目标是代代相传,牺牲个体利益获得家族的承传,但是城市更注重个体和当下的生存质量。总而言之,承载了家庭使命的乡下人进城读书要比个体进城打工要显得复杂。
二、 进城仪式与心态变化
乡下人进城是一个抹杀自我历史的过程,乡村的包袱越多,在城里遭遇的问题越多。从本质上来说,城市与乡村是对立的。“从乡下到城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挪移,同时也是乡村文化记忆不断被城市文化吞噬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乡村文化来说,应该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②农裔女大学生恰恰是城市和乡村矛盾的结合体,她们最渴望融入城市,但她们也背负着最沉重的精神包袱。宋小词的小说很少写到这些女孩子在大学期间的城市洗礼,而把这个过程后移到恋爱和婚姻中。婚姻是进城女性栖身的关键。在进入婚姻之前,她们面临着从身份到身体的苛刻的审视。
《开屏》中秦玉朵第一次进南府见婆婆,是她最重要的进城仪式。婆婆听到秦玉朵是农村的,惊呼了一声。叙事者没有很快地跟进秦玉朵的情绪,而是客观冷静地说明了一下,“那声惊叫充满了对农村人的嫌弃与厌恶,很是伤了秦玉朵的自尊”。紧接着说明漂亮的秦玉朵看上的是南府的门第,为了解决工作的事情,决定和身高不到一米七、体重一百五十斤的南翔谈恋爱。同时她还想起来母亲的教诲和期待。“妈最怕的就是她会红颜薄命。妈见多了没好下场的漂亮女人,她自己就是,落在农村里,受一辈子穷。”“妈还说漂亮女人没好下场,是因为她们缺心孔,头脑容易发热,特别是感情上把握不住自己,仗着漂亮,经常贱卖给了花言巧语和甜言蜜语。甜言蜜语值几个钱?真金白银才不落虚空。”可见,母亲最希望她能在城市里享受富贵。在感情和物质利益的天平上,母亲告诉她物质利益第一位。可以说,秦玉朵是在母亲的精神指引下,忍下了未来婆婆的嫌弃和冷落,选择了物质利益。
《直立行走》中杨双福虽然也在城市里上了大学,并在一个小公司里上班,但是她真正受到城市检验是第一次去酒吧并认识周午马。小说中这样写道,“她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世面,她确实不会喝酒,这样的场合使她感到恐惧。她的衣着也明显跟这里不搭调。她为自己的圆脸、雀斑、杂乱的眉毛和光秃秃的手指感到难为情,一看就是从乡里出来还没有被城市格式化的姑娘,话里也夹杂着浓重的方言”。 在典型的城市交际空间中,杨双福感觉到自己不合时宜,会喝酒,拥有尖脸、光洁的皮肤、精心修饰的眉毛和纤长的手指才是都市美女的样子。不仅如此,她的衣着和身材也受到了考问。“里面穿着一件黑毛衣,还是她母亲亲手织的那种,紧紧地箍在身上,赘肉如丸子般这里鼓出一团那里闪出一坨。在空调的烘烤下,热得额头冒汗,可是哪里敢脱去外套,一脱,她的穷酸与窘迫将一览无余。”杨双福在局促的同时,产生一些懊恼的情绪。“她对自己越发的不自信了。她搞不清楚这满世界的男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只觉得贞节、忠诚、本分、善良这样的传统美德似乎过时了。这个时代都要求女人学妖精,丰乳肥臀,伶牙俐齿,风流妩媚,自私自利,以美色去俘获男人的下半身,而不是以操守去打动男人的心灵。”她的道德观念不自觉地动摇了,稍做犹豫就答应了周午马目的清晰的邀约。
舍勒说:“现代现象不仅是一种事物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它是人自身的一场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而且是人的生存的标尺的转变”,“心态(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③。从农村进入城市,秦玉朵和杨双福这两个女性的心态转变为其中的时代内涵切换做了经典的注释。在身份和身材容貌被质疑的前提下,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为原始的手段——身体/性来打通城乡的隔阂。秦玉朵不惜“到医院还做了上环手术,免去了他戴套之苦”,杨双福则随时应约。但是性关系的建立,仅仅使人物表面的关系成立了,城乡隔阂依然存在。
三、 基于物质表达的尊重与爱恋
城市创造了丰富的现代物质景观,物质是城市的外部躯壳,也是城市的精神内核。区别于乡村生产的农业器物体系,城市的工业产品/商品俨然自带诱人的光辉,宋家银为了自行车和手表驱逐丈夫进城打工④,明惠因为一身洋气的衣服决定到城里当按摩女⑤。与这些打工者相比,宋小词笔下的农裔大学生既追求精神尊严,也追求物质利益,但二者往往会因为乡村身份不能兼得。卑微的地位与身上“二两骨头”反噬一般令人痛苦,进退之中有乡村礼俗与城市文明的摩擦,更有文化想象和社会现实的撞击。
《开屏》中,秦玉朵进城后,“每次给妈钱都用汇款单寄,每月六百元”。不仅如此,秦玉朵当着村人的面花三千元包车接母亲回省城。村里人正是看到了秦玉朵的阔绰和孝敬,才承认秦玉朵是“能干的女儿”,“比儿子还靠得住”。这也是秦玉朵和母亲想要的效果,“他们对妈的羡慕就算是替妈出了当初憋下的气”。这本来已经实现了秦玉朵进城的目的。但是,母亲进城打破了这一平衡,近距离地进入了秦玉朵的生活,她怕“妈多心,会觉得是自己打扰的缘故”,另外怕“妈发觉她的日子过得不好”。如果说嫁入了南府,获得的经济实惠,让秦玉朵母女解决了社会尊重的困扰,那么母亲进城,秦玉朵要解决的是内里尊重的问题。真正的冲突在于秦玉朵要同时实现物质利益和情感尊重。在《开屏》不长的篇幅中,秦玉朵和南翔的冲突频频发生。“两碗方便面”“婆婆反锁的门”“弯腰捡钥匙”等等细节都会引发秦玉朵的怒气,觉得自己和母亲被轻视、怠慢,进而产生屈辱、愤怒的情绪,还时常流泪,大哭。我们如果仔细分辨会发现,秦玉朵渴望全面支配南家的财产,内心期待南家按照乡村礼俗接待贵客一样接待母亲。但从城市文明习惯来说,私人空间不可侵犯,因此“婆婆锁门”有点过分,但捍卫自己的空间却无可厚非。年轻的女性进入城市婚姻中,想要掌管家庭财务大权是普遍想法,但是“财务独立”也是常见的情况。每次与南翔商量点事情,都要以性事铺垫,这是她自愿选择的,而不是南翔强迫的。因此秦玉朵因为摆不出阔气而生出怨气,因为得不到编制保障而生出仇恨,从本质上来说是由于乡村时代的物质匮乏和情感匮乏。她迫切地希望以丰富的物质和亲密的感情来肯定她的价值和尊严。秦玉朵虽然接受了大学教育,但还不是一个成熟独立的现代个体,她的怨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乡村期许和城市现实冲突的结果。
同样,失落也出现在杨双福身上。《直立行走》中,二人刚刚恋爱时杨双福还略略觉得有些盼头。周午马第一次开着香槟色的小轿车来接杨双福,“她从生锈的铁电梯一步步下来,闻着各种被沤烂的气味,第一次有了一种在尘埃里绽放的神色”。但是很快,她感觉到屈辱了,觉得自己就像“周午马的夜壶”。而屈辱的主要原因是约会直奔主题,没有一点“精神文明”的内容,情人节没有鲜花和巧克力,平时也不嘘寒问暖,约会的时候快捷宾馆里只有“纸一样薄的拖鞋”“带着霉味的床铺”,二人性事之后没有任何过渡又如陌路人一样分开。男女关系从性爱到情感的升华这一主题在现代文学里探讨得很充分,为什么杨双福不能把周午马旺盛的性需求当作一种爱情的表达呢?从本质上来说,是因为物质形式单薄使情感失去了依托,或者说是恋爱的文化想象和现实严重不相符。《膏肓有疾》中有一段标准情欲生成场景。穆可可下了考场,住进了刚刚认识的男友订的房。“进了房她才发现这是间大床房,窗明几净,温度适宜,装修精致又奢华。她冲了澡,洗了头,换上浴袍,整个人一身轻松。她烧了壶水,用自带的山里的毛尖泡了杯茶,喝了几口,觉得空虚无聊,便上床睡觉。床垫松松软软,躺哪就立刻沦陷在哪。她在床上舒服地滚来滚去,有些后悔不该将他放走,这么好的床,只有两个人滚才端的是种享受。”“柔软的大床”“适宜的温度”“鲜花”“金钱”,是城市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恋爱生活范式。只有在身体舒适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情欲的荷尔蒙。
在宋小词的叙事中,物质和情感难分彼此。如果说在同时代其他作家笔下,城市还有一些具备诗意和文化内涵的器物体系,那么宋小词更习惯用商品表达品位和情调。物质丰富等于情感肯定,物质贫乏就会质疑对方的诚意。恋爱前期杨双福在周午马面前忍不住自卑,并努力掩饰和隐忍。当杨双福第一次造访周午马家,“从这栋黑咕隆咚的楼里敏感地嗅到了穷和困的气味”,突然有种平等的感觉。但精神平等又不是她的第一追求,“成为武汉人”,获得大家嫉妒的眼神才是她的目标。因此她不断地夹杂在物质利益和精神尊严之中,不断地生出自卑、委屈、抱怨的情绪。
四、 “怨羡”情绪与批判主体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和乡村天然的不平等造就了乡下人对城市的“怨羡”情结。乡下人一方面对城市文化充满了艳羡,努力效仿和融入,另外一方面又因为被压抑的屈辱而对城市充满了怨恨。这二者之间的共生和转化奠定了乡下人进城的心态。秦玉朵和杨双福虽然如愿进城工作生活,但遭遇了城市里金钱造就的物质景观和权力等级的精神震撼,秦玉朵念兹在兹的编制与身份认同和精神价值无关,而是关乎生活水平的问题。而杨双福在遭遇城市底层家庭后,个人愤懑经由同情上升到社会批判。
宋小词的《所有的梦想都会开花》就涉及农裔女大学生的物质匮乏与精神自卑的问题。其中有一段场景描述了来自乡下的穆小纱捡行李的场景,“过往的行人很多,众目睽睽之下,我狼狈拣拾那些上不了台面的食品。不远处,有个人在帮我拣,我用余光瞟了一眼,看到了一双运动鞋,是耐克的,至少四十码,像船一样。还看到了一只手,手也很大,腕上还戴着一串珠链,是茶色水晶,里面有云纹,是天然的,很贵。我曾经在一家水晶店里问过,要七百多块。不知为什么,我不敢抬头看他”。来自家乡的食品“上不了台面”,与其说是因为其材料之类的原因,不如说是它们没有被“估价”,或者价钱很低。而“耐克鞋”和“茶色水晶手链”之所以令人畏惧,最直接的原因是价格昂贵。想要越过障碍,实现体面也不是难事。穆小纱和章子涛恋爱后,章子涛送她一件“宝姿”连衣裙。“不穿不知道,一穿吓一跳,原来我是那么美,连莫佩佩都被我比下去了。镜子里有一刻空气是凝固的。怪不得我妈说我是衣架子呢。”自卑的穆小纱和美貌的莫佩佩只差一件“宝姿”连衣裙。占有价格昂贵和品味高雅的商品快速地填补了主体虚空。也是因为如此,秦玉朵才会忍不住向母亲炫耀孩子姑姑送的摇篮“要万把块钱呢”,“让妈猜她身上这件衣服多少钱,妈往死里猜说一千,秦玉朵鼻子一哼,说,五千。又让妈猜她的包包多少钱,妈洪亮地说,五千。秦玉朵鼻子又一哼,说,一万”。这些天文数字本身就具有震撼的效果。法国情景主义学者认为,在现代商品生产体制下,大多数人的创造力都被转移和抑制,社会成员已经被划为生产者与消费者、演员与观众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双福们在这个体系里是“消费者”和“观众”,她们遭受着双重的精神压迫:一方面是因贫穷遭受的财富压迫,另外一方面是因自卑无力抵抗城市商业文化逻辑。
双重的匮乏使她们产生自我价值怀疑,进而怨恨家庭和社会。周午马约杨双福到家里见父母,她在衣橱里找了半天的衣服也没有找到,突然生出懊恼。于是“她忽然讨厌起自己的生活,她仇恨贫穷和自己的出身,她痛恨起那些光鲜靓丽的、会穿衣打扮的女子,她们依靠着姣好的面容和身材俘获有钱男人过着有房有车的日子,然后她痛恨起这个不要脸的社会来,竟纵容这样的风气,竟允许这样的败坏,让她们年纪轻轻却能不劳而获,享受丰富而全面的物质生活,让她们这些勤劳诚实的女子汗水洒一地,却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买不起”。这种“怨羡”心理在参观完周午马的房间以后,她找到有效的投射和共鸣点。杨双福在与周母的交谈中获得了城市另一端隐秘的历史。国企改革,职工下岗,铺垫了当下的市场经济大潮。她在历史向度上找到了城市罪恶的根据,也为自己批判社会找到了道德依据。上个世纪80年代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进城挑粪受到张克南母亲的辱骂后,曾经发出这样的灵魂质问:“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⑦而杨双福在与女记者对峙中说:“你以为我们是要争这三十平米吗?我们争的是我们作为人的尊严!”“三十平米”和“人的尊严”等同起来。高家林和杨双福批判的具体对象不同,但是其中的屈辱和愤怒是一样的。
总而言之,“乡下人进城”这一文学主题在宋小词的小说里有着具体而实在的推进。她聚焦于农裔大学生这一群体,他们在无乡可返的背景下,表现出进城扎根的坚定决心。城乡之间因文化、身份、地位等方面差异带来强烈的精神摩擦。其间释放出的“怨羡”情结并不指向窥透“物化”的本质,而是指向物质平均分配的社会诉求。这种诉求如何实现,还是一个暂时没有答案的时代命题。
注释:
①张志平:《情感的本质与意义: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②孟繁华:《“到城里”和底层写作》,《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③刘小枫:《中译本导言》,马克斯·舍勒著,罗悌伦等译:《资本主义的未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6~7页。
④刘庆邦:《到城里去》,《小说选刊》2003年第8期。
⑤邵丽:《明惠的圣诞》,《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
⑥居伊·德波著,梁虹译:《景观社会评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⑦路遥:《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