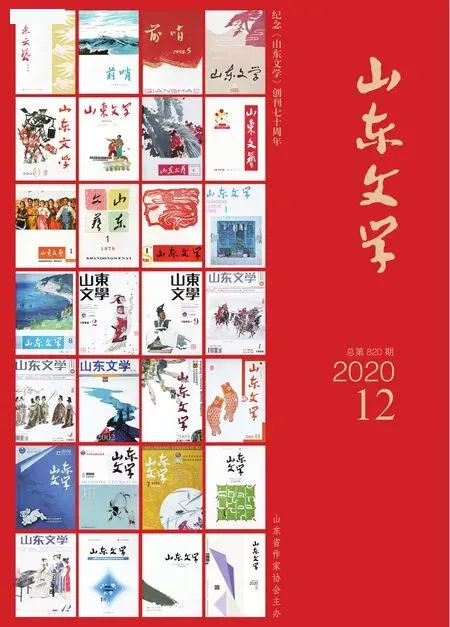从洪家楼到八里洼
——我与《山东文学》三十年
刘照如
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文学青年们大都有一个类似“文学刊物地址录”之类的小本本,上面写满自己心仪的文学刊物所在的城市、街道、门牌号码,以备投稿所用。我也有过这样一个小本本。这个小本本废弃20年之后,现在依然张口就能说出来的地址还有很多,比如上海市巨鹿路675号(《收获》),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中国作家》),南京市颐和路2号(《钟山》),等等。当然,还有两个“10号”,像球迷记得足球场上的10号球员那样,印象特别深刻,其中一个是北京市农展馆南里10号(《人民文学》),另一个就是济南市洪家楼南路10号(《山东文学》)了。
当时的洪家楼南路,几乎算不上是一条马路,而是一条胡同。走过大半截胡同,拐一个小弯儿,才能看到洪家楼南路10号,大门口挂着“山东文学社”的牌子,有点儿曲径通幽处的意思。每次走在那个胡同里,我都想起“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俗语,觉得《山东文学》社就是应该在胡同里,而不应该在大街上。如果在大街上,它是人家的,在胡同里,它才是我们的。它在幽僻处,才适合我们这些文学朝圣的人出入。那个北京市农展馆南里10号,不也是在胡同里么?古代有一种说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因此才有“里弄”之说。所以说,《人民文学》杂志社所在的农展馆南里,最初也是一条胡同。
大约有10年左右的时间里,除了我的工作单位《当代小说》杂志社,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洪家楼南路10号那个小院子。渐渐地,我的朋友们也都集中在那一带了,他们大都在那个院子里工作,家离单位也不远。我喜欢泡在那个院子里和朋友们喝茶聊天,或者到附近的小餐馆去喝酒,洪家楼一带的小餐馆,我们几乎都踢过他们的门槛。说是喝酒,却没有几个人有酒量,我们只是借着酒,说一些年轻张狂的话。有好多次,喝完了酒,我坐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我住在郎茂山,公交车几乎要穿过整个城市,车程需要一个多小时,望着车窗外的夜景,我心里很放松,或者说很兴奋。
当时《山东文学》所在的办公楼,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小楼,编辑部的几间屋子,都是门朝西,后窗朝东,或者门朝东,后窗朝西,这和平时的习惯大有不同,我因此在那几间屋子里总是失去方向感。我觉得门朝南,后窗朝北,或者门朝北,后窗朝南。就是说,我在《山东文学》编辑部始终是迷向的。
我在济南有两个地方迷向,一个地方是《山东文学》编辑部所在那座小楼,另一个地方是济南老火车站。1992年的时候,济南老火车站拆掉了,再后来,《山东文学》编辑部也搬离了洪家楼南路10号。两个让我迷向的地方倒是都在视线中消失了,可是如今,却成为我最为怀恋的两个地方,想回去已成为奢望。
多年后我把在济南两个迷向的地方讲给朋友听,朋友帮我分析说,在济南老火车站迷向,是因为我过于向往城市,城市带给我这个出生成长在贫困农村的年轻人巨大的压力,而济南老火车站的大气、沉静、华美和异域风情把我震慑了;在洪家楼南路10号的小楼里迷向,则源自于我过于向往文学,渴望成功带给我巨大的压力,那座小楼里浓厚的文学氛围让我自卑,因而迷失了自己。朋友的分析好像麦芒一样扎了我一下,我们相视而笑。
后来《山东文学》编辑部随山东省作家协会一起搬到了舜玉路40号,这个地方原来名叫八里洼,是老济南著名的地标之一。原来的洪家楼南路10号我再也没有去过,想必那个院子和那座小楼早已拆掉了吧?新址《山东文学》编辑部的几间屋子,都是门朝南,后窗朝北,或者门朝北,后窗朝南。我再去的时候,倒是不迷向了,可是在编辑部迁址前后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我中断了写作,一字不写。偶尔我到编辑部坐一坐,会觉得自己像是蹭大喜婚宴的二流子,感觉有些不舒服。
1992年,我在《山东文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题目叫《穿过你的黑发》,责任编辑是好友陈文东,他早已经离开了编辑工作,可是在我心里,他依然是我“入坑”时重要的“老师”之一。写作中断10年之后,2013年我50岁的时候重新回到写作者的行列,很快又和《山东文学》取得了实质性的联系。此后三年,我每年都在《山东文学》发表一篇小说,巧的是,这三篇小说都被《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转载了,有的进入了年度选本。我自己最满意的小说《蓝头巾》也是《山东文学》首发的。
或许是当时对洪家楼南路10号的景仰,或许是我在那几间门朝西、后窗朝东或者门朝东、后窗朝西的屋子里迷过向,一直以来,我和《山东文学》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感情。从洪家楼到八里洼,我和这本刊物始终相伴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