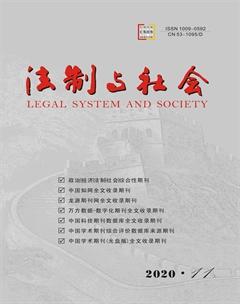浅议我国亲属容隐制度的法律价值
摘 要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古代对亲属犯罪行为的相隐在一定范围内认可且予以保障的法律规定,蕴含着中国家庭维系亲情关系的传统思想观念。新修订的刑诉法关于容隐制度虽然存在局限性,但表明在法律制度设置时除法理外也要考虑情理的特殊性。
关键词 亲属容隐 法律价值 亲情 作证
作者简介:马楠,北方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11.084
一、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亲属容隐制度的变化
容隐亦称亲亲相隐,指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亲属们应当相隐犯罪行为不向官府揭发,若揭发反而会受法律处罚。注重道德、亲情是我国自古至今社会环境、集体情感相互渗透影响的结果,容隐制度作为我国古代一项道德原则与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变化发展。
(一)我国古代亲属容隐制度立法起源
春秋时期,宗法制度日益衰落,百家争鸣,出现了很多与宗法等级制度不同的新观念,孔子为倡导礼治率先提出亲属相隐的主张,其认为“父子相隐”是“仁”和“孝”的体现。但非绝对,对于晋国大夫叔向因其弟徇私枉法有罪而杀之的行为却又获得了孔子的赞同,由此可见孔子主张:亲属间小罪当隐,大罪不可隐,隐小罪以重亲亲,刑大罪以行国法的容隐原则。
孟子对于对亲属容隐进一步阐释,舜因父亲的原因陷入了亲情与国法之间的矛盾中,孟子为其提出“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的建议,主张身为一国之君不能为维护亲人而扰乱国家制度,但作为儿子帮助父亲规避处罚又是人伦之中必须行的孝道。这样的选择不仅符合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对家庭情感重视的理念,也是孔子所倡行的亲属相隐思想的延伸。至此,关于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行为逐渐被世人接受,为国家所用,也为后世亲属间容隐制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但以韩非子为代表的的法家对此进行批判并主张国家至上主义,在忠孝难两全的情况下倡导弃孝足忠,亲人犯罪亦应告发,不能互相隐匿罪行。
秦统一六国后重用法家,亲属容隐观念未能大步发展。例如《法律答问》中“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这表明在秦朝同居亲属中,如果发生了尊长杀伤卑幼、主人杀伤奴妾的人身伤害行为,卑幼不能状告尊长,奴妾也不得去官府告發主人。虽然这些法律规定表面上似乎体现了亲属容隐观念,但实际这种下对上单向隐匿的规定主要体现的是身份等级秩序,而非为维系亲情、伦理道德所规定的容隐观念。[1]
(二)我国古代亲属容隐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完善
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一直为汉武帝所青睐采纳,随着“孝悌”氛围不断加强,仁孝理念从学术思想走向政治法律。汉宣帝时期,颁布“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明确表达了维系亲情的立法意图,由秦时卑幼隐匿尊长这种单向隐匿发展成为卑幼尊长之间双向相隐,但所规定容隐的亲属仅限于夫妻、子女和祖孙之间。“亲亲得相首匿”诏令倡导亲属间积极主动地施行容隐行为将犯罪的亲属藏匿,这标志着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亲属容隐制度的地位。
两晋南北朝时期,亲属间容隐制度在双向相隐的方向继续发展。这一时期人们还注意到株连对容隐原则的破坏。如东晋人卫展反对“考子证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2]这些观念都体现了对利用行刑方式强制亲属间互证罪行行为的反对,认为这种方式有违亲属伦理关系。除了反对强制亲属间互证其罪外,这一时期容隐亲属的范围也有所扩大,从以往父母长辈的近亲属扩大到了兄弟姐妹的同辈亲属。
隋唐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已经比较完备,规定了相隐的亲属范围、违反的法律后果、适用的范围、例外规定等。纵观历史,亲属容隐制度自秦萌芽到汉的确立,在唐朝趋于完善一直备受青睐,流传至今也不足为奇。
(三)我国古代容隐制度的存在基础
社会政治基础。我国古代的宗法制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国一体社会形式,这种形式无疑会对影响到各项政治制度。亲属容隐制度受历朝统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是稳定社会的作用,国是千万家,一个国家的稳定必然离不开千万小家的和谐共处,而容隐制度正符合维护家庭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的要求。但容隐制度并非没有限制,若某种行为扰乱国家秩序,威胁统治阶级的利益时,如谋反、叛国罪,此时法律不再让位于亲情,这也是历朝统治者不可逾越的底线。
亲情伦理基础。中国古代法律将习惯、礼仪、伦理等多方因素融合,让法律制度难逃“人情”的理念,亲情伦理也贯穿于古代法律观念中,容隐制度便以对亲情伦理的重视为依托不断发展。中国古代是一个被儒家思想渗透的时代,“仁”“孝”“礼”理论影响深远,亲属容隐正是在这样的观念环境下产生的,亲属互隐是被大家接受的行为,是人们心中认为的理所当然的“情理”,是对亲情关系的维护,也是对儒家伦理观念的呼应。[3]
二、我国现行法中关于容隐制度的变化
(一)新中国成立到刑诉法第二次修改前容隐制度的缺席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方面都为巩固新生政权做准备,刑事司法的重点则是要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打破一切封建主义的法律制度,亲属容隐制度自然逃不过作为“封建糟粕”的命运被否定。
文革时期,“大义灭亲”“六亲不认”被作为革命原则大肆宣扬,一个革命者必须秉持“大义”原则,即便面对亲情也毫无例外可言,那时子女揭发父母罪行、夫妻间相互揭发的事例屡见不鲜。1979年的《刑法》与《刑诉法》中都规定知悉犯罪嫌疑人情况的任何人,包括亲属在内,都不能作伪证,不能实施窝赃、包庇行为,否则要追究刑事责任。[4]通过1979年关于包庇罪、伪证罪的法律规定来看,法律要求每个人都有必须履行作证的义务,即便面对自己的骨肉至亲也无法免除指证义务,但这样的强制要求不仅违背人性伦理,造成作证亲属的精神压力,也与中国古代秉持的文化理念相悖,如此一来,法律在社会实际运行时会与最基本人情发生碰撞冲突的窘迫,1996年《刑诉法》和1997年《刑法》的修订,仍相沿如旧,虽然在逐渐淡化法律的政治化,但这种思想仍然存在惯性残留在当时中国法律制度中,亲属容忍制度便难以于法律中彰显。[5]
(二)新刑诉法修订后容隐制度的体现
随着人权法治的热潮,“大义灭亲”式的法制模式逐渐受到质疑和批判,人们又开始重新追求对家庭亲情的理念,强调法律的“温度”。
2012年新《刑诉法》修订时设置了“不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规定,规定一出,便引起学者们的讨论,对于是否说明亲属间作证的义务自此不再强制存在不同观点,但不少学者认为这项规定,虽不能说完全允许近亲属之间相互容隐,但也部分肯定了亲属容隐制度。[6]
实际上,《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对于法院可以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新增加的“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的规定,相较于中国古代亲属间相隐的制度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该条的修改并不意味免除近亲属作证的义务,只是在作证方式上不再强制出庭,但仍然需要通过书面、录音、录像等方式指证自己的近亲属,因此这条规定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亲属容隐制度。
三、容隐制度法律价值分析
(一)平衡法律与亲情
亲情本是人类感情的起源,生存在社会生活中的人类与生俱来便有维护亲情的本能,在司法诉讼中,亲情关系不可避免的会与国家利益、法律义务产生冲突,此时国家利益、法律义务在一定程度都应让位亲情。法律中的亲属容隐制度规定,便充分体现了道德人权与法律人权的融合,平衡了法律与亲情之间的利益关系。
一部良好的法律应当具备不强人所难的特质,法律本身规范的主体就是人,是为普罗大众制定的,那么其所禁止或者许可的事项便应当符合一般人所能够接受的标准,法律本身就是融合多方面因素综合制定,社会道德也是法律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这部法律设置了一般民众都难以服从和接受的制度,违背了人情道德,那么自然也难以被遵守,就难以称为“良法”。维护自己的亲人,使其免受刑罚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亲属容隐制度便符合这样的普世价值,尊重人性的法律制度,才能为人所接受,如果这种源自天性的容隐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久而久之,人性是否也会渐渐淡化。
法律不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恶魔,法律也不是一个冰冷无情的工具,法不外乎人情,法律制度不过是由普罗众生的人情铸成的,亲属容隐制度允许亲属在特定的场合下可以因亲情而不履行法律规定的指证、揭发犯罪的义务。亲属容隐制度充满着对人性弱点的宽容与体谅,比较好地协调了国家利益与亲情伦理之间的关系,为平衡法律与亲情关系提供了一个支点。
(二)符合法律的效益
法律的效益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指法律在社会运行中尽可能利用小的成本基础上取得最大的回报,若想达到法律效益最大化,那么在设置法律制度时就要考虑用较小的法律成本赢得较大的司法收益,亲属容隐制度在古代社会发展运行中总体体现了法律效益的考虑。
刑诉法修改前,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了任何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在具体的法律实施中,极少有人会主动揭发自己亲属的犯罪行为,这样一来不仅不能如期达到法律效果,也浪费立法资源。亲属出庭作证率低,是因为出庭指证亲人犯罪行为必然会遭受亲情关系破裂以及个人内心的谴责压力,用法律的刑罚来对待亲属间的容隐,可能会加重社会潜在的道德危机从而破坏社会秩序,最终可能因为这种不近人情的法律适用对社会造成困扰,从法律的效益角度考量,相较于成功追诉几个罪犯来说,这样的困扰对社会伤害的成本过于高昂,不符合法律效益的理念。
法律本身就是法治社会中平衡法理与情理关系的工具,需要调和各个利益间的冲突与矛盾,追求法律效益的最大化,只有能够和谐调整社会效益的法律才具备了一部“良法”的基础,从而真正实现法律的价值,而法律中容隐制度的设计就是符合法律的效益追求。
四、結语
现代文明的社会法治主义国家必定要做的是努力追求真正达到良法善治的,亲属出庭作证容隐制度必须尊重了传统、尊重了亲情伦理、符合了法律的效益,是真正达到了良法善治的重要举措。新的刑诉法对于亲属间作证规定中所涉及的容隐权,虽然有很大的法律局限性,但也映射出如今立法者在制定法律制度时不再单单以犯罪事实作为唯一评判标准,也开始注意到亲情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注意到了法律中“情理”的保护价值。
参考文献:
[1] 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5,135.
[2] 《晋书·刑法志》.
[3] 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 李拥军.“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博弈:亲属豁免权的中国面相[J].中国法学,2014(6):89-108.
[5] 梁玉霞.传承与移植的失却——对我国亲属作证义务的反思[J].中外法学,1997(4):83-86.
[6] 陈瑞华.从认识论走向价值论——证据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2001(1):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