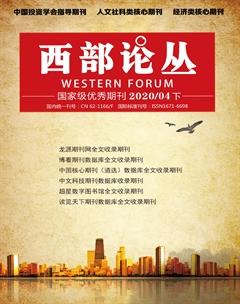合同解除溯及力问题研究
摘 要:合同解除是否产生溯及力直接影响合同解除的效果的构建,笔者通过分析“有溯及力说”对合同解除效果的构建,提出“有溯及力说”无法适用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原则并有悖物权公示效力,采“无溯及力说”符合合同解除的功能,利于维护交易安全。
关键词:溯及力;恢复原状;合同解除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规定于《合同法》第97条[1],对于该法条理论与实务中均有诸多争议,这些争议如下:何谓恢复原状,此处所谓恢复原状是否与《物权法》中对恢复原状的表述内涵一致,该恢复原状指的是物理层面还是法律关系层面。诸争议之核心在于恢复原状与溯及力是否有必然联系。即合同解除是否产生溯及效果。
针对以上争议,全国人大法工委也曾作出解读,其主要观点为:合同解除后,对于合同双方各自未履行的部分,履行义务消除,自然也无权要求对方将来付诸履行;而已经全部完成或者部分完成部分,则判断选择“恢复原状”或“采取补救措施”,在给付之物有折损或者已经灭失,于现实情况已不能恢复时,有权一方可主张损害赔偿,“信赖利益损失”为其赔偿范围。法工委的解释并没有解决合同解除溯及力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表明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倾向于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因其主张损害赔偿的实质为当事人信赖利益损失,因为在实务中,所谓信赖利益赔偿,往往是因合同一方为了使合同能够订立而付出了准备费用,赔偿的范围是因合同没有订立,因此赔偿该支出的费用。若合同解除产生溯及效果,合同恢复至未订立之时,此时产生信赖利益的损失。笔者认为,信赖利益损失不仅仅产生于合同订立之时,还产生于合同履行的过程之中,比如合同一方当时人基于相信对方的履行而作出一些特殊安排,从而因对方不履行而产生损失。因此,法工委的解释并不能确定合同的解除是否产生溯及力。
我国民法典第566条在保留《合同法》第97条内容的基础上,补充规定解除不碍违约责任的主张,此规定表明,合同解除不影响当事人主张违约责任,笔者认为该规定似乎表明了我国立法机关的态度,即合同的解除不产生溯及效力。因为合同解除若具有溯及效果,合同回复至订立之时的状态,双方当事人不再受原有的合同关系的约束,自然无法主张违约责任。
虽然民法典明确了合同解除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但是并未明确有无溯及效力的问题,而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对于合同解除法律效果的路径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本文旨在对合同解除并无溯及力进行论证。
二、合同解除“有溯及说”对解除效果的构建与分析
(一)“有溯及力说”对解除效果的构建
以崔建远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坚持认为根据法条自身的逻辑出发,九十七条的立法逻辑应是直接效果说。该学说核心观点认为合同解除有溯及力,溯及至订立之初,合同解除则面向没有履行的“给付义务”免于履行,已经履行的“给付义务”则产生返还请求权。
为了直观的展现,“有溯及力”對合同解除效果的影响,笔者将假设如下案例,甲与乙签订买卖合同,合同标的为黑色汽车一辆,合同中约定,合同签订后车辆仍由甲占有,乙先支付价款的20%,车辆在甲占有期间遭到火灾灭失。后乙因无力支付价款,甲主张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甲主张其已占有改定的方式履行了给付义务,要求乙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恢复原状,因标的物无论在物理层面还是法律关系层面都现实的不能返还,遂甲要求乙赔偿损失。若采“有溯及力说”将对假设案例做以下回应:甲主张解除后,合同消灭,无有效的债权合意合同,而我国又未认可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由此,甲乙之间未发生过物权变动,甲仍为所有权人,因此甲可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若标的灭失,可主张损害赔偿。有鉴于此,“有溯及力说”将支持甲的主张。在假设案例中,若支持甲的请求,显示是对乙不公平的。但是,“有溯及力说”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其阻碍在于,若合同解除有溯及力,则不能适用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原则,若采“无溯及力”说,则可运用风险负担原则解决此问题,因为占有改定并非实际的交付,所以在甲交付前风险由甲承担,乙可以此抗辩。
(二)对“有溯及力说”的反驳
崔建远教授认为,“恢复原状”之法条表述,旨在要求合同关系回复至合同订立之初,因此只有承认合同解除之溯及力,依照逻辑才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恢复原状”这一表述[2]。同时崔建远教授认为,不能一概的认为所有的合同都有溯及效力,要区分继续性合同与非继续性合同,合同的内容是交付物,还是提供某一类的劳务,在非继续性合同的当事人行使解除权时,一旦解除则产生溯及订立之时的效力,继续性合同因其合同具有整体不可分性,其已履行的部分常常已经互为对待给付 ,无“恢复原状”之必要,因此,亦无溯及的必要;对于交付物的合同因有恢复原状的必要,因此具有溯及力,对于提供劳务的合同,劳务本身无论在物理层面还是法律关系层面均无法复原,即无恢复之客观可能性,有鉴于此,无溯及效力。
总结分析崔建远教授的观点可以得出,其认为,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完全要看物理层面和法律关系层面或者所有权归属层面是不是可恢复。此种处理方法导致不同性质及现实状况的合同解除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并且“恢复原状”的客观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也不得而知,若将判断标准置于法官自由裁量,则裁判标准不仅不统一且会有自由裁量之范围过大的弊病。若立法规定,实务中“恢复原状”的情形难以类型化,会增加额外的负累。
三、合同解除无溯及力的论证
(一)从合同解除的功能分析
有观点认为,合同解除的目的是打破当事人之间的僵局,因为合同已发展至解除局面,自然无挽救的意义,其制度意义是排除双方在原合同框架内的束缚。持有此观点的人对合同解除溯及力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进行如下反驳,其认为,如果合同解除没有溯及效力,那么基于有效的合同所受领的给付,均具有合法性,既然受领合法,那么如何产生返还的法律效果?只有肯定合同的溯及力,才会自然的使得原有受领失去合法性,从而基于物权请求权或者不当得利请求权来要求返还所获受领。
笔者赞成该解除之目的的表述,但是笔者认为,这是合同解除意欲达到的效果,而合同解除作为实现该目的手段,其承载的功能不仅仅是消除双方的对待给付义务,更重要的是将已经履行的部分通过清算,使得合同双方当事人达到利益平衡。笔者认为,在合同要走至解除之阶段之时,无论是依法还是依约均是因有致无法实现双方当事人最初签署合同时的目的违约的发生,在合同一方作出了全部或者部分的给付,对方未依照约定作出对价履行时,该方当事人之受领便失去了合法性。因此,在合同解除的情形下,合同履行已至终局,未履行对待给付的违约一方再无机会使得该受领行为具备合法性,即受领方之受领终局的成为“不当得利”。在此情况下,仍然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主张返还,同样达到了“恢复原状”的功能。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将恢复至原状作为合同解除的目的是不对的,恢复原状只是清算“不对价的履行”的一种手段,将“恢复原状”作为有溯及力的支撑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二)从交易安全角度分析
笔者认为,合同解除不应当产生溯及的效力,因为合同存在并且已经有过履行的情况已经成为了法律事实,即便视为自始不存在,这些法律事实也不会随之消失,如若肯定合同解除的溯及力,则会产生危害交易安全的后果,对交易安全的危害既包括对意欲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影响,也包括对潜在第三人的影响。
对交易双方的影响体现在,合同溯及既往的灭失,合同当事人对于该交易付出的一切成本、精力均付诸东流。合同因为违约方的不履行而产生消灭的效果,显然不利于交易安全。有观点反驳,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以通过主张损害赔偿来止损信赖利益[3],上文亦提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对合同解除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为信赖利益损失。在我国实务中,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仅仅是为合同的订立或者履行而支出的费用,甚至部分法院仅支持缔约过失损害赔偿,此种损害赔偿并不能很好的救济守约方,因此应当否定合同溯及既往的消灭,守约方可主张违约责任。
对第三方交易安全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买卖合同之中,比如:将上文构建的假设案例进行如下变形:甲将汽车交付与乙后,乙又出卖与丙,若因乙不支付价款,甲主张解除合同,则乙与丙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如何处理。依照“有溯及力说”的解释甲乙之间视为未发生过物权变动。由此,乙的出卖行为是否要依无权处分处理,若丙明知甲乙之间的买卖关系及乙未支付价款的事实,丙又是否能构成善意第三人。这样就导致乙和丙之间的交易行为处于一种不确定之中。
综上所述,“有溯及力说”不能解决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问题以及于物权公示效力之间有悖,影响交易安全。主张溯及力无非是为“恢复原状”的法条表述提供了逻辑上的支撑,但在对待给付不能的情况下,合同解除的制度设计不应当是消除给付,而是清算已处于履行状态的不对价的给付关系,因此“恢复原状”在当事人处于清算关系中时,视为清算的手段之一,也符合法条之间的逻辑。因此,笔者赞成解除合同不具有溯及力。
注 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2] 崔建远:《解除权问题的疑问与解答·下篇》[J],政治与法律,2005,(4)
[3] 高嵩:《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02):45-50
参考文献
[1]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 崔建远:《合同法总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 崔建远:《解除权问题的疑问与解答·下篇》[J],政治与法律,2005,(4).
[4] 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27-728;
[5] 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62.
[6] 蔡立冬:《論合同解除制度重构》[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5)
[7] 李开国,李凡:《合同解除有溯及力可以休矣——基于我国民法的实证分析》[J],河北法学,2016(05):22-32
[8] 高嵩:《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02):45-50
[9] 符欣欣:《合同解除后恢复原状的定性与适用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7(04):17-32
作者简介:王亚娟(1995-),女,汉族,山东泰安市人,法学硕士,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民商法学专业,研究方向:商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