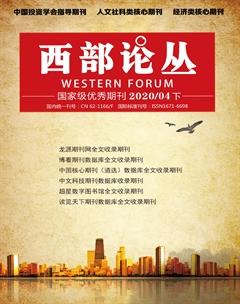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研究
摘 要:诈骗行为是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核心要素,诈骗行为的实质在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使得被害人陷入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产。行为人的欺诈行为要想构成诈骗行为,必须达到足以使可能受骗的同类一般人陷入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的程度。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诈骗行为可以分为事实诈骗与价值诈骗,作为诈骗与不作为诈骗。
关键词:诈骗行为;实质;程度;价值诈骗;不作为诈骗
我国现行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立法者采用简单罪状的方式规定诈骗罪,并未对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特征作详细描述,根据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普遍认识来看,要构成诈骗罪,必须同时满足五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要素,即:“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1]而行为人实施的诈骗行为是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核心要素,对于诈骗罪的成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诈骗行为进行深入研究。
一、诈骗行为的概念
从词源上来看,《汉语大词典》中“诈”是指“欺骗;作假、假装;用语言或手段骗人,诱使对方透露真情”。“诈骗”是指“讹诈骗取。”[2]《辞海》中“诈骗”一词是指“以假冒身份、伪造证明、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诈手段来骗取公私财物以及其他招摇撞骗的行为。”[3]可见,“诈骗”一词在词源意义上具有两层含义,即“骗”与“取”。“诈”是指欺骗、欺诈,包含行为人虚构、隐瞒等欺骗行为;“骗”是指通过骗人的手段以取得对方的财物。其中“诈”是行为手段,“骗”是行为目的,行为人通过欺骗、欺诈行为以最终实现取财的目的。但是,作为诈骗罪客观方面构成要素之一的诈骗行为,其重点应在于“诈”而不在于“骗”,因此诈骗行为应仅包括行为人为实现取得他人财物的目的而实施的欺骗、欺诈行为,不包括后续的取财行为。综上,笔者认为,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应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使被害人陷入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产而实施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行为。
二、诈骗行為的实质
行为人所实施的欺诈行为并非都属于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要构成诈骗行为,必须满足“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欺诈行为足以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因行为人的欺诈行为而陷入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并‘自愿处分财产”的行为模式。行为人所实施的欺诈行为与被害人陷入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即被害人是因为行为人的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的,如果没有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被害人就不会处分自己的财产。但是,若行为人确实实施了欺诈行为,而被害人却没有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则该欺诈行为就不是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例如,甲使用伪造的演唱会门票,被检票人员识破未放行,随后其又趁检票人员不注意偷溜进演唱会现场的,不属于诈骗行为。但是,如果甲将伪造的门票交给检票人员查验,检票人员误以为该票为真实门票,从而放甲通行的,则属于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
综上可见,诈骗行为的实质在于行为人所实施的欺诈行为使得被害人陷入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产。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开启了诈骗罪的大门,如果被害人没有陷入错误认识,或者虽陷入错误认识但处分行为并不是基于该错误认识而作出的,被害人就不会跨进诈骗罪的大门,不成立诈骗罪。
三、诈骗行为的程度
社会生活中的欺诈行为无处不在,特别是在商业活动中,例如某服装店在商店门口挂着“清仓大甩卖,最后五天!”的广告牌,但事实上该商店并未真正进行亏本甩卖活动,挂广告牌只是他的一种营销手段。这些欺诈行为实际上都属于行为人对某一事实的吹嘘或夸大,但却不属于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因为在社会生活中,行为人对某一事实进行一定程度的吹嘘或夸大往往是能够被人们所容忍的,人们通常也能够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辨别该行为的真伪,一般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具有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的可能性。此外,如果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就能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刑法就会有过多干预人们日常生活之嫌,刑法的过分规制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并非所有的欺诈行为都能构成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只有当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传达虚假信息的行为具有使人陷入或维持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的可能性时,该行为才达到构成诈骗行为的程度,才有可能成立诈骗罪。
那么究竟应以何种标准来认定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具有足以使人陷入或维持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的可能性?目前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主观标准说认为,判断欺诈行为是否能够达到足以使他人陷入或维持错误认识的程度,应当根据具体的、特定的受害人的情况来确定,综合考量被害人的年龄、性格、对诈骗行为的谨慎程度、辨别能力、生活经验等要素来认定。而客观标准说则认为欺诈行为能否达到足以使他人陷入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的程度,应以社会一般人的判断能力为标准。笔者认为,若坚持主观标准说,则需要根据欺诈行为所指向的特定对象的具体特征进行综合分析,若被害人受教育水平低、认知能力较一般人弱,即使是对于其他人而言十分荒唐的骗局他也可能深信不疑;若被害人社会经验丰富、警惕性高,即使行为人的诈骗手段十分高超,他也不会因此上当受骗。这样一来,对于诈骗行为的认定就会失去统一标准,使得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丧失定型性,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因此主观标准说并不可取。对于客观标准说,笔者亦不完全赞同,因为社会生活中的诈骗行为无处不在、各式各样,而行为对象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社会经验、警惕性等主观因素确实也各不相同,若仅以具有普通认识水平、认知能力的一般人的判断为标准来认定诈骗行为,则会使得某些欺诈行为得不到合理定性,不利于对社会上的弱者及缺乏社会经验的人给予刑法保护。[4]因此,笔者认为在认定诈骗行为的程度时,应以客观标准为主,同时适当考虑主观标准,即认可客观标准说中以一般人的判断能力为标准认定诈骗行为,但应通过主观标准对“一般人”进行限定,这里的“一般人”应指在特定情形下与被害人情况相似的可能受骗的一般人,而不是具有普通认识能力、辨别能力的所有社会一般人。应考察他们在相同的情况下是否也具有被骗的可能性,若答案是肯定的,则应肯定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已经达到构成诈骗行为的程度,成立诈骗罪。
综上,行为人对外传递虚假信息的行为要想构成诈骗行为,必须达到足以使可能受骗的同类一般人陷入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产的程度。以此作为诈骗行为的统一认定标准,既能最大限度地给予弱者刑法上的保护,又能更好地实现诈骗罪的规制效果。
四、诈骗行为的表现形式
(一)事实诈骗与价值诈骗
根据行为人在实施诈骗行为时所使用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判断,可以将诈骗行为分为事实诈骗与价值诈骗。
1. 事实诈骗
行为人以“事实”为依据向被害人传递错误信息的行为是诈骗罪中最常见的诈骗行为之一。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所使用的“事实”既可以是外在的事实,如自然事实,行为人的身份、能力,行为人或他人已经实施的行为,法律规则,也可以是内在的事实,如心理意思、支付能力。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事实”,只要行为人虚构或隐瞒的该事实在客观上足以使被害人陷入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并因为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即可。具体来看:诈骗行为人利用自己的身份、能力进行诈骗是指行为人为实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对自己的身份、能力进行伪装,通过伪造假证明、假文件,制造开设公司的假象等方式把自己摇身变成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并通过该虚假的外表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以便于更好地实施后续的诈骗行为。就规则进行诈骗,是指行为人通过对法律、法令以及其他规则的虚假陈述,使对方陷入错误。[5]即法律或有关规定明确将某一行为规定为有效/无效行为,但行为人利用被害人对他的信任,歪曲法律规定,使被害人认为其行為是符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进而实施违背其真实意愿的处分财产行为。利用心理意思实施诈骗,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或他人的心理活动内容进行虚假表示,致使对方陷入或维持错误认识。心理意思属于个人的心理活动内容,他人不易察觉或对其加以证实,但行为人往往是利用心理意思的该特点来欺骗他人。
2. 价值诈骗
价值判断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于各种事物、现象所作出的好与坏、正确与否的判断。价值是由人来判断的,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不同的人由于知识结构、认知能力、生活经历及价值观等不同,在对同一事物进行评判时难免会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因此,对于行为人是否能就价值判断实施诈骗行为这一问题,理论上也存在不同的主张。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只有事实才有真假之分,意见或价值判断属于一个人的主观评价,其不是事实,也无真假之分,因此虚构事实中的“事实”不包括价值判断的内容。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就价值判断进行虚构也能构成诈骗行为,如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指出:欺骗行为,是指使人陷入错误的行为,除此之外没有特别限定,因此,不仅可以是有关事实的欺骗,而且可以是有关评价的欺骗。[6]
笔者赞同肯定说的观点,首先,诈骗行为的实质在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产,因此行为人无论是对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虚构,还是对价值判断进行虚构,只要行为人所虚构的内容足以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即可构成诈骗行为。其次,虽然价值判断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在社会生活中对于某一事物、现象的价值判断往往存在着能为大众所认可并接受的公认标准。通常情况下,一般人对某一事物、现象的评价结果相较于公认标准而言并不会存在太大的偏差,一旦出现偏差过大或与公认标准截然相反的情况,就可以认定该评价与事实不符,若行为人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主观上还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该行为最终也导致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的,即可认定行为人成立诈骗罪。
(二)作为诈骗与不作为诈骗
根据诈骗行为所违反的规范类型的不同,可以将诈骗行为分为作为诈骗和不作为诈骗。对于作为的诈骗行为,理论和实践中都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于诈骗行为能否表现为不作为这一问题,理论上则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1. 作为诈骗
在刑法中,“作为是指行为人以身体活动实施的违反禁止性规范的危害行为。”[7]从表现形式上看,作为是积极的身体活动;从违反法律规范的性质上看,作为直接违反了禁止性的规范。即积极地违反法律规定,不应为而为一定的行为。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绝大多数犯罪都可以以作为的形式实施,诈骗罪亦如此。作为诈骗既可以以明示的方式实施,也可以以默示的方式实施,其中明示的作为更为常见,包括利用自己的身体实施的诈骗行为、利用工具或动物实施的诈骗行为及利用他人实施的诈骗行为。而默示的作为则表现为行为人通过可推知的举动进行虚假表示。
2. 不作为诈骗
不作为是与作为相对应的另一种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不作为,就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的危害行为。[8]即消极地不履行法律义务,应为而不为一定的行为。对于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能否表现为不作为,国内外理论中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全面否定说认为,行为人的不作为不能构成诈骗行为,因为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诈骗罪可以由不作为的方式实施,若将不作为认为是诈骗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则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部分否定说认为,诈骗行为可以表现为不作为的形式,但是需要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作为只有与作为具有等价性时,才能构成诈骗行为。肯定说是目前刑法理论上的通说,其认为诈骗行为既可以表现为作为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的形式。
笔者赞同肯定说的观点。首先,诈骗行为的实质在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使被害人陷入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产,而刑法并没有对诈骗行为的方式进行限制,因此只要是能够使被害人陷入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的行为,无论是以作为还是不作为的形式表现出来,都属于对“不得诈骗他人财物”的禁止性规范的违反,当然构成诈骗行为。其次,当行为人负有向被害人告知真相的义务以防止被害人陷入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时,被害人相对于行为人而言处于弱势地位,此时被害人对事实的判断依赖于行为人所传递的信息,若行为人不向其告知应说明的事实,极易使被害人陷入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由于行为人的不作为掌控了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这一危害结果发生的因果进程,行为人应对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承担责任。可见,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诈骗行为与以作为方式实施的诈骗行为具有同等的社会危害性,可以构成诈骗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不作为都能构成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说“不作为的欺骗要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就必须与作为具有等价性。[9]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存在基于保证人地位的作为义务。只有处于保证人地位的人的不作为引起侵害结果,才能与作为引起的侵害结果同等看待,才能肯定这种不作为符合构成要件。[10]即只有当行为人处于保证人的地位,具有法律所赋予的告知义务,能向被害人说明真实情况但不说明,致使被害人陷入或者继续维持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产的,行为人的不作为才构成诈骗行为。如果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不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而且行为人也不负有向被害人说明真实情况的义务,其只是单纯地利用他人的错误认识取得财物的,此时行为人单纯的沉默不构成诈骗行为,不宜认定为诈骗罪。参照一般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的判断,不作为诈骗中的保证人的作为义务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内容: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以及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
注 释
[1] 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汉语大词典》(第11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
[3] 《辞海》(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4] [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5] 张明楷:《论诈骗罪的欺骗行为》,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第3期
[6] [日]平野龙一著:《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
[7]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8]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9] 张明楷:《论诈骗罪的欺骗行为》,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第3期
[10] [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东京有斐阁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信息:杨璟(1995-),女,云南普洱人,上海大学法学院2014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