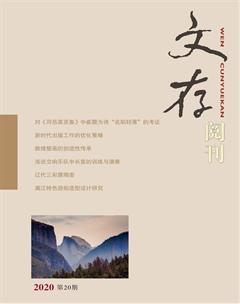《南方车站的聚会》
李颖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男女主角的生存境况、行动逻辑等进行综合剖析,阐释影片中主人公悲剧结局的深层哲学原因,并引申至处在每个身处消费社会的个体所面臨的爱欲困境,资本在消除一切差别性的同时空前的填充了人们对于爱欲的同一性想象,人们沉溺自我,爱欲死亡。
关键词:南方车站的聚会;资本;爱欲
引言:阿兰·巴迪欧在评价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作品《爱欲之死》时谈到“当今社会越来越像一个同质化的地狱,而爱欲的经验不在其中。个体的内在危机在于,一切事物均成为被消费的对象,从而毁掉了爱欲的渴望。”这句论断亦揭示了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中角色悲剧性命运的根源:个体在对幸福的追求中被金钱所遮蔽从而使得每一个选择的判断依据发生偏差,最终亲手建构了令人叹息的命运。男主角周泽农自我献祭式的自首,刘爱爱在爱欲和金钱中的反复犹疑以及杨淑俊内心对于举报款“得”与“不得”的激烈博弈。这诸多表面矛盾的背后深藏着资本世界社会意识中的“幸福”与真正的“幸福”之间的根本对立,每一个主角在奋力追逐前者的过程中无意识地与后者背道而驰。
一、“正直的犯罪者”
周泽农无疑是这部叙事片最核心的角色。他自身携带着宿命的限定性,虽然是社会底层却并非是好吃懒做的标准底层符号化形象。作为一个中年人,他却有着不合时宜的少年血性,自身又背负着作为中年人的社会性责任。这种棱角使角色充满张力却造成了家庭的支离破碎。而遭对手暗算死里逃生却失手杀死警察的事件遭遇又规定了他的脆弱。与健壮身体所对应的,是他极易被摧毁的命途。在国内的电影语境中,人物的此开端也直接表露了故事结局,死亡是他唯一的归属。因此,影片最本真的情绪氛围是一种困兽之斗的悲凉与逃无可逃的绝望,他所有为了抵抗的行动的底层都是最深的消极性与否定性。手下兄弟因自身的比拼承诺而死,丈夫与父亲双重身份的失职造成了周泽农社会性身份的湮灭。在消费主义背景中,唯有金钱是他一切的救赎,金钱亦成为其追求的悖论。为了物质,他走上犯罪之路,但他的行动举止间却充斥着一股子侠气,包括他决定以自己为妻儿换取30万的线索费总是有些舍生取义的意味。这位“正直的犯罪者”,他的行为与目标却处在两个极端,极度对立。倘若他不以追求金钱为目的,围绕他的,就是另一套生活逻辑了。这不仅是周泽农单一层次群体的生存困境,甚至也不仅是当代中国底层大众的困境,而且是如今的状况,是人类面对人生概念的模糊性与采取行动的具体性的矛盾,是确定性行为与不确定性结果的失控。
二、“脆弱的自我保护者”
影片文本的叙述人毫无疑问是刘爱爱,陪泳女的身份好似一把无形的锤子在不断敲击她濒临瓦解的灵魂。与此相呼应的,金钱是她的唯一可能的保护罩,男性角色无法带给她持久的安定,周泽农赐给她片刻的欢愉后又用金钱打破了她的幻觉,她赤裸地意识到自己身份的不堪,甚至低于杀害警察的凶手。而随后刘爱爱所遭受的性暴力又彻底摧毁了她对于男性的想象。这些境遇,将她推入了对物质的追求。如果情感是虚无与不确定,那么她便选择物质这种实在,并以此成为她抵抗世界的盾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周泽农作为男性象征着资本逻辑的效率与权力,他目的的达成却是刘爱爱这个柔弱的女性角色来实现。这不可谓是另一种女性意识的书写,他身边几乎所有的男性角色都因为这笔举报费背叛他,给他内在支撑的,都是女性的力量。
尤其是他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妻子杨淑俊。妻子形象很明显具备某些“传统中国美德”,她坚忍不拔,默默守候,在丈夫角色缺席五年的情况下依旧照看家具店并抚养儿子。即便她如此坚韧,命运亦紧紧依靠着男主人公。这个角色更像是男主人公救赎自己的解药,在影片中或者在这个故事中,她和男主角周泽农的爱欲始终缺席。表面看来,周泽农是要给她带来“更好的生活”才背离她,但进入更深的内里,远离与抛弃是同一行为的“一体两面”。如果说周泽农被射杀的结局是这场群体暴力的显性承担者,那么作为妻子的杨淑俊以及被误杀警察的妻儿则是暴力的隐形承担者,以一种缓慢而又持久的方式。
三、“毒药”与“解药”的身份迷思
影片中刘爱爱去找杨淑俊并告知她周泽农要见她一面时,杨淑俊有句台词:“他说要去赚钱,一走就是五年”。话中所提及的“赚更多的钱”其实是资本世界给与人们的诱惑,它与网络社交平台相融合,将极少部分“有钱人”的生活展示暴露于大众眼前,借助虚假幻象的同时配合消费主义的话语来建构起物欲社会,刺激大众并使其进行自我剥削。相较于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剥削,这种剥削往往被受剥削主体内化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将其看作是追求成功的唯一路径。在当今数字化社会的表象之下,资本,或者说金钱成为唯一的尺度。人在其中被挤压、被考量而难以收获真正的爱欲。如同韩炳哲认为当下人们执着于成功便会加剧自我束缚,他者无法显现,爱欲随之消失。“当今世界,自恋主体的核心是追求成功”,成功可以通过确认“我”的成绩而与他者分离,他者就成了“我”的参照物,这一奖赏性的逻辑将自我更加牢牢地编织在了自我的主体之中,使得自我与爱欲步步远离。”
四、结语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异质现象的原因来自于其一致性:金钱使得一切没有任何不同,它消除了事物本质上的差别。[1]这也是影片悲剧性的根源所在,金钱在主人公心中是一切抽象概念的本质表现与具象身份,它是男主人公失诺的丈夫与缺席的父亲身份的同一性补偿,是女主人公诚信的证明与衡量,是二人的“爱情替身”,是两个女性角色结契的抵押物,是诱惑亦是背叛,而在影片的社会层面也是公权力实施正义的手段。
这也是当前个体生存所面临的具体困境,人类生活的核心是对爱的追求。可当下的人们却在爱中感受到的疼痛越深。资本的介入下,人类的本质追求被金钱与成功所笼罩,在此背景下的人们误以为追求后者便能达到幸福彼岸,殊不知这样却走向了名为“自我”的空间。这种追求愈极致,自我的束缚便愈发牢固,最终堕入“自恋”式的忧郁症无法挣脱而消亡。而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达带来想象力的无限填充。人们从自我出发对爱进行想象,这种想象又并非源自主体,而是被资本牵引具备着特定的指向性。这种由资本制造的想象无法产生真正的爱,只会制造无数同质化的客体。
参考文献:[1]韩炳哲(德),宋娀(译).爱欲之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