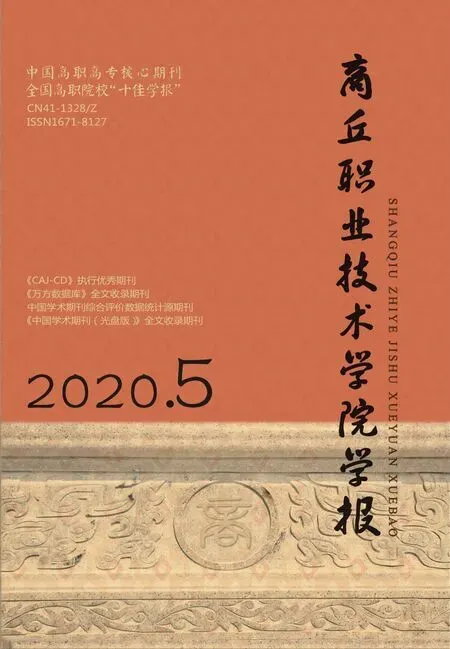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事业探析
冯静静,袁文科
(1.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2.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并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革命干部,支援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陕甘宁边区主要包括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区域,地处黄土高原中北部,这里因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自然灾害频发,医疗卫生事业长期得不到发展,疫病丛生。随着20世纪40年代边区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党和政府逐渐认识到医疗卫生防疫事业的重要性,因此,逐步采取制定防治疫病的政策法规、加强各级干部对防疫工作的领导、健全医疗卫生组织机构、加强中西医结合、开展卫生防疫宣传破除封建迷信、改善边区环境卫生等一系列卫生防疫措施,以降低边区疫病的病发率和死亡率,改善落后的医疗卫生情况。
一、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现状
陕甘宁边区地处中国西北部,土地贫瘠,人烟稀少,自然灾害多发,粮食产量不高,20世纪40年代一度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经济十分困难的局面。边区人民群众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长期贫穷落后,医疗卫生资源匮乏。同时,国民党长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边区所需物资无法及时补给,边区群众大多食不果腹、营养不良。在这种情况下,疫病一旦发生,就会迅速在边区蔓延。李维汉曾回忆说:“陕甘宁边区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们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1]如“1941年5月至7月,边区卫生处医药防疫队调查各地疫病及卫生情况,发现从1941年1月起至3、4月间,甘泉、富县、志丹传染病流行最严重,仅甘泉县一、二、三区即达876名,死者达186名,死者中小孩死亡数占2/3”[2]。“1942年1月至10月中旬,延安市各区流行法定传染病,登记121人,内死亡10人。其中包括伤寒55人,内死亡6人;赤痢33人,死亡4人;斑疹伤寒4人,无死亡;回归热18人,无死亡。定边县各乡区自1942年5月至8月发生伤寒、斑疹伤寒等传染病,该县缺医乏药,疫情尤为严重,共计死亡377人”[3]503-504。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因疫病而亡的人数居高不下。如“1944年,赤水五区的一、二、三乡发生流行病,2个月死亡75人,特别是一乡第二行政村郭家掌、小塬子等村因不注意清洁卫生、靠近山地医生少就死了43人”[4]。1944年,曲子县土桥区一个行政村561人中患疾病者占26.7%。延安县在1944年1月至5月因传染病而致死者即达2016人,占全县人口3.2%[5]。产妇和新生儿因破伤风、产褥热等疫病而亡的人数也极高。如据对志丹、安塞、子长部分地区的调查发现,188个妇女共生婴儿1028个,死去就有645个,占总出生婴儿的62.7%。甘泉杨庄窠在1944年共生婴儿30个,而同期1周岁以下死亡的婴孩则为38个,为出生数的126%[5]。同时,牲畜因传染病、粮草缺乏、棚圈不洁,生病得不到及时医治等原因而亡的数目亦相当惊人。如“1943年,全边区牛的死亡占出生61%,羊死亡占出生81.1%,驴死亡占出生23.5%”[5]。这些数据触目惊心,其产生原因亦相当复杂。
二、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原因
(一)自然灾害频发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常年遭受春旱、秋涝、霜冻、雹灾、水灾、虫灾等自然灾害侵袭,导致群众食不果腹,流离失所,疫疠也伴随饥荒大面积暴发。“1940年,陕甘宁边区11县受旱灾,受灾人口558 681人;73区受水灾,受灾人口45 307人,受灾损失162 091.5亩;27区三联保受雹灾,受灾人口35 120人,受灾损失42 200亩。脑脊髓炎、猩红热、天花、白喉等瘟疫伴随旱灾、水灾、雹灾等自然灾害大范围暴发,仅盘龙区就死亡500余人。”[6]1940年,陕甘宁边区部分县受水灾、雹灾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1940年陕甘宁边区部分县受水灾、雹灾情况统计表①
由表1可知,陕甘宁边区各地普遍遭受自然灾害侵袭,且各种灾害同时发生或一种灾害连续不断发生,灾害普遍发生在6、7、8月,受灾损失严重。1940年6月,志丹遭受水灾,造成田禾损失51 318亩,牛羊驴损失1485头,受灾群众达12 253人;遭受雹灾,造成田禾损失近30 000亩,羊损失405头,损失惨烈。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各种自然灾害高度频发和群发,造成的损失相当严重,灾害发生后往往引发大规模的瘟疫。如1947年,陕甘宁边区发生春旱、秋涝、霜冻,部分地区还遭受雹灾、水灾、虫灾,以永坪、沙家店、横山韩家岔、靖边长城为中心,形成四大灾区,灾民约250 000人,马上断粮的就有45 600人左右,延川禹居因疫疠而死亡人数占人口总数的8.6%,1947年,蟠龙、永坪一带养下的娃娃十有八九不活[7]。
(二)不良的卫生习惯
陕甘宁边区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大部分群众卫生观念淡薄。20世纪40年代,边区群众常常因喝不卫生水、吃腐败或蝇蚊虫叮咬过的食物而引发伤寒、痢疾等肠胃传染病,因常年不洗澡、不洗衣服、不晒被而引发斑疹、回归热等疫病,因剪脐带和产妇坐月子不洁而引发婴儿四六风和产妇产褥热等。“关于食品的卫生知识和清洁农民是不大理会。往往以为食物若叫苍蝇落在上面吃了,倒是与人有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等说法,随时可以听见。”“男人冬天贴身的衣裤少有没虱子的。女子的内衣大多数有虱子。”“厕所与猪圈相连,猪可以吃人的粪。”“厕所内的小便从里面流到街上,有碾行路,又有气味。苍蝇往来其中自然是方便的。厕所与井相离很近,农民不知道注意。”[8]“1944年2月间,延安市北区杨家湾到处都是牲口粪、破柴、乱草。风一吹,便秽气冲鼻,到处肮脏。村里人都是不洗脸,很少洗衣服,常是一两年不拆洗被子,虱子很多。该村大小孩都喝生水,吃冷东西。村内没有厕所,不分男女,都随地蹲下大小便。虱子多,苍蝇多,疾病也就特别多。而且,一有了病就请巫神,不请医生。”[9]因此,群众不良的卫生观念和生活习惯是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封建迷信盛行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由于文化落后、卫生教育不到位、缺医少药等因素导致大量的巫神存在。“据统计,当时延安县共有200余巫神,其中59个巫神据调查即害死200余人;华池温台区一个行政村49户300口人,每年每人迷信消耗达3斗零8升粮食,若据此推测,全边区迷信消耗则一年需粮45万石。”[5]“仅延安东关一个乡,149户400余人口中就有巫神3个。”[10]同时,边区群众封建迷信根深蒂固,生了病大多数人烧香拜佛,请巫神来治。如“1944年,延安市白家坪居民常志胜儿媳白氏患头痛腹痛,白氏的生母请来巫神杨汉珠为白氏治病,该巫神当即在病人两虎口及鼻孔下连钉上三根钢针,不仅无效,反使病情加剧。后复请边区医院一名中医诊视,始知为小产,随即打针吃药,小孩生下后半小时就死了,大人无恙。医生走后,白氏中风发昏。巫神杨汉珠见有机可乘,硬说这是‘鬼病’,不准白氏再吃西药,并把白氏的药品投入水中,大吹其‘捉鬼驱鬼’的本领,随后将白氏治死,而且在他的捉弄敲诈下,常家的小本生意也完全倒闭,陷于人亡财破的悲惨境遇。此事件发生后,经地方法院详细调查,发现其一贯利用‘巫术’,敲诈度日,仅因捉鬼治病而活活将病人打死者,共计5人”[11]。这些巫婆神汉欺骗群众,谋财害命,常常借“安砖”“吊瓦”“烧黄表”“钢针扎肉、裸体鞭打、头顶放炮”等无稽之谈的方法为群众“治病”,或者“骗鬼捉鬼”说神道鬼大敲竹竿,或者借造谣欺骗以谋生,以至于谋财害命,恶行种种,劣迹斑斑。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封建迷信的盛行,巫神的大量存在,不仅使疫病没有得到控制,而且为病人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
三、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措施
(一)制定疫病防治的政策法规
20世纪40年代,为有效地防治疫病的发生和蔓延,党和边区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疫病防治的政策和法规,为边区卫生防疫事业的开展指明了方向,打下了基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把卫生防疫工作落到实处,确立了‘面向群众服务,中西医结合,预防为主、医药为辅’三大正确的防疫方针”[12]。《速防伤寒传染,中央总生卫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了预防伤寒的十条注意事项:“1.一切饮食品均须蒸煮后食用;2.饮食用具用开水洗涤后使用;3.大小便后饮食前须洗手;4.不吃冷食、不喝生水;5.减绝厨房食堂的苍蝇;6.病人要隔离;7.护理探视病人后须洗手消毒;8.病人用具和大小便器用后须分别消毒和掩埋;9.自己有病不要接触别人;10.消毒法可用水煮洗、掩埋、焚烧、日光曝晒、石灰水浸洗等。”[13]1944年,华池白马区六乡白马庙村制定了卫生公约:1.二十天剃头一次;2.两天扫院子一次;3.半年洗被子一次,两天晒被子一次[14]。1949年7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夏令卫生防疫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凡作战区域,做好打扫战场工作,尸体必须深埋;原为胡马匪军蹂躏地区,人畜粪便、污物、垃圾应及时清除;各机关、学校、工厂定期举行清洁检查,宣传防疫卫生常识;遇急性传染病及时上报和医治;公共场所、居民密集地方等做好防疫等。”[15]1940年至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公约、办法、通知、条例等一系列卫生防疫政策法规,简单易行,便于群众接受,对防治疫病的发生和蔓延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二)加强对防疫工作的领导
20世纪40年代,边区疫病的防治离不开党、政、军、民、学各方面各级干部的领导和支持。边区各级干部克服麻痹、夸夸其谈、不着实际的作风,发扬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优良传统,接受防疫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认真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这对防治疫病的流行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1944年11月16日,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明确规定:“今后各分区各县、区、乡村的卫生医药工作,是否普遍、是否深入、是否有效,将与生产工作同样成为边区政府对各地考查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各旅、团卫生部门对地方卫生医药工作帮助的大小,亦将成为联司考查工作成绩的标准之一。”[16]该规定将地方卫生医药工作作为考查地方政绩的重要标准及考查各卫生部门工作成绩的标准之一,有效地督促了各机关各级领导切实做好疫病防治工作。1947年7月,边区在遭受胡匪侵扰和自然灾害的同时,伤寒、霍乱、麻疹、痢疾、天花、疟疾、回归热等疫病大肆暴发和蔓延,7月12日,边区政府发布了“扑灭时疫紧急指示”;华池白马区六乡指导员亲自医治患病群众;米脂河岔区区长常迎吕为患病群众提供粮食救济;龙镇区八乡乡长李树明帮助患病群众锄草;十里铺区青年主任杜兴平亲自护理患病群众等[17]。这一时期,各级干部发扬关怀和解除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积极投入到防控疫情工作中,有效地遏制了疫病的蔓延。
(三)建立医疗组织机构
建立专门的疫病防治医疗组织机构是边区防治传染病流行的重要环节。“1942年4月29日,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了边区防疫委员会领导防疫事务,由民政厅负责,刘景范为民政厅主任,该会负责辅助指导边区各级卫生机关执行防疫事务等。”[3]134-135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成立后,延安市旋即建立了各分区防疫委员会、各支会等组织,并令各县亦成立分会,同时制定管理传染病的规章制度和防疫工作制度。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对基层医疗组织机构的建设工作。“1941年1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卫生处门诊部的建设费预算准予财政厅归入本年度预算,建设地址由民政厅直接令市政府饬该地居民迁移,并酌给搬家补助。”[18]281942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陇东卫生所,将其规定为甲等卫生所编制,并于1942年8月决定成立三边分区卫生所[3]289。为了方便群众看病,减轻公家医药费的负担,延安市于1944年4月决定在各区建立公私两便的卫生合作社,由群众自己出费买药,各医务所代为诊治[19]。据《解放日报》报道:“抗大总校一大队卫生队在王家崖设立军民医药社,广为群众医病。该社设有手术室,可以开刀,并有化验设备。诊病不定时间,随到随诊,出诊随请随到,且一律不收诊费。对于贫穷或鳏寡孤独者,医药费也不收。”[20]至1949年11月,陕甘宁边区大荔、渭南、三原、咸阳、汾县、宝鸡等各分区县所建立的分区卫生院有工作人员32名,其中有28名卫生人员;建立的甲等卫生院有工作人员13名,其中有11名卫生人员;建立的乙等卫生院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有7名卫生人员。这些卫生院必须有院长、医师、护士、助产士、调剂员、事务员等编制,分区卫生院各科设的床位必须要有30张[21]。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建立的卫生医疗组织机构很好地承担起边区人民的健康和疫病防治工作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疫病的发生和蔓延。
(四)加强中西医合作,确保医务人员的生活补助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为了提高疫病防治的医疗效果和弥补边区医务人员短缺的问题,边区政府提倡加强中西医结合,倡导“中医科学化,西医经验中国化”。反复提倡医生可以带徒弟,倡导打破门户之见,培养边区实际需要的医务人才。“1940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国医研究会,团结了进步的国医,至1943年已经发展到13个分会,破除了‘家传秘方死不授人’的封建传统而经常进行开诚布公的研讨。这发展了中医药事业,为中西医互学互鉴创造了平台。”[22]1944年7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号召中西医合作互助的主张:“中医改良应从整理庞杂的医书,研究过去的经验;增加国家的治疗设备,采取西医的护士制度;研究和提炼中药,炮制各种特效的丸散膏丹以提高国医的功效等方面入手。”[23]同时,为了解决医务人员生活困难的问题,边区政府明确规定,医务人员可以享受一定的政策待遇和生活保障,确保其安心工作。如1942年7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给予卫生处边府卫生顾问张经等四人生活优待。这四人系边区得力的医务人员,但生活甚为困苦,为了确保其身体健康、安心工作,政府给予其一定的生活优待:粮食每人每日全部发给白面或大米一斤三两,菜金每日每人按半斤肉价发给[3]297-298。
(五)开展卫生防疫宣传,破除封建迷信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向群众宣传卫生防疫常识和揭露巫神打着“治病”的旗号谋财害命的恶行,旨在使群众提高卫生防疫认识,相信科学的医学治疗,破除封建迷信。这一时期,党和政府采取的宣传方式主要有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书报、画图、庙会、展览会等,且效果显著。如1945年2月,联防军卫生部和中国医科大学组成了一个50余人的宣传队,他们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排练了《军民联合反巫神》《家庭卫生》等秧歌,这些秧歌均以宣传讲卫生和破除迷信为内容[24]。1943年,三边开展卫生运动展览会,其中有《马兰婆姨》《王东花的媳妇》《梁玉才》三套关于宣传卫生知识的连环画。《马兰婆姨》主要讲述了马兰婆姨请卖狗皮膏药的看病,结果针断在肚子里,最后医院帮她把病看好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百姓,“医院看病比阴阳神官强”。《王东花的媳妇》讲述了王东花的媳妇在生产时采用旧法接生,因不讲究科学,导致难产,最后医院救了她的故事[25]。这一时期,宣传的形式多种多样,宣传的内容都是根据边区所发生的事实整合的,便于群众接受。这对打击巫神、推动反巫神运动,破除封建迷信,做好群众卫生防疫常识教育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六)改善环境卫生,树立卫生模范
防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环境卫生。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通过各种方法加大对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改善,使群众自觉做到不喝生水、不吃过气饭、食物防蝇、灭蝇灭蛆、人畜分居、修厕所、勤开窗、勤洒扫、洗浴、洗衣、晒被、采用新法接生等。“从1942年6月至9月底,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为改善环境卫生,共发出环境卫生改善补助费71 125元,受补助费机关共39个。为了倡导群众喝开水,该会令市公安局于各通衢大道设置公共饮水站8个,以供给来往行人喝水。为了解决新市场一带人口众多、公共场所厕所缺乏和人、马粪便到处可见的问题,该会令市政府及市卫生事务所择地建立了公共厕所一座。”[26]“1944年,米脂县清洁卫生运动已从城市深入农村,疾病大大减少。米脂城区街道污水沆已修成通畅之水濠,建立了很多公共厕所,城内垃圾堆已消除空了,各菜贩摊均集中指定地区营业等。在乡村家家户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拆洗衣被,煮开水喝,扑减苍蝇等。”[27]
1940年至1949年,陕甘宁边区各县、区、乡普遍开展了卫生清洁运动,并树立了大批的卫生模范村和模范试点,进一步激励了群众讲卫生、爱清洁,降低了疫病的病发率和死亡率。“1944年,后沟村村长和卫生组组长对卫生工作很积极,动员了后沟村11户人家,每家做了一个蝇拍,几天里就打了7000多个苍蝇,刘占红最多,有2000多个。他们还举行了大扫除,拆洗了被子,这村过去比较脏,现在争取卫生模范。”[28]“1944年,驻区‘胜利’部卫生队在甘泉设立‘胜利’诊疗所,此外,卫生队与当地党政和学校共同组织了一个卫生委员会,专为群众进行卫生工作,并决定首先把驻区所在的村变成卫生模范村,然后推广全区。”[29]“1945年,新宁姚家川21户,每家都有厕所、猪圈,住的窑洞开了大窗子,打了烟洞,用具都放在一定地方。他们不吃剩饭,不喝生水,碗盆洗得很干净,被子一年洗两次,衣服也常洗,常洗脚,女娃都放了脚,街道上的粪便拾得很净,因而该村的环境卫生很好,他们害病的也很少。该村被评为卫生模范村庄。”[30]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积极组织群众改善环境卫生,树立卫生模范村和卫生模范试点,营造了边区群众人居环境新面貌,改善了边区社会风气。
四、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成效
20世纪40年代,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医务人员对疫病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边区卫生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群众的卫生观念不断增强,人畜疫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逐渐降低。“1941年,仅中央医院一处共收治伤寒病人133例,而1942年,全延安伤寒病人数目较1941年仅中央医院收治的少一半还多,共发生55例。1941年,伤寒病人大多数在5月及9月、10月发病,发病地区集中在延大、鲁艺、党校等机关流行,而1942年,伤寒病人从4月起至10月散在的发病,到9月、10月渐渐绝迹。1941年,大多赤痢病人在家中治疗,而1942年,大多数病人则是入院隔离。据中央医院统计,1941年,伤寒及赤痢等传染病者,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及工作干部,而1942年,则为文化水准较低的杂务人员及战士、老百姓。”[26]这充分说明,边区在疫病防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
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在疫病防治过程中开办了各种卫生医药训练班,培养了大批的卫生人员,为边区卫生防疫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1941年1月至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部分县区抽调150名学兽医人员和卫生人员,将其送往边区卫生处所办的卫生人员训练班学习。卫生人员和学兽医人员要有高小程度文化,年龄在15—25岁,身体强健,毕业后各归原地进行卫生兽医工作”[18]22-24。“1944年,抗大卫生部医院附近成立保育训练班,训练一批保育人员,由该部正副部长亲自任教员,由各县选送学员,学员文化程度为高小毕业,并全是妇女。8月初开学,第一期学习时间为3个月,课程为普通保育、妇女卫生、助产学等。”[31]这些训练班在20世纪40年代为边区培养了大批的医务人员,解决了边区医务人员短缺的困境。同时说明陕甘宁边区政府将疫病防治工作落到实处,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总之,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在党和边区政府以及广大医务人员的努力下,边区卫生防疫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边区政府根据边区疫病防治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降低了边区人畜疫病的病发率和死亡率,提高了边区群众的卫生防疫和科学的就医意识,促进了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边区城乡的环境卫生面貌,促进了边区社会的进步。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卫生医疗防疫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政权,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及当下社会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注释:
① 表中各县的总人数是1938年和1939年各县统计的数目,于1940年7月1日完成汇总制定。此表为文献中原始表格,本文未做加工。《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纂委员会:《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8—5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