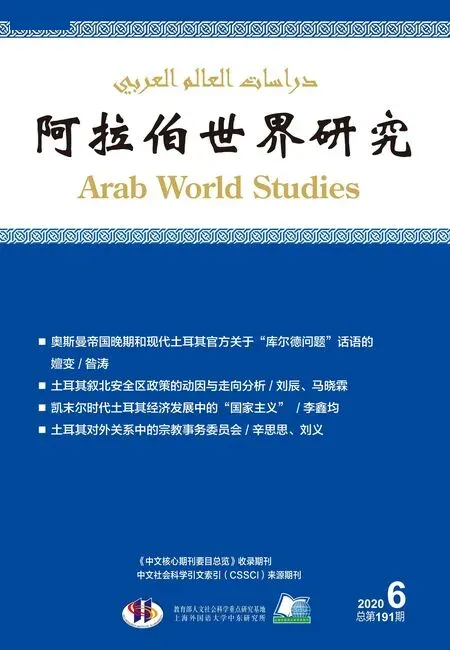黎巴嫩去极端化的理念、政策及实践*
包澄章
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各自在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相互重叠和交织的现象,以及不同国家对相关概念界定标准的差异,使得联合国机构、各国政府甚至一国内部不同部门难以对这些术语形成统一的定义。以“暴力极端主义”为例,美国联邦调查局将该术语定义为“鼓励、纵容、辩解或支持实施暴力行为,以实现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社会或经济目标”的思想;美国国际开发署则将暴力极端主义定义为“鼓吹、参与、准备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出于意识形态动机或赋予暴力合法性,以进一步实现社会、经济或政治目标”。(1)“The Development Response to Violent Extremism and Insurgency:Putting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USAID Policy,September 2011,p.2.英国政府对该术语的定义相对宽泛,指在促使他人激进化和鼓励他人积极参与暴力“圣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体活动(2)House of Commons,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Sixth Report of Session 2009-10,UK Parliament,March 16,2010,p.82,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910/cmselect/cmcomloc/65/65.pdf,登录时间:2020年8月10日。,强调这些人即使不直接参与暴力,但其言行也会对他人产生重要影响,劝导或鼓励他人“为他们的事业做出贡献”。(3)Lindsay Clutterbuck,“Deradicalization Programs and Counterterrorism:A Perspective on the Challenges and Benefits,” Middle East Institute,June 10,2015,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deradicalization-programs-and-counterterrorism-perspective-challenges-and-benefits,登录时间:2019年12月18日。澳大利亚政府将暴力极端主义定义为“支持或使用暴力以实现意识形态、宗教或政治目标的信仰及行动”(4)Cat Barker,“Australian Government Measures to Counter Violent Extremism:A Quick Guide,” Parliament of Australia,February 10,2015,https://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s/rp/rp1415/Quick_Guides/Extremism,登录时间:2020年7月18日。。加拿大政府将暴力极端主义界定为“主要出于极端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观点动机”的犯罪行为。(5)“Assessing the Risk of Violent Extremists,” Research Summary,Vol.14,No.4,September 2009,p.1.国际组织对暴力极端主义的定义也存在差异,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其定义为“挑起和煽动暴力以宣扬特定信仰、助长可能导致社会暴力的仇恨”;(6)“DAC High Level Meeting,Communiqu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February 19,2016,https://www.oecd.org/dac/DAC-HLM-Communique-2016.pdf,登录时间:2020年4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将暴力极端主义定义为“支持或使用暴力以实现意识形态、宗教或政治目的的人的信仰和行动”,包括“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7)UNESCO,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 Through Education:A Guide for Policy-makers,2017,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7764,登录时间:2020年4月13日。
世界主要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学者欧麦尔·纳沙比(Omar Nashabe)指出,将暴力极端主义等同于恐怖主义的做法存在缺陷。尽管很多暴力极端分子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从事暴力活动、存在意识形态动机且具有明确的目标和方法,但暴力极端主义也可能是由间接事实驱动或受意识形态较低程度影响的结果。(8)Omar Nashabe,“The Challenge of Defining Violent Extremism,” Lebanese 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January 2019,https://www.lcps-lebanon.org/featuredArticle.php?id=207,登录时间:2020年4月7日。
根据与意识形态联系程度的强弱,暴力极端主义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强意识形态型暴力极端主义。“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是该类型的典型代表,其大多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攻击对象和暴力实践手段,通过二元对立的宗教叙事,将其他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群体列为攻击目标。强意识形态型的暴力极端分子严格遵循极端组织头目颁布的所谓“宗教法令”(法特瓦),因而在行为模式上具有明显的集体化特征。第二,弱意识形态型暴力极端主义。黎巴嫩的民兵组织和激进政党分支成员是该类型的典型代表,他们中大多为参加过黎巴嫩内战或被1990年《大赦法》赦免的武装分子。与强意识形态型暴力极端分子不同,弱意识形态型暴力极端分子并不严格遵循政治领导人的指示,他们仅代表社区内部一种对其他宗教、社会和文化持偏狭态度的极端主义趋向。第三,无意识形态型暴力极端主义。由个体或环境激发的零星暴力肇事者是该类型的典型代表。无意识形态型暴力极端分子可能从属于任何宗教团体,但容易煽动社会恐慌情绪。2011年叙利亚战争导致大量难民涌入黎巴嫩境内后,由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引发的暴力事件明显增多,黎巴嫩军队在黎叙边境与极端组织的交火时有爆发,黎国针对叙利亚籍难民和工人的暴力极端主义事件较此前更加频繁。青年男性暴力极端思想的形成也与环境有关,非政府组织“国际警戒”(International Alert)针对长期处于动荡状态的的黎波里地区青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地男青年使用暴力、携带武器或加入武装团体,有时是为了“炫耀”、“展现阳刚之气”或“避免被别人当成懦夫”,有的青年认为使用暴力是“保护自己、朋友和家人”和“站稳脚跟”必要的生存技能。(9)Muzna Al Masri and Ilina Slavova,More Resilient,Still Vulnerable:Taking Stock of Prevention of Violent Extremism Programming with Youth in Tripoli,Lebanon,International Alert,October 2018,pp.33,36,https://www.international-alert.org/sites/default/files/Lebanon_PVEProgrammingTripoli_EN_2018.pdf,登录时间:2020年1月2日。
当极端主义相关概念界限的模糊性、发展阶段的重叠性和界定标准的差异性进一步延伸至政策领域时,各国政府围绕“去激进化”“去极端化”“反激进主义”“反极端主义”“反恐怖主义”制定政策的目标、对象和手段会产生分歧。
中国政府将极端主义定义为“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的主张和行为”。(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2018年10月9日,http://www.xjpcsc.gov.cn/article/216/lfgz.html,登录时间:2020年2月19日。极端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行为表现及其对偏激思想和暴力的渲染程度不一,在不同因素的驱动下沿着前极端化、准极端化和极端化的路径发展和演变。极端化是极端主义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去极端化是遏制、阻止和防止极端化进一步发展、为极端化的个人提供一种非暴力替代选择的过程。去极端化伴随对个体极端化的各种驱动因素的治理,对极端化在不同阶段驱动因素的治理和改造,决定了极端主义是否会在其他因素的刺激和影响下发生逆变、消失或继续进入下一阶段发展。
黎巴嫩在打击和治理极端主义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极端主义的特征,建立了从国家到个人的多层次预防体系,在去极端化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黎巴嫩模式”。
一、极端主义与黎巴嫩国内和地区政治的互动
黎巴嫩的安全形势长期受到国内冲突环境、暴力行为体跨境活动、域内外力量持续干预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复杂性与矛盾性。其中的复杂性表现为国内政治、社会和安全环境深受叛乱政治、教派政治和难民政治的影响,这些问题自身的发展及其交织可能诱发新的安全问题,而国家对特定领域问题的治理也会引发其他领域问题的反弹;矛盾性则表现为黎巴嫩在同域内外力量的交往过程中,既要防止外部力量过度干预本国事务造成的国家独立性缺失问题,又因国家治理能力不足而不得不依赖外部力量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尤其是机制化的安全保障,而国内同时存在的亲西方和反西方力量,又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影响黎巴嫩与外部大国的安全合作。
利用叛乱运动、教派矛盾和难民问题来寻求发展空间、构建极端意识形态和壮大武装力量,是暴力极端主义同黎巴嫩国内和地区政治互动的典型表现。
(一) 叛乱运动与暴力极端主义的政治预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威权主义统治处于强势支配地位的影响,非暴力抵抗成为中东社会运动的主要策略选择,但“在阿拉伯国家中一直存在对暴力抵抗方式的推崇”(11)曾向红等:《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中东变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8-59页。。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看,叛乱是由具有社会亢奋和动机的行为体为应对存在于现有政治实践中的不满和机构缺失等问题,协调针对一个或多个执政机构的、具有争议的暴力行动而组成的草根运动,目的是将从本质上改变或推翻主权作为一种必需的规范或政策变革的手段。(12)Shane Drennan,“The Socially Constructed Insurgency Using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Insurgencies,” in Warscott Nicholas Romaniuk and Stewart Trista,eds.,Insurgency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Modern War,Boca Raton:CRC Press,2016,p.18.在实现社会运动目标的过程中,非暴力抵抗相较于暴力抵抗的优势主要表现为前者可以最大限度激起民众对公共事业的同情与支持,更利于解决长期积累的社会不公、驱除个体恐惧感以构筑强大的心理力量,易在当局与抗议者之间建立沟通桥梁、争取安全力量在抗议运动中保持中立。(13)曾向红等:《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中东变局研究》,第59页。但是,以暴力抵抗为主要手段的叛乱运动同样可以借助激发对抗社会不公的集体能动性来塑造政治想象,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与当地民众尤其是具有暴力倾向群体融合的机会。
中东地区有能力实现跨境活动的主要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其最初形态大多是在地区冲突国家内部兴起的叛乱运动或组织。在冲突环境中,叛乱运动将意识形态和暴力观念作为激发民众反抗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动员工具,以此塑造一套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政治想象。政治想象是在现有物质背景下对替代性政治生活的思考,包括政治身份、政治秩序、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替代性政治制度安排、替代性意识形态等内容。当政治想象成为一种大众信念,并将之付诸行动,便有可能带来现有政治生活的改变。(14)同上,第123页。强化政治想象的合理性、提高抗争手段的合法性,有利于暴力行为体在冲突环境中提升目标受众对抗争结果的政治预期。在此基础上,暴力行为体才能利用冲突环境整合资源、招募成员,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
叛乱运动通过塑造政治预期来操纵民意,进而提升其支持者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抗争的意愿。“非国家战斗人员对政治、社会、道德和个人动机的需要,远远超出由国家训练和资助的专业士兵坚持不懈战斗所需的能力”,因此,“对正义者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操纵当地民众的社会政治观点,是鼓励从被动或主动支持非暴力手段转向暴力叛乱的关键”。(15)Shane Drennan,“The Socially Constructed Insurgency Using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Insurgencies,” pp.22-23.叛乱组织针对所在国政权和安全部队发动暴力行为时所使用的各种借口,如治理不善、失业率高企、腐败盛行、社会不公造成的挫败感等,均可成为极端组织用以开展广泛政治动员、煽动暴力反抗社会公正和变革现行制度的话语工具。而现行政权对叛乱运动的镇压,反过来为极端组织塑造自身受压迫者的弱势形象提供便利,进而为其组建形成呼应与共情的暴力抗争网络奠定基础。
在黎巴嫩内战和冲突环境中兴起的极端组织在塑造以暴力对抗“叛教”政权、维护穆斯林“被占领土”这一典型话语的同时,也需要借助冲突画面来调动整个地区暴力反抗的能动性。“伊斯兰国”组织在宣传视频中以蒙太奇手法展现冲突画面,目的不仅是通过美化暴力塑造一种只有以暴力手段才能改变现行秩序的政治想象,提升有志于暴力对抗“叛教”政权的“圣战”分子的预期,更是为了将暴力反抗塑造成一种“为主道而战”的“宗教事业”,以此重塑当地民众对冲突环境的认知。而“伊斯兰国”组织宣传中女性“圣战”分子的出现,则标志着性别被引入叛乱活动的政治叙事中,女性在极端组织内部的角色变化(16)Alexis Henshaw et al.,“Understanding Women at War:A Mixed-Methods Exploration of Leadership in Non-State Armed Groups,” Small Wars &Insurgencies,Vol.30,No.6-7,2019,pp.1089-1116.正是极端组织在构筑政治想象时运用性别叙事提升政治预期的表现。
伊斯兰极端组织在构建极端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都注重对世界进行“伊斯兰区”(daral-Islam)和“战争区”(daral-harb)的二元划分,这构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理论家号召穆斯林以暴力手段排斥异己势力、保卫伊斯兰世界领土的合法性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定叛”(takfir)和“圣战”(jihad)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界定斗争对象、合法化暴力行径的重要法理依据。

自1982年黎以战争以来,黎巴嫩国内伊斯兰极端势力不断策动针对黎境内公共场所和外国机构目标的暴恐袭击,反对外部势力的入侵,在此过程中不断塑造自身暴力抵抗的合法性。“定叛”为伊斯兰极端势力针对非穆斯林或“非伊斯兰”实体使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以“圣战”名义对伊斯兰国家发动的武装叛乱不仅被视为合法行为,而且被穆斯林个人视为应当履行的“宗教义务”。(21)Bernard Haykel,“On the Nature of Salafi Thought and Action,” in Roel Meijer,ed.,Global Salafism: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London:Hurst &Company,2009,p.50.而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借助“圣战”观念赋予暴力合法性、以“捍卫伊斯兰教”为名挑战世俗政权的过程中使用的合法性依据包括:第一,以暴力手段应对侵略行为是完全合法的;第二,针对不实行伊斯兰教法或向“敌方”提供支持的穆斯林统治者发动的攻击是合法的;第三,为报复“异教徒”支持对穆斯林发动战争而实施的报复性杀戮行为是合法的;第四,“殉教”行为是对异教徒侵略者进行自卫的合法武器。在冲突环境中,叛乱运动正是通过不断强调借助暴力抗争手段推翻现行秩序的合法性,以“受害者”视角来塑造弱势群体的政治叙事,以此提升具有反抗意识的民众建立替代性秩序和制度的政治预期,进而调动民众暴力反抗的能动性。
(二) 教派主义对极端意识形态的改造
教派主义是黎巴嫩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的另一重要根源。首先,教派分权体制催生的教派主义,成为助长黎巴嫩国内教派仇恨的主要因素。1943年《民族宪章》确立了黎巴嫩的教派分权体制,总统、总理和议长分别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伊斯兰教逊尼派人士和伊斯兰教什叶派人士担任。黎巴嫩国内有18个受到官方承认的宗教团体,包括4个伊斯兰教教派、12个基督教教派以及德鲁兹教派和犹太教。根据美国中情局2018年数据统计,黎巴嫩人口中30.6%为逊尼派,30.5%为什叶派,33.7%为基督教徒,5.2%为德鲁兹派。(22)“Lebanon,” The World Factbook,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e.html,登录时间:2020年10月8日。高度教派化的政治体制和人口分布不仅导致黎巴嫩国内政治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也为宗教极端势力渲染教派仇恨进而煽动教派冲突提供了空间。
1975年黎巴嫩爆发内战,长达15年的内战并没有改变该国教派色彩浓厚的政治体制。教派分权制仍是内战后黎巴嫩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和政治制度最显著的特征。(23)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71页。在黎巴嫩内战期间壮大的国内武装力量的激进派别,为此后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实体化奠定了基础。黎巴嫩国内各教派大多建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武装力量,内战的爆发加速了国内各派系的武装化进程。内战期间,什叶派、逊尼派和基督教民兵武装相互争夺对黎巴嫩的控制权。内战的冲突环境为黎巴嫩国内不同宗教政治力量的激进化、暴力化提供了土壤,个别激进武装派别的分化重组,则为此后极端组织的实体化创造了条件。真主党在1982年黎以战争期间成立,在资金、人员培训、武器装备方面常年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支持,奉行反以色列、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抵抗战术,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据以色列军方估计,至2017年6月,真主党已在黎巴嫩南部240个村庄部署了军事力量。(24)Tom O’Connor,“Israel’s Next War on Lebanon Will Kill Civilians,Air Force Commander Says,” Newsweek,June 22,2017,https://www.newsweek.com/israel-next-war-lebanon-kill-civilians-air-force-628321,登录时间:2020年9月10日。真主党在黎巴嫩各地开办学校、设立营地和建立宗教项目网络,注重通过在黎巴嫩青少年中招募新兵来充实其武装分支的兵力。真主党从黎巴嫩各地发掘和培养新人,资助他们接受灌输真主党意识形态的宗教教育和军事训练。例如,真主党旗下的青年组织“马赫迪童子军”(Mahdi Scouts)的成员自幼便接受反以、反西方意识形态的灌输。(25)Lars Erslev Andersen,The Neglected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Lebanon and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9,p.33.
从地区政治的角度看,真主党对叙利亚战争和也门战争的干预,激化了黎巴嫩国内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矛盾。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来自“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逊尼派极端组织的数百名武装分子从叙利亚潜入黎巴嫩境内,在当地频繁发动针对什叶派真主党目标的暴力袭击。与此同时,黎境内逊尼派武装分子与阿拉维派的冲突也时有发生。2013年,逊尼派民兵组织控制了的黎波里部分路段,在街上公开杀戮阿拉维派平民。2017年,真主党通过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将叙利亚叛军赶出了黎巴嫩边境地区。从民意调查数据来看,黎巴嫩国内民众对真主党介入叙利亚战事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一方面,真主党干预叙利亚所导致的国内教派冲突加剧,使得逊尼派对真主党总体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什叶派和基督徒对真主党打击“伊斯兰国”的行为总体持肯定态度。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黎巴嫩国内什叶派、逊尼派、基督徒三大群体对真主党的支持率分别达86%、9%和31%。(26)“Concerns About Islamic Extremism on the Rise in Middle East,” Pew Research Center,July 1,2014,http://www.pewglobal.org/2014/07/01/concerns-about-islamic-extremism-on-the-rise-in-middle-east/,登录时间:2020年8月1日。黎巴嫩贝鲁特研究和信息中心于同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二的黎巴嫩基督徒认为真主党使国家免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袭击;66%的基督徒支持真主党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行动,而2013年该数字仅为39%。(27)“Lebanon:Extremism &Counter-Extremism,” Counter Extremism Project,https://www.counterextremism.com/countries/lebanon,登录时间:2019年8月1日。
在中东地区,教派政治往往使得地区小国沦为地区大国之间地缘政治博弈的牺牲品。长期以来,黎巴嫩是沙特与伊朗开展代理人竞争的“主战场”之一。2017年11月4日,时任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在访问沙特期间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引发地区紧张局势。2016年底哈里里再次出任黎巴嫩总理后对真主党所持的妥协立场曾引发沙特方面的不满。2017年11月哈里里在访问沙特前夕会见了来黎访问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外交事务顾问韦拉亚提,这进一步激怒了沙特当局。哈里里辞职事件不仅反映出沙特对近年来伊朗在地区势力范围持续扩张的战略焦虑,而且折射出地区小国黎巴嫩国内政治受制于地区大国的整体政治环境,逐渐沦为地区大国政治角力牺牲品的悲观现实。经过叙利亚内战“洗礼”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大幅提升,进一步加深了沙特对真主党向也门境内渗透的担忧,沙特遂将其对伊朗势力范围扩张的焦虑转移到对黎巴嫩政局的干涉上,希望通过影响并改变哈里里政府对真主党的立场来遏制伊朗地区影响力的上升。
(三) 难民问题与极端主义的渗透
难民问题本身不是引发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的原因,但难民问题的持续发酵及其连带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和安全问题,则可能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向难民群体渗透提供新的渠道。难民问题与社会安全问题的交织,使得难民营易成为政治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泛滥的温床。
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2019年1月数据统计,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人数约47.5万,占该国人口的近10%。其中,45%的巴勒斯坦难民生活在黎巴嫩境内的12个难民营中。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叙利亚原先收容的巴勒斯坦难民(28)自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至2016年12月,黎巴嫩共接收了150万从叙利亚涌入黎境内的难民,其中巴勒斯坦难民数量达5.3万。参见Lars Erslev Andersen,“The Neglected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Lebanon and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 DIIS Report,No.12,2016,p.5,http://pure.diis.dk/ws/files/739488/DIIS_Report_2016_12_Web.pdf,登录时间:2019年9月18日。和战争造成的叙难民大量涌入黎巴嫩境内,导致黎巴嫩国内难民营人满为患,加之难民营内部管理混乱、生存条件恶劣,械斗、抢劫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在有关难民问题与极端主义关系的讨论中,难民青年的失业问题常被认为是极端组织向难民群体进行渗透的经济动因。失业的难民青年因“可能被经济激励、成就感或社会认同所吸引”而更容易成为极端组织的招募目标。但也有研究表明,难民青年的失业与极端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相关研究认为失业问题只是导致极端主义众多因素中的一种。(29)Drew Mikhael and Julie Norman,“Refugee Youth,Unemployment and Extremism:Countering the Myth,” Forced Migration Review,No.57,February 2018,p.57,https://www.fmreview.org/sites/fmr/files/FMRdownloads/en/syria2018/mikhael-norman.pdf,登录时间:2020年4月20日。黎巴嫩虽然被国际社会列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因就业劳动力不足,该国多项经济指标落后于其他同类国家。(30)“ILO Response to Syrian Refugee Crisis in Lebanon,”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http://www.ilo.org/beirut/areasofwork/employment-policy/syrian-refugee-crisis/lebanon/lang--en/index.htm,登录时间:2018年4月20日。2018年,黎巴嫩失业率高达46%。(31)“Jobless Rate at 46 Pct,President Warns,” Daily Star,March 30,2018,http://www.dailystar.com.lb/Business/Local/2018/Mar-30/443613-jobless-rate-at-46-pct-president-warns.ashx,登录时间:2020年5月2日。黎巴嫩境内叙利亚难民群体中从事经济活动的难民数量只占一半,能够就业的难民人口只占三分之一,且其中大多数从事的是非正规和低技能职业。
当经济、社会、安全等因素相互作用时,尤其是国内政策因素造成的权利被剥夺、社会边缘化、政治排挤等问题,容易使难民群体产生挫败感和孤独感。在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无法享有与其他在黎境内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同等的权利,黎巴嫩政府禁止巴勒斯坦难民拥有黎巴嫩国籍、从事39种职业和拥有不动产。(32)“Where We Work,”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January 2019,https://www.unrwa.org/where-we-work/lebanon,登录时间:2020年2月8日。与此同时,黎巴嫩法律限制黎巴嫩军队在国内12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开展军事行动,这导致难民营常常沦为国内外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的“避风港”。极端组织利用巴勒斯坦难民的挫败感和绝望情绪向其灌输暴力极端主义和从中招募成员。
2007年,驻扎在黎巴嫩北部巴里德河(Nahr al-Bared)难民营的安全部队与“伊斯兰征服”组织(Fatahal-Islam)(33)“伊斯兰征服”组织是由巴勒斯坦难民沙基尔·阿卜西(Shaker al-Abssi)于2006年11月在巴里德河难民营成立的极端组织。发生交火,造成400多人死亡、3万人流离失所。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叙黎边境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伊斯兰国”和“支持阵线”等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以难民为掩护,向黎巴嫩境内多处难民营渗透,与当地的极端组织相互勾连,从难民营中招募成员或培养支持者。被招募的成员有的赴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从事叛乱运动或暴恐活动,有的则留在黎巴嫩境内攻击真主党等什叶派目标。随着叙利亚乱局的溢出,“伊斯兰征服”等黎巴嫩境内极端组织的成员中除巴勒斯坦难民外,也出现了大量从叙利亚潜入黎巴嫩境内进而渗透至的黎波里和巴里德河难民营的“圣战”分子。在黎政府下令拆除巴里德河难民营后,他们辗转至赛达地区的艾因·希勒瓦(Ain al-Hilweh)难民营,占据此前黎巴嫩安全部队的庇护所,(34)Lars Erslev Andersen,The Neglected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Lebanon and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pp.31-32.加剧了赛达当地安全形势的恶化。
从动机来看,近几年“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将触角伸向难民群体,主要是因为该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区域大幅缩水后,战略目标已从之前的领土扩张转变为蓄积实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区乱局来维系组织的有生力量和建立跨国网络。因此,“伊斯兰国”组织不断向外围进行战略转移,在战术上转向非对称作战,通过认领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恐怖袭击来维系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宗教极端意识形态和暴力观念的输出。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数据统计,2018年全球圣战萨拉菲组织数量达66个,与2016年的数字持平,全球范围内圣战萨拉菲武装分子数量高达23万名。(35)Seth G.Jones,“America’s Counterterrorism Gamble,” CSIS Briefs,July 26,2018,https://www.csis.org/analysis/americas-counterterrorism-gamble,登录时间:2019年12月25日。极端组织的战略调整使得叙利亚境内的极端分子选择藏匿于当地极端组织的同情者或平民社区之中,伺机发动报复性袭击或叛乱活动,如位于叙利亚和约旦边境地区的鲁克班难民营中就藏匿着相当数量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及其家人,这些人的活动更加隐蔽且难以监测。(36)Josie Ensor,“ISIL Still Has up to 30,000 Members in Syria and Iraq,UN Report Finds”.
二、黎巴嫩去极端化的理念与政策
在黎巴嫩所在的西亚地区,极端主义的成因复杂多元,地区国家去极端化的成效不仅取决于政府对相关领域治理的战略及政策规划,也取决于治理主体的能力、手段、策略以及配套制度的建立。而国内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博弈和外部力量对地区政治的干预,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相关国家的去极端化实践。在西亚地区,伊拉克和叙利亚动荡局势引发的极端主义抬头,以及国内冲突环境的长期化趋势,使得当前两国去极端化工作整体上仍以稳定国内安全局势和降低冲突烈度为重。
黎巴嫩国内政治、安全环境不仅受到教派体制的影响,也深受周边国家安全形势的影响。内战后黎巴嫩政府一直致力于实现各派之间的和解,预防极端主义在内部反弹和从外部输入。自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黎巴嫩国内政局处于低烈度动荡,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且集中在的黎波里、赛达等城市。黎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实现各派政治和解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增长、构建多元融合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为黎巴嫩在去极端化过程中的综合施策和开展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黎巴嫩在去极端化的战略规划、政策理念等方面具有显著特色,注重吸收国外经验和开展国际合作。
2017年,黎巴嫩政府成立国家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协调官办公室,负责领导黎巴嫩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国家战略的制定。2018年3月,黎巴嫩议会通过《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国家战略》(NationalStrategyforPreventingViolentExtremism,以下简称《国家战略》),标志着黎政府去极端化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国家战略》体现了黎巴嫩政府在去极端化领域进行源头治理的思路。该战略确定了黎巴嫩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总体框架、战略目标、实施主体和实践路径。在综合考虑文化、经济等诱发暴力极端主义的结构性因素和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去极端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国家战略》确立了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并从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制定相关的监测和评估体系。
从世界各国的去极端化经验来看,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简称CVE)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简称PVE)本质上是应对和治理处于不同阶段的极端主义及其形成的结构性因素。从目标来看,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针对的是被认定具有激进思想倾向或思想面临极端化风险的特定群体,目的是阻止该群体从事危害社会的暴力极端行为;预防暴力极端主义针对的对象则是易受极端思想感染的个人或群体,其思想尚处于前极端化阶段,并不具有激进或极端倾向,预防的目的是阻断该群体接触极端思想的渠道,消除使其思想激进化的各种社会因素,或改善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使个人或群体重新融入主流社会。
在概念定义上,《国家战略》从三个方面界定了暴力极端主义的范畴,即可能导致结构性暴力的个人和集体仇恨蔓延、拒绝多样性、不接受他人以及将暴力作为表达和施加影响的手段,威胁确保社会稳定的社会价值的行为。(37)Presidency of Council of Ministers,National Strategy for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2018,p.14,http://www.pvelebanon.org/Resources/PVE_English.pdf,登录时间:2019年12月16日。该战略强调,预防工作需要制定可转变为增强社区免受暴力极端主义侵害能力的社会文化政策,在全社会形成可持续的“预防文化”,具体方式包括:通过监测和预测个体和社区层面可能导致暴力极端主义的社会、文化、发展和行为转变,提高对暴力极端主义风险的认知;制定社会、经济、环境、文化、安全等领域的风险清单,通过建立专门的社会观察站来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38)Ibid.
在总体框架上,《国家战略》确立了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九大支柱,即对话和预防冲突;促进善治;司法、人权和法治;城乡发展和地方社区参与;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教育、培训和技能开发;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战略传播、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青年赋权。(39)Presidency of Council of Ministers,National Strategy for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2018,pp.18-77.这九大支柱涉及经济、社会、法律、教育、媒体等领域,覆盖城市、乡村、社区、家庭和个体等层面,将青年、妇女等关键群体纳入预防工作的对象。
在战略目标上,《国家战略》将“重获社会信任”“促进公民身份”“实现社会公正”“监测社会转型”确立为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四大目标。首先,使预防对象重新摈弃仇恨和暴力观念,接纳他人和融入社会,是该战略的首要目标。其次,促进和强化黎巴嫩人的身份认同、公民身份和国家归属感,是预防暴力极端主义战略的关键目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文化将为确保该战略及后续措施的实施奠定基础。再次,社会公正是各类公共政策的起点,涵盖个体、社会和区域等不同层次。最后,暴力极端主义的复杂性和跨领域特征,要求政府制定预防性和积极主动的对策,借助高校、科研机构、官员、社区和国际机构来监测、研究和跟进社会转型中的各种因素,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出现。(40)Ibid.,pp.16-17.
黎巴嫩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国际合作、部委协调、社会动员等方式,逐渐形成了去极端化的“黎巴嫩模式”,该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践行预防为主、控制为辅的去极端化理念。丹麦、荷兰、比利时、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年来通过实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计划,防止国内激进主义演变成暴力极端主义。西方国家呼吁将“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计划纳入国际社会对黎巴嫩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中(41)Lars Erslev Andersen,The Neglected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Lebanon and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p.33.,通过发现激进化的早期迹象来预防个体的激进化和暴力化转向,提升社会对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抵御能力。长期以来,巴勒斯坦难民被视为潜在恐怖分子的论调,是黎巴嫩政府制定和实施反暴力极端主义政策的主要依据。但这种忽略难民本身社会、经济现状的政策制定逻辑,对于解决黎国内难民问题和防止极端主义抬头,均难以产生实质性效果。在进行政策反思和汲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黎巴嫩政府近年来不断探索去极端化的可行路径。2018年《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国家战略》的出台,标志着黎巴嫩预防为主、控制为辅的去极端化理念的确立。“黎巴嫩模式”注重将极端主义遏制在萌芽的前极端化阶段,针对激进思想或极端思想的易感群体,借助脱离接触、职业培训、心理辅导等手段推进“康复计划”,使该群体重燃对生活的信心,为其重新融入社会提供更多机会。
第二,重视吸收国际经验和开展国际合作。丹麦是欧洲地区较早启动去极端化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并取得实质性成效的国家之一,尤其是“伊斯兰国”兴起后,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因预防暴力极端主义计划的实施成功阻止本国公民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冲突国家(42)得益于奥胡斯城市预防暴力极端主义计划的实施,从该市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丹麦公民从2012年至2013年峰值时的30人骤降至2014年的1人,这一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模式也被称为“奥胡斯模式”(Aarhus model)。参见Manni Crone and Khadije Nasser,“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 in Lebanon:Experience from a Danish-Lebanese Partnership,” EuroMeSCo,No.38,European Institute of the Mediterranean,May 2018,p.11,https://www.iemed.org/publicacions-en/historic-de-publicacions/papersiemed-euromesco/38.-preventing-violent-ex-tre ̄mi ̄sm-in-lebanon-experience-from-a-danish-lebanese-partnership,登录时间:2020年1月2日。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黎巴嫩内政部通过与丹麦政府“和平与稳定”基金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赛达、的黎波里、马吉达勒·安吉尔(Majdal Anjar)三座城市试点“丹麦模式”。该模式强调预防与干预相结合的理念,采取金字塔结构的行动原则。位于金字塔底层的是“一般性预防”,其并不针对特定个体或群体,而是覆盖更加广泛的受众和环境,注重通过提升年轻人的社交能力、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增强其社会适应力。位于金字塔中间层的是“预期干预”,干预主体是市政当局和地方警察,针对一个或多个被当局评估为具有激进化“风险”但尚未实施犯罪行为或未成为极端分子的个体,通过向其提供教育、住房、工作来提升社会边缘群体的福祉,使该群体重新融入社会。“预期干预”有利于一线工作人员及早发现个体的极端化风险,但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干预对象接受干预,因此有时采用“迂回战术”,通过对干预对象的父母提供指导来解决青少年或青年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位于金字塔顶层的是“直接干预”,其针对暴力极端组织的活跃成员,或被认定有能力实施暴力等犯罪行为或前往国外冲突地区的个体。干预主体是情报部门和执法机构,这些机构通过没收干预对象护照或与其开展“预防性对话”来阻止潜在的罪犯行为的实施。在实施预防行为的过程中,相关机构组建合作网络,以实现相互间的信息共享。(43)参见Manni Crone and Khadije Nasser,“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 in Lebanon:Experience from a Danish-Lebanese Partnership,” EuroMeSCo,pp.14-16.黎巴嫩政府还重视同联合国相关机构开展国际合作。2019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贝鲁特美国大学联合举办了为期三天的“青年与预防暴力极端主义”主题活动,活动旨在通过授课、研讨等方式加强青年群体在预防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独特作用。(44)“MOST School on ‘Youth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t Extremism’ in Lebanon,” UNESCO,June 20,2019,https://en.unesco.org/events/most-school-youth-and-prevention-violent-extremism-lebanon,登录时间:2020年8月7日。
第三,建立跨部门协调的去极端化工作机制。黎巴嫩内阁要求各部委在实施《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依据自身职权范围参与特定支柱领域的行动,制定相应政策和相互协调行动。《国家战略》强调,各部委在推进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国家战略实施方面需要进行持续协调,并在战略制定、实施和评估方面同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45)Presidency of Council of Ministers,National Strategy for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p.19.为此,黎巴嫩政府专门设立了“国家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协调小组”(National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 Coordination Unit,以下简称“协调小组”)。“协调小组”设在黎巴嫩总理府,由“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国家协调官”(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直接领导,负责协调黎巴嫩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制定、行动规划和具体工作的实施。“协调小组”的主要任务包括:从国家层面制定《国家战略》九大支柱的具体行动计划,组建国家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网络,制定《国家战略》监测和评估框架,开发预警系统,推动社会团体和组织广泛参与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编制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培训材料,等等。(46)参见“National PVE Coordination Unit,” National Strategy for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http://pvelebanon.org/NationalCoordination.aspx,登录时间:2020年7月1日。在实施《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建立跨部门协调的工作机制,有利于在充分发挥各部委职能的同时,广泛吸收政界、学界、媒体界、科技界、法律界等社会各领域专业人士的参与,实现去极端化工作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第四,建立从国家到个人的多层次预防体系。黎巴嫩政府注重在国家、城市、社区、家庭、个人等不同层面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在城市层面,黎巴嫩政府依托联合国“强大城市网络”(Strong Cities Network)计划,与丹麦等国开展去极端化领域的合作,在受极端主义影响严重的城市建立“地方预防网络”(Local Prevention Networks),加强社区预防能力建设,打造本土化的预防暴力极端主义模式,提升黎巴嫩主要城市预防各种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的社会凝聚力和社区适应力。(47)“Capacity Building for Stronger Cities:Lebanon and Jordan,” The Strong Cities Network,January 2019,https://strongcitiesnetwork.org/en/wp-content/uploads/sites/5/2019/01/A4-SCN-ENG-1.pdf,登录时间:2020年3月3日。“地方预防网络”覆盖国际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协调官、“强大城市网络”地方团队、市政联络点和市政厅的预防体系,吸收教育从业人员、地方发展机构、宗教机构和宗教领袖、公民社会领袖、市政官员、青年代表和活动家、社会工作者和青年团队等七大群体参与预防工作的实施。(48)“Strong Cities Network:Policy and Practice Model,” Strong Cities Network,February 2019,https://strongcitiesnetwork.org/en/wp-content/uploads/sites/5/2019/02/ENG-SCN-Policy-and-Practice-Model.pdf,登录时间:2020年3月3日。在乡村层面,《国家战略》重视对农村地区的年轻人进行农业方法和生活技能的培训,为当地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孵化农村企业文化,实现城乡间的平衡发展。(49)Presidency of Council of Ministers,National Strategy for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pp.39,73.
在家庭层面,黎巴嫩政府充分认识到家庭在去极端工作中的特殊性。家庭既可以在预防青年激进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也有可能在促使青年激进化方面扮演消极角色。代际关系破裂、家庭内部冲突是导致青年从脆弱转向激进化、极端化的特殊根源。(50)Dallin Van Leuven et al.,“Youth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Lebanon:Drivers of Marginaliz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in Tripoli,”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June 2019,p.6,https://www.sfcg.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Search-for-Common-Ground-Youth-and-Con ̄ten ̄tious-Politics-in-Lebanon.pdf,登录时间:2020年7月10日。一方面,在家庭内部建立良性的代际沟通渠道,有助于解决发生在青年身上的各种冲突,防止青年滑向暴力极端主义的深渊。另一方面,家长持有的激进观点或宗派主义观点,会深刻影响下一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促使子女与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接触,有的家庭甚至将因参加暴力活动而丧生的子女称为“烈士”。(51)Presidency of Council of Ministers,National Strategy for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p.42.因此,《国家战略》提出通过组织家庭见面会,实现家庭内部和解,提高对父母角色和加强家庭成员联系重要性的认知。(52)Ibid.,p.22.
在个人层面,《国家战略》注重协同黎巴嫩各部委机构和发挥各自职能,提高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例如,人权事务部、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联合行动,提高社会群体,尤其是边缘化和弱势群体、贫困社区的就业机会;(53)Ibid.,p.35.文化部则致力于制定针对边缘化和弱势群体及地区的文化活动和计划,实现文化发展的公平性;(54)Ibid.,p.39.社会事务部与司法部开展合作,在囚犯获释前或回家后,为他们举办重返社会和康复培训班。(55)Ibid.,p.22.
三、“地方预防网络”与黎巴嫩城市去极端化的实践
的黎波里是黎巴嫩第二大城市,也是黎国内受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至2017年1月,的黎波里常住人口约50万,当地接收了7万名叙利亚难民和3万名在册巴勒斯坦难民,这些难民分布在1个难民营和5个集会点。(56)Khaled Ismail,Claire Wilson and Nathan Cohen-Fournier,Syrian Refugees in Tripoli,Lebanon,Somerville,Feinstein International Center,Tufts University,March 2017,pp.3-4,http://fic.tufts.edu/assets/Tripoli-FINAL-5-July.pdf,登录时间:2020年1月9日。的黎波里巴卜·塔巴内(Bab al-Tabbaneh)和杰巴勒·穆赫辛(Jabal Mohsen)两大社区间的敌对态度可追溯至黎巴嫩内战期间。巴卜·塔巴内社区居民以阿拉维派为主,杰巴勒·穆赫辛社区居民以逊尼派为主。2008年至2014年间,两大社区之间共爆发了20次冲突,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严重的经济损失。在难民问题和教派政治的交互影响下,的黎波里长期被视为一座充满暴力和不安全感的城市。2014年黎巴嫩政府在的黎波里推行一项安全计划后,黎巴嫩军队进驻当地以维持稳定。(57)Muzna Al Masri and Ilina Slavova,“More Resilient,Still Vulnerable:Taking Stock of Prevention of Violent Extremism Programming with Youth in Tripoli,Lebanon,” International Alert,October 2018,p.14,https://www.international-alert.org/sites/default/files/Lebanon_PVEPro ̄gr ̄am ̄ming ̄Tripoli_EN_2018.pdf,登录时间:2020年1月2日。
针对当地暴力和极端主义泛滥的现状,自2016年开始,黎巴嫩赛达、的黎波里、马吉达勒·安吉尔三个城市的市政当局与联合国“强大城市网络”计划开展合作,在当地建立“地方预防网络”。该预防网络的职责主要包括:确定风险行为的成因,激励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士开展预防工作,提高对暴力团体宣传和招募策略的认识,制定地区年度行动计划,分享有助于维护社区安全的活动信息和知识。黎巴嫩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地方预防网络”建设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58)“Strong Cities Network:Policy and Practice Model”.
第一,与国家主管部门和部委开展协调。尽管市政当局是“地方预防网络”的主要参与者,但市政当局仍需通过与国家主管部门协调相关政策的实施。为此,赛达、的黎波里、马吉达勒·安吉尔的市政当局事先就相关工作与黎巴嫩“国家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小组”进行协调,确保政策措施的落实。
第二,确定预防网络协调官或联络点。“地方预防网络”需要设立联络点或协调官。协调官对本地预防网络的各项行动和活动直接负责。联络点由市政当局指定熟悉当地背景、具有强大社交网络、良好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专人或公务员负责,联络点负责人应具备召集、激励、启发地方预防网络成员的能力。
第三,组建预防网络团队。组建预防网络团队对协同城市和社区层面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地方预防网络”一般由8~12名代表不同宗教和族群社团的成员构成。“地方预防网络”的建设需要吸纳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尤其是青年专家,同时吸纳地方政府代表、警察、社区等工作者。这些成员大多为志愿者,具备改善当地社区的意愿、专业知识和行动能力。
第四,完善事前技能审核与响应意识评估体系。在开展预防工作前,联络点对预防网络成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进行初审,同时提供各类培训资源,向其成员提供识别和应对极端主义早期迹象所需具备的知识和工具,并依据风险和干预指标来评估成员的响应意识。响应意识按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一般意识、预防意识、目标意识和直接干预。其中,“一般意识”针对整个社区的活动,主要关注儿童和年轻人的社交技能、批判性思维和责任感;“预防意识”针对脆弱或易遭受暴力侵害的地区或社区的活动;“目标意识”针对脆弱或易遭受暴力侵害的个人的活动;“直接干预”针对曾经的极端组织的活跃成员,或被认定易遭受暴力等其他犯罪行为的个人的活动。
第五,建立本地协调机制。建立本地协调机制是推进“地方预防网络”计划落地的基础。黎巴嫩的地方预防网络每个月或每两个月举行一次协调工作会,目的是使各成员接受专业人士的培训,与其他市政当局交流经验,以及有针对性地设计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相关行动,以此降低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的风险。
第六,确立地方优先事项和组织社区活动。“地方预防网络”建立后,地方当局基于地方风险评估和地方需求认定,列出优先事项清单,并在此基础上策划和组织相关的社区活动。在这方面,的黎波里等城市的“地方预防网络”举办了诸如对话会、青年艺术项目、宗教布道、教师培训、预防暴力极端主义指南宣介等一系列活动。
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非政府组织“国际警戒”就预防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对的黎波里及其周边的巴达维和纳赫莱地区143名14岁至16岁的青年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人员将调查对象按是否参与预防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驱动暴力极端主义的关键脆弱性因素包括:被政治边缘化的感觉、受到安全部队的不平等对待、社会和经济的不公正感、就业机会的匮乏、教育基础设施和学习机会的缺失、未来前景渺茫、破坏性的社会背景和暴力经历等。(59)Muzna Al Masri and Ilina Slavova,More Resilient,Still Vulnerable:Taking Stock of Prevention of Violent Extremism Programming with Youth in Tripoli,Lebanon,p.4.这些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层面的脆弱性因素,既能解释青少年加入极端组织的动机,也能说明极端组织在招募成员时的侧重点和主攻方向。接受暴力极端主义的青少年此后能否有效完成思想转化,关键在于加强其心理适应能力、社区凝聚力和正能量网络、对多样性的容忍和支持、理解和尊重人权、归属感、理解和处理非暴力冲突的能力以及发展与当局的积极关系。
四、“与生活和解”计划与黎巴嫩监狱青少年去极端化的实践
监狱是极端主义形成和传播的重要场所,监狱去极端化是黎巴嫩去极端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鲁米耶监狱(Roumieh Prison)曾多次发生大规模骚乱和越狱事件,是黎巴嫩最臭名昭著的监狱之一。该监狱距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12公里,设计容量为1,050人,至2017年实际关押的犯人数量已达设计容量的三倍。(60)Idowu Biao,ed.,Strategic Learning Ideologies in Prison Education Programs,Hershey:IGI Global,2017,p.166.澳大利亚学者因迪·菲利普斯(Indi Phillips)2019年对鲁米耶监狱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监狱内部设有7个监区,犯恐怖主义罪的囚犯被关押在其中的3个监区。其中,A监区关押的囚犯以什叶派为主,B监区关押的囚犯以逊尼派恐怖分子为主,其中包括“伊斯兰征服”“伊斯兰国”“支持阵线”(61)2016年7月,“支持阵线”头目朱拉尼宣布该组织脱离“基地”组织,并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等极端组织的成员。(62)Indi Phillips,“Prison Radicalization:Indirect Processes of Radicalization at Lebanon’s Roumieh,” European Eye on Radicalization,December 18,2019,https://eeradicalization.com/pri ̄son-radicalization-indirect-processes-of-radicalization-at-lebanons-roumieh/,登录时间:2019年12月23日。除关押成年囚犯的监区外,鲁米耶监狱内部还设有未成年被拘留者的监区,用于关押年龄在18岁以下、被指控犯有暴力极端主义罪行的青少年。
(一) 教派同质化的管理格局
鲁米耶监狱依据教派而非犯罪类别和等级关押囚犯,这使得监狱内部形成了教派属性同质化、警戒等级混合化的管理格局。黎巴嫩教派色彩浓厚的政治环境,使得教派矛盾即使在监狱内也是引发社会动荡的潜在风险。监狱内部按教派属性确立的囚犯隔离模式,虽然有利于降低监狱内部教派暴力的发生率,但不按罪名和警戒等级关押囚犯的群体性隔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同一教派意识形态从激进化转向极端化的可能性。更严峻的现实是,看管整座鲁米耶监狱的狱警人员只有30名。(63)“Invisible Women:Gendered Dimensions of Return,Rehabilitation and Reintegration from Violent Extremism,” ICAN,January 2019,p.88,https://icanpeace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ICAN-UNDP-Rehabilitation-Reintegration-Invisible-Women-Report-2019.pdf,登录时间:2020年2月9日。B监区的850名囚犯分布在三个楼层,但每个楼层只有两名狱警负责看守。监狱设计的1:36的警囚比,如今可能已降低至1∶125。(64)Indi Phillips,“Prison Radicalization:Indirect Processes of Radicalization at Lebanon’s Roumieh”.群体性隔离虽简化了对囚犯的监管,但在囚犯数量远超出监狱设计容量和狱警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囚犯与警卫人员的关系产生倒置,监狱当局无法有效行使监管权力。(65)Indi Phillips,“Deradicalization Programs Inside Prisons in Lebanon,” European Eye on Radicalization,December 18,2019,https://eeradicalization.com/deradicalization-programs-inside-prisons-in-lebanon/,登录时间:2019年12月23日。
鲁米耶监狱内部警囚比的失衡加剧了囚犯与警卫人员之间关系的倒置,迫使囚犯必须通过依附监狱内部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极端组织头目来换取食物、空间和人身安全。个人的生存利益成为囚犯思想发生激进化、极端化转向的主要驱动因素。在监狱内部的生存环境中,物质利益、生存空间、人身安全的获得,取决于囚犯是否具有稳定且持续强化的极端意识形态以及本人对极端组织头目的忠诚度。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此前曾在其宣传材料中承认并赞赏黎巴嫩鲁米耶监狱B监区囚犯的行动,这确立了B监区在黎巴嫩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中的地位。(66)Indi Phillips,“Prison Radicalization:Indirect Processes of Radicalization at Lebanon’s Roumieh”.“伊斯兰国”组织还通过资助囚犯家人来强化监狱内外的联动,这种激励机制能够确保有影响力的囚犯对极端组织的忠诚度,使囚犯自身奉行极端意识形态的动机得以增强。学者菲利普斯通过调查发现,B监区囚犯群体内部形成了某种复杂的自治机制,选举制度、宗教法院系统和惩戒委员会等功能性机构的设立,使得B监区内部呈现出高度的等级制结构。(67)Ibid.这种封闭的、难以渗透的环境,有利于囚犯之间相互传授和交流犯罪技能、极端思想甚至暴恐实施策略,阻碍了传统的监狱去极端化计划的实施。
黎巴嫩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不同政治派别也通过操纵囚犯来实现各派的政治利益,鲁米耶监狱的囚犯由此成为黎巴嫩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工具。有什叶派力量利用逊尼派囚犯策动和协调监狱外恐怖分子发动暴恐袭击,来打击逊尼派政治对手和改变逊尼派的人口结构;也有逊尼派力量通过大规模逮捕逊尼派囚犯的家属和以行政手段恶化监狱内部的生存条件,强化逊尼派的受害者叙事,以此巩固逊尼派对国内宗教政治话语的主导权。B监区内部有影响力的囚犯也会通过争取囚犯所在社区的大批选民,与不同的政治派别进行利益交换。(68)Indi Phillips,“Deradicalization Programs Inside Prisons in Lebanon”.
监狱去极端化是黎巴嫩《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国家战略》的重点领域之一,狱方一般采用五种方式对监狱内部的成年囚犯实行关押和管理。一是隔绝,即将犯有与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罪行的每个成年囚犯关押在与外界其他囚犯完全隔绝的空间,其优点是将囚犯限制在个体的激进状态,缺点是可能会刺激个体的“过度激进”。二是分离,即将犯有与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罪行的一批囚犯与其他囚犯进行隔离,其优点是便于管理和减少其他囚犯思想激进化的渠道,缺点是被隔离群体中的激进主义者可能受到思想最极端的囚犯的影响。三是集中,即将犯有与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罪行的囚犯集中关押在专用牢房,其优点是便于狱方为极端分子提供额外的安全措施,缺点是在去极端化方面立场动摇的囚犯或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选择放弃“脱离接触”治疗而转向加强与专用牢房中其他囚犯的联系。四是驱散,即将不同监狱中犯有与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罪行的囚犯统一关押至同一座监狱或监区,其优点是有利于防止极端组织在监狱内部招募成员,缺点是使极端分子能够面对面交流和接触,降低了其思想转化的可能性。五是融合,即将犯有与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罪行的囚犯与其他类别的囚犯关押在一起,其优点是防止同质化的囚犯群体的形成,使具有不同的观点、立场和思想的囚犯处于同一空间,有利于“脱离接触”和“重新融入社会”康复计划的实施,缺点是作为极端组织头目的囚犯可能会借此招募成员和传播极端思想。(69)Lebanes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Ministry of Interior and Municipalities,“The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in Detention with Offences Related to Violent Extremism or Terrorism in Lebanon,”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19,pp.31-32,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middleeastandnorthafrica/2019/First_National_Report_on_The_Rehabilitation_of_Children_in_detention_with_Offences_Related_to_Violent_Extremism_or_Terrorism_in_Lebanon.pdf,登录时间:2020年10月8日。
黎巴嫩政府对犯有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罪行的未成年被拘留者主要采取融合手段,其目的是将这类未成年被拘留者置于多样化的监狱环境中,使该群体在与其他类别的未成年被拘押者的交往过程中,逐渐转变自身认知和消除观念偏见,防止被进一步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2012年至2018年,黎巴嫩国内共有4,382名被指控犯有暴力极端主义罪行的罪犯。从年龄分布来看,这些罪犯中15~18岁未成年被拘留者占比达3%(138人),18~25岁青年囚犯占比达59%(2,585人),25岁以上成年囚犯占比达38%(1,659人)。鲁米耶监狱中被指控犯有暴力极端主义罪行的未成年被拘留者占比达19%(23人)。从国籍分布来看,2013年前这些未成年人都是黎巴嫩籍,但2013年后叙利亚籍和巴勒斯坦籍的未成年被拘留者人数明显增加,2018年叙利亚籍的未成年被拘留者比例已高达67%,凸显了叙利亚战争导致的极端主义抬头对地区未成年人的影响。从被拘留事由来看,鲁米耶监狱138名未成年被拘留者中,46%因参与或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而被捕,34%因加入恐怖组织而被捕,20%因为恐怖主义辩护而被捕;其中,37%的未成年人据称是同恐怖组织中的同龄人及/或家庭中的成年人共同实施暴恐活动的,32%的未成年被拘留者的家人被关押在成年囚犯监区。(70)Lebanes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Ministry of Interior and Municipalities,“The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in Detention with Offences Related to Violent Extremism or Terrorism in Lebanon,” pp.37-39,45.这表明,在对未成年人开展去极端化工作的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对其家庭进行干预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必要性。从拘留期限来看,在被鲁米耶监狱拘留的138名未成年人中,74%在庭审前被释放,26%被判拘役;2012年至2016年间的平均拘留期限达7个月,但2017年以来平均拘留期限增至22个月。(71)Ibid.,p.43.
(二) “与生活和解”计划
黎巴嫩政府自20世纪末便开始探索针对鲁米耶监狱的囚犯尤其是被关押的未成年人开展去极端化工作的路径。1999年,鲁米耶监狱少年监区与黎巴嫩司法部少年局合作设立了“与生活和解”试点计划。该计划是针对鲁米耶监狱因被指控暴力极端主义罪名的未成年人的强制性康复计划。
从实施过程来看,“与生活和解”计划分为“准入”“早期观察”“指导”“参与”“准备释放”五个阶段。在准入阶段,黎巴嫩内政部指派的社会工作者为每位未成年被拘留者建立医疗、社会和法律档案,该档案跟踪未成年人在被拘留期间的进展,评估康复计划的具体成效。在早期观察阶段,未成年被拘留者需接受为期15天的初步观察。其间,工作人员对其个人需求、与权威的关系、个性、期望和兴趣等进行评估,以便后续根据每个未成年人的特性开展个性化指导。在指导阶段,工作人员根据每个未成年人的特征和能力制定涵盖社会、心理、教育、家庭等各方面的个性化“生活计划”,旨在通过评估未成年被拘留者的处境,采取促使其重新融入社会的必要措施。在参与阶段,未成年人根据“生活计划”接受社会心理层面的康复治疗。“生活计划”将心理咨询、家庭关系、文化活动、教育指导等各层面因素纳入整个康复过程,恢复未成年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同时注重未成年人被释放后的社会“安全网络”的构建;通过一系列职业培训为其提供就业技能,降低未成年人被释放后辍学的风险。在准备释放阶段,工作人员与未成年被拘留者的家庭为孩子重返家庭和社区后,在重新融入社会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情感、身份和关系方面的挑战做好应对的准备。(72)Lebanes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Ministry of Interior and Municipalities,“The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in Detention with Offences Related to Violent Extremism or Terrorism in Lebanon,” pp.51-55.
从实施目标来看,“与生活和解”计划旨在实现三大目标:第一,树立规则意识。所有未成年被拘留者必须穿戴统一的、无宗教标识的服装,不得要求组织集体礼拜。第二,建立包容多元信仰和观点的环境。该过程旨在挑战部分未成年人在思想极端化过程中形成的片面教条观念。鲁米耶监狱针对未成年人的去极端化经验表明,通过宗教领袖与极端分子开展宗教对话使后者脱离接触极端主义的做法,对宗教观念尚不成体系的未成年人并不适用。而文化教育和体育活动对促进未成年人之间的跨文化对话、树立规则意识的效果更明显。例如,狱方在圣诞节期间组织所有未成年被拘留者参与制作圣诞树,提升他们对不同宗教和文化的开放性和宽容度以消除偏见;体育活动则有利于增强青少年的非暴力规则意识。在此过程中,监狱工作人员也需要接受培训,树立对被指控犯有暴力极端主义罪行的未成年人的中立和同情态度,在监狱内部“创造有利于增加他们重返社会机会的环境”(73)Lebanes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Ministry of Interior and Municipalities,“The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in Detention with Offences Related to Violent Extremism or Terrorism in Lebanon,” p.91.。第三,完成从脱离暴力向与生活和解的康复过程。“与生活和解”计划旨在通过组织园艺、绘画、写作等各种形式的康复活动,使未成年人的关注焦点从“暴力和破坏”转向“生活和创造”,在与生活和解的过程中明确自己的人生定位。(74)Ibid.,pp.61-63.例如,鲁米耶监狱狱方会在母亲节组织未成年人向自己的母亲献花,使其与母亲之间重新建立情感纽带。
从评估指标来看,“与生活和解计划”确定了风险和进度评估的五大指标。一是宗教信仰对本人及其与生活各方面关系和行为的影响;二是在为自己行为尤其是暴力行为辩护时本人对宗教信仰的运用程度;三是对具有不同观点和信仰的其他人的接受度;四是在面临生活困难时管理情绪和以乐观态度应对的能力;五是对暴力极端主义进行反思和评估的程度。该计划聘请不同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士每个季度就前述指标对未成年被拘留者进行一次风险等级评估,观察每个未成年人在行为、对其他未成年人和监狱工作人员态度、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变化。(75)Lebanes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Ministry of Interior and Municipalities,“The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in Detention with Offences Related to Violent Extremism or Terrorism in Lebanon,” p.69.
从实际效果来看,“与生命和解”计划对未成年人放弃暴力极端主义成效明显。从准入阶段的第一次评估到三个月后的第二次评估结果来看,参与该计划的鲁米耶监狱未成年被拘留者中,保持稳定的占55%,风险降低的占21%,风险加剧的占23%。其中,暴力极端主义风险加剧的原因可能是,部分未成年人在准入阶段接受评估时因对工作人员不信任而不愿意分享其生活的某些方面,导致最初的风险等级被低估。拘留期间第四次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处于暴力极端主义中等风险的未成年被拘留者的风险等级下降了100%。(76)Ibid.,p.79.
需要指出的是,“与生活和解”计划只是针对宗教意识相对淡薄的未成年群体的去极端化康复计划,该计划的实施尚未扩大至18~25岁的青年囚犯群体以及25岁以上的成年囚犯群体。不同年龄段的囚犯在宗教信仰、身份认同、价值观、社会适应力、暴力使用程度、与家庭成员关系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与生活和解”计划这一去极端化模式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其他年龄段的囚犯。
五、结语
黎巴嫩安全形势在极端主义与叛乱政治、教派政治和难民政治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黎巴嫩在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的过程中,通过制定《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国家战略》,对本国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总体框架、战略目标、实施主体和实践路径进行整体规划,逐渐形成了去极端化的“黎巴嫩模式”。该模式践行预防为主、控制为辅的去极端化理念,为极端化的个体提供非暴力的替代选择和融入主流社会的机会;重视吸收国际经验,采取预防与干预相结合的行动原则;建立跨部门工作机制和覆盖从国家到个人的多层次预防体系,广纳社会各界专业人士,实现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以赛达、的黎波里和马吉达勒·安吉尔“地方预防网络”为代表的黎巴嫩城市去极端化实践,通过市政当局与国家主管部门和部委开展协调、确定预防网络协调官或联络点、组建预防网络团队、完善事前技能审核与响应意识评估体系、建立本地协调机制以及确立地方优先事项和组织社区活动,加强城市边缘和脆弱群体的心理适应能力、社区凝聚力和正能量网络,消除驱动暴力极端主义的关键脆弱性因素。
以鲁米耶监狱“与生活和解”计划为代表的未成年人去极端化实践,通过制定个性化的“生活计划”,在思想、情感、身份和关系等层面对受极端主义影响的未成年被拘留者进行精准帮扶与管理,使接受强制性康复计划的未成年被拘留者树立规则意识、建立包容多元信仰和观点的环境、完成从脱离暴力向与生活和解的康复过程,帮助其恢复对生活的信心,提升其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
黎巴嫩政府对城市去极端化和监狱去极端化模式的探索,尤其是其中开展全社会动员、建构“地方预防网络”、建立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鼓励社区和家庭参与、创建宽容环境的理念和经验,对于冲突国家及其周边国家的去极端化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