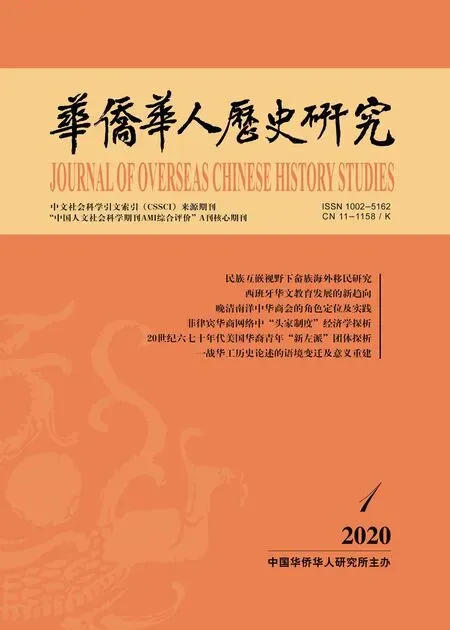美国1882 年排华法的前奏: 1875 年《佩奇法》实施的背景及影响
顾国平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英语学院,北京 100024)
1875 年,美国国会绕开中美两国《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中“自由移民”的条款,通过了以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贺拉斯·佩奇(Horace F. Page)的名字命名的《佩奇法》。该法实施后,限制了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苦力和女性移民美国,成为七年之后1882 年美国全面排华的前奏。对于《佩奇法》的背景及其影响,美国学者乔治·佩弗尔(George A. Peffer)通过对史料的挖掘,矫正了学界先前对《佩奇法》的漠视,指出该法极为有效地将中国女性阻挡在美国国门之外;[1]凯利·亚布拉姆斯(Kerry Abrams)则将该法置于当时美国国内扫黄运动和反对一夫多妻制的背景下,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了《佩奇法》出台的背景与过程;[2]另有学者追溯了《佩奇法》出台前美国加州通过立法限制华人妇女入境的尝试。[3]
国内学界对美国移民研究中排华主题的研究,多集中于1882 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出台的原因和影响[4]以及美国排华期间的华人处境[5]等,具体到早年华人女性赴美的研究,数量还不是很多,已有的研究包括对华人女性早期赴美动机的论述,[6]对华人女性在美国的处境和地位变化的探讨等。[7]关于中美1868 年《蒲安臣条约》,由于其中“自由移民”的条款,梁启超远在百年前就称其为中国“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8]徐国琦在2019 年初出版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中,也称该条约是“中美两国之间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这或许是清朝在19 世纪唯一的平等条约”。[9]关于该条约如何客观抑制了美国国内对华工的排斥,[10]保护了出国华工和华侨等,[11]学者们都已有论述。相比而言,国内对于《佩奇法》及其对华人赴美影响的研究几乎尚未触及。无怪乎学者韩玲在梳理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内美国移民政策史研究的文献后,认为国内对“重要转折阶段的政策研究欠缺”。[12]
《佩奇法》作为美国第一部联邦层面限制移民的法律,既是美国排华立法过程中从加州立法向联邦立法的过渡,也是中美移民史上美国联邦政府层面从抛弃《蒲安臣条约》转向拥抱《排华法案》的一个重要过渡性法律和政策。《佩奇法》中对华人赴美的部分限制,是美国在华人移民问题上从自由移民向全面限制的一个中间站和重要转折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性别失衡的早期美国华人社区
在19 世纪中期前往美国西海岸加入淘金浪潮(Gold Rush)的华工中,男性占绝大多数,性别失衡严重。当时的美国西海岸尚未完全开发,属于边疆性质,性别失衡并非华人社区独有,但是华人人口的性别失衡问题尤为突出。1850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平均男女性别比例是12︰1,而华人中的男女比例则是39︰1。在加州的旧金山,当时的华工主要还在金矿从事苦力活,尚未定居城市,其性别失衡问题更为严重。以1852 年为例,生活在旧金山的华人中有男性2954 人,女性19 人,男女比例高达155︰1;而到1860 年,这一比例进一步失衡,达到186︰1。[13]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1860 年、1870 年和1880 年,在美国的每1000 名华人男性对应的华人女性人数分别是54 人、78 人和47 人。[14]
美国华人中当时如此严重的性别失衡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既有中国传统社会习俗的制约,也有经济因素的影响,更有美国当时排华环境的作用。首先,在传统的中国家庭权力结构中,父母占据主导地位,夫妻关系从属于父子/母子关系,儿子结婚后有义务将其妻子带回家服侍父母。因此对已婚女子来说,对公婆的责任在其所有家庭责任中处于第一位,她需要服从婆婆的指挥,承担家中各种不同的职责。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写道:“当中国男性外出谋生时,他们的妻子被要求留在家中抚养孩子,照顾公婆。直到20 世纪之前,这样一种社会规范一直制约着从中国南方向海外的移民,在东南亚的华人移民是如此,在北美和澳洲的华人移民也是如此。”[15]
第二,早期前往美国的中国男性华工的“旅居者心态”(sojourner mentality)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当时的男性华工与来自欧洲的移民不同,他们赴美务工只是一个短期打算,挣到钱后最终要回到中国。这一旅居者心态让大多数华工的妻子选择留在了国内,照顾家小,等待丈夫归来。实际情况也表明,早期前往美国的男性华工中有一半左右最后都回国了。[16]
第三,横跨太平洋的高昂旅费以及美国较高的生活成本,也是阻挡女性前往美国的重要原因。[17]
第四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当地社会对华人尤其是对华人女性的敌视态度,以及美国法律缺乏对华人的保护。在美国学者佩弗尔看来,中国传统习俗、华工的旅居者心态和经济因素等固然重要,但不足以解释“美国华人性别失衡问题如此严重,而且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中国的家庭传统虽然要求女性恪守各种规范,但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地方经济状况的变化,中国家庭一直在为适应变化而做出调整。此外,通过比较早期美国华人社区与其他诸如新加坡和夏威夷等海外早期华人社区可以发现,其他海外华人社区的华人较早地经历了从旅居者向定居者的转变,其地方当局很早就意识到鼓励华人女性移民可以缓和男性占绝大多数的华人社区的多种矛盾和问题。因此,美国华人社区性别比例长期严重失衡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当地敌视华裔妇女的环境。[18]
二、早期美国华人女性:卖淫业与一夫多妻制
在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华工旅居者心态以及美国当地社会敌视态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华工人口中的女性一直很少,华人聚居的地方形成了所谓的“单身汉社区”。餐馆、赌场、鸦片馆和妓院等场所构成了当地华人社会的活动中心,基本都以男性华人为服务对象。在为数不多的华人女性中,除了极少数包括外交人员、商人和学生等属于特殊阶层的女性配偶外,大部分从事卖淫业,另外一部分是条件较好的华人男士的妻妾,其余的从事着洗衣、挖矿、裁缝、厨师和女佣之类的工作。根据不同学者对当时旧金山华人人口构成的统计,1860 年华人女性中妓女的比例在85%至97%之间,1870 年这一比例是63%至72%,1880 年大约是18%至50%。[19]
(一)卖淫业
19 世纪中期的加利福尼亚州尚属美国西部边疆的一部分,人口构成以年轻男性为主。西部艰苦的条件造就了他们敢于冒险勇于闯荡的性格,而边疆社会也缺乏文明社会的各种约束。各种专门针对单身男性的活动和消遣应运而生,卖淫业即为其中之一。当时,加州有来自世界各地各个种族的妓女,本地出生的白人女性、新来的欧洲和拉美女性以及黑人女性和印第安女性都有从事卖淫业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华人妓女的人数最多,超过其他妓女人数的总和。[20]究其原因,当时加州华人人口性别严重失衡、中国南方当时贫苦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华人帮会对卖淫业的操控等,都是重要因素。
19 世纪上半期,中国清朝与西方相比正经历着不可逆转的国势衰退,而人口却从18 世纪末的3亿左右增长到了1850 年前后的4.3 亿,人口压力与日俱增,而广东省则是其中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与此同时,内忧外患不断困扰清朝政府,尤其是南方省份。19 世纪40 年代的鸦片战争带来的是巨额赔款以及广州等口岸的被迫开放,为了偿还赔款,政府加重了税收。而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的入侵,则使得广东市场上充斥西方的廉价商品,民间落后低效的手工业受到挤压,难以为继。外患之后是内忧,19 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广东红巾军起义、土客冲突,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加剧了广东民间的贫苦程度。在这样的内外背景之下,为了生计,售卖子女甚至弃婴杀婴等做法都成为不少家庭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由于男尊女卑的传统,与儿子相比女儿更容易成为出售的对象。[21]
当然,即使家庭条件再艰苦,也很少有父母会同意将女儿卖给妓院,但这在人口贩子眼里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买卖过程中,他们保证说什么这些女孩绝对不会被卖到妓院,而是去美国当家佣或者是嫁给美国华工当妻子。这类信誓旦旦的保证确实起到了缓减买卖女儿时情感上的痛苦,因此也让交易变得更为顺畅。除去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买卖外,一些蛇头还通过坑蒙拐骗来诱骗年轻女性,甚至直接绑架。这些女性一般都被许以到美国去结婚或务工之类的承诺,待到在美国登岸才发现自己被卖给了妓院。更有甚者,一些女性直接被绑架。不少关于美国早期华裔女性的著作都有此类记载和论述。[22]有一位广东少女受邀参观一艘泊在港口的美国汽船,然而当她正在船上参观之际,那艘船却起锚发动,扬帆驶向旧金山。[23]在华裔女性作家严歌苓那本基于充足的史料写成的小说《扶桑》中,主人公扶桑也是同样遭遇了绑架后被卖到美国从妓。
就当时华人女性卖淫业的运营而言,1854 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华人妓女同来自其他国家的妓女一样,处在“自由放任”的状态,相当于从事一种自由职业,有基本的人身自由。但1854年以后,华人帮派开始接手卖淫业,妓女的境遇变得更为惨淡。她们终日生活在妓院,与外面的世界基本隔离,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难以跳出服务契约。一般的妓女契约在4 年到6 年之间,其间没有工资,而且规定如果妓女发生生病或怀孕等情况,都需要相应延长契约时限。陷于卖身契的妓女都受到严厉的剥削,很多妓女活不到卖身契到期之日。当然,就像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妓女的生活也有其幸运的一面。首先,妓女身上的商业价值使得帮会和妓院老板在对妓女实施严重的人身伤害时会有所顾忌,而且,顾客们也因为不想身份曝光一般不会对妓女施加伤害。还有一些妓女更为幸运,或因自身的坚持或因中意顾客的介入获得赎身,此外,也有的和情人私奔或在当地教会寻求庇护逃出妓院。[24]
(二)一夫多妻制
除了占比最大的妓女之外,当时美国华人女性中人数上占第二位的群体是一些条件较好的华人男性所纳的妾。这里涉及美国与传统中国在家庭和婚姻制度上的巨大不同。在美国,历史上除了摩门教所在的犹他州外,在婚姻制度上历来实行一夫一妻制,而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允许一夫多妻。在19 世纪以前,中国的男性只要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就可以纳妾,三妻四妾是男士能力和地位的象征。如果这些有妻妾的男士短期或长期外出,一般的安排是妻子留在老家,负责照顾全家老少,妾跟随外出。这种情况在赴美务工的华人中间也相当普遍,当时美国西海岸与条件较好的华人男士生活在一起的女性一般也都是妾。[25]
综上所述,19 世纪中期美国西部的华人社区中,男性多为单身汉,或者虽已成家但妻子留在国内,因此也形同单身;女性主要是妓女或一夫多妻制中的妾,符合美国一夫一妻制传统的家庭和婚姻关系在华人社会中较为少见。这些占大多数的华人男性和女性在当时美国社会中非常规的从业和生活状况,逐渐引发了当地白人社会的不解与担忧,并成为后来美国白人排华反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排斥华人女性:种族仇视与传统差异
华人女性在美国西部的职业和生活状况,给当地社会制造了不少或真实或想象的问题。如果说在经济领域白人社会关注和担忧的是华工带来的经济威胁的话,[26]那么华人女性则是当地社会道德担忧的主要对象。白人社会对华人女性的担忧和排斥一方面源于种族偏见,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和传统中国巨大的文化和制度差异所致。由于绝大部分的华人女性在美国不是从事卖淫业,就是一夫多妻制中的小妾,因此在美国当地社会眼中成为“异类”,违背美国传统的婚姻道德和性道德。华人妓女和小妾的存在,不仅被认为冲击到了美国一夫一妻的家庭婚姻制度,而且还被认为与当时美国刚刚废除的奴隶制相似,威胁到了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
(一)种族偏见与仇视
美国当地白人社会对华人女性的歧视和排斥,首先源于种族主义偏见,认为华人女性由于其种族属性,属于落后与堕落的阶层,而华人女性中妓女的比例如此之高,则是该种族堕落的证明。这一种族偏见与当时流行西方的有关人种分类的“伪科学”有关,即认为人类由不同人种构成,且不同人种天资与能力各异,形成一个种族的等级格局。鉴于白种人当时相对于其他种族技术上更为领先,他们普遍被认为处于人种等级格局的顶端,是凌驾于其他种族之上的“高等”种族。这一人种伪科学还认为,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的通婚会导致“高等”种族或民族的堕落和退化,因此,白人在与其他人种交往的过程中,需要防范相互通婚,防止自身的退化。这些观念当时虽然也有争议,但在整个西方相当流行。以1862 年在美国出版的《华人移民与一个国家堕落的生理原因》(Chinese Immigration and the Physiological Causes of the Decay of a Nation)为例,作者亚瑟·斯塔特(Arthur B. Stout)充满种族偏见与对黄种人的仇视,在书中宣扬排华立场。作者写道:“自然界的第一法则是保卫种族的纯洁性……种族自卫的法则要求我们制定国家的第一部保护性立法。”为了说服读者,他还引用种族伪科学,挑拨读者对异族的恐惧心理:“如果我们与东亚人(Eastern Asiatics)混居通婚,我们会生下堕落的杂种。”[27]
除了基于当时流行的人种理论而引发的一般性的道德恐惧之外,华人妓女还在当地白人社会造成一种切实的道德忧虑。在白人眼中,华人妓女离经叛道,严重偏离了维多利亚时代要求女性矜持端庄的道德正统。[28]此外,正如小说《扶桑》中描述的,相对于来自其他国家的妓女,华人妓女收费更为低廉,而东方女性在白人男性眼中又充满神秘感。猎奇心理加上廉价服务,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十几岁的白人少年用他们的零花钱时常光顾华人妓院。这一现象造成了白人家长的担心,他们大力谴责华人妓女导致了当地传统道德的崩坏。
当时的医学知识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时的医疗知识体系中,华人妓女被认为威胁到了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存续。当时的医生们“诊断”出了一种所谓的“反常”(deviant)行为,源于先天的生理缺陷,是智力低下与落后的“症状”。其中,性病就与这些先天的缺陷相关。而妓女相对于其他人群来说,确实是一个更容易患上各类性病的群体。这种针对华人妓女的医学偏见很快传遍社会,华人妓女很快就被贴上了“不道德”、“异族”、“淫荡”等标签,被认为是性病尤其是梅毒的传染之源。另一种当时流行的有关疾病的所谓“瘴气理论”(miasmatic theory)认为,流行病的爆发与该地的环境或卫生条件相关。旧金山的卫生官员与医疗人员将矛头指向唐人街,认为唐人街到处管道漏水,水沟破烂,垃圾遍布,脏乱环境正是该市大气污染、“乌烟瘴气”的根源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人妓女连同其他华人一起被指控犯下了“卫生罪”(sanitary evils),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白人的生存环境。[29]
关于华人妓女会带来道德败坏与身体疾病的看法,在加州上到官员下至普通白人,十分流行。加州联邦参议员科尔(Cornelius Cole)1870 年接受《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采访时说:“在那些来到我国的华人中有一类最不受欢迎的人——我指的是华人女性,因为她们在我们白人中传播疾病和道德败坏的种子。每当我看到这类人,我就问自己要不要对她们的入境进行限制。”[30]在1875 年美国国会通过《佩奇法》之前的发言中,议员佩奇所引用的加州移民官员(Commissioner of Immigration)的一封信也表达了类似的恐慌:“众所周知,加州的每个城镇都有华人妓院,数量之多足以将疾病传播给我们那些少不更事的白人青年。”[31]
(二)文化传统的差异
其次,19 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当地白人社会对华人女性的排斥,也源于两国当时不同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华人女性中占绝大多数的妓女和妾的生活状况和地位,使得白人将其与奴隶制联系起来。如上文所述,传统的中国家庭允许一夫多妻制,这一传统习俗也被华工带到了海外。华工一旦通过自身的打拼条件转好,多会选择纳妾,原配妻子留在国内照顾家小,妾则陪伴在身边。华工的这一做法即是对传统一夫多妻制习俗的传承,也是其在海外成功地位的证明。华人社会不仅认可一夫多妻制,对于妓女也表现出较大的宽容。海外华人社区中的“妓女”与“妻子”之间的界限并非一成不变,妓女中有不小的比例在从事一段时间的卖淫业后又嫁给男性华工成为其妻子。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底层并不给妓女贴上“堕落”或“无可救药”之类的道德标签,这些“失足妇女”只是听从父母之命,为了帮助贫困的家庭而牺牲自己。因此,底层贫苦家庭的男子并不排斥从良的“失足妇女”。这一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严重失衡的男女比例,使得加州华人社区的男性华工娶妓女为妻的现象更为普遍。[32]
与传统华人社会不同的是,在美国社会中,妓女与普通女性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制也是无法兼容。如上文所言,大量华人妓女的存在已经造成了白人眼中的道德与卫生方面的威胁,而华人社区所允许的一夫多妻制,严重挑战了美国正统的婚姻制度。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社会将妓女制度和一夫多妻制与奴隶制度联系起来,认为绝大部分华人女性不是妓女就是妾,处于一种类似奴隶的状态。
卖淫业与奴隶制的关联,建立在白人社会对华人妓女受帮会控制没有人身自由的认识基础之上。与卖淫业相似,一夫多妻制也被美国白人社会认为与奴隶制有紧密关联。在1856 年美国共和党全国大会上确定的竞选纲领中,就明确指出要在美国的西部领地上同时废除奴隶制和一夫多妻制,认为这两种制度都是“野蛮时代的残余”。[33]而且,对于内战前的美国来说,这两种制度在美国南方种植园得到了结合,因为当时南方种植园实施的奴隶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一夫多妻制,白人男性种植园主对种植园的全部黑人女性拥有性特权。[34]美国社会对一夫多妻制的抵制还表现在对西部摩门教徒的立法打击。1862 年7 月1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反一夫多妻制法》(Anti-Polygamy Act,全称The Morrill Act for the Suppression of Polygamy),立法对象是生活在当时还是犹他领地的摩门教徒。在主流白人社会眼中,实行一夫多妻制不仅对个人身体有害,而且是一种变态的行为,不仅使社会风气败坏,道德堕落,更是一种政治暴政,给深陷该制度的男男女女套上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枷锁。[35]白人主流社会对一夫多妻制与奴隶制的这一关联,确实给摩门教徒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使其于19 世纪90 年代早期宣布废除一夫多妻制。犹他州于1894 年被接纳为美国一个州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禁止一夫多妻制。
鉴于美国主流社会对一夫多妻制和奴隶制的关联,孔飞力做出了如下论断:“在美国,当地人对于奴隶制度的深恶痛绝,却在对待中国移民的问题上起着奇怪的、具有讽刺意义的作用。”[36]当华人男性引以为傲的一夫多妻制遇上美国的婚姻传统,不仅被认为是一个异类,而且还是一种罪恶的制度。文化传统的差异难以调和。
综上所述,美国当地社会戴着种族主义的有色眼镜,认为占华人女性多数的华人妓女不仅构成了人种上的威胁,直接危害到了白人文明的存续,而且还是一种道德污染源,威胁着美国传统的性道德。而美国与中国传统社会在婚姻制度与家庭习俗上的差异,再加上美国当时反奴隶制、反一夫多妻制的历史背景,使得美国白人社会认为,大部分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女性(还有男性苦力华工)无异于奴隶,无法成为美国参与式民主制度中合格的公民,是不受欢迎、需要排斥的。
四、1875 年《佩奇法》及其实施
在美国当时机会主义盛行的政治环境中,弥漫于白人社会的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是不会被政客们放过的,加州议员们很快便开始在华人问题上大做文章。为了赢取选民支持,他们不仅利用了当地社会普遍存在的排华情绪,还夸大华人带来的各种威胁。华人妓女和妻妾带来的道德、种族和医学等挑战与华工的经济威胁被打包组装,成为一系列加州当地排华法案的主要内容。[37]但这些地方法案都被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无效,原因是它们违背了1868 年中美两国《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中允许“自由移民”的条约精神。[38]在地方上不断受挫后,加州议员便将立法努力转向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国会。
(一)《佩奇法》的制定
相比于法案中的“华工经济威胁”条款,华人妓女带来“道德威胁”条款在全国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更多的呼应与支持。在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卖淫与道德腐败等是许多人关注的政治议题,像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总统和海耶斯(Rutherford B. Hayes)总统等政治人物,虽然从经济角度尚不支持禁止华工入境,但他们认同妓女造成的道德冲击,也加入了加州政客的行列,一道谴责华人妓女。[39]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加州联邦众议员贺拉斯·佩奇,1875 年的《佩奇法》即以他的名字命名。佩奇是共和党人,因其排华立场而闻名,1873 年当选联邦众议员后,他便在众议院大力推动排华立法。当时除了华人较多的西部各州之外,排华议题还不是其他地区议员们关心的话题,佩奇推出的多项排华议案均无疾而终。在竞选连任的过程中,由于第一任期内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他担心选民弃他而去,因此更是信誓旦旦,誓言将排华立法努力进行到底。获得连任后,佩奇马不停蹄,为了议案获得通过,他采取了新的策略,对原来完全排华的目标做了妥协,小心绕开了《蒲安臣条约》中“自由移民”的条款。1875 年2 月10 日,新一届国会开始不久,佩奇便提出新的法案,指出华人移民中大多不是自由移民,而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苦力和妓女,应当禁止入境。他坚持认为联邦国会必须就此立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黄祸”威胁和从中国输入的道德沦丧的问题。[40]
为了通过《佩奇法》,佩奇在国会发表演讲,长篇大论为何大部分赴美华人不是自由移民这一主题。他特别强调的是华人女性对美国的家庭和婚姻传统造成的冲击和对白人种族纯洁性的威胁。他无中生有,煽动美国人的恐惧,说什么中国把美国当成一个“粪池”(cesspool),把臣民中最堕落的、受奴役的人群——包括苦力和妓女或小妾——派往美国。佩奇进而指责中国破坏了《蒲安臣条约》,没有遵守其中“自由移民”的条款。而美国只是通过法律禁止苦力和妓女赴美,并没有限制两国之间受《蒲安臣条约》保护的“自由移民”。[41]此外,为了掩饰其中限制移民的本质,佩奇等人对法案的名称句斟字酌,最终以《现有相关移民法律的增补法案》(An Act Supplementary to the Acts in Relation to Immigration)为名提交,巧妙掩盖了该法对原有移民法律的巨大改变。[42]《佩奇法》没有遭到太多的反对便在国会获得通过。该法抓住了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反对奴隶制和一夫一妻制的情绪,以保卫美国传统的婚姻制度和民主制度为名,成功地对被当地人等同于奴隶的东亚尤其是中国苦工和女性关上了大门。
《佩奇法》最终限制的对象是华工苦力和华人妓女,在国会开创了针对某一种族和民族的特定群体立法进行移民限制的先例。就该法规定的惩罚措施而言,妓女买卖与苦力贸易相比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法律对从事苦力贸易的违法者施加最高1 年监禁和最高2000 美元的罚款。而从事华人妓女买卖被认定为“重罪”(felony),一旦定罪,最高刑期为5 年,最高罚金是5000 美元。[43]除去之前被最高法院否决的加州地方排华法案,《佩奇法》成为当时最为严厉的限制部分华人移民的美国联邦法律。
(二)《佩奇法》的实施与影响
与法律条文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的执行。《佩奇法》没有达到阻止苦力华工赴美的目的。从法律出台到1882 年《排华法案》之间的七年间,移民美国的华人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个以七年划分的时间段。但是在阻止华人女性移民美国方面,该法相当成功。法律实施后的七年间,到达美国的华人女性与之前的七年相比下降了68%。七年间美国的华人人口总共增长了超过32,000 人,但是华人女性占美国华人人口的比例却从1870 年的6.4%跌落到了1880 年的4.6%。[44]该法实施后,不仅禁绝了华人妓女赴美,而且连其他普通华人女性也受到牵连与打击,她们前往美国的正式渠道基本被切断。正如孔飞力指出,“虽然该法令只是限制娼妓入境,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使移民当局得以以此为借口,将华人妇女都当成娼妓而拒绝其入境。”[45]
鉴于当时华人前往美国主要经由香港与旧金山,该法的执行实际落在了香港和旧金山两地的移民官员手中。就香港方面而言,美国驻港领事馆官员在华人赴美的程序环节中负责把第一道关。他们与港英当局以及东华医院(Tung Wah Hospital)等机构合作,开展申请资料审核、离港前体检和面对面盘问等工作。以《佩奇法》刚实施时在任的美国驻香港领事大卫·贝利(David H. Bailey)为例,当他得知该法获得通过后,对其上级说希望借此能够阻止那些出于下流和不道德的目的前往美国的华人女性。他为此专门设计了一系列用于筛查妓女的问题,对每位女性申请者进行盘问。问题包括“你是已婚还是单身?”“你是自愿去美国的吗?”“你去美国做什么工作?”“你是去美国从事卖淫业吗?”“你在香港、澳门或中国大陆的妓院生活过吗?”“你曾经从事过卖淫业吗?”“你是一位有德行的贞洁女子吗?”,等等,其中有不少都是华人女性申请者在日常生活中闻所未闻、难以启齿的问题。[46]这些盘问环节之后,领事官便下结论写报告,并上报美国国务院申请批复。由于国务院距离远,缺少其他的信息渠道,对驻港领事官的报告一般都会例行公事,程序性地签署批准。因此,对于出境审核,香港领事馆拥有事实上的最后决定权。当然,由于领事官员玩忽职守、腐败受贿以及从事妓女买卖的蛇头绕开出港手续的各种伎俩,《佩奇法》颁布后并未完全阻断华人女性赴美的渠道,但确实有很多华人女性申请者因为新法律要求的各种严厉手续而被拒之门外。而每一位被拒的申请者都会产生示范效应。她们受挫的经历在当地传开后,不少其他原本有意申请的女性也就打消了申请的念头。
就旧金山港而言,考虑到加州此前在排华反华方面不断立法不断受挫的经历,《佩奇法》的通过对其是一大鼓舞,他们在法律的实施方面尤为卖力。旧金山的移民官员同样心怀前述针对华人女性的种族和道德偏见,在执法过程中打击范围扩大的现象经常发生。很多华人女性通过了香港的层层检查与盘问,又经过了远洋航行到达旧金山后,却发现自己又被旧金山港口移民官扣留,而申请解除扣留的法律手续极为复杂,港口的法官又敷衍塞责,结果是不少华人女性因被怀疑与卖淫业有牵连而又被长途遣返回中国。[47]
从1875 年《佩奇法》实施到1882 年《排华法案》之间的七年时间,美国驻香港领事官员与旧金山移民官员共同严格执法,不仅将华人妓女成功排除在赴美的官方渠道之外,还将法律的打击对象扩大到所有正常赴美的华人女性,成为华人女性前往美国的一道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该法实施一年后,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调查华人移民的情况,参与听证的旧金山港检查员格雷(Giles H. Gray)作证说,在《佩奇法》实施前,每月有两艘华人移民船抵达旧金山港,每艘船平均载有200 至400 名华人女性。法律实施后,抵美的华人女性人数急剧减少。实施后的前4 个月(1875年7 月—10 月),抵达旧金山的华人女性减少至161 人,而到了1876 年的第一季度,总共只有15 位华人女性登岸,[48]这足见该法在限制女性入境时的执行力度。
五、结语
《佩奇法》实施后,来到美国的华人女性越来越少,华人社区中女性比例愈发降低。前文提到的美国人口统计数字显示,从1860 年到1870 年,在美国的每1000 名华人男性对应的华人女性人数从54 人上升到了78 人,但到1880 年,即《佩奇法》实施后的第5 年,这一数字又下降到了47 人,不仅大大低于1870 年的水平,与1860 年相比也有较大的回落。鉴于该法基本阻止了华人女性移民美国,有学者将这七年时间命名为“限制华人女性入境期”(female exclusion)。[49]
《佩奇法》与中国文化传统、华工的旅居者心态等因素一起,有效阻止了华人女性前往美国,而相比于其他因素,《佩奇法》带来的更大的不良后果是使这一现象长期化。华人女性赴美受限,反过来加剧了北美华人社区性别严重失衡的问题,正常的以婚姻为基础的华人社区长期难以出现和发展,而卖淫业等与单身汉社会相关的产业得以继续兴盛。此外,这一法律还在联邦层面开创了针对某一特定群体排外立法的先例。加州议员继续推动更彻底更全面的排华法案,并得到其他地区议员越来越多的响应,最终导致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法案,即通常所谓的1882 年美国排华法案。
[注释]
[1] George Anthony Peffer, “Forbidden Families: E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Women under the Page Law, 1875-1882”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6, No. 1,Fall, 1986; George Anthony Peffer,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2] Kerry Abrams, “Polygamy, Pro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05, No. 3, April, 2005.
[3] Sucheng Chan,This Bitter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n Agriculture, 1860-19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4] 曹雨:《美国〈1882 年排华法案〉的立法过程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 年第2 期;李晓静:《19 世纪中期到20 世纪初美国排华政策对华人社区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 年第4 期;梁茂信:《论19 世纪后期美国对华移民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98 年第6 期。
[5] 杨国标等:《美国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陈尧光:《美国华人境况的变迁》,《美国研究》1987 年第2 期。
[6] 令狐萍:《十九世纪中国妇女移民美国动机初探》,《美国研究》1999 年第1 期。
[7] 刘卓、杨大伟:《从边缘到主流:华裔美国妇女社会地位的上升历程》,《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6 期;令狐萍:《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8]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1200 页。
[9] 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59 页。
[10][38] 谢青、罗超:《蒲安臣条约对美国排斥华工的客观抑制作用》,《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3 期。
[11] 刘华:《评1868 年中美〈蒲安臣条约〉——以华工出国及华侨保护问题为视角》,《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1 期。
[12] 韩玲:《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内的美国移民政策史研究》,《世界民族》2016 年第6 期。
[13] Benson Tong,The Chinese American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0, p.25; Judy Yung,Unbound Voice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99.
[14][43][49] George Anthony Peffer,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24、p.115、p.8.
[15][36][45] 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223、200、236 页。
[16] Thomas Sowell,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BasicBooks, 1981, p.136.
[17] Benson Tong, The Chinese American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0,p.25.
[18] George Anthony Peffer, 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pp.5-6, 11-27.
[19] Elmer Clarence Sandmeyer,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1939, Repri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91, p.9; Benson Tong,Unsubmis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pp.4, 15, 94; George Anthony Peffer,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p.31.
[20][31][33][34][35] Kerry Abrams, “Polygamy, Pro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05, No. 3, April, 2005.
[21] Susie Lan Cassel,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History from Gold Mountain to the New Millennium,Alta Mira Press, 2002, p.24; 令狐萍:《十九世纪中国妇女移民美国动机初探》,《美国研究》1999 年第1 期;Shih-Shan Herny Tsai,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3.
[22]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 辑》,中华书局,1984 年。
[23] 类似的绑架故事参见Benson Tong,Unsubmis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p.40; Judy Yung,Unbound Voices: A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pp.125, 130-131, 148-149.
[24] 参见Judy Yung, Unbound Voices :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pp.125, 141; Benson Tong,Unsubmis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pp.75, 101-105, 144-145, 201.
[25] Yung,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pp.19, 320.
[26] 对于美国排华因素的经济解读,可参见Elmer C. Sandmeyer,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27] Arthur B. Stout,Chinese Immigration and the Physiological Causes of the Decay of a Nation, 1862, Xerographic Reprints, UMI, 2001, pp.6, 8.
[28] Benson Tong, Unsubmis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pp.27-28, 131; George Anthony Peffer,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 pp.73-86.
[29][39] Benson Tong,Unsubmis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pp.129-132、pp.132-133.
[30] Kerry Abrams, “Polygamy, Pro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05, No. 3, April, 2005.
[32] Yung,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41.
[37] Sucheng Chan(ed.),Entry Denied: Exclusion and the Chinese in America, 1882-1943,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96.
[40] George Anthony Peffer,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pp.34-36; Andrew Gyory, Closing the Gate, p.71.
[41] 关于议员佩奇在法案通过前的国会演讲及听证证人证词等内容,参见Kerry Abrams, “Polygamy, Pro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Law” , pp.692-694.
[42] Kerry Abrams, “Polygamy, Pro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Law”,Columbia Law Review,Vol. 105, No. 3, April, 2005.
[44] George Anthony Peffer, “Forbidden Families: E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Women under the Page Law, 1875-1882”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6, No. 1,Fall, 1986.
[46] George Anthony Peffer, “Forbidden Families: E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Women under the Page Law, 1875-1882,”pp. 31-32.
[47] George Anthony Peffer,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pp.57-72; Benson Tong,Unsubmis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pp.47-50.
[48] Kerry Abrams, “Polygamy, Pro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Law”,Columbia Law Review,Vol. 105, No. 3, April,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