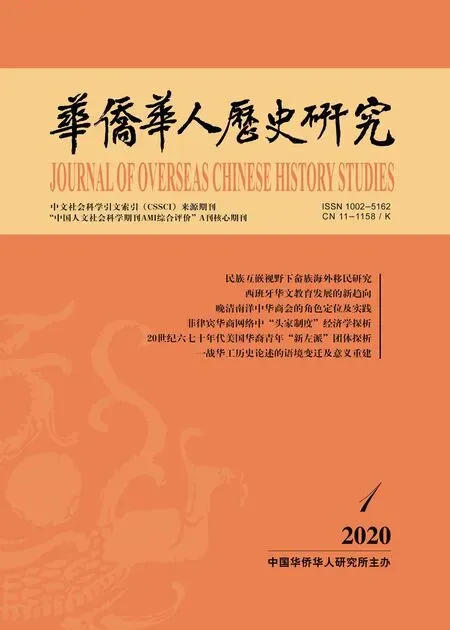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语境变迁与意义重建*
张 岩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一战华工”是个现代的称谓,意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俄三国为补充自身人力短缺,来华招募的数十万男性劳力。在历史上,该类华工则多被称作“参战华工”或“欧战华工”。由于俄国在十月革命后退出战争,此后提及一战华工多指英、法两国政府招募的、在西线战场工作的约14 万名华工,亦可称为“西线华工”。①至于一战华工数字问题,根据徐国琦教授的研究,西线华工人数约14 万,其中,英招华工约94,000 名,法招华工约4 万名;另据奥尔加(Olga V. Alexeeva)的研究,俄招华工数字难以明确,俄官方记录仅经西伯利亚铁路进入俄国的华工就达159,972 名,加上坐船赴俄的华工,人数会更多。见徐国琦著,潘星、强舸译,尤卫群校:《一战中的华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47~49 页;奥尔加(Olga V. Alexeeva):《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华工:战争的另类受害者》,魏格林、朱嘉明主编:《一战与中国:一战百年会议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年,第461 页。本文讨论的“一战华工”仅指“西线华工”。
目前,虽然学界围绕一战华工已积累了不少成果,但主要侧重“历史本身”,诸如一战华工的招募与交涉、工作与生活、贡献与影响等方面史实的重建,②相关著作可见第三节,此不赘列。在“历史论述”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③保罗J.贝利(Paul J. Bailey)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华工:一段被忽视的插曲,中国外交政策与现代劳工史的演变》(收入《一战与中国:一战百年会议论文集》,第477~493 页)一文对当代法国、中国一战华工的论述有所涉及,本文则更侧重探讨历史上中国方面相关论述的语境变迁与意义重建。。鉴于此,本文拟针对中国各类与一战华工相关的论述展开分析,阐述这些论述形成的特定语境及特定意义,并着眼于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语境变迁,探讨重建当代一战华工历史论述及意义的困境所在。
一、中国参战语境下的华工历史论述
参加一战的想法对于当时贫弱的中国而言包含了一种外交政治上的想象,即为维护和恢复中国自身权益,提升国际地位,提供了可供想象的空间。这种想象促成了一战华工历史的第一次建构。
(一)中国在华工招募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形塑
英、法两国来华招工始于1916 年。此时中国尚处“中立国”地位时期,作战一方在华进行大规模的招工难免不带有某种外交敏感性。故此,北京政府对待招工表现殊为谨慎。就起步较早的法国招工而言,时任北京政府税务督办的梁士诒与法国官方代表密商,采用了民间运作的方式进行招工,具体即由前者成立招工公司——惠民公司——为后者代招工人,双方在1916 年5 月14 日签订了一个民事关系的合同,而北京政府表面上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批准他们之间的合同。④围绕法国招工中、法双方的交涉,详见陈三井:《华工与欧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年,第15~19 页(该书简体版由长沙岳麓书社2013 年出版)。然而,在1916 年6 月,袁世凯政府垮台,梁士诒以帝制祸首之名被通缉,之后的政府并未认可与延续袁政府的外交理念与招工政策。1916 年11 月,伍廷芳就任外交部长以后,更是尽可能地让政府处于超然地位,在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不做左右偏袒,即既不禁止招工,开罪于协约国一方,也不介入招工,授同盟国以口实。后继来华招工的英国政府,所订招工合同就未能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因此,英国的招工严格来讲属于“私招”。⑤详见张岩:《一战华工招募与中英交涉(1916—1919)》,栾景河、张俊义主编:《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409~444 页。伍廷芳援引国际公法以作为政府处置依据。1907 年《中立国和人民在陆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第六条规定,“中立国对某些个人独自越境为交战国一方效力的事实不负责任。”[1]比照此一条规,华工应募前往协约国工作属于不带国家、政府色彩的个人行为,原则上不会构成违反中立的行为,在国际法上确实可以打擦边球。但北京政府出于保护国民的考虑,也并非完全置外人招工于放任不管。1917 年1 月30 日,外交部向涉及招工的省份发过一道密令,即“外人来华招工一任人民自由应募,官府不加以干涉”,由地方商会出面代政府办理(主要是议定合同),“表面上虽纯由地方商会办理,而实际上则仍由地方官默为主持”。[2]当然,地方政府在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3]
北京政府决定参战之际,一度有意改变其在英、法华工招募过程中保持缄默的角色。1917 年2、3 月间,北京政府在讨论对德奥参战案时,曾考虑把“供给(或‘补助’)华工”作为中国的一项“参战义务”。[4]但主战派内部在中国“参战程度”,即是否出兵问题上发生分歧,对“供给华工”可多大程度上作为“参战义务”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反对出兵的一方认为,按照中国当时的国情国势,似没有能力出兵远征,只能依靠“供给华工”等方式间接补助战事。[5]而力主出兵的段祺瑞则坚称,由于“华工本已成为事实”,因此,仅把“供给华工”作为参战义务“亦不鲜商量余地”。[6]
1917 年8 月,中国政府对德奥宣战,其在中立问题上的顾虑相应消除,作为参战国成员,接下来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履行“参战义务”的问题。但最终北京政府也没有遣兵赴欧,且亦未能以政府名义主动派遣或供给华工——仍延续此前的政策,任由英、法两国在华自行招募华工。不过,即使北京政府在招工问题上失之于主动,“一战华工”仍在客观上尽到了中国参战的“义务”。正如曹汝霖回答段祺瑞“以何参战”之问时讲的那样:“华工去了将近十万,虽非正式派遣,总是华工,这亦是武器,为参战的资本。”[7]
到大战结束前后,为增加外交筹码,争取协约国支持,尤其是当北京政府遭遇协约国对华提出的“参战不力”的指责之际,中国方面开始主动尝试建构其在华工招募过程中主体地位的论述。这些论述的建构形式大致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是北京政府开始建构其在招募华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该层面的论述主要立足于北京政府当初默许(未禁止)英、法在华招工这一点。例如,1918 年10 月29 日,在大战行将结束、协约国胜利在望之际,北京政府发布了一条《大总统布告》,历数中国自参战以来对于协约国所尽义务,其中有一点便是“允准大批华工前往欧洲尽力于备战之工作”[8]。此外,也有人就建构该层面的论述献议如下:
是中国力助招工往法,即参战之力也,而战场上又实获华工之巨效。[……]或谓此英、法自行招募,我国无与;[……]我政府不惟不下令禁止,且设局助其招募,即为我国参战之力之一证。[9]
此献议中提及“设局助其招募”,这一内容应指北京政府曾针对华工招募设立侨工事务局之事。实际上,该事务局并没有真正帮助外国招工,其职能只是“监督侨工之招募及保护事务”[10]。
其二是中方招工代理公司——惠民公司——试图建构其在招募华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需要说明的是,惠民公司并非法国起用的唯一招工公司,但却是唯一受北京政府批准招工的中方公司。据对天津惠民公司的调查,其每招募并交付一名华工,就可以得到法方140 法郎的费用。最终,其所招华工人数达31,656 人,约占法招华工总数的79%,占英、法所招华工总数的23%。[11]
继前述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后,惠民公司代表梁汝成等人随即于1918 年11 月20 日向国务院侨工事务局呈交了一份“办理华工赴欧助力参战实绩”的报告,请求政府予以“奖励”并将惠民公司的事迹“公布”于国人。该报告力图构建惠民公司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表明其招工活动并不纯粹是民间商业行为,惠民公司幕后的指使人实际是北京政府。其中写道:
民国五年,欧战方兴,梁君士诒、曹君汝霖、叶君恭绰等逆睹潮流之所至,默查友邦之所需,预谋我政府他日国际上地步起见,当秉承政府意旨,密以私人资格,力求所以助我协约友邦战事上之补助者,因思战斗实力以人为本,而吾国人之宜于工作,又为列邦所称,故特创惠民公司,募集工人,为协约各友邦后方工作之举。[12]
此时,梁士诒业已被取消通缉并重回北京政治舞台,招工之事无疑是他政治上的加分项。日后,梁汝成又进一步将梁士诒等人提出的招募华工参加一战的构想概括成“以工代兵”参战策略,成为论证中国在华工招募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关键证据。[13]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策略的真实存在,但认为梁汝成的描述夸大其词。按梁汝成的说法,梁士诒等人至迟在1916 年初①1916 年1 月,法国招工团已来华招工,5 月4 日即与惠民公司签订招工合同。见陈三井《华工与欧战》,台北:“中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年,第15~16 页。便已预测到德国的败局,因此,应与协约国一方站队。但这一预测的依据却难以让人信服,就1915—1916年初大战的形势而言,交战双方正处相持状态,胜负难分,战争的结果实难预料。②丘吉尔曾经回忆道,假如德国1917 年不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就能够在当年“满意地媾和”。可见梁士诒在1915—1916 年初就能预测大战的结局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参见:[英]温斯顿·丘吉尔著,刘精香译,吴良健、吴衡康校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 年,第679 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工代兵”的描述当中却没有提及曹汝霖的名字。这可能与“五四运动”之后曹汝霖名誉扫地有关,而曹汝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及自己参与过为政府办理招工的筹议。③曹汝霖仅提到:“当欧战紧急之时,法国公使康悌曾与梁燕孙(注:梁士诒)密商,以法国人工缺乏,拟招华工赴法,不加入战事。燕孙以华工出洋,恐招物议,遂设惠民公司,秘密进行。”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 年,第197 页。在上述报告提出时,曹汝霖正代替梁士诒担任交通银行的总理,因此上述报告将曹列入其中,难免给人以趋炎附势之感。
惠民公司不仅试图建构其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还强调公司自身的国家身份,间接重建了中方在招募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举国上下莫不欢欣鼓舞。惠民公司这时也附和舆论形势,举办了一场庆祝协约国胜利的茶会。茶会的邀请发起人为梁士诒、叶恭绰等。茶会召开前,惠民公司在报刊登载了一则告示表明茶会召开的目的,即该公司“倡募华工,涉险赴欧,间接助我,卒收今日效果,际兹庆祝。”[14]1918 年11 月23 日下午,茶会召开,与席的中外各界人士计有一千余名。公司总理李兼善在开会词中特意强调了惠民公司对协约国“尽心助力之热诚”,希望“协约友邦对于我国之工商实业日益相助”。[15]可见,这次庆祝活动主要针对的是工商界人士,旨在推动协约国帮助中国的工商实业,其中自然包括交通系控制的铁路和交通银行。故而李兼善并未强调惠民公司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而是将惠民公司定位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
此外,惠民公司就其招工缘起还提出过另外一套论述。1918 年3 月,该公司出版了一本《华工赴法》的报告,称国家贫困的原因在于游民过多,而招募华工正是减少及改良国内游民的捷径,游民出国之后可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赚取外汇、见识欧洲文明,获利颇多,此即惠民公司名称的本意,即“纯为国民谋生之计”而设。[16]这套说法究竟是游辞巧饰,还是确有其意,实无从考证。但此说遮蔽了其盈利的目的。旅法华工会领袖袁子贞对惠民公司的招工发表了相反的看法:“吾国一般官僚政客,交通系如梁士诒、叶恭绰等,素注目投机事业,今借法国需用工人甚急,于是乘机而起,来包办这项洋行买卖,随成立了一个惠民公司。”[17]
综上而言,受当时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的影响,北京政府在华工招募过程中并未能充分发挥主动性。最初,梁士诒一派的招工活动虽说间接代表了政府,但自1916 年6 月北京政府与梁士诒做出切割之后,梁的招工活动也就变为私人行动。大战结束前后,北京政府与惠民公司对各自在招工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的论述,既出于对国家利益的争取,也不免源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中方包括政府与民间组织在招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为日后华工史的叙述提供了多重可能。
(二)华工之参战角色的形塑
1917 年8 月,中国政府对德奥宣战之后,赴法华工的身份客观上发生转变。他们不再仅是附属于招募国家的契约性质的劳力,而是变成中国派往协约国的“参战代表”。到大战结束,中国获得战胜国身份后,华工更被认为是国家的“功臣”。华工参战角色的论述也由此产生。有关华工参战角色的建构主要着眼于两个层面,即华工的应募动机及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就华工的应募动机而言,大多数华工选择出国是为了自身和家庭的生计,并不存在协助协约国战争事业与承担中国参战义务的主观意图。[18]但在中国参战以后,华工不仅被认为,且自认为是中国的参战代表。在表述上,华工的应募动机被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是一首写于战后的《华工出洋歌》,它将华工的应募动机描述为:“我工人,冒险而至,一为众友邦,二为自己,中华人,最爱好名誉。”[19]
不仅如此,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份宣传材料也存在相似的说辞:“吾国人民亦素怀急公好义之热忱,识此为维持和平之必要,刻不容缓。是以不畏强御,不顾危险,抛妻子,别父母,亲历海洋,远越异域[……]尽力为联军助战。”[20]这些表述大抵是青年会干事或某些知识分子为了塑造华工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而提出,当然,也不能否认某些华工在国外接受一定宣传和教育之后,①北京政府教育部就曾试图对华工施加此类教育,见傅增湘:《侨工须知》,1919 年,第58~59 页。认识到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与神圣性,由此会自发地产生如上论述。
围绕华工对国家所作贡献而建构的论述主要涉及华工为中国所尽“参战义务”。山东华工蒋镜海在旅欧期间记下了一篇名为《恭颂旅欧华侨诸同胞功德》短文,其中讲到:“我国加入战团,以固国本。我辈效力欧战,为国增光。不避枪林弹雨,何畏电火飞艇,直接助战,宿露卧风。卒致欧战告终,还我文明,联邦各国,中原策功,伊谁之力,吾数十万华工。”[21]追溯蒋镜海旅欧的心路历程,不难发现,他在赴欧之前并不存在对个人工作与国家利益关系的考量,②其应募动机只是为了赚钱养家,如其在笔记中写道,“十块洋(注:每月安家费)合京钱廿余吊,我家中有几口能度光阴”。但在中国参战以后,蒋镜海把自己从事的工作与国家的“参战义务”联系起来,从而把对自身角色的认识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在中国举国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氛围之下,华工对国家和世界所作贡献也为社会舆论所肯定。11月16 日,蔡元培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讲,对华工的贡献大加称赞:“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22]
中国得以列席巴黎和会及此后在华盛顿会议上收回部分利权,某种意义上不能不承认是拜华工参战所赐。梁士诒年谱曾引述梁汝成的说法,称:
尔时(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陆征祥以前任外长资格,在欧洲声言:“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炸弹,制枪子,无论在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侃侃抗争。各国代表皆为色动,遂定下帖设座之议。至民国十年,华盛顿会议,陆征祥、顾维钧二氏(注:此说不确,此时陆已经退出外交舞台),为中国争回国格,亦以二十万华工为武器也。[23]
除梁汝成以外,华工代表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此不赘列。[24]然而,究竟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有无提及一战华工?1919 年1 月13 日,在和会开幕前夕,北京政府专门向和会代表陆征祥电达了一份参考书,列述了中国尽力欧战的事实,以备参会代表在和会提出意见时参考。该参考书关于华工部分表述如下:
欧战以来,我国派赴欧洲之华工为数甚夥。[……]此等华工所以补助协约国人力之数甚大,盖此等人物并非全为寻常之劳励者,其中有各种手艺之机器匠,战线后方各项制造事业皆有华工参与。其间又因从事工作身罹死亡者甚多,在受敌人飞艇之攻击或在敌人炮火之下其所尽之责任几同于作战之兵士,此吾国所尽力于工业者。[25]此部分内容与梁汝成的表述多有不同。
在正式公开的档案记录中,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及华工的部分目力所及仅有以下一条:陆征祥向北京汇报会议状况的一则电文中提到,1919 年1 月25 日,和会所议五项议题中有一条涉及“规定劳动家之法律”,而中国却被限制列席讨论,为争取参与此项国际劳动立法,陆征祥于是辩称,“中国工人在英、法方面工作不下十五万人,战事结果,华工间接出力不少,应请加入”。[26]遗憾的是,此番辩论并未能影响和会的结果。以上梁汝成与华工代表之所以强调华工的外交贡献,实际具有特定的指向:前者是借华工来展现梁士诒等人的贡献,后者则是为了呼吁政府安置归国华工。
在1919 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实则遭遇到了“战败国”的待遇,当人们从战胜的喜悦中清醒过来,华工所作贡献也就不再为社会舆论所热捧。正如鲁迅所讲:“我们那时的所以入战胜之林者,因为曾经送去过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欧战的劳绩。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战胜也忘却了,而且实际上是战败了。”[27]
二、社会革命语境下的华工历史论述
以上中国参战语境下的华工论述着眼于国家视角,带有与生俱来的矛盾,这种矛盾源自华工的客观贡献与主观意图并不尽能统一;政府在华工招募及归国安置的过程中有所缺位或失位,如果强调政府在“供给”华工参战方面具有远见卓识与华工对于国家的贡献,何以政府在华工招募过程中置身事外,在华工归国之后不予妥善安置?20 世纪40 年代一则评论梁士诒年谱的短文讲道,梁氏一生“最贻人口实者,为洪宪筹安、华工参战两事”,“编谱者于后事则谓凡尔赛和会中国所以得争回国格,端赖华工赴法一节。而于此二十万华工之遭遇,则只字不提;不教而战谓之弃民,乃云可争国格,亦善于说词者矣”。[28]这体现的正是国家视角与华工视角之间论述的张力所在。就华工视角的论述而言,最为典型的是一战结束后社会革命语境下的华工历史论述。本文所谓社会革命语境指的是反军阀、反帝以及既反帝又反军阀(以下称“反帝反军阀”)三种形式的语境。
(一)反军阀语境下的北京政府暗卖华工说
“一战华工”当中不乏致力于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革命人士,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吴世英。吴世英,湖北武昌人,毕业于法政大学,曾参与武昌起义。后借英、法招募华工之机出走欧洲。1921 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政府召见吴世英(吴三民),拨助其千元经费,并“面受方略”,在上海成立驻沪参战华工会,以招待归国华工,接受“党化训练”,参加革命运动。[29]这就注定了该会的宗旨便是如此。驻沪参战华工会为法国“旅法华工会”的国内改组机构,由吴世英担任评议长。[30]截至1923年初,该会会员已经发展到1 万8 千余名,并且在南京、汉口、杭州、潮州等地都设有支部。[31]
驻沪参战华工会成立不久,就在报刊发表了一篇宣言,公开指责北京政府的种种“罪行”,呼吁国人“自决互助”,在北京政府与西南政府之间做出选择。[32]1921 年12 月,梁士诒上台组阁担任国务总理后,孙中山随即于次年1 月9 日以大总统名义下令通缉梁士诒等人。驻沪参战华工会这时在报刊登文“痛骂”梁士诒,称梁士诒的招工行为实为“暗卖”华工,并对之表示“深切痛恨”。另外,当驻沪参战华工会听闻华工某代表向北京政府侨工局请援之后,更是反对称:“参战同人既为北庭暗卖,是北庭显然为吾侪之仇敌,反对犹恐不及,岂有乞援之理。[……]似此行为为北庭利用,毁坏同人名誉是可断言。”需要说明的是,驻沪参战华工会反军阀立场坚定,但并不存在反帝的取向,反而认为法国政府对待华工至优,且允许华工加入军事范围,因此对之还心存感激。[33]
(二)反帝语境下的帝国主义压迫、背叛华工说
1925 年5 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并由此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运动。这时,《晨报副刊》①由于《晨报副刊》的母报《晨报》依附于北洋军阀,因此,《晨报副刊》在政治立场也不会带有明显反军阀的色彩。连载了一篇名为《巴黎和会中之华工》的文章,其所描绘的如同是另外一个时空中的“五四”场景。文章特意描写了华工的爱国举动以及英国和日本对华工的虐待与镇压,实际隐喻的是日本伙同英国制造的五卅惨案,以此号召工友再次团结起来,进行反帝爱国的运动。[34]
1931 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政府随即以日本违背1922 年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等项国际公约,向国联提出控告。在此背景之下,“一战华工”又一次被提起。该次有关华工的论述便主要围绕华工与《九国公约》的关系展开。1932 年12 月1 日,《申报》登载的一则消息称:
参加欧战之华工签约全权代表梁汝成,为力争《九国公约》信用来京,访美、法两使,述二十余万华工参加欧战,死亡失踪者不下六万余人,以碧血换来之《九国公约》,今已为日本破坏无余。法为直接援助国,美为《九国公约》盟主,若不援引公约严厉制裁日本,则美、法威信何在。两使对梁陈述颇注意,已请梁用书面陈述,俾转达本国政府。[35]
然而,美、法等国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1935 年,梁汝成又向国民政府建议设立“一战华工纪念塔”,将《九国公约》镌刻塔上,以此“警告列国,使其负疚神明”。[36]到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有关华工与《九国公约》的论述再次被人提起。白蕉在1937 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世界大战中之华工》的长文,写到文末,他对于时势不无感惧地叹息:“今三十万华工赴欧参战,以碧血换得之《九国公约》且被撕坏矣,我人倚赖国联,国联其能坚持之乎?”[37]虽然这种论述把华工与《九国公约》联系在一起显得比较牵强,但却反映了中国对待西方态度的转变。然而,当时国民政府并不认可以上说法,指出华工虽然参与协约国重要工作,但在休战后此工作业已结束,《九国公约》是在此之后签订,因此二者不存在直接联系,梁汝成的提议“设想迂远,无甚意义”[38]。
(三)反帝反军阀语境下对华工命运、境遇悲剧性的揭露
反帝反军阀话语下的华工论述主要出现在20 世纪60 年代,老华工白宝纯在1965 年出版的家史便是最好的例证。[39]该书是为呼应“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展现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压迫阶级的控诉特意撰写的。在这种语境体系之下,华工成为劳动人民这一阶级群体的代表,而当时代表中国的北京政府以及英、法两国政府则被视为与劳动人民对立的阶级。“华工招募”因此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两个反动阶级合谋贩卖劳动人民的行为。[40]学术界也出现了相同的看法。蔡夏认为,梁士诒“以工代兵”策略是“旨在牺牲中国人民”的“向帝国主义输诚效劳”的政策,背后实际隐藏着“企图诱骗广大劳动人民为帝国主义战争服劳役、充炮灰”,“赚取高额酬金,大发横财”的“罪恶目的”。[41]这与上述一战结束前后的华工招募论述可谓大相径庭。
这类论述对帝国主义罪恶形象的刻画尤为深刻。如书中一例,对于那些因逃跑而被编入“囚犯队”的华工,英国工头不仅专挑重活累活让他们干,而且为折磨他们,还使用了“狠毒的刑罚”。[42]所谓的“西方文明”也被彻底唾弃。白氏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名叫刁庆祥的学生“以为外国人文明”,“只要能上趟外国,就好比身上镀了一层金”,于是报名充当华工翻译,到了国外才体会到“帝国主义有什么文明?光会哄骗人、剥削人、压迫人、打骂人、屠杀人”。[43]显然这些观点把资本主义的野蛮性、罪恶性做出了深刻的揭露,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两面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复杂性做了简单的否定。
三、当代改革开放语境下的华工历史论述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革命话语在社会话语体系当中的一元性地位逐渐瓦解,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对西方文明与资本主义价值有了全面、深入的认知。经历这样一个转变,有关华工历史的正面论述也就没有理由不被接纳——只是存在何种意义上、何种程度上被接纳的问题。华工历史所呈现的中国现代化、国际化的元素和改革开放的现实可以直接对接,华工历史由此展示了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直接的现实意义。
对一战华工历史意义的重新发现,应该说是由西方官员、学者及华侨华人首先敏感地意识到的。以法国侨界为例,他们自20 世纪80 年代起就开始发起一战华工纪念活动。至1988 年11 月即一战停战70 周年纪念之际,华裔融入法国促进会促成了一次隆重的华工纪念仪式。是次仪式上,法国总统代表、邮电和航天部长保罗·基莱斯不仅为华工纪念铜牌揭幕,且向两位健在的华工颁发了法国级别最高的勋章——“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成为一战华工纪念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人民日报》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并引述基莱斯的一句致辞,称此次活动“是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阵亡的华工致敬,亦是对一项遗忘的补偿”。[44]基莱斯的致辞说明法国官方承认了华工对法国历史所做贡献。此种论述侧重华工的族群象征意义的表达,有益于提升法国华侨华人的历史地位,促进华裔进一步融入法国,增进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且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也不乏积极的意义,从华工的国家象征意义层面,它可以被解读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及国际地位提升的表现,也是中法友谊加深的象征。①早在1987 年,《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记者凭吊华工墓园的文章,称华工墓园是“旧中国国势孱弱、民不聊生的千古不泯的印证”,认为此时不乏外国人前去悼念,是中国“国力的不断强盛以及中法交往增加”的表现。参见:《亡灵节吊华工墓》,《人民日报》1987 年4 月5 日,第7 版。
此后,法、英、比等国纪念一战华工的活动以及官方针对一战华工的讲话层出不穷。特别是在2018 年一战结束一百周年之际,1 月8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西安大明宫的演讲中特意向一战中支援法国的华工致敬,称他们是法国“危难时刻的兄弟”。[45]11 月11 日,在由法国官方举办的一战结束百年纪念仪式上,一位华裔女孩朗读了华工翻译所撰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进一步显示华工是一战纪念不可忽视的因素。举凡这些纪念与讲话,主旨都在追认华工为西方国家做出的历史贡献。中国官方曾借此回应过当下的问题,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就利用“欧洲领导人也意识到当年华工为欧洲的和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证明欧洲国家与中国存在加强合作的意愿。[46]在2018 年4 月法国侨界举办的一战华工祭奠仪式上,中国驻法大使也曾借纪念一战华工的契机,表达中国“维护和平的决心”与“实现民族复兴的誓言”。[47]
西方学界对一战华工历史的关注更早一些。1973 年,俄克拉荷马大学博士生尼古拉斯(Nicholas John Griffin)在参考英国陆军部、殖民部、基督教青年会等机构档案的基础上撰写了学位论文《1916—1920 年英国军队对中国劳工的使用——所谓“原装进口”的范围和问题》。[48]中国学界从事一战华工研究的主要是在港台地区。1986 年,台湾学者陈三井利用北洋政府外交部,法国外交部、陆军部等方面的档案出版了《华工与欧战》。[49]现任教于香港大学的徐国琦教授曾在1999 年撰成其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纯真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寻求国家认同》,[50]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专著《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51]其中的一个章节即涉及到了一战华工。之后,他于2007 年出版了专著《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52]于2011 年出版英文专著《西线战场的陌生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劳工》。[53]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格雷戈里(Gregory James)亦于2013 年出版了一本专著《一战华工(1916—1920)》。[54]
比较来看,西方学者侧重从西方的历史脉络讲述一战华工历史,而陈三井教授与徐国琦教授则侧重以中国为中心探讨这段历史,特别是关注中国在华工招募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华工对中国的贡献。两位学者均认为:其一,中国政府在华工招募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即华工赴欧系由中国政府派遣,依据便是上述梁士诒的“以工代兵”策略;其二,华工为战后中国提升国际地位、争取国家权利做出了贡献。徐教授更是进一步从中国国际化的角度,探讨了华工在中国在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以及国际化中的贡献,认为华工是“中国放眼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社会的先行者”。[55]
这类论述似乎接续了前文中国参战语境下的华工论述,二者都是立足于国家视角,且内容上不无相似之处。但当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一战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或许只有在当代这样一种语境下,我们才能够理解华工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以及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2009 年,中央电视台制作并播放了一部华工纪录片——《华工军团》,主题即参照徐教授《文明的交融》中的相关论述,其对华工评价道,“(华工)扮演的角色,并不是普通劳工,而是北洋政府外交斡旋的赌注,他们对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政局和国际地位,居然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56]此外,该片上映时间正值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故着重强调了华工与五四运动之间的联系,认为华工“和北京、上海的青年们,同样是五四运动的先驱者”。[57]
尽管过去的革命语境已然消解,但华工视角的论述并不会销声匿迹。陈三井教授一方面强调华工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指出华工在归国后却没有得到“政府应有之恤悯与社会各界广泛之同情”,因此对华工而言就是一个悲剧。[58]巴斯蒂教授亦特别强调,华工的经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集体角色与集体命运”,他们不过是历史的次要角色,并且在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们“不知不觉地被当成了工具”。[59]可见,这种个体视角的论述依然不失为国家视角论述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视角,两种视角之间的张力仍然突显,这不仅仅是由历史论述造成的,也有历史本身的原因。
四、结语
一战华工是探讨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题材,在中国当代语境之下,该题材的现实意义愈显突出。加之受上述海外相关纪念与研究的影响,一战华工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三本华工著作《华工与欧战》、《一战华工在法国》、《一战中的华工》陆续引入大陆出版,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属单位五洲传播出版社曾于2017 年1 月专门出版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专著《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华工的故事》。两部华工纪录片《华工军团》、《潜龙之殇:一战中的华工军团》分别于2009 年与2016 年在央视上映,一个华工纪念馆于2020 年在威海落成。新语境下中国重建一战华工论述面对的困境仍然是隐含在两类论述——国家角度与华工角度——之间的内在张力。而要消除这种张力,或许可以从社会史或有学者提议的中国劳工史的角度回避外交政治话语进行论述,但要直面这种张力,还是应把握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即历史上两类论述建构的过程与存在的问题,设法平衡华工的客观贡献与主观意图、个体境遇之间的矛盾,这是大陆当前建构一战华工新论述应该注意的问题。
[注释]
[1] 《发驻英施公使函》(1917 年8 月29 日),陈三井、吕芳上、杨翠华主编:《欧战华工史料1912—192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494~495 页;《中立国和人民在陆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郭金才主编:《世界通鉴:影响人类生活的一百个国际公约》,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 年,第37~42 页。
[2] 《发沿江沿海东三省各督军省长密函》(1917 年1 月30 日),陈三井、吕芳上、杨翠华主编:《欧战华工史料1912—1921》,第20 页。
[3] 张岩:《一战华工招募与中英交涉(1916—1919)》,《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上卷,第409~444 页。
[4][5] 《对德奥参战》,张国淦著,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年,第153~197 页。
[6] 《段总理宴国会议员》,《大公报》1917 年5 月4 日,第2 版。
[7]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第168~169 页。
[8] 《政府公报》第991 号(1918 年10 月30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政府公报》(影印本)第134册,上海:上海书店,1988 年,第791~792 页。
[9] 《对于欧洲和平会议之献议》(1919 年2 月27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7-007-03-033。
[10]《侨工事务局暂行条规》,《东方杂志》第14 卷第10 期(1917 年),第202~203 页。另一种可能就是指成立惠民公司。
[11][58] 陈三井:《华工与欧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年,第25~29、190 页。
[12]《政府公报》,第1023 号(1918 年12 月2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政府公报》(影印本)第136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8 年,第40 页。
[13][23]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年,第299~300、301~302 页。
[14]《惠民公司举行庆祝茶会》,《益世报》1918 年11 月15 日,第2 版。
[15]《惠民公司庆祝会》,《大公报》1918 年11 月24 日,第6 版。
[16] 惠民公司:《华工赴法》,1918 年,第1~2 页。
[17] 袁子贞:《旅法华工会的经过》,《工人旬报》第21 期(1923 年五一纪念号),第9 页。
[18] 张岩:《光环之下的个体世界:一战山东籍华工应募动因考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 年第2 期。
[19] 威海市档案局,档号:229-001-0298。
[20] 驻法华工总青年会编:《驻法华工队青年会事业略说》,Paris:Herbert Clarke,1919 年,第9 页。
[21]《蒋镜海笔记》,此笔记由蒋镜海嫡孙蒋德山先生收藏。
[22] 蔡元培:《劳工神圣》,《新青年》第5 卷第5 期(1918 年),第438~439 页。
[24]《山东欧战华工之呼吁电》,《大公报》1923 年6 月14 日,第6 版;《山东欧战华工之呼吁电》(续),《大公报》1923 年6 月15 日,第6 版。
[25]《政府电致陆使之参考书 我国对于欧战尽力之经过》,《大公报》1919 年1 月14 日,第6 版。
[26]《法京陆专使电》,1919 年1 月2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主编:《秘笈录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70~71 页。
[27]《补白》,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第104 页。
[28]《图书介绍: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凤冈及门弟子编)》,《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 年第1 期,第161 页。
[29]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2 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 年,第185~186 页。
[30]《参战华工会通电释谣》,《申报》1923 年1 月28 日,第14 页。
[31]《驻沪参战华工会分设支部》,《申报》1923 年1 月18 日,第13 页。
[32]《参战华工会对内宣言》,《申报》1921 年10 月28 日,第14 页。
[33]《驻沪参战华工会通电》,《申报》1922 年4 月22 日,第13 页。
[34] 赵信天:《巴黎和会中之华工》,《晨报副刊》沪案特号(1925 年),第63~64 页;《巴黎和会之华工》(续),《晨报副刊》第1220 期(1925 年),第31~32 页;《巴黎和会之华工》(续完),《晨报副刊》第1221 期(1925年),第37~39 页。
[35]《华工签约代表梁汝成访英法两使》,《申报》1932 年12 月1 日,第8 页。
[36][38]《外交部致行政院秘书处》,1935 年2 月23 日,台湾“国史馆”:《留法参战华工救济(三)》,数位典藏号:020-990600-3116。
[37] 白蕉:《世界大战中之华工》,《人文(上海1930)》1937 年第8 卷第9/10 期,第67~68 页。
[39] 白宝纯口述、高锴等整理:《六十年悲欢》,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 年。
[40][42][43]白宝纯口述、高锴等整理:《六十年悲欢》,第18、22、26~27 页。
[41] 蔡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服军事劳役的华工》,《历史教学》1963 年8 月。
[44]《里昂车站立铜牌 纪念参战华工 法国政府致敬意 授勋历劫骑士》,《人民日报》1988 年11 月29 日,第6 版。
[45]“法国总统在大明宫的演讲”,法国驻华大使馆网站:https://cn.ambafrance.org,2019 年8 月6 日访问。
[46]“2018 年11 月14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613056.shtml,2019 年8 月7 日访问。
[47]“驻法国大使翟隽在一战华工墓园清明祭扫仪式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dszlsjt_673036/ds_673038/t1549939.shtml,2019 年8 月7 日访问。
[48] Nicholas John Griffin, “The Use of Chinese Labour by the British Army, 1916-1920: The ‘Raw Importation’, Its Scope and Problem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73.
[49] 陈三井:《华工与欧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年。
[50] Guoqi Xu, “The Age of Innocenc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51] Guoqi Xu,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译版:徐国琦著、马建标译:《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
[52] 徐国琦:《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 年;修订版:徐国琦:《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华工的故事》,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 年。
[53] Xu Guoqi,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徐国琦著,潘星、强舸译:《一战中的华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54] Gregory James,The Chinese Labour Corps(1916-1920),Bayview Educational, 2013.
[55] 徐国琦:《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华工的故事》,第9 页。
[56][57]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华工军团》,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 年,序言。
[59] 巴斯蒂:《华工归国:为世人留下什么遗产》,马骊编著、莫旭强译、胥弋校:《一战华工在法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 年,第46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