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星故事(四)
刘超
“现代化学之父”的诞生
在化学历史上,拉瓦锡对于发现氧气顺序的描述的确有失大家风范,他曾公开宣称:氧气是普利斯特里和舍勒与我大约同时发现的。他还曾拒不承认收到过舍勒的来信。但在1790年,拉瓦锡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不得不承认在发现氧气的顺序上,自己确实晚于普利斯特里和舍勒,并且在一些论文上确实有杜撰和弄虚作假的成分。
我们无法从道德的视角评判一位科学家的是非对错,但从能查到的记录、史料和专著中的描述,可以总结出:拉瓦锡的诸多成就中,有许多结论是在重复他人实验的基础上得出。但值得肯定的是,他所重复的这些实验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重复工作,而是将这些实验结果相互结合建立起了新的理论体系。波义耳、卡文迪许、普里斯特里和舍勒等人只是制出了砖瓦,而用这些砖瓦建成大厦的则是拉瓦锡。德国科学家李比希由此总结道:“拉瓦锡没有发现过任何新的物体、新的性质和未知的自然现象,他的不朽的光荣在于:他给科学的机体注入了新的精神。”
平心而论,拉瓦锡之所以成功,靠的并不是更加勤奋和实验能力。论勤奋,他不如卡文迪许;论实验能力,他不如英国化学家布莱克。很显然,是传统的错误观点遏制了卡文迪许和布莱克的才华。由此可见,对科学家来说,勤奋、动手的能力都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还要有一个善于科学思维的头脑。
18世纪的化学,如同刚从母体孕育出的婴儿,母体的印记是那么的清晰。当时,化学界对物质的命名以及所使用的化学符号,在现在看来是如此的原始,这完全是对之前炼金术的延续,蒙昧之极。这些名称和符号含混晦涩,充满着怪异,已经脱离了物质本身。随着新的物质和元素被不斷发现,命名方法必须系统化和科学化,这便是当时有化学家认为化学界应最先解决的当务之急。这个人就是居顿·德莫沃。
德莫沃是拉瓦锡的好友,年长拉瓦锡6岁,是一位在化学界颇具建树的化学家,他创办的工厂首次实现了法国的工业化制碱。在一次科学家的聚会中,德莫沃将想组织一批化学家对化学命名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和规范的想法与拉瓦锡进行了畅谈,得到拉瓦锡的坚决支持。随后,德莫沃又邀请了伯托利特和福克鲁瓦2位著名科学家一起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伯托利特是第一位接受“氧化学说”的法国科学家,而福克鲁瓦也在较早时候开始支持拉瓦锡的学说。因此,团队中的几位合作者之间就有了共同处事的基础,而事实也证明了,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在系统科学的近代化学命名体系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个团队虽由德莫沃发起,但在之后几人的合作中无疑都由拉瓦锡扮演了主要领导者的作用。1787年,几位科学家共同的研究著作——《化学命名法》出版,这部书对化学物质的命名法则进行了规定:每种物质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单质的名称要尽可能表达出其特征;化合物的名称必须根据所含单质表示出其组成;酸类和碱类用所含元素命名,盐类用构成其的酸碱命名;过去称为金属灰的物质,改为“金属氧化物”;矾油或钒酸改成“硫酸”。
《化学命名法》为后来化学物质的科学命名提供了理论支撑,其规定的许多化学命名方法依然被现在化学学科沿用。近代化学于19世纪传入中国,徐寿等一批开明化学家翻译的中文化学元素和物质名称也是根据《化学命名法》的规定进行翻译和造字。
拉瓦锡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化学之父”,不只因为他推翻了统治化学界很久的错误学说,建立了对自然界认识更加深刻的新理论,更在于他的科学思想让一个学科产生了本质变革,掀起了一场化学史上的重要革命。这场化学革命则成为化学学科“现代化”的转折。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狂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凝聚了拉瓦锡毕生的化学思想著作——《化学基础论》 (又译为 《化学纲要》,见图7) 问世,这部著作从提纲的形成一直到完稿,历经12年,这部在世界化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帙之于化学的意义,丝毫不亚于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于物理学和达尔文《物种起源》之于生物学。《化学基础轮》总结了拉瓦锡对化学的全部研究成果,详尽阐述了推翻“燃素说”的各种实验和关于燃烧的“氧化说”理论,对各种化学现象都提出了作者富有真知灼见的见解。但书中也有在现在看来不免具有很大局限性的论点,如书中提到“所有酸类都含有氧元素”的认知局限却让之后数十年的化学界颇为困惑。瑕不掩瑜,科学家对自然的认知存在局限性是在所难免的,但他们对人类提升对自然界的认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可磨灭。
革命洪流中湮灭的科学巨人
写到这里,拉瓦锡的人生似乎到达了巅峰,按照正常的“剧本”设计,他该功成身退了,在余下的生活中即使不扑在科学研究中,以之前的成就靠“吃老本”大可风花雪月,享受人生。但是,“完美的人生”只是传说,命运让拉瓦锡的人生辉煌就此打住,一场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洪流绝情地收割了他的生命。遗憾的是,布鲁诺被烧死后还被称为“殉道者”,而拉瓦锡只是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牺牲品”。
当时的欧洲,封建国家已呈摇摇欲坠之势,在法国之前,荷兰、英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法国的统治阶级为了避免重蹈英、荷的覆辙,更是加强了对权力的的掌控。皇族、贵族、高级僧侣等为代表的的统治阶级长期以来的骄奢淫逸掏空了国库,为了延续这种奢靡生活,他们开放“包税”种类以增加国家收入,这才有了拉瓦锡获得包税权的机会。中世纪法国的包税制度诞生于公元16世纪,到拉瓦锡时代已经存在200多年,其源于他专制的封建王权财政需求的增长所带来的债务关系,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这的确是降低管理成本的最有效办法,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腐败和横征暴敛问题严重。拉瓦锡正是因这种制度,为自己的科学研究积累了丰厚的经济基础,但也招致了民众的仇恨和讨伐。这其中涌现出来的两人,最终将拉瓦锡送上了断头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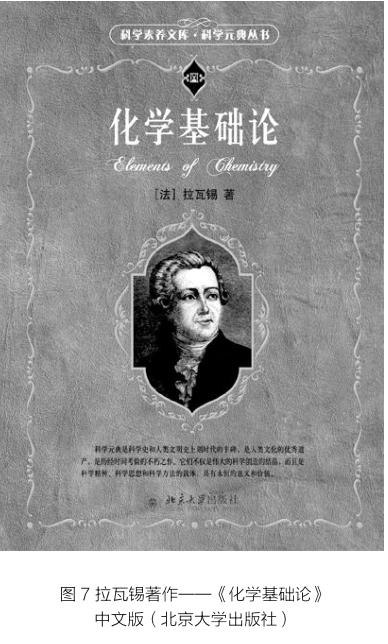
一位是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年),法国医生,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活跃的民主派革命家,那幅著名的画作《马拉之死》中的主人公就是他(图8)。马拉与拉瓦锡的交集仅有一次,但正因为这一次交集,让马拉对拉瓦锡心生怨恨,这种怨恨在复仇心极强的马拉身上势必要找到机会释放,他曾扬言要将拉瓦锡“吊死在街头”。早在大革命以前,马拉凭借一些已经过时的理论申请过加入法国科学院,但因为其理论禁不住推敲而被诸多院士怀疑,拉瓦锡更是对马拉严词拒绝。两人的“梁子”就此结下。马拉在《人民之友》上公开谴责拉瓦锡:“我公开揭发你这个冒充内行的考里费厄斯(考里费厄斯是古希腊戏剧中合唱的领唱人),拉瓦锡先生,强夺土地者的儿子、日内瓦投机者的学生、承包税收商人、火药和硝石的管理人……他要求公众认可花费3 300万里弗尔在巴黎周边筑一道墙,把巴黎人投入监狱,隔断新鲜空气……愿上帝把他吊死在街灯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