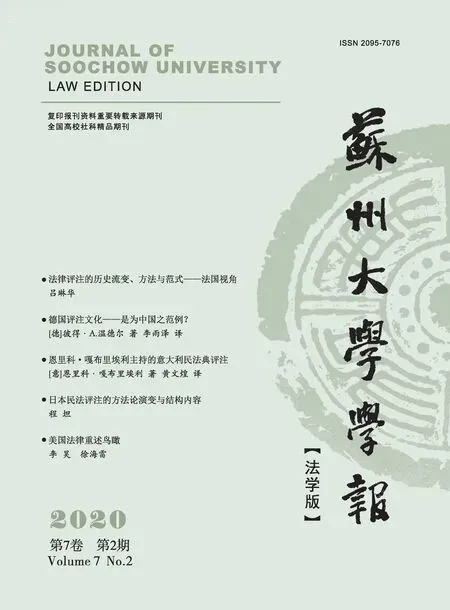废除种族隔离案件判决的合法性*
[美]小查尔斯·隆德·布莱克 著 阎 天* 译
假如那些宣告种族隔离违法的案件(1)Brown v.Board of Educ. (学校种族隔离诸案), 347 U.S.483 (1954); Bolling v.Sharpe, 347 U.S.497 (1954); New Orleans’ City Park Improvement Ass’n v. Detiege, 358 U.S.54 (1959); Gayle v. Browder, 352 U.S.903 (1956); Holmes v. Atlanta, 350 U.S.879 (1955); Mayor & City Council v. Dawson, 350 U.S.877 (1955); Muir v.Louisville Park Theatrical Ass’n, 347 U.S.971 (1954).判错了,那就该推翻它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职业观点使人确信那些案件判错了,那就该推翻它们,或慢或快,或公开或隐蔽。不重要的错误无论有多么明显都可以保留,因为确定性所带来的便利超过了错误所带来的不适。而重大的错误不能保留,也不会被保留。(2)对比Pollak,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Judicial Integrity:A Reply to Professor Wechsler, 108 U.Pa.L.Rev.1, 31 (1959)。我自始至终都受益于这篇文章,虽然我提出来支持判决的论证与波拉克(Pollak)教授不同。不过在我看来,他的论证是去除种族隔离判决的另一个可行基础。
所以,认为种族隔离案件无法被证立的观点具有实用的意义,它要求采取行动。(3)See Wechsler, Toward Neutral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Law, 73 Harv.L.Rev.1, 34 (1959)。本文受到威克斯勒(Wechsler)教授质疑的直接启发。不过不该把本文看作正式的“答复”,因为我在本文中只谈及了他的论证的一部分,而我的思考线索也只是部分地回应了他对问题的看法。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这些案件的判决是否正确不仅在智识上是重要的,而且对实践也有影响。我认为这些案件判对了,因为理性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抗拒的影响力,而我想在此解释自己为何坚信这一点。
我在论述开始时遇到的困难是修辞上的——更准确地说也许是时尚方面的。简约已经过时了,而能够证立这些案件的基本推理架构却异常简单:第一,应当将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解读为:黑人作为种族,不该被州法置于显著劣势的地位。第二,种族隔离是州法针对黑人作为种族的、大规模的故意劣化。一点机巧也没有。然而我无法不确信,种族隔离案件的全部就在于此。如果这两个命题都能够获得优势论证的支持,那些案件就判对了。如果它们得不到如此的支持,那些案件就危险了。
总体来说,第一个命题据我所知迄今从未被最高法院的判决否定过。在此我所依据的是屠宰场诸案(The Slaughterhouse Cases)(4)83 U.S.(16 Wall.) 36 (1873).和斯特劳德诉西弗吉尼亚案(Strauder v. West Virginia)(5)100 U.S. 303 (1880).的笃定认知,大法官斯特朗(Strong)先生在其中这样谈论第十四修正案:
它命令各州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克减合众国公民(显然是指新成为公民的人,他们作为合众国的公民,被宣告也是各自居住地所在州的公民)的特权或豁免的法律。它命令各州不得不经由法律的正当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也不得拒绝给予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以法律的平等保护。除了如下的意味,该修正案怎么可能还有其他意义呢?它宣告各州的法律对待黑人和白人时应当是一致的;包括有色人种和白人在内的所有人在州法面前一律平等,并且对于本修正案旨在保护的主要对象即有色人种而言,法律不得由于他们的肤色而歧视他们。诚然,修正案采用了禁止性的措辞,但它们必然包含着一种引申出来的积极豁免或权利,这对于有色人种来说最为珍贵——免于承受针对其有色人种属性的不友善立法——免于遭受那些暗示他们在市民社会低人一等的、让他们更难享有他人所享有权利的法律歧视,以及那些一步步将他们降格为受支配种族的歧视。(6)Id.at 307-08.
如果有人认为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Ferguson)(7)163 U.S.537(1896).对上述原则有所迟疑,那么我就退回原则本身。而最高法院在普莱西案中明确提出,其任务在于证明种族隔离并没有真的让黑人居于劣势,除非是出于黑人自身的选择。(8)“我们认为,原告论述的内在缺陷,在于预设了两大种族的强制隔离会给有色人种打上等而下之的烙印。果如是,这并非出自做法本身的原因,而完全是由于有色人种选择将那种理解赋予做法。”Id.at 551.(着重号系后加。)冷漠和愚蠢的曲线在它们各自的最高点相交了。这并没有否定屠宰场诸案和斯特劳德案的原则;普莱西案的迟疑存在于其小前提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之中。
隐伏的困难并不在于“种族”案件,而在于广义上的“平等保护”的整个哲学之中。“平等保护”在适用到整个州法上时,必须允许让某些人居于劣势,因为所有的法律都会让某些人居于劣势;只把驾照颁给优秀的司机就会让不好的司机居于劣势。所以在将“平等保护”适用到法律整体上时,必须设法在其中植入“合理”一词。在这个宽泛的背景下,“合理”一词的含义应当和从前一样,即“可为合理考量所支持”。(9)See Lindsley v.Natural Carbonic Gas Co., 220 U.S.61 (1911).所以,“平等”并不真的意味着“平等”,而是指“除非有相当站得住脚的理由支持不平等,否则就平等”。
当第十四修正案被运用到更宽泛的语境下时,就得做出必要的限制。然而,出台第十四修正案时的悲剧性背景阻止了将这些限制加诸其核心意图。或许“平等保护”本来旨在超出种族,进入更宽泛的领域。但是,历史毫无疑义地指明,总司令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图都是确保对于黑人的平等保护。几乎无法对这一意图施加可能导致其无法实现的限制,即使这种限制在对碳酸气加以平等保护时是适用的。如果是这样,则对于黑人而言,“平等保护”意味着“除非更青睐站得住脚的、支持不平等的理由,否则就平等”。如此看来,黑人可以拥有财产、签署遗嘱、结婚、在法院作证、在街上行走、上学(哪怕是去种族隔离的学校)、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等等,前提是各州立法机关无法找到显然站得住脚的理由来禁止他们做这些。1866年的争论不可能只是针对这一点。
回到当时历史场景下,第十四修正案必须被理解为要求黑人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他是黑人这一事实本身不得被看作拒绝给予他平等的充足理由,无论这个理由在某些人看来有多么“合理”。支持歧视黑人的一切可能论证,无论多么有说服力,最终都被第十四修正案拒绝了。
有人认为,在第十四修正案被采纳的历史过程中,一个特定的限制被写入了“平等”的概念——也即,该修正案意图将种族隔离排除出为平等所禁止的法律歧视的范围,而不论种族隔离实际上是否导致了不平等。亚历山大·毕克尔(Alexander Bickel)教授在论文中讨论了这个观点,(10)Bickel,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Segregations Decision, 69 Harv.L.Rev.1 (1955).他虽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学校种族隔离并不处于修宪者旨在用该修正案即刻纠正的罪恶之列,(11)Id.at 58.但也认为,修宪者还意图为后来的切实适用建立一个宽泛的概念。(12)Id.at 61-65.其他最近的作者都有类似的观点。(13)Wechsler, supra note 3, at 31-32; Pollak, supra note 2, at 25.就他的第一个观点而言,毕克尔教授所呈现的资料并没有说服我,虽然他自己被说服了。(14)事实上,我对毕克尔教授结论的异议恰恰在于他的结论的准确含义。诚然,我从他的资料中得出结论,相关人士并无“意图”去废除种族隔离,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主动地、有意识地生发出那么做的意图。而当用语宽泛起来时,这个结论就没有意义了。我没有被说服之处在于,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将《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Bill)与第十四修正案视作等价物(修正案的立法史中并无相关内容),也就不能将法案的历史附会到修正案上,更不能据此证明确有意图将种族隔离排除出修正案宽泛用语所发出的禁令范围——这个意思与谓语“并非意图”的含义截然不同。依毕克尔教授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写入如今的平等保护条款完全令人无法理解。对比Fairman, Does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Incorporate the Bill of Rights?, 2 Stan.L.Rev.5, 41 (1949)。考虑到毕克尔教授和我在实践层面达成了一致(至少我认为如此),修正案的发展与限制以及观点是否获得支持,所需要的讨论显然都比当下形势所能保障的要更多。而为了支持他的第二个观点,他提出了一连串想法来论证立法史并没有让种族隔离案件成为不当判决,而我很高兴支持他这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我只想补充一点:我们所知的、1866年时的人们对于种族隔离的“意图”,需要我们用远比通常认为的那样更海阔天空的办法去猜测,因为人们当时并不了解如今美国南部所盛行的制度。猜测他们针对20世纪中叶的某项制度的命令是预设了一个虚构的前提,而猜测越清晰,前提就越荒谬。就20世中叶的制度来说,他们只可能给我们留下宽泛的意见;修宪结束时,具体的意见还没诞生呢。我不理解毕克尔教授为何持有与此截然不同的观点。
那么,种族隔离是否侵犯了平等?与一切宽泛的概念一样,平等存在边缘地带,并且在那里遭遇哲学上的困难。然而,如果整个种族的人都发现自己身陷于一个体系之中,而建立和维持这个体系的目的恰恰在于确保他们处于等而下之的地位,如果此时还郑重其事地提出讨论这个种族是否获得了“平等”对待,我想我们应该行使哲学家的一项特权——哈哈大笑。(在我们止住笑以后)剩下的唯一问题是种族隔离体系是否符合这一描述。
在此,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又要忍不住笑了。我在南方长大,种族隔离在那座德克萨斯州的城市中根深蒂固。我相信无论白人还是有色人种都从来没有就种族隔离的含义提出过疑义。“平等”的虚幻程度就相当于追索侵占物之诉中“调查结论”的虚幻程度。我想几乎不会有哪个坦率的南方人会否定这一点。许多南方人完全真诚地宣称,种族隔离对黑人来说“更好”,而并非意图伤害他们,这种观点可能会误导北方人。而我认为,略微深究一下可知,南方人的意思其实是黑人最好接受等而下之的地位,至少在无尽的未来都应当如此。不过,主观上看来显然的事情,需得有更多公开资料作为后盾才能应对质疑。哪些公开资料让我确信自己对于种族隔离社会意涵的解读不是一厢情愿的呢?
首先,当然是历史。种族隔离是作为奴隶制和斯科特案(Dred Scott case)的使徒来到南方的。南方为维持奴隶制而战并落败。之后南方尝试制定《黑人法典》,也失败了。再后南方四下寻找其他办法,发现了种族隔离。种族隔离运动是旨在维持和延续现存“白人至上制”的运动的固有部分;其胜利[就如伍德沃德(Woodward)教授所证明的那样]代表着极端种族主义者压倒了对于黑人的温和同情。(15)Woodward, 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 ch.II Capitulation to Racist, at 49-95 (1957).See generally id. passim.当下对种族隔离的辩护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黑人作为种族不适合与白人为伴。
历史还告诉我们,种族隔离是一个种族强加给另一个种族的;并不存在自发的合意,也没有外部命令要求达成合意。种族隔离在南方生长出来并得以存续的原因是且仅仅是白人希望如此——这个事实无可争辩,而其本身就几乎无法与平等相协调。这个事实或许比其他任何事实都更能够加深南方生活可能给观察者留下的印象,无论观察是随意的还是深入的——白人和黑人并非互相隔离,而是一个隔离他人的群体(in-group)充分享受正常的公共生活,另一个被他人隔离的群体(out-group)被禁止享受这种生活,并且被迫沦入自己等而下之的生活之中。当白人南方作家提及“南方”的悲苦时,你是否知道他是指“南方白人”?难道南方的社会背景没有让这一点显露无余吗?当你身在利维尔(Leeville),听到有人说“利维尔高中”,你知道他指的是白人高中;黑人学校另有名称——或许是卡沃尔高中(Carver High),或许是林肯高中,这就尴尬了。当一个种族将被隔离的地位强加给另一个种族时,你能期待的不过如此,事实也确是如此。
历史地看,种族隔离与同时代一系列做法的功能复合体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做法无可辩驳地极具歧视性。我尤其想到将黑人排除出投票范围的做法,它不仅长期存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效。这里有两点要讲:一是特定的一群人被“隔离”了。二是几乎与此同时,同一群人中的每一位都被禁止或试图禁止参与共同体的公共政治生活——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而有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说,种族隔离并非意在伤害被隔离的种族,也并非意图给他们打上等而下之的印记。我们还要忍多久才能笑?
在此,可以补充的是,总体而言,在那些针对黑人的法外歧视最为严酷的社区,种族隔离会成为法律的常态,黑人受制于最严格的“不成文法”约束,这涵盖了就业机会、社会交往、居住分布、使用后门、被以名字而非姓氏相称、使用尊称(“Sir”),以及其他一切可悲的做法。这些事情本身当然不需要、通常也不涉及“州行为”,第十四修正案因而无法适用于它们。但是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州行为的意涵,并评估其影响。
“隔离但平等”的设施几乎从未真正实现平等。有时涉及的是小事——如果“白种”人的房间同时安装了冷热水龙头,那么“有色”人种的房间也可能分别安装这两种龙头;公交车总是把后排座位留给黑人;“林肯海滩”几乎不可能像普通海滩一样好。有时则可能涉及至关重要的事——在种族隔离的整个历史上,有色人种的学校都极为可耻地劣于白人学校;共同体仍在撒谎说这会让人们“平等”,而谎言如同恶魔献祭般地毁掉孩子,如果共同体中还有谁对此充耳不闻,那么能够原谅他们的理由就只剩下愚昧了。
人们对于这些不平等的关注往往就事论事,以为通过细节的命令就能加以矫正。而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些不平等显然能够作为证据,证明种族隔离对于强加它的人和屈从于它的人都意味着什么。就事论事、一点一滴的矫正并不能抹杀这种证明能力。一个体制如果在所有可以度量的方面都实施了再明显不过的不平等,那么它还可能在意图、总体社会意涵和影响上都是“平等”的吗?“闻言可以观人”;种族隔离在一切可见的地方都吞吞吐吐地只说一种方言,那就是不平等。
进一步的证据还可以层层加高,因为我们在此所不得不面对的是整个地域文化中最显而易见的特征。在南方,说一个白人是黑人,属于可诉的诽谤。(16)See Mangum, Legal Status of The Negro ch. II Libel and Slander (1940), 其中引用并讨论了案件。为了种族隔离的目的,一丁点黑人“血统”都能让一个人沦入等而下之的种族;(17)Id.ch.I.这和人们对待污点的态度毫无二致,就像对待越橘的致癌基因一样。
以上提到的事情的分量不同;不是每件事本身都足以表明种族隔离的性质。然而,把它们合在一起,就获得了无可辩驳的力量。这个社会曾经想让黑人永世为奴,曾经试图用准奴隶制的“法典”来约束黑人,虽然都失败了,但是仍然将黑人的血统视为污染,将黑人的名字视为羞辱,并且在法律之外将低等种族的所有羞辱性印记都强加到黑人身上,直到昨天还在用私刑处置黑人——这个社会罔顾黑人同意与否,采取法律手段先剥夺了黑人的投票资格,继而禁止黑人融入共同体的一般公共生活。最高法院曾经拒绝在这一切当中发现不平等,这就产生了绝无仅有的、注定丑恶的法律——基于自我诱导的视若罔闻的、公然抵触已知事实的法律。
以上各点的论述都很简略,因为它们早已臭名昭著,这些事情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且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是重要的背景知识,对于司法的关注来说则不那么重要。法院会注意到这些事实,就像会注意到许多其他的事实那样:我们是个“有信仰的民族”,国家工业化水平早就超过了杰斐逊时代,父亲对孩子大方是很自然的事,刑事制裁被普遍认为有震慑作用,钢铁是我们经济中的基础性商品,对不贞的诋毁会伤害妇女。在事实基础上所做的类似判断是一切法律的根基,无论是裁判法还是制定法。一个事实是,种族歧视的社会意涵让黑人处于被隔绝的等而下之的状态;同样浅白的事实是,这样的待遇对人有害。如果例外地要求法院在面对当下问题时忽略美国社会的这些浅白事实,就堪称最不中立的原则了。正是基于忽略事实的判断,南方的法院判决将白人安置到黑人列车车厢中构成可诉的侮辱;(18)See id.at 209-10, 219-20.法院难道真的必须假装不知道黑人在其中的处境才是侮辱性的吗?
我认为,围绕这一问题的、人为制造的困惑的迷雾,都源自一个基础性的错误。看问题的角度是所谓社会学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sociology):“种族隔离一定构成歧视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有一天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或许足以给出答案。我们的问题是:在20世纪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州,法律所强加的种族隔离当中是否存在歧视。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而答案只能从历史和关于具体时空的生活现实的常识当中去找。
当然,我不必、也并不主张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这并不重要。有人坚称种族隔离不过意味着为各种族的平行发展创造有益的机会,我们无须质疑他们的真诚;他们在极少数分散的个案中可以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我们对此也该感到高兴。而我们要问的是:烙饼的哪一面是朝上的?(19)威克斯勒教授在那篇我所回应的文章中说:“裁判的优劣……完全取决于支撑它的理由,以及基于这些理由下令做出任何价值选择的充分性;还要加上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基于这些理由下令拒绝做出任何选择的充分性。”Wechsler, supra note 3, at 19-20. (着重号系后加。)除非最高法院选择倚赖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社会学而不加反思,或者遵循逃避问题、没有意义且不合常规的程序,将这件事留给国会去处理(See id.at 31-32, 否定了上述两种不解决问题的做法;关于后一种做法,见本人即出,The People and the Court, at 137-39),最高法院怎么可能判决肯定我们所知的种族隔离确实是平等的呢?特别是考虑到如下的事实——我认为应当承认这一点,即各州依据种族进行归类的法律至少可以说缺乏强有力的合法性假设作为支撑。
事情看起来是如此地一边倒,以致于很难理解:在试探性地询问最高法院究竟如何理解种族隔离系统的真实特性时,反对者到底有什么可抗议的。反对者的意思似乎是,虽然对于种族隔离的目的及其所支撑和实现的社会范式并无疑义,但是最高法院却缺乏常规路径来获知那些对所有人及大法官个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事实。不过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法律的头脑当然只有一件合适的任务要完成——那就是开辟让最高法院能够利用其所知之事的路径;任何其他的建议都没有出路。同样确定的是,最高法院将关于广大社会样态的常识信以为真,这一点(最起码)应当处于抗议内容清单中很靠下的位置。
据此,我的结论是,最高法院判决种族隔离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的理由再充分不过了。这些理由补全了我在文章起始时所构建的三段论:第十四修正案命令实现平等,而我们所知的种族隔离属于不平等。
让我再来谈一些次要问题。诚然,可能不易证明种族隔离给每个被隔离个体的生活都带来了特别的伤害。(20)See Wechsler, supra note 3, at 32-33.对此,正如波拉克教授所认为的那样,(21)Pollak, supra note 2, at 28.只要知道其他宪法权利从未面临类似的证明要求,就足够了。认罪自首在某些个案中可能是新的、更好的生活的开始。在现实世界中,对于个别男孩来说,以种族作为区分标准的宵禁可能再好不过了。一个人在事发十年之后,可能感谢那位当年将他拉下舞台并制止他搞怪的警官。宗教迫害会强固信仰,这是人尽皆知的。人们通常都不会如此引申,也不会如此狭隘地看待事物。基于大量历史证据和常识,某种做法意图导致,并确实导致了将其受害者置于劣势地位的后果,这对于法律来说就足够了。至少通常来说这就足够了。
我可以真心附和那种认为种族歧视对白人的伤害和对黑人一样大的观点。(22)See Wechsler, supra note 3, at 34.暴行会腐蚀警察;压制思想的人会失去明见;共同体一旦蜕化为一伙暴徒,堕落并操纵审判,所带来的伤害可能无法治愈。这种伤害的相互性注定存在于一切强加的错误之中,它能够论证错误本身是合法的吗?
最后,学校种族隔离诸案或许也包括其他关于种族隔离的案件,都无疑表明了在两种结社自由之中所做的选择。免于承受大规模种族隔离之错的自由,必然意味着白人一方自由的相应损失,他们现在必须与黑人在公共场合结社,这正如我们都需要在这种场合去和许多我们并不希望发生关联的人结社。可以把这两种相互竞争的诉求放到对称的位置,质问是否有宪法上的理由来偏袒黑人参与和融入公共生活的愿望,而压制白人让黑人无法靠近其公共生活的愿望。(23)See Wechsler, supra note 3, at 34.
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但我打算采取一种在我看来更常规的路径——这是我们更经常用在其他一切权利上,用来比较两种对称事物的路径。第十四修正案禁止不平等,禁止利用法律将黑人置于劣势。修正案出台时肯定预见到这一命令会引发某些南方白人的异议。这种异议可以有许多形式,比如白人可能不喜欢有一位黑人邻居去行使自身拥有房产的平等权利,或者不喜欢参加有黑人在列的陪审团,抑或不喜欢十点钟之后的街上除了自己以外还有黑人。(24)1909年,摩拜尔(Mobile)的白人居民以社团的身份起诉,要求保护这种特定的“不结社自由”。See Woodward, op. cit. supra note 14, at 86-87.如果执行平等的命令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白人不悦,那么白人的“自由”就必然受到损害。如果第十四修正案命令实现平等,而种族隔离违背了平等,那么“自由”的相互地位就自动确定下来了。
第十四修正案还命令让黑人成为各州的“公民”,我认为这至少在精神上加固了上述观点。我很难想象,如何操作才可以既让一个人成为“公民”,又避免他偶尔与其他公民结社。比如,要是他行使“公民权”,当选学校委员会成员,那么白人成员可能会(就像最近在休斯敦所发生的那样)把他冷落在房间的一角,但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们“不结社”的自由。事实上,那种自由只存在于家中;在公共场合,我们都必须与有权出现在这里的任何人结社。当我们决定他是否有权出现在这里时,关于我们不与他结社的权利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结论。
我并不是真的要为自己在种族隔离案件上的简约思维辩护。这些判决呼唤一场宏大的板块运动。只有在简约思维获得了可靠论证,从而让法律摆脱了取巧并成为技艺时,我们才能够呼唤这样的变革。唯有如此,才能够赞同国家下决心支持最高法院所宣示的法律;唯有如此,才能够调和南方白人与法律命令之间的冲突。在此,内在逻辑的一致性(elegantia juris)和概念的代数学毫无用武之地。我不想假装自己的论证是周详完备或确定无疑的,而是试图证明,有理由相信,我们作为法律工作者,可以在既不作伪也不模仿的情况下,向专业以外的人们,也向我们自己展示种族隔离判决的理据,并且达到伟大论证的高度。
与一切判决一样,这些判决必须立足于其法律的正确性及其事实的真切性。如果认为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宣示了让黑人种族切实获得平等的广泛原则,且修正案并没有随意设置例外,以至任何做法如果在事实上将黑人种族降格到等而下之的地位都将与修正案不符,那么这些判决的法律就是正确的。如果种族隔离系统确实旨在维持黑人等而下之的地位,且确实充当了实现这一点的手段,那么这些判决的事实就是正确的。这次我敢说,这些判决最终恰恰会因为上述理由而获得法律界的接受。在痛苦压力下作出的判决会留下许多可以改进之处;(25)我在此无意加入对布朗案判决的攻讦之列。指责判决的“社会学”属性要么是老生常谈,要么是谎言——如果指责的意思是最高法院和无数其他法院在面对无数其他法律案件时都必须也确实解决社会事实问题,那么这恰恰是最高法院在普莱西案中所做的,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如果指责的意思是判决把正式的“科学”权威文献当成了主要依据,那就是撒谎,因为判决只在一个脚注中提到这些文献,而且只不过用它来证明常识而已。在我看来,判决犯了个可原谅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指出:由于我在本文中所展现的原因,种族歧视应被理解为将沦为次等的种族隔绝起来的手段。(我猜法院略去这一点的原因是不愿意谈论南方种姓制度令人不快的细节。)而最高法院也没必要过多地论述这种对待通常不利于儿童。或许选择仅针对个案(per curiam)的判决方式并不明智。然而,这些判决无论在法律还是事实上都再正确和真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