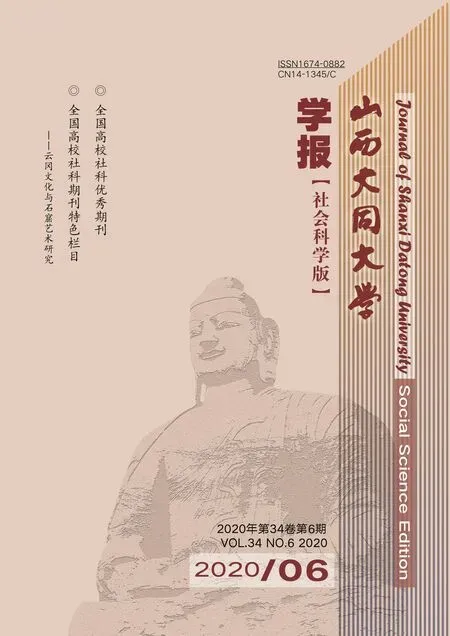艾芜“南行系列”小说中的异域书写
魏籽琦,程小强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艾芜的南行“不是为创作而去阅读生活这本书的,而是阅读了生活这本书之后才开始创作的”。[1] (P40)1925 年,艾芜因不满学校守旧教育,并借反抗旧式婚姻为契机从成都出发,一路漂泊,凭一双脚板走遍云南、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1931 年,被英国殖民地当局以“有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驱逐回上海。作为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者,艾芜曾经在红十字会医院中做过勤杂工,也曾在克钦山茅草地一带成为打扫马粪的伙计,甚至流落街头与贩夫走卒为伍,终日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困顿生活。在此类苦难的经历中,他得以接近和了解各式流浪者,洞察下层苦难生活,并用自己的赤诚和善良去理解、同情他们。流浪体验直接促成艾芜的“南行系列”小说,浪漫主义的传奇性故事、性格特异的各色流浪者形象、绮丽迷人的边地风光都使作品充满了异域色彩。
一、“异域”场景的文学呈现
艾芜所写的“异域”场景,主要集中在滇缅边境,毗邻老挝、越南,聚集着傣族、景颇族、哈尼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多民族聚居的地理位置及文化空间的特殊而复杂性造就了艾芜小说审美空间的独特性。无论是边地的自然风光,还是边地子民的衣着服饰、民间语言等都充满了异域文化特色。
(一)“异域”风景大量的风景描写成为艾芜小说叙事最重要的特色。艾芜曾经说,“没有自然景物,可以说就没有我的小说。我一想到大自然,就好像进入一种梦幻,人物也就出来了。”[2]因此,艾芜在小说创作中极为重视自然风景的描写。“南行”系列小说中的风景大多呈现出奇崛凶险的山地景象,展现着原汁原味的特点。如《我的旅伴》中描写傍晚时分的江景:“当我进去的那一刻,正是半下午的时候,宽阔的江面上,照着一片向西的阳光,金辉灿烂地从窗上门上,反应进来,使屋子越加显得丑陋。对面远远的江岸上,一排排地立着的椰子树和露在林子中的金塔,以及环绕在旷野尽头浅浅的蓝色山影,都抹上了一层轻纱似的光雾,那种满带着异国情调的画面,真叫人看了有些心醉。”[3](P238)这些充满南国情调的风景,椰子树、金塔以及那浅浅的霞光无不给人以视觉上的强烈美感,甚至还有那些奇崛险怪的景象,如《私烟贩子》对西南山地雨季的描写:“天空仿佛低矮了许多,铅色的胸膛,直向小小的山谷,压了下来。四周布满森林的高山,则把头伸入云雾里面,一向藏着虎豹野象的地方,越发显得凶险不测了。有些时候,终天飘着丝丝细雨,树叶上,都凝结起了水珠。有些时候,又哗啦哗啦下着,兼有雷电助威,好像房屋都要一下子倒塌似的。”[3](P257)在这些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克钦山谷中,私烟贩子们为了躲避英国警察的缉私查烟,不得不住在这个小小的山谷中。虽然生存环境恶劣,但对他们来说是自由自在的,难怪“我”在离开私烟贩子时几乎想要留在他身边了。再如《山峡中》:“江上横着铁链做成的索桥,巨蟒似的,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终于渐渐吞噬在夜色中了。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的冲打崖石,激起吓人的巨响。两岸蛮野的山峰,好像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无法避开一样,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夏天的山中之夜,阴郁、寒冷、怕人。”[3](P26)正是在这样可怖的环境中,“我”与一群走私行窃的流浪者们同路。在看到他们偷走市集老板的布匹,并把重伤的小黑牛抛入江中后,“我”的内心充满愤恨,决心离开他们。只是当他们留下野猫子来干掉“我”时,却没料到最终反而是“我”救了野猫子。或许是为了报答,他们留下“我”继续上路了。在荒山野岭中“我”作为观察者所遇见的这样一群“被世界抛弃”的流浪者们,尽管干的是打家劫舍的勾当,但心中仍存有良善之心,那些可怕的环境与他们的善良之心形成鲜明对照。西南边地那咆哮的松涛、奔腾的江水、黛绿的群山、雨期的瘴雾等滋养着边地的纯朴子民,为他们注入狂狷剽悍的野性因子,彰显着边地人民野性自然、纯朴善良的美好品性。从柄谷行人的理论来说,风景描写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完全独立的风景,既然是人观照出来的,同时也是人在观照,就必然有人的主体的介入。”[4]艾芜只身一人流浪在边地,孤独的灵魂无处安放,他无视外在生活条件和自然条件的恶劣不堪,在行走的沿途中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向往自由、热爱大自然的心对西南边地的景物倾注了一腔热血。也正是这样,才使读者从其作品中感受到西南风景独特的异域之美。
(二)“异域”语言异域化、民间化的语言是艾芜在“南行”系列小说中的一大看点。艾芜被称为“流浪文豪”,在“南行”系列中的不少流浪者们出口即粗俗的污言秽语。如“魁鲁德”(缅语,意即狗入的)、“丢亢妈个害”(广东台山话,意即入他妈的)、“干你蜡伍”(福建厦门话,意即入你老母)、“妈的”、“老子他们”、“充狠”、“婊子”、“狗头”等等。这些粗俗语言的使用,使作品呈现出一种纯朴原始不加修饰的自然特点,同时也符合典型语言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流浪者们大都居无定所,整日为生计发愁,打架斗殴坑蒙拐骗之事常态化,语言的粗鄙能够真实的再现底层小人物们在生活重压下对不满情绪的发泄。另外,由于西南边地少数民族居多,语言体系尤其庞杂,艾芜的作品中频繁出现一些云南少数民族的俚语俗语以及缅语、马来语。如《森林中》的私烟贩子口中的“喊声”(意即如果)、“冲壳子”(意即扯谎)、“打上福”(意即说好话)以及马头哥口中的“发梦天”(意即说梦话)、“舵把子”(意即首领)等方言的大量使用,还有不少篇章中“扁达”(意即警察)、“坐痛”(坐监狱)、“木头枷”(意即汽车)、“慈雅基”(意即先生)、“阿哥几”(意即大哥)等缅语的使用,甚至《海岛上》出现的英语“坎蒲”(意即拘留营)以及马来语“德白,端”(意即敬礼,先生)的使用。这些语言的大量使用使得艾芜作品中独特的异域色彩更加鲜明突出,在表现人物形象的同时增添了小说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民间语言是广大民众世代相传的集体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传达和反映着民众的思想、感情和习俗。”[5](P298)民间语言的运用,能增添小说的地域特色,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为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服务。
(三)“异域”服饰与汉族不同,少数民族的衣着服饰本就具有辨识度,艾芜在小说中有大量细致的描绘。如少数民族克钦人的服饰:“男的头上缠着黑布帕子,浅发的头顶,或是头顶绾的髻子,则露在外边。包的帕子,剩余三两寸长,则向上翘着,仿佛斜插着一截什么东西。嘴里嚼着槟榔,嘴唇显得血样地红。他们的腰上,经常带着一把齐头的长刀。女的多半是十五六岁的姑娘,头发剪得短短的,披在头上。穿着黑布短衣,镶着细条的红布边子。围着黑布裙子,只达到膝头上。膝头上和脚肚上的那一部分,则缠着细细的黑色藤子,约有数十圈光景。”[3](P306)还有那位生活在仰光的缅甸女子的衣饰:“她穿着水绿色绸笼基,从胸以下,一直拖到脚背上。上身穿着薄薄的白纱短衣。头发大概还掺有很多的假发,则绾成一顶圆形的帽子一样,高约五寸,全笼在头上,只有一小撮,软软的从头上拖到耳边。这在缅甸妇女的装饰说来,这撮头发是一个未嫁的姑娘的标记。如果嫁了,便用不着这样拖一撮头发,只是全部都绾成一顶帽子了。”[3](P357)此外,还有一些头上包黑纱的傣族女人,上身着西装下面穿中式裤子的缅甸华侨,头戴宽边呢帽、腰挂长刀的偷马贼,包着白布套头、穿着黄衬衣的印度兵,踩着黑皮鞋、长毛袜的英国绅士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服饰文化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身份的象征。对于西南边地的少数民族而言,普通百姓穿着多为便于劳作的短装型上衣下裙、上衣下裤式结构,以卖柴为生的克钦男子腰间常配长刀,而受洋人影响较多的有钱人在穿着上就更加洋化。除此之外,衣饰装束也是反映少数民族男女的年龄以及婚姻情况的标志,成为一种独特的符号象征。
(四)“异域”风俗在艾芜笔下,边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不相同。《森林中》中的克钦人就有祖传的规矩,他们在每年下钟的时候,都要杀一些外乡人祭谷地以祈求来年的好收成。《月夜》中的回族女子因历史矛盾不允许汉族青年在自己家中过夜等。在“吃”上,小说中出现最多的要数槟榔、饵块、咸肉以及鸦片了。嚼槟榔借以打发寂寞无聊的时光,饵块、咸肉都是便于储藏携带的东西,这些吃食都是行走边地的人们常备之物。鸦片是和违法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而在这样一片“法外之地”,却有许多人都干着与鸦片有关的职业:种植鸦片,走私鸦片,贩卖鸦片,吸食鸦片……鸦片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因为种植鸦片,所以很多人都抱着可以偶尔吸两口不怕上瘾的心思,毕竟自己家就有很多鸦片,不怕供不起,更何况当地人认为吸食鸦片有助于在充满瘴气的山林中安全行走。对于那些吸食鸦片成瘾的人来说,烟枪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松岭上》那位白发老人不就将烟枪看作他的大女儿吗?除了种植鸦片的人,走私贩卖鸦片的违法行为就更不是他们所担心的。因为早在第一次英缅战争期间英国人就将罂粟种子撒向了缅甸国土,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缅甸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况且鸦片市场需求大,相比农作物来说利润更加可观,底层小人物为了生存也并不过分抗拒。这些独特的边民特色充分展现了西南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正是通过这样的叙写才使艾芜的作品充满着独特的异域情调。
二、“异域”子民的生命意志
艾芜笔下的西南边地,无疑是一个不受道德、法制规范约束的“化外之地”,要在这片险山怪水中生存,必须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艾芜亲身体验过苦难的流浪生活,他所遇见的那些边地子民,大多处于社会底层,如打家劫舍获取不义之财众强盗、铤而走险的响马贼和私烟贩子,以及那些因为人命案件而不得不隐居此地的罪犯。艾芜曾说过:“由于思想上尊重劳动人民,又在生活中同下层的人一道同甘共苦过,因此,对于劳动人民有着真挚的热爱,所写的短篇、中篇以及长篇小说,大都以劳动人民为主要人物,他们虽有不少缺点,但其本质,则是崇高的、美好的。”[6](P163)边地子民身上所具有的野气、蛮性,充满了强悍古朴的原始生命力量,展现出极强的生命意识,“这种‘野蛮人’不承认任何现代文明(如理性、伦理),奉行着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7](P121)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下,他们被视为“坏人”或“渣滓”;但艾芜不这样认为,那里充满着对生命意识的颂扬,边地子民身上的放纵、野性和蛮性已经超越善恶二元对立,铸就了他们的生命强力。
(一)求存意识《南行记》第一篇《人生哲学的一课》中,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具有坚韧顽强的求存意志的流浪汉——“我”的形象。“我”初到昆明,身无分文,陷入生存困境。为了能够有钱吃饭,“我”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草鞋,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必须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想到黄包车也拉不了,厨师亦做不成,又遭逢“我”的鞋子被人偷走。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幸的遭遇后,“我”并没有怨天尤人,甚至还同情那位偷鞋者,充满了善良之心。故事的主人公“始终是个斗志昂扬的自我,在情绪上、知识上始终如一,没有发展变化。在他的人生第一课里,作为流浪者的自我的这个人物就已经形成了,它的力量也已经被证明了。它仅仅是在顺利通过每次考验以后积聚了更多的愤怒,并不断重申一定要活下去的愿望”。[8](P83)那一声顽强的呼喊“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脚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的生存”,[3](P25)迸出作为流浪者的“我”身上坚韧的生命力。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给予他的苦难遭遇时并没有被打倒,而是勇敢的迎头而上解决问题,并将其看做“人生哲学的一课”去锤炼自己顽强的意志,这正是作者所颂扬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不仅仅体现在具有强健体魄的男人身上,在那些边地女性身上 同样具备。《芭蕉谷》中的姜大嫂是一个苦命女人,是一个在命运的捉弄中不断顽强挣扎的女人,她的人生命运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些类似。祥林嫂的人生以贺老六之死为分水岭,而姜大嫂的人生则以第一任丈夫之死为分水岭。姜大嫂的第一任丈夫勤劳能干,她的生活每天都充满幸福;然而男主人不幸身染瘴气病死;此后,姜大嫂的人生就遭逢接二连三的磨难,直至生命终结。作为寡居女人,她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生存压力,但从未放弃自己的生命,一次次坚持与不幸的命运作斗争,求存意识极为强烈。
(二)反抗精神正是因为边地子民身上顽强的求存意识促发的反抗精神,使他们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瞎子客店》中瞎子父亲一家人本在外州县公馆里做工,那时的瞎子父亲尚未双目失明,因为惹怒了公馆少爷而被惩罚到花园栽花,后来同一个遭受公馆少爷欺压的丫鬟明珠一起私奔。他们二人从公馆毅然逃走,源于稍微觉醒的反抗意识。正如鲁迅所言:“艾芜的《南行记》把那些在生活的重压下有着强烈求生欲望的朦胧反抗行动刻划在作品当中。”[9](P430)瞎子父子二人虽然永远的生活在黑暗之中,但却从来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追寻光明的未来。《松岭上》中,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二十年前偷了地主家的米被发现,老人的妻子为了不让丈夫坐牢不得不委身于地主,老人知道后不仅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杀了地主老爷一家,然后躲在深山老林中孤独的与烟枪烈酒为伴,并把烟枪和烈酒看做自己两个已逝的孩子。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老人在地主的压迫下早已丧失理智,面对压迫和屈辱,他不惜杀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以泄愤,这是一种强烈的原始复仇行为。艾芜在作品中塑造了许许多多诸如瞎子父子和“老人”的底层小人物形象,他们的生活愿景就是踏踏实实的像个人一样勤勤恳恳的活着,但在粗粝的社会环境中却面对着来自地主家庭以及无耻无行洋官的压迫与剥削,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得不到保障。不反抗,是死;反抗,尚有一丝活路。《洋官与鸡》中的店老板为了讨好洋官,每次都把最为肥美的鸡献给他们,天真的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洋官们手下留情,最后仍然遭受着无理的压迫,还把送肥鸡看做理所当然,变本加厉的索要肥鸡,可见逆来顺受也不是出路。
(三)侠义之气顽强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反抗意识是边地子民得以生存的必备要素。勇敢强悍的英雄侠义之气成为优秀品格,懦弱胆小的人没有活下去的余地。《山峡中》的小黑牛因为在打家劫舍的行动中受了伤,睡梦中发出了“害了我了”“我不干了”的呓语,并诅咒自己的同伴们“不得好死”,首领老头子一行人就狠心的将他在深更半夜扔进江水之中。老头子认为在西南边地这样一个“法外之地”,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他们杀了小黑牛,甚至准预备杀掉想要离开他们的“我”,只是在偶然情况下“我”救了野猫子。他们作为报答不仅没有杀“我”,还留下了三块银元。行走边地,打家劫舍本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如果这一行人心肠软一点,不够勇敢强悍,那就必死无疑。这样的生存逻辑尽管残酷,但艾芜通过这个故事向读者展示了西南山林匪盗的生命强力以及侠义之气。“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充斥着太多‘阉鸡’似的男性软弱者,太多孤苦无依的‘零余者’和太多敏感多疑的神经症患者、精神病狂人。只有在艾芜的笔下,我们才能真切地看到如此生动真实的‘骠汉’形象。”[10](P166-167)《流浪人》中与“我”同行的矮汉子和小伙子是两个私烟贩子,他们一路上吹牛,开玩笑,斗嘴,并想方设法调戏打花鼓的母女俩,令“我”心生不满。后来他们二人在“我”吃饭休息的时候打闹着跑开,将没有结账的“黑锅”留给了“我”,“我”不得不将自己仅有的钱和一件好衣裳贴进去。没想到在“我”到达下一个城镇的时候,矮汉子正在场口等着“我”,犹如一个顽皮的孩子道:“老弟,你看我是不是有心害你嘛?我就怕你找不到我,我才在这口子上等你!我老实告诉你,你要是比我有钱,我今天就不管你了!各人走各人的!”[3](P286)不仅如此,他们临行前还给了我许多钱,“你用好了!你我穷人都不用,还有啥人配用!”[3](P287)这样的两个人正是“侠义之士”的代表。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获得财富,大把的挣钱,大把的挥霍,甚至劫富济贫,慷慨豪爽的将金钱赠予有需要的人,正是民间“侠文化”的再现。
三、“异域”书写的文学意义
现代以来,许多从欧美、日本等地留学归来的青年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拿起笔杆,以自己的留学经历为素材,写下了不少具有异域风情的小说。其中以郁达夫、张资平、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以及许地山、老舍等人,包括1940 年代的徐訏、无名氏等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异域书写做出了重要贡献,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小说的表现领域。作家们通过对异域空间的书写,将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风景、风俗引入中国文学之中,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表现。与其他书写异域题材的小说家不同,艾芜的南行叙事具有高度化的个人体验,以文化思考为切入点,具有深刻的文学意义。
(一)对“化外之地”的文化认同感艾芜的“南行”系列小说所描绘的滇缅边境,是一个环境恶劣、盗匪横行、毒品泛滥的“化外之地”。对于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们来说,西南边地是一个气候环境恶劣、充满凶险与荒蛮的地方,但艾芜在勾画边地世界时却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异域。文中边地子民面对来自英国、缅甸等洋官的黑暗压迫,仍然有一颗善良宽容、慷慨大度的心。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坚韧顽强的与命运作抗争,这源于艾芜从人性的视角出发去理解边地子民对于自由生命意义追求:“人生的意义全是由各人自己寻出来、造出来的:高尚、卑劣、清贵、污浊、有用、无用……全靠自己的作为。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或一只猫、一只狗,有什么分别?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于自己怎样生活”。[11](P30)艾芜笔下的底层小人物们没有大的人生志向,追寻自由就是他们全部的生命意义所在。即以职业而言,响马贼、流浪汉、私烟贩子、抬滑竿的、赶马的,他们多靠体力谋生,充满随意性与自由性,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大把的花钱,抽鸦片喝酒是他们的生活常态,甚至他们不愿意有固定的家庭。出于对自由的向往,他们往往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女人对于他们来说,可有可无。包括叙述者“我”,也是一个漫无目的、边走边看的赶路人,而路在何方,“我”是不知道的,或许自由自在的行走本身就是目的。童年时的艾芜面对着来自祖父的压力,刚满十岁又被父母强定终身,后因受到“五四”新思想洗礼而毅然离开封建家庭,孤身一人踏上南行之旅。“漂泊是艾芜的主动选择,作为青年人,他不甘寂寞,不愿被束缚在故乡偏僻角落过平庸生活,想要在漂泊流浪中开阔人生视野,认识世界,让自己的生命力得到尽情释放,满足自己本性当中探索和冒险、追求自由生命境界的需要。”[12](P281)所以,边地子民为了获得自由与命运进行顽强抗争,他们面对黑暗压迫时能够毅然反抗,是为艾芜所极力张扬的。
(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从现代中国文学主流来看,与艾芜同时期的作家大多旗帜鲜明的分属于“为艺术”派或“为人生”派,而艾芜则以浪漫主义的笔法对人生世相进行现实性的描绘,是现实主义写作与浪漫主义精神融合的产物。就题材来说,艾芜基于自身体验,扎根于现实的土壤,把自己南行经历中的所见所感表达出来,向读者展现边地子民们在黑暗压迫下顽强求存的生命意识,流露出作家浓重的现实主义关怀精神。作品中的人物生动形象,无论是“我”还是其他底层小人物,都是从现实情况出发,经过艺术加工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真实可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此外,尽管作家扎根现实,但并没有执着于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而是将浪漫主义精神融入作品之中,使作品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南行”系列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景物描写在作家笔下的篇幅之大和作用之重。很多作品中开篇写景,中间依然写景,甚至贯穿全篇,这些边地异域风景的描写为艾芜作品的浪漫主义形成奠定了基础。边地子民对待生活积极奋进,乐观进取,尽管很多都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但却充满着对生活的激情和对自由的向往,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顽强抵抗,追求光明的未来,且永远对未来抱有希望。那些“袍哥”式的人物都具有英勇侠义之气,性格慷慨豪爽。这些都洋溢着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息。总的来说,艾芜的创作倾向决定了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只是在文学创作上将浪漫主义精神贯穿于其中。
在“南行”系列小说中,艾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文坛留下了具有“异域”色彩的西南边地小说,将滇缅边境的风俗人情、世相百态用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带来了别样的文学体验。这位被称为“墨水瓶挂在脖子上写作”的作家,只身一人漂泊于滇缅边境,将自己的青春奉献于文学道路,这种写作精神值得每一位作家学习。王晓明曾指出:“艾芜缺乏其他现代小说家那样长久的注视丑恶的特殊耐性——越是感到黑暗现实的沉重压力,就越要向人们表达对美好事物的执着信念;这就使他必然转向对漂泊经历的亲切回忆;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找到足够明亮的色彩。”[13](P128)在孤独的流浪生涯终结后,西南边地成为艾芜的创作家园和心灵净土,那些边地子民纯朴善良、坚韧顽强的美好品性散发着人性的光芒。作家用独特的异域书写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点的异域形象,开拓了新文学的表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