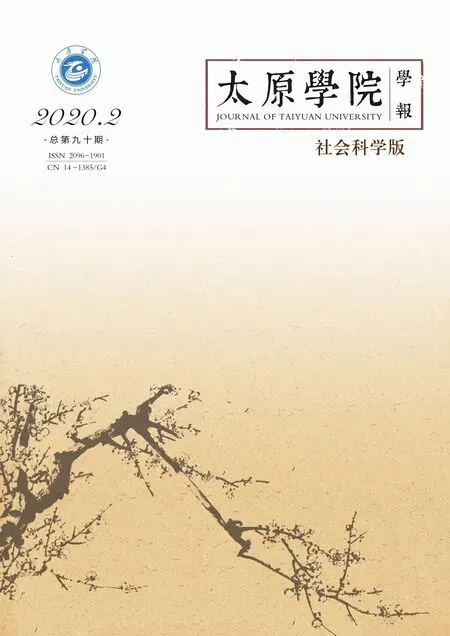谈对鲁迅内心非理性因素的把握之必要性
彭冠龙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鲁迅研究已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有学者统计,“从1913年到2012年的100年间,中国各类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共计31030篇,出版相关研究著作1716部”(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这些数字的精确度如何,并不重要,它们的意义在于描绘了这一领域已被开掘的广度和深度,数万篇文章和上千部著作已经从多个角度塑造了一个“大先生”的文学史形象。这是一个随时处于理性状态中的形象,他每一个观点的提出、每一次选择、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密切关注并深度参与当时的文学发展历程;他在回顾和总结中国文学史脉络和经验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并提出了若干深刻的文学观念。可以说,“大先生”形象是符合鲁迅其人实际情况的,然而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即“鲁迅崇拜”或“圣化鲁迅”,甚至《鲁迅全集》在特定时期会成为“国家原典”(黄海飞:《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考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9期)。之所以会走向这个极端,原因很复杂,仅就文学研究方面来讲,是因为“大先生”形象只是鲁迅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鲁迅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却被放大为整个鲁迅形象。在近年来强调“回到鲁迅本身”的情况下,作品和各类史料得到重新解读和探索,然而这一努力的方向仍然是研究一个随时处于理性状态中的鲁迅,或者说是将理性状态作为研究的默认前提。
人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非理性因素在人的言行举止中起着重要作用,鲁迅也不例外,他的很多作品所表达的是一种不稳定的情绪。比如《野草》,《题辞》的开篇就讲“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沉默时的思绪往往是纷乱的、驳杂的、任其驰骋的,几乎不可能条理清晰地向着一个维度延伸,非理性色彩很强,鲁迅以此感到充实,开口表达这些思绪则需要理智的约束,此时的空虚正显示了理性因素的缺失,这句话很好地展现了一个处于非理性状态中的鲁迅形象。《野草》中的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我的心分外地寂寞”,多次描述的“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我梦见自己在做梦”“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作为主要场景的“秋夜”“暗夜”“昏沉的夜”以及与之相关的“黑暗”,几乎都是非理性的,是在某种刺激下形成的令人心乱、难以言表的感受,只能通过一系列幻象表现,而这些幻象正是人在沉默时脑海中的画面。其他作品如《药》,“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如《明天》,“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也都不能说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这些“呐喊”,据《呐喊·自序》的陈述,是源于未能忘却的“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也并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这些话反映出的正是理性力量的虚弱,不足以限制心中的某种冲动,只能任由冲动释放。
鲁迅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因素有很多种,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游民的生活感受,二是被排挤的压抑感。
所谓游民生活感受,是指飘泊游荡的生活状态和由此产生的游离于宗法社会秩序、主流秩序之外的感受,鲁迅一生多次感觉自己处于游民的状态中,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里说“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这种对居住环境和生存状况的回忆所反映出的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游民体验,必然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比如这间屋子或许就是《阿Q正传》中土谷祠的原型,又如作品中所写“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或许就是鲁迅当时生活状态的写照,这些都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却真实地进入了作品,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南下广州的途中,鲁迅给许广平的信里说:“所以我此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游民而创作?倘须兼顾,即两皆没有好成绩。” 鲁迅显然是将自己的游民状态与创作联系了起来,而且认为这是创作的必备条件。这种游民生活感受对其创作最明显的一个影响在于,鲁迅笔下的故乡总是暗淡的,“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故乡的景象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点活气”,记忆中的故乡,“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故乡》中所写的回乡见闻几乎都笼罩着一层阴暗色调。《在酒楼上》所写的故事发生在“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的地方,气候环境仍然是“深冬雪后,风景凄清”,心情同样不是很好,“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也呈现出晦暗的色彩。《朝花夕拾》中,“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正是给许广平信中所言“作游民而创作”的时候,“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自然也是游民生活状态,八成篇章都在这种状态中写成,可以看到凡是回忆故乡的内容,虽然有比较愉快的内容,但是并没有流露出愉快的语气,甚至夹杂了一些不愉快的记忆,总是呈现出一种对故乡的隔膜感和疏离感。诸如此类的晦暗、隔膜,并不是形于文字表面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其中可能不包含任何思考,它的形成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其根源在于长期游民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游离感。对故乡的怀念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地域认同感,而游民生活感受则是对宗法秩序的背离,这一非理性因素给鲁迅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被排挤的压抑感主要集中于鲁迅的晚年,特别是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在鲁迅的通信和相关文献中,反复出现以下语言,“说起我自己来,真是无聊之至,公事、私事、闲气,层出不穷”,“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一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今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自问历年颇不偷懒,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常有人要趁这机会把我扼死,真不知何故”,“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冯雪峰在《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一文中回忆了他与鲁迅对话时的一个细节:“谈到上海当时文艺界情况,他神情就显得有些愤激;他当晚说的许多话大半已经记得不大清楚,其中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是‘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另一句是‘我真想休息休息’”,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鲁迅面对当时文坛论争局面,尤其是一些革命文学家对他的批评,压抑感已经达到了自己无法承受的地步,突破了理性所能控制的限度,进入了一种长期处于非理性状态中的生活。灰心和疲倦使他“想什么也不做”,“时常想歇歇”,开始忽略眼前不必要的琐事和麻烦,眺望“中国文艺的前途”,产生了许多独特的想法。加之此时疾病缠身,甚至长期昏迷,其思想中的理性力量越发疲弱,于是表现出了很多让我们难以理解的举动,比如《自嘲》一诗,很不符合一个“战斗者”鲁迅的形象,如果结合此时的日记,会看到这段时间鲁迅一直在治病,持续时间较长的疾病状态必然影响了他的心态,又如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事件,如果从理性角度展开讨论,就会显得迷雾重重,因为这件事本身就发生在鲁迅的非理性状态中,挫败感渐渐占据了他的内心世界,病痛已经夺走了他旺盛的精力,“累”是他的主要感受,“休息”是他的最大愿望,他还想入世,但这种入世是超脱现时的。对于这样一位鲁迅,我们在考虑他一贯坚持的原则和主张的时候,会发现这些原则和主张已经无法完美阐释这个人的言行,只有充分理解了他此时的非理性状态,才能从他的处境和心态出发,充分把握其内心感受,感悟他的精神世界,不然就可能造成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