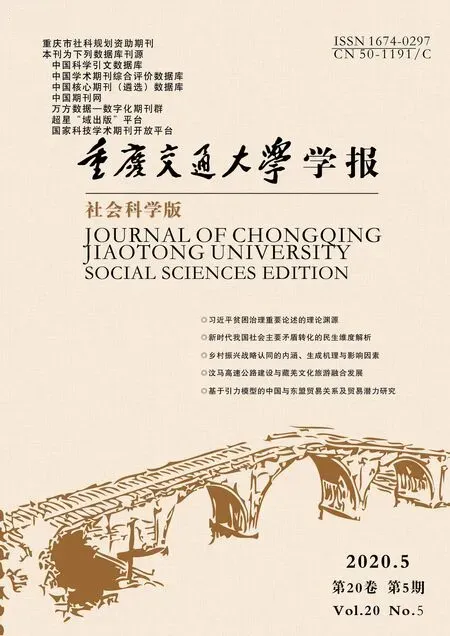飞扬中的悲凉
——评须一瓜新作《五月与阿德》
徐 翔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69)
须一瓜可以称得上是新世纪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新世纪伊始,原本是政法记者的须一瓜陆续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知名刊物上发表小说并引起广泛关注。曾经的记者身份让须一瓜成为文坛上的一个另类,各种案件和卷宗成为她创作的灵感源泉,《淡绿色的月亮》《雨把烟打湿了》《蛇宫》《太阳黑子》等作品都可以看到她职业身份的痕迹。但须一瓜并没有让这些犯罪类型小说成为市民们津津乐道的奇闻逸事和谈资,她总能抓住隐藏在事件背后的人的欲望和灵魂。在她的笔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隐秘的精神世界一一呈现,令人惊叹,难怪须一瓜被称为“精神警察”[1]。
须一瓜发表于2019年《收获》长篇小说专号的新作《五月与阿德》令人有种惊喜,体现了作家在创作上新的开拓。小说不同于以往须一瓜的类型小说,没有什么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案情,非常接地气,写了两个小人物之间的暧昧情感、信任、依靠和背叛,小说里的人生是毛茸茸、热腾腾,极具质感的。这是一部以人物构筑的小长篇,作品名字就是小说里的两个主人公五月(女)和阿德(男)。初看小说篇名,再联系须一瓜以往的创作,会让人猜测小说也许是关于一男一女的爱情故事,事实上却不是。一个是患有脊柱侧弯的年轻女孩,一个是做人做事一丝不苟的独居老人,当他们相遇并住在同一屋檐下,会发生什么?从这一点看,小说又有着须一瓜以往类型小说极具戏剧张力的故事。在创作谈中,须一瓜提到曾经采访过脊柱侧弯和老少暧昧情谊的人,但她并没有把这样的题材写成“吸睛”的类型小说。“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其实给我提供了最开阔的认识人生的窗口。它对我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呈现了怎样的生活状态,它可能更好地给我提供了一个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世相的非常好的方式。它给予我的东西,要远远大于给所谓素材的本身。”[2]也许以往的素材给了须一瓜创作的灵感,但这篇小说不再执着于探寻人性的善与恶、灵魂的罪与罚,而是转向人的生命。
一、身体与梦想
小说是关于梦想的故事,五月活在现在和未来关于城市的梦想当中,阿德活在过去人生光荣岁月的梦想当中,他们的梦想却都与身体相关。在须一瓜看来,身体就是移动的梦想,她一直想写一部关于身体的小说。在她看来,身体延伸了心灵,身体的力量就是精神力量的展示。我们理解他人,理解社会,领悟百态人生、万千世相,任其山高水长,都从身体出发。
小说中的五月是一个生活在岭北菇窝村的乡村女孩,从她出生,她的身体就与家人格格不入,更是与封闭、落后的乡村格格不入。她的母亲是“干枯焦黑”,两个哥哥“像田鼠一样”,父亲“又懒又脏,常年鼻涕不止,活了四十多年,从来就没有过人的正形”。而五月出生的时候,“眼如星光,一头柔软鬈发,美好地掩映着净如满月的脸”,“真是五月的花朵啊”(1)本文未标注出处的引文均出自须一瓜的《五月与阿德》原文。。花朵般的五月似乎投错了胎,“像一张打错的牌”,这样美丽的女孩生在菇窝村总让人有暴殄天物的感觉。长到十三四岁的五月,仅仅是干干净净,没有新衣服的装饰,就显示出异于常人的清美。五月在菇窝村是一个异类,也许是老天爷发觉自己的牌打错了,于是“老天开始纠正错误了”,五月发现“自己身体的长法不太周正”,“她的腰好像有点直不起来了。她听到自己两只脚落地的声音,好像轻重不一”,“还有乳房。它们也越来越不整齐长了”,“她一边的肩胛骨渐渐厚了起来”。五月的脊柱侧弯(俗称剃刀背)症状开始慢慢显现出来。老天打错的牌不仅如此,五月不是人们惯常思维当中淳朴、勤劳、安分守己的乡村女孩,相反,她又懒又馋,生性还不安分,山货客拿几个金鱼尾巴的酒心巧克力就让五月不断地遐想外面的世界。那个年代,农村女孩向往外面的世界很普遍,尤其是五月这样美丽的女孩,她似乎天生就不属于菇窝村,但五月又不是铁凝笔下的香雪,香雪是淳朴善良的,是自尊自爱的。五月的不安分却是危险的,她并不自爱,几个巧克力就让她被山货客蛊惑,失了身,山货客用四万元钱和“一定会来娶你”的谎言脱身。不甘等待的五月决定独自去骊州城闯荡,找到山货客,因为“她要和他结婚”,“她可以在城市里,坐个月子,让她的身体变好”。
故事到这里,似乎是常见的“乡村女性进城”的主题,乡村女性进入城市,便置身于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会遭遇种种困难,诸如物质困境、身份困境、光怪陆离的都市诱惑等。五月在骊州城没有找到山货客,结婚、坐月子、养好身体的憧憬破灭了。五月不得不自力更生养活自己,并无一技之长的五月在那个号称“小香港”的骊州城生存下来谈何容易,偏偏她又不是勤劳能干的,反而有着和她身份不相称的娇气、贪小便宜的市侩气,从最初在“丝丝美”发廊做洗头妹,后到东方之珠足浴城做收银员,她的日子并不轻松,尤其是还要面对城市的种种诱惑。尽管五月脊柱侧弯,但她还是美丽的,美丽的女人在城市往往也是危险的。在别人眼里,五月“新鲜得就像长错地方的狗尾巴草”,“青春日益逼人”,随便戴上一顶贝雷帽,就有“脱胎换骨般的性感迷人”。这样的美貌女孩总是男人觊觎的对象,加之五月本身的虚荣,很可能沦落为出卖肉体的风尘女子。但幸运的是,五月遇到了阿德,他们的相遇仿佛是命运使然,五月住进了阿德在真武路21号的别墅,脊柱侧弯也有了治愈的希望。就这样,身体让五月有了进城的梦想,有了让自己脱胎换骨的梦想,有了扎根城市结婚有房有娃的梦想。
五月的梦想是关于当下和未来的,而阿德的梦想则是关于过去的。阿德的人生就是五月憧憬的城里人的高贵样式,这高贵样式同样来自阿德的身体。不同于五月身体的缺陷,阿德的身体除了有点轻微罗圈腿之外几乎是完美的,“一米八三的身高、八十公斤的体重”,有着“直正的腰背和擎天柱气势的脖颈”。这样的身体让阿德拥有了一段光荣岁月。年轻的阿德到了北京,成了中央警卫队仪仗营的一员,参加了赫鲁晓夫到访的欢迎仪式,因优秀的礼宾表现立了功,如果不是受了腰伤,阿德的光荣岁月会更长。作为仪仗兵的四年时光是阿德人生的巅峰,“这四年的黄金岁月所激发出的生命之光,好比心如灯笼,一直照耀着他的胸襟和他前行的步履”。很多年之后,阿德仍保持着傲然的身姿,“看上去就像一颗笔直的水杉,始终保持着生长直上之气势”,能踢出标准的正步,能保持眼睛迎风三十秒不眨眼。只是阿德没有发现,他只是活在过去的光环中,他的梦想是停留在过去,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乌托邦。“从军四年的金色时光,犹如巨大的灯塔,照耀着阿德一生的生命航船,尽管灯塔之光与航船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几近完美的身体成就了阿德一生的荣光,也养成了他一丝不苟的性格和严谨刻板的生活方式。面对五月,阿德不仅在身体上占领了高地,继而在道德上也占领了高地,容不得五月身上不符合他生活方式的陋习,拒绝五月怕鬼的封建迷信,容不得五月的欺骗。这样的阿德,在五月眼里有着日晕般的光芒。
正如须一瓜所说,身体是移动的梦想,五月的梦想从乡村移动到了城市,阿德的梦想从过去移动到了现在。只是,梦想虽美,但却是脆弱的。吃不了苦、懒散,有着女人自私的小心机的五月难以在城市立足,也难以纠正自己有缺陷的身体;活在过去光环中的阿德难以抵挡岁月流逝带来的身体的衰老。不论是五月飞扬的青春,还是阿德飞扬的过去,都难免悲凉的结局,身体终究不能成就他们的梦想。
二、镜像与卡利斯玛:关于身体的战争
五月与阿德两个本无交集的人,因为一场意外的“英雄救美”相遇。五月在晚上回家途中被一男人劫持,刚好路过的阿德呵斥退歹徒,不但亲自护送五月回到住处,还邀请五月到他家中居住,五月当然也毫不客气地住到了阿德位于真武路21号的别墅中。阿德发现了五月的脊柱侧弯,带五月看医生,并且开始了对五月身体的矫正训练,这样一个对身体的改造过程可谓是一场拉锯战,做事虎头蛇尾、充满惰性的五月遇上行事坚毅的阿德,注定了这场身体改造的战争的艰苦。
这是一场和身体有关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始于五月和阿德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没有相遇之前,两人对自己身体的认知都有点脱离现实的幻想成分。五月一直遮掩自己的身体缺陷,因此在别人眼里她是“直正的,健康的”;对实际已五十多岁的阿德而言,“他家的立柜穿衣镜从来都告诉他,他看上去最多四十出头”。五月是刻意回避自己的身体,而阿德如水杉一样的身体可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但阿德还是理想化了自己的身体, 他们对自己身体的认知似乎都和现实有些错位。直到两人住在同一屋檐下,不得不近距离接触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自己真实的身体。对方的身体就像一面镜子,映射了自己真实的身体,“人对于自我的认识是通过自己在外界的映像反作用于人的心理,在水中或是其他反射物比如镜子中得到自己的印象,凭借这种映像,人可以确立自我的形象”[3]。阿德伟岸如水杉一样的身躯时时提醒五月是一个脊柱侧弯患者,直到被阿德发现,她有缺陷的身体仿佛处在聚光灯下无所遁形,她不得不面对自己有可能变成一只扁壳蜗牛的命运。五月有缺陷的身体勾起了阿德内心关于身体的隐痛,他有轻微的罗圈腿,他逝去的妻子宝玲也有括号般的罗圈腿,这成了他人生中一个巨大的遗憾,一个消失不去的记忆,尽管阿德的罗圈腿经过痛苦万分的强力矫正已看不出来,但五月脊柱侧弯的身体仍时时提醒着他身体上曾经有过的小小瑕疵。可以说,阿德是一个对身体有着偏执洁癖的人。
当他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真实的身体的时候,这场身体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阿德矫正罗圈腿的经历告诉他,身体是可以人工改变的,自己就是一个人定胜天的活样板。阿德带五月看医生,当得知暂时不用动手术时,就开始了对五月身体的改造过程。阿德在院子中准备了旧单杠,监督五月每天要完成吊单杠、燕子飞等脊柱牵引动作,从最初磨合期的不适应到逐渐适应,“阿德拿出了超人的意志,全力以赴在修正上帝的错误。他立志创造一个好的女人”。对五月身体的改造仿佛也能消除阿德生命中那个小小的身体瑕疵,是在完成他对于完美身体的幻想。为此,阿德十分享受这个过程,“他很享受自己的果断与苛刻,享受着令出必行、行必有果的巨大妄想”。对于这样的身体改造,懒散的五月总想逃避,但次次都失败于阿德的“卡里斯玛”(charisma)效应。“卡里斯玛这个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人的一种非凡品质……被统治者凭着对这位特定的个人的这种品质的信任,而服从这种统治。”[4]在五月眼里,阿德是有着个人威信和魅力的人,充满着光华,是她理想中父亲的样子,“干净、威严、什么都懂”,她对阿德有着父亲般的崇拜和敬畏感。有着父亲光环的阿德在五月面前有着卡里斯玛式的权威,在对五月身体改造的过程中,这种权威总能战胜五月的懒散和退缩。阿德还会不断用语言来强化卡里斯玛权威,他会不断告知五月不矫正就会变成扁壳蜗牛,不断重复当年做仪仗兵练习正步的各种艰苦训练场景。阿德利用自己的卡里斯玛权威对五月进行身体改造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身体的规训。他也曾用捆绑双腿的形式矫正妻子宝玲的罗圈腿,事实上,这种规训不仅体现在身体上,还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纠正五月的种种恶习,要求五月背诵《世界名人名言》,以至于后来五月能脱口而出各种名人名言。
这场有关身体的战争,表面看是阿德在改造五月的身体,实际上五月年轻、生机勃勃的身体也在改造着阿德,这种反改造像缓慢流淌的河流,不易察觉,却能以阴柔的力量冲刷着河床。阿德为了矫正五月的脊柱侧弯,不仅要求五月学会保健按摩,也为五月进行脊柱侧弯的保健按摩,五月为阿德受伤的腰椎进行保健按摩,她向阿德敞开自己充满秘密的美好身体。当有一天,阿德看到五月熟睡的赤裸的美丽身体时,潸然泪下,“躺在一半阳光中的身体,静水深流着阿德看不见的生命潜流”,五月的身体“像另一面旗帜,它在无声地传承着过去岁月的静好深流”,“那身体天成的纯然之美,令他哀伤失落”。阿德的身体是一面旗帜,几乎是完全精神性的东西,他就活在这面精神旗帜之下,以自己了不起的身体为傲。事实上,阿德从未感受到身体的生命力、身体天然的美。对他来说,身体似乎带有某种肉欲的原罪感,这是阿德无法接受的,可他这种认知猝不及防地受到五月年轻、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五月的身体对阿德同样有着卡里斯玛效应。五月对阿德的身体保健按摩有时候游走在性的边缘,此时的阿德总是既享受又懊恼,“这一辈子,他终于拿着废弃的旧门票,偷偷重返游乐城”,这让阿德意识到自己过往的岁月实在是过于枯燥呆板。阿德是一个在性上非常寡淡的人,似乎崇尚身体上的极简主义。妻子宝玲去世后,他对爱慕自己的小姨子宝红视而不见,本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体验到身体的生命活力,但宝红丰满动人的身体对阿德来说就是洪水猛兽。面对五月年轻的身体,阿德无法控制地挣扎在身体自然属性的召唤之下,感到自己以往的人生和身体是那么苍白。五月婚后和丈夫大麦与阿德同住,夫妻俩闺房之乐的声音总是冲击着阿德的神经,“阿德不断被捕获,乃至眩晕漂浮,身首分离。阿德这辈子第一次明白,女人是可以被男人奏响的”,“一年又一年,那个等待他奏响的好时光,可能就那样淡漠荒芜了”。阿德这一辈子没有奏响过女人的身体,他的身体也没有被女人奏响过,他觉得自己辜负了什么,他的一生本可以另一种方式度过。阿德的心态变化正体现了五月对他不动声色的反改造,他本立志要在五月那个残缺的身体里开发出显示理想的现实性潜能,他想赋予它以美与价值,没想到他想要改造的身体却以更娆美的物质性、更丰赡的经验力,纠偏着、嘲讽着他。
这场身体的战争始于对身体的认知,纠结着改造与反改造的较量。阿德试图把五月的身体改造成他理想中的精神性的身体,最终却被五月年轻美丽的身体征服,他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和身体原来那么苍白。
三、谎言与背叛:身体的敞开与灵魂的隔膜
五月与阿德之间的身体战争,让他们彼此彻底看见对方,他们跨越了性别年龄和时代鸿沟,将自己的身体向对方敞开。但身体的敞开并没有让他们的灵魂更近,无论谁对谁的改造,都并不容易完成。事实上,他们彼此的根基都太差了,最初的相遇每个人都怀着一撮小小的杂念,而最终造成他们人生悲剧的根本是由小小的杂念和心机导致的谎言与背叛。他们向彼此敞开自己的身体,却没有敞开自己的灵魂,这摧毁了他们生命所有的努力与满足。
来自乡村的五月来到了城市,住在真武路的别墅,看似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但实际上她从来就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如同她身处的真武路那栋红砖小楼,“这个楼房的一楼,充满陌生与对抗,还有强烈的排斥她的阴沉气息”。阿德对五月的接纳不乏怜惜的成分,可五月身上的乡巴佬气也让阿德油然而生城里人的优越感。他们的相遇从一开始就有着某种落差,既有物质性的差距,也有精神性的差距。阿德尤其享受对五月的优越落差,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对幸福的确认”。面对五月,阿德会不断盘点自身的优越,“那个缺识少教、心性孱弱的小丫头,激发了他另一种生命理想。阅历丰富,天命尽知的阿德,参照凸显出自己不平凡的优越人生”。五月想努力融入城市,竭力包装自己,阿德享受面对五月的那种优越感,这种杂念注定他们不会向对方敞开自己的心灵。
他们相遇的最初就充斥着谎言,五月骗阿德说自己的父亲是村里的老师,面对城市,五月有着某种自卑感,她需要用谎言来伪装自己,借此摆脱心理的弱势,谎言“担负着协调她和骊州之匹配的责任”。阿德面对五月同样也有谎言,他含糊其词地口述家族史,让五月对他和真武路的红砖小楼充满了敬畏感。事实上,阿德家并不是真武路小楼的主人,阿德祖上只是原屋主家的下人,受托看顾房子而已,真正的主人们散居海外,没人愿意兴师动众漂洋过海来行使权利,导致阿德作为房屋管理人仿佛就是房子的主人。无论是五月美化自己的父亲,还是阿德美化自己的家族史,都是谎言,都带着小小的心机。五月要让自己的出身和城市更匹配,阿德要让家族史与自己曾经的光荣岁月更匹配,并且享受着这种优越感,反而体现出他们面对对方时,尽管原因不同,都有些许胆怯,充满种种杂念的谎言最终摧毁了他们的人生。五月与阿德之间的美好情谊遭遇的第一个危机,源于五月的另一个谎言。阿德允许五月在自己家白吃白住是因为对五月的怜悯,也能满足自己的优越感,尽管五月又懒又馋,在阿德眼里仍不失为一个好女孩,直到阿德发现五月夹衣里的两万元钱,五月暗藏的秘密太多了。在阿德追问下,五月只得坦承钱是当年委身山货客得来的,并且还有两万元埋在家乡的破砖窑里。得知真相的阿德虽然心如死灰,浑身颤抖,但最终还是原谅了五月,让五月以他的名义把钱存进银行,但谎言还是让彼此之间的情谊出现了裂痕。
五月有着女人的小小心机,也有着城里人的狡猾,不仅是对阿德,面对丈夫大麦也是如此。五月与大麦结婚后,始终对丈夫隐瞒存在阿德那里的小金库,面对同床共枕的丈夫,五月仍旧充满了谎言,变得越来越“作”。五月因为怀孕,硬要租住更好的房子,大麦因为经济紧张,不得不放弃了和朋友合伙买二手车跑运输的生意;五月生孩子因为并发症几乎病危,大麦不得不去求姐姐;生完孩子后的五月无法工作,大麦生意不赚钱,只得接受姐姐援助开了窗帘店,五月在夫妻俩生活艰难的时候也绝口不提存在阿德处的私房钱。当五月流露出想拿回私房钱的时候,阿德总会以种种理由说服她,阿德这样做,也有着自己的私心,如果五月拿回这笔钱,她和阿德一点联系都没有了,这个女孩也许会彻底走出他的生命。五月在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因为严重的并发症不得不动用私房钱,可对丈夫已经撒了谎的五月不得不继续编造谎言,说钱是向阿德借的,并且写了借条,不知情的大麦一旦有钱就会去还阿德利息。大麦后来经济状况好转,和五月考虑买房落户口,五月依然不提私房钱,两人只买了能落一个户口的小房子,五月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应先获得户口,但没想到大麦先落了户,发了疯的五月立刻让阿德出面以儿子生意失败急需用钱为由逼丈夫还钱。那张借条阿德还给五月,五月却没有收好,阿德又收了起来,而这张借条的失误让五月和阿德的人生最终落到了地狱。
落户事件之后,五月一度过上了幸福的小日子,她经常处于“赚大钱做手术,然后扬眉吐气当城里人”的遐想中。此时的阿德却中风住了医院,在五月眼中,阿德“完全就像一根丢在墙角的肮脏拖把”,五月厌弃这样的阿德。当某天阿德的儿子拿着那张借条逼五月还钱时,五月成了一只尖叫的野兽,终于讲出了假借条的事情,丈夫对她彻底失望了。原本作为谎言高手的五月,已经“失去了启用任何谎言的基本要件。是她自己堵死了调度一切谎言庇护的机会”,真相太残酷了,把这个甜蜜之家伤得支离破碎。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的五月最后到老人院找到阿德,当面指责阿德是骗子,可于事无补,阿德只是哭求五月带他走。阿德偷藏借条的背叛让五月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绝望的五月最终纵身从医院天台跳下,阿德则惨居于养老院中。
五月和阿德的悲剧都源于谎言与背叛,如果当初两人相遇时都能对对方坦诚一些,如果五月能对丈夫大麦坦诚一些,他们的命运也许就不同了。五月的谎言是想改变自己卑微的命运,成为城里人,能有个正常的身体,日子过得舒适体面点,也带点女人的心机;阿德的谎言是想维系曾经的光荣岁月带给自己的尊严和光环,以及对青春的渴望,阿德最后收起借条的行为无疑是想让它成为留住五月的最后砝码,他试图用谎言留住自己苍白人生中的一点生命气息。五月和阿德都不曾想到,谎言引发的背叛最终让他们一无所获,五月失去了钱,失去了丈夫和孩子,失去了生命;阿德则失去了五月,失去了人生中因为五月的介入而曾拥有的生命气息。相比身体的敞开,心灵的敞开和信任原来更难。
《五月与阿德》全然不同于须一瓜以往的类型小说创作,显示了作者对既往写作经验的挑战和不断自我突破的努力。这是一部极具个性的反类型小说,尤其是小说中两位性格上都有点“作”的男女主人公和他们之间借身体而展开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同时显示了须一瓜写作上所具有的能力,对人物、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游刃有余的艺术表现力,这种能力足以支持作家写出或类型或个性的小说。这种能力在《五月与阿德》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呈现了小人物有质感的生命,写出了他们飞扬中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