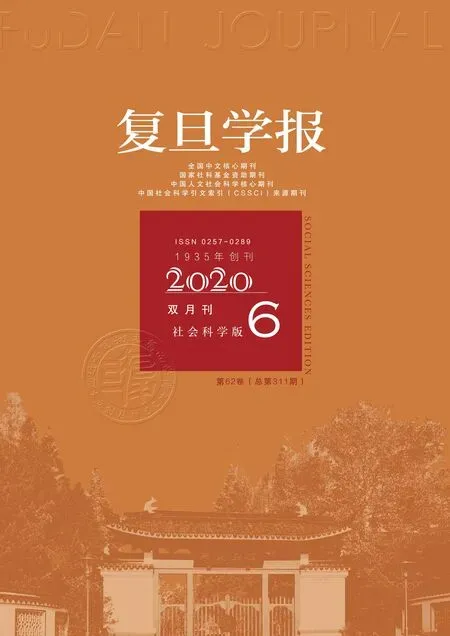形式批评理论与现代《楚辞》研究范式
——以《卜居》《渔父》研究为例
王汝虎
(曲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日照 276826)
在近现代《楚辞》研究中,之于《卜居》与《渔父》两篇真伪问题,一直是诸学者争论的焦点,其中以句法与体式为中心的形式分析更成为其训释与立论的基础。因其涉及辞赋体式在历史中的源起与发展,又关涉到古代文学研究中形式批评理论的展开,故可作为一种案例加以详叙。其背后除体现诸现代学者对传统诗学和文章学的承继外,更可见西方知识资源特别是西方古典学、形式主义等理论传统起到的旁照作用,在对句法、体式和韵文观念发生发展的探讨中,他们实际触及了在经典文本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形式审美和历史意识的互动关系。闻一多曾在《楚辞校补》中指出《楚辞》研究同时具备三种困难,包括年代久远史料不足所造成的背景说明之难、多用“假借字”而造成的诠释字义之难和传本讹误所造成的校正文之难。(1)闻一多:《楚辞校补·引言》,见《闻一多全集》第三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第7页。由此,在现代《楚辞》研究中,对屈赋文本与形式的厘定、体认和评判,是其中最为确实和重要的理论切入视野。如刘永济先生曾总结道:“今人衡建古文艺,喜从句度韵律,断其时地,辨其真伪,于屈赋为尤甚”(2)刘永济:《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页。,更直接点出了此种形式批评理论与视野之于屈赋研究的重要性。在新时期学科分类影响下,版本校勘与语辞规则往往被分划为语言学、训诂学和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古文学与古文论研究则往往以理论观念和意义探讨为研究对象,此种知识领域的区隔对于有着漫长经学背景和修辞学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遮蔽和疏离。故分析现代《楚辞》研究实践中的形式批评理论,对于当下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论史话语体系建设与学科有效性的探寻,均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与方法论价值。
一、 《卜居》《渔父》作者考辨与形式批评方法
当然,《卜居》《渔父》两篇的真伪和作者问题古人早有论及,如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虽然一面肯定“《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但在《渔父》解题中,又言“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也”。(3)见[宋]洪兴祖撰,黄灵庚点校:《楚辞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9、286页。
此种注释给后世二篇文献的作者与真伪问题留下了争议空间,如清人崔述在《考古续说》中言“是知假讬成文,乃词人常事。然则《卜居》《渔父》亦必非原之所作也。”(4)[清]崔述:《考古续说》卷一,见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47页。然从司马迁、刘知几、朱熹到汪瑗、顾炎武等人均承继王逸肯定之言,大多以二篇为屈原所作无疑。而受古史辨派疑古思想和西方科学精神影响,二十世纪诸多楚辞研究学者,除刘师培(《楚辞考异》1911年)、梁启超(《屈原研究》1922年)和谢无量(《楚辞新论》1923年)持肯定意见外,鲁迅、胡适、郭沫若、游国恩、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朱东润、王泗原等人则多认同此二篇并非屈原所作而为后人伪托。当然更有廖平(《楚辞新解》)、卫聚贤(《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何天行(《楚辞新考》)、丁迪豪(《离骚的时代及其他》)等人或否定此二篇为屈原所作,或更激烈地否定《离骚》非屈原所作,诸说此文且不论。
现代《楚辞》研究中,除陆侃如(《中国诗史》1931年)和郭沫若(《屈原研究》1953年)外,较客观地、学术性讨论《卜居》《渔父》,并否定屈原为其作者的,以游国恩先生的观点为代表,他提出:
现今所传的屈原作品二十五篇中,最成问题的是《卜居》《渔父》两篇……《卜居》和《渔父》两篇,从前崔述就怀疑过。他认为都是后人假托的,这和庾信的《枯树赋》讬之桓大司马,谢惠连的《雪赋》讬之司马相如,谢庄的《月赋》讬之曹植是同样的作风。假讬成文,是赋家的常事。据我看,这是颇有道理的。(5)游国恩:《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见《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7页。
而以陈子展先生和姜亮夫先生为代表,则认为《卜居》《渔父》二篇为屈原所作而非后人所托名。陈子展先生在《〈卜居〉〈渔父〉是否屈原所作》(载《学术月刊》1962年第5期)、《论卜居、渔父为屈原作》(载《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七辑)两文中独标旧说,以为现代诸学者否定屈原为作者的立论并不成立,他引朱熹《楚辞集注》和洪兴祖《补注》之说,认为“这就说明了《卜居》的主题,而作者当为屈原,他人不见得一定处此境地,有此思想情感,有此作的必要。”(6)陈子展:《楚辞直解》,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50、669页。姜亮夫先生在其名作《重订屈原赋校注》(1931年成书,1957年出版)中亦全面肯定汉人王逸的观点,以为包括《九歌》《卜居》《渔父》和《远游》等在内常为近人质疑的篇目,均为屈原所作或屈原润色而成,他从思想情感与寄情讬兴角度肯定曰:
一则以离骚为本幹,总其义类;以九章为枝叶,以渔父、卜居条其理趣,澌为波澜;以远游充其情思,以尽其流。凡此皆以个人感喟为主,从己身之修姱自洁,以引入于去国出世之思理。(7)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见《姜亮夫全集·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当然姜亮夫先生的楚辞考证除建基于对传统训诂学的继承上,更充分汲取了现代考古学、神话学、宗教人类学等学术理念,来建立起其丰赡完备的楚辞学理论体系。
上述诸多论证,除古人以意逆志式的推断和一些其他历史材料的旁证外,两种对《卜居》《渔父》作者问题截然不同的立场,其立论核心正如陈子展先生所言:“很多论点都像是偏重于形式方面而立说的。”(8)陈子展:《楚辞直解》,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50、669页。在对《卜居》《渔父》的辨伪研究中,诸家对此二篇在古代文体发展中的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唐文治所言“《卜居》《渔父》两篇在有韵无韵间,后来设难之体,实权舆于此,六朝问答之文,皆其支流也”(9)唐文治:《论文琐言》,见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392页。。亦即是说《卜居》《渔父》两篇独特的韵散体式和设难问答形式,于汉赋和六朝文影响巨大,故对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从文献诠释的角度而言,勘定包括《卜居》《渔父》在内的屈赋作者与文本的可靠性,必须回溯到汉代楚辞文献形成的初始时期,特别是汉代刘安、刘向、王逸、司马迁等人关涉楚辞文献形成初期的编纂情形,通过对文本篇目、次序、语句单元、异文的比对校勘,去探讨作为累积性文本其内部的构成过程。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要勘定传世文献特别是先秦文献的真实性,实要参考三个维度,即文献的流传历史、语言的使用情况和其内容是否与相应的历史状况相一致(10)[美]夏含夷:《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36页。。我们认为,在此之间涉及用字、用韵、语法结构、章法体式和整体风格等形式特征,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由此构成了经典诠释中的形式批评方法与视野。此是在现代《楚辞》研究中,特别是在《卜居》《渔父》研究中多偏重于形式上立论的主要原因。
二、 韵散形式与《楚辞》体式批评观念
《卜居》《渔父》之所以被怀疑非屈子所作,而为后人托言,最核心的论据在于此二篇为问答式的散体韵文,与《离骚》式严格用韵的“骚体”迥然不同。依据对“散体韵文”(即骈散结合的体式本质)体制形态所产生时代的认知,导致了对二篇产生年代和作者的直接质疑,如游国恩先生所总结的:
我们再试从文体上看来,也可以证明这两篇是假古董。屈原作品除了《天问》一篇保存着《诗经》的形式外,其余的全是所谓“骚体”诗。他们对于“三百篇”虽然是比较的解放了,但比较汉后辞赋(散体或俳体)却仍是很束缚的,因为它们的句法都已经确定了一定的长短和韵式。而《卜居》、《渔父》则不然,他们全是一种散文诗,句法既极其参差,用韵又很随便。(《渔父》一篇用韵更少。)比较“骚体”诗自然更解放的多,同时可以说是艺术上的进步。(11)见《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9页。
在这里,囿于时代局限,我们当然可对据艺术上所谓的“进步”观念,进而以《卜居》《渔父》比《离骚》更解放和更自由的论断持异议。但我们要分析的是游先生所作论断的基础,即是认为《卜居》《渔父》所代表的散体韵文不是屈子时代的产物。由此,在其文学史观中,从骚体到散体韵文再到汉代辞赋构成了一种完整的形式审美发展链条,且后者比前者更自由更解放。此种体式进化观念,贯彻于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影响巨大,成为一种主流性文学史形式观点。同样,胡适亦曾明确提出:“《卜居》《渔父》为有主名的著作,见解与技术都可代表一个楚辞进步已高的时期。”(12)胡适:《读楚辞》,见《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7页。马茂元同样认为,《卜居》《渔父》“作为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新的体裁,是‘不歌而诵’的汉赋的先导,是从《楚辞》演化为汉赋的过渡时期的产物”(13)马茂元等:《楚辞注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5页。。此种体制进化观念,均是从后来的文学作品与时代来逆推《卜居》《渔父》的形式价值,构建了一种从楚辞到楚辞变体再到散文用韵的形式发展闭环。聂石樵在其《先秦两汉文学史》中则取一种中和的立场,一方面认同于郭沫若的否定观点,以为《卜居》《渔父》虽为后人所作,但“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另一方面又通过古韵的比较,裁定《卜居》《渔父》为先秦作品(14)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见《聂石樵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24页。。归根到底,此种观念实以为第三人称的对话问答体即决定了此不是屈原作品,但又通过文本的用韵和同时期的互文本,以为这样的文本可出现在屈原时期。
当然上述认识是对古代《楚辞》研究的一种继承,如李贺言“《卜居》为骚之变体,辞复宏放而法甚奇崛”,王世贞则曰“今人以赋作有韵之文,为《阿房》《赤壁》累固耳。然长卿《子虚》已极漫衍,《卜居》《渔父》实开其端”(15)同见[明]蒋之翘评校:《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五,见吴平、回达强主编:《楚辞文献集成》第二十三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16176页。,二人均将《卜居》《渔父》看作赋辞文体的发源之所在,当然他们并不质疑二篇非屈原所作。此种发展观念,可谓是自《文心雕龙·诠赋》以来古代诗学最正统和主流的文体价值观念。亦即是说诸多现代学者虽多认为《卜居》《渔父》乃至《远游》《九章》不为屈原所作,但在文体审美上,却多承继了诸多古人的观念。从形式分析的角度而言,这可以说是对古代形式批评传统的一种隐在的传承,尽管上述诸位学者多不认同古人用“以意逆志”的方式确认二篇的作者,但在语言风格、赋体形态、文法结构上却潜在地认同古人的观念。
姜亮夫、陈子展二先生则独取古人之意,以为二篇实为屈原所作。同样是对此二篇散体用韵的确认,陈子展先生则以为《卜居》《渔父》的散体韵文形态恰恰是战国文体的最普遍形态,此是一种在共时性指向上文体形态的确立。从文体渊源上讲,陈子展先生引章学诚、刘师培等人之论,以为《卜居》《渔父》与同时期的《庄子》《孟子》《战国策》等文体形态相比:
无一不可以看出屈宋辞赋中的问答体裁,修辞方法,和他们的学派相通。而且它们的艺术成熟之处,或有在屈宋辞赋之上者。即说屈宋出于纵横家,看来并没有是什么不可。何况在屈宋之时,《老子》和《周易·象辞》以及《文言》、《系辞》的一部分,那种散体韵文的成就,已经很高。(16)陈子展:《楚辞直解》,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78页。
亦即是说,如若我们放在历史情境中,散体韵文形式在当时的产生是可能和必然的,并不存在从骚体到《卜居》《渔父》再到汉赋的纵向时间进程,这只不过是一种虚构的形式“进化”线索。如赵奎夫所言:“屈赋中的各种句式和几种主要的诗体形式在屈原之前就已经存在”(17)赵奎夫:《屈骚探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36页。;林庚则更是以为:“《楚辞》的体裁是战国时期诗歌的新形式”(18)林庚:《九歌不源于二南》,见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5页。,这种新形式产生的依据正是此时勃发的诸子散文。从历史主义角度而言,并不能简单以后人见到的屈赋为此一诗体和句式的突然生发点,它必然是有着历史的孕育和渐变的过程。
三、 主客问答与设问体式批评
《卜居》《渔父》与《离骚》《九章》《九歌》不同,其以屈子与太卜郑詹伊、渔父的对话和问答为体式,其文皆以“屈原既放三年”、“屈原既放”第三人称叙述为开端。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曾把赋的结构方法分为两类:“一为直叙体,一为设问体”(19)[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发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8页。,进而把《卜居》《渔父》与宋玉赋作为设问体的代表。此种设问体式,尤为怀疑论者所以为《卜居》《渔父》是后世之人所叙述而成。如清人顾天成不同意汉代王逸及宋代朱熹所作“襄王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复作《九歌》《天问》《远游》《卜居》《渔父》等篇”(20)[宋]朱熹:《楚辞集注·离骚经第一》,见《楚辞文献集成》第三册,第1749页。的旧说,在《读骚列论》中引申曰:
《卜居》一篇固非秦以下手笔,盖战国人问其事而为之者。文虽斐娓,意实浅陋。……予所以断其为伪者,则以起数语。以为放于怀耶?则怀未尝有放之三年不得复见之事。以为放于襄耶?则原自甘退闲,无智可竭无中可尽,何所有冀于见,而心烦虑乱,不知所此从也。考其时,度其势,无当。故疑之。(21)见《楚辞文献集成》第二十五册,第17705页。
这是从语义上判读此种问答体式的时代,而清人崔述则以为主客问答形式而确定此二篇非为屈原所作:
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词》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遗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甚耶!(22)[清]崔述:《考古续说》卷一,见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41页。
现代学者则多依上述清人怀疑之论,在此形式体制发展向度上,怀疑此为屈原之后世人所作无疑。如廖平以为楚辞数十篇中,“惟《卜居》《渔父》二篇中有屈子名姓,故曰后人遂以为屈子作《楚词》”(23)廖平:《楚辞讲义》,见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8页。,当然他认为包括《卜居》《渔父》在内的“楚词”实为秦博士所作。前述游国恩先生立论基础即在于从此种问答体式出发,以《卜居》《渔父》必为后人伪托成文,非屈原所作。刘永济先生亦以为“卜居、渔父二篇,明是他人叙述之文,非屈子自作”(24)刘永济:《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页。,在其《屈赋通笺》中直接忽略不入其笺释范围。又如王泗原先生亦以为:“卜居渔父那种设为屈原与人问答之辞,又称屈原姓与字,也不合是屈原自作。”(25)王泗原:《楚辞校释》自序,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页。
而坚持认为《卜居》《渔父》为屈原所作者,亦是从此体式角度说明此二篇是屈原所作。因在庄、屈的时代,作者自可假讬成文以第三者的语气而做问答体,此正是同时代的文学描写手法。实际上,后世赋多以此问答形式为赋之体制,而《卜居》《渔父》为其开端,古人多不怀疑屈原可以做此问答体或寓言式对话。古代最有代表性的肯定观点,为洪迈《容斋五笔》中所言:
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杨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两京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太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26)[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04页。
洪迈所论,为徐师曾《文体明辨》所引,特别标明了屈原问答体之于后世辞赋乃至后世诗歌创作的巨大影响。章学诚则言“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27)[清]章学诚:《诗教上》,见[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6页。,由此他以为汉代司马相如的《客难赋》与扬雄的《解嘲》二赋,不过即是承继战国时期中《卜居》《渔父》的问答体和《庄子》中庄周与惠子的辩论体式。此均指出了《卜居》《渔父》作为战国时的文体形态,与诸子散文的同时代性。
不管是如何确定《卜居》《渔父》的作者真伪,即使是前引清人之论以及后世现代学者之说,都特别指出了此种问答体之于中国文学史的重大意义。如郑振铎就由洪迈之论,引申言:
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文学里的名为“词赋”的一个“文体”是在屈原影响之下而发展的。一部“词赋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受屈原影响的一类特种作品的历史。(28)郑振铎:《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见《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30页。
而实际上,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出土文献,更是在地下材料意义上推翻了诸多清人以主客问答形式不可为屈原时代所有,《卜居》《渔父》绝非屈原所作的结论,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陈子展先生的推证。从卜筮的角度而言,更有当代学者提出“简帛文献确实为《离骚》提供了一个切实可信的、可以互相取证的、占卜文化的背景”(29)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页。。除陈子展先生所引用的马王堆帛书中所存主客对答形式外,1972年银雀山汉简出土的二十多枚辞赋类竹简,对于解决诸多楚辞中如唐勒、宋玉赋的真伪问题亦提供了考古学上的支持与佐证。正如有学者所言“它们对于解决《卜居》、《渔父》可否是屈原所作,其实具有同样的价值。……既然这种文体能够出现在宋玉时代,稍前不久的屈原为什么不可以也用这些文体进行写作呢?”(30)廖群编:《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年,第240页。扩而及之,诸多出土文献的出现,对补充、证实或改写从诗到楚辞的文体发展的诸多历史不确定性亦有着重大的意义,如青木正儿所以为“赋诗的终熄与‘楚辞’的兴起之间,找不到因果关系”(31)[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发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2页。的结论,显然很难再立得住脚。
在艺术创作手法上,除设问体式外,屈赋所广泛采用的设喻法,更是关联艺术本质的形式问题。姜亮夫先生曾将屈赋的表现手法分为两类:一是包括《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的十三篇,以设喻之辞为多;一是不用设喻的《九歌》,则是直状事物,因其为民间之狂乐。虽然他并不否定《九歌》直陈情感的价值,但他特别指出上述十三篇中所用的设喻之法,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因“十三篇委曲以求全,婉而多讽,故以隐喻为贵。”(32)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见《姜亮夫全集·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此种对隐喻作为文学本质的强调,显然来自于对西方文学传统、特别是对西方现代美学观念的体察。当然此种设喻法,又关涉于古代诗歌的“兴体”本质,以“芳草”“美人”而托事于物和托物起兴,正是构成楚辞文章之美的艺术本质所在。如蒋天枢先生所言,屈原用古诗“兴”体来托喻隐晦的情感,“其所讬事类之繁赜,物态之纷纭,于以构成屈文‘采’之主要成分”(33)蒋天枢:《楚辞新注导论》,见蒋天枢:《楚辞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页。。此种中西文学与文论的比较视野,显然是现代《楚辞》研究与古代《楚辞》研究的区分之所在。
四、 “法语之言”与句法批评观念
姜亮夫先生在《〈远游〉为屈子作品定疑》一文中,除分析《远游》主题与屈原思想一致外,更是详细分析了《远游》与其他屈赋在文风、语法和音韵规律上的一致性。依托于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言学理论,他对《远游》文本进行了详尽的文本细读,由此得以确定《远游》为屈原所作。在此研究范式背后,实即蕴含着丰富的形式批评理论意识,如其言“作文集字法以成句、集句法以成篇,仔细观察作者用字、修辞、造句直至行文布局的素习,往往可以帮助判断作品的真伪。”(34)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见《姜亮夫全集·八》,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7页。由此可见,与思想分析和文化批评相比,对字法、句法和章法的形式分析恰是文本考证最可靠和最具说服力的一种维度。对于流传复杂的中国上古文献来说,形式批评不啻是一种最真实可靠的考据基础。此种以文本和风格为核心的形式理论观念,除受西方科学考证主义的影响,最主要的还是基于屈原生平的复杂隐晦和《楚辞》版本的歧异纷繁,此是研究对象本身决定着研究方法的展开。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据句法判断语意及词义的疑难,是研究古语文特别重要的方法”,甚至“必须究明句法,然后训诂之用才落实”(35)王泗原:《古语文例释(修订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页。,王泗原先生以此为现代语言学超越古代训诂学之所在,故句法批评自是先秦文本考证的中心方式。
落实到古今《卜居》《渔父》二篇的研究上,通过句法、字法和用韵法来确定作者真伪,更是一种内在的有效理路。顾炎武引孔子之言,曰:“《卜居》、《渔父》,‘法语之言’也;《离骚》、《九歌》,‘放言’也。”(36)[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81页。将《卜居》《渔父》与《离骚》《九歌》并置,认为两类文本在写作意义、道德立场上有对比,虽是从文意出发做出的论断,但却很好地点出了二者之间语言风格之差异。明人黄文焕曾高度赞扬《卜居》句法章法的文学史意义,以为《卜居》既有“段段句法匀停”处,更能“破整齐为参差”,极尽章法内寓参差于整齐之变幻,更以为《渔父》章法有寓方于圆之意味。故黄文焕从章法句法出发,言屈赋既有如长篇《离骚》“艳丽益以增美”,又有如短篇《卜居》《渔父》者“清空亦足呈奇”之美,继而提出屈赋的这两大类风格足可见屈原“以章法善变为赋心”的结构创造(37)[明]黄文焕:《楚辞听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16页。。
而两类屈赋句法之不同,实来自于用词造句细处上的差异。或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考察《左传》和《国语》同作为先秦文献的真实性时所言,除了用字习惯和文法组织上的一致性外,“《左传》助辞的特殊组织,是它的真伪问题的最后且最好的证据”。(38)[瑞典]高本汉:《左传真伪考及其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1页。同理在楚辞文本真实性的考辨中,更为典型的是,《离骚》《九歌》中多用“兮”作语助之词,形成了骚体诗最典型的语法风格。而《卜居》《渔父》则不用“兮”字,《卜居》在句末用“乎”字,《渔父》除文末渔父所唱“沧浪歌”中用“兮”字外,句末反问语气时亦用“乎”字。显然语助词或虚词的用法实是句法判断的核心特征,故此种句末语助词的不同,实关涉对此二篇时代及其渊源的确定。故如闻一多所总结的:“从《楚辞》‘兮’字用法的考察说,对作品时代的考订,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可作为估订作品价值的标准。”(39)见闻一多:《闻一多西南联大授课录》,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85页。实际上古人也早已指出“诗人用助词,多用韵在其上”(40)[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见《历代文话》,第1596页。的语法规律,而在此助词体例上,《卜居》《渔父》与《离骚》显然分属不同的表达体例和用韵系统。郭沫若更是引清人孔广森之论,以为“‘兮’字在古时北方的文字中每每用‘乎’字来代替”(41)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36页。,并以为此种语助词都是当时的口音或白话。
宋人祝尧《古赋辨体》中曾言《卜居》《渔父》句末用“乎”字,“即荀卿诸赋句末‘者邪’、‘者与’等字之体。”(42)[宋]祝尧:《古赋辩体》,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三六六册·集部·三○五·总集类》,第739页。明人蒋之翘评校《七十二家评楚辞》中则言:“《卜居》句末用‘乎’字,‘乎’字上必叶韵成文。《渔父》则逐段摹写有《国策》风,此乃传记体也,赋家安得误认之而效其法乎?”(43)[明]蒋之翘评校:《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五,见《楚辞文献集成》第二十三册,第16179页。游国恩等人正是由此语法差异来确定《卜居》《渔父》与《离骚》正为不同时代的作品,且代表着从楚骚到汉赋文体发展历史中的过渡阶段。而姜亮夫、陈子展二先生则以为屈子和荀子相距不远,此二种之间的用字和句法理应在同一时代。
撇开上述两种不同的立场,在现代语言学的视野中,语助词的不同使用方法确实代表着古代语言形制和美感发展的历史性进程。如闻一多就认为“兮”字用法的减少,代表着诗与散文体审美形态的不同:
按诗的语言与散文的语言之差异,在文句之有无弹性。虚字减少则弹性增加,可是弹性增加以后,则文句意义的迷离性、游移性也随之增加。(44)见闻一多:《闻一多西南联大授课录》,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85页。
郭绍虞先生在《释“兮”》一文中,认为“兮”字的文法意义有三个阶段,即从作为发声词、收声词或语间词阶到成为语气助词阶段,再到可转为其他语气词三个阶段(45)见郭绍虞:《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318、316页。。从《诗经》中的“兮”字到《离骚》中的“兮”字用法,代表着语言组织日趋严密的历史进程。当然他并不认为可以简单凭借个别字词来确定文体先后次序,其言:
语言的演变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所以对于古时文艺语言语义的推求,也不能通过简单的方法作单纯的理解。有文法的关系,有词汇的关系,更有修辞的关系;而在文法中,有构词法的关系,有造句法的关系,至词义的引申转化又有从实到虚或从虚到实的不同。(《试论汉语助词和一般虚词的关系》)(46)见郭绍虞:《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318、316页。
另外,除“兮”字外,像《离骚》中的“也”字、《招魂》中的“些”字(47)[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一引《蔡宽夫诗话》曰:“楚人发语之辞曰羌曰蹇,平语之辞曰些。”蒋礼鸿先生认为“平语之辞,谓语已词也。”(蒋礼鸿:《词义释林》,见《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4页。)、《大招》中的“只”字,在屈赋句法中都承担特殊的用法和丰富的含义,是屈赋文本的核心句法特征。郭沫若、汤炳正等均认为这些代表“骚体”诗的特殊用词,大多是来自于楚国当时的方言,代表着楚辞的语言风格。正如汤炳正先生所总结的:
屈赋的特征,确实是充分利用了人民生活歌唱或吟诵时的尾声“兮”字,以加强诗歌的感情作用和音律色彩。这是屈子适应诗歌内容的需要而在形式上的伟大继承与创造。(48)汤炳正:《屈赋与荀赋》,见汤炳正:《楚辞类稿》,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77页。
他还由此出发,推翻了以《诗经》为北方诗歌形式、屈骚为南方诗歌形式的成见,更指出古今学界常以为的骚体乃《诗经》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实是一种错误的观念(49)见汤炳正:《渊研楼屈学论稿》,北京:华龄出版社,2013年,第126页。。可见对“兮”字的语法批评,实关涉对屈赋形式的本质性认识。当然更有日本学者竹治贞夫,从“兮”在屈赋中的不同位置出发,确立楚辞可分为三种诗体类型,分别为:“兮”字在奇数句末的《离骚》型;“兮”字在偶数句末的《橘颂》型;“兮”字在句中的《九歌》型(50)[日]竹治贞夫:《楚辞研究》,见尹锡康、周发祥等编:《楚辞研究集成·楚辞资料海外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1页。。基于“兮”字的位置和句法用字,竹治贞夫从结构分析的角度提出屈赋中的抒情作品内部大多可分为本文与“乱”(或“重”)两部分,而两部分的诗型往往是不同的,并由此认为屈赋的章法特质是一种“二段式结构”。此种类似于巴赫金所言小说中的“复调式”结构特征,对于认识古代文学作品的功能和特征,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具体的语句疏校正中,现代的句法批评和文本互证往往起着核心作用,如闻一多指出《渔父》中的“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中,应据他本删“而”字,因其应与上文“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句法上保持一致(51)闻一多:《楚辞校补》,见《闻一多全集》第三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第103页。。同理,根据句法关系亦可确定字之衍异,王泗原就认为洪兴祖《楚辞补注》(汲古阁本)中“物之汶汶者”应与“身之察察”相对,故“者”字应为衍字。(52)王泗原:《楚辞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08页。他还通过比较《卜居》“世浑浊而不清”段、贾谊《吊屈原赋》“时不详”段和刘向《新序》“五默默”段三者的章法,指出文选五臣注“默默”为“嘿嘿,不言貌”的错误,以为其中的“默默”的含义应是形容世之浑浊不清,而不是沉默不言貌。进而得出,在古语文中作为单字的“默”和作为叠字的“默默”,实因叠音而生新义,不应以原单字来疏解。(53)王泗原:《古语文例释(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8页。此正是通过章法、句法来厘定词语涵义的现代语言研究范式,而其中的主要方法即是通过较近时期的互文本比较,在从整体意义上来决定个别词语的意义。又如在疏通词义上,《卜居》中“瓦釜雷鸣”句,王逸注曰“群言获进,一云愚让讼也”,《文选》五臣注曰“瓦釜喻庸下之人,雷鸣者惊众也”,姜亮夫先生以为古人注并不准确,在《楚辞通故》“瓦釜”条中,除以引古代器具形制加以说明外,他还特别指出“瓦釜雷鸣”与“黄钟毁弃”为对文,一为民间日用器,一为贵族乐器,故其语意应为:“瓦釜本为无声之物,不以为乐,而贫者或以之节舞者也。此用舍之不清,所谓溷浊之一也。”(54)姜亮夫:《楚辞通故》,见《姜亮夫全集·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9页。此为“对文”形式在疏通语义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是传统训诂学方法的一种现代性转换。
蒋天枢先生亦认同上述文本诠释的角度,他以为《楚辞》研究需要有两个视野:一是要把作品放到其所在的历史中去理解;二是“需从全部作品来研究局部;从和作者时代接近的著作中来研究作者身世”(55)蒋天枢:《楚辞校释·叙》,见蒋天枢:《楚辞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页。。其中第二点实际指出了要从文本和互文本的整体中理解语辞及其意义,此正是一种形式批评的理论视野。这种将文体研究与语言研究相结合,不脱语用环境而进行文艺研究的视角,正与西方圣经诠释学中的形式批评流派和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新形式美学趋向遥相呼应。换言之,西方的经典诠释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方法和研究视野,实早已内涵于现代《楚辞》学研究实践中,故值得当今重回经典和文本细读的理论主张所继承和发展。当然我们并不是赞同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或英美新批评等所彰显的“文本主义”或“文本中心主义”,而是说上述现代《楚辞》研究实践正说明了那些拒绝涉及“文本”和“文本性”的研究并不能解决任何文学与文化研究上的问题,或如西方学者所言:“如果我不去面对那些围绕文本概念产生的问题,我们将会受限于自己已有的那些未经检验的猜想,而文本的问题总是与我们同在。”(56)[美]乔纳森·卡勒:《理论中的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6页。
综上所述,在我们梳理二十世纪《楚辞》研究中关涉《卜居》《渔父》真伪问题的理论观念时,可清晰地发现吸收了西方美学观念的形式批评理论与视野之于《楚辞》研究的重要性。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二十世纪的楚辞研究,就是在这种执着民族文化传统又广为吸纳西学观念的时代风气下起步的。”(57)周建忠:《中国近现代楚辞学史纲》,见周建忠:《楚辞考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7页。在此其中,形式批评理论代表着现代文学审美观念对于《楚辞》文学审美性、想象性的重新挖掘和重视,表征着“五四”以来摆脱传统道德批评而重视形式审美的研究指向。刘永济先生在反思屈原研究方法时,亦总结屈赋研究的理论范式为义理、考据、辞章三途,并以为:义理之学为哲学探讨,可对应为“宋学”;考据训诂为博考名物,可对应于“汉学”;而辞章之学,“讲求文律,工为篇章”,可对应于“文学”(58)刘永济:《屈赋研究方法之商榷》,见刘永济:《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5页。。在其方法论意识中,我们尤需明白其对古代道德批评、历史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区分和融汇,而且他尤重视在 “文” (作品之篇章字句)、“辞”(谋篇、造句、用字)、“志”(作者思想感情)三者关系中“辞”的重要性,以为“‘辞’为‘文’与‘志’之中介”、“‘文’必准‘辞’以敷设,‘志’亦藉‘辞’而显示。”(54)刘永济:《屈赋研究方法之商榷》,见刘永济:《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4页。而此种文学本位立场,或可显示其对西方形式主义美学和新批评理论的吸收,并以文本细读和形式分析为道德批评、文化批评和政治批评的前提和基础,亦可谓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楚辞》研究中最为内在的和有效的理论批评方式。